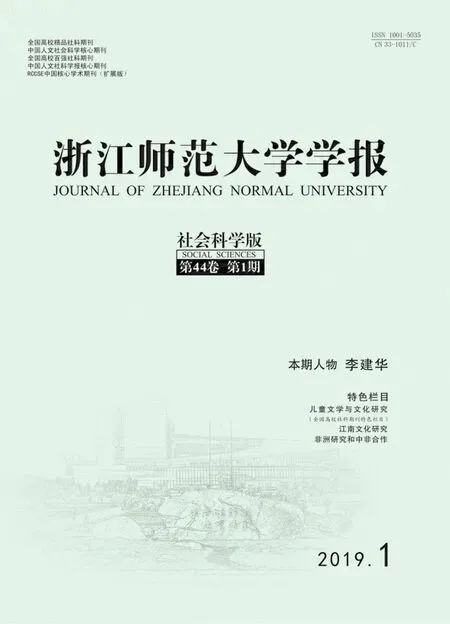论约翰·怀德曼作品的沉默书写 *
2019-01-30张琼
张 琼
(江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约翰·埃德加·怀德曼(John Edgar Wideman,1941—)是美国当代著名的非裔作家和评论家,被评论界誉为“黑人版的福克纳、贫民版的莎士比亚”。[1]他迄今撰写并出版了十部长篇小说和五部短篇小说集,与他的小说相比,其文论虽然为数不多,但其影响力却毫不逊色。他的文论与小说创作相互关联、相互指导,并形成独特的文学视角。在长达五十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沉默(Silence)一直是他作品的关注对象和创作手法。
事实上,怀德曼作品中的沉默已经引起美国学界的关注。他的《霍姆伍德三部曲》出版后,杰奎琳·贝尔本(Jacqueline Berben)就注意到他小说的话语之外更具有言说力,其形式除了手势、歌声和感应式思维外,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便是沉默。[2]对怀德曼作品中沉默叙事的深入研究始于伊夫查尔斯·格朗雅(Yves-Charles Graendjet),他意识到怀德曼的小说中有很多令人眩晕的停顿,这样的停顿实质是沉默言说的一种形式,且这样的沉默言说构成了怀德曼文本的共同基础,并指出“怀德曼的小说持续地扩展了沉默的意义和价值”。[3]此外,克劳德·朱利恩(Claude Julien)认为,在怀德曼的短篇小说《自由女神》中,“那两个白人女性使沉默的黑人男性声音具体化,从而把整个文本变成欺骗的比喻”。[4]这三篇评论折射出怀德曼作品中的沉默是他创作的突出特征,但这些研究更多的是从叙事学角度进行关注,缺少了历史及文化维度的考量。对于他作品尤为突出的特征,国内未有该方面的研究未免有些遗憾,因此,本文将结合他沉默书写的时代背景探究他作品中沉默的丰富文化和伦理内涵。
一、沉默书写的背景
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领域的黑人权力运动与意识形态领域的黑人文化艺术运动相互呼应,形成了一股黑人反对种族主义和争取权益的洪流。在黑人组织的领导下,黑人民众纷纷主张“以暴制暴”和“黑人权力”,同时城市暴乱也此起彼伏。大批非裔作家即文艺战士积极响应黑人权力运动的主张,在作品中为其呐喊助威,其中以阿米里·巴拉卡、约翰·威廉姆斯为典型代表。正值创作初期的怀德曼以局内人的身份站在局外保持沉默,凝视了那场轰轰烈烈的黑人权力运动和黑人艺术运动。其原因是他不赞同黑人权力运动的激进性,更不认同以牺牲作品的文学性而成为战斗武器的黑人艺术运动。后来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接受采访回顾黑人艺术运动时道出了实质:“60年代,一些活动被承认和选定——也就是说,得到了宣传,得到了公众的注意——很多东西已经丢失了。就如此时此刻那些‘举足轻重’的作家是因为很多原因变得很重要,而不是因为他们是最好的作家。”[5]同时,他也没有对其进行批评或抨击而选择保持沉默,是因为批评或抨击本身就是对一种理论或学派的支持,使它成为学界和社会瞩目的中心。可以说,沉默是反抗姿态的另类表达,同时,怀德曼把这种姿态化为文学视角和创作手法融入自己的创作中,并形成独特思想。
同时,怀德曼开始创作的时期刚好处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过渡时期,后现代主义试图摆脱一切传统模式的束缚,否定权威,否定中心,提倡多元化,且沉默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趋势和否定策略。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暨后现代主义的开创者之一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在《批评的前沿:沉默的隐喻》(TheFrontiersofCriticism:MetaphorsofSilence, 1970)中指出,当代文学的趋势是反对自身和渴望沉默,且沉默作为一种隐喻,是“对文学自身观念和西方社会的质疑”。不久,哈桑在《肢解俄尔普斯:走向后现代文学》(TheDismembermentofOrpheusTowardAPostmodernLiterature,1971)一书中利用古希腊神话俄尔普斯的故事形象地揭示当代文学的特征是沉默,就像虽然俄尔普斯被肢解,但“仍在‘没有琴弦的七弦竖琴’上继续歌唱,在毁灭和创造中继续前行”。[6]怀德曼正是在这一趋势和潮流中采用沉默这一解构语言的方式质疑种族主义及西方社会,在反叛传统文学的同时保持作品的文学性,让作品的文学性和思想性并存。
怀德曼不仅在小说创作上融入了后现代主义的沉默血液,还专门写了文论《塞隆尼斯·蒙克的沉默》(“The Silence of Thelonious Monk”,1997)和《赞美沉默》(“In Praise of Silence”,1998)阐释了他对于沉默的深刻思考。事实上,怀德曼不仅把沉默置于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潮中进行实践,而且将其置于美国黑人民族特殊的历史和符号背景下,使沉默更具有深刻的文化和伦理涵义。
二、“历史语境化”:被动沉默与生存哲学
怀德曼在美国学界素来是一位以“严肃”[7]著称的作家。他的严肃性表现在对于社会问题的敏锐洞察、对于民族问题的深邃思考和对于作品语言的客观表述,其中不乏对于沉默的关注和运用,因为沉默中蕴涵的是深沉的情感和历史的厚重感。事实上,怀德曼对沉默的关注和表现是基于对美国非裔民族历史的了解从非裔民族经历中汲取而来的。
美国非裔民族的沉默是特定历史阶段和环境的产物,在非洲奴隶到达美洲之初,沉默以客体的心理模式而存在,这样的沉默成为胆怯和绝望的外在形式和掩盖面具。怀德曼在其经典文论《赞美沉默》中揭示了先辈们沉默形成的历史动因及心理模式:“想象一下你自己结束了一段漫长且折磨的痛苦之旅后,在一个陌生的海岸登陆,你不确定自己是否可以活下来。你生病了,变得虚弱,严重迷失方向。你担心并没有到达某个地方而是滑进了噩梦的另一面。”[8]642显然,美国非裔民族的沉默可以追溯到奴隶制的形成时期,在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当非洲黑奴在无助中找不到任何一丝希望时,他们只能在沉默中忐忑地接受白人对他们命运的主宰,胆怯、绝望和惊愕的心理跃然纸上,这是沉默中美国非裔民族心理的呈现,也是怀德曼将沉默进行“历史语境化”的策略之一。
将沉默进行 “历史语境化”除了追溯先辈被贩卖的历史,还包括还原非裔的日常生活常态和普通非裔大众抗争的历史图景,尤其是被动沉默的历史。美国著名艺术家帕特里夏·邓肯(Patricia Duncan)在其专著《讲述沉默:亚裔美国女性作家和言说的政治》(TellThisSilence:AsianAmericanWomenWritersandthePoliticsofSpeech, 2004)中将沉默区分为主动沉默和被动沉默,认为被动沉默是外力作用的结果,尤其是种族歧视的作用,但也参与了历史话语的建构。[9]具体到美国非裔民族,其被动沉默是奴隶制和种族歧视外力作用的结果,且在长期的生活中逐渐内化为他们的生活方式。
怀德曼在小说中塑造了一批被迫沉默和被压制的他者,并揭露了被动沉默形成机制中的暴力因素。《私刑者》(TheLynchers, 1973)从反面揭示美国非裔民族一旦发声便被压制和残害的社会现实,从而迫使非裔民族一直处于沉默的生活状态。为了彰显对白人的反抗姿态,霍尔和其他三位黑人青年计划私刑处死一位白人警察。霍尔受过一定的教育且有很好的演讲才能,当他为了建立良好的群众基础在一所中学进行慷慨激昂的演讲时,被警察发现而遭受暴打,最后被抓进精神病院。这是白人种族主义者用血的事实告诫当代美国非裔民族:只有继续继承父辈的沉默传统和品格,继续把沉默内化为日常行为方式,才能免于受伤害。同样,小说《鲁本》(Reuben,1987)中的鲁本是代表非裔群体发声的律师,他在大学公寓当清洁工时利用白人学生的课本和笔记自学了法律,后来在社区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为非裔穷人提供法律援助,但最终警察以没有律师资格为由逮捕了他。对于处于从属地位的美国非裔群体来说,任何争取自己权利的发声都是不被允许的,只有使自己处于沉默的状态才会有基本的生存权。可以看到,沉默的“历史语境化”揭示了非裔群体沉默形成中所遭受的暴力,如 “镣铐”“鞭打”“监狱”“歧视”[8]641等。根据福柯的观点,身体是权力实施的重要场所,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人的身体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决定着权力的分配。在此,白人种族主义者通过暴力来规训非裔民族的身体,从而建立起压迫机制,试图把非裔永远禁锢在被否定、被排斥和被拒绝的边缘,不断巩固中心和边缘的二元模式。因此,非裔通过沉默在边缘回避中心的攻击,使得沉默具有防御性功能,因为沉默能让局外人保持镇静并产生一定的优越感从而使当事人减轻伤害或者免受伤害。正因为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群体以“不可见”的形态存在于社会之中。前辈作家拉尔夫·埃里森创作的《看不见的人》(TheInvisibleMen,1952)是权力压迫下非裔群体被迫沉默的最好例证。托尼·莫里森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典礼上的演讲中指出,“压抑语言比采取行为上的暴力更为有效”,[10]就这一意义而言,剥夺言说的权力在阉割权力、消解主体性上胜过任何一种刚性暴力,这也是美国非裔族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沉默的原因所在。
可以看到,非裔民族为了实现基本的生存权在白人的暴力规训中变得不想说也不敢说,无论是非裔的奴隶史、日常生活史还是普通大众的抗争史无不折射出美国非裔民族在奴隶制和种族歧视的蹂躏下的生存哲学。这样的沉默与族裔历史融为一体,不可分割。诚如怀德曼在论述沉默与历史的关系时指出的, “沉默是一位熟悉的老同伴。时间与沉默同在,沉默与时间同行”。[8]641也就是说,黑人的沉默扎根于民族的独特生存经历,形成于民族历史的土壤中。同时,沉默也参与了非裔民族历史的构建,展现了一个群体被阉割的痛苦,成为美国黑人民族历史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总之,怀德曼将沉默 “历史语境化”,揭示了美国黑人族裔被动沉默的形成机制,也呈现了沉默形成中的民族心理,同时也折射出这一群体在美国历史中所承受的压抑和苦难,参与了历史话语的建构。更确切地说,怀德曼以黑人族裔的沉默为视角巧妙且准确地反映了美国黑人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哲学,表达了其族裔关怀。
三、“符号语境化”:主动沉默与反抗策略
诚如诸多的传统批评,沉默的被“历史语境化”显示了沉默与言说之间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关系,也揭示了行为主体与客体之间压迫与被压迫的权力关系,这也是被动沉默的内核所在。然而,随着民族意识和主体性的提高,非裔选择以主动沉默来解构二元对立的沉默与言说的关系,并试图推翻压迫与被压迫的权力关系,使得沉默具有符号意义和言说功能。事实上,大批批评家深刻洞察了沉默作为符号的意义和言说功能。
关于沉默的符号属性,最为经典的阐释要数丹尼斯·科曾(Dannis Kurzon)。他在《沉默的话语》中提出了零或者沉默是语言符号并具有意义的理论:“我们应该把零或者沉默作为能指和作为所指区分开来。零是沉默的先驱, 因为一个明显的语言元素缺席, 而该缺席又与在场的语言元素形成对比, 这种缺席就是有意义的;这是沉默富有意义的表现。”[11]此外,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在其著作《眼和心》中明确了沉默的符号属性,即在一个符号系统中符号的缺失也是一种符号形式。从两位的观点可以看出,虽然沉默作为非语言实体的符号,只要能与周围的语言符号区分开来,沉默便能成为一种语言符号,且具有充分的言说功能。
此外,法国哲学家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明确提出沉默是“一种非实在、虚构的语言”。[12]而且,海德格尔认为文学语言呈现出的“沉默、无言和寂静”是在凸显语言本质自身,[13]他还强调了沉默的言说及表意功能:“一个人可以无休止地言说,但实际什么都没说;另一个人可以闭口沉默,却说出了很多。”[14]由此可以看出,沉默无疑是一种语言符号 ,甚至有时是一种文化符号,其意义由语境决定。
怀德曼在充分肯定沉默作为语言符号的言说功能基础上,让其语境化,同时赋予非裔民族的沉默更多文化内涵和积极意义。他在《塞隆尼斯·蒙克的沉默》中指出,“不说什么并不是不知道什么”。[15]554在此“不说什么”不再是先辈们到达美洲之初的被动沉默,少了惊愕和绝望,更多的是主动沉默,多了淡定和平和。正如福柯在《性经验史》中写道,“如同沉默一样,话语不是一劳永逸地服从于权力或反对它。……它加强权力,又损害权力,揭示权力,又削弱和阻碍权力。同样,沉默与隐秘庇护了权力,确立了它的禁忌”,[16]非裔民族的主动沉默是对权力的损害和削弱,是面对霸权和专制的无畏。可以说,非裔民族正是在淡定及平和的沉默中言说着美国虚伪民主下奴隶制和种族歧视的非人性。此外,怀德曼强调了沉默所具有的反抗性:“说什么呢,尼格鲁人?谁说我撤退到寂静处?撤退个屁!我是在另外一个方向进攻”,[15]557在此,作家一语中的地揭示了沉默符号的深层结构,即佯装妥协的同时其实质是在向种族压迫反击,对以种族主义为内核的社会体制进行反叛。
就具体策略而言,美国非裔民族试图在社会边缘凭借沉默从文化的角度来对抗强权。语言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很多词汇承载着明显的文化信息,反映社会文化生活,甚至每一种语言都对应某一特定的文化。同样,非裔民族的语言是非裔民族文化的载体,是非裔文化生活的反映。非裔民族的沉默在表面上是对白人强加给他们的语言的拒绝,在深层上是对白人文化的排斥和拒绝,这也使得沉默这一符号成为在文化层面反叛和攻击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武器。怀德曼在《赞美沉默》中如是表述:“在某些语境下,沉默是衡量抵抗力和张力的手段,沉默也是关于差异的激烈表达,这样的差异维持着使用语言和被语言使用的区别。这是历史,但今天并没有多大改变。几个世纪都没有消除被当作奴隶带到新大陆的非洲人和那些宣称拥有这片新大陆、拥有非洲人的身体和思想的那些人之间的原型差异。张力和反抗性是非洲后裔的行为特点,他们通过其行为与强加的语言和规则保持距离。”[8]642这样的表述充分肯定了美国非裔民族的沉默言说所具有的攻击性,蕴涵着抵抗力和张力。他无疑非常理解他的民族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进行反抗的目的,即继续保持其差异性,维持其黑人性。在非裔民族看来,白人的语言是强加给他们的语言,只要保持沉默就能与他们的语言和规则保持距离,才能保留族裔的黑人性,维持其族裔身份。因此,“我们中的一些人选择非常少的说话,或者干脆不说”。[8]642一个民族的语言对于维持文化身份的重要性可以在革命斗士弗朗兹·法侬的阐释中窥见一斑:“说话,就是能够运用某种句法,掌握这种或那种语言的词语,但尤其是承担一种文化,担负起一种文明。”[17]拒绝白人语言、选择沉默事实上是对自身族裔语言和文化的坚持,这就使他们把沉默符号的所指拓展到对于非洲文化和文明的坚守。基于此,怀德曼揭示了美国黑人英语的形成机制,即“很多的习得和非习得就在沉默中发生”,[8]642“在沉默中发生”即为对自身语言和文化的坚守,可以说美国黑人英语是非裔对强势文化排斥和同化的结果,同时也暗含了对强势文化的否定和抗议。
怀德曼把他关于沉默符号具有言说功能和表意策略的这一诗学理念运用于小说创作,在短篇小说《天蛇》(Damballah)中,奥里安这一角色集中体现了非裔民族的沉默言说所具有的攻击力。奥里安到达美洲后浑身都充满了不适感,选择主动沉默,决定“再也不说那些决定要杀他的白人的话语了。[18]12而且,他的沉默言说具有令奴隶主都害怕的攻击力,就如奴隶主在给奴隶贩子的信中写道,“从他刚来到现在,一个英语单词都没从他嘴里划过。关于他的易驯服性和易管教性,我仅仅看到他很乐意暴露着牛皮一样的背接受一顿顿的皮鞭,这是他持续的不当行为替他赚得的”。[18]16在此,怀德曼揭示了美国非裔以沉默对抗种族歧视和文化霸权的事实,再次证明了沉默符号作为抵抗策略所具有的文化属性。
四、“伦理语境化”:作为物质载体的沉默
有学者在分析沉默的符号意义时指出,“死亡意味着沉默的终极表现,是该符号的终极意义,是无言反抗权力的最终目标,也是话语流动的最后终结,更是摆脱控制的终极自由”。[19]从一般意义来看,这样的探析是有道理的,但对于非裔这个有着特殊经历的民族,怀德曼注意到并非死亡是沉默的终极表现和符号的终极意义。他将非裔民族的沉默“伦理语境化”,认为伦理理想才是沉默的终极表现和符号的终极意义。
从哲学层面看,美国非裔民族强调了沉默的物质性和真实性,沉默是事物的言说媒介和方式,是相关事物的一部分。诚如被动沉默参与了历史的建构,是非裔历史的组成部分,怀德曼强调了沉默的物质性和真实性,把沉默看成了一种载体,具体而言,非裔民族的沉默是民族伦理理想的载体。在他看来,无论是非裔的被动沉默还是主动沉默都是暂时等待,都是作为物质载体承载了整个民族对于伦理理想的追求。他对美国非裔的历史进行了精准的概况,即“等待的历史”:非裔民族从约旦河开始等,等到非洲的西岸,最后等到了美洲大陆。非裔选择沉默只是暂时的回避正面冲突并不是放弃,而非裔民族在沉默中真正蕴涵或者想要表达的,是“等待奴隶制和种族歧视的终结,等待作为一等公民的正义和尊重,等待监狱的大门打开,等待城市医院的紧急病房和门诊的病人能够永生”。[8]641由此可以看出,这四个“等待”折射出美国非裔民族理想伦理的图景和期待,前两个“等待”是对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民主理想的追求,这是他们四百年来几代人为之奋斗的目标;后两个“等待”是对和谐友爱理想社会的期许,这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基于此,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及和谐友爱的伦理理想就赋予了沉默终极意义和最终目标,同时也是非裔民族在沉默中获得的话语终结和终极自由。
此外,怀德曼辩证思考了沉默、等待和伦理理想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认为沉默是非裔民族愿望和梦想的载体,而等待是沉默的外在表现形式,且沉默成为现实苦难和民族理想的联结纽带,同时也是历史和未来的过渡地段。他在《赞美沉默》中如此写道:“沉默伴随着等待,等待贯穿了被迫沉默的整个时代。当无尽的等待继续的时候沉默是愿望被雕刻的地基,沉默是所有等待的事物都可以想象的梦想空间,若是等待的事物没有到来,梦想破灭的空间又再次溶解成沉默。梦想萌芽又破灭,然后又在沉默的子宫里萌芽。沉默虽然时时被失望和等待玷污着,但仍然也是希望的蓄水池。”[8]641-642从这段表述可以看出,对于非裔民族而言,没有任何一种方式在揭示美国种族制度的荒唐和非裔民族的屈辱方面能跟他们的沉默相提并论;同时沉默作为物质载体成为美国非裔的迦南之地,寄托了他们所有的梦想和希望。怀德曼非常清楚伦理理想实现的艰巨性,但他相信无论经历多少挫折和失望,但沉默总归最后会成为“希望的蓄水池”,这充分反映了非裔民族坚韧不拔的精神,同时也颂扬了他们作为弱势族群在极端的逆境中仍保持乐观主义精神的超然生活态度。
伦理理想源于对现实的强烈不满,也源于对现实的反叛,怀德曼的写作中随处弥漫着对现实的强烈抨击,这是他关于“写作就是搏击”理念的践行。然而,怀德曼对民族伦理理想的实现自始至终都渗透着人性的理念,从而也赋予了沉默人性和道德的光辉。事实上,怀德曼曾被问及如何评价充斥着暴力的黑人权力运动时,他坦率地说道,“有些东西错了”,“争取和平和独立的斗争变得越来越热……我感觉被威胁,被狠狠地威胁了,不仅仅我个人感到威胁,还包括整个群体”。[20]从他的表述可以看出,无论何时他都认为激烈的斗争和冲突不能实现民族理想,“以暴制暴”不能解决美国的种族问题。因此,他把希望寄托在“等待”中,因为“等待”无论如何最终总会化为希望。他鼓励非裔民族应该拥有更多的耐性和乐观,在沉默中等待白人人性的复苏和道德的回归,因为等待即为沉默也是一种反抗策略,他确信这一定会实现。在讲述自己家族起源的短篇小说《霍姆伍德的起源》(TheBeginningofHomewood)中,怀德曼用祖辈西伯拉·欧文斯的故事证明了这一点。19世纪40年代出生的西伯拉是位黑奴,她经过无尽的等待拥有了奴隶主的儿子为丈夫,也有了丈夫带着她和他们的子女逃离庄园的经历,她最后获得自由在霍姆伍德定居下来,有一个“幸福的结局和开始”。[18]155怀德曼相信黑人与白人的矛盾并非完全不可调和,无论是哪种皮肤的人在增进了解后都可以和平共处甚至相濡以沫,最终实现人类的平等友爱。《鲁本》中代表非裔群体发声的律师虽然被警察逮捕而陷入沉默,但怀德曼对他给予了厚望,他在接受采访时说,“鲁本是坚不可摧的,这是我的看法。鲁本是一种神——他不会发生任何事;他此刻存在的特殊形式可能会消失,但是他会回来,他是一个准则”。[21]鲁本作为律师是公义准则的化身,怀德曼相信并等待鲁本的归来,其实质是对公平正义的伦理准则的实现充满信心,而非裔民族需要秉持乐观的态度耐心等待,等待它在消失太久后的永久归来。
沉默在表面来看是妥协,是等待,然而他仍然赞美沉默鼓励非裔在沉默中等待,因为沉默作为物质载体被非裔民族赋予了新的伦理内涵,使公平正义、和谐友爱和自由平等成为其内核。有了这三个内核作为支撑,非裔的沉默不再是消极的等待而是积极的进取,在彰显反抗姿态的同时自我消化种族仇恨和避免激烈的正面冲突,学会在夹缝中求生存,同时充分发挥人性和道德的调和作用,最终实现非裔民族及人类共同的伦理理想。
总体而言,怀德曼以沉默为视角折射出非裔民族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使得沉默成为他文学创作的一个标签和文学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第三部小说《私刑者》之后,他就极力从非裔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寻找写作素材、灵感和主题,并力图建立拥有黑人独特性的文学范式。在他的写作中,非裔沉默与非裔方言、非裔音乐相提并论,非裔沉默不仅是非裔历史的组成部分,还是非裔民族文化的折射,更为重要的是它反映了非裔民族独特的生存状态和反抗策略。他赞美沉默,是因为非裔民族被奴役和隔离、被剥削和歧视、被贬低和边缘化的独特经历都融入了他们的沉默之中,其实质是对非裔坚强不屈应对苦难的赞美;他赞美沉默,是因为非裔民族在何等的逆境中依然赋予了沉默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和谐友爱的伦理内涵,其实质是对非裔生活在深渊的底部依然能持乐观主义态度的赞美。怀德曼作品中的沉默与非裔历史、文化和伦理已经融会贯通,充分展现了他对非裔民族的信心和热爱,同时也揭示了他对文化、人性和道德力量的忠贞不渝。同时,在其小说创作中,怀德曼充分地将沉默与后现代主义策略相融合。这种把非裔民族历史、文化、伦理与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书写,不仅能充分展现黑人的历史真实和生存状态,还能促进美国黑人文学的丰富和发展,也必将成为当代美国非裔文学研究的新趋势。
注释:
①关于该段的译文本文参考了粱中贤在《权力阴影下沉默的符号意义——析〈斯可比先生的谜语〉》的译文。
②涂年根在分析海德格尔的思想时也有相同的论断,详见涂年根在《海德格尔的沉默观及其对叙事交流的启示》(载《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第79页)一文中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