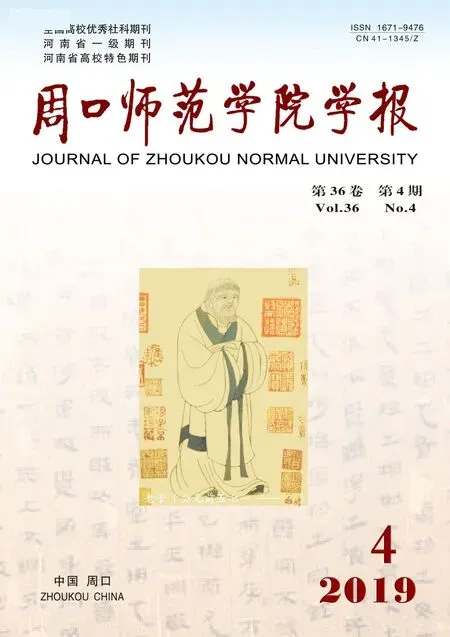韩愈与鲁迅:中华文化思想史上的千年契合
2019-01-30张弘韬
张弘韬
(郑州师范学院 中原文化研究所,河南 郑州 450044)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说:“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涌现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王充、何晏、王弼、韩愈、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鲁迅等一大批思想大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1]其中,唐代韩愈和近代鲁迅,二人所处的时代不同,思想性质不同,但推动学术思想史的转折,展示中国文化思想史的方向是一致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说:“苏东坡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讲的是从司马迁之后到韩愈,算起来文章衰弱了八代。韩愈的文章起来了,凭什么呢,就是‘道’,就是文以载道。”又说:“鲁迅先生说,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2]作为思想家、文学家的韩愈、鲁迅以文改造人的思想,达到时代振兴的思想、做法何其肖似,真是千年的契合。
一、变革时代的文艺方向
在中国发展史上,唐代是世界公认的强大帝国。从太宗的励精图治,经武后大胆创获,到玄宗稳步发展,使唐朝的发展达到民富国强的鼎盛时期。创获难,破坏易,唐朝出现了由极盛到极衰的转变。经玄宗末至代宗,爆发了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平定后虽稍安定,德宗年间又起“五王二帝”之乱,把个好端端的国家糟蹋得不成体统。到中唐,虽有志士仁人希望振兴,却找不到振兴之路。虽有人试图变文风,写古文,却未能与时代振兴挂钩,更无“振兴一代”的胆识魄力。作为具有特殊性格、特殊思想、特殊才艺的哲人,在社会动乱变革之时韩愈应运而生。他明确提出“振兴一代”的口号,找到了振兴的路子和具体实施的办法,且参与了“振兴一代”的社会实践。即以“古文”为工具,以“儒学道统”为思想武器,以“修辞明道”为号召,统一全国上下君民的思想,致力于国家的统一、振兴。出现了国君敢“断”,重臣敢战,贤臣献谋,将士用命的好形势;使旷日持久、师老无功的淮西之战以短短三个月就取得了全面胜利,震慑了大河南北的藩镇,国家出现了振兴之势。
鲁迅也处于中国近代大变革时期:晚清王朝统治的腐败积弱,经历旧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本来可以走向民主共和的社会,却又陷入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传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孙中山先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开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本可以顺势而下,使中国走向民族振兴的富强之路;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又面临着深重的民族危机。鲁迅正是在这个大变革时期产生的哲人与文学巨匠。鲁迅先学医,崇拜达尔文的进化论,欲以医学救国。他见到中国人被砍头示众,而围观的看客却是一群麻木不仁的中国人,震惊于中国国民性的缺失,就拿起文艺武器,致力于改变人的思想的战斗。后来,他读了《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又与共产党人交谊,开始信仰马列主义,终于成为共产主义战士。鲁迅正是和韩愈一样,在社会变革的实践中找到了前进的方向、振兴的道路,掌握了改变人们思想的武器。
正如习近平所说,韩愈“凭什么呢,就是‘道’,就是文以载道”[2]。韩愈的“道”是什么呢?是他总结的由“尧舜”至“孔孟”传承的优秀文化思想。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证明:凡是遵循这一思想,社会就兴盛;凡是背离了这一思想,社会就衰弱,以至于灭亡。夏朝禹之于桀,商朝汤之于纣,都是殷鉴不远的镜子。正如李汉所说:“日光玉洁,周情孔思,千态万貌,卒泽于道德仁义,炳如也;洞视万古,愍恻当世,右大拯颓风,教人自为。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坚,终而翕然随以定。呜呼!先生于文,摧陷廓清之功,比于武事,可谓雄伟不常者矣。”[3]1又如《新唐书》所论:“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4]5269正因为正确且有转动历史车轮的价值,韩愈才敢在与同辈、上级,乃至皇上辩论时都能理直气壮,折服他人。
鲁迅认准了文艺是改造国民精神的武器。故在《〈呐喊〉自序》里说:“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5]439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名曰复古,实则创新。在战斗的实践中鲁迅以杂文为武器,以拯救国民性为旨归的文化事业,则成为照耀文艺界前进的明灯。如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说:“鲁迅先生说,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2]这就是毛泽东指出的:“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6]698
二、狂人韩愈与鲁迅的《狂人日记》
韩愈是一个有特殊思想、特殊性格的人,确有狂放不羁的性格,与众不同的作为。裴度是韩愈的上司、老友与知己,批评韩愈直言不讳。在《寄李翱书》里说:“昌黎韩愈,仆识之旧矣。中心爱之,不觉惊赏。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作者,不及则已,及之者当大为防焉尔。”[7]批评韩愈写《毛颖传》《应科目时与人书》一类文章。这两篇文章前者为毛颖(笔)立传,后者自比为不得水而困顿的怪物“龙”。毛颖也罢,怪物也罢,都说明韩愈狂放怪奇的性格,对于这样狂放的人,奇怪的文章,裴度告诫今之作者都要当洪水猛兽大为防范。韩愈抗世俗为师,抗时风为古文,都遭到了世人的唾骂,为社会所不容,把他视为“狂人”。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里说:“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8]2177是褒、是贬,是讥、是笑,不用说,读者自明。宗元《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又说:“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又不为人师。”[8]2197韩愈四为学官,三为教授,均为师教徒,被贬州县时均办学教徒,在潮州甚至把自己的薪俸捐献给州学。宗元所说当是实情,就当时的社会情况和一些文献推断,当有过之无不及。张籍、李翱都是韩门子弟,却都以“兄”称之,不愿为师弟子,也可见当时社会风气之一斑。韩愈没有被世人挤压骂疯,不像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被逼而疯而病,实则他何尝疯?何尝病?窃以为,《狂人日记》里的狂人,何尝没有作者的影子。鲁迅和韩愈一样,虽被逼迫成狂人,但他们始终是一位清醒的哲人。
《狂人日记》写成于1918年4月2日,在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是年5月发表,是中国第一篇用白话写成的小说。一发表,即为世人震惊,或以鲁迅为狂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说:“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出现了,……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9]246《狂人日记》塑造了一个内涵深邃,形象鲜明活泼的人物——狂人。狂人乃作者中学良友之弟,被迫害致“狂”。“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以狂人出狂言之曲笔,辛辣地揭露了造成其狂的原因。并表明“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说明“狂人”不狂,所以狂者,乃被周围人迫害所致。文章层层推进,一步一步地叙写把他迫害成“狂人”的情况。赵贵翁、赵家的狗、交头议论的七八个人、一路上的人、要咬几口儿子才出气的女人、狼子村打死恶人还要吃他心肝的一伙人、老头子何先生,以至于“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本来都是被人吃的人,却不知不觉地都成为心安理得吃人的人,说明“狂人”周围的环境是一个吃人的网。可见,吃人的人凶恶残酷,被吃者又去吃人且心安理得,说明这个环境的残酷与黑暗,被人吃而吃人的人的愚昧。对那个环境的揭露层层深入,笔笔见血。
小说揭出了“狂人”致“狂”的谜底——4000年的封建专制和这专制下的封建礼教;“狂人”不狂,他清醒地认识到:在吃人的社会里是没有真正不吃人的人,连他自己也不免混进吃人的一伙中也去吃人。从文章开始介绍“狂人”病愈赴任,到“救救孩子”说明“狂人”的病是可以治好的,关键是人们都要觉醒,去做“救救孩子”的工作。值得一说的是第3节“狂人”的一段自白:“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证明“狂人”是一个清醒的人,这清醒正是作者赋予他的;也证明作者是睁眼看历史的清醒者,是挺立在大革命历史洪流潮头的战士。这个社会的统治者是以“仁义道德”来掩盖他们吃人的本性,维护那“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的黑屋的制造者,概而言之,即在第六节里说的“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的人,淋漓尽致地揭出了那伙人面兽心的本质[5]444-455。
作为封建社会的哲士仁人,韩愈之所以成为“狂人”,正是因为他冲破那个时代世俗的樊篱,高张文化革命的旗帜,开辟了一条新的文化之路。因此为世人和维护旧传统观念的势力所不容。韩愈的这种品质,正是历代圣贤可贵的品质,也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思想的积淀。这一优秀的文化思想必然为后世的哲士仁人继承,鲁迅的思想里也含有他们的血液。这就是韩愈这个“狂人”,与鲁迅心里的“狂人”的必然契合:都是被逼而成为“狂人”的。
三、奇怪而不荒诞的《毛颖传》与《阿Q正传》
每当读韩愈的《毛颖传》时,就常常想到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传”名字之特出,已是常人难以想到,为“毛颖”和“阿Q”立传,更是匪夷所思。这种奇怪而不荒诞的思维,正可以看到韩愈与鲁迅思维的相似处,或者就是二人思维深处的契合。鲁迅教过中国文学史,撰写过《汉文学史纲》和《中国小说史略》,熟知韩愈,对奇文《毛颖传》当感兴趣。为阿Q作传,是否参酌了《毛颖传》,尚无直接文献可考,然思维是一致的。
1.立传的总体思考。《毛颖传》落笔直书,接着一一道来,至结语借太史公之口,道出为毛颖立传理由:“毛氏有两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于毛,所谓鲁卫毛聃者也。战国时,有毛公、毛遂。独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孙最为蕃昌。春秋之成,见绝于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将军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诸管城,世遂有名。”[3]434此乃正叙倒插。而《阿Q正传》则是先正名,接一一叙来。鲁迅先生说:“我要给阿Q作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但一面要做,一面又往回想,这足见我不是一个‘立言’的人,因为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究竟谁靠谁传,渐渐的不甚了然起来,而终于归结到传阿Q,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5]512再说立传需要交代的事:立传之由,立传正名,通例,不知阿Q名字的写法、阿Q的籍贯。这使我想起韩愈《燕喜亭记》之定名。韩愈与王仲舒议亭名时说:“既成,愈请名之。其丘曰‘俟德之丘’,蔽于古而显于今,有俟之道也;其石谷曰‘谦受之谷’,瀑曰‘振鹭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黄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时也;池曰‘君子之池’,虚以钟其美,盈以出其恶也;泉之源曰‘天泽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3]204虽为如《阿Q正传》明分四款,却分六层,依次叙来推出题名。两文都是议论后定名的。
2.《毛颖传》与《阿Q正传》的写法。或谓韩愈《毛颖传》乃南朝俳谐文《驴九锡》《鸡九锡》之类而小变。俳谐文虽出于戏,实以讥切当世封爵之滥,退之之意亦正在“中书君老而秃,不任吾用……今不中书”数语[3]433,亦非徒作。这种游戏文字何尝不也是借鉴了当时流行于民间的《燕雀赋》燕雀争巢的故事。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五章《唐代的民间歌赋》说:“像这样的游戏文章,唐人并不忌讳去写。韩愈也作了《毛颖传》。‘争奇’一类的写作,本来也是从《大言》《小言赋》发展出来的。”[10]151一“奇”字道出了写这类文章的妙谛。鲁迅《阿Q正传》不也是借阿Q有关奇特滑稽的人和事,揭出时代国势与人性的大主题吗?两《传》的具体写法皆以叙事与议论结合,依次论述传主行年事迹。《阿Q正传》的《优胜记略》《续优胜记略》,也和韩愈常用的方法一样正话反说。阿Q无姓无名,无产无家,更别说“行状”了。可他却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阿Q头上有秃疮,讳“癞”讳“亮”,凡有人触其忌讳者,见口讷的便骂,见弱者便打,可总多吃亏。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去“自轻自贱”不说,就只余下“第一个”,便觉得自己也和“状元”的“第一个”一样高贵。蒙赵太爷打他嘴巴后,自认为是赵太爷的本家,于是想“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又得意起来。这就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一些中国人身上的劣根性。即《恋爱的悲剧》开头的议论:“然而我们的阿Q却没有这样乏,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看哪,他飘飘然的似乎要飞去了!”
《生计问题》写阿Q被逼得无以求生的时候打定进城的主意,从写法上是一个巧妙的过渡。《从中兴到末路》阿Q的中兴其实是参与窃贼的偷盗。因为分得一点东西,回到未庄,便夸耀了一番。别人以为他真的阔绰了,他自己也飘飘然。可是当人们揭出他“中兴”的谜底后,“斯亦不足畏也矣”。笔锋又一转,《革命》一章写阿Q闹革命。阿Q的革命,本无啥可说,鲁迅先生却以讽刺的议论手法,写了“阿Q式”的革命,深刻揭露了当时革命者的所谓“革命”。《大团圆》名字奇特,以阿Q游街示众被枪毙而告结。最后鲁迅先生议论道:“至于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而城里的舆论却不佳,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5]512-552还是愚昧的时代,还是愚昧的人性。而这写法也像《毛颖传》结尾。
3.不同的舆论,相同的艺术效果。《毛颖传》一出就遭到裴度等人的批评。五代刘昫也说:“《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谬者。”[11]4204宋释契嵩说:“韩子为《毛颖传》,而史非之。《书》曰:‘德盛不狎侮。’又曰:‘玩人丧德,玩物丧志。’韩子非侮乎?玩耶!谓其德乎哉?”[12]也有识其实质,充分肯定的。如唐柳宗元说:“有来南者,时言韩愈为《毛颖传》,不能举其辞,而独大笑以为怪,而吾久不克见。杨子诲之来,始持其书,索而读之,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韩子之怪于文也。……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圣人之所弃者。《诗》曰:‘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太史公书有《滑稽列传》,皆取乎有益于世者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艺百家,大细穿穴用而不遗者,毛颖之功也。韩子穷古书,好斯文,嘉颖之能尽其意,故奋而为之传,以发其郁积,而学者得以励,其有益于世欤!”[8]1435-1436明茅坤则说:“设虚景摹写,工极古今,其连翩跌宕刻画,司马子长。”[13]《毛颖传》通篇将无作有,用滑稽之笔,澹荡起伏,遇事点掇,篇末以“颖始以俘见,卒见任使,秦之灭诸侯,颖与有功,赏不酬劳,以老见疏,秦真少恩哉”[3]434点睛,骂尽历代上下用人见弃者嘴脸。与《阿Q正传》以辛辣之笔揭出阿Q时代各色人等的灵魂一样。
如鲁迅先生《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所说:“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14]83阿Q典型的不朽价值在于他高度概括了在数千年封建文化窒息下形成的中国国民性的弱点,阿Q的基本性格就是自我意识的严重缺失。阿Q思想的基本特征是“精神胜利法”。在阿Q“精神胜利法”的各个阶段,我们都会感到阿Q在精神人格上已经分裂为二:一个是受欺侮的实际的阿Q,一个是在精神上为这种受欺侮而辩白的阿Q。即自轻自贱,虚妄自居于人上的人。
四、多用曲笔的《杂说》与《野草》
1924年至1926年,鲁迅在《雨丝》上连续发表了23篇散文诗,1927年结集出版,增写题词,名曰《野草》。鲁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里说:“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现在举几个例罢。因为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作《我的失恋》,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复仇》第一篇,又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作《希望》。《这样的战士》,是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腊叶》,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段祺瑞政府枪击徒手民众后,作《淡淡的血痕中》,其时我已避居别处;奉天派和直隶派军阀战争的时候,作《一觉》,此后我就不能住在北京了。”[15]365由于难以直说,《野草》在艺术上深沉含蓄,多用隐喻曲笔。具有诗的凝炼,韵味的深长,深沉的含蓄,生活的哲理。以内心抒发为主,交织着严肃的自省与世俗抗争的骨鲠,抒发内心的苦闷与愤愤的不平。尤其是《秋夜》,开头即说:“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枣树虽然受到损害,只剩下枝干,但它“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致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地眨着许多蛊惑的眼睛”[16]166-167。夜游的恶鸟哇的叫声;小青虫为了追求灯光,千方百计地撞进室内,勇敢地以身扑火。这样的开头,这种隐喻曲笔,颇可从韩愈《秋怀》和《庭楸》找到契合的因素(1)《秋怀》:窗前两好树,众叶光薿薿。秋风一披拂。策策鸣不已。微灯照空床,夜半偏入耳。愁忧无端来,感叹成坐起。天明视颜色,与故不相似(《韩昌黎全集》第19页)。《庭楸》:庭楸止五株,共生十步间。各有藤绕之,上各相钩联。……我已自顽钝,重遭五楸牵。客来尚不见,肯到权门前。权门众所趋,有客动百千。九牛亡一毛,未在多少间。往既无可顾,不往自可怜(《韩昌黎全集》第118页)。,表现在艺术上是象征主义艺术方法的广泛应用。《野草》中的多数篇章并不是现实生活的直接描绘,而是把作者深刻的人生感受,通过主观想象的作用,化为具体象征性的艺术形象,奇幻壮美的意境。如《秋夜》以浓郁的抒情笔调,叙写洒满着繁霜的园里,小粉红花、枣树、恶鸟、小青虫经过作家思想感情的灌注,人们可以从草木虫鸟身上,得到富有社会意义的启示。
《野草》艺术上的隐喻曲笔,大都可以在韩愈《杂说》四首,及其他有关文章里找到与之契合的地方。《杂说》四首:龙说、医说、谈生说、马说。《马说》借伯乐与马及饲马、策马之道讲当权者不视才、不育才、不用才的社会现实,为有才有德之士鸣不评,抒发他胸中的愤懑。《医说》讲视履考祥,善医善计,隐喻统治者治人治世的无能。若将《龙说》与其《应科目时与人书》中自比于龙,使之于水者参读,便可了解韩愈乃用隐喻曲笔,揭示社会人与人、人与环境的辩证关系。《谈生说》则揭示了不能以貌取人的至理,骂杀那写禽兽不如的人。皆以荒诞写真实,以隐喻明事理,有深刻的哲理内涵。
《野草》也正是以鲁迅的情结揭示了时代苦闷与人生苦闷,其内容自我主观感情情绪的象征性表现和对自我存在价值的象征性肯定与韩愈以《杂说》揭示内心的郁闷,世间的不平而愤世嫉俗异曲同工。
五、“不平则鸣”与“呐喊”
《呐喊》初版收入小说15篇,包括《不周山》,后改名《补天》,入《故事新编》。乃1918年至1922年所作。这15篇小说大体写了三类人物:一类如《孔乙己》里的孔乙己、《药》里的华老栓、《阿Q正传》里的阿Q,皆失去民族精神,缺失正常人的个性;对他们既揭露鞭挞,又惋惜同情;且向他们大喊一声,希望他们在浑浑噩噩中警醒,找回缺失的民族性。一类如《明天》里的单四嫂、《一件小事》里的车夫、《风波》里的九斤老太和她的乡亲们、《故乡》里的闰土,则是作者极同情,又极爱怜,极称赞的人,先生则呐喊着为他们所处境况鸣不平。一类如《补天》,作者对战争给天地人类造成灾难的憎恶,对女娲奋力补天英雄的赞颂。如“天边的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流动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那一边,却是一个生铁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16]357。在曲折的故事和生动的描写里揭出了赞颂的“呐喊”。鲁迅先生《〈呐喊〉自序》说:“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5]441“因为我们都曾经走过苦难的道路,现在还在走——一面寻求着光明。”[9]544为寂寞而呐喊,为爱怜而呐喊,为不平而呐喊,为希望而呐喊,可见鲁迅在这一时期的思想。这不平的呐喊,当出自中唐韩愈。韩愈在《送孟东野序》里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3]276打开《韩集》,处处可以看到不平之鸣:或为时代统一鸣之,或为才不得其用而鸣之,或为百姓灾难鸣不平……如宋李涂云:“退之《送孟东野序》,一鸣字发出许多议论,自《周礼》‘梓人为筍簴’来。”[17]78宋俞文豹也说:“《送孟东野序》云:‘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无声风挠之,金石无声或击之。’‘人之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皆鸣其不平者也。’文豹谓此说甚伟。”[18]128王元启谓:此序或以为一“鸣”字成文,或又以为重在善鸣,单举“鸣”字,实则“鸣与善皆不重”,只重“不得其平”四字。“不得其平”,谓有触而动于中也,后“鸣国家之盛”及“自鸣不幸”,其实皆“天”使之也。起句便暗藏一“天”字,末后“在上奚喜”二语,乃通体精神归宿处[19]528。
六、结语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杂文堪称史诗性的作品,反映了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发展,也描述、解剖了这个时代的各种社会现象和不同类型的人物,是中国社会思想百科全书式的作品。《韩昌黎集》则是中唐由衰到兴再到衰的社会生活和思想历史画卷。
这种散文形式至今仍是散文创作的主体样式。韩愈写了大量的杂作,影响其后的杂文写作,也影响了鲁迅等人的杂文写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鲁迅的杂文里,都能找到韩愈杂作的影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的写作贴近现实,为社会服务。韩愈提出“自振一代”,正可以历史经验证明今天振兴中华民族的大方向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或谓鲁迅向韩愈学习并没有明显的迹象。诚然,鲁迅学韩愈,如韩愈学孟子不像孟子,欧阳修学韩愈不像韩愈一样,皆不袭其貌,而似其神:这才是虽学前人的经验,却能独具自己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