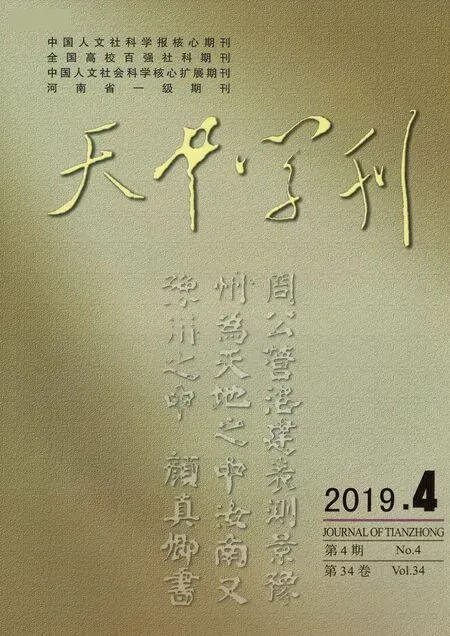伍子胥故事研究综述及其前景展望
——以中国叙事文化学为依据
2019-01-19陈玉平
陈 玉 平
(广西中医药大学 基础医学院,广西 南宁530200)
春秋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乱世,风云变幻,英雄辈出,在这段风起云涌的历史中,伍子胥实在是不得不提的人物。伍子胥(?―前484年),名员,出生于楚国,楚大夫伍奢次子,因入吴后封于申地,也称申胥。清人王摅《谒伍相祠》“报父有心终覆楚,杀身无计可存吴”,概括了他一生的行迹。春秋后期,列国争雄,在这特殊的历史情境之下,伍子胥以过人的心智,忍辱负重,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为父兄向国君复仇,最终完成以匹夫抗万乘的壮举。《左传》《国语》《史记》《越绝书》《吴越春秋》,对伍子胥有着从粗陈梗概到浓墨铺排的叙述和记录。与之相应,当时的诸子各家,对伍子胥也都各有评说,如《庄子》《荀子》《墨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在某种意义上,先秦著述里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图谱,越是靠近原点,辐射生发的可能性就越大。后世的文人墨客对伍子胥事迹进行加工改编,踵事增华,从春秋至清代,一直颇为丰富,体裁涵盖史书、诗词、变文、小说、戏曲等。伍子胥故事从先秦两汉的以史传为主要载体逐渐演变成以文学文本为主要载体,同时主人公伍子胥也完成了从历史人物到文学人物的演变。
一、伍子胥故事文本的研究意义
伍子胥形象充满矛盾性与复杂性,复仇与忠君是其主要标签,在他身上,复仇与忠君以极其矛盾的方式并存。无论是复仇还是忠君,他都是以极致的方式表达,复仇就鞭尸泄愤,忠君则忠谏亡身。在民间信仰中,伍子胥从潮神到土神,香火不断。作为人格化的神,从护佑渡江过河到保佑士子科举得第,他无所不能。自春秋后期至清代的两千多年历史中,几乎每个阶段都有伍子胥故事,体裁涵盖史传、诗文、戏曲、小说等多种文体,故而其故事可以作为一个可供开采的矿藏,不断地被发掘。
首先,在某种意义上,伍子胥是复仇的代名词,是春秋大复仇的代表人物。纵观伍子胥故事的文本演变,其复仇的形象及对其复仇的评价在不同的朝代亦有所更变。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风尚、时代思潮,都能够左右人们对复仇这一问题的看法。从先秦到明清,伍子胥复仇故事几经演变,从一开始的《左传》粗陈梗概,到后来《东周列国志》的仔细铺排,人物有增加,情节有变动,情感有游移,这一切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
其次,伍子胥辅佐吴王夫差,忠谏而亡,成为千古忠君的典范。“忠”作为传统道德最基本的规范之一,历经千年演变逐渐成为封建道德体系的主要支柱。从伍子胥故事文本的演变中可以窥见忠君观念的演化过程。与之同时,不同时期士人对其忠谏亡身这一事实的评说议论,也是体察士人心态的绝好途径。
再次,从民间信仰流变的角度考察伍子胥信仰,也有待深入探讨。在民间信仰里,伍子胥从抗灾御害的潮神转化为护佑一方百姓的土地神,从一开始只是在吴越地区信仰到后来逐步扩展到全国各地,这一转变过程之中蕴含着众多文化信息。通过研究伍子胥故事的演变,体察伍子胥的民间信仰,可以丰富民间信仰的个案研究,亦能丰富和完善伍子胥题材的研究。
最后,近些年来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之间联系的研究成为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伍子胥生为楚人,深受楚文化熏陶。楚人忍而阴,刚烈轻死,这种性格潜移默化影响了他的复仇行为。入吴之后,作为一代忠臣,他辅佐吴国两代君王,修建阖闾大城,是吴越文化的早期开拓者。统观伍子胥故事的文本演变,总结归纳出地域文化对伍子胥形象的影响,可以对楚文化和吴越文化有一个直观清晰的解读,以此为基础的伍子胥文化意蕴研究和论述才不会显得无本可依。
二、20世纪以来伍子胥故事的研究现状
20世纪以来,研究伍子胥故事的论文专著众多,其中既有关于人物形象与生平事迹的研究,亦有与伍子胥相关的民俗与风物研究,域外汉学和出土文献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颇丰。
(一)历史人物伍子胥生平事迹研究
伍子胥一生中最具有传奇色彩的事迹莫过于他的复仇壮举,这自然为学界所关注,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相关的研究论文主要有李晓一的《〈史记· 伍子胥列传〉复仇观的价值特点》(《渤海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尹富的《〈伍子胥变文〉与唐代的血亲复仇》(《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岳淑珍的《〈伍子胥列传〉的复仇意识及其内涵》(《河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舒大清的《伍子胥和楚国的复仇模式》、刘丛的《由正史到杂史——伍子胥复仇故事在史传系统中的流变》(《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朱湘蓉的《文学史中伍子胥复仇情节的形成——以湖北云梦睡虎地77 号汉墓伍子胥故事简为依据》(《中原文化研究》2005年第2期》)。苗江磊的硕士论文《伍子胥复仇形象研究》以复仇为中心,考察了伍子胥形象从先秦到清代发生的变化,紧扣主旨,把伍子胥复仇形象分为孕育期、成型期、演变期三个不同时期,并从荆楚风气、孝治政策、社会现状来阐述分析不同时期其形象发生变化的原因[1]45―56。王立、刘卫英的专著《传统复仇文学主题的文化阐释及中外比较研究》分析了春秋战国时代忠奸观念与伍子胥复仇之间的联系[2]432―434。涂又光《楚国哲学史》则从哲学思辨的角度阐明了伍子胥与他的复仇哲学,通过逻辑推理给出了“屈原尚有血亲复仇的原始思维的影响”的答案[3]124―143。
对由复仇引申而来的伍子胥是否鞭尸的问题,一些研究者也作出了回应,如张君《伍子胥何曾掘墓鞭尸》(《武汉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仓林忠《关于伍子胥是否对楚平王掘墓鞭尸的辨析》(《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0期)。这两篇论文从历史学的角度,对伍子胥是否鞭尸作出考证,虽然两文结论相反,但都言之有理,持之有故。
(二)伍子胥故事流变的文献梳理与研究
关于伍子胥故事流变研究的论文有刘树胜《正史·传说· 讲唱文学——由〈伍子胥变文〉看伍子胥故事的嬗变》(《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4期)、黄亚平《伍子胥故事的演变——史传系统与敦煌变文为代表的民间系统的对比》(《敦煌研究》2003年第2期)、高云萍《伍子胥故事的历史演变》(《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2期)、单芳《〈伍子胥变文〉与〈伍员吹箫〉杂剧比较》(《敦煌研究》2008年第5期)、杨华和冯闻文合作的《伍子胥故事的文本流变和中国古代的价值观》(《长江学术》2013年第3期)、熊贤品《先秦两汉文献中伍子胥故事及其形象流变》(《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顾永新《伍子胥故事丛考》(《国学研究》第10 卷)。这些论文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伍子胥故事的流变,其中黄亚平把伍子胥故事分为史传系统和民间系统,并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做了图解式分析。
(三)伍子胥相关史传与文学作品研究
伍子胥形象先见于《左传》及诸子著作,后见于《史记》《越绝书》和《吴越春秋》,嗣后又见于唐代变文、元代杂剧、明代传奇、清代鼓词,这些历史和文学作品共同塑造了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谓十分丰硕。
研究史传作品中伍子胥形象的论文有:蒋昕宇《汉代公羊学影响下的伍子胥形象》(《现代语文· 学术综合版》2012年第5期)着重考察了《史记· 伍子胥列传》和东汉杂史《吴越春秋》中伍子胥的形象,并认为其形象塑造受到了汉代公羊学的影响;肖楠《〈伍子胥列传〉伍子胥形象之司马迁自我精神的体现》(《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则认为司马迁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我胸中之块垒,借对伍子胥隐忍成就功名来抒发命运感喟[4]44―46;曹林娣《论〈吴越春秋〉中伍子胥形象塑造》认为《吴越春秋》已经将伍子胥神话成一个文武盖世、忠孝两全的英雄,成为后世演义类小说军师的鼻祖原型[5]31―33;吴玉贞《〈吴越春秋〉试论》(四川大学2015年硕士论文)用一章的篇幅探讨了伍子胥形象,认为伍子胥是一个较为成功的忠臣和谋臣。
关于伍子胥变文的研究成果很多:陈筱芳《〈伍子胥变文〉的历史真实性及价值取向》(《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12年第12期)对变文的历史真实性作了考证;李明《〈伍子胥变文〉的文化内涵》(《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阐明伍子胥变文分别受儒释道三家影响,是三种不同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结果[6]41―44;黎聪《论〈伍子胥变文〉中的儒佛交融》(《语文学刊》2009年第8期)则认为变文受到儒家思想如天人感应、劝善惩恶,佛家思想如极乐世界、因果报应的影响;李渝刚《试议佛经对〈伍子胥变文〉的影响》具体分析了佛经文学(伏魔经文)和佛教释梦是如何影响变文的叙述方式的,得出伍子胥变文是借历史故事来宣扬佛理的结论,佛理才是其精神内核。
关于伍子胥戏曲作品的讨论有李则桐《元杂剧〈伍员吹箫〉》论析》,查洪德、张弦声《论〈楚昭公〉的主题与郑廷玉杂剧的思想性》(《中州学刊》1993年第4期),姜文娟《全忠全孝——通过〈二胥记〉看孟称舜的济世思想和创作思想》(《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8期),卢新蕾《从〈浣纱记〉中的因果抉择分析人物形象——以夫差、伍子胥、勾践、范蠡为对象》(《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李洪蕾《复仇——尽忠——伍子胥在〈浣纱记〉中》(《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伍子胥作为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经过不同时代不同作品的演绎,其形象变得厚重而深刻。从先秦史传到清代戏曲,每一次形象的变动都映射出时代与社会文化发生的变化,寄予着创作者各自的审美理想和价值观念。
(四)伍子胥相关民俗风物与信仰的研究
伍子胥与端午节风俗的产生、演变和流播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方面研究的论文有蒋康《试论伍子胥的崇祀习俗》(《苏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富世平《伍子胥、屈原在先秦两汉文献中的不同书写及其对端午习俗的影响》(《嘉兴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弋春源《端午节起源于伍子胥考》(《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和《从屈原与伍子胥的关系看端午节的起源》(《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尤岩《伍子胥与端午吴地风俗》(《江苏地方志》2006 第3期)。
在民间信仰中伍子胥成为水仙、潮神,有着广大的受众群。关于这方面研究的论文有:龚敏《唐诗中的伍子胥信仰与传说》(《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吴恩培《吴、越文化融汇的古代例证——伍子胥文化的层累透视》(《苏州职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仓修良《伍子胥与钱江潮》(《文史知识》1993年第2期)、赵立新《逃离与眷顾——伍子胥悲剧命运的文化阐释》(《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徐静《苏州胥门与伍子胥》(《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徐海《伍子胥白马素车形象考》(《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徐海《伍子胥信仰中的灵验故事探析》(《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李金操与王元林《由恶变善:潮神伍子胥信仰变迁新探》(《安徽史学》2017年第1期)。硕士论文有虞海娜《伍子胥文化意象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2年)、徐海《伍子胥信仰研究》(兰州大学,2013年),其中虞海娜用一个章节的篇幅分析了伍子胥在民间传说中由“仇怨索命”到“抗灾御患”形象的转变,指出随着官方的褒奖和推广,伍子胥开始从水神化身成为遍布乡村的土地神[7]12―16。
(五)伍子胥相关出土文献研究
20世纪80年代,包括《盖庐》在内的一大批汉简在湖北张家山出土,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除了对简帛做文字考释识别以外,《盖庐》本身也是一部军事著作,其中透露着伍子胥对治国用兵的看法,是全面了解伍子胥军事思想的可贵资料。相关的论文主要有曹方向《云梦睡虎地77 号西汉墓“伍子胥故事残简”简序问题刍议》(《江汉考古》2013年第3期)、连邵名《张家山汉简〈盖庐〉考述》(《中国历史文物》2015年第2期)、邵鸿《张家山汉墓古竹书〈盖庐〉与〈伍子胥兵法〉》(《南昌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田旭东《张家山汉简〈盖庐〉中的兵阴阳家》(《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曹锦炎《论张家山竹简〈盖庐〉》(《吴越历史与考古论丛》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福田一也《张家山汉简〈盖庐〉中的黄帝与阴阳流兵法》(台湾《文与哲》2008年第12期)。
王洪强《伍子胥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从地缘战略设计、战术应用、水战与城防思想、《盖庐》兵学思想四个方面考察了伍子胥的军事思想。
(六)域外汉学对伍子胥故事的研究
在域外汉学领域中,宇文所安《论叙事的内驱力》用叙事学的视角考察了伍子胥复仇故事,认为《左传》中吴国对越国的复仇在很大程度上是伍子胥的自我创造,复仇成为叙事的中心,其相关叙事从此带上了政治色彩[8]68―98。姜士彬《伍子胥变文及其来源》把伍子胥故事分为口头传统和书写传统两项,并把伍子胥故事变异的原因归之于受众的不同,底层民众和社会精英从伍子胥的故事中各取所需。姜士彬另撰有《Epic and History in Early China:The Matter of Wu Tzu hsu》(无中译本),在这篇论文中,姜氏运用西方研究民间文学常见的方法——母题研究分析伍子胥故事中的情节单元,如逃命亡奔、渔父搭救等[9]96―98。日本学者水越知撰写的《伍子胥信仰与江南地域社会——信仰圈结构分析》一文,绘制了伍子胥信仰的相关地图和吴方言分布与伍子胥信仰关系图,让人从地域分布上对伍子胥信仰有了直观的了解[10]316―351。
从以上六个方面纵观伍子胥的研究成果,不可谓不丰厚,但若从总体上考察伍子胥故事,这六个方面则显得各自为营,或侧重生平事迹的研究,或偏重具体作品中形象的分析。这些研究虽对伍子胥故事流变做了梳理,但却没有从总体上对故事的变异情况做出分析,或是分析略为简略和单薄,对伍子胥故事的情节、人物、内容的变化还可以有更为仔细的审定和分析。域外汉学的研究者运用一些新的研究方法,用“第三只眼睛”考察伍子胥故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西方研究民间文学的方法,如母题研究,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叙事文学的研究。
如上文所述,近年来学界关于伍子胥的研究成果丰硕,且已不限于从文学角度进行的研究。随着多学科交叉的介入,宗教学、民俗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和路数也被引进文学研究中,传统的文献资料被重新评估解读,一些新的观点脱颖而出。但是就伍子胥的个案研究来说,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尚待弥补。
学界对先秦子书、两汉史传、唐宋诗词、元明戏曲、明清笔记小说、清代说唱文学中的伍子胥形象研究已经十分到位。传统文学史一些常见的研究方法也运用娴熟,如人物形象分析、艺术特色的挖掘、文本的深入解读等。但若是从整体伍子胥故事的发展流变来说,由先秦到明清,伍子胥故事中人物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不能做单一的、静止的考察。在漫长的历史区间,人物有增减,如浣纱女,渔父之子;情节有变动,如由鞭尸到鞭坟;且在民间信仰中,民众对伍子胥的情感由恐惧到敬畏,伍子胥从潮神、水神变为遍布乡里的土地神,不仅要保佑风调雨顺还要保佑士子科举得中。虽然有一些论文对此做出回应,但给出的答案流于形式,点到为止,并未就此展开深入系统的分析。同时,多学科交叉的伍子胥研究不够深入,如关于伍子胥的出土文献——张家山汉简,需要从文字学的角度进行考释;要赏析绍兴出土的伍子胥画像镜就少不了文物学、考古学的背景知识;关于伍子胥《盖庐》的军事思想,则需要涉猎一些军事学方面的常识。另外,如关于伍子胥民间信仰的研究,要考察潮神形象由恶到善的变迁原因和信仰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灵验故事,更需要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进行观照,否则就只能在文学研究里兜圈子。
三、中国叙事文化学视野下的伍子胥故事研究展望
中国叙事文化学是宁稼雨针对传统文学研究领域的困境所提出的一种另辟蹊径的想法和实践。宁稼雨认为20世纪以来中国的学术范式是在“全盘西化”价值观大背景下西体中用的产物,中国传统的小说戏曲这类叙事文学的研究模式,主要以零散批评和评点式研究为主,自鲁迅和王国维之后转为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研究。得益于这种“西体中用”的研究方法,中国叙事文学研究变得系统而严谨,摆脱了过去的吉光片羽、即兴点评。但是,随着中国叙事文学研究的深入,这种研究方法逐渐暴露一些缺陷。小说和戏曲这些文体要素只是叙事文学的外在形态,叙事文学的内核应该是故事,若以此为出发点,那么单一的作家作品研究很难对那些从时间上横跨若干朝代,形式上跨越多种文学体裁和兼有多种文学作品的故事类型作出合理的解释。
宁稼雨提出的中国叙事文化学以故事类型作为研究对象,这样就突破了文体和单篇作品的藩篱,从故事本身动态演变的角度研究叙事文学作品。“其实,中国式的主题学研究不仅有范例,而且时间久远。1924年顾颉刚写作《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这和德国人提出主题学方法的时间大致相同。《孟姜女故事的转变》表现出明显的中国特色,其中最为精彩之处就是作者几乎能把孟姜女故事每一次变化的原因在其产生的历史文化土壤中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用这种结合传统历史考据学和西方实证主义的方法来解读中国叙事文学故事主题,显得十分清晰和明快,应当成为我们以中为体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范本和楷模。”[11]14―16
中国叙事文化学是关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文体的文化研究,何为古代叙事文学文体,什么样的作品属于叙事文化学的研究范围,宁先生也作了界定:“比较明确的叙事文学体裁如小说、戏曲、史传等;文体外要关注本身不属于叙事文学,但和叙事文学有着非常密切关系的文献,如诗词、文物等。对于叙事文学之外的历史学、民俗学等学科中与叙事学有关资料的关注,是从中国叙事文化学角度对于叙事文学研究的新角度,这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性质有关。”[12]20―23
以中国叙事文化学的角度和思路研究伍子胥故事的文本具有广阔前景。首先,在材料的搜集上突破文体和学科的限制,一切与伍子胥故事相关的材料都在考察范围之内。突破了单一作品的壁垒,打破戏曲研究者只研究戏曲、小说研究者只研究小说、诗词研究者只研究诗词的各守一端的局面。诸如民俗学、考古学都可成为解读伍子胥故事文化内涵的利器。在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思路指导下,史传、诗词、变文、戏曲、小说、简帛、出土文物、方志等所有与伍子胥故事有关的材料都应全面搜罗,并尽力呈现这些作品的文化学意义。其次,突破以往以人物为中心的研究模式,以故事情节主题单元为中心,可以把伍子胥故事分为若干个故事主题系列,如复仇故事、逃亡故事、忠谏故事、潮神故事。这些故事情节单元分别与复仇文化、忠君文化、地域文化、民间信仰相联系。探究故事情节的流变与文化主题的关系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的一个理论创新。再次,无论是作为历史人物还是文学人物,伍子胥都已浓缩为一个文化符号,甚至是一种文化现象。比如在复仇文化的视野之下伍子胥的复仇故事可以有多种解读。在忠君文化的视野之下伍子胥的忠谏而亡,在纵向的历史长河中有时被看成忠君的典范,有时则是愚忠的代表。每一次变动都有着深层次的文化动因,可以说是历史发展与文化逻辑合力影响的产物,而这一切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大有裨益。引进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不仅能够扩大伍子胥故事的研究视角,也能够加深对该故事文化内涵的剖析和挖掘,为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大厦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