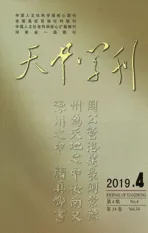东汉河南的区域治理及其文化表现
2019-01-19崔建华
崔 建 华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710119)
东汉定都洛阳,改管辖洛阳的河南郡为河南尹。相比西汉时期,作为京师所在,河南地区①的政治地位得到空前提升,但其区域治理面临十分复杂的形势,区域文化发展的轨迹及基本面貌也呈现出不同于邻近地区的特征。
一、东汉建立之前的河南区域管理实态
关于汉代的河南区域治理,有两个故事颇为史家津津乐道。第一个故事发生于南阳人卓茂身上。此人“习《诗》、《礼》及历算,究极师法,称为通儒”,汉哀帝时期,“以儒术举为侍郎,给事黄门,迁密令”。密县属河南郡。卓茂到任后,“吏人笑之,邻城闻者皆蚩其不能。河南郡为置守令,茂不为嫌,理事自若。数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遗。平帝时,天下大蝗,河南二十余县皆被其灾,独不入密县界。督邮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见乃服焉”。后来,当卓茂离任之时,“密人老少皆涕泣随送”[1]871。第二个故事的主角是关中人鲁恭。十五岁时,鲁恭“习《鲁诗》”,“为诸儒所称,学士争归之”。汉章帝时期,担任河南中牟令,“专以德化为理,不任刑罚”[1]874。“建初七年,郡国螟伤稼,犬牙缘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闻之,疑其不实,使仁恕掾肥亲往廉之”[1]874,结果确实是名不虚传。就在上级准备拔擢鲁恭的时候,鲁恭因守孝而离职,“吏人思之”[1]875。
两则故事前后相去80年左右,为时已不是很短,然而行事方式与效果竟不谋而合。若不细究,或许会以为西汉晚期以来的河南基层社会比较质朴,需要而且适合由注重“德化”“教化”的官员来治理。但是,在史料批判的基础上,这样的认识有重新思考的必要。
卓茂、鲁恭德感蝗螟的事迹早在东汉人所著《东观汉记》中已有记载[2]472―476。有学者指出,“飞蝗出境”是“中古史家构建地方良吏形象时习用的书写模式”,这种模式是由“以《东观汉记》为代表的东汉文献确立”的[3]7。既然是为了塑造传主形象而采用的模式,其真实性便值得怀疑。王充曾针对卓茂事迹做出了“此又虚也”的判断,其理由有二:(1) “贤明至诚之化,通于同类,能相知心,然后慕服”,蝗虫与人不同类,“何知何见,而能知卓公之化”;(2) 蝗虫聚集“多少有处”,“过县有留去”,此乃自然之理[4]258―259。也就是说,蝗虫不在县境停留,原是一种自然现象,世人神乎其事,遂认为是县令德化所致。
王充的论辩很有道理,德感蝗螟的故事纯属虚构。尽管如此,史书所载卓、鲁二人注重“教化”“德化”的基本施政风格应当还是可信的。只不过,民众神化这样的地方官员,反映了基层社会对河南区域治理的一种想象与期盼,故事的另一面往往反映的是冷峻的现实。实际上,两汉之际的河南并非卓茂、鲁恭事迹中所看到的官民和洽状态,官方对河南的治理是以如临大敌般的严控苛察为特点的。这个形势自西汉中期即已出现,当时为了控制豪族势力在基层社会的蔓延,朝廷往往委任酷吏来管理河南,最典型者如在河南太守任上被称为“屠伯”的严延年。这个状态到西汉晚期,才出现了些许改变。汉元帝时期,九江人召信臣任河南太守,“其治视民如子”,“为人勤力有方略,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5]3641―3642。汉哀帝时期卓茂大兴教化的事迹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但是,对道德教化适用的程度似乎不应做过高的估计,教化个案的出现毕竟只是区域文化转变的开端,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欲实现区域治理风格的根本变革,前提条件便是地方豪强被消灭或愿意与官方合作。西汉晚期显然没有形成这样的条件,之后的新莽时期及战乱年代亦复如是。
王莽以和平手段结束汉朝统治后,热衷于依《周礼》进行改制,对地方基层社会的重塑难有实质性的作为。新莽末年兴起的战乱对河南的影响并不是太大。更始政权推翻王莽的关键战役发生于颍川郡的昆阳县,在洛阳方向并未见到十分强大的攻势,倒是武关方向率先实现突破,攻克了长安,随后便获得了“拔洛阳”的重大战果。就时间节点来看,新莽政权的洛阳守将实际上是见大势已去而主动投降的,并非被更始政权所攻克。此后,更始政权定都长安,“遣舞阴王李轶、廪丘王田立、大司马朱鲔、白虎公陈侨将兵号三十万,与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阳”[1]642。更始政权在河南布置重兵,防范的对象主要有两个:一是兴起于齐地的赤眉军,二是活动于河北的刘秀。更始二年冬,赤眉军“入颍川,分其众为二部”,其中一部“拔阳翟,引之梁,击杀河南太守”。按说势头不错,赤眉军似可进一步攻取河南,但他们的选择却是兵分两路,一路“自武关”,一路“从陆浑关”,“两道俱入”,直捣关中,绕开了河南[1]479。建武元年(25年),刘秀定都洛阳,乃是更始政权的洛阳守将朱鲔“悉其众出降”的结果[1]655。
综上,两汉之际的河南基层社会并没有在改制与动荡之中受到太多的触动,这使得地方强宗豪族仍然能够维持其发展的自然脉络。
二、东汉前期河南区域治理的两面政策
东汉政权建立伊始,首要任务是平定各方割据势力,服务于统一事业,京畿地区尤其需要保持稳定。因此,光武帝刘秀并不敢大刀阔斧地重构河南的地方秩序。
当时,颍川人丁綝因“从征伐”,“将兵先渡河,移檄郡国,攻营略地,下河南、陈留、颍川二十一县”,军功显著,遂于建武元年被任命为河南太守[1]1262。以军功人士控制河南,只是从更始政权手中夺得河南之后的权宜之计,并不利于长治久安。因为军管式地方治理起效很快,但亦有缺陷。比如,“将军萧广放纵兵士,暴横民间,百姓惶扰”。河内人杜诗当时职为侍御史,负责“安集洛阳”,见此情形,“勑晓不改,遂格杀广”。刘秀得知此事后,“召见,赐以棨戟”[1]1094,对杜诗深表赞许。可见,刘秀十分重视维护地方社会的原有秩序,而军事色彩浓厚的管理方式有时反倒是一种障碍。
在短暂的过渡之后,刘秀改河南郡为河南尹,并选择乐安人欧阳歙为第一任河南尹。欧阳氏世传《尚书》学,至欧阳歙已为第八代,其人“既传业,而恭谦好礼让”[1]2555。刘秀任用这样的儒士治理河南,显然抱有不欲惊扰河南的意图。欧阳歙在职五载后,渔阳人王梁因“将兵征伐,众人称贤,故擢典京师”,继任为河南尹。虽以功臣任职,但王梁并无太多作为。他自建武五年上任,建武七年就左迁为济南太守,仅在位两年,其间见于记载的主要举措是“穿渠引谷水注洛阳城下,东写巩川”[1]775,与打击豪强、导民以德之事基本无涉。
然而,刘秀是不会无限期容忍横亘于国家与编户齐民之间的豪强势力的。建武十二年(36年),东汉政权消灭割据蜀地的公孙述,统一了全国。虽然“中央政权的力量推行到各处,但是地方性豪强的势力也并未消灭”[6]295。在稍事喘息之后,刘秀于建武十五年(39年),“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1]66,此举使地方官员进退两难,很多郡守、刺史选择向地方豪强妥协,“优饶豪右,侵刻羸弱”。尤为典型的是,因“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踰制,不可为准”,政治生活中甚至形成“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的潜规则[1]780―781。刘秀得知后大怒,“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非常之举促使地方官员积极执行诏命,但遭到了基层社会的强力反弹,“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所在,害杀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1]66―67。由此可见,东汉初年基层秩序的主导权在地方豪强手中,他们拥有大量的田产与依附人口,这一社会特点在河南并不例外,甚至比较典型。
尽管史书记载光武帝最终平定了地方上的乱局,但豪强主导河南基层秩序的局面并没有实质性改观,东汉政府仍不得不面对这一社会现实。只不过,经历了光武帝时期的激烈冲突,地方官员在强硬施政的同时,再一次体会到承认、维护强宗豪族利益的必要性。
广汉人郭贺于永平四年(61年)任河南尹,其人“能明法”,具有强硬的一面,但为治却“以清净称”,又体现出无为、不扰的柔性一面[1]908―909。永平五年,沛人范迁为河南尹,其曾任渔阳太守,“以智略安边,匈奴不敢入界”,此为能吏特质,然而,当他在河南尹任上被擢升为司徒时,升职理由却是“有清行”,即清廉自守,并非以善于控驭河南官属的能吏身份而获得升迁[1]941。明帝末年至章帝前期,汝南人袁安任河南尹长达10年,“政号严明”,“京师肃然”。但他也有柔性举措,“未曾以臧罪鞠人。常称曰:‘凡学仕者,高则望宰相,下则希牧守。锢人于圣世,尹所不忍闻也。’”[1]1518所谓“学仕者”,其家族大多数应有一定的经济、文化背景,袁安对这些人的经济犯罪概不追究,个中因由除了“不忍闻”之外,对辖区内的豪强加以笼络也应当是其内心更为隐秘的意图。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地方豪强在基层社会的广泛存在,属于东汉时代全国性的普遍问题,因此,东汉政府对河南地区的豪强势力实行既限制又笼络的两手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时代共性的体现。但河南毕竟不同于其他地区,它是帝国的政治中枢,牵一发而动全身。就这个角度来说,东汉的河南治理绝非单纯的地方行政,其全局意义甚为明显。与此相应的是,东汉政治生活中所呈现的结构性问题,也势必以高于其他地区的力度传导在对河南的管控上。
三、东汉权力格局与河南区域管控
众所周知,在东汉的皇权政治中有三大政治势力,集知识分子、官僚两重身份于一身的士人群体是其一,此外还有外戚、宦官。不过,这三大势力的发展步伐并不一致。士林在汉光武帝时期因“退功臣而进文吏”的用人导向而兴起,外戚至汉章帝时期开始深度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宦官是在章帝之后的和帝时期才开始崭露头角的。可以说,在东汉大多数时段,士人是管控河南地区的主要角色,但外戚、宦官势力对河南的区域管控造成了很大干扰。
对于外戚来说,施压于河南尹,进而获得其支持,是他们攫夺权力的一个重要途径。比如,外戚窦氏在章帝时期即已非常跋扈,章帝死,和帝继立,章帝窦皇后升格为皇太后,窦宪“内幹机密,出宣诰命”,诸兄弟“皆在亲要之地”[1]813。当时,为窦氏擅权张目者即有河南尹。《后汉书· 袁安传》记载,司徒袁安曾“奏司隶校尉、河南尹阿附贵戚,无尽节之义,请免官案罪”。李贤注引《续汉书》曰:“安奏司隶郑据、河南尹蔡嵩。”[1]1519据此,蔡嵩为支持窦氏的河南尹,持此立场,或许有个人操守的因素,但窦氏的势力与压力必定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汉顺帝时,河南尹田歆曾对外甥王谌说:“今当举六孝廉,多得贵戚书命,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尔助我求之。”[1]1826所谓“贵戚书命,不宜相违”,指的就是外戚施压的情形。
但有的时候,对河南尹以威势相压并不一定奏效。在此情形下,安插政治代理人担任河南尹便成为外戚的进一步选择。《后汉书· 乐恢传》记载:“是时河南尹王调、洛阳令李阜与窦宪厚善,纵舍自由。恢劾奏调、阜,并及司隶校尉。”[1]1478李贤注引《袁山松书》说:“河南尹王调,汉阳太守朱敞,南阳太守满殷、高丹等皆其宾客”[1]1518―1520。由此可知,窦氏曾安排与己“厚善”的宾客掌管河南。此犹不足,遂有大量以外戚身份直接出任河南尹者。比如:汉安帝时期,太后邓氏之兄邓骘辅政,遂以从弟邓豹任河南尹[1]617;汉顺帝时期,皇后梁氏的兄弟梁冀、梁不疑先后担任河南尹。桓帝时期,梁不疑被免,又由梁冀之子梁胤接任该职[1]1178;梁氏诛灭后,桓帝又任命皇后的从父邓万世为河南尹[1]445;灵帝时期,皇后何氏的兄弟何进、何苗亦先后担任河南尹[1]2246,等等。
外戚如此,那么宦官又是如何影响河南的呢?有学者指出:“在东汉,由于外戚和宦官对国家事务的干预,他们多将其亲信、亲属和子弟选任为河南尹”,目的“只是试图牢牢控制河南尹这一职务,为他们的政治集团服务”[7]61。从之前的分析来看,东汉外戚“试图牢牢控制河南尹这一职务”在理念与实践上都是有据可查的。我们相信,宦官势力定然也有这样的企图,但在实践上并不是很显著。在目前的史料中,尚未见到宦官子弟担任河南尹者,然而,有的河南尹的确与宦官走得很近。比如汉灵帝时代的凉州名将段熲,因平定羌乱有大功,回京后“转执金吾河南尹”,最终做了太尉。仕途如此顺遂,其原因在于“熲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贵”[1]2153。这样的选择与有的士人投靠外戚一样,也是慑于权势。在宦官势力最为强盛的桓灵时代,有所谓宦官“五侯”。值得注意的是,五侯之中有两个来自河南——“单超,河南人”“左悺,河南平阴人”[1]2520。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认为宦官弄权对河南的区域治理毫无影响,恐怕是不符合实际的。
在宦官最盛的时期,朝廷的河南尹人选往往具有强烈的反宦官倾向,有很多人实际上就是后来的党人名士。比如:冯緄为河南尹,主张“中官子弟不得为牧人职”[1]1284。颍川人李膺为河南尹,当时河内人张成“以方伎交通宦官”,“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李膺“竟案杀之”。张成的弟子牢修“因上书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宦官乘机煽风点火,由此发起了对士人的大规模迫害[1]2187。颍川人杜密在地方任职时,“宦官子弟为令长有奸恶者,辄捕案之”,后来他担任了河南尹[1]2198。中山人刘祐为河南尹时,“权贵子弟罢州郡还入京师者,每至界首,辄改易舆服,隐匿财宝,威行朝廷”[1]2199。泰山羊陟任尚书令时,因太尉张颢等多位公卿“并与宦竖相姻私,公行货赂”,因而对他们进行弹劾,桓帝虽然没有采纳,但“帝嘉之,拜陟河南尹”[1]2209。
党人名士控制河南,对宦官势力的扩张当然是一种有力的牵制。在清除宦官的关键时刻,河南地区的控制权更为士人、外戚联盟所关注,所选必为大力反宦官者。比如:灵帝即位之初,陈蕃、窦武谋诛宦官,即请党人刘祐出山,第二次担任河南尹[1]2199;灵帝死后,袁绍、何进又欲诛宦官,遂安排太原人王允为河南尹,而王允早年曾在家乡捕杀宦官赵津,又曾得罪十常侍之一的张让[1]2172,与宦官矛盾甚深。与外戚、士人用反宦官者为河南尹相比,宦官为求得自身的生存,在政变过程亦可能会考虑更置河南尹。比如,何进诛宦官不成而身死,宦官旋即矫诏罢免王允,而以少府许相为河南尹。
四、东汉政治博弈对河南文化发展的影响
士林、外戚、宦官三大势力对河南地区控制权的争夺,深刻影响着东汉河南的文化发展。笔者在这里主要谈两个问题:一是东汉河南少党人的现象,二是东汉河南文化生态的复杂性。
先看东汉河南少党人的现象。如果仔细观察范晔《后汉书· 党锢列传》所列人物的籍贯,我们不难发现,河南周边的南阳、颍川、汝南三郡,是盛产党人名士的地方。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党人散见于其他传记中。有学者对此做过全面统计,最后的结论也是“汝南、颍川、南阳三郡豪族党人最多,在两次党锢之祸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1]289。与此构成极大反差的是,东汉王朝政治中心所在的河南本地,却显得很平静。何以如此?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必须知道三郡党人发挥其影响力的根本因素是什么,然后再看河南是否具有相同的条件。有学者指出,三郡士大夫只有“深深植根于地方宗族、乡党、士林广泛而坚固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政治气候”[8]135。不过,这种以宗族、乡党、士林等纽带结成的人际关系,会损害皇权的至尊地位。
在党锢之祸酝酿过程中,有个情节很值得关注。当时“汝南太守宗资任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又为谣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1]2186民谣所反映的舆论耐人寻味:郡太守由皇帝委任,代表国家权力,然而,到任之后,其权力却被本地出身的吏员架空,这是对国家权力的公然挑衅。后来,范滂、岑晊被列为党人,命运悲惨。客观地来说,宦官中伤他们,皇帝惩罚他们,也不是毫无缘由的。在宦官、皇帝眼中,劫夺国家权力,正是党人的罪责所在。而乡里人物之所以具有这样的能量,恐怕也不仅仅是学问大、风节高的问题,他们的背后应当是活跃于基层社会的宗族势力,他们本人即是地方豪强的代表。
由范滂、岑晊的事例来看,地方豪强的存在是育成党人名士的重要前提条件。河南地区是不乏强宗豪族的,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官方对河南的治理风格就已凸显出了这一点。与汝南、南阳豪强相比,东汉河南地方豪强的力量显然没有达到实际控制河南的程度,但这并不是说河南地区的豪族势力在绝对力量上弱于汝南、南阳。实际上,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河南地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造成的。作为京畿,无论士林、外戚,抑或是依傍宦官者,只要担任了河南尹,那就必定在施政过程中面临着来自中央机构甚至皇帝本人的压力。这种压力在其他郡国也有,但对河南尹而言,治理成效的考课所造成的压力往往是最大的。因此,士人任河南尹,虽然有时会向地方豪族表示妥协,适当照顾其利益,但河南地方豪族要想架空河南尹,那是不可能的。至于外戚、宦官支持者主管河南的时期,那些被拉拢的地方豪族,自然在道义上已不具备成为党人名士的资质,而那些疏离外戚、宦官的士人,河南尹更不可能放任他们操控地方政治。
接下来,我们讨论复杂权力格局对东汉河南区域文化基本面貌的影响。党人名士稀缺是东汉河南区域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但这并不代表这一时期的河南就是文化荒芜地带。事实上,东汉时期河南虽然没有出现弘农杨氏、汝南袁氏那样典型的以儒学入仕进而累世公卿的家族,但河南儒学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就。比如:东汉初年,緱氏人孙堪,“明经学,有志操,清白贞正,爱士大夫”[1]2578;桓帝时期,有成皋人屈伯彦,后来的人才评鉴大家太原人郭林宗曾师从之,“三年毕业,博通坟籍”[1]2225,由弟子观其师,屈伯彦应当也是一位“博通坟籍”的人;灵帝时,荥阳人服虔“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学受业。有雅才,善著文论,作《春秋左氏传解》,行之至今。又以《左传》驳何休之所驳汉事六十条”[1]2583。
然而,相对于东汉200年的历史而言,上述几个大儒难免显得孤单。有学者指出,东汉时期“河南地区的学校教育最为发达,洛阳设有全国的最高学府——太学,各郡国的官学、私学也极其兴盛,学校考试更加系统化”[9]147。这个描述是符合实际的。不过,河南地区,更具体地说是洛阳,汇聚了全国范围内最有学识的高级官僚士大夫,太学容纳了全国范围内资质最为聪颖的知识分子,这只能说明京畿是一个国家级的政治、文化舞台。客观地来看,对优质人才资源的吸纳能力并不代表区域文化的本质,河南区域文化究竟处于怎样的水准,还要依据当地人才产出情况来加以说明。
在东汉河南儒学的发展历程中,开封的郑氏家族值得特别关注。西汉晚期,开封人郑兴“尝师事刘歆”[1]936,“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遂积精深思,通达其旨,同学者皆师之”[1]1217。由此可见,郑兴的学术水准很高。东汉初年,郑兴官至太中大夫,其子郑众“从父受《左氏春秋》,精力于学,明《三统历》,作《春秋难记条例》,兼通《易》、《诗》,知名于世”,“受诏作《春秋删》十九篇”[1]1224。后来,郑众官至大司农。郑众之子郑安世“亦传家业”[1]1226。郑众曾孙郑太“少有才略”,“名闻山东”,官至议郎[1]2257。郑太之子郑袤“少孤,早有识鉴”,曾为临淄侯文学②。从郑兴到郑袤,共六代人,除了第四代未见记载,第三代不知官位外,其余皆有名有官,已粗具累世通经入仕的家族特征。但是,开封郑氏与弘农杨氏、汝南袁氏相比,其发展程度毕竟还有不小的差距。郑众是其中职位最高者,但大司农秩级为中二千石,亦不过为九卿,郑氏家族还远未达到累世公卿的高度。
与仕途平淡无奇的经学世家构成鲜明对比的是,东汉河南并不乏学术背景不甚明晰却位至三公者。目前史料所见担任东汉三公的河南人士有庞参(太尉)、尹睦(司徒)、尹颂(太尉)、吕盖(司徒)、吴雄(司徒)、陶敦(司空)、种暠(司徒)、种拂(司空)、孟(太尉)。一般而言,对于那些仕至高位者,如果其具有浓厚的儒学背景,史家往往会在传记中专门叙述,如范晔记弘农杨震“受《欧阳尚书》于太常桓郁,明经博览,无不穷究”、汝南袁安“习《孟氏易》”等。但上述河南士人为三公者,大多语焉不详。其中尹睦、尹颂是同一家族的人,种暠、种拂是父子关系,与郑氏家族历代仕宦的情形具有较强的可比性。据记载,尹氏出自河南巩义,履历不详,只知其“家世衣冠”[1]2208,含义不明确,不知是否因儒术而世代为官。种氏出自洛阳,种暠以孝廉入仕,所担任的多为“主刺举”、主治边、主军政的职官,种拂“初为司隶从事”,亦主纠察[1]1829。由此观之,种氏父子似乎并非以经学高明而显贵。当然河南籍三公之中也有学术背景鲜明的特例,顺帝时代的吴雄“以明法律,断狱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非但如此,“及子訢孙恭,三世廷尉,为法名家”③。吴氏家族以法律之学而三世显赫,与通经入仕的儒学世家更是大异其趣。
经学家族仕宦遭遇瓶颈,学术背景模糊者往往位至三公,这反映了东汉河南区域强宗豪族的经学化进程与官僚化进程并没有实现深度融合。之所以会呈现这样的特征,一方面是因为治理河南的压力很大,管控相对严格,经学家族想要在本地形成盘根错节的势力,并进而攫取更高层次的政治权力,难度较大;另一方面也与东汉政治的基本权力结构有很大关系。士林、外戚、宦官都有掌控河南为本政治集团服务的欲望,后两个政治集团因其特定的立场,自然不愿重用河南豪族中的经学世家,这无疑会阻碍河南经学家族的官僚化进程。
“光武帝的建国,是地主政权即豪族政权的确立”,故光武帝本人对豪族“半推半就不即不离”。这是“开明君主所必须采取的”,但“开明君主不能常有”。于是,待东汉政权传承两三代后,权力落入外戚宦官手中,整个社会便“转入豪族自由支配时期了”[10]10。对这个历史判断而言,河南区域控制的演变过程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微观而具体的实例。在光武帝执政的大多数时段,乃至整个东汉前期,河南区域治理的策略都是承认豪族利益的。而东汉中后期,士林、宦官、外戚对河南控制权展开激烈争夺,这其实是东汉不同类别的豪强在博弈。尽管皇帝本人以维护皇权为目的打击文化豪族,但仍逃脱不了为另一类豪强利用的历史命运。
注释:
①这里所用“河南地区”的概念,其地域范围远小于现代的河南政区,大体上局限于西汉河南郡、东汉河南尹所辖。
②见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44“郑袤传”。另外,同书卷33“郑冲传”也记载,“郑冲字文和,荥阳开封人也”,“起自寒微,卓尔立操,清恬寡欲,耽玩经史,遂博究儒术及百家之言”,“及魏文帝为太子,搜扬侧陋,命冲为文学”。从郑冲为开封人看他有可能是郑兴后裔,然而郑冲“起自寒微”,又不大像郑兴后裔,暂存疑。
③见《后汉书》卷46“郭躬传”。《水经注》卷24“睢水”条记载,太尉桥玄冢列数碑,其中一碑为“故吏司徒博陵崔列、廷尉河南吴整等”“共勒嘉石”。从吴整籍贯、官职看,似亦为吴雄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