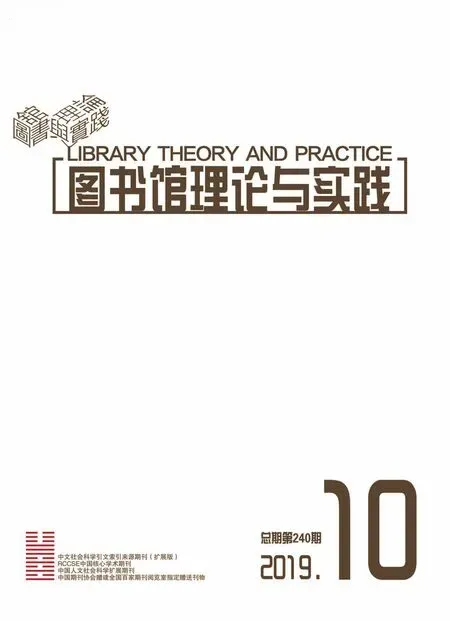目录学视域下的地域总集范畴辨析
2019-01-19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与法学院
夏 勇(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与法学院)
本文所谓地域总集,或称地方性总集,即着眼于某一区域而采收作者作品的总集。传统目录学多名之为“地方艺文”“郡邑之属”等。其编纂活动正式发轫于唐,勃兴于宋,发展于元明,至清代乃臻于繁盛。
随着数量的增加,晚明时地域总集乃被目录学家聚合起来,成为集部总集类下的一个专门类目。如《徐氏家藏书目》于总集类下设“总诗类·各省”之类目,祁承《澹生堂藏书目》于总集类下设“郡邑文献”之类目。该方式被后世广泛继承,尤其20 世纪以来,各家书目往往在总集类下列出专门类目,以容纳相关总集。
虽然地域总集已成为专门类目,但如何界定其范畴,却至今未有比较确切的表述。现有书目著录它们时,每每体例不一甚至混淆错乱。本文力求在目录学的视域下,提供一个明晰的关于地域总集范畴的方案,为研究者更好地认知它们打下基础。
一、循名责实:“郡邑”还是“地方”
考察地域总集的范畴,首先需厘清的是命名问题。
晚明以来地域总集的类目命名方式主要有两种:一则名之为“郡邑”;二则名之为“地方”。前者可追溯到《澹生堂藏书目》,该书在总集类下设七个类目,其一即“郡邑文献”。后世的《中国丛书综录·子目》《中国古籍总目·集部》《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山东文献书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 等均沿袭“郡邑”之名。后者可追溯到清沈初等《浙江采集遗书总录·辛集》,该书分总集类为“总集类一”与“总集类二”两部分,“总集类二”标题下有“以地为次”之标注,[1]集中著录地域总集。此后,孙殿起《贩书偶记》于总集类下设“地方文”“地方诗”之类目,傅增湘的《藏园群书题记》《藏园群书经眼录》、王重民的《中国善本书提要》以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等则均设“地方艺文”之类目。
从现代语言学的观点来看,若某一名称同它实际指涉的事物间建立起约定俗成的联系,则以之为相关事物的类名,自是顺理成章。“郡邑”与“地方”虽然名号不同,但都被作为地域总集的代称,所以某种程度上亦可作如是观。
不过若严以绳之,“郡邑”与“地方”的概念还是有区别的。“地方”是一个颇为宽泛的概念,不论自然地理地域,还是行政区划,也不论涵盖数省的大区域,还是乡里村镇这样的基层区域,均可以“地方”指称之。反观“郡邑”,则有其特定含义,涵盖面相对较狭。
具体来说,邑的本义是人聚居的地方,后用为县的别称。柳宗元《封建论》 云:“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2]郡邑即郡县之谓。史称秦始皇分天下为若干郡,每郡辖若干县,是我国早期的郡、县二级行政区划体系。随着我国疆域的扩大、中央政府对国土统治的深入,相对扁平的二级体系日益不敷使用,至东汉末,乃正式形成州、郡、县的三级体系。州取代郡,成为新的第一级行政区,郡、县则相应降级,此后,我国行政区划体系屡经变迁。汉代的州先后演变为唐代的道,宋代的路,元代以来的行省、布政使司等;郡先后演变为唐宋的州及宋代以来的府等,但无论如何,仅以“郡邑”或“郡县”二字,难以囊括各种区域概念。一方面,郡县二级制只在秦代以降的有限时段内施行,大抵包括秦、汉、隋三代与唐代前期;而地域总集编纂却恰恰要到唐代中期才正式发轫。可以说,地域总集编纂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国实行的都是三级行政区划制度。再就地域总集的实际情况来看,除面向“郡”和“县”的总集外,明代以来还产生了大量面向一省的总集,如,明杨慎辑四川诗文总集《全蜀艺文志》,清许玉彬等辑广东词总集《粤东词钞》,民国年间林传甲辑黑龙江诗总集《龙江诗选》等。这些省级总集与“郡县”概念之间,显然圆凿方枘。另一方面,郡县制指涉的是各级行政区,而地域总集却还包含一批面向非行政区,亦即自然地理地域者。如,清邓显鹤辑《资江耆旧集》,收人辑诗即“以资水发源、经过、归受之地为断”,[3]乃一部面向湖南资水流域的总集,而无法归入当时湖南辖下的任何一个行政区。
由此可见,地域总集实际面向的区域类型颇为复杂,一则涵盖至少三级行政区,再则也包括自然地理地域,这就并非涵盖面相对狭窄的“郡邑”概念所能囊括的。名称应尽可能让人清晰了解相关事物的属性。虽然“郡邑”在不少书目中就是指代地域总集,但最好还是使用一个能更贴切地表现事物属性的名称,以更好地达到名实相符。因而笔者认为,以较宽泛的“地域”或“地方”概念来指称它,是更加合适的。
二、地缘特质及其首要性与双重性
将地域总集的范畴问题落实到目录学的具体操作层面,主要是如何合理区分地域总集与其他类型总集。关键环节有二:一是地域总集的特质;二是区域范围的上下限。
先看前者。显然,地域总集的特质就是着眼于一片区域,是基于地缘属性而成立的典籍类型。但如何认知地缘属性,并将它与其他属性清晰切割,却并非一目了然,无需辞费。我们也由此看到,现有书目著录相关类型总集时,每每存在不当或有出入之处。例如:
《贩书偶记》“总集类·地方诗之属”著录的清盛谟等撰《豫宁三盛诗》 与阮元辑《山左诗课》,前者实为宗族总集,应归入该目“家集之属”;后者的性质与该目“课集之属”著录的清江标辑《沅湘通艺录》等书一致,都是地方学政考课士子的产物,可视为课艺总集。
《贩书偶记续编》“总集类·地方诗之属”著录的清王原辑《于野集》,虽然作者大都来自当时的江苏松江府,但实为一部唱和总集,应归入该目“唱和题咏之属”。
《中国丛书综录·子目》“总集类·郡邑之属”著录的谭新嘉辑《碧漪集》《续集》《三集》 系列,实为一部明清嘉兴谭氏家族诗文总集,应归入该目“氏族之属”。
《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总集类·郡邑之属”著录的清桂超万等辑《青山诗选》、陈銮辑《薲洲闻咏集》等,与该目“唱酬之属”著录的众多总集性质相同;清阮元辑《山左诗课》、陆宝忠辑《沅湘揽秀集》等,亦与该目“课艺之属”著录的《沅湘通艺录》等性质趋同;清李调元辑《粤风》、吴湛辑《粤歌》①均为广西歌谣总集,与该目“谣谚之属”著录的清赵龙文辑《猺歌》、吴代辑《苗歌》、黄道辑《獞歌》②等广西歌谣总集性质相同。
《岭南文献综录》“总集类·地方艺文”著录的清陈士规等撰《莲山家言》、王定镐辑《三渔集约钞》,以及周大樽辑《法性禅院倡和诗》、李长荣等辑《庚申修禊集》等,前二者应归入该目“家集”部分,后二者则应归入“唱酬题咏”部分。
上述现象之所以屡见不鲜,部分原因在于编目者未细审原书、分类失误乃至体例未甄详备;而另一重要原因则是各类型总集确实往往含有地缘因子。以宗族与唱和总集为例。前者由于古代宗族多以聚居地为依托,加之相关总集亦常冠以地区名号,如明董应举辑《眉山苏氏三大家文选》等,故或被“视为地方类(总集)的进一步深化”。[4]后者由于唱和活动多发生于某一区域,甚至专以该区域内人士为参与主体,事后形成的总集亦每每冠以区域名号,如唐皮日休等撰《松陵集》等,遂屡被纳入地域总集的范畴。
任何文化活动都在地缘空间内展开,相关类型总集含有地缘因子自不足怪,但我们不能仅据它们含有地缘因子这一点,就定性其为地域总集,因为这势必导致地域总集之范畴泛滥无边,同时也会影响书目分类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功能的实现。
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在于厘清相关类型总集的属性结构。考察各类总集所收作者作品,往往具备多元属性。即就地域总集来说,便时常可以从中解析出宗族、唱和、闺秀、方外、谣谚等属性因子。如,清马长淑辑《渠风集略》 着眼于收录历代山东安丘人作品,但卷五“专辑马氏一家诗”;[5]清陈增新等辑《柳洲诗集》 着眼于收录明末清初浙江嘉善人作品,其中“取同人倡和之作为多”;[6]至于在书末排列闺秀、方外、谣谚专卷,更是历代总集的通例。在《渠风集略》等总集的诸多属性因子中,占首要位置的显然是地缘,而宗族、唱和等则悉数只是次要属性,这是我们定性其为地域总集,而非其他类型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拥有地缘属性只是确认地域总集之范畴的充分条件,此外还需配合以必要条件,即地缘属性乃相关总集的首要特质。
基于该充分必要条件,地域总集与若干其他类型总集即可得到清晰区分。如宗族总集虽具备地缘属性,但只是处于次要位置,其首要特质乃亲缘、族缘属性。这使之与地域总集的差别相当明显。又如唱和总集的首要特质在于它是集会、唱和活动的产物,编者的目的侧重于将相关活动之过程反映出来,将创作实绩保存下来;至其地域色彩,则往往是因相关活动的具体地点而造成的附带效果,并非编者主动追求之故。更何况,诸如全国、宗族、唱和、题咏等类型总集,均特征鲜明、为数众多,堪称历代总集的主类;且其渊源均可追溯到唐代,甚至是两晋南北朝,可谓和地域总集同样古老,甚至是更加古老的总集类型。因此,它们完全有资格也有必要同地域总集划清界限,自成一类。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地缘特质及其首要性这一充分必要条件尚非确认地域总集范畴的万能钥匙。面对纷繁复杂的客观事物,简单的硬性标准往往难以贯彻始终,而须根据实际情况变通折中。就全国、宗族、唱和、题咏等类型而言,大体可以明确其与地域总集的分野;而就课艺、谣谚、闺秀、方外等类型来说,却存在一些不易同地域总集斩截切割的特殊地带。
即如专收与考试有关之作品的课艺总集,其中的地方官员测士部分,便与地域总集关联颇深。我国古代有专人负责考课某地士子,如,北宋于各路设提举学事司,负责所属州县的学校和教育事务;金代的提举学校官、元明的儒学提举司与之类似;清代各省多设督学道,长官称提督某省学政,简称学政。诸如提学、学政等承担教育职能的地方官员,任职期间须定期巡视所在辖区,考课当地士子,从而留下大批课艺作品,这就为自明代起,特别是清代大量涌现的面向某一地区的课艺总集奠定了制度基础。以清代山东省为例,便至少有冯誉骥、陆润庠、黄体芳各自编纂的三部《山左校士录》、姚丙然辑《山左校士编》、李企澍等撰《山左试牍存真编》、尹铭绶辑《齐鲁讲学编》与前及《山左诗课》等传世,大抵均出自时任山东学政之手。此外,如,清范寅辑《越谚》、黄任恒辑《粤闺诗汇》、佚名辑《滇释诗稿》等谣谚、闺秀、方外总集,同样立足于某一区域而采收作者作品。
上述《山左校士录》《滇释诗稿》 等,可谓具备双重属性。就其作品内容、形式与作者身份来说,归入课艺、谣谚、闺秀、方外类顺理成章;而就其采收范围限于一隅而论,又确乎具备地域总集之实。对于这些特殊形制的总集,若相关书目未设课艺等类目,自然可以直接归为地域总集;若设立了相关类目,则不妨基于它们乃由若干小类构成的特点,在其内部将相关小类划分开来,依次著录。如闺秀总集,尤其清代的闺秀总集,内部便可划出全国、地域、宗族、唱和、女弟子等多个小类,如,黄秩模辑《国朝闺秀诗柳絮集》、前文提到的《粤闺诗汇》、李心耕辑《二余诗集》、任兆麟辑《翡翠林闺秀雅集》、袁枚辑《随园女弟子诗选》等。这既反映出清代女性文学的高度繁盛,又承载了当时地方与宗族女性文学群体、女性集会唱和活动、女弟子群体层出不穷等现象。书目分类的功能并非止于检索,而是具有学术认知的重大意义。这种在大的类名下进一步分小类著录的方式,既有利于凸显相关大类下的地方性小类,同时对于我们认知其内部形态及相关文化现象,也是颇有裨益。
由此可知,地域总集应由两大板块构成。其一以地缘属性为首要特质,容纳某一区域的各类型作者与作品,可谓典型的地域总集。其二则具备双重属性,即:地缘属性既十分突出,同时又面向特定类型的作者(如闺秀、方外人士) 与作品(如课艺、谣谚作品),可谓特殊形制的地域总集。
三、区域范围上下限及其他
既然地域总集的特质乃是着眼于一片区域,则考察“区域”本身的某些属性,自然有助于我们认知其范畴,关键在于“区域”范围有多大,亦即其上限与下限何在。
(1)先看下限问题。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区分地域总集与题咏总集。地域和题咏是历代总集的两个主要类型,但在不少书目中,二者却没有清晰的区分。尤其若干着眼于题咏某处景观的总集,往往被划为地域总集。如,《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总集类·郡邑之属”著录清黄肇颚辑《崂山艺文志》、沈槱元辑《柯园十咏》、曹尔堪等撰《平山堂诗词》、祁寯藻等辑《方山艺文志》等;《中南、西南地区省、市图书馆馆藏古籍稿本提要·馆藏钞本联合目录》“总集类·郡邑之属”著录清陈焯辑《道场山归云庵题咏》、徐敏辑《集古今名人游览太华山诗纪》《续刻》、民国方树梅辑《龙泉观诗文录》等。究其实际,这些总集更应列入二目的“题咏之属”。
欲厘清两类总集间的纠葛,首先须界定“地域”概念的内涵。笔者认为,地域总集所谓“地域”,应是人类社群成规模地开展生产生活的一片区域,人们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地缘划分,实现地缘认同。如,清严如熤辑《山南诗选》面向的陕南地区,王豫辑《江苏诗征》、顾沅辑《吴郡文编》、周铭辑《松陵绝妙词选》面向的清代江苏省、苏州府、吴江县,便都是这样的区域。与之伴生的,则是陕南人、江苏人、苏州人、吴江人等标示地缘身份的概念。
从该定义出发,可清晰辨认出若干题咏总集与地域总集的差别。其一,对于《崂山艺文志》等面向自然山川的总集来说,这些山川本身既不易成规模地开展生产生活,又难以内生出成规模的人类社群,更难以产生基于地缘认同的社群概念。实际上,它们大抵只是作为自然景观而得到文人题咏,进而形成总集。其二,对于《柯园十咏》等面向亭台楼阁、园林宅第的总集来说,相关对象或为地图上的一处点状建筑,或虽占有一定区域,但面积过于狭小、功能过于单一,不足以内生出人类社群,更无法以之为基础实现地缘划分与认同,因此终究只能作为人文景观而接受题咏。
将面向某地之自然山川与人工建筑的总集,尤其是后者,从地域总集剥离后,由此衍生出的问题便是:欲符合“地域”概念之内涵,则地域总集的区域范围下限究竟何在?这可以从我国古代的基层社会组织与地域总集的实际情况两方面来看。
我国古代最低级别的行政区是县,其间存在县与城的分野。城即县城,是秦代以降的国家基层权力所在地;县则指包括城市及城外农村地区的整个县域。县以下,古代虽未设置正式行政区,但驻扎县城的基层权力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乡村地区实施了有效治理。早在战国秦孝公时,即将全国人口编为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的单位,又“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7]形成县下有乡聚、乡聚下有什伍的基层社会体系。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将该体系调整为乡、亭、里的三级治理模式。此后,这种模式为很多朝代所实行,包括北周的党、闾、里,宋代的牌、甲、保,明清的乡、都、里或乡、都、村等。诸如乡、里、村等概念,即古代实现地缘划分与认同的基层区域单位。
反观地域总集的实际情况,清代以来也确实产生了众多面向乡、里、村等地缘单位的总集。如,文汉光等辑《古桐乡诗选》所谓“古桐乡”,指清代安徽桐城县辖下的北乡,该乡“北与舒城接界,南至朱家桥,东与庐江接界,西至石井铺,广袤几及百里”;[8]李光基辑《梅里诗钞》、李维均辑《梅会诗人遗集》、李稻塍等辑《梅会诗选》、许灿辑《梅里诗辑》、沈爱莲辑《续梅里诗辑》《梅里词辑》等,均面向清代浙江嘉兴县城南三十余里的梅里(又名梅会里、王店);管鑅辑《桂村文录》、何兆麟辑《桂村诗钞》 等,均面向清代江苏常熟县辖下的桂村。在基层权力中心——县城方面,清代同样产生了面向城内或城内外某片区域的总集。如,赵时敏辑《郭西诗选》,面向清代浙江钱塘县城(亦为浙江省城与杭州府治所在地)之西部片区。编者自述其范围是:“城内自吴山至涌金门,城外自万松岭至涌金水门,统名曰郭西。”[9]汪隆燿辑《西郊诗存》 与之类似,所谓“西郊”,指清代江苏镇洋县城(亦为太仓州治所在地)之西部片区。
古代存在于广大农村的乡、里、村等,以及城市的某个片区,既是地缘划分与认同的最基层单位,又有《古桐乡诗选》等一批总集提供文献支持。其中体现的正是地域总集的区域范围下限,而不可与面向某处景观的题咏总集混为一谈。
(2)再看上限问题。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区分地域总集与全国性总集。
地域或地方乃相对于全国而言。同地域或地方性总集对应的,自然是全国性总集,只是名实之间往往难以严丝合缝,不少全国性总集所收作者的区域分布范围其实并不广,这就和地域总集产生了两重纠葛。
一是若干全国性总集的收录范围有所偏重。如,明李先芳辑《明隽》,凡含《燕赵集》《秦晋集》《齐鲁集》《河洛集》《淮扬集附江北藩献》《蜀集》六集,主要采收北方诸省人诗作,兼及西南的四川,而摒弃其余省份,这使它作为一部全国性总集自是颇有缺陷。但若视之为跨省的地域总集,一则区域范围未免太大,再则将华北、西北、西南诸省合为一个地区看待,又显得不合情理。地域总集面向的区域确乎可以涵盖数省,但若无清晰的标准加以限定,则区域范围难免泛滥,从而和全国性总集发生混淆。也就是说,地域总集需要一个区域范围上限,使之能和全国性总集明确区分开来。
笔者认为,该上限应由两条标准构成。① 涵盖数省的地域总集需有明确认定的区域着眼点;② 该区域必须是一片自然地理区域,而不能生硬拼凑。如,清李少元辑《吴楚诗钞》,意在收录吴、楚两地人诗作,完全符合第一条标准。所谓“吴楚”,指涉的是长江中下游流域诸省,视之为一片自然地理区域完全可行,因此,将该书归为地域总集亦顺理成章。至如《明隽》,则并不符合这两条标准,应归之于全国性总集。
仅解决区域范围上限问题,还不能将这两类总集彻底区分开来。因为二者间还存在另一重纠葛,即不少全国性总集所收作者集中于某地,如,清冯舒辑《怀旧集》,向来被归入总集类“断代”之属,③与《列朝诗集》《明诗综》等综合选本并列。然而细绎该书所收作者,均来自江苏常熟,这就和地域总集产生了更深的纠葛。
处理此种深度纠葛的简便办法,须视编者宗旨而定。对此,朱则杰主张,全国性总集可以包括“不曾明确表示限收某地区作家”[4]的总集,因而如“冯舒辑《怀旧集》,尽管所收作家均同出一县,但并非从搜罗地方作家角度出发”,[4]故亦可归为全国性总集。由此,我们便能反推出另一条准则:明确表示限收某地作家的总集,即为地域总集。如,清李夏器等辑《同岑集》,单从书名看,确乎可视为全国性总集。然而卷首李令皙序云:“《同岑集》 者,镌吾郡同人之诗,举景纯赠太真‘异苔同岑’之句以名其集者也。”[10]凡例第四款亦云:“一郡已分七邑。一邑之中,环聚城市者十之一,散处村落山泽者十之九。”[10]所谓“吾郡”,即清代浙江湖州府。可见编者有明确的区域定位,是则我们应尊重其意愿,把该书归为地域总集。④
四、结语
综上可见,目录学意义上的地域总集或地方性总集,是明确着眼于一片区域而采收作者作品的总集,是一种基于地缘属性而成立的典籍类型。只有地缘属性在相关总集的属性结构中占首要位置,才能将其归为地域总集,这当中又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地缘属性为相关总集唯一的首要特质;二是相关总集拥有双重的首要特质,地缘属性为其中之一。至于“区域”概念本身,一则它应是人类社群成规模地开展生产生活的一片区域,人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实现地缘划分与认同;再则它包括各级行政区域与自然地理地域两大类型。但不论哪一类型,都必须符合我们对地缘单位的实际认知,而不能生硬组装,符合上述限定条件者,自然可以纳入地域总集的范畴,不然即应据实归为其他类型。
[注释]
①所谓“吴湛辑《粤歌》”,实为“吴淇辑《粤风续九》”的误写。
② 赵龙文辑《猺歌》 而下三书,均为吴淇辑《粤风续九》的组成部分。
③《中国丛书综录·子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中国古籍总目·集部》等均著录《怀旧集》于总集类“断代之属”。
④《中国丛书综录·子目》即列《同岑集》 于总集类“郡邑之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