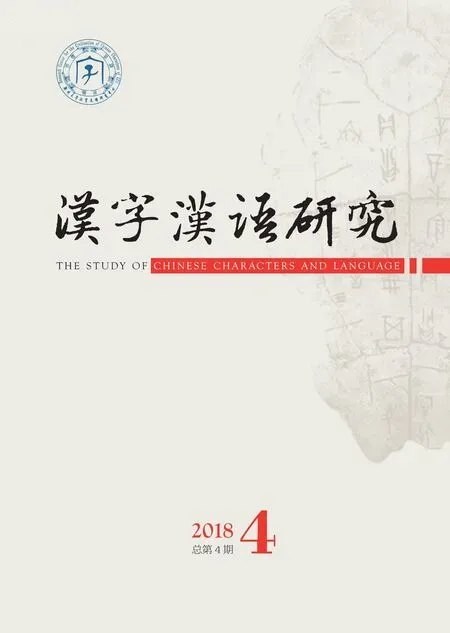汉字双重性质论纲
2019-01-17李如龙
李如龙
提 要 汉字作为汉语的语素兼有语言的性质是汉字能够长期使用、拒不拼音化的内部基因。汉字和汉语经过了千年的磨合,使汉语发生了类型的转变:产生声调,单音词占优势,放弃形态变化。汉字和汉语的互动决定了汉语发展的路向(双音化、语法化、连读音变),汉字的贯穿古今、沟通南北更为汉语和中华文化的统一做出了贡献。汉字拼音化运动的百年风云以及如何适应社会需求继续进行必要的改革尚待研究。
1.汉字和汉语研究中的悬案
关于汉字和汉语,从引进现代语言学的理论以来,一直存在着一些悬案,就二者的关系来说,有如下几点: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它的特殊性质究竟是什么?既然表音度不高,表意又很多样,形体古怪、笔画繁、字数多,难学难记,为什么能够沿用数千年?经过百年拼音化的冲击,虽制定过种种改革方案,也经历过艰难的试验研究,最后的结论还是“拼音化不可行”,于1986年停止了“拼音化改革”。支撑汉字的强盛生命力究竟是什么?
汉字不是简易灵便的表音符号,而是一面作为记录音节的符号,一面又是集形音义于一体的语素。民国初年,北大还用“文字学”来统括汉语研究和教学,以下再分为“音篇”和“形义篇”,为什么后来又要用第一性和第二性来区分汉语与汉字,把音、义划归汉语,只把形体留给汉字?如此把汉语和汉字强行分离,使汉语和汉字的研究分道扬镳、各行其是,这给汉字和汉语的研究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
汉语确有些“单音节”性(就中古以后的汉语看,应该是单音词为核心,双音词为基础),没有像西方语言那样用“形态”来表示语法意义;最基本的词类(名动形)没有断然的界限,虚词和实词在口语中常常兼用;语义关系和语用环境都对语法形式有重大的制约作用,字、词、语、句之间弹性十足,字可以成词、成句,词可以沦为语素,也可以离合和紧缩,惯用语可以用为“句套子”。为什么找不到语法的“本位”?汉语这种与众不同的词汇语法系统的结构特征,和它使用了表意汉字作为文字形式有没有关系?用落后的“孤立语”能够解释吗?
汉语历史悠久,分布地域广,使用人口多,为什么几经战乱和分裂,纷繁复杂的方言并没有变成不同的语言?尽管书面语和口头语早已分道扬镳,古今语言历经演变,浩瀚的历史文献为什么还能世代相传、维持民族文化的统一?我们如果能够正确认识汉语和汉字的关系,了解二者的互动和达到的和谐,也就能够理解汉语的诸多特征和汉字的多种特异功能了。
为什么古老的汉字经过百年的炮轰和清算还能顶得住?汉字拼音化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今后的应用又有哪些问题需要研究?
2.汉字具有文字和语言的双重性质
已知的世界上的文字都是从文字图画脱胎,而后按照表形—表意—表音的方向演进,这大概没有什么争议。汉字的“六书”也是从最初的“象形”发展成“指事、会意”(表意),最后走向“假借”(借音)、“转注”(半借音半借义)和“形声”(半表意半表音)。由形及意是从形象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由意及音是把意象和音感做对应的理解。汉字和拼音文字的根本区别在于造字法思维的综合和分析。汉字是形音义的综合,其实就是文字和语言的综合,“形”属于文字,“音义”属于语言;形音义之中,“形”是笔画与构件在方块中的综合,“音”是声韵调在音节的框架里的综合;“义”是言语运用中的初义、引申义、附加义的综合。拼音文字把音节分析为元音和辅音,用不同的字母表示,又根据实际语音的分析,用字母组成词语来表示相应的意义。可见,汉语汉字一开始就是综合的,绝大多数的“字”都有一定的音和义,都是词或语素,组成词语和句子之后,字音和字义还要在实际言语中再次进行综合,调整为词音和词义。正是“综合”,更离不开人的知性活动。早在1826年,德国语言哲学家洪堡特(2011:193-195)就有很精彩的见解:“汉字用单独的符号表示每个简单的词和复合词的每个组成部分,所以,这种文字完全适合于汉语的语法系统。也就是说,汉语的孤立性质表现在三个方面:概念、词、字符。”又说:“汉字必定强烈地(至少是频繁地)促使人们直接感觉到概念之间的关系,同时淡化了语音的印象。……在汉语里词源却很自然地具有双重性质,既跟字符有关,也依赖于词。……在中国,文字实际上是语言的一部分。”而拼音文字的字母就像汉字的笔画,本身只是不表意的字符,按照实际读音组成或多或少的音节才和意义挂上钩。文字表达语言是跟着语言的结构走的,因为文字只是语言的记录和随从,简明而有序。可见,东西方的文字和语言的不同关系正反映了不同的思维和文化的差异,洪堡特熟知印欧语,他应是西方语言学家对于汉语“旁观者清”的第一人。
2005年,周有光(2010:149-150)在他年至百岁时发表了《汉字性质和文字类型》,针对讨论多年的“汉字的性质”问题,提出了他的文字类型“三相说”。他的结论是:“现代汉字体系,从‘语言段落’看是‘语词和音节’文字(又称‘语素文字’);从‘表达方法’来看是‘表意和表音’文字(又称‘意音文字’);从符号形式来看是‘字符’文字。……多数人认为现代汉字是‘语素文字’。一些人认为现代汉字是‘意音文字’。这两种说法并非相互矛盾,而是相互补充的。分歧发生在,各自抓住一个方面的特征。前者以‘语言段落’为根据;后者以‘表达方法’为根据;两个方面的特征是同时并存、彼此说明的。兼顾各个方面,就能得到完整的看法。”乍一看,这好像是在“和稀泥”,其实是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断:汉字具有双重性质,作为记录语言的“表达方法”,是意音文字;作为“语言段落”,是语素文字。扣除表音字和联绵字,作为语素不就是汉语的最小语言单位吗?确实,只有兼顾这两个方面,我们才能对汉字的性质有完整的认识。
然而,研究汉字的名家早有把汉字局限于字形研究的提法。唐兰(1979:6)说:“……文字学本来就是字形学,不应该包括训诂和声韵。一个字的音和义虽然和字形有关系,但在本质上,他们是属于语言的。严格说起来,字义是语义的一部分,字音是语音的一部分,语义和语音是应该属于语言学的。”其实,字音和字义不但是语音、语义的一部分,而且也是汉字的主体,是随着语言的音义演变的,字典不就是跟着词典不断修订的吗?汉字正是兼用为语言的符号才和世界上其他的文字区别开来,成为独特的类型。后来,裘锡圭(2013:10)说:“如果不把文字作为语言的符号的性质,跟文字本身所使用的字符的性质明确区分开来,就会引起逻辑上的混乱。”“只有根据各种文字体系的字符的特点,才能把它们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对此,李运富等(2006)说:“构件的特点当然能反映汉字的属性,但为什么‘文字作为语言的符号的性质’就不是汉字的属性呢?为什么‘只有根据各种文字体系的字符的特点,才能把它们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呢?似乎很难说通。”应该说,汉字从诞生之日起,就是集形、音、义于一体的,为什么汉字独有的这种字符不是另一种类型呢?识字就是为了学话、读书、作文,传承与播扬文化,这是几千年的传统习惯,也是每个汉语人的经验感悟,就中国人的直感说,字形和字音、字义是不可拆分的,至于作为学术研究,不但形音义要区分,形还要分甲金文、篆隶楷草体,音还得分上古、中古和近现代,义也得分字义、词义、语法义、语用义,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1988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周祖谟(1988:160)所撰“汉语文字学”条,开宗明义就指出,文字学是“研究汉字的形体和形体与声音、语义之间的关系的一门学科”。谈到“文字学研究的内容”时,又再次强调“应当照顾到形、音、义三方面,因为三者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不能全然脱离音义孤立地去研究文字”。不知何故,三十年过去了,周先生的这一观点还没有被文字学界普遍接受。
汉字与汉语相结合、兼具语言的性质,是经过长时期磨合和积累的。从字形说,上文所说的由表形到表意又到表音就经历了千年。据李孝定(2011:68)统计,从甲骨文到按《说文》统计的《六书略》,“六书”数量及占比如表1所示:

表1 甲骨文至《六书略》“六书”数量及占比
可见,这千余年间,表形、表意的汉字(象形、指事和会意)占比从56.52%下降至5.99%,表音的汉字(假借和形声)占比从37.76%上升至92.47%。(转注未计,比例也不大)
汉字找到了“形声”制度,并用它来规整绝大多数的字形,这就意味着它获得了语言的功能,既能含糊地表示语音,也能记录思维劳动的成果,联系上下文并不难理解它所表达的意义,还能超越一定的时空,它就这样知足止步了。
事实上,认真地分析,作为单字的音义和作为语素的音义,虽然有时也不太好区分,但还是有明显界限的。单字的“形符”,从结构说,是由笔画或部件组成的方块形体;从字体说,有正体、简体和篆隶楷行草等书写体;而作为语素,则有另一套俗体、异体、古今字、方言字、错别字。单字的“声符”就是声旁(独体字大多也就是声符),作为词语里的字,则有多音字、异读字;作为语素的字音,则有正音、方音、俗读、误读、训读等。就单字的“义符”说,是部首、形旁和兼表意作用的声旁;而作为语素的字义则有本义、初始义、引申义、词汇义、语法义、语用义、修辞义(比喻、比拟、借代等)。以往因为没有认真地把单字和语素分开,两种相关而有别的 “形音义”也就一锅煮、混为一谈了,如果要把语言和文字彻底区别开来,这还是一项需要仔细研究的课题;如果把所有的“音义”都归了语言,汉字不就成了读不出音、想不起义的空壳儿了吗?
承认汉字的双重性是研究汉字和汉语的基本点,从这一点出发,汉语和汉字的研究应该有一番新景象,本文开头所提出的“悬案”也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这就是本文所要论证的主题。
3.汉字和汉语的磨合曾引起汉语的类型转变
语言有几十万年的历史,而最早的文字也只有几千年历史,这是可以肯定的。文字学界不同意“汉字有语言性能”的主要是研究古文字的学者。他们的理由之一是汉语和汉字的产生不同步,汉字产生以前的汉语已经无从查考,古文字很少记录口语,和早期汉语能否切合也难以论证。事实上,一百年来地下发掘了大量古文字,经过细密研究,从甲骨文到“隶变”千年间,汉字造字法的演变是,如上文所述,形符让位给义符,为了表音,先是“假借”,因为造成同音,又找到形声之路,便迅速扩展,形声制度的形成和汉字的定型是同步完成的。汉字之所以能神奇地兼备语言的性质,就是因为经过这千年的磨合。用方块形体的形声字记录上古汉语占大多数的单音词,两者是十分合拍的,这就是汉字和汉语的第一次和谐。
裘锡圭(2013:19)说:“有可能古汉字里本来是有念双音节的字的,但是由于汉语里单音节语素占绝对优势,绝大多数汉字都念单音节,这种念双音节的字很早就遭到了淘汰。”最早的甲骨文只是占卜的记录,当时的口语语料已经失传了,后来的“不律为笔” “风曰孛览”,以及《诗经》里大约占四分之一的叠音词、联绵词,都是一个字标注一个音,联绵词在秦汉之后逐渐少了,先秦歌谣里的联绵词可能是早期多音词的残存。这也是得到上古汉语研究证实的结论。
除此之外,数十年来汉藏语的比较研究也取得了多方面的进展。许多结论也证明了从远古汉语到先秦的上古汉语,确实发生过类型的演变。熟悉印欧语演变过程的高本汉(1931:26-27),在1923年出版的《中国语与中国文》一书中,谈到汉语的“单音节”和“无形态”的“最重要特性”后写道:“……并非亘古至今,都是这样的。中国语里‘音调’上几种特点还留下双音缀语根语词的遗迹,就是转成作用的附添语(指形态变化的语缀——引者注)的残痕……许多散文足以表示当时在人称代名词上,具有格位的形式变化。”他的结论是:“早先的学说把中国语分列为‘初等’的语言,以为他还未进到变形的阶级,这种学说恰好和真理相反。事实上,中国语正和印度欧洲语言演化的轨迹相同,综合语上的语尾渐渐亡失了,而直诉于听受者(或诵读者)纯粹的论理分析力。现代的英语,在这方面,或者是印欧语系中最高等进化的语言;而中国语已经比他更为深进了。”1926年,高本汉(1934:13-17)在奥斯陆的一次演讲中又进一步说明:“原始中国语也是富有双音缀或多音缀的文字,有些学者亦承认中国最古的文字形式中,还有这类的痕迹可寻。……中国文字的刚瘠性,保守性,不容有形式上的变化,遂直接使古代造字者因势利导,只用一简单固定的形体,以代替一个完全的意义。”“……在纪元前的时代,中国语的形式与声音,已经达到极单纯的局势;遂使其文字的结构,具有一种特别的性质,辗转循环,又影响于后来语言的发展,至深且巨……”这是他在百年前就有的先见之明。
关于汉语的声调,自段玉裁提出“古无去声”之后,黄侃倡“古无上声,唯有平上而已”,王力解释为“舒促长短”之分,上古汉语声调“由无到有”逐渐明确。对于四声的形成,周祖谟(1966:113)指出:“……以四声区分词性及词义,颇似印欧语言中构词上之形态变化。”邢公畹(1996)在谈到原始汉藏语分化于甲骨文出现以前时说:“……藏缅语分化出来的时间较早,而原始汉藏语是无字调的,所以原始藏缅语也无字调。……原始汉台苗语在将近一千年的行用中,有三种舒声特定韵尾(包括零特定韵尾)和一种入声韵尾转换为平上去入四种字调,所以分离之后的原始汉语、侗台语、苗瑶语一开始就有相同的四个调类。”
后来,关于上古汉语语音和语法的形态变化,联系汉藏语及南方方言的比较,又有许多新的发现。美国著名汉学家包拟古(2009:60)说:“有关系的词组成词族是上古汉语跟许多藏缅语的特征。词族中的这些词之间具有规则的音系关系,包括元音交替、声调交替。声母交替,如带音与不带音的对立,送气与不送气的对立。介音的有无。韵尾变化,如塞韵尾跟同部位鼻韵尾的交替,以及其他等等。形态词缀——特别是前缀、后缀,但是中缀也有——在许多藏缅语中也是很常见的,而且一定也是原始语的显著特征之一。……更重要的是形态上的相似性,对于确定语言的亲属关系是强有力的证据。”
郑张尚芳以许多东南方言上声字读为短调为依据,推测上古汉语用紧喉的-ʔ尾,表示小或少(少短浅省简紧扁迩寡淡)或指亲昵(祖考父母子女姊弟嫂舅);又通过中古音的“祭泰夬废”来自-t、-d尾后来变为-i韵尾,藏文带-s尾的词多与汉语的去声字对应,并引证俞敏“梵汉对音”中-s尾用去声字对译,证明了上声来自-ʔ尾、去声来自-s尾的假设。郑张尚芳(2003:218)说:“……古汉语最初大概也跟藏语类似而没有声调,后来由于紧喉的作用,伴随产生了一个高升调,是为上声,即《元和韵谱》所谓‘上声厉而举’……又由于清擦音尾的作用,伴随产生了一个长降调,所谓‘去声清而远’……入声字则因都是塞音尾,伴随一个短调,所谓‘入声直而促’……这一系统约于晋时形成,南北朝时才为文人所认知,依调型排序,被分称为平、上、去、入四声。”
法国汉藏语专家沙加尔研究的结论与此相当接近。他认为,上古汉语是“无声调、不是严格的单音节、形态基本上是以前加缀为主兼有中加缀和后加缀的派生法。在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中间某个时期,不知何故,一系列变化导致汉语偏离了这种模式。加缀法开始冻结……一个趋向严格单音节化,声母及韵尾复辅音丰富的新的形态规则宣告诞生。……音节仅限于带响音尾或塞音尾,导致声调的产生”(沙加尔,2004:17)。此外,金理新(2006)关于上古汉语的形态还有更多的研究和分析。应该说,沙加尔说的“单音节化”和声调的产生要前推到先秦,他说的“不知何故”,则应该是上文所说的,汉字定型并作为汉语的书写符号、作为语素,造成了汉语的类型变化。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国内外汉语研究者和汉藏语研究者联手合作,已经取得丰硕成果,汉藏语比较研究的深入发展,一定能为早期汉语的类型变化提供更多的论证。
承认汉语在采用汉字作为书面记录符号的前后,确实发生过类型转变,以此来理解汉字何以能获得双重性质,就顺理成章了。
4.汉语汉字的互制和互动所演绎的汉语史
从“隶变”到现在的两千年,正是汉字和汉语相结合、相制约和相推动的时期,演绎了一部汉语史。让我们看看,汉语汉字的互制互动是如何论证已知的汉语发展的历史过程的。
就语音系统说,为了适应方块汉字一个形体表示一个音节和一个意义的机制,不但原有的多音节词(联绵词)不能再生,就是带有复合辅音的语词也受到限制;然而由于音节数有限、语词的发展无穷,单音词的增长很快就受到音节总量的局限。虽然增加了四个调类使音节数增加了不少,但在春秋战国文化繁荣、语言迅猛发展的形势之下,还是不能满足词汇扩展的需求,于是秦汉之后声类韵类也大量增长。先秦的声母,黄侃定为19声,现代闽语是公认比较接近上古音的,至今都只有“十五音”,加上丢失的全浊声母,不就是19声吗?而到了隋唐的中古汉语,声母就有“36母”。对于上古韵部数量,各家分歧不多,大体都是29个,可是到了《广韵》系统的206韵,扣除声调差异还有50个左右。汉唐之后,双音词大量发展,音节的局限不存在了; 近代汉语之后,入声消失、全浊清化,声类韵类就又从增走向减了。这就是汉语音类自古至今的“橄榄形”演变。
除了音类的增加,上古音还有大量的包括声韵调在内的异读别义。王力先生晚年用四年时间精心分析,搜集了3000个音义皆近、音近义同、义近音同的同源字,编成《同源字典》。这些字,从韵类说有“对转”(背/负、迎/逆、伦/类、宽/阔),“旁转”(饥/馑、柔 /弱、回 /还),“通转”(存 /在、境 /界、强 /健、岩 /岸);从声类说有各种双声(冷/凉、辨/别、趋/走、命/令);从调类说有异调别义(买/卖、阴/荫、坐/座、奉/俸);从词性说有异类兼用(鱼/渔、臭/嗅、禽/擒、亭/停、甘/柑、平/评)。王力(1982:3,12)指出:“同源字,常常是以某一概念为中心,而以读音的细微差别(或同音),表示相近或相关的几个概念。”“同源字的形成,绝大多数是上古时代的事了。”为什么上古之后这种近音派生词不再时兴了?因为汉代之后双音词兴起了,音节局限和同音字太多的压力大大缓解了。
到了近代汉语,双音词、多音结构大量增加之后,有些字义的相加和词义有了差异(如东西、大人、笑话我、爱人儿),于是作为多音词语的语音结构就不宜拿单字音简单相加。为了适应音步、韵律和节奏的需要,各种轻重音、轻声、儿化以及变声、变韵、变调等连读音变便产生了。这些音变,在不同的方言中进度不一、规律各异,有的刚冒头,还没定型,有的尚未发生。这是语言结构促使字音发生的新一轮系统变化。
就词汇方面说,语言要发展,要适应表达思想、沟通社会生活的需求,就必须不断扩充词汇。上古汉语的单音词显然不够用了,同音太多、异读太多也不便交际,于是上古后期(春秋战国)就开始出现了联合式和偏正式的双音词,后来又从句法借用了其他造词法。汉字对汉语的最大贡献是它的表意功能。原有的单音词往往是多义项、多词性的,两个单音词(或语素)按照不同的方式进行“语义合成”,就能造出无穷无尽的词语(生:先生、学生、新生、考生、寄生、终生、回生、来生、人生、畜生、卵生、活生生、研究生,生命、生人、生日、生病、生怕、生吃、生性、生活、生火、生产力、生生不息)。汉唐之后的多音合成的康庄大道,使汉语词汇形成了“以单音词为核心、双音词为基础”的系统,加上后来把多音词语压缩减为双音的“缩略法”,又使这个系统富有弹性。现代汉语大约有70%的双音合成词,又有大约70%合成词的词义就是字义相加或相关,掌握了几百个常用字,就不难理解大量的合成词。这种汉语特有的词语生成方式,有效地弥补了汉字繁难的缺陷。
在语法方面,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形体孤立、标音不灵的方块汉字难以标记字音的“屈折”,抑制先前有过的一些形态变化。上古汉语的“异调别义”(“圈破”)就是语音的屈折,即用声调的变读来区别不同的词性,例如非去声的名词变读去声用作动词:衣、冠、枕、王、间;非去声的形容词变读去声用作动词:劳、远、近、好、后;非去声的动词变读去声用作名词:观、传、从、过、骑。直至汉代这种变读还没有消失,许多早期的字书还记录了这类异读,中古之后就不再能产了。
就构词法说,先秦汉语已是单音词占优势,《诗经》的民歌中还有大约四分之一的联绵词,秦汉之后,联绵词受到抑制应该与方块汉字的“孤立”性也有关系。
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还保留了一些“格”的差异,如第一人称“吾”用于主格,“我”用于宾格;“朕、乃、其”等也只用于领格。秦汉之后,变格逐渐消失。
此外,古代汉语语法的发展还有名词词尾“子、儿、头”和动词词尾“着、了、过”的形成。用这些虚化成分表示语法意义,都是魏晋以后在言语使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字形基本不变,字义虚化、字音弱化,这也是汉字形音义的互动发展,汉字与汉语的相适应。
以上各点可参阅王力(2015)第三章。
综上所述,汉字定型之后,和汉语一路同行,相互适应,各自不断改进自己的功能,达到新的和谐。上古汉语结束时,产生了声调,词汇中单音词占了优势,各种形态变化(异读别义、人称代词分格、部分动宾倒置等)逐渐消失;进入中古汉语后,形成“四声”的声调格局,声韵系统复杂化,形成单音词为核心、双音合成词为基础的词汇系统和双音节音步;近代汉语时期口头语和书面的文言扩大差异,“子儿头、着了过”等表示语法意义的后缀逐渐成熟,后期又产生了多音词语的连读音变。可见,仔细考察汉语和汉字的互动和谐,就不难看出汉语发展的历史分期。
5.汉字独具的特异社会功能
在中国,由于汉字兼备了语言的性质,自身的形音义又是独具一格的:字形虽然特殊,“隶变”后却长期稳定,且不断有艺术的加工和创造;字音虽不能准确标记实际口音,却因长期使用获得了古今南北相对应的“音类”;字义不但可与字形和字音相联系,做到望文生义和听音知义,而且也可适应生活和认知的需求不断扩展或收缩。正是这些特性,使它发挥了其他语言文字所不具备的以下多种社会功能。
(1)汉字的字音虽无法准确标示一时一地之音,但由于长期的使用却获得了超时空的能力。识字的人按字典所定的音去读,不识字的人按本地语言传承的音去说,古今的语音、通语和方言的语音在演变中总是存在一定的客观对应,这就是未经“约定”却是“俗成”的“音类”。认得了字形、了解了字义,不论读音各异,都能有共同的理解。长期的实践使汉语人都获得折合音类对应的能力,这就是汉字能够超时空通行的原因。高本汉(1931:45-46,50)说:“中国地方有许多种各异的方言俗语,可是全部人民有了一种书本上的言语,以旧式的文体当作书写上的世界语……不但可以不顾方言上一切的纷歧,彼此仍能互相交接……而且可以和已往的古人亲密的交接,这种情形在西洋人士是很难办到的。……中国人对于本国古代的文化,具有极端的敬爱和认识,大都就是由于中国文言的特异性质所致。” “中国所以能保存政治上的统一,大部分也不得不归功于这种文言的统一势力。”唐兰(1979:5,12)说:“中国人把文字统一了古今的殊语,也统一了东南西北无数的分歧的语言。”“它能代表古今南北无数的语言,这是拼音文字所做不到的。”可见,正是汉字的“表音不力、表意高超”的优劣互补,使它能够时传古今,地通南北。用汉字记录的汉语文献,从甲骨文到现代汉语,都能得到考释。虽然浩瀚无边,却永具活力。中国能够成为文献大国,成为统一的文化古国,汉字的双重性质及其与汉语的互动发展功不可没。
(2)汉字虽然表音不力,却有特强的表意能力。字义的分解,不论是同义、近义、反义,还是引申、虚化,都有广阔空间,不识字的人可以用口语造词,识字的人则可以用字义组合造出书面语词。例如“长”,长短、长虫、长工、长期、长寿、长久、长远、长年累月、取长补短、家长里短、说长道短、长话短说、天长地久、细水长流、扬长避短,细长、专长、特长、狭长、延长、日久天长、一技之长,可能是平民大众口语造的;长卷、长编、长途、长度、长策、长辞、长治久安、扬长而去、万古长青、气贯长虹、来日方长、源远流长、发短心长,应该是文人学士书面造的。就像黄河和长江,书面语词和口语词汇各自滚滚向前,也各具情味,雅俗共赏,久而久之还能相互交流,彼此都得到充实;不仅如此,古代的言词还可以提炼为成语,做典故引用,也可以翻新、变用。这就使得词汇系统不断扩充,得到多样化的发展,为汉语全方位的应用、多姿多彩的表达提供广阔的空间。
(3)汉字的形体虽然延续两千多年没有重大变化,却有历代的书家陆续创造了多样的艺术手法,形成了独特的汉字书法艺术。而且,表意的汉字,写意的中国画,按照汉语特有的音律和中国情境创作的诗歌,“诗书画”融为一体,共同缔造了数千年的中国式的艺术长廊。对此,高本汉(1931:84-85)也有很到位的说法:“中国文字是真正的一种中国精神创造力的产品……中国文字有了丰富悦目的形式,使人能发生无穷的想像……中国人在书法上能巧运其笔……书和画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中国的艺术家常为书法家而兼绘画家,在他们的画作上,喜欢插入……古诗上短的节句……因之文学和书法又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这又是西洋人所不能理会的。”
6.汉字改革百年风云应有个历史总结
现在来讨论本文开头提出的另一个问题。
在中华民族灾难最为深重的时候,一批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为了“国之富强”,提倡“切音为字”“字话一律”“字画简易”(卢戆章,1956:3)。这就是晚清的“切音字运动”。之后,民国初年成立了读音统一会,公布了注音符号。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倡导“文学革命”的同时提出“汉字革命”的口号:“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的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的用国语写出。”(钱玄同,1922)不久,学者们先后研究制定了“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在艰难困苦的抗战岁月中,各地纷纷成立新文字协会,上海的难民营和延安的夜校,都在教新文字,唱国语抗敌歌曲。几年之间,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学者研究认认真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设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委员会)”,开展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和制定推行汉语拼音三项工程,十几年间就取得丰硕成果。80年代,普通话已经大大普及,简化字深入人心,汉语拼音方案被联合国认定为拼写汉语的规范在全世界通行。到了1986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宣布停止汉字拼音化改革。至此,汉字改革画下句号,百年风云尘埃落定。
从那时到现在,又过去三十多年了,现代化建设的新课题一个个接踵而至,信息革命、网络化的浪潮滚滚向前,社会的转型一直没有止息。作为牵连全社会的语言文字生活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有了种种不同的想法和做法。有关汉字和汉语的语文现代化建设,就有许多问题亟待回答。以下试谈几点想法向方家请教。
第一,为什么古老的汉字能够长盛不衰,顶住世界的拼音潮流,保住自己的青春?
百年的“文改”之所以不能实现,其原因不是社会制度、思想认识和经济能力这些外因,而是在于汉字的结构和功能的内因。它不单是文字符号(形体),还是音义组成的汉语的结构因子——语素。这种“一身二任”的双重性质,使它具备了沟通古今汉语和南北方言的魔力,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哪怕是不太常用的书面语,使用未多的新词语、省略语,只要用汉字写下来,就可以“望文生义”,使古今南北的人都能够共同理解;如果改成拼音,用惯了的古语“三人行必有我师”“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成语“刻舟求剑”“守株待兔”之类,可能今人还能听懂;如果是不太常用的,哪怕只是双音的书面语,如鲁迅《阿长与山海经》中的“惊异、诘问、惧惮、疏懒、震悚、粗拙、渴慕、惶急”,或是朱自清《匆匆》中的“挪移、凝然、遮挽、蒸融、游丝”,即使是用汉字写的,几十年后恐怕也并不好懂,若改成拼音,虽然拼读不难,却无法听懂。即使是报章时文,像“给力、首战、获刑、助攻、狂饮、暴跌、售武、课纲、猛增”等,不论是汉字还是拼音,都得多读几遍上下文才能理解。至于大量的文言词、古语词、方言词、成语典故,乃至口语罕用的书面语,拼音化之后恐怕都得被淘汰,此外,同音词势必大大精简,缩略语、新词语也很难存活,作家别出心裁的修饰手段也会受到很大的限制。论说文、应用文里那些无法一口气读完的长句,还不知道怎么处理!把汉字改成拼音,确实不是换一件外衣,于语言无损;也不是刮一点孔毛、稍换个模样,而是要伤皮肉、动筋骨的。
关于汉字为什么不宜改成拼音,周有光(1992:120)有过最简洁的说法:“汉字适合汉语,所以3000年只有书体的外形变化,没有结构的性质变化。”对此,高本汉(1931:50)在1923年也有发人深思的说法:“中国人果真不愿废弃这种特别的文字,以采用西洋的字母,那决不是由于笨拙顽固的保守主义所致。中国的文字和中国的语言情形,非常适合,所以他是必不可少的;中国人一旦把这种文字废弃了,就是把中国文化实行的基础降伏于他人了。”
然而时至今日,还有人在继续提倡汉字拼音化改革的研究,可见这还是一个需要讨论解决的问题。
第二,现存的汉字还有必要进行改革吗?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优缺点并存的,任何工具在使用过程中都得根据实际需要不断加以改革,这也是普遍规律。汉字虽有长寿基因,自身固有的缺陷却也依然存在并继续在妨碍应用,这是不能不正视的客观事实。
汉字最大的缺陷是什么?一是表音度差,二是字数太多。汉字走的是表意的路,要提高表音度就得更改整个形体系统,这是无法办到的;字数太多可以留用高频字、淘汰罕用字。其实,这两点早就由日本人相当成功地解决了。他们确认“当用汉字”,加注“假名”都是聪明的办法。晚年的周有光(2010:170)说:“现代通用汉字有7000个,其中半数3500个是常用字。按照‘汉字效用递减率’,最高频1000字的覆盖率是90%,以后每增加1400字提高覆盖率十分之一。利用常用字,淘汰罕用字,符合汉字规律。与其学多不能用,不如学少而能用。”当然,这两点说是容易,做就难了。“猞猁、茱萸”是动植物名词专用的低频字,如果要淘汰,必用时怎么替代?同音替代,拼音替代?电视节目里有“汉字书写大会”,还在表彰小学生认记生僻字呢。至于夹用拼音,经过一番争议,“字母词”终于获得了现代汉语词典的准入证了,如今应该有十亿人学过汉语拼音,全国范围内推广普通话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电脑的拼音输入早已打倒“五笔字型”而得到普及,应该说,扩大拼音的应用已经有了社会基础,还有哪些语词可以分期分批地替代汉字夹用于文本?首先可能的是,仅有表音作用的外国人地名、外来词、拟声词、感叹词、语气词、助词和无意义的“音缀”,如果给这些成分也发了准入证,可能是满纸拉丁字母,甚至比日文里夹用假名还多。这样做,洋人可能欢迎,国人就未必了。这都得立项研究,经过试验,逐步推行。此外还有些不太合理的简化字、同音替代字,要不要适当调整?扩大汉语拼音的应用也有许多事可做,这都是需要探讨的系统工程。
第三,在语言教育中怎样更好地发挥汉字的作用?
在母语教育中,电脑普及后,少年儿童“提笔忘字”的现象已经普遍显现出来,如何用有效的方法切实解决这个问题,怕是比穿着长褂子、带着瓜皮小帽、扎上腰带,学跪拜、背三字经(所谓承继国学传统)更加重要。显然,滥用儿童的记忆力,要求小学生认写太多汉字是不宜的,但是对覆盖率90%的1000个常用字却不能放松要求。要让初学者过硬地掌握常用字,也是个系列工程。教材要分阶段合理地出现生字,恰当地选取和注解义项,在课文中有足够的复现率。有关汉字的各种统计数据和资料,研究者都已经给备齐了,就是落实不到编教材和教学过程中去。这不是一件怪事吗?在二语教育的教材和教学中,问题就更加严重了。覆盖率90%和99%的常用字是1000个和2400个,常用词则是13000个和18000个,用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把常用字和常用词的义项及其种种属性都整理出来,严格按照字频、词频和字词的义项频度编好入门教材,应该是可以办到的。可是时下的对外汉语教材净是按照从国外引进的新理论,用“情景、功能、结构”的理念来编写课文和练习册,又是游览“颐和园”“祈年殿”,又是“把字句”的几种用法,难字多、复现少,课文枯燥乏味。难怪在华学生宁可上街去听相声、学口语,送到外国孔子学院的教材总是被堆放在墙角。
语言文字是开启代代新人智力的钥匙,是协调社会生活的润滑剂,是沟通不同文化的桥梁。中国人要获取智慧,谋求社会发展,走向世界,就应该对汉语汉字的教育有足够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