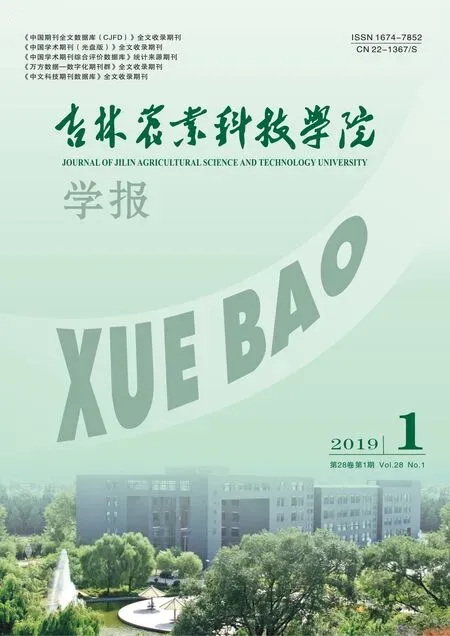后现代主义与莎士比亚戏剧之文化内涵
2019-01-11张明薇
张明薇,纪 颖
1 对命运与自由的主题探究
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通过背离传统的文学批评形式,例如专注于作家系统、作品系统的传统文学批评理论,转而专注于读者为中心所进行的文本阐释。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批判了理性至上的道德论说、积极解构感伤主义和超验主义等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1],来倡导个性解放的文学批评理论以满足人的完全自由及人的审美生活的彻底实现。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在现今时代深受文学批评家和读者们的欢迎,不仅源于它以读者为中心的创新性文学批评理论视角,更在于它与时俱进地剖析了当代社会背景下,经典文学作品的现实意义,使经典焕发出新的光彩。
回望十七世纪的英国文学发展史,文艺复兴时期作为一个熠熠生辉的早期现代主义文学时期,在经受了中世纪封建宗教神权黑暗的封存后,人们普遍开始挣脱宗教带给他们的精神压抑与束缚[2]。文艺复兴时期下的人文主义者们,乐观地追寻和复写着古希腊时代光辉的文艺理论,高呼古典时期古希腊文化中以人为本的光荣理念,积极肯定自我价值,谋求自身基于遵从本心至上的更高发展,即人文主义时代的人们更多期望在世俗社会中取得自我成就。文艺复兴时期所体现的现代性,与实现人类的自由解放息息相关。
作为人类情感最直观的表达途径之一的文学,在辗转几个世纪后,跨越了时间与空间,仍旧为实现人类思想的自由解放而演变着。人们通过文学获取心理安慰,并对一切现实中的矛盾予以想象性解决。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巨匠莎士比亚深刻地领悟中世纪的宗教神学理论,亦反思和分析了古希腊的命运观念与英雄史观。在古希腊文艺理论里,人民大众和欧洲哲人都抱有着共同的社会理论观念,即以英雄史观为核心的社会建造论,这潜移默化地强化着英雄的重要性,使人们相信英雄造世。由此生发出古希腊悲剧理论的常态:不屈的英雄生存在无情的命运中,英雄的顽强不屈却抵不过命运的捉弄。例如在《俄狄浦斯王》中,即使主人公设法逃脱既定的命运,但却始终逃避不了弑父娶母的悲剧结局,他终究被玩弄于命运的股掌。在痛苦中,他戳瞎了双眼并以失败者的姿态接受了命运的无情。然而莎士比亚却结合着当时人本主义的社会背景予以创新发展,积极地进行解构。从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到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不难看出,莎士比亚在文艺复兴的人文背景下,转换着主体角色的作用以及主人翁自我的身份认同,展现着对人类自由彻底实现的不懈求索。
在莎士比亚的悲剧著作《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延宕复仇的这一行动,对其所处的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具有深刻的艺术概括性。正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的第六章所述:“悲剧所模仿的不是人,而是人的行动[3]。”悲剧作家在演绎或讲述悲剧时所用的描写手法,也在刻画着人物的悲剧式行动,“作者不是为了表现‘性格’而行动,而是在行动的同时附带表现‘性格’。”在深受古希腊“个性解放”的文艺复兴社会背景下,人们既渴望积极救世又寻求遁世解脱,既歌颂着伟大理想及现世幸福,又对放纵的生活感到担忧懊悔,且无意识地被教义宗法所束缚。而这本身就是对古希腊“放纵情欲”的人文理论的一种解构,亦即哈姆雷特对于复仇这一事多重考虑和犹豫不前的原因之一。哈姆雷特的行动暗示了由社会矛盾背景造成的抑郁质性格,而这忧郁的性格又是对当时社会背景的镜像映射。
哈姆雷特,正是对人性和社会有着复杂矛盾的思考[4],才会多次将复仇的行动止于一刻。例如在文本中,他在经过祷告室,看见克劳狄斯无所戒备的祷告时,他的心理活动是这样的:
“现在我正好下手,他既然在祷告;
现在我就干,这样他可升了天;
而我就报了仇。那个却还得考虑:
一个恶贼杀了我父亲,为那事,
我,我父亲的独子,却把这恶贼送上天。
啊,这简直是酬恩,而不是报仇[5]。”
当哈姆雷特路过祈祷室,碰巧看见克劳狄斯正在祷告,他意图在此时杀死克劳狄斯。但转念一想在克劳狄斯涤净灵魂时被杀,他的纯净灵魂就有机会进入天国[6]。那么这样的结局对哈姆雷特来说这不叫复仇,甚至是对克劳狄斯的恩赐!让这个罪大恶极之人升上纯净美好的天国,这与复仇的初衷大相径庭,所以他继续延宕复仇,等待着下一次时机的到来。
这下一次机会,根据哈姆雷特的心理铺陈,则想选在克劳狄斯在做恶毒邪恶之事时,他再伺机行动。这一踌躇徘徊的行动体现着他的矛盾哲思,哈姆雷特既想杀死克劳狄斯,一解心头之恨去实现自己为父伸冤的人文主义理想,又唯恐克劳狄斯在祈祷可以涤净灵魂升入天国的宗教思想。
“收起来,剑;要把握更凶残的机会:
等他喝醉酒死睡,或狂怒的时分,
或在床褥间纵情乱伦的时候,
在赌博,在赌咒,或是在干什么
绝对没有得救希望的坏事的当儿。[5]”
哈姆雷特盼望着他复仇计划的完美实现,重视自身在此事件中的利害关系,希望避开任何阴差阳错的命运捉弄。如此强调情节中主体行为的主动性,更多看重主人公的自我意识,这即是莎士比亚在对古希腊悲剧中不可抗拒、不能违背的命运观念进行着积极地解构。
对于哈姆雷特而言,这样的社会现实,如亲生父亲被叔父克劳狄斯杀害,叔父成为国王,母亲在父亲尸骨未寒时嫁给杀父仇人[7],本对他无道德可言。他相信人性本恶,他为父报仇的行为即在敌对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可完全否定人性之恶也就是否定了人的现实存在,那么杀掉克劳狄斯顺而继承王位之后,在否定人的现实存在的条件下,他的“重整乾坤”也就成了空话,追求人生自由,积极治世的人生理想到最后也还是虚空一场。于是读者无奈且绝望地认识到,人终究无法实现彻底的自由。而人类自由实现的失败原因却是,社会的矛盾背景下,人们的自我意识的束缚。正如卢梭所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2 多元化创作手法
后现代主义之所以拥有它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很大程度源于多元性的创作手法。如结构不一的长短句,多元化的写作文体,低俗与高雅文化的混杂。他并不拘泥于某一种特定的写法,只要是能被后现代主义拿来为读者服务的,即可兼收并蓄。
莎士比亚戏剧在对人类情感的表达方式上运用了多种手法,包括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主义手法、于字里行间刻画的浪漫主义描写、追逐虚无主义本身的表现主义,乃至在十四行诗中充满着象征意味的象征主义描写等独特方式[8]。莎翁将人类的情感放在社会情景中深入勾勒,具有经久不衰的普世价值和多元意义。
在莎士比亚创作早期,他对人性秉持乐观态度,对人类社会的光明前途抱有希望。他用现实的笔触揭露着社会中的一些弊病,同时又幻想着通过简单且乐观的方式予以解决聊以自慰[9]。这一时期莎士比亚主要创作历史剧、诗歌、喜剧,也有一些悲剧作品。作品采用多种创作手法,不同程度地渲染了欢乐的气氛和其乐观理想,即便是悲剧也带着某些喜剧特征。例如《亨利四世》《亨利五世》,莎士比亚寄希望于帝王的道德自治,他幻化了社会律令的约束力量。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莎士比亚展现了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爱情观,“爱能做的,爱就敢做。”在其笔下,悲剧之所以成为悲剧,是因为每个人都有其善良且令人同情和理解的一面,只有这样的人有了苦难和苦衷,则是真实且令人恻隐,没有极大的恶人也无极善的好人。然而他们在当时社会渴望通过自由恋爱而获取终身幸福则是难以实现的。
在《威尼斯商人》中,莎士比亚幽默讽刺地批判了压迫者和统治者的丑恶嘴脸,这样雅俗共用的混杂手法达到了挖苦讥笑被压迫者得势状态的目的,让观众同情之处有憎恨,怜悯之处却捧腹。
在《威尼斯商人》中,莎士比亚在描绘鲍西亚时,更多地采用了诗意的浪漫主义手法[10],而莎士比亚以显著的现实主义手法描绘了反映当时社会阴暗面的喜剧角色——夏洛克。而对夏洛克的自身身份认同观念,确是二十世纪文学批评所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一位犹太商人,在主体为英国人的社会中,即是在文艺复兴时代背景下的“他者”,夏洛克作为一个被边缘化了的人物,努力地寻求着认同自己的身份,充满希冀地寻找着能够进行他自身身份认同的理想处境。
例如,夏洛克和安东尼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夏洛克说了一大段作为遭受迫害的犹太人的亲历,其话语让人心生怜悯,倍感辛酸,随之他的话语一转又变得狡猾诡谲,形象地展现了犹太商人的圆滑精算,活似一个压迫者。于是,夏洛克的角色巧妙地从被压迫者转变成了压迫者。文本体现是这样的:
当前乡村振兴过程中,各类涉农惠农强农富农资金不断注入,其间涉及大量专项资金的管理,若疏于监管,极易产生腐败。十八届中央纪委向党的十九大提交的工作报告显示,五年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处分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27.8万人。庞大的数字一方面反映了纪检监察机关严查腐败问题的力度不断加大,另一方面也表明基层腐败问题的治理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夏洛克:安东尼先生,好多次您在交易所里骂我,说我盘剥取利,我总是忍气吞声,耸耸肩膀,没有跟您争辩,因为忍受迫害,本来是我们民族的特色。您骂我异教徒,杀人的狗,把唾沫吐在我的犹太长袍上,只因为我用我自己的钱博取几个利息。好,看来现在是您要来向我求助了;您跑来见我,您说,“夏洛克,我们要几个钱;”您这样对我说。您把唾沫吐在我的胡子上,用您的脚踢我,好像我是您门口的一条野狗一样;现在您却来问我要钱,我应该怎样对您说呢?我要不要这样说,“一条狗会有钱吗?一条恶狗能够借人三千块钱吗?”或者我应不应该弯下身子,像一个奴才似的低声下气,恭恭敬敬地说,“好先生,您在上星期三把唾沫吐在我身上;有一天您用脚踢我;还有一天您骂我狗;为了报答您的这许多恩典,所以我应该借给您这么些钱吗?”
安东尼面对如此尖酸刻薄、直戳脊梁的言论,回答时也是充满愤怒,并要求夏洛克只按规章行事。莎士比亚对这一情节的刻画,也使读者有一种复杂的心理转变:从同情曾经的被压迫者犹太人民夏洛克,到憎恶如今的压迫者——狡猾的犹太商人夏洛克,继而同情此时的弱势方安东尼。
夏洛克前后由被压迫者向压迫者的身份转变,则透露出了他自身在主流社会中“他者”形象的心理暗示,随即在他可以施展身手之时,产生了如此的身份转变,急迫地进行着自我焦虑之下的身份认同。
除了极富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混杂形态的创作手法和批评理论外,莎士比亚的“矛盾修饰法”用以表达人物内心极为复杂的心灵状态更是恰当至极。他用两种相互对立的方面组成词语意图表达在爱与恨的情感中[11],人们的狂欢化了的感官体验,使戏剧更加丰富生动,妙趣横生为读者津津乐道。
例如,自《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罗密欧因爱生叹的话语:
罗密欧:“啊,吵吵闹闹的相爱,亲亲热热的怨恨!啊,无中生有的一切!啊,沉重的轻浮,严肃的狂妄,整齐的混乱,铅铸的羽毛,光明的烟雾,寒冷的火焰,憔悴的健康,永远觉醒的睡眠,否定的存在!”
莎士比亚灵活生动地运用“矛盾修饰法”[12],既体现了爱恋中男女主角的复杂矛盾心理,又愉悦了读者的细腻的思维。
朱丽叶在误解的苦痛中也有一段描述罗密欧的话:
“美丽的暴君!天使般的魔鬼!披着白鸽羽毛的乌鸦!豺狼一样残忍的羔羊!圣洁的外表包复着丑恶的实质!”
诸如此类双关语与矛盾修辞法等创作手法的运用,使读者的语言中心产生强烈的反应从而完成对其含义的理解,极富感知地对文本自身进行愉悦的体验与解读。这超越时空的主题刻画与多种创作手法的运用都体现了莎士比亚戏剧的超凡性。
莎士比亚戏剧能够成为经久不衰的文化符号,源于其历久弥新的文化特征。在不同文学批评视域下解读其作品,读者会有不同的新鲜感受。在不同历史时期背景下,读者也会体会到莎士比亚历史性文学给当今后人带来的珍贵反思。对后现代主义视角下莎士比亚戏剧的研究,有助于多角度地理解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