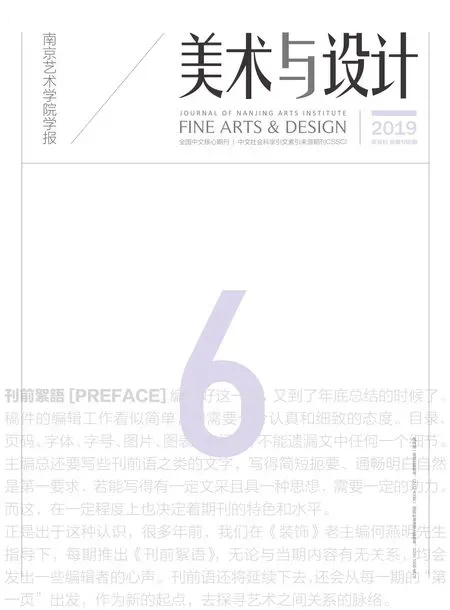何谓中华美学精神?①
2019-01-10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江苏南京210000
康 尔(南京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1]此后,“中华美学精神”这个概念,便频繁出现于各大媒体以及官员报告和红头文件中。何谓中华美学精神?对此,学界虽有讨论,但理据兼备、直奔主题的回答,似乎还未出现。
有人认为,中华美学精神就是中国人在艺术创作中所遵循、所呈现的价值取向、风格追求以及有别于西方的民族化的表现方式。
有人认为,中华美学精神与中华艺术精神大同小异、内涵相仿,其区别仅在于前者属于美学范畴,后者属于艺术学。
笔者以为,把对于中华美学精神的探讨圈定在艺术创作论或艺术学的范围内,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其视阈还不够开阔,因为美学关乎自然、社会、人生与艺术,因为学界一直就有自然之美、社会之美、生活之美与艺术之美之分,所以,在探讨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涵与构成时,不能仅仅关注艺术抑或艺术创作。对于中华美学精神进行凝练、概括与描述时,应该观照不同的层面,应该采取更多的纬度。
“精神”作为一个范畴,与“物质”相对应,其近义词是“精髓”“精义”等。人们通常用“精神”一词去指称一个思想体系中最重要、最主流、最具特色的内核与要义。对于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涵的探讨,自然也应紧扣上述三个“最”。因为只有这样,方可能获得相对明晰、合乎学理的解。否则,难免陷入众说纷纭、枝词蔓语的槽臼,难免坠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迷茫。
任何一个思想体系,一定有几个理论支撑点,一定是由若干个观念、观点甚至主张、追求所组成的。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涵,理应包括中华民族尤其是这个民族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美学家和艺术家长期认同、普遍持有的宇宙观、生存观、审美观、艺术观、创作观以及鉴赏批评观。换言之,中华美学精神,至少应由以下六个最重要的观念所构成:
一、天人合一的情义宇宙观
宇宙观,是人类对于宇宙本体、大千世界总体的、根本的看法。中国的先哲们认为,宇宙、自然、天地、人生是一个彼此关联、共生共荣的整体。这一思想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庄子讲:“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孔子讲:“天下归仁焉”。汉代的董仲舒,则将这种以“一”“归”为关键词的宏观看法引申为“天人感应说”。宋明的程朱理学,将其进一步演化为“天理说”。总之,天人合一,也称天人合德、天人相应,是中国古人对于宇宙本体、大千世界的本性最根本的看法,其要义在于万物皆有联系,万事均有关联。
中国人的宇宙观,还有一个特色,那就是认为宇宙、自然、天地、人生是一个充满了情义的存在,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所言:“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在清代画家石涛的心目中,名山大川不仅是有生命的,而且还是艺术家的友人、亲人甚至恩人,否则,他也不会在《画语录·山川章第八章》中发出这样的感慨:“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所以终归之于大涤也。”
以“天人合一”和“情义”为标志、为特征的宇宙观,对于中国人的审美以及创作、解读、赏析艺术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独酌”于花间的李白,明明是一个人在喝酒,但他“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了。杜甫所面对的,明明是不知“山河”“烽火”为何物的花草与飞鸟,但他却写出了“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诗句。
《红楼梦》120回,集中写了一个字:“情”。《水浒传》120回,主要写了一个字:“义”。《三国》和《西游记》,着重描述的也是“情”和“义”。汤显祖写《牡丹亭》,让他的主人公杜丽娘说死就死、想活就活,写得堪称一脚天上、一脚地下,让后人看得惊诧不已、赞誉不绝。汤显祖之所以能够写得如此潇洒,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阴阳两界联系密切也就是一栋房子的楼上楼下而已。在民间传说中,将月亮视为寒宫,将星辰视为眼睛,将动物视为投胎有误的家人或亲友,更是屡见不鲜。
天人合一的情义宇宙观,也是中国艺术家普遍拥有关联性思维、普遍采用比兴手法的缘由。何为比兴?朱熹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关雎》的作者明明想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但他先唱“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种先说水鸟求偶再说男子求爱的叙事方式,是关联性思维、比兴手法在言情叙事中最早的呈现,但几千年来一直未变。在民间话语中,关联性思维与比兴手法也是比比皆是。例如:“十朵菊花九朵黄,十个女儿九像娘”“十个梅子九个酸,十个官儿九个贪”“好铁要经三回炉,好书要经百回读。”前一句总是说自然现象或常识,后一句才是言说者希望表达的真意。若要深究这一现象长期存在的原委,无疑是天人合一的情义宇宙观使之然也。
二、逍遥自在的个体生存观
生存观,是人们对于生命价值、生活意义以及理想的生存状态的认定、坚守与憧憬。我们的先哲,始终追求、一贯倡导自由自在、任情适性、优雅潇洒、大彻大悟地活在天地间。中国的文人,则将这种追求与倡导更加具体化了。他们偏爱幽野之趣,推崇放浪不羁,讲究风骨奇伟,主张人格独立。有个传播道家思想的小故事,流传久远、意味深长。说是楚国的国君听说有个叫庄周的人聪明绝顶、才华盖世,便差遣下属去找他,邀他出山为官。那天,庄周正在濮水岸边钓鱼。使者向他转达了国君的美意,然而庄周未置可否。庄周对来人说:“你们看,河边有只乌龟。它是愿意死去而享受被供奉、被祭祀的高贵,还是愿意在泥涂中自由自在地活着?”来人说:“那当然是活着好啦!”于是庄子说:“哦,那我还是留在这里钓鱼吧。”这种宁愿做一个泥潭中打滚的乌龟也不愿当享受供奉的高官、接受祭祀的牺牲的选择,体现的正是逍遥自在的个体生存观。
这种生存观,对于中国人看待人生、体悟人生、规划人生、发现生活的真谛,影响是巨大的。例如,陈寅恪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例如,梁启超认定:“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再如,蔡元培主张:“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再如,胡适说过:“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这些至理名言、人生感悟的出现,与逍遥自在的个体生存观是脱不了干系的。
这种生存观,对于中国历朝历代、在野在朝的艺术家的创作,影响也是一以贯之的。例如,无论是古琴曲《酒狂》《广陵散》,还是民歌《信天游》《顺天游》以及新近发掘出来的《华阴老腔》,除了旋律的音层关系有些约定,在音长、音强、节奏、音色等方面,都是可以随性而为、自主演绎的。有人认为,这是古代的记谱方式简单、落后所致,笔者不敢苟同。在古籍中,我们时常见到“文不逮意、词不达意”的焦虑,但从未见过语言符号无法标注音长、音强、节奏、音色的忧伤。再如,在中国的诗词界、绘画界,“垂钓”“踏青”“牧羊”“放牛”“赏花”“品茶”“饮酒”“对弈”“操琴”“听曲”“访友”“探幽”甚至“红杏出墙”“雪夜闭门读禁书”,一直是千古不变的主题。若要追问其原委,其源头一定是逍遥自在的个体生存观。
笔者比较过中西审美教育的理论主张与具体实践,得出的结论是:中西学人都主张人的感性与理性同样重要,都主张两者均应得到长足的发展。但其区别在于:西方的理论及做法是,通过美育培养情感丰富的理性的人;而中国的传统是,借助美育培养克己复礼(或曰遵规守矩)的感性的人。虽然,中西学人都主张感性与理性应该比翼双飞,但是最后的落脚点,还是有差异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因为逍遥自在的个体生存观,已经融入国人的思维里、文化中。
三、表里兼顾的意象审美观
西方的美学家,大多主张在审美的过程中着重关注对象的形式与表象。从毕达哥拉学派试图从几何关系中寻找美,到荷迦兹在《美的分析》中提出,“美是由形式的变化和数量的多少等因素相互制约而产生的”;从康德指出,“在所有美的艺术中,最本质的东西无疑是形式”,到赫尔巴特主张:“美只能从形式来检验”,内容、内涵通常不在西方美学家的视野中。“审美无关利害”说,是西方美学中最具统领地位的观点。
而中国的艺术家、美学家,则把审美的目光聚焦在形式与内涵、表象与蕴意的综合体“意象”上,也即古人常说的寓意之象、孕意之象、表意之象、尽意之象上面。换言之,在审美的过程中,中国人从来都是既关注形式层面上的“象”,也不剔除与“象”同在的“意”的。国人欣赏美、把握美的实践活动,既包括感官层面上的观看、聍听、品尝与触摸等,也包括认知层面上的知晓与理解。眼下,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同意这样的观点:要想把握中国传统的乐舞之美、诗词之美、书法之美、绘画之美、陶瓷之美、雕刻之美、刺绣之美等,离开了对于内涵、蕴意的知晓与理解,是很难实现的。中国古代教师爷的第三个职责——“解惑”,也包括对于事物美否、美在何处的解析。在民间,无论是“打回原形”“剥去画皮”的传说,还是“东施效颦”“滥竽充数”的故事,体现的都是中国人表里兼顾的审美主张。
中国古代的艺术家,总是借助艺术境界来表述人生境界;总是将人生境界寄托于艺术境界;把人生境界当成艺术境界来追求。如果他们所营造的艺术境界只是一些赏心悦目的形式与表象,与内容、内涵没有联系、毫无关系,那么,自古便有的 “寄托说”“抒怀说”“补偿说”“慰藉说”等一概无从谈起。
美学家李志宏认为:“如果以系统论的眼光看待审美活动,则审美活动是一个整体,由两大子系统构成:一是由机体的结构和功能构成的自然子系统,一是受到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的意识—观念子系统。或者说,整体的审美活动有两个层次,一个是自然层次,一个是观念层次。”[2]既然审美活动与人的“观念”是有关系的,那么,就不可能与“利害”毫无瓜葛,也不可能不涉及“生存利害性”“社会利害性”以及“是否于人有利”的问题。笔者认为,美的事物并非从来就有;美与不美只是审美者对于事物的特征、属性的认定;判断事物美与不美的依据,是审美者自主建构的或在不知不觉中自然形成的审美标准或曰“知觉模式”;而审美标准或“知觉模式”的萌芽、发展与成型,是一个长期积淀、潜移默化的过程。尽管,审美标准或“知觉模式”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地域性、从众性、变异性、不确定性等特征,但在审美标准形成的过程中,是否“于人有利”,一定会在冥冥之中发挥其主导作用。从审美实践出发,美是人类知觉到的(而不仅仅是感觉到的)多种情感之一。美所指称的对象,通常是“合乎情理”“于人有利”并能显现出真与善的某种存在。
如果审美者毫不顾及形式背后的内涵,“合乎情理”何从谈起?如果,审美者并不关心表象背后的蕴意,如何知晓对象是否“与人有利”?总不能把形式光鲜、表象灿烂的白骨精、罂粟花认定为是美的存在吧?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无意在这篇短文中对不同国别、不同时代的审美观作出谁对谁错、孰优孰劣的价值判断,只是试图对中国传统的审美观所具有的表里兼顾、关注意象的显著特征,或曰与西方的差异性,作一个事实判断,同时对这种审美观的由来与合理性,做一个简要的说明。
四、虚实结合的诗化艺术观
中国是诗的国度,《诗》为六经之首。在中华文化璀璨的宝库中,诗歌堪称成就最高、最具有代表性的国粹。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刘禹锡、枊宗元、李商隐、苏东坡、辛弃疾、陆游等一代代诗人创作的经典诗篇,经由世代传颂,对于国人的艺术观的形成,一直在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中国是诗教大国。童子开蒙借助于诗,情感交流借助于诗,移风易俗借助于诗,认知“鸟兽草木之名”同样也借助于诗。历朝历代的仁人志士认为:“不学诗,无以言”(孔夫子语), “腹有诗书气自华”( 苏东坡语)。久而久之,诗情、诗语、诗意,融进了国人的血脉;诗性、诗心、诗道,也注入到了国人的基因。就连农民出身的刘邦,也能吟诵出“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诗句。即便是放牛娃出身的朱元璋,也能写出《金鸡报晓》《天地日月》《咏菊》等36首诗篇来。
虚实结合,是诗歌艺术状物抒怀、表情达意的主要特征。元代的马致远,写过一首题为《天净沙·秋思》的小令:“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虽然作者只用了二十八个字,但是读者普遍认为,这首小令描绘了一幅古朴凄凉的秋郊夕照图,同时也将独行旅人孤寂、凄苦的心境,刻画得淋漓尽致。如果依据源自于柏拉图的模仿说去审视这部作品,马致远笔下的夕照图,描述得并不详尽,交代得也不够清楚。《秋思》中描述的季节,是初秋还是深秋?其大环境是丘陵还是原野?“图”中的那位主人公,是老叟还是壮汉?是谪官还是墨客?那匹瘦马,主人是骑着还是牵着的?但是千百年来,没人提出过这样的疑问。显然,中国的文学家、鉴赏家、批评家以及普通读者,都已经接受了虚实结合的诗化艺术观。
中国的传统绘画,也是虚实结合且充满诗意的。例如,张大千画的荷花图,花瓣、花蕊与花朵,总是画得很具象、很实在,但他表现荷叶、水草与清波时,则求传神而不拘泥形似了。再如,张大千画风景同样也是如此。山间的小路、林中的庙宇以及画中的人物,回回都画得很仔细、很具体,但他描绘群山峻岭、千沟万壑,则习惯采用泼墨的手法去表达其诗意了。
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中国戏曲表演体系之所以精彩,之所以特别,之所以能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的主张并称三大表演体系,其主要的原因也在于采用了“时虚时实”“以实带虚”“虚实相生”“虚实互补”“虚实结合”的表现方法,进而让舞台表演充满了诗情画意。
中国的民族歌剧,其本质就是“诗剧”。剧中的许多唱词,如《江姐》中的“春蚕到死丝不断,留赠他人御风寒;蜂儿酿就百花蜜,只愿香甜满人间”,如《刘三姐》中的“山顶有花山脚香,桥底有水桥面凉;心中有了不平事,山歌如火出胸膛”等等,体现的都是虚实结合的诗化艺术观。
五、情志并重的中和创作观
“言志说”是中国古代艺术创作论的开山之“说”。其要义在于写诗作文源于“言志”,为了“言志”、必须“言志”。此“说”最早出现在《尚书·舜典》中,后经孔夫子及弟子们的阐述,一度占据了创作论中的主导地位。
“缘情说”的源头,也可追溯到先秦。其核心主张则为:吟诗行文源于“抒情”,为了“抒情”必须“抒情”。此“说”经由《毛诗序》的作者毛苌、《文赋》的作者陆机等人的钩沉与强调,最终成为与“言志说”地位相当、侧重点有别的另一个主流观点。
到了唐代,经学家孔颖达指出:“言志说”与“缘情说”其实并不矛盾,也无本质区别。在《毛诗序正义》中,孔夫子的这位三十一世孙写道:“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进而化解了纷争,形成了被创作界普遍认同的“情志合一说”。
当代学者认为,“情志合一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艺术创作论已经走向成熟。越来越多的艺术家相信,艺术创作的起因、目的等并非单一的是为了“言志”或“抒情”,寄托、表达、张扬、传播作者内心二者合一的“情志”,才是艺术创作的缘由,也是艺术创作活动的价值之所在。
在中国的艺术创作论中,言说者使用的概念,总是成双成对的出现。例如:情与志、文与道、雅与俗、刚与柔、形与神、喜与怒、哀与乐、主与次、发与节、言与行、轻与重、缓与急、清与浊、明与暗、张与弛等等。这种思维习惯,显然与本土哲学中的阴阳互补、阴阳互化、阴阳转换、阴阳合一的系列说到有关。如何处理一个存在或一件事物中两个不同的、对立的、矛盾的元素?中国人通常的做法,是使之实现“中和”。《中庸》中讲:“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乃天地安位,万物成长。”
中和,与中庸、合一、辩证统一是近义词。中和的追求,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创作论的滥觞、形成与发展,起到了主导作用,也对历朝历代的艺术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在情感的表达上,艺术家主张:“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发乎情止乎于礼”;在色彩的使用上,艺术家主张“紫而不姹,红而不嫣,绿而不嫩,黄而不娇,黑而不墨,灰而不暗”;在人物尤其是正面人物的形象塑造上,艺术家主张:“文质彬彬,温柔敦厚,知书达理,内外兼修。”在结构的安排上,中国的神话、小说、戏剧、戏曲、评书、评话等,即便讲述的是悲剧故事,通常也会以善得善报、恶有恶果或者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来结尾。让显在的叙事主体诉过苦、喊过冤、论过理、骂过人之后,采用复仇团圆、升天重圆、封赠团圆、明君神仙帮忙团圆等多种方法,给观众一个慰藉,也让作品在总体品相上符合情志并重的中和创作观。
六、自成一体的鉴赏批评观
较之于西方美学,中华传统的美学思想、艺术理论,是自成体系、自成一派的。其标志性的特征是,所使用的范畴、概念是本土的、独特的、非常中国化的。正因为如此,中华传统的鉴赏批评观,也是特色鲜明、自成一体的。
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美学范畴以及相关概念的出现,呈现出时代遴选、优胜劣汰、不断生成、逐步细化的特征。例如,境这个核心概念,被普遍用于艺术鉴赏、审美批评之后,便生成、细化出了苦境、贫境、晚境、暮境、老境、败境、惨境、窘境、厄境、险境、危境、绝境、殊境、生境、顺境、佳境、幽境、乐境、梵境、佛境、真境、道境、逸境、莲境、凡境、化境、静境、诗境、词境、文境、胸境、情境、意境、仙境、妙境、悟境、夢境、神境、圣境等一系列子概念来。最终,境这个一级概念,也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学界所说的范畴。
此外,意、气、趣、妙、新、静、古、拙、巧等内涵丰富、传承有序的重要概念,也在千百年来的艺术鉴赏、审美批评实践中,最终都成了具有统领地位的一级概念或范畴。其架构及隶属关系如下图:
中华美学范畴与系列概念(部分)
境:情境、意境、仙境、妙境、悟境、夢境、神境、圣境等;
意:意境、意蕴、意象、意味、意趣、意向、意旨、意态等
气:气韵、气势、气概、气质、气派、气息、气度、气节等;
趣:雅趣,童趣、谐趣、静趣、野趣、奇趣、异趣、妙趣等;
新:新颖、新奇、新锐、新异、新美、新鲜、新巧、新兴等;
静:清静、寂静、幽静、恬静、娴静、雅静;沉静、柔静等;
古:古色、古香、古朴、古远、古怪、古典、古韵、古奥等;
拙:拙朴、拙雅、拙稚、拙陋、拙讷、拙劣、拙直、拙钝等
巧:精巧、小巧、细巧、灵巧、乖巧、奇巧、慧巧、智巧等。
妙:奇妙、美妙、绝妙、精妙、高妙、诡妙、贤妙、丽妙等;
……
中国传统的艺术鉴赏与审美批评,在方法的层面上也是特征鲜明、自成一体的。在宏观着眼、整体把握的思维传统影响下,中国的鉴赏家、批评家,从南朝的钟嵘到唐代的司空图,从宋代的严羽到明朝的胡应麟,再到清代的王士祯、袁枚以及清民之交的王国维,都特别重视对于作品的风格定位与批评。由司空图(一说李嗣真)编著的《二十四诗品》,将诗的风格细分为雄浑、冲淡、纤秾、沉着、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与流动二十四种,在世界批评史上,都是别具一格、独树一帜的。
结 语
综上所述,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涵极为丰富,至少应包括以下六个组成要件:
1、天人合一的情义宇宙观;
2、逍遥自在的个体生存观;
3、表里兼顾的意象审美观;
4、虚实结合的诗化艺术观;
5、情志并重的中和创作观;
6、自成一体的鉴赏批评观。
概而言之,中华美学精神,是经过历史长河的冲刷、涤汰后留传下来的文化瑰宝,是由天人合一的情义宇宙观、逍遥自在的个体生存观、表里兼顾的意象审美观、虚实结合的诗化艺术观、情志并重的中和创作观以及自成一体的鉴赏批评观所构成的思想及话语体系。
当然,中华美学精神,也是一个海纳百川、不断演进的开放体系。继承和发扬中华美学精神,既要守正,也应拥有与时俱进的胸襟与情怀。唯有如此,才会真正有利于文化艺术在新时代的繁荣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