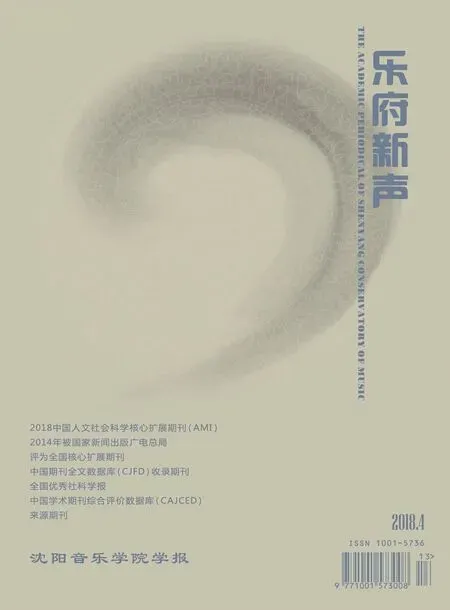语言学视阈下的声乐艺术研究— —以“动词核心说”为例
2019-01-08李梓郡
李梓郡
[内容提要]声乐艺术是语言艺术和音乐艺术的结合体,世界上任何一种唱法的歌唱活动都是一种艺术美的创造性活动。艺术家们可在尊重一度创作者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艺术理解与修养,把作品的艺术内涵和美感生动地展示给观众。在此过程中,要做到把握歌唱语言的科学性、诠释作品的完整性以及绘声绘色表达作品的艺术性,则需要歌者反复推敲字与字、词与词、句与句之间的语言属性,也正是因为这些不同属性的语言成为传递信息、表达思想的有效艺术手段,更是语言的美学设计、艺术运用以及“声”、“乐”互融的综合表达的艺术路径。
回顾过去学界对声乐艺术的探究,从理论层面上述论较多,对曲式本体与演唱技术技法的讨论较多,然而声乐作为一门语言艺术,脱离语言,仅仅叙述技巧则华而不实、昙花一现。语言作为交际的工具,存在于对白中的语音、语调,围绕逻辑重音而展开,这些重音的相互关系传递出语言的应用意义,忽略这种结构,就造成了句意的误读,而在音乐艺术范畴中,“声乐艺术是唯一直接运用语言和音乐相结合来表达思想感情、塑造艺术形象的艺术形式”[2]酆子玲.歌唱语言训练[M].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因此,不深入理解句意,就难以诠释歌曲的真实情感,具体到作品中每一个句子都有其独特的语义结构,演唱的节奏都应当根据意义的表达方法加以调整,没有结构的乐句是无法传情达意的。
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活动,歌唱充满想象力与创造力,声乐演员通过画面进行想象,而熟悉歌词中的语言属性与相互关系,从形式和内容方面研究自我情感表达逻辑,分析词与词之间的内在逻辑以及乐曲音乐戏剧化的进程,既可以保证演员探索适合自己的艺术风格,也可以为歌唱技艺进行有效的实践。擅长语言学理论研究的学者虽然高屋建瓴,但其专门结合歌唱艺术研究涉及较少,而具有声乐演唱丰富实践经验的同行,却又无力在文艺理论上有所建树。
通过本人对声乐演唱多年的研究,发现曲词里“动词中心”的现象和重要特征,并逐步找寻到动词在每一句唱词中所扮演的重要地位,并且通过动词的研究和演绎可以对表达人物情感、塑造歌曲意境起到关键的作用。因而,以汉语词性对歌唱的影响研究为立论,既能在歌唱艺术的理论界定、文化内涵以及语言学、美学阐释等方面进行宏观研究,同时又能在声乐歌唱本体的技术层面上,对歌唱艺术的发展及其艺术特色提供丰富翔实的理论依据,本文就以汉语语言中动词分析为基础,进一步阐述语言属性对声乐艺术不同层面的多位影响。
一、“动词核心说”符合歌唱语言的实际
众所周知,语言是对客观世界的逻辑思维表现形式,具体呈现在词性中动词与名词的处理方法上,也就是说,客观世界对自然语言的把控,集中地反映在各种语法理论体系之中,尤为重要的就是确立了“动词中心说”。
动词的语法特点是词义丰富、句法行为较为活跃,这就决定了其句法语义多样化的本质属性,它的这一属性一定意义上制约了结构中的其他词类,影响整个句法结构,承上启下,无可争议地成为了语义、句法结构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对于语言研究领域来讲,“动词中心说”的定式早已被广泛认可,但也仅针对语言本体而言。笔者认为,如果将之放在歌唱艺术领域中,其状态应确切为“动词核心说”,一字之差,前者一个“面”,后者一个“点”,而歌唱中声乐技术技巧与情感表达的逻辑是需要用“核心点”作为支撑来展开的,即核心词,因为它展现了行动和情绪的动态关系,放在歌曲曲词中,更是促使音乐前进的“行动线”。不难发现,中外作曲家往往会在动词、形容词以及名词等处给予较多逻辑重音的创作手法,这就需要歌唱演员去捕捉和强调。“歌词文字的分析要以‘句’为单位进行;每一句话都有一个中心思想,核心词的选定可以按照动词、形容词、名词的先后顺序来进行择选。充分理解并体会核心词的情感,并在语句歌唱的吸气准备阶段就将其植根在心里,随着演唱一直延续到该语句结束。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地用情感把句中文字紧密串联在一起,在避免了语句的破碎和情感散落的同时,还能让乐句的音乐更有张力和延续性”[1]周强.浅谈原创民族歌剧<回家>中角色把握的几个层次[J].中国音乐,2005,3.。
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中唱到:“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它的语法的从属关系为:住房→飘荡→炊烟,在汉语言研究关注中非常强调动词对句中其他成分的制约作用,然则对于歌唱,“飘荡”作为表示呈现着某种状态的动词,即“动词核心词”,诠释好此句就有了步骤,唱至“炊烟”时需脑中呈现着“飘荡”而吟,如此一来“炊烟”在当时演绎的形态感更加丰富饱满,将这种感觉保持,保持到动词的制约对象“住房”,最后保持到核心词“飘荡”上来,这种情感的保持与连贯,其实从歌唱技法层面剖析,与气息横膈膜的保持不谋而合,融会贯通,观众听起来惟妙惟肖,歌曲诠释更为得体具象。
二、“动词核心说”与歌唱的情感表达
诗词歌赋的创作讲究“气”的贯通,而“气”最重要的成份就是情感,动词核心说对于情感的表达尤为关键,可谓“情”不达则“气”不通。有言:“歌词为先、节奏次之、声音居末”,这里的“歌词”并非单纯意指歌唱词语本身,不仅要搞清楚其字面含义,更需要理清文字的词类属性以及前后的逻辑关系,目前我国声乐艺术在此方面的忽视,也是制约我国声乐艺术完整表达的因素之一。纵观西方歌唱艺术,尤其美声唱法的发源地意大利,无论是歌剧咏叹调还是早期艺术歌曲,其语言的科学性为它成为世界歌剧中心而奠定了基础。例如,莫扎特歌剧《唐璜》中男主角的唱段《Il mio Tesoro intanto》(《我亲爱的宝贝》),曲中几乎所有延长音的保持、大幅度的音程跳跃和极为复杂的音节跑动等等歌唱难点都在词语“cercate”中进行的,其词意为寻找,同样作为表示呈现着某种状态的动词,表现出男主人公誓死为爱人复仇内心状态的持续以及真挚爱情的情感抒发的轨道走向。
诚然,西方语言氛围下的歌唱艺术,无论是歌唱发音的科学性还是对语言体系的概念结构性都较发达。追溯中国音乐历史,不难发现也蕴藏着大量有关声乐艺术的论述,留下了丰富的音乐理论遗产,相关歌词、诗词等围绕语言的典著更是不胜枚举,有力地证明了“中国自古也有独到的声乐理论体系”[1]曹章琼.中国古代唱论与现代歌唱理论的几点比较分析[J].音乐研究,2010,2.。中国古代诗歌语言都是根据情感逻辑所创建,情感结构是在感情节奏不断变化中而变化的,此种感情节奏具有一定的音乐性,并且诗歌还要求声情并茂,能够一唱三叹。我们在对古诗进行欣赏的过程中,并不能够默默的读,而是要反复的朗读,从而能够充分了解到其传神的地方。
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正是基于古人对于诗词与音乐深入细致的探究,方才影响了《诗经》遣词造句与其诗体的形成,并形成了与之相关的歌唱技法。以诗经《周南》当中五诗之一《芣苡》为例,加以说明:
采采芣苡,薄言采之。采采芣苡,薄言有之。
采采芣苡,薄言掇之。采采芣苡,薄言捋之。
采采芣苡,薄言袺之。采采芣苡,薄言襭之。
整首诗歌仅仅变化了六个动词“采”、“有”、“掇”、“捋”、“袺”、“襭”,则生动地展现出妇女采摘芣苡的劳动场景。“《毛传》曰:“有,藏之也”;“掇,拾也”;“捋,取也”(以手轻握植物的茎,顺势脱取其子);“袺,执衽也”(手兜起衣襟来装盛芣苡);“扱衽曰襭”(采集既多,将衣襟掖到腰间)。孔颖达进一步解释到:“首章言‘采之’,‘有之’。‘采’者,始往之辞;‘有’者,已藏之称,总其终始也。二章言采时之状,或‘掇’拾之,或‘捋’取之。卒章言所盛之处,或‘袺’之、或‘襭’之,归则有藏之”。借景抒情,情景交互的情感体验正是基于作者对于核心动词的精心选择,这种行之有效的艺术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造就了不朽的《诗经》。”[2]赵敏俐.论歌唱与中国早期诗体发展之关系[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观其动词的变化,勾画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场景,这也正是作为诗与歌最初形态的有机融合,诗与歌对于真、善、美的艺术要求不谋而合,借助恰当的修辞手段,尤其是动词的修辞手法,将动词的意向形态在演唱之前形成于大脑之中,把抽象的感觉要领在形象思维中变得具体化、简单化,为歌者生动地诠释作品提供了情感保障,深深地把握住每一位听众的心。
“动词核心说”在中国民族歌剧歌唱艺术中也有体现,如歌剧《江姐》的主题歌《红梅赞》,唱词为“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昂首怒放花万朵,香飘云天外,唤醒百花齐开放,高歌欢庆新春来”,唱词中动词依次有“开”、“踩”、“惧”、“开”、“放”、“飘”、“唤醒”、“歌”等,细致的观众可以发现,艺术家在动词的表现上格外强调语气、重音以及呼吸的连贯和保持,其演唱逻辑为:唱“红岩上红梅”时,脑中始终呈现着“开”的意念,将此保持至“开”时的刹那间,对“开”进行一个语气强调或轻微“喷口”处理,有一种向下的发动力,从歌唱发声技巧上看,也可以被认定为声音牢牢地“坐”到呼吸低位置上了,然后迅速将动词核心切换下一画面“踩”中的“踩”上,同理,带着“踩”的坚定,更满腔热情地去诠释“千里冰霜的脚下”之意,其余同上。因此,无论作为何种类型动词,从某种角度上来说都把控制着“行动”和“情绪”的动态走向,在艺术家的演绎中可以深刻感受到其动词的捕捉对作品诠释的精准度,惟妙惟肖、真实自然,
此外,结合语境对于歌词潜在内涵的把握也尤为重要,内涵义往往隐藏在字面义之下,字面上理解为对于红梅品格的赞颂,而作品的内涵义却是在托物言志,歌颂革命的忠贞,以及对敌人的坚决抵抗、革命必胜的自信心。由此歌者在演绎前必须准确把握歌词的内涵义,尽可能地在脑海中还原这一情境,最后运用语言的变形(即歌唱)将情感诉诸于听众。也就是说,有效地捕捉歌词中所蕴含的情感信息是歌者的首要工作,接着通过对接自身情感的体验对内涵义进行充分理解。但长短不一的歌词没有提供小说或戏剧那么具象化的场景,通常是几个字概括了词面背后的隐喻义。可见,要想全面、完整地表达作品,不仅需要对其字、词属性逐步推敲,更需要结合语境兼顾挖掘它的潜在内涵,对歌词内在的情感进行分析和表现,以便更准确地表达作品情感。
三、“动词核心说”与声乐演唱的技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专业教育水平和质量的大幅度提高,以及民族唱法对于美声唱法的借鉴和融合日趋深化,中国声乐艺术逐渐走向成熟,但一系列问题也接踵而来,以歌剧演唱为例:“歌剧演出队伍中90%以上都是各地高等艺术院校声乐系、声乐歌剧系或音乐剧系培养的毕业生,除了极少数表演者能够胜任表演艺术的高度综合性要求、担纲主演之外,其他绝大部分皆因表演或歌唱等某一方面技能存在明显弱项或缺项,故只能在剧中扮演跑龙套角色,或担任群舞演员或合唱队员。”[1]智艳.我国歌剧音乐剧复合型表演人才现状分析[J].中国音乐学,2016,4.从声乐演唱方面来说,即便是那些优秀演员,也多受制于某种特定唱法,无法适应多种曲风体裁在唱法上的广泛需求。如今真正可以被称为“大师”的人寥寥无几,仅会“歌”不会“演”,或者会“演”不会“歌”的现象日益严重,音色类型多为千篇一律的“学院派声音”,大多表演者歌曲感性体悟很多,想象力也很丰富,殊不知这样的感性认知是需要用一定的理性定式来得以精确表达的,尤其是在塑造中国歌曲意境时,其歌唱美学与观众审美情趣都有着特殊的表演定式,对表演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以歌唱的呼吸、共鸣、咬字吐字为例,自西方声乐艺术传入我国之日起,一批留洋归来或接受外来思想的声乐教育者对中西艺术碰撞后产生的“关闭”、“丹田呼吸”、“高音头腔共鸣”等歌唱概念进行初创加工,孰不知正是由于传播者在译介上面的误差导致中国声乐艺术在成熟之际逐步失去自我表演品格的同时,偏离了科学发声方法。因此,以“动词核心说”为例的声乐语言技术探索,正是对中国歌曲演唱定式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以动词为核心的歌曲表达,对情感保持与连贯的处理和把握最为关键,而吐字咬字作为最重要的一环恰恰被国内许多师者所忽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解决发音咬字问题即解决歌唱技巧关键之所在。男高音歌唱家孔德成教授讲学要义中曾强调歌者必须先放声“朗诵”歌词方才歌唱,因为字与字的关系就是音与音的衔接,音乐情感表达等同于对语气语调的体验。细化到每个字、每个词以及每句话,在充分明晰词意词性寻找科学逻辑重音的基础上,注意语气的精准拿捏。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应是结合歌唱的状态,做到元音之间完美的衔接,从一个元音走向另一个元音时,尽可能地保持元音间的无痕过渡,而不因辅音的变化将歌唱位置与音乐语言上受到影响,以此保证歌唱时发音位置的统一,从而完整地诠释科学歌唱,在这个层面上,动词的处理尤为关键,作为动词的字头更是重中之重,字头的“时差感”决定了情感表达与音乐上的起拍状态,与此同时这个字头起止状态一定是充分落在双肋横膈周围,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呼吸支撑歌唱,呼吸表达情感,而不是很多歌者营造出“假、空、虚”的造作情感,并且这种表达方式一度影响着众多声乐演唱者,认为“虚”声更为美妙和贴切表达作品情感,殊不知这种“虚”与美妙贴切一定是建立在充分的呼吸保持上进行的,更为科学,从而精准地表达歌曲戏剧中的情景和情绪。同时与动词核心说对情感表达的保持要求不谋而合,融会贯通。
以抗战歌曲《嘉陵江上》为例做具体阐述,歌词为:“那一天,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亮,我已失去了一切欢笑和梦想。江水每夜呜咽地流过,都仿佛流在我的心上。我必须回到我的家乡,为了那没有收割的菜花,和那饿瘦了的羔羊。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刺刀丛里回去。把我打胜仗的刀枪,放在我生长的地方!”
参看前文所提供的歌词不难发现,重点标记的皆为不同情景状态的动词,那么我们在演绎作品时就有了头绪,如“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作曲家在“失去了”处运用了三连音的写作手法,同时又是该句动词核心点,就要求歌者应在此处呼吸饱满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强调语气,与前一句“那一天,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中的动词核心词“打”字形成情感表达与技术技巧的“支撑点”,如此一来,作品中动词与动词的连接就是情感表达与技术技巧保持的“行进线”,每一个动词的出现就诸如电影镜头的切换,每一个画面所叙述的内容都不相同,但都有着关联性,这样串起来就是作品的完整表达,观众听起来更加具象与得体。
此外,“动词核心说”与汉语曲词中音腔与润腔的影响也关系密切,对于汉语演唱来说,最典型的“音腔”就是一个字的咬字、吐字过程。因为,汉语是以单音节词(也就是字)为基本表意单位的。一个字的发声由作为“字头”的辅音、作为“字腹”的元音和作为“字尾”的韵尾构成。其中,“字腹”元音的时值最长,正对应着“静感音响”——“体”;而“字头”、“字尾”时值短小,相对元音来说就是其前后的“动感音响”。根据上面的定义,则一个汉字咬字、吐字的发声过程就正是一个典型的“音腔”。故而,与欧洲各民族的语言和声乐演唱截然不同,汉民族声乐演唱成分变化突出体现在一个单音节字所对应的“音腔”内部,尤其是对动词的掌握,就是对整个核心唱段的整体把握,更要做到中国民族声乐演唱的“依字行腔”、“字正腔圆”的演唱特色。与此同时,润腔所“润”的“腔”,就正是这样由单音节字所对应的“音腔”。
此外,中国戏曲演唱中的“润腔”对“动词核心说”又有何种影响呢?陈幼韩先生在《戏曲表演美学探索》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戏曲演唱同歌曲演唱的不同之处在于,歌曲演唱是语音服从于旋律,是“言从于歌”;而戏曲演唱则是旋律受到语音的制约,是“歌从于言”。那么相对于歌曲来说,戏曲的润腔更加强调“依字行腔”,更加强调词性的动态制约作用,也就更加强调对单音节字所对应之“音腔”的润色与装饰手法。换言之,戏曲的润腔更接近于汉语的发音规律,也就更接近于民族声乐演唱的本质要求。研究词性核心与戏曲演唱的润腔,则更有助于我们认知和掌握民族声乐演唱的本质规律。这就是研究动词核心说与润腔技法对于民族声乐演唱与教学的重要作用。
相对于歌曲润腔手法,有些教育家指出了“喉阻音”(包括虚阻音和实阻音)及“立音”乃是彰显戏曲韵味的润腔手法。那么在下文中,我们就借助戏曲表演中的“立音”(也叫“刚音”)来例证研究戏曲润腔技法对于在民族声乐演唱与教学中对动词核心说的重要作用。
“立音”是戏曲中一种特色化的前倚音。陈幼韩先生之所以特别指出“立音”最能彰显戏曲韵味,就是因为它能够在一个字腔(音腔)中凸显峥嵘的棱角感,也就能够有力地刻画出人物刚毅、坚强的品格特质,足以为观众带来独特的审美感受。“立音”在河北梆子等北方戏曲中应用最多。以河北梆子为原型的民族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之《娘在那片云彩里》选段为例,来诠释“立音”润腔的独特表情功能:(见下例)

在“眼看着春天就要来”的“来”字处,歌曲运用了一个富有河北梆子特色的“立音”,这就极大地强化了“来”这个字发音的力度和气势,凸显了杨母坚贞刚毅的品格。而且,在“来”字之后的拖腔当中,作者仍设计了两处“立音”,构成了别具特色的“疙瘩腔”,更进一步强化了杨母的语势和品格。陈幼韩先生说过,戏曲实际上是生活语言的旋律化。而从美学来讲,歌曲也是日常语言的一种陌生化的变形。只不过相对来说,戏曲的语言陌生化是比较保守的,它保留了生活语言的某些棱角,而歌曲则走得更远了一些,把语言的陌生化发挥到了极致,把字音打磨成了适应旋律的“鹅卵石”。然而,如果我们在歌曲中加入一点儿如“立音”一样的戏曲润腔,就可以收到“四两拨千斤”般的奇崛功效。《娘在那片云彩里》的这个唱腔设计,就是一个充分的例证。
在这里要强调的是,表达作品不是为了强调动词而去“做”音量与力量,而是在动词前预设情绪在动词进行时与气息和声门的自然诉出,当然,这个过程需要不断揣摩与熟悉,建立起词性、“画面”的敏感度,久而久之,熟能生巧,灵活运用。
诚然,歌唱综合美的呈现,并非观察词性的状态即可把握,还需诸如咬字吐字中的字头、字腹、字尾、喉器状态、字与腔的辩证运用等等技术环节的综合运用,但以汉语词性对歌唱的影响研究为立论的视角应加以重视。囿于笔者能力之所限,暂时还难以将形容词、名词、叹词、虚词等面面俱到、巨细毕究,故仅能窥其一斑,为声乐表演者和学习者提供一种可供借鉴的理论视角和可资参考的艺术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