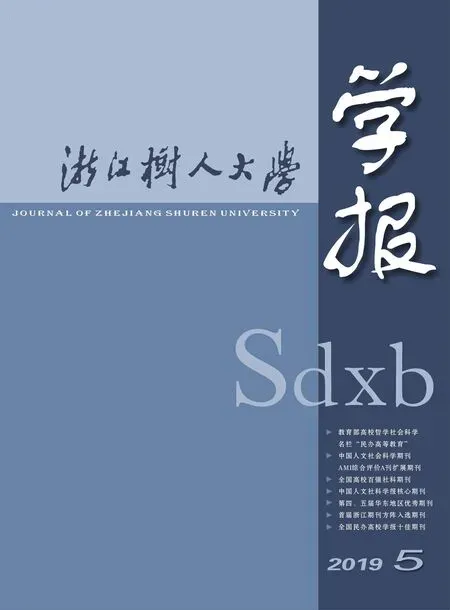电影的审美追求与观众的审美期待
——以电影《死侍》为例
2019-01-04卢苇
卢 苇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710069)
电影《死侍》(Deadpool)在2016年2月上映后,以5 800万美元的制作成本,收获了近7.83亿美元的票房,并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轰动,同时获得2016年美国青少年选择奖“最佳动作电影”和第43届美国人民选择奖最受喜爱动作电影。不同于以往的美国超级英雄电影,《死侍》不再拘泥于老套的超级英雄模式,甚至完全走向与美国传统超级英雄相反的另一极。影片最大限度地展现了主角“死侍”丰富而独特的个性特征,成功地把这个人物塑造成一个“反英雄”式的角色。《死侍》不但在票房上获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而且在审美价值的追求和创造上也取得重要成就,在审美趣味上契合了观众的审美喜好和需求。
一、别样的观影体验
相较于其他“大制作”“大投资”的美国超级英雄电影,如《美国队长》《钢铁侠》等,《死侍》的制作成本大为逊色,但这并未影响影片的观赏价值及其带给观众的另类视听感受。从电影叙事学的角度来看,电影的目的是要讲故事给观众听,讲故事的人即电影故事叙述人,是由电影作者根据电影叙事的需要而虚构的角色。电影《死侍》中的叙述人正是死侍这一角色。从电影叙述人的视角看,《死侍》以第一叙事人称叙述故事,吐露心声,带有直观感知的听觉性,也影响着接受主体对人物情感和认知的认同。从主体建构的角度看,一部影片的意义结构正是通过叙述主体、人物主体和接受主体三者之间的关系配置而得以形成的。而电影作为视听艺术,其叙事功能和过程主要是由画面空间和视听语言来完成的,电影要通过画面空间和视听语言在银幕上制造一种“幻象真实”,并以这种最大限度接近生活真实的“梦幻”,让人们沉浸在影片所创造的特定情境中,亦即将之构建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虚构空间。而电影能够再现虚构空间叙事体系的先决条件,是要求电影在拍摄过程中,演员不能直视摄影镜头并与观众进行互动交流,这也是将观众的想象引入这一虚构空间的工具。而《死侍》将这一要求彻底打破,影片中主角人物的目光与摄影机镜头直接相遇,这种相遇并不是简单地呈现其面部表情变化,而是直接与观众进行互动交流。如电影中死侍坐在立交桥上,随着音乐画画,突然直接转向镜头对观众说“Oh hello!”即“打破第四面墙”。
“第四面墙”的观念源于戏剧,也就是分隔观众与戏剧舞台上演员的“隐形墙”,当这面墙被“打破”时,戏剧舞台空间就与观众的真实空间相交融。正式使用“第四堵墙”这个术语的是法国戏剧家让·柔琏。他认为:“演员的表演应该像在自己家里那样,不去理会观众的反应,任他鼓掌也好、反感也罢。舞台前沿应是一道‘第四堵墙’,它对观众是透明的,对演员来说是不透明的。”(1)孙依群:《打破“第四面墙”与“空间幻觉”的断裂》,《影视制作》2016年第5期,第84-88页。把银幕比喻成一个内嵌式舞台,左面、右面和正面共三面墙、三个向度,而与银幕正对着的,是一道敞开的无形的墙,便是“第四面墙”。正是这“第四面墙”的确立,达成了表演者与观众之间空间幻觉的共识。而“打破第四面墙”的主张,最先是由德国戏剧理论家布莱希特提出的。“通常人们演剧好像舞台不仅仅有三堵墙,而有四堵墙,观众所坐的地方就是第四堵墙。这样就造成和保持了一种假象,即舞台上发生是生活中的一个真实事件,那自然不会有观众。用第四堵墙的演剧方法演剧就如同没有观众一样。”(2)贝·布莱希特著,丁扬忠、张黎、景岱灵等译:《幻觉与共鸣的消除》,出自《布莱希特论戏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页。布莱希特的目的是希望观众能保持理性的反思立场,“把观众变成观察家,唤起他行动的意志”,并“促使观众作出抉择”(3)转引自张庚:《戏剧艺术引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06页。。布莱希特正是出自对观众的敬重才提出了间离效果的概念,旨在提高观众的参与意识。因此,电影中的“第四面墙”被打破之后,观众承认了电影的假定性,从而使观众能够跳出电影本身,引发自身对电影内容或形式的思考。
电影中死侍与观众直接交流次数多达15次,且每一次交流都是直视摄影机与观众直接对话的,有时甚至直接触碰摄影机令其改变拍摄角度和方向。如在影片中,死侍在逼问反派特工时,他直接伸出手移开了摄影机,并告诉观众这里不要看,从而规避了过分血腥的场面。死侍从一开始便明确自己是个电影里的人物,他肆意地解构和颠覆着传统电影所遵守的规则,将演员的身份和摄影机的位置直接暴露,再加上直视、触碰摄影机等一系列举动,让观众感受到银幕只是一个虚构的空间,观众便从电影的“幻象真实”中抽离出来,从而产生间离效果。一直以来,电影为人们呈现的是一种“真实的梦幻”,人们沉浸在其中已成为一种观影常态,同时演员在“第四面墙”内进行锁闭式的表演,呈现一种“当众孤独”的状态。间离却与之相反。在戏剧中,布莱希特为了达到间离效果,让剧中的演员扮演两个角色:一个角色,他有一个特定的名字(比如死侍),这是演员所演的角色;另一个角色是演员自己,即演员从他所演的角色中脱身而出,并在解释着他所扮演的角色的态度和行为举止(比如演员瑞安·雷诺兹)。在电影中可以看到,瑞安·雷诺兹抽离出死侍这个角色,在与观众调侃着死侍这个角色的同时,顺带调侃了自己以前所演过的其他超级英雄(如绿灯侠)角色,更进一步实现了电影的间离效果。
《死侍》将观众与影像拉开距离,观众与银幕的想象和幻觉关系被打碎,这种艺术表现策略,使观众感受到一种别样的视听体验,从而获得审美主体的愉悦。当然,电影中“打破第四面墙”并不是将“戏剧舞台的幻觉”全部消灭,而是一种新的幻觉形式。间离效果也不是为了简单地打碎观众与银幕幻象之间的关系,而是为了在两者间实现一种更高层次的共鸣与认同。电影中人物与观众多次带有自嘲和调侃口吻的直接交流,其实也是将观众更深层地吸引到影片的叙事中,使之彻底进入叙事网络。如在电影中,死侍多次在闪回部分告知观众“这样就接上了”或是“后来我们就清楚了”之类的语句,试图通过这种与观众的直接交流,让死侍如同坐在观众身边的好友,在加深与观众交流的同时,实现观众的参与感。这种具有奇观化的视听处理方法,在让观众产生共鸣的同时,满足了审美主体多样化和新奇化的审美趣味。
二、反英雄的身份认同
在DC和Marvel公司开启的超级英雄的世界里,超级英雄们都呈现一种类型化的特点并给观众以一种符号化和脸谱化的感觉,如超人、蝙蝠侠、蜘蛛侠、美国队长、钢铁侠和X战警等,他们都拥有超凡的神力,近乎理想化的品格和人格,保护着地球和人类乃至星际的和平,但与人类这一群体还是保持着一种超越的距离感,观众在观看这类英雄电影时一直处于仰视和膜拜的角度,但《死侍》的主角呈现一种“贱萌”的“反英雄”式人物影像。
“反英雄”(anti-hero)与“英雄”不是一个完全对立的概念,反英雄可以看作是电影中的一种角色类型,它不是“反面人物”或“反派角色”的同义词,甚至连近义词都不是。这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他可以是主角或重要的配角,通常有着反派的特点,但同时又具备英雄气质或者付诸英雄行为,至少他们的动机并不邪恶。在美国电影中,英雄常与个人主义精神等美国人的价值观捆绑在一起,从某一角度或层面不懈地为美国的利益而战。但艺术终究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就像民众的利益有时也不完全等同于国家或政府的利益。作为美国社会历史的一种映射,超级英雄形象记录并呈现美国特定时代的特殊情绪,如反战、厌战,对政府、军方和情报机关存在的不信任态度等。当这种负面情绪达到一定值域时,便会催生不同于传统超级英雄一个的分支——“超级反英雄”。
死侍没有超级英雄们完美高尚的人格和崇高纯洁的理想,性格中的诸多弱点显而易见。如他最初的战斗动机便是为了复仇,在孤立无援时没有像以往宣扬个人英雄主义的超级英雄一般独自面对困境,而是转而求助X战警的帮忙。同时,不断的调侃和嘴炮也是死侍的一大性格特点,如电影中死侍呈现一种近乎话痨式的自言自语,不断解构着人们对超级英雄的原本认知。他调侃其他超级英雄、吐槽编剧、暗讽自己的超能力等,极具反叛性,从而使观众产生一种另类的审美体验和情感共鸣。
在美国电影超级英雄的世界里,也存在着诸多反英雄人物,“金刚狼”是越战后涌进美国通俗文化中典型的反战、反政府的反英雄角色。20世纪70年代,涌现了其他著名反英雄形象,如1972年诞生的“恶灵骑士”、1974年诞生的“超胆侠”,还有1986年问世的“守望者”等。与这些反英雄角色一样,死侍不同于以往那些高高在上的“类神”一般的超级英雄,其外表是不具备“英雄”素质的,他在未注射血清之前,出身于社会底层、游离于体制之外,靠着一些在法律边缘的差事过活。他最终选择注射血清也是因为得了癌症后没有足够的钱医治,只能加入一个“免费治疗计划”。接受该计划的病人都是社会的边缘人物,他们要么自我放弃,要么被亲人朋友放弃,而这个所谓的治疗计划也不过是个圈套,实际是在利用这些人进行违法的人体试验。死侍在治疗中被全身烧伤毁容,虽然获得了不死的超能力,但在巨大的创痛之后无法回归原本的正常生活。较之主流超级英雄,反英雄往往背负着更为悲惨的命运以及难以承受的创痛,这些在无形中彻底地扭曲了他们的性格,使他们对政府、军方抑或是权力机构乃至整个社会和人性都产生了质疑。在获得超能力后,他们随个人好恶,毅然化身为审判者与执法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或取人性命,或知法犯法,或以暴制暴。
从观众的观影效果来看,电影《死侍》及其主角更富有平民色彩、更接地气。传统超级英雄有关国家、正义以及拯救世界、爱好和平等颇为宏大的叙事格局与严肃主题,在这部电影里统统没有。导演将死侍的行为动机完全“私欲化”,在接受治愈癌症的实验性治疗后,为了恢复面貌而整容,为了家庭而追杀反派。这些私欲化的外在行为之下,体现出一种对个人爱情和幸福的顽强追求,而这种追求是常人最经常也是最本真的一种追求。想要守护爱情、守护整个家庭的初衷,也让观众对死侍这一人物产生了同情与理解,从而让死侍所有的“暴力原罪”得到一个近乎合理的解释。死侍的反英雄体现了对英雄概念的消解和重构,他虽然对世俗社会的现状不满,怀有反抗和抵触的情绪,但经过一番挣扎反叛之后,往往归于世俗。从表面上看,他可能卑微琐碎,对社会政治和道德采取轻蔑、嘲弄和愤怒的态度,甚至在行为上有些简单粗暴和反理性,但在这里,反叛、戏谑和调侃只是一种表象,其真正的内核是关于爱、家庭与责任。电影给予观众更多的是现实生活中如同朋友般的告诫,而非遥不可及的仰望,因而更易让观众接受并产生共鸣,更能让观众因现实处境引起的心理焦虑和生存压力得以缓解,从而拉近观众与电影的距离。
三、游戏娱乐的心理满足
与其他类型的艺术一样,电影有其审美的认知、教化和娱乐三大功能。通常情况下,几乎每部电影都会具备上述功能,区别仅在于侧重的不同。在《死侍》中,电影的娱乐功能较为突出,更值得关注的是,这部电影为迎合观众的审美趣味,对电影的娱乐功能有着明显的刻意追求倾向。如电影中快速动感的打斗追逐场面,打破了第四面墙与观众的另类互动,包括节奏感十足的背景音乐、男主角“反英雄”人物的塑造、底层小人物的出身、私欲化的动机处理以及为家庭和爱情战斗的初衷等。
超级英雄“漫画之父”斯坦·李曾说:“我所知道的就是一部好的超级英雄电影,要有打斗动作、悬念、有趣的人物、新颖的角度——这些就是人们喜欢的东西。超级英雄电影就像是给大人们看的童话故事,你所想象过的所有那些东西——比如希望自己能飞啦,或者自己最强大啦——都与愿望的实现有关。正因为如此,我相信它们永远都不会过时。”(4)《新东方英语》编辑部:《让生命绽放美丽——改变世界的50位名人(下)》,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9页。他笔下的超级英雄之所以深受大众的喜爱,是因为这些英雄有深度有弱点、有缺陷有烦恼,这才是真实的。“电影也是生存之镜,每个人都在其中安置自己,想象自己,寻找应对现实的生存策略。在一些电影展示的生存图景中,观众希望能从中看到个人在整个时代和整个社会中所处的位置,以求得一种对自身的关照和认同。”(5)杨辛、甘霖、刘荣凯:《审美原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34页。当下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为了生计而每日辛劳奔波的人们,需要电影带来娱乐体验,以宣泄心中的不快和身体的劳累。于是,电影艺术便随着市场化的步伐逐步淡化和消解其认知与教化功能,凸显其娱乐功能,观众的游戏和娱乐心理亦随之到来。尤其是超级英雄电影带给人们的释放和娱乐,人们近乎沉浸于“白日梦幻”一般的超能力世界,暂时忘却了当下的诸多烦恼。
《死侍》中有大量调侃嘲谑的对白和独白以及对当下社会问题的讽刺与讥笑,死侍身上具有不同于其他超级英雄完美的品质,与普通人一样有明显的毛病和缺点,从而使观众产生一种自我认同,在嬉笑娱乐的过程中宣泄个人情绪。值得一提的是,电影能将人们心灵深处禁锢已久的游戏本能激发出来。在超级英雄电影中,观众随着主人公如完成游戏任务一般,在NPC(非玩家角色)和主辅线之间穿梭,如在《死侍》中,主线是主角一直在寻找组织头目阿贾克斯,希望能将自己由于治疗癌症而损毁的容貌恢复过来。在这一寻途中,观众犹如在游戏中一般,跟随死侍一步一步接近幕后的大BOSS。期间还有死侍去寻求钢力士与黑后的帮助及死侍与女友凡妮莎的爱情副线,观众可以在观影过程中获得一种代偿性体验,通过观看电影人物的生活,去感受自己未曾尝试过的生活。这种观看过程丰富了观众对自身以外生活的体验和理解,同时这种玩游戏的心理也是观众娱乐心理的一种重要体现。随着市场化、商业化机制的渐趋完善,电影的游戏化和娱乐化必然会成为一种常态。即便如此,电影作为一种现代高雅艺术的存在,决不能因迎合观众需要而出现为娱乐而娱乐的世俗化倾向。为使电影艺术健康发展,需将其娱乐功能与其认知、教化等功能结合起来,融为一体,毕竟观众的审美需求和心理期待是极为丰富多彩的。
任何艺术的创新,都与其市场的需求紧密相连,或者说市场需求推动艺术创新。电影作为一门最活跃、最具创新潜力的艺术种类,其紧随市场需求不断创新是必然的,这也是电影艺术本身发展的需要。而电影的市场需求,即观众的审美需要或审美期待,则直接决定和推动着电影的审美追求。《死侍》对“第四面墙”的有效突破、对反英雄的角色塑造以及对观众娱乐心理的满足等,都可视作一种艺术表现的创新,其创新的目的直指观众尤其青少年观众的审美需求和审美趣味。电影的受众主要是青少年,因此《死侍》的创新目标直指这一群体。但要注意的是,电影在满足观众审美趣味的同时,应更加关注对自身审美需求和审美趣味的引导乃至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