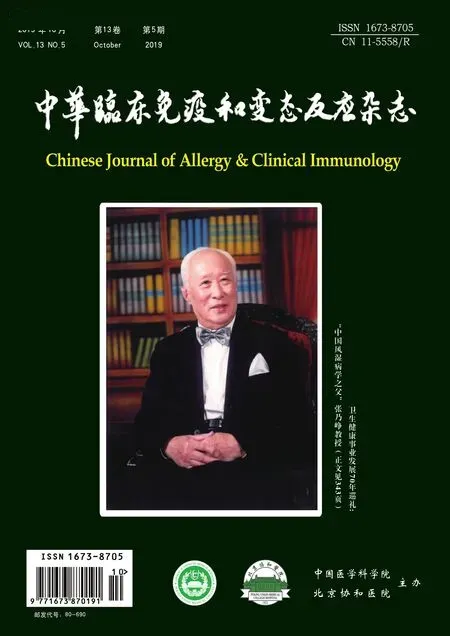固有淋巴细胞在哮喘发病机制及治疗中的作用
2019-01-03薛玲娜张惠勇郭晓燕马改霞马子风鹿振辉
薛玲娜,张惠勇,郭晓燕,王 钰,马改霞,邱 磊,马子风,鹿振辉
哮喘是一种以气道炎症、气道高反应性、可逆性气流受限为特征的慢性呼吸道疾病,临床上多表现为喘息、气促、胸闷、咳嗽等症状[1]。哮喘的发病机制复杂,作为一种异质性疾病,具有多种表型,主要包括过敏性与非过敏性哮喘表型。以Th2型细胞因子产生为特征的过敏性哮喘多与过敏原接触引起的特异性免疫应答相关,而非过敏性哮喘多由空气污染、感染、肥胖等引起,主要涉及固有免疫。近十年来,诸多研究发现固有淋巴细胞(innate lymphoid cells, ILCs)与炎症性疾病相关[2-3],可以产生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 IL)-5、IL-13等多种细胞因子,与巨噬细胞、嗜酸性粒细胞、中性粒细胞、自然杀伤细胞等共同参与哮喘的发病。本文主要综述固有淋巴细胞及其在哮喘发病和治疗中的作用,以期为临床防治提供参考。
1 ILCs的分类
ILCs是新发现的一类缺乏特异性抗原识别受体的淋巴细胞,主要位于气道、肠道和皮肤的屏障表面,通过释放相关细胞因子和介质来调节免疫反应,在哮喘、变应性鼻炎、炎症性肠病、银屑病等过敏与非过敏性炎症疾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4-5]。ILCs来源于骨髓中的共同淋巴祖细胞,根据其调控的转录因子和产生的效应细胞因子的不同可分为4类:ILC1、ILC2、ILC3和ILCreg。
ILC1主要受T-bet转录因子调控,由IL-12、IL-15、IL-18活化后分泌γ干扰素(Interferon-γ, IFN-γ)和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 α, TNF-α),通常与病毒感染和肿瘤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相关。机体在稳态时,ILC1在皮肤、肺、肝、肠中的数量较少,但在接触病原体后,ILC1数量会增加以抵抗病原体,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克罗恩病等慢性炎症疾病中,ILC1数量较多[6-7]。目前关于ILC1在哮喘中的作用还不明确。
ILC2类似于Th2细胞,经IL-25、IL-33、胸腺基质淋巴细胞生成素(thymic stromal lymphopoietin, TSLP)激活后可分泌IL-4、IL-5、IL-13等Th2型细胞因子,受转录因子GATA3、RORα调控,与蠕虫感染、过敏反应相关。动物模型及人类研究均证实ILC2在变应性气道炎症疾病中起关键作用[8-10],其分泌的细胞因子与Th2细胞之间相互作用,促进黏液产生、嗜酸性粒细胞和肥大细胞浸润[11]。
ILC3可分为淋巴组织诱导细胞(lymphoid-tissue-inducer cell, LTi)和非LTi两类,根据是否表达自然细胞毒性受体NKp46又可将非LTi分为NCR+ILC3和NCR-ILC3。ILC3受转录因子RORγt调控,由IL-1β、芳香烃受体 (aryl hydrocarbon receptor, ahr)等活化后可产生IL-17、IL-22,在肥胖型哮喘、银屑病、炎症性肠病等非过敏性疾病中发挥重要作用[12-13]。
与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cells, Treg)相似,ILCreg主要起免疫抑制作用,以平衡其他ILCs的效应。有研究报道,ILCreg通过分泌IL-10抑制肠道炎症,同时,亦可抑制ILC1、ILC3活化来减轻这两种细胞的促炎作用[14]。
在机体稳态条件下,所有ILCs亚型均存在于人类肺中,其中以ILC2和ILC3最为常见[15-16]。研究发现ILCs具有可塑性,ILCs在炎症环境的驱动下可进行反向分化。比如,ILC2在微环境的改变下可转向ILC1或ILC3分化,ILC2在白色念珠菌环境中可转化成分泌IL-17的ILC3[17],小鼠在臭氧暴露下,ILC2可转为ILC3,并分泌IL-17A、IL-33[18]。ILCs在哮喘的发病中有重要作用,目前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ILC2介导的过敏性哮喘和ILC1/ILC3介导的非过敏性哮喘[19]。
2 ILC2与过敏性哮喘
大多数过敏性哮喘患者在儿童时期发病,少数患者(约4%~13%)在成年后发病[20]。过敏性哮喘通常以嗜酸性粒细胞在气道浸润引起的炎症反应为特征,由Th2、ILC2产生IL-4、IL-5、IL-13等2型细胞因子驱动,但目前尚不明确在过敏性哮喘发病过程中Th2、ILC2这两种细胞的相对重要性[21-23]。Th2与抗原提呈细胞(如树突状细胞)呈递的抗原或过敏原接触后,产生IL-5、IL-13;此外,过敏原还可直接激活上皮细胞,释放TSLP、IL-25、IL-33等活化因子,激活ILC2产生IL-5、IL-13,进一步引起嗜酸性粒细胞浸润。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报道神经细胞与ILCs相互作用,共同驱动肠道和肺部的免疫反应[24]。ILC2在解剖位置上与肺神经内分泌细胞相毗邻,均位于气道分叉处,研究者发现肺神经内分泌细胞在黏膜屏障处识别过敏原或其他信号,继而分泌降钙素基因相关肽和γ-氨基丁酸,降钙素基因相关肽可刺激ILC2分泌IL-5,引起嗜酸性粒细胞在气道聚集;γ-氨基丁酸可导致杯状细胞增生,继而气道黏液分泌增多[25]。
研究者认为IL-33是驱动嗜酸性粒细胞型炎症的关键细胞因子[26-28]。Cayrol等[28]在无预先致敏的情况下,将IL-33缺陷小鼠局部暴露于链格孢菌中,其气道和肺泡灌洗液中嗜酸性粒细胞减少,炎症反应减轻,这表明IL-33在嗜酸性粒细胞型炎症中起一定作用。Lund等[27]对体内敲除ILC2小鼠(IL-7受体缺陷鼠)给予IL-33鼻内刺激,发现肺泡灌洗液中2型细胞因子和嗜酸性粒细胞并无明显升高,这表明ILC2可对气道中的IL-33起直接反应。因此,局部过敏原刺激产生IL-33并驱动ILC2活化,导致嗜酸性炎症是过敏性哮喘的重要机制,ILC2或IL-33可作为过敏性嗜酸性哮喘的治疗靶点。
临床研究提示重度过敏性哮喘患者肺泡灌洗液中IL-33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29]。嗜酸性炎症的哮喘患者,其痰和血液中ILC2数量增加[30-31]。然而,对于重度嗜酸性哮喘患者ILC2水平较轻度哮喘患者升高或减少,目前仍存在争议。Smith等[31]报道了重度嗜酸性粒细胞患者血中ILC2高于轻度哮喘患者,与Yu等[32]研究结果相反,Yu发现轻度哮喘患者血中ILC2水平较中重度哮喘患者明显升高,这可能是由于Yu研究纳入的对象均为新诊断哮喘的患者,肺功能水平较Smith研究对象高,且无使用糖皮质激素等用药史,两项研究对哮喘严重程度的评价存在一定差异[32]。研究发现支气管哮喘患者血中ILC2百分比与痰中嗜酸性粒细胞的数量、呼出一氧化氮、IgE水平相关[33],这提示ILC2可能作为哮喘患者嗜酸性气道炎症的生物标志物,也可作为临床治疗效果的评价指标之一。
嗜酸性哮喘患者通常对糖皮质激素治疗较敏感[34-35]。然而,Jia等[36]认为激素对ILC2活性的抑制作用较Th2差,说明了ILC2在哮喘控制不理想的患者中存在的潜在作用。研究发现吸入糖皮质激素后仍控制较差的患者,其血中表达IL-13的ILC2(IL-13+ILC2)水平升高[36],这提示我们在哮喘治疗时可以选择ILC2作为治疗的靶点。
总之,ILC2在哮喘患者的发病中起重要作用,当气道接受过敏原刺激后,上皮细胞释放IL-33,驱动ILC2活化并释放细胞因子,引起嗜酸性粒细胞浸润。对于激素治疗不敏感的过敏性嗜酸性哮喘患者,ILC2可能是一个潜在的治疗靶点。
3 ILC1/ILC3与非过敏性哮喘
非过敏性哮喘多在成人发病,与长期接触污染物、感染、病原体、剧烈运动、职业和肥胖等有关,临床治疗中多对激素不敏感。炎症反应通常表现为Th1/ILC1、Th17/ILC3型炎症[37-38]。
除了经典的Th17细胞,ILC3亦可分泌IL-17,招募中性粒细胞在气道聚集引起炎症反应。目前对气道中ILC3的研究较少。Kim等[39]发现,ILC3分泌IL-17是引起肥胖哮喘小鼠气道高反应的关键环节,肥胖状态会导致肺巨噬细胞M1型分泌IL-1β,进而活化ILC3分泌IL-17,而通过IL-1β阻滞剂可抑制ILC3产生IL-17。Everaere等[40]发现,与对照组相比,肥胖小鼠NCR-ILC3水平较高,而消除ILCs后,肺泡灌洗液中淋巴细胞减少,气道高反应性减轻,这提示除了T、B等免疫细胞,早期触发适应性免疫系统的细胞因子可能来源于ILCs。总之,ILC3产生IL-17,招募中性粒细胞在气道内浸润,引起气道炎症。Hekking等[41]发现,在成人发病的重度哮喘患者的诱导痰中,ILC3相关的特异基因上调,这提示ILC3这一亚型在哮喘中有重要意义。
ILC1与Th1细胞均可产生IFN-γ,重症哮喘患者痰中的IFN-γ水平高于轻、中度哮喘患者,这提示产生IFN-γ的ILC1可能参与了哮喘的发病[42]。另一研究通过对哮喘患者肺部提取ILC1,发现ILC1促进嗜酸性粒细胞凋亡,并具有抑制嗜酸性气道炎症的作用[43]。Kim等[44]发现哮喘患者诱导痰中ILC1、ILC2、ILC3水平均较健康人高,ILC1、ILC3与非嗜酸性粒细胞型哮喘相关,与巨噬细胞共培养后,巨噬细胞呈M1型极化。总之,ILC1在哮喘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尚不清楚[45],有待进一步深化研究。
4 ILCs可作为哮喘的潜在治疗靶点
2018年GINA指南对哮喘的治疗仍提倡以糖皮质激素和支气管扩张剂为主[46]。体外研究显示,从过敏性哮喘患者肺泡灌洗液中分离出的ILC2细胞对激素治疗敏感,然而,来源于TSLP水平升高的重度哮喘患者肺泡灌洗液的ILC2细胞对激素治疗反应较差,这表明TSLP可能在ILCs对激素不敏感中发挥作用[47-48]。因此,抗TSLP治疗可能成为重度哮喘且对激素不敏感患者的有效方法。临床研究表明,在轻度过敏性哮喘患者中,抗TSLP治疗可降低呼出一氧化氮、血及痰中嗜酸性粒细胞比例,升高乙酰甲胆碱PC20水平,从而降低气道高反应性[49]。另一项Ⅱ期临床试验研究发现,在未控制的嗜酸性粒细胞型哮喘成人患者中,与激素治疗对比,使用tezepelumab(针对上皮细胞来源的细胞因子TSLP的特异性人单克隆抗体)治疗可明显降低哮喘发作次数[50]。小鼠哮喘模型发现,抗IL-33可减轻Th2型炎症[51],目前关于抗IL-33单克隆抗体治疗轻度过敏性哮喘患者的Ⅰ期临床试验正在进行[52]。
鉴于IL-1β可激活ILC3,抗IL-1β可用于抑制ILC3活化,在严重的哮喘小鼠模型中,抗IL-1β可减轻中性粒细胞炎症和气道高反应性[53]。ILC3分泌的细胞因子IL-17亦可作为哮喘治疗靶点,抗IL-17可减轻肥胖哮喘小鼠的气道炎症和气道高反应性[54],然而,抗IL-17受体-brodalumab在对中重度哮喘患者的临床试验中未取得满意疗效[55],有待进一步深化研究。总之,ILCs主要通过表达关键的转录因子,在特定细胞因子的刺激下分泌相关细胞因子,从而发挥其功能,因此,通过阻断ILCs通路上的转录因子、细胞因子及其代谢物来调控ILCs,可进一步控制哮喘的炎症反应,这在临床上具有广阔的治疗前景。
5 总结与展望
ILCs是一种新型的淋巴细胞,其发现为研究哮喘的发病机制及治疗开辟了新的路径。ILC2主要参与以嗜酸性粒细胞浸润为特征的过敏性哮喘的发病,ILC1/ILC3介导非过敏性哮喘的作用机制。近10年来对ILCs在哮喘发病机制中的研究取得了一大进步,但仍存在许多问题,如ILC1、ILCreg对哮喘的作用尚不明确,ILCs各种亚型在哮喘发病中是否存在协同活化或相互抑制作用,ILCs在人体中发挥怎样的作用目前还研究较少,有待进一步探索。期待未来ILCs能像其他免疫细胞一样作为治疗靶点,如通过抗原抗体结合阻断ILCs的作用从而抑制哮喘的发生,或通过小分子药物抑制ILCs的活化,或开发相关疫苗来调节免疫反应,总之,ILCs通路上下游分子相关拮抗剂有望成为新一类的抗哮喘药物。随着对ILCs在哮喘发病中作用机制的深入研究,相信未来会发现更多涉及通路靶点的药物,为人类治疗哮喘提供新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