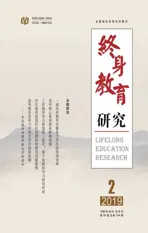中国近代社会教育发展的三个特征
2019-01-03万妮娜
□ 万妮娜
在中国近代教育领域,社会教育是一项值得关注的教育活动。它兴起自清末,民国初年取得教育行政上的地位,发展曾盛极一时。近年来,随着终身教育理念的提出,在建设学习型社会的现实需求下,近代社会教育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产生了大量的学术成果。相关研究多在教育史和社会史领域展开,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和个案研究。这几类研究互有渗透,呈现出学科交叉的研究趋向。但总的来说,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研究尚未得到深层融合,由此制约了对近代社会教育发展路径的认识,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近代社会教育史研究的深度开展。中国近代社会教育有其独特的发展路径,不仅区别于学校教育,也区别于世界其他国家。本文拟从跨学科的视野出发,围绕理论与实践、传统与现代、官方与民间三个角度,厘清中国近代社会教育的发展脉络,揭示其发展特征,推动近代社会教育史研究的深化,并为社会教育的当代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一、外域引入,本土筛选
应该说,近代社会教育的理论体系源自异域。据考证,“社会教育”一词最早在中国出现,是由日文翻译而来。1902年7月,我国近代最早的教育刊物《教育世界》刊登了日本学者利根川作的《家庭教育法》,其中首次提到了“社会教育”。此后,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形态,国外社会教育理论得到进一步引介。1902年8月,《教育世界》刊登了日本学者佐藤善治郎著的《社会教育法》,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译自国外的社会教育著述。随后,留日学生创办的《游学译编》翻译了日本学者中岛半次郎的教育学讲义,对社会教育进行了深入介绍。从1904年10月起,《教育世界》连续介绍德国著名社会教育学家的思想主张。如1905年2月起分3期介绍贝尔格曼的《社会教育学》,4月起分5期介绍维尔曼的《教化学》,同年8月介绍纳托普的《社会教育学》,1906年9月又介绍巴尔善的《教化论》。[1]这些五花八门、观点迥异的社会教育理论,拓宽了人们的眼界,增长了人们的见识。晚清后10年,社会教育在中国逐渐发展成为一股颇有影响的教育思潮。正是在此基础上,国内教育界开始撰写相关文章,尝试对社会教育进行吸收、消化与理论构建。
在理论引介尚处于起步阶段的情况下,社会教育被仓促地纳入了制度规划中。民国建立后,教育部设立社会教育司,开始从国家层面推进社会教育。但是,由于理论认识不足,社会教育司的分科和职掌屡屡调整,难以切实指导社会教育实践。基于此,在教育部的主导下,国内教育界加强了对国外社会教育实践的学习。1912年10月,日本通俗教育研究会编著的《通俗教育事业设施法》在国内翻译出版,成为新成立的社会教育司开展社会教育的主要参考。随后,国内教育界组团前往日本,对社会教育实践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并于1916年11月出版了《调查日本社会教育纪要》。这本书一度被视为举办社会教育的“准则”。[2]在此基础上,直到1918年12月,社会教育司的分科和职掌才逐渐定型。对比《调查日本社会教育纪要》①和《教育部分科规程》②,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那就是:民国初期社会教育的制度规划带有明显的日本痕迹。
但是,社会教育的根本要义,在于“社会性”。而“社会”是具体的。与较早迈入世界强国的日本不同,近代中国的发展缓慢而落后。国情的差异,决定了两者的社会需求不同,社会教育的侧重点势必也不尽相同。制度设计“照搬”日本,使得中国近代社会教育发展出现“有名无实”和“有实无名”两种怪相。一方面,大量见诸规划的社会教育设施和事业,如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动植物园、民众娱乐、公共体育等,或形同虚设,或地位边缘,甚至仅仅停留于文字。究其原因,这些“高雅”的社会教育活动,脱离了一个贫穷落后国家的现实需求。即便到了南京政府时期,情况也未见好转。如1928年,全国仅有博物馆27处、美术馆24处、古物保护所40处、游泳池91处。[3]另一方面,一些未及规划的社会教育活动却应运而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文化补习和生计教育。
与日本相比,近代中国存在着数量庞大的文盲群体。这是历史遗留的沉重包袱,也是中国迈向现代强国的严重障碍。基于切身感受和清醒认识,国内教育界在开展社会教育伊始,便自觉地将对失学民众的文化补习作为发力点和着力点。比如,在北京,社会各界创造性地开办了半日学校、露天学校和公众补习学校,为失学民众补习文化知识。[4]在之后的历史演进中,这些社会教育设施的名称虽有所改变,却一直坚定地承担着教育救济的重任。到了南京政府时期,文化补习最终被纳入了社会教育司的职掌。
与文化补习相类似的还有生计教育。20世纪20年代末起,国内经济环境的恶化,催生了一种新的社会教育活动——生计教育。其内容包括面向城乡居民的职业补习、面向农民的农业指导以及面向青少年的工读教育。各地相继出现了众多的职业补习学校,补习范围涉及各行各业,如打字、化学工艺、银行簿记、木工、无线电、英文、汽车驾驶、缝纫、雕塑等。农业指导成为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主题。工读教育则尝试将中小学教育和职业补习相结合。可惜,这些具有较强灵活性与适应性的社会教育活动,虽然屡屡见诸社会教育调查报告,却始终没有被纳入国统区的制度规划中。
可见,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活动,中国近代社会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世界到中国的过程。理论引介是社会教育兴起的助推力,本土筛选则是其发挥效能的根基。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教育的内涵由模糊逐渐清晰。但同时,由于缺乏自信,国内教育界在理论层面始终固执地迎合世界,理论脱离实际,以理论裁剪实践,不能正视一些在实践中展示出活力的社会教育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土特色的社会教育理论体系的形成。
二、源自传统,与时俱进
中国近代社会教育的发展不仅是中外教育交流的产物,更与本国传统密不可分。中国古代的一些教育或政治活动已然带有社会教育的基本特征,成为近代社会教育的实践渊源。
前已述及,面对失学民众的文化补习虽然未能见诸民国初期制度规划,却一直是近代社会教育实践的重要内容。这是因为,即便在片面重视精英教育的古代中国,社会教育也并未被完全忽视。中国古代孕育过一些带有文化补习性质的教育形式,其中有三种具有代表性。一是义学。产生于北宋时期,多由乡绅捐资设立,免费教授民间孤寒子弟读书识字。二是冬学。这是一种冬闲时开办的季节性学校,最初见于宋朝,由宗族或者私人开办,招收子弟入学杂字、百家姓之类。三是社学。萌芽自唐末,元代得到政府的认可与推广,其性质类似于义学。这些教育形式历经朝代变革沿用不绝。以今天的眼光看,它们已经具备了社会教育意义上文化补习的基本特征。历史进入近代后,时代的变化使得文化补习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各地相继出现各类简易学堂,包括简易识字学塾、半日学堂以及面向特定对象的补习学校,成为近代社会教育萌生的标志。清政府对此进行了初步的制度规划与推广。据1911年学部调查统计,全国有简易学堂29 000所以上,分布在16个省。[5]131显然,民国初年兴起的文化补习,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实践基础上,是古代教育层累与递进的产物。
再如,民初社会教育围绕通俗教育展开。其中,相比其他见诸规划的设施与事业,通俗讲演显得更有声色。究其原因,除了外来理论的阐释外,也应归功于源自传统的实践基础。众所周知,古代中国有一个源远流长的政治和教育传统——教化。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对万民的教化,将其视作治国家、得民心的重要国策。在技术落后的古代社会,宣讲作为基本的信息传播方式,被广泛地应用于圣谕讲解等教化活动中。就本质而言,民初兴起的通俗讲演就是宣讲,只不过内容和功能发生了改变。在民初颁行的相关政府文件中,通俗讲演当时还被称为宣讲,通俗讲演机构也被称为宣讲所,清楚地显示出两者之间的延续性。直到1915年10月,教育部颁发《通俗教育讲演所规程》,具有现代意义的“通俗讲演”一词才取代宣讲。[6]可以说,民初通俗讲演的盛行,是建立在对古代教育资源承接的基础上的。
民国时期还出现过一种综合性的社会教育设施——民众(通俗)教育馆③。这一设施初设于民国初年,南京政府时期成为“实施社会教育之中心机关”。民众(通俗)教育馆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新事物,检视历史却也能寻见其踪影。宋朝,范仲淹曾在姑苏买良田数千顷,开办“义庄”。庄内设有养老室、养疴室、育婴室、读书室、严教室。“凡族中嫁娶丧葬,有力不能举者,皆赡给之”。台湾学者李建兴认为,“与现在综合的社会教育机关,如社会教育馆相近似”。[5]97
在延续古代传统的同时,近代社会教育发展还呈现出与时俱进的特征。文盲众多的国情,使得文化补习成为近代社会教育的起点和重心。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到了南京政府时期,社会教育的重心开始转向生计教育。生计教育虽然未能纳入社会教育行政,其重要性却在不同场合被反复强调。如大学区时代,时任中央大学区扩充教育处处长的俞庆棠,在其制定的《中央大学区民众教育实施纲要》中提出,民众教育除了“注重认识最应用之字”外,在乡镇应“兼重农业知识”,在城市应“兼重工商业知识”。[7]1931年,国民会议通过的教育设施趋向案也指出:“社会教育,应以增加生产为中心目标,就人民现有之程度与实际生活,辅助其生产知识与技能之增进”。[8]可以说,社会需求是社会教育发展的前提,也赋予了社会教育不同的时代主题。近代和现代的一些学者常常指责社会教育事业“全面开花”,成为制约其成效的主要弊病。由于理论的移植性,近代社会教育看似内容庞杂,实则有其内在的发展理路。不同社会教育实践兴起和存续的时间不尽一致,不同时期也各有其侧重点。在关注共时相存的同时,不能忽视历时演变。
另外,这种与时俱进还表现在,科技的发展赋予了社会教育新的表现形式。比如,盛行于民初的通俗讲演,到了20年代末,逐渐被简便经济、更具表现力的电化教育(包括播音教育和电影教育)所取代。电化教育应科技进步而兴,体现了社会教育的革新与发展。
综上,古代中国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教育,一些教育实践却在无形中孕育积累了社会教育的若干要素。表面看去,社会教育是近代新兴的教育形态,但其实它与中国传统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发展过程中不自觉地接受了传统教育资源的引导。社会教育由社会变革的需求引发,其教育功能带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随着社会的变迁,社会教育的内容和侧重点势必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三、官民共举,教育救国
与学校教育不同,近代社会教育并非国家主导,而是呈现出官民共举、交替主导的发展特征。这在社会教育发展的不同时期各有体现④。在萌芽期,社会教育发展尚处于自发状态,实践主体多元,既有清政府,也有众多热心教育的民间团体和个人。在确立期,社会教育开始得到有计划、有组织的推进,呈现出政府主导、民间辅助的阶段性发展特征。在发展期,政权不稳,高校师生挺身而出,成为推动社会教育的新兴的主要力量。在分化期,政府和民间力量共同成为社会教育的践行者。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社会教育在方针、政策、目标、方式上都进行了新的探索。假如以国民党政府为“正统”的话,那么苏区和根据地社会教育的发展,无疑也是“民间”力量的产物。
在指出官民共举的同时,更应该强调,民间力量为近代社会教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萌芽期,社会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民间的吁请。正是在各界有识之士的理论引介和舆论呼吁下,社会教育才逐渐受到清政府和社会的重视。在确立期,民间成立各种团体,积极配合政府,研究和推广社会教育。这些教育团体的贡献体现在:调查本国社会教育现状;考察国外社会教育实践;翻译出版相关书籍;提出社会教育议案;倡办通俗教育活动。在发展期,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对社会教育进行系统思考,揭开了乡村建设试验的序幕。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引领下,社会教育开辟了工农教育的新方向。在分化期,国统区社会教育的不足和欠缺越来越明显,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教育则立足工农,开启了一种崭新的社会教育,从而为近代社会教育发展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民间力量投身社会教育,还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社会教育资金的不足。在教育经费异常拮据的近代,学校教育经费尚且难以得到保障,更何况社会教育。尽管南京政府时期对社会教育经费提出了明确要求,规定各省市社会教育经费应占到教育经费总额的10%—20%,但实际上根本难以达到。比如在北京,据统计,1929至1936年间,历年社会教育经费仅占到教育经费总额的6%—9.54%之间,从未超过10%。[5]167同时,还应当看到,政府投入并不是社教经费的唯一来源。在有的省市,民间经费投入甚至超过政府投入。如在社会教育相对发达的浙江省,1930年政府经费投入仅为479 305元,而民间投入经费则为522 547。[9]政府常常因为经费不足苦恼不已,但民间资金的注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压力,为社会教育正常开展、社教功能有效发挥提供了保障。
近代社会教育之所以发展成为一场官民共举的教育实践,有其深层原因。在近代内忧外患的特殊国情下,社会教育的兴起,不仅仅是为了变革教育,更被赋予了改良社会、救国图强的政治期许。以通俗讲演为例,与清末相比,民初通俗讲演内容有了质的突破,蕴含了现代国民所应具备的初步知识和道德修养。1915年10月,教育部更是颁发《通俗讲演规则》,将讲演主题限定为鼓励爱国、劝勉守法、增进道德、灌输常识、启发美感、提倡实业、注重体育、劝导卫生[10],体现出提高民众素质的愿望与努力。20年代以后,公立通俗讲演逐渐衰退,高校师生走上街头,讲演内容的政治色彩更为浓重。以当时颇有声名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为例,其讲演主题中,政治类接近三分之一。讲演题目振聋发聩,譬如《爱国》《国民快醒》《青岛关系我国之将来》《亡国之痛苦及救国之方法》《唇亡齿寒》《革命二字大家为什么要怕听他呢》等,彰显出鲜明的政治诉求。
2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农村经济日益崩溃,平民教育的重心开始由城市转向农村,并在此基础上掀起了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这一运动目前已经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其历史价值得到了较为充分的阐释,但却较少有研究将其纳入社会教育的领域内加以思考。其实,从社会教育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乡村建设运动是社会教育的阶段性产物。梁漱溟就此曾指出,社会教育和乡村建设,“好像两道合流,上游不是一个源头,而下游则彼此汇合为一流了”,“不但社会教育将归功于乡村建设,乡村建设之所趋,亦终不能外乎社会教育”。[11]尽管这些乡村建设团体的背景、性质、成分都比较复杂,有官办的,有民办的,还有半官半民的,但是他们的目标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希望通过乡村建设的实验,寻求一条改变中国农村贫穷落后面貌的途径。这样,社会教育与社会治理建立了初步关联。
抗战爆发后,社会教育的政治功能进一步凸显。基于战争需要,社会教育被注入了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抗战热情的新内容。相比国民党,共产党更为重视社会教育,并将其发展为全面的政治动员。随着社会教育的开展,根据地民众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洗礼,开始认同并且追随共产党的领导。[12]
综上,在近代救亡图存背景下兴起的社会教育,其发展凝聚了社会各界的力量和心血。尽管存在很多问题,但不可否认,社会教育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补习开辟了民众接受教育的新途径;生计教育着眼于民生福祉,并为之做出了初步探索;通俗讲演、电化教育等一些寓教于闲的社会教育活动更是以一种润物无声的方式,将新知识、新道德的甘霖播撒于民众心田。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教育之于社会改造和社会动员的政治功能,越来越得到世人的认可。
四、结语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教育实践虽未停止,但是地位严重边缘化。放眼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社会教育被视为与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相并立的教育形态得到重视并切实践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已经体认到我国教育领域的这种失衡,提出社会教育要系统化、制度化、学科化。近代社会教育发展留下了诸多宝贵经验,我们应当以史为鉴,在理论体系、制度建设和实践模式方面,探索一条适合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教育发展之路,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重任。
注释:
① 《调查日本社会教育纪要》介绍了日本35种社会教育的设施与事业,内容如下:图书馆、通俗图书馆、巡回文库、博物馆、教育博物馆、游就馆(展览馆)、公园及名胜旧迹、动植物园、通俗音乐、戏剧、寄习、美术展览会、电影、通俗教育调查委员会、通俗图书馆、通俗教育模型、通俗教育讲演会、学术讲习会、路上教育、巡回教育、感化院、养育院、济生会、爱国妇人会、卫生会、青年会、东京民育协会、处女会、谈话会、夜学会、公共运动场、体育会、矫风会、保姆教育、儿童玩具。
② 根据1918年12月颁发的《教育部分科规程》,社会教育司分设两科。第一科职掌博物馆、图书馆、动植物园、美术馆、美术展览会、文艺和音乐等事项。第二科职掌包括通俗教育、讲演会、通俗图书馆、巡行文库、通俗戏剧和词曲等事项。
③ 北京政府时期称为通俗教育馆,南京政府时期改称民众教育馆。
④ 关于近代社会教育的发展阶段,目前学界有几种不同的划分意见。本文采用王雷的分期方式,将近代社会教育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萌芽期(1895—1912)、确立期(1912—1919)、发展期(1919—1927)、分化期(1927—1949)。这也是目前认可度相对较高的划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