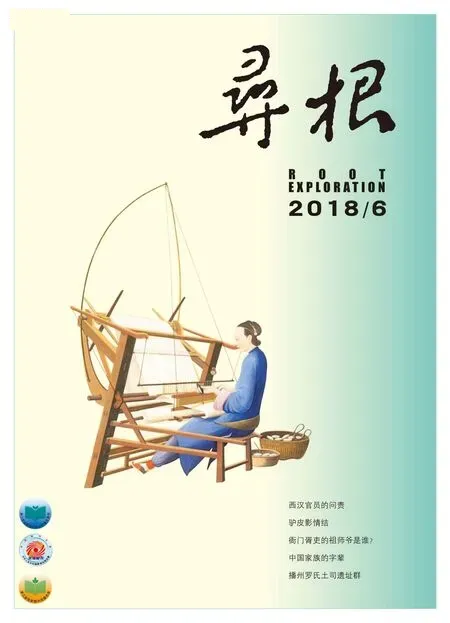童谣《张打铁》如何风靡南方
2018-12-14尧育飞
□尧育飞
徐珂(1869-1928)在《清稗类钞·迷信类·湘中童谣》中曾如是记载:
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刀送姊姊。姊姊留我歇,我不歇,我要回去学打铁。打铁一,苏州羊毛好做笔。打铁两,两个娃娃拍巴掌。打铁三,三两银子换布衫。打铁四,四口花针好挑刺。打铁五,五个粽子过端午。打铁六,六月不见早禾熟。打铁七,七个果子甜蜜蜜。打铁八,八个娃娃砌宝塔。打铁九,后花园里好饮酒。打铁十,十个癞子戴斗笠。打铁十一年,拾个破铜钱。娘要打酒吃,仔要还船钱。
文后另有注释云:“仔,小儿也。或曰张、李者,即献忠、自成之谶。其打铁一以下,均暗兆顺治以后年号,然乎?”徐珂所记载的这首童谣《张打铁》,不仅盛行于湖南,还流传于安徽、江苏、江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地。1937年,北大《歌谣》周刊刊登了张为纲《“张打铁”的研究》一文,文章梳理了25种不同的版本,遍布长江流域。可见《张打铁》是十分流行的一种叙事“母题”。那么,这首童谣最早起源于何时何地,又是如何在南方地区风靡起来的呢?
根据张为纲的记载,在20世纪30年代,《张打铁》这首童谣不仅仅用来传唱,它还与一些动作相匹配,实际上是一种儿童游戏。具体的游戏方法是:两个小孩分别伸出自己的左右手,互相合拢,交互摩擦一次,然后你唱一句“张打铁”,我唱一句“李打铁”,依次将左右手交互击打对方的右左手,如此循环往复,直到唱完,再循环几个来回。这个游戏并不难以理解,因为它的玩法与今天仍然流行的儿歌“你拍一我拍一”并无区别。至于它的传播路线,张为纲先生认为,《张打铁》最早可能起源于安徽安庆望江一带,然后分三路传播全国:一支东传,“流传到江苏江宁、溧水、溧阳、宜兴等地”;另一支往南,“流传到江西省南昌、临川、丰城等县,再经江西省往西流传到湖南省长沙、凤凰等县;由湖南省往南,又流传到广西省兴安、桂林等县”;还有一支则往西,“流传到湖北省罗田、汉阳等县,再由湖北省往西,便流传到四川省梁山、重庆、南充等县;由四川省往南,又流传到云南昆明、蒙化、腾冲等县”。经由张先生的梳理,《张打铁》的流传路线图较为明晰了。然而徐珂曾认为“张”指张献忠,“李”指李自成,颇让人生疑。
我最近翻阅《曹典球辑》,发现早在1954年,曹典球先生(1877-1960)即发现这则歌谣的最早出处:
天启时,南直有童谣曰:“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刀送姊姊。姊姊留我歇,我不歇,我要回去学打铁。”皆连臂而歌,手作打铁势。
又见明李介《天香阁随笔》。介,字介立,江阴人,《天香阁随笔》收入《粤雅堂丛书》中。此童谣余儿时尝歌之,而不知起于明天启时,录之以作谈资。
曹典球是湖南长沙人,为湖南近现代知名教育家,1895年因一篇《文选学赋》受知于湖南学政江标,后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湖南省代主席等职。通过曹典球的笔记可知,在清末长沙地区,《张打铁》这首童谣仍广为传播。而它最初见于文献乃是李介的《天香阁随笔》,李介即李寄(1619-1690),是著名旅行家徐霞客之子,其母为徐霞客妾,因不容于嫡,改嫁于李氏,故姓李。李寄历经明清鼎革,对明末历史有切身的了解。他在《天香阁随笔》第四卷的记载清楚显示,《张打铁》在明天启年间已经流传开来了。而李自成和张献忠起事在明崇祯年间,因此徐珂推测张、李二人的具体姓名肯定是不准确的。在民间歌谣中,张、李原本是极为寻常的姓氏,本不必寻求具体指代哪一位历史人物,但民间文化往往希望从童谣中解读出别样的隐喻来,譬如汉献帝时期,长安地区有童谣云:“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当时普遍的解读都认为这首童谣暗示董卓将以臣凌君。如此一来,童谣且带有预言的性质,颇有点类似《推背图》或《烧饼歌》。不过,研究者早已发觉历史上的此类预言都是“后见之明”,诚如著名学者李零所言——“这也是后人假托预言以证后事”。《张打铁》的歌谣传唱以后,李自成、张献忠起义,随后清军入关,天下大乱,等到顺治以后,神州大地才逐步安宁,所以民间将这段历史置放在童谣的理解中也不难理解。正如鲁凯特所著《流言理论和问题理论》指出的:“不论流言明确与否,它都会导致可操作性的建议、采取行动的指令或者不采取行动的指令。”清代中期对《张打铁》这一童谣背景的诠释,显示出清代人已经认识到李自成和张献忠的起义对社会生活的极大破坏,因此他们通过童谣反复提及这两人,似乎是以此告诫下一代,珍惜彼时较为安定的繁荣局面。
从李寄记载的版本,到现今诸多通行于各地的《张打铁》版本,充分显示了歌谣传承过程中的不稳定性。《张打铁》这一歌谣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在歌谣游戏的动作方面,明天启年间“连臂而歌,手作打铁势”,看来是两个儿童并排挽手站立,做打铁架势,散发着充沛的男子汉气息,而后来的拍手对唱,显然温婉了。其次,这种动作的改变,也与唱词的变化有关。天启年间的《张打铁》歌词十分短小,指向不明,因而具备很大的开发空间。四川成都地区的版本在“我要回去学打铁”之后,紧接着的是:“东家屋头有根蛇,把我耳朵嗷出血,我就哭到告爷爷,爷爷正在裹烟叶。我又哭到告婆婆,婆婆又在洗饽饽。我又哭到告爸爸,爸爸又在搓嘎嘎。我又哭到告妈妈,妈妈又在铲锅巴。我又哭到告娘娘,娘娘又在搽香香。我又哭到告哥哥,哥哥正在补砂锅。我又哭到告妹妹,妹妹正在翻柜柜。”湖北罗田地区的版本是:“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刀送姐姐。姐不接,留我歇,我怕姐的床上有臭虫,把我的耳朵咬一个缺。我要回去对爹说。”这种改写具备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即初版中的打铁符号蜕变为一个固定的言说模式,而起初略微提及的“姐—弟”亲情关系则得到极大的拓展。姐姐在后续衍生的歌词中占据的分量逐步增加,同时,家族中的父亲、母亲、奶奶、爷爷、哥哥等人也纷纷登场。这就使得这首童谣不仅是儿童简单的唱词,而且成为一个家族亲情的叙事,由此更具有人情味,也便于家族其他成员参与这一童谣的普及和推广。
总而言之,虽各地《张打铁》版本差异非常大,但其文本的组成结构则大致可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李寄所记载的简略版,另一部分则是此后衍生出的另一段歌词。其中,长沙地区所记载的从数字“一”到数字“十一”是最为流行的模式。这种数字模式童谣的流行,可能与儿童对数字的热爱和教育功能有关。
笔者新近翻阅《上海图书馆藏稿抄本日记丛刊》,里面有《何绍基日记》,其中末页杂项记载了另一个版本,即一种三段式的唱词,为此前各大民谣文献所未载,姑记如下:
打铁一,梳清羊毛好作笔。打铁二,两个孩儿拍巴掌。打铁三,三根头发拥金冠。打铁四,四口针儿爬出刺。打铁五,羊角粽子过端午。打铁六,六月禾苗不见熟。打铁七,盘盘果子甜如蜜。打铁八,百岁公公白头发。打铁九,后花园里好饮酒。打铁十,天上落雨地下湿。打铁十一年,年年打鼓找□船,找到灵官庙,拾个破钱。爷要打酒吃,□□讨婆娘。讨个婆娘拜,又□□□子三□□□个月,干也三年,湿也三年,□□又三年,□□□办里又三年,捡起来,卖□铜钱。
何绍基(1799-1873)生活于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年间,他记载的《张打铁》早于徐珂的《清稗类钞》,且根据何绍基的记载,在“打铁一”到“打铁十一”之后,似乎民间又增添出新的故事桥段,这个桥段说的是捡钱故事,“捡钱”也是民间故事的另一大母题。从何绍基的记载可以看出,从明天启年间到清中叶,历经200多年后,张打铁的故事已经从一段变为三段,而三段故事的拼接对童谣来说已经太长了,这对参与游戏的儿童来说可谓不堪重负。因此,何绍基之后,《张打铁》的歌词版本似乎又开始了精简的历程。譬如民国时期云南腾冲地区的《张打铁》版本为:“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子送小姐;小姐留我歇,我不歇;打到正月正,骑着花马看龙灯。打到二月二,两个铜钱四个字。打到三月三,荠菜花儿赛牡丹。打到四月四,四个铜钱八个字。打到五月五,糖包粽子送丈母。打到六月六,打开箱子晒霉绿。打到七月七,织女牛郎会此夕。打到八月八,八个老人打滑踏。打到九月九,九个娘娘来朝斗。”由两部分内容构成的《张打铁》版本得以流传到云南边陲,足以证明两段式这种改编的成功。

◇何绍基日记中的《张打铁》
《张打铁》选取民间较为常见的职业行当,又裹挟着晚明农民起义的历史大事件,具备隐喻和寓言的功能,因而在明末清初获得了极大的传播功能。伴随着明末清初各地人口的大迁徙,如“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这首童谣于是在整个长江流域和西南地区传播开来。在传播过程中,各地的儿童和文人纷纷对这则童谣进行本地化的改造,由此造成童谣歌词的版本歧出的现象。但最终固定下来的文本则是两段式的改写形态,这也足以证明民间文本虽然不稳定,但自有不可忽视的客观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