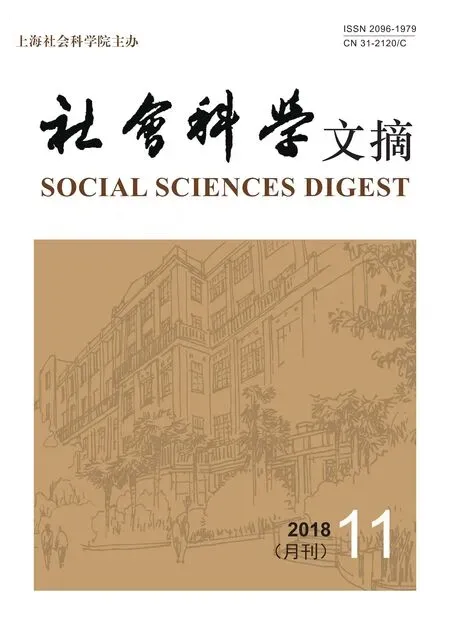中国刑法学研究40年
2018-11-17
如果以1978年为改革开放的元年,今年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1978年不仅是改革开放的元年,而且是法治建设的元年,还是法学研究的元年。以此作为一个时点,回顾我国刑法学科走过的40年历程,并展望我国刑法学的未来发展,是极具现实意义的。可以说,刑法学科是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恢复重建的,刑法学科的命运是与国家刑事法治建设息息相关的。因此,只有从国家法治建设的大格局下,才能描绘与勾画出我国刑法学科的发展脉络。
刑法学科的恢复重建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国民党六法全书的废止,我国开始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刑法典的制定也随之提上议事日程,我国1950年就着手草拟刑法典,由于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尤其是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对国家法制建设形成巨大冲击,刑法典的制定工作随之而停摆。在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从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的时间内,我国是在没有刑法典的情况下度过的,这对于一个具有7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在这样一个没有刑法典的时代,刑法学研究就成为一种学术奢侈品。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翻译出版了苏俄刑法教科书以及个别刑法专著。其中,较为著名的是1950年由大东书局出版、彭仲文翻译的《苏联刑法总论》(上下册)一书。除了上述苏联刑法教科书以外,影响最大且深远的当属特拉伊宁的《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一书。该书由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教研室王作富等人翻译,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50年代是一个政治上向苏联一边倒的年代,同样在刑法学上也直接嫁接苏联学说,在此基础上开始了我国刑法学的初创。
以1979年刑法颁布为契机,我国刑法学进入了一个恢复重建的阶段。这里的恢复重建表明,刑法学并不是完全从头开始,而是以原有的成果为基础的。当然,由于从1958年以后刑法理论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这个期间出版的刑法方面的书籍,基本上属于政治宣讲和政策解读的资料。及至1982年高铭暄主编的司法部统编教材《刑法学》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刑法学的恢复重建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该书前承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引入的刑法学理论,并吸收我国此后取得的刑法学研究成果,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对我国宪法条文进行了体系化和理论化的阐述,无论是在体例还是在内容上都有所突破,成为此后我国刑法教科书的样板。该书于1988年1月和6月分别获得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和司法部优秀教材奖,是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刑法教科书。
我国刑法学从20世纪50年代模仿苏俄刑法学开始蹒跚起步,不久就因为政治运动而夭折。此后将近20年,我国刑法学处于冰封状态。1978年开始,我国重建法制,尤其是1979年刑法典的颁布,犹如一夜春风来,顿时唤醒了沉睡已久的刑法学,使我国刑法学在一片废墟中萌发新芽。这段刑法学起死回生的历史值得追忆,值得铭记。
法律学科具有与法律规范的高度关联性,尤其是部门法,例如刑法,随着部门法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在我国各部门法中,刑法是立法最早的一个部门,因此刑法也是较为成熟的一个部门法学。我国刑法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以立法为中心到以司法为中心的过程。其中的分界点,是1997年刑法的颁布。换言之,以1997年刑法为标志,我国刑法学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97年刑法颁布之前,我国刑法学长期处于以立法为中心的研究状态;而在1997年刑法颁布之后,我国刑法进入以司法为中心的研究状态。
以立法为中心的刑法学研究
如前所述,随着1979年刑法的颁布,我国刑法学开始重新获得了生命,刑法学研究的春天终于到来。1979年刑法于1980年1月1日正式实施以后,刑法的司法化就成为刑法学关注的重点。然而,我国刑法学的司法化未及深入,刑法修改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因此我国刑法学很快就进入了以立法为中心的研究状态。对此,我们需要从刑法本身的先天不足和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等多维度地揭示其原因。
1979年刑法实施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随着新旧体制的交错,经济领域的犯罪大量出现。而1979年刑法还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上的,刑法与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抵牾表现为各种形式的经济犯罪。在这种情况下,1997年刑法难以应对惩治经济犯罪的现实需要。例如,在1979年刑法第117条设立了投机倒把罪,这是一个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犯罪。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以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被认为是投机倒把的犯罪行为都被认为是正当的经济行为,亟待对此予以非犯罪化。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出现的各种非法经济行为,例如我国《公司法》颁布以后,违反《公司法》的行为需要予以犯罪化;我国建立证券制度以后,违反《证券法》的行为需要予以犯罪化。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在经济领域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客观需求构成了推动刑法修改的内在动力。
此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进入一个社会转型时期。在此过程中,社会失范行为大量出现。尤其是黄、赌、毒这三种违法犯罪现象沉渣泛起,对此需要采取较为严厉的刑事处罚措施。但1979年刑法对于黄、赌、毒犯罪的规定相对简单,处罚也较轻。1979年刑法在其实施之初,就表现出对于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不适应性。因此,这个时期的刑法学研究,就刑法一般理论而言,主要是围绕着犯罪概念、犯罪构成、犯罪未遂、共同犯罪、罪数等犯罪论问题而展开。但理论热点问题还是刑法修改研究,相当多的学术资源投入到立法研究之中。我国学者曾经对刑法的修改与完善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80年的“1979年刑法实施”到1983年,为刑法修改研究的萌芽期;第二个阶段是从1984年到1987年,为刑法修改研究的出版展开时期;第三个阶段从1988年开始,为刑法修改研究全面繁荣时期。如果按照这个划分,则从1979年刑法实施不久,对该刑法的修改问题就进入了刑法学研究的视野。从1988年立法机关正式启动刑法修改,到1997年3月14日颁布修订后的刑法,在这10年之间,我国刑法学的主要课题就是刑法修改研究。
刑法修改研究是一种以立法为中心的研究,其目的是立法的完善。在刑法学中,这种以立法为中心的研究称为立法论。立法论的刑法学研究具有不同于司法论的刑法学研究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研究目的的特殊性。以司法为中心的刑法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司法机关正确适用刑法,因此具有司法导向,更加关注的是司法实践中刑法适用的疑难问题。而以立法为中心的刑法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为刑法修改提供正确方案或者意见,因此具有立法导向性,完全是围绕着刑法修改的节奏和需要展开理论研究。其二,研究方法的特殊性。以司法为中心的刑法学研究采取的是法解释学或者法教义学的方法,对刑法规定进行语言的和逻辑的分析与推理,以便在刑法适用中采用。而以立法为中心的刑法学一般都采用价值分析方法,对现行刑法规定的缺陷和不足进行揭示,并提出修改的意见和建议。其三,服务对象的特殊性。以司法为中心的刑法学研究的言说对象是司法实务人员,以及辩护人等与刑事司法活动具有相关性的人员。而以立法为中心的刑法学研究的言说对象是立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并且只有在立法过程这样一个特定的时段才具有意义。如果不在刑法修改时期,立法论的研究往往不具有现实意义。而且,立法论的研究不具有持续性,任何关于刑法修改的研究成果在立法修订完成以后,就阶段性地完成了历史使命,不再有其他作用。而司法论的研究则具有持续性,可以长期累积,为此后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因此,司法论的研究是刑法学研究的常态,而立法论的研究则是刑法学研究的非常态。在1979年刑法刚刚颁布实施不久,以司法论为中心的常态刑法学尚未成熟,随着刑法修改的立法进程的启动,我国刑法学就不得不跟随着开启了一段时间不算太短的立法论研究,从而推迟了司法论研究的进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当然,这也是迫不得已的。
我国以立法为中心的刑法学研究不是以现行立法为根据的规范性研究,而是如何完善立法的应然性研究。因此,主要研究内容也是以价值论为导向,以应然性为目的而展开的。
以立法为中心的刑法学研究对国家的刑法立法作出了重要贡献,推动了我国刑法的发展完善,这是不可否定的。尤其是,通过对刑法的全面修订,创制了一部统一的刑法典,即把所有刑事法律规范集中规定在刑法典之中,这就为此后的刑法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平台和框架。当然,在我国刑法学恢复重建不久,在没有来得及建立刑法解释学基础的情况下,就贸然进入以立法论为主导的刑法学研究阶段,对于我国刑法学发展带来了消极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这主要表现在对刑法规范的批判成为刑法学者的权力,而未能形成合理地解释刑法规范的传统。此外,立法论过于强势,刑法研究产生了居于刑法规范之上的习惯,不利于刑法教义学的产生与养成。
以司法为中心的刑法学研究
1997年刑法正式颁布以后,刑法修改终于告一段落,我国刑法学研究的重点开始转向司法论的刑法学。司法论的刑法学是建立在刑法规范基本完善的基础之上的,随着刑法修订的完成,这一条件也就具备了。1997年刑法确立罪刑法定原则,对我国刑法理论研究会带来重大影响,这就是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刑法解释理论。
刑法学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它具有跨越国界的性质,而刑法规范的效力才是受到国界限制的。随着德日刑法知识不断传入我国,我国刑法理论获得了更新与提升,中外刑法学的畛域也被破除了。刑法教义学带来的不仅仅是德日刑法理论,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分析工具和话语体系。以司法为中心的刑法学研究,是以刑法规范为依归的。因此,刑法规范是刑法学逻辑推理的出发点,并且是刑法理论的归宿。在司法论的视阈中,法律不是被嘲笑的对象,更不是被批评的对象,而是被信仰的对象。在以司法为中心的刑法理论中,首先应当注重对刑法明文规定的解释,阐发蕴含在刑法规定的文字之中的语义内容,从而为定罪量刑提供理论支持。与此同时,刑法规范也为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提供具有参照性的规则。
德日刑法知识传入我国并不断累积,从量变到质变,推动了刑法知识的转型。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以苏俄为模本的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与德日的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之间的摩擦和碰撞,并在我国刑法学界引发了一场具有影响力的学术争论。这场学术争论发生在2010年前后,争论的焦点在于犯罪论体系的选择。如前所述,四要件是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从苏俄引入的犯罪论体系。尤其是特拉伊宁的《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一书,对四要件理论在我国刑法学界的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四要件理论不仅成为刑法教科书的当然之选,而且随着学生毕业进入立法和司法领域,因而对于实务界也具有较大影响。由于四要件是刑法犯罪论的基本理论框架,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其他部门法学科的苏俄影响已经完全消弭,但刑法学科的苏俄影响却还是挥之不去。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我国学者曾经围绕着四要件理论的改造展开过讨论。但这种讨论仍然是在四要件的语境当中,对四个要件进行删减或者顺序调整,而并没有触及四要件的要害。因此,这一讨论最后不了了之,而没有取得理论的进展。及至1997年刑法颁布以后,随着更多的德日刑法知识传入我国,三阶层理论在我国不再是作为外国刑法知识被接受,而是成为我国刑法知识的主要资源。例如,笔者主编的《刑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首次在我国学者编写的刑法教科书中采用了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此后,我国学者认识到,四要件与三阶层的区分,并不是犯罪成立条件的数量之争,而是刑法方法论之争。这里的方法论,就是指阶层思维方法论。尽管目前在我国刑法学界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还具有较大影响,但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以其逻辑性与实用性,越来越受到青睐,在以司法为中心的刑法学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刑法理论的发展前瞻
经过40年的发展,我国刑法学科已经走过了褴褛筚路的草创阶段,经历了从以立法论为中心到以司法论为中心的刑法学转变,进入了一个以教义学为主体知识的阶段。因此,我国刑法学的教义学化将是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发展方向。笔者曾经提出“走向教义学的刑法学”的命题,揭示了教义学应当是我国刑法学的未来走向。此后,笔者又阐述了“刑法知识的教义学化”的观点,认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以立法为中心的法治实践将向以司法为中心的法治实践转变。相应地,也存在一个以立法为取向的法学知识向以司法为取向的法学知识的转型问题。刑法学也是如此。因此,我国刑法学将来应当以教义学为自己的走向。这是以司法论为中心的刑法学的更高发展阶段,也是刑法学演进的正途。
当前,在我国法学界存在所谓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之争。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对法学话语权的争夺。每个部门法学对于教义学研究的需要程度是有所不同的。一般来说,一个部门法学的教义学化程度与这个部门法的立法进度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性。当一个部门法忙于立法的时候,相关的部门法学是不可能发展教义学的,而必然以法律价值论位中心。只有当一个部门法较为成熟,完成了立法使命,建立起了一套基础性的制度和规则,相关的部门法学才能集中精力致力于教义学的研究。在我国各个部门法中,刑法无论是在立法的时间上,还是在立法的质量上,都是走在前面的。因此,刑法学的教义学化也是最早的、最为迫切的。
我国刑法学在教义学的研究过程中,需要引入刑事政策的内容,处理好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之间的关系,这是十分重要的。刑法教义学绝不是单纯的对刑法规范的诠释,其中必然包含了价值判断的内容。只不过,这种价值判断应当受到刑法规范的约束。以往在我国刑法知识中,刑法学与刑事政策是作为两个不同的学科而独立存在的:刑法学主要研究刑法关于犯罪与刑罚的规定,属于规范学科;而刑事政策主要研究国家的刑事立法政策和刑事司法政策,这些刑事政策对于刑法具有指导作用。在这种刑法学与刑事政策分立的状态下,刑事政策处于刑法之上或者之外。笔者认为,刑事政策不能自外于刑法学,刑事政策并不是对某一具体政策的解读,而是融合了刑事政策的一体化思考。刑法教义学不应该排斥刑事政策,而是应当吸收刑事政策的内容,以此克服教义学所具有的形式主义带来的僵硬性,保持刑法学具有对社会的即时反应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