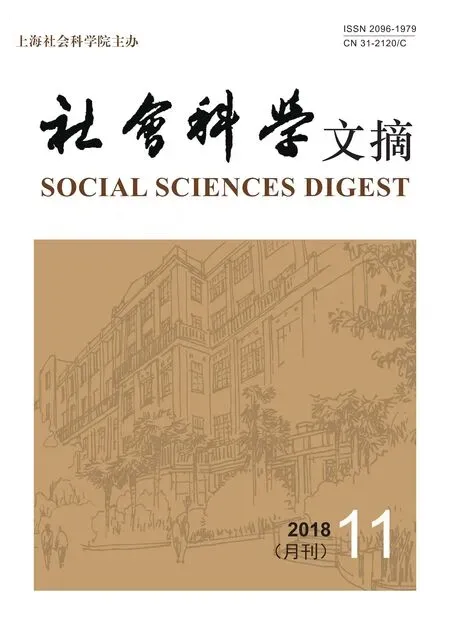改革开放40年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回顾、反思与前瞻
2018-11-17
对电影特性的自觉探索
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以自我正名和追求解放的奋进姿态构筑起了充满激情的文化空间。“大幅度地、大踏步地、放手地发展电影事业”成为推动中国电影打破文化禁锢、释放创作源泉的引领旗帜,创作自由与理论民主的观念迅即进入中国电影的价值观念系统,中国电影的文化生态发生深刻变革,为新时期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较为宽松自由的政治氛围。夏衍、陈荒煤、钟惦棐等老一辈电影工作者,以独特生命感悟滋润荒芜的批评原野,开拓出了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的新绿洲。这一时期,思想解放的演进逻辑开始主导彼时电影理论批评的发展走向,以现代理性为主调的新启蒙主义作为最具影响力的现代化意识形态,承继五四精神内核,凝聚知识分子的启蒙情怀,公开批判扭曲僵化的话语环境和思想路径,在理论批评和创作实践的双重空间内,建构起了关于电影方法现代化的精神理念和价值范式。为有力驳斥长久扼制国民创造活力的“工具论”思想,打破否定人性、人道主义的极“左”思想的桎梏枷锁,厘清自身属性、反思旧体制余毒成为电影理论的重要旨归,电影研究要回归自身话语逻辑开始成为业界共识。
罗艺军先生认为,80年代的论争与电影创作上的创新浪潮紧密切合,相互促进,是中国电影理论的黄金年代。1979年,白景晟的《丢掉戏剧的拐杖》,张暖忻、李陀的《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等文章的发表,响亮地提出了电影语言的现代化问题,标志着新时期电影意识最初的觉醒。与之相呼应,钟惦棐也及时提出了“电影与戏剧离婚”的观点,但他从来没有反对电影的戏剧性,而是反对动不动就用戏剧手段解决本可以用电影手段本身来解决的问题,甚至完全用戏剧手段代替电影手段。然而,当时电影理论界并没有从完整意义上去充分理解钟老的电影“离婚”说,造成了中国电影“重造型轻叙事”的偏颇发展。这一时期,关于影戏、影戏美学的大讨论亦如火如荼,陈犀禾、钟大丰等人以思辨性的姿态为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电影观念的革新以及电影本体论的探索生成了颇具“理论厚度”的宣言。
当电影理论界围绕“戏剧性”展开激烈争论时,电影与文学的关系也成为这一时期的理论焦点。在张骏祥看来,真正的电影文学的完成形式是最后在银幕上放映出来的影片,所以,导演的任务是用自己所掌握的电影艺术手段把作品的文学价值充分表现出来。这一观点触动了彼时业界所倡导的“电影是一门独立的艺术种类”的支配性理念,引发激烈争议。郑雪来的观点代表了当时电影理论的主要取向:即主张电影与其他艺术门类“分家”和“离婚”的理论“时尚”。如今回望历史深处,关于电影与戏剧、电影与文学的理论争鸣早已沉寂良久,本体论也在实践中愈发苍白无力。不过,近40年来的电影实践作出了现实回应:解构乃至颠覆了文学基础,导致中国电影长时间出现“瘸腿”现象,找不到“拐杖”,甚至发出“电影急需文学支撑”的呼吁。
历史充分证明,钟惦棐、张骏祥两位电影理论大师当年能够在追捧“电影性”的热潮中保持冷静平和的心态,辩证思考电影的戏剧性、电影与文学的关系问题,这种理论的自信不仅来自丰富的创作实践,还来自对真理的坚守和执着。事实上,我们的理论批评不仅要“向后看”,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还要擅于“往前看”,展开前瞻性思考和布局。当前在电影工业化的进程中,文学对电影支撑和支援的方式已经发生变化,文学改编电影这一创作性劳动开始趋向碎片化。然而,无论是文学还是电影,并没有充分适应互联网语境下的碎片化思维,仍需在长时间的磨合中找到新的支点,重新思考电影与文学的关系也必将成为构建中国电影学派的历史性命题。
这一时期,电影界也开始曲线引入西方理论资源,自觉探求中国电影通往现代化的路径。此间,巴赞的纪实美学理论作为中国电影革新的艺术旗帜,其引发的热潮正是中国电影界急于推翻旧有创作思想的心理使然,传达了彼时电影人对艺术创作自由的强烈诉求,以及对“政治工具论”的决绝反抗。正是理论界对电影特性的自觉探索,以破竹之势驱散了被意识形态高度控制的阴霾,其中倡导现实主义精神的“西部片”理论引发强烈反响。1984年,钟惦棐先生率先提出的“立足大西北,开拓新型的‘西部片’”理念,倡导拍摄有自己特色的西部片。他认为,即使中国今天还没有可称为“中国模式”的东西,也决不因此停止在这个方面的努力,“中国模式”也不应该是封闭性的。正是在这一理论的启蒙和影响下,《野山》《老井》《黄河谣》《秋菊打官司》等经典西部片亮相海内外银幕。这些有民族特色的扛鼎之作在国际影坛上大放异彩,开始推动中国电影走向世界。
电影理论批评渐趋差异化、多元化和复杂化
80年代中后期,不断革新的方法论也为电影理论批评拓宽了研究视野,电影本体性研究跃入更广阔的认知空间。以“谢晋电影模式”的讨论为例,朱大可曾批评谢晋模式是中国文化变革进程中严重的不协和音,是一次从“五四”精神的轰轰烈烈的大步后撤。但是这种精英式批评实则将谢晋电影视作“俗文化”,忽略了电影大众文化的本质属性,电影观念依旧封存于狭隘的认知范畴中。这次争论以钟惦棐的《谢晋电影十思》作为总结,钟老先生将电影与观众的关系放到电影本体维度来思考,充分肯定谢晋电影的大众性,认为谢晋的影片雅俗共赏、老少咸宜,谢晋是一个孜孜以求艺术与群众相结合的电影导演,并作出了“时代有谢晋,而谢晋无时代”的经典论断。
事实上,在精英电影话语为主调的批评氛围里,《黄土地》等为代表的先锋探索电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它们即便在市场上遭遇“冷落”也能够得到评论界的肯定与认可。而娱乐电影及其创作者被挤到边缘的位置,观众的狂热和理论批评的漠视见证了娱乐片的“冰火两重天”。不过,娱乐片的创作热潮随即打破了理论界意味深长的缄默,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电影本性,以“对话:娱乐片”为标志,从理论上阐述娱乐片的合理性,掀起了为娱乐片正名的学术争鸣。随后,文化人类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心理学等批评理论成为剖析娱乐片的新视角。
这一阶段,国内资深电影学者开始有选择地对西方电影理论进行翻译与推介,并积极与世界当代一流电影理论学者进行对话,力图从完整意义上把握西方电影理论体系。1984—1988年间,中国电影家协会连续5年举办暑假国际电影讲习班,诸如比尔·尼克尔斯、尼克·布朗等一批学院制体系下的一流学者,相继到中国教授和传播现代电影理论。在青年电影学者的集体推动下,符号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意识形态批评、精神分析批评等现代电影理论跃入批评视野,扭转了中国电影理论的薄弱局势。固然,学院派的电影理论批评浮现出更为科学化的样貌,但纯粹性的学院理论往往与电影实践相脱节,独立于创作实践之外的理论,无法真正地深度剖析中国电影现象,无法在实践层面指导电影创作与生产,只会陷入“自说自话”“闭门造车”的怪圈,以致丧失了构建原创的中国电影美学体系的机缘。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对中国电影产业快速发展的复杂态势,学院派电影理论批评日益彰显出捉襟见肘的尴尬。
进入90年代,电影本体批评、传统的社会学批评以及各种新潮批评方法论交相辉映,从整体上反拨和超越了单一僵化的理论批评模式。相较于以往以教化、引导为主调的批评范式,市场经济转型语境下的电影批评不仅显现出宏阔的视野、剖析的深度和范围的广度,还以其独立性、个性化、差异性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尤其是对多种批评方法的综合运用,形成了不少颇具影响力的高质量的电影批评,为低谷中行进的中国电影带来了理论智慧和方法启蒙。不过,这一阶段,在电影界乃至整个文艺界,理论批评领域也主动走向了分化。这也就意味着电影评判标准、评判维度、批评立场开始走向差异化、多元化和复杂化,电影界在众声喧哗中努力摸索着新的话语方式和生存路径,也发生着艰难的转型和蜕变。尤其是面对“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等类型并存的创作局面,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却找不到任何一种理论批评话语可以诉诸多元类型电影的完整表达。在新媒体语境下,中国电影理论批评一度陷入方法论空白的危机,甚至发出了“电影批评何为”的质疑和呐喊。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电影理论批评体系势在必行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媒介传播方式趋向多元化,网络影评以其灵活性、自主性和互动性迅速崛起,催生了与互联网语境相适应的批评新生态。21世纪以来,“后窗看电影”等网络电影论坛相继出现,成为电影爱好者的集聚地,尤其是随着博客、微博的开放,依凭媒介的力量激发了大众影评的新活力。还有像《今日影评》《老梁看电影》等电视影评栏目,充分利用电视媒体的影像优势,以通俗性与专业性相结合的叙述方式走近观众,依托各种媒体的立体化传播,以接地气的内容和形式引导当代影评的良性发展。近几年,炙手可热的微信影评开启了“人人都是批评家”的新时代,既有“当代电影杂志”等学术化影评,也有“豆瓣电影”等通俗化影评,还不乏“文慧园路三号”等个性化影评,它们共同凝聚交汇成当前电影评论的新潮流,以各种方式影响着当前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消费方式。可以说,多种媒介的交融为电影批评提供了更便捷、更广阔的公共话语空间。不过,也正是由于网络影评的互动性、匿名性等媒介特征,往往使影片陷入“恶意谩骂”等舆论困境之中,尤其是在资本利益的操控下,有些网络影评异化为噱头炒作的筹码,失去了应有的公信力和责任感。
在全媒体时代,学术性的理论阵地也发生巨大革新,中国电影理论领域一方面开始围绕产业、商业、市场等话题纷纷展开讨论,并以此为核心辐射出诸多的热点、现象和话题争议。随着不少新方法、新理论、新学科的出现,如产业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传播学等不同学科的方法论进入电影批评场域,形成了中国电影的多元认知体系,为理论批评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角,拓宽了学院派批评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电影界开始有意识地凝聚力量,挖掘、收集传统电影理论资源。如罗艺军的《20世纪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丁亚平的《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等书较为全面地收入了代表性电影理论文章,勾勒了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批评谱系,为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的整理工作开腔起调。由此,为了能够实现更好的继承,我们需要进一步细化和完善这些思想理论资源,在过去理论建设的基础上开拓创新,结合新的实践生发出更为丰盈的理论内涵,转化为当代电影发展的理论智库。
不过,面对日益繁盛的创作格局,当前电影理论批评缺乏科学的、差异化、包容性的类型评价体系,导致不少影片陷入片面狭隘的认知误区,挫伤了创作者的勇气。由于电影理论批评队伍知识结构的不完善:熟悉本土理论的未必了解西方理论,而熟悉西方理论的未必能掌握本土理论,当前还没有出现学贯中西的大师级人物,发挥不出应有的理论优势。这种尴尬往往导致理论批评陷入偏颇狭隘的境地,难以提炼出具有说服力的经典论断,也无法生发出掷地有声的批评话语。由此,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理论批评体系势在必行。我们要从当前中国电影的丰富实践中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电影话语体系,建构电影理论批评的中国学派,形成建立在当下中国电影实践基础上的科学话语体系、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
近两年,中国电影理论批评新力量正在崛起,既有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中青年学院派批评家,也有作为主流媒体、网络媒体、自媒体评论主力的影评人。他们逐渐成长为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的中流砥柱,而其身份、立场和表达方式的差异也形塑了差异化、多元化的批评景观。尤其是网络影评人,作为最具传播力和影响力的群体,表达方式生动活泼,充分发挥“隔空对话”的功能,有效化解电影界的误判、误差现象。网路影评的繁盛或将催生中国电影评论的“新黄金时代”。2017年成立的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网络影视评论委员会便是推动理论批评新力量的重要阵地。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倡导相互倾听和对话的理念理应成为业界共识。不过,无论是专业化影评还是大众性评论,必须要坚守伦理底线,与时俱进地改善自己的存在方式,积极匹配新媒体传播渠道。当前中国电影理论批评新力量崛起的速度、力度和强度,尚无法满足当前中国电影的发展诉求,只有补充和完善理论队伍的知识结构短板,关注当下中国电影实际问题,发出专业性、理性的、建设性的声音,才会打造出适应中国电影升级换代的理论批评体系。
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电影舆论场显现出日趋激烈的态势,作为舆论场制高点的话语权,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经济领域的定价权:有作为,才可以获得话语权、定价权;而无作为,则会被边缘化乃至被淘汰。尽管融媒体时代下所谓的“渠道为王”不容小觑,但是真正意义具有价值的理论批评,往往提炼于丰富的本土电影实践。这要求学者们在喧嚣糟杂之中努力保持一种学术定力和学术自信,积极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话语表达方式,善于利用多媒体、新媒体传递自己的声音,实现学术理论话语的大众化表达,以富有专业性、建设性的态度赢得公信力,真正为中国电影提供智库资源。
当前,构建“中国电影学派”的提出是对电影强国建设的一种积极回应,是中国电影繁荣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使然,更是电影界长期学术积累和演变发展的过程。它的提出承载着中国电影界的多重期待和多种诉求,并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沉淀明证其合法性、合理性与重要性。中国电影学派的内容建设将涵盖电影史学、创作、美学、理论批评、政策、市场、产业以及教育等领域,旨在有机整合电影的艺术、工业、文化和美学等层面。它在响应“电影强国”和“中国梦”战略号召的同时,将加快推动中国特色国家电影智库建设,进而形成理论与创作良性互动的、“产学研”相结合的、具有本土与国际双重视野的创新性话语体系。
中国电影学派不仅从百年中国电影发展史中汲取和提炼经验,还会凝聚数百位中国电影学人资源,形成具有文化内涵和精神沉淀的思想观点,为解决当前中国电影产业问题提供新的路径参考,以期增强中国电影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在国际电影理论批评版图上发出自己响亮的声音。作为兼具理论与实践双重期待的战略构想和方法体系,也必将激活潜存于百年中国电影发展史中的理论资源、创作经验和艺术传统,为当前中国电影产业探求新路径、新方法和新观念,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自觉中实现中国电影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