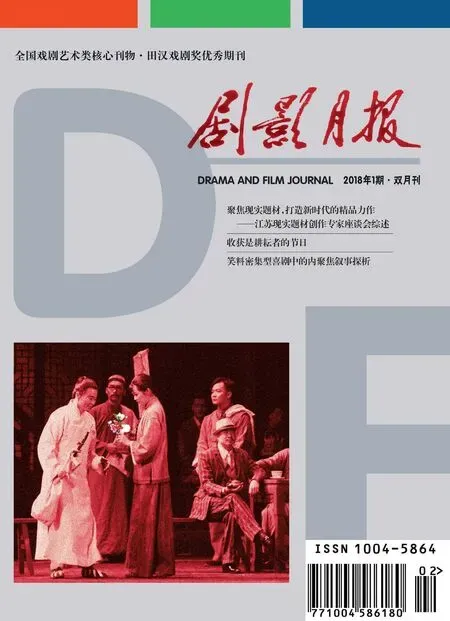表演艺术家司寿峰先生印象
2018-11-14高之均
■高之均
司寿峰先生生于1917年10月,曾用名司小奎、司奎官。原籍山东滕县,童年随其母逃荒颠沛来到徐州。一个没有进学堂读过书,更没有坐过科学过戏的穷家孩子,日后成了享誉徐淮地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探究原因,就要从其童年、少年、青年及至壮年这二、三十年间,在徐州这方传统文化沃土中成长、成熟的经历说起。
上世纪二十年代来末,徐州的京剧爱好者曾组织过一个票房,取名“正风社”,坐落在当时城隍庙东廊房内(位于现在的青年路市公安局原址院内)。司氏母子来徐州后便落脚在这里,负责看门、照应票友们活动时所需茶水等。“正风社”票房是徐州近一百年来第一个京剧爱好者组织。知名票友有赵鹤皊(老旦)、刘保祥(后改名为刘仲秋,工老生)、张金石(工老生)、李可染(琴师)、徐宜之(工青衣)、姜照初(工花脸)、程志启(工小生)等人。票房的艺术指导,是当时极负盛名的票界名宿苏少卿,苏先生不时组织票友们在剧场演出。
司寿峰来徐时不到十岁,在这样的氛围里便很快与京剧结缘。长大后个头高、两肩宽,又有些耸肩,活脱脱是一个架子花脸的胚子。加之悟性好、肯吃苦钻研,跟着这帮大人学了戏,很快便能登台表演。日寇占领期间为了生计,他正式下海唱戏,加入了“光明戏院”,该戏院坐落在现在的解放里(当时叫金谷里)。后来又曾去蚌埠混了一段时间,抗战胜利后返回徐州,不久便与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合股成立了“人民京剧团”,地址在市粮食局老俱乐部(现市三院对街附近)。几位合股人有票友王寿华,大中银行的张果为,金融合作社的赵某某,物华银楼的任廷枫,市银行的职员王文杰(著名电影演员王馥荔的父亲,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调入江苏省戏校担任琴师)。49年解放后,党和政府派了薛锦波、曲永庆等参与领导,正式成立“徐州市京剧团”。司任团长,张春安任副团长。此后又吸收了大同街“胜利戏院”不少演员,其中就有来自北京的名丑张文元。1951年胜利戏院迁建新院址,改称“人民舞台”。五十年代,司寿峰正值壮岁之秋,精力充沛,不仅组织领导一个剧团,而且几乎天天都参与演出,演艺大进。
“人民舞台”四个隶字为黄龙先生所书写。遒劲有力,磅薄大气。黄龙先生也是一位名琴票,主拉京二胡。落成典礼时,是由张金石同父小弟金潭先生介绍,由来自北京的以言少朋(马连良弟子)为首的新华京剧团举行首演,阵容强大。旦角有张蓉华,武生黄元庆,花脸周和桐等,轰动一时。正因为那个时期能与来自北京、上海等地来的名角同台演出,司寿峰戏路逐渐拓宽,眼界也上了一个层次。后来剧团事务越来越多,他便在后台管理(旧称坐钟,现在叫剧务),也当过舞台监督,还兼任工会主席,成了整个剧团不可或缺的人物。
发生在解放前的两件事可诠释司寿峰学戏时曲折刻苦的过程。《法门寺》中刘瑾有句台词“见了洒家,为何不抬起头来?”结果小小的他上台后一时紧张,背的词竟成了“见了洒家,为何不头起抬来”?结果很长时间给观众留下笑柄。还有一次戏刚散场,脸上的油彩还没有来得及洗掉,他就急忙跑出后台,在离去的观众中找到一个经常来看戏的,看似有文化的人请教戏文中不认识、不会念的字。教他认识“窈窕淑女”四字的文化人叫李家惠,建人民舞台时,他的商号“李同茂”捐过款,场场都可以免费看戏。
试想若司寿峰从小不随其母从山东来徐讨生活,很可能一生与京剧无缘;即便日后干了这一行,恐怕也很难成为一个受人敬仰、故去三十多年仍能让我辈后人记得住的京剧表演艺术家。
我认为是徐州这方文化热土培育、造就了司寿峰。徐州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四省交界,五省通衢,和平年代乃是商贾云集之地,人口流动量大,用旧时戏班的话来说,徐州是个大码头!被称之为“一代帝王乡”的名城,传统文化根基深厚,喜爱国粹京戏的群众基础广泛,学戏、演戏、看戏、品戏这个文化消费市场需求一直很热、很旺。
大家都有体会,欣赏喜欢上一门艺术,是在一个特定氛围里面,于潜移默化之中而被“熏陶”出来的。这门艺术日后便会成为其生命的一部分。如果进而痴迷进去,如唱京戏,那就要拜师学艺,唱念做舞,一字一腔;手眼身步,一招一式,都必须规范讲究。如同写毛笔字,要有章法一样,不得自由率意。到了这个层次,才能说有了“文化”。此处广义之文化,似乎与这个人读过多少书、识得多少字并没有太大的因果。具备了这种“文化”后,便会对所钟情的艺术门类有了自信的审美眼界。它既是痴迷者经过长期的实践累积而成,更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师者口传心授的教诲、浸润中“熏陶”出来!换言之,作为习学者,纵观他日后的成就,一方面与之潜心修行下的苦功及悟性有关,更与其授教者本身的艺术水准之高下,息息相通。因为只有在他们东风化雨、润物无声的言传身教中,追随者才能自觉不自觉地对所学艺术的内涵、修养、气韵获得日深一日的心灵感受。
司寿峰是幸运的,在其最初成长的十余年间,知遇了几位贵人的提携、呵护与培养。
刘仲秋,曾拜李洪春为师,专攻老生,擅长唱功。l931年在南京考入了梅兰芳、余叔岩创办的国剧传习所。1937年,他与同学刘英等赴西安抗战,组建了“夏声剧社”,第二年他主持创办了“夏声剧校”,担任了繁重的教学工作。他先后任第三野战军文艺工作第三团副团长,华东戏曲实验学校副校长、东北戏曲学校副校长,中国戏曲学校副校长。长期从事京剧的教学工作,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京剧人才。当年他对司的教诲最多。还有一位梅大师的学生郭荐英,和仲秋师长一起,时刻提携这位后生,能给他们配的花脸戏总让司上台参与表演。十年动乱时期,刘校长被下放到天津青先农场。1972年8月在该农场病故。
李可染,“正风社”第一把胡琴。最初得苏少卿先生亲授,之后苏又介绍他拜孙佐臣进一步深造。他长司寿峰十岁,给予司的教诲也很多。可染先生15岁考入上海美院,22岁又考入杭州国立艺术部研究院。次年回徐州老家与苏娥完婚。从此夫拉妇唱,开启了这对志同道合伉俪近十年的戏曲生涯。纵观其一生,拉胡琴是可染先生视为生命的爱好追求,而绘画则是他的“第二职业”。两年前的今天可染先生于1964年完成的一幅“万山红遍”(当时由荣宝斋以80元人民币收藏),场外竞拍最终以一亿八千四百万天价成交。李氏三十年代的琴艺与他六十年代的画艺是完全可以相匹配的。惜哉!现在的人们对艺术的品评往往只看重有形的财富,而忽视了某些触摸不到的,非物质的,然而又极其珍贵的文化价值。夫人苏娥得乃父苏少卿亲传,工青衣,比司寿峰大七、八岁,对这位名叫“三柱子”的小兄弟格外呵护,也总让他来配戏。苏娥女士28岁患上斑疹伤寒,生下第四个孩子便撒手人寰。此时徐州已沦陷,之前,可染先生已携小妹去武汉,投奔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的郭沫若先生,融入抗日洪流。
张金石,长可染先生两岁,两个人意气相投,还都在不满二十岁的年龄段上便与诸多乡贤:阎咏百、王琴舫、王继述、萧龙士、王子云、王寿仁共同发起,于1924年创建了徐州市第一家艺术专科学校。金石先生也工老生,供职于市银行。加上家道殷实,对票友演出活动多有赞助。上海解放前夕,金石先生随其供职的农业银行去了台湾。值得一提的是46年他在上海为小弟张金潭极其风光地筹办了拜李慕良大师的拜师仪式。有了这层关系,二十刚出头的青年学子有一段时间便能经常到马连良大师住处为其吊嗓。这也是金潭先生晚年经常提起的最引以为荣的经历。建国之初,金潭先生又赴京拜了尚小云先生,并在尚剧团工作了一段时间。纪念徽班进京二百周年之际,笔者随金潭老师去北京,到家中拜谒了李慕良大师夫妇,与祖铭、祖龙兄弟遂成朋友。离京前探望了尚小云大师遗孀。半年之后长荣先生(中国戏剧家协会前任主席)来信,寄来了他为我们与其慈母在尚小云大师巨幅剧照下拍摄的合影,并告知老人家已驾鹤西去。
苏少卿生于1890年,早年投身于文明戏,是我国话剧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在日本期间,孙中山先生在极为繁忙的革命工作之余还曾到演出的后台看望过苏少卿及演职人员。后来他又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京剧艺术,成为我国京剧史上著名的教育家、评论家。孟小冬拜余叔岩为师前曾拜他为师。少卿先生离开徐州后当过记者、办过报纸、编过戏,还在上海电台创办“空中教育”,教戏长达二十年之久。他的锦绣文章是上海舞台演出的忠实记录,臧否人物,干预倾向,提倡“健康”艺术,为广大内外行所服膺。特别是在全国评选四大名旦难解难分之际,是他的文章,一语定乾坤,平息各种争议,终使“梅、程、尚、荀”排序获得圆满解决。1957年经田汉同志推荐,少卿先生由沪赴京到中国戏曲研究院工作,在京呆了八年,主要讲授京剧的音韵学。1971年终老于上海浦东东沟地区的一所农宅里。
少年的司寿峰,有缘与上述这些名人雅士相识,并得到他们的引导、提携、教诲、熏陶,走上京剧表演事业之路,实在是一生经历中的大幸事!生于斯长于斯的仲秋师长、苏李翁婿、张家公子,他们这辈先贤得徐州大地山川之精华,集文气才气逸气于一身,禀赋天成。他们口含珠玑,袖透幽香,指下琴声玉振,笔端丹青飞扬,终成一代大师、宗师,既成就了自己,也培育了后人。他们德馨永泽,精气长存,为我们徐州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有形的和无形的财富。我们徐州人在弘扬戏曲艺术、繁荣群众文化的事业中,当以上述先贤为骄傲为榜样,怀着满满的文化自信,去拥抱给我们带来更加美好生活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