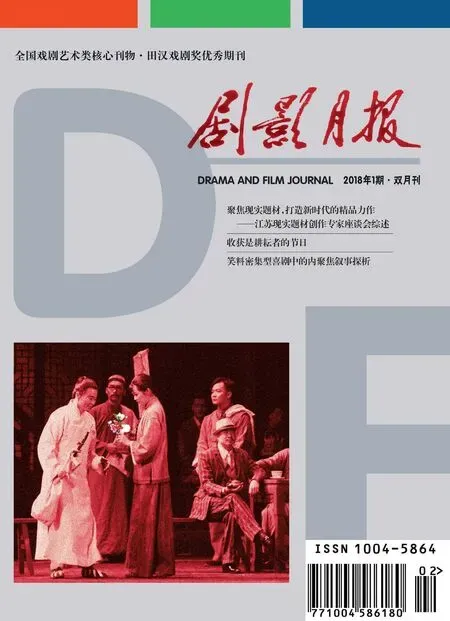穿越“克劳德镜”的反思话语
——读周安华著《亚洲新电影之现代性研究》
2018-11-14张斌宁
■张斌宁
在今天这样一个被人们戏称为后后现代的碎片化世界里,谈论现代性是否仍有意义?这是我打开周安华新著《亚洲新电影之现代性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2017年12月版)时蹦出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即亚洲新电影“新”之何在?
先说第二个问题。亚洲电影无疑首先是个区位概念。虽同属亚洲,但东亚的中国(台湾、香港)韩国和日本,东南亚的越南、泰国、新加坡,西亚的伊朗以及南亚的印度等在历史沿革、社会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其实有着天壤之别。相较于它们的共性而言,其差异更为夸张瞩目。毋宁说,亚洲电影这个概念只是在地缘政治的层面上对亚洲各国电影创作所进行的一个抽象、含混甚而草率的描述,它的底色多少透露着一种无可奈何的勉力与挣扎。而周著的特殊贡献在于,他仅仅通过一个“新”字就为这个先天不足的概念赋予了一种时间向度,使得我们可以同时在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方面去考察亚洲各国的电影生产与传播。它的要害在于,经由时间性的介入,亚洲电影的内部肌理得以伸展,获得了被充分描述的各种可能和潜在空间。正如该书所界定的那样,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以在亚洲各国此起彼伏的“新浪潮”运动为标志,亚洲新电影各个国家之间的比较视野得以建立。由此,对外,相对于以好莱坞为标的的西方主流电影,亚洲电影整体上呈现一种虽松散却坚韧的“突围”形态;对内,亚洲新电影各个国家间互为参照,此消彼长,在竞争中探讨和发现各种对话合作的有效途径,凸显不同国家间由时间差带来的现代性进程及其效果,从而构建起一个关于亚洲电影文化政治生态圈的立体模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精准的描述了亚洲电影,为后继的现代性研究厘清了概念障碍。
众所周知,现代性是欧洲启蒙学者基于科学理性精神对未来社会进行的一个整体哲理规划,其核心在于主体性的确立。在质疑、批判和反思的过程中,工具理性压倒了价值理性,过分注重效率和构建秩序的倾向常使主体感到虚无、焦虑,自由似乎渐行渐远,人类不得不从源头开始怀疑一切,从而滑入利奥塔所谓的知识游戏规则紊乱失效的后现代情境。此间,幸有哈贝马斯独出机杼。在他看来,遑论后现代,现代性本身尚属一项未竟工程,其中仍有很多议题亟待澄清。看上去,现代性就像一座烂尾楼,这边的沉渣还未来得及清理,那边后现代大厦的奠基仪式已然喧嚣尘上,浩浩汤汤弥漫过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而使问题更加扑朔迷离。而作为后发现代性国家,对于以中国为首的很多亚洲国家的电影生产与传播,在剥离时间差之后,回到源头,从现代性的视角而非后现代性去考察,无疑是一个更为冷静更为严肃的选择。正如周著本身所言:“现代性为电影提供了一种新的审视维度,即电影作为社会病症的反思之镜,理应对现代社会发展的后果、危机、道德和意义困境予以关注,形成一种社会现代性预估、诊断或者批判的审美范式,这正是亚洲电影现代性命题应具的题中之义。”
在周著看来,这种审视维度最关键的落脚点在于亚洲新电影主体性的确立,以及由此形成的亚洲新电影的他者及其主体间性的转变关系,它直接关涉到亚洲身份、亚洲文化以及亚洲作为一种方法的可能性。《亚洲新电影之现代性研究》的作者认为,就亚洲新电影的具体语境而言,所谓主体与他者这对哲学范畴实质上对应的正是民族文化与文化全球化/西方化的问题。换句话说,这个主体性的确立有助于从根本上厘清亚洲新电影民族性与现代性的辩证关系,即,如果说亚洲电影的现代性解决的是它与自身电影传统的关系,那么亚洲新电影要解决的则是“霸权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冲突,外来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冲突以及新型技术文化带给民族文化的挑战”。譬如说,在区域合拍过程中,因资本、技术、人员、语言、故事(历史、空间)等因素导致的流动性和混杂性,其现代性特征远远大于参与各方自身的传统,这种斡旋博弈就是亚洲新电影的现代性命题之一。因为这当中的主体身份与他者凝视是一个互为你我、动态平衡的复杂过程。而如何对待它们的关系和权重之转变正是现代性进程带给亚洲新电影的挑战。此问题的解决会避免将主体性看作铁板一块,而忽视了它内部的各种变量。这也是为什么该书倾向于将亚洲新电影当作复数性质来看待而并非单单强调它们的单一性。
不同于以往很多著述谈及电影现代性问题时的模棱两可和语焉不详,周著另外一个特色是比较明晰地区分出了电影形式的现代性和电影观念的现代性。这其中,形式上的现代化特征须得依附于内涵上的现代意识,否则,皮之不存,毛将附焉,电影现代性终将沦为一句空谈。这样一来,无论是中国的贾樟柯、侯孝贤、杨德昌;还是日本的北野武、岩井俊二、是枝裕和;韩国的金基德、奉俊昊、张哲洙;越南的陈英雄、包东尼;伊朗的马基迪、阿巴斯;泰国的阿彼察邦、沙赞那庭;或者印度的米拉·奈尔、拉库马·希拉尼等,这些乍看上去风格迥异的作品都能够在观念层面上获得相对统一的解释。也即,主导它们的首先是现代观念而非仅仅是对现代电影技巧的吸纳扬弃。由此,一个共性与个性互为表里、异质多元的现代性主体就呼之欲出了。在论证观念层面的现代性时,该书从亚洲独属的物候、饮食和仪式等角度出发,将其视为联结个人感觉体验和集体历史经验的“社会快感结构”,不仅从中读解出亚洲新电影“天人合一的韵味和意境”,而且将其看成一种抵御西方现代性的有效方式。譬如越南影片《恋恋三季》利用越南气象的旱季雨季再加上虚拟的“希望”之季,将越南的殖民记忆、阶层分化在现代性进程中被倾轧的尴尬状况表露无遗,委婉地批判了西方现代性的冷漠无情。又如《樱桃的滋味》中,从现代文明世界逃离出来想要自杀的主角,最终将“人生的艰困与乏味,于小小果实的丰富滋味中得到消解”,从而使“人与世界的关系,也在樱桃中达成了和解”。这种读解,使得抽象的观念得以借助小小的符号被具象化,变为真正可感知得到的对于西方现代性的含蓄批判,也证明了亚洲文化内含“沙粒世界”式的睿智辩证思维,可以在终极意义上帮助人类达至自由的境地。
通过对主体性的探讨和对形式现代性与观念现代性的辨析,周著敏锐地注意到亚洲新电影现代性的建构逻辑与欧美等先发现代性国家的逻辑迥然不同,而这种差异及其潜在的诠释价值正是今日语境下探索亚洲新电影现代性的意义所在。在作者看来,亚洲新电影的现代性命题从根本上讲,就是如何借助作为现代媒介隐喻的电影技术本身去处理本土文明在面对文化全球化时所产生的文化焦虑。具体而言,它由以下几组矛盾构成:“一是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发现之间的转化;二是西方现代性话语之于本土文化的适用性;三是产业背景下电影艺术策略的两难选择。”至于如何解决这些矛盾,《亚洲新电影之现代性研究》给出的答案十分简洁,即审美救赎。不止于此,该书还详尽分析了不同时期的审美救赎之道。如果说昔日的侯孝贤、阿彼察邦们以克制隐忍、含蓄内敛又不乏诗意的长镜头为旨归,以确认差异来建立美感秩序的话,那么当下的徐峥、吴京们却正是通过对好莱坞主流电影语法的娴熟运用与改写来寻求观念上的突围与沟通。譬如《泰囧》《港囧》《战狼2》《横冲直撞好莱坞》等这类异域旅游作品,通过将故事发生地设置在传统修辞上的边缘地区和发达地区,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对现代性中心的置换和反讽,将旅游视为现代性危机的解决之道,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消解了现代性批判中的主体身份位移问题。
十八、十九世纪,很多画家或旅行者常常随身携带一块被称之为“克劳德镜”(Claude glass)的黑色凸面反射镜,他们借助它来观察自然。经这块镜面折射后的景色能为现实赋予一种幽微神秘的整体性,从而达成某种“理性的增魅效果”,在现实和经由媒介建构的景象之间诠释一种迷人且内含矛盾意味的修辞风格。在我看来,现代性就像那块“克劳德镜”,我们透过它观察到的亚洲新电影既熟悉又陌生,既理性又神秘。而《亚洲新电影之现代性研究》所做的尝试,就是为读者在那块镜子后面安排了一个位置,于安全距离之外静静反思,足以令人沉迷,却不至于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