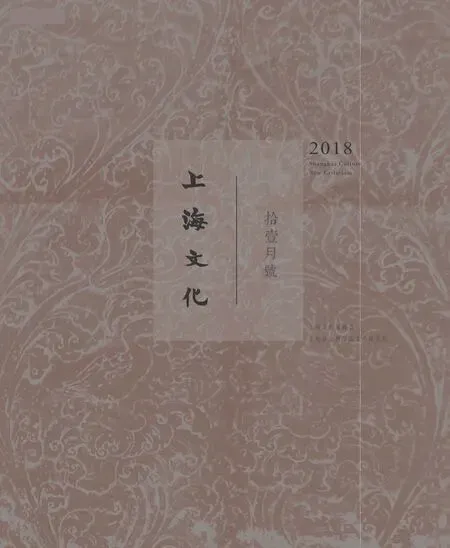奥登态度和修辞的改变 ①
2018-11-06贾雷尔
贾雷尔
连晗生 译
我们从未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赫拉克利特
在这篇文章第一部分,我想分析奥登在他早期诗中为自己所设定的总体位置,并呈现他后来的诗迥然不同的态度如何从其发展而来;在第二部分,我将描述早期诗的语言和近期诗的修辞,并试图显示为何一个自另一个发展而来,我已经从一本非常好的书——肯内特·伯克的《面对历史的态度》借用了几个术语——我乐意因此而承认。
一
他意识到深刻的异化,智力上的、道德上的、审美上的——甚至金融上的和性上面的
日期是1930年,地点是英格兰,奥登(及其打成一片的朋友群体)不能或不愿接受他发现自己身处其中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权威以及总体的世界图景。他意识到深刻的异化,智力上的、道德上的、审美上的——甚至金融上的和性上面的。既然他拒绝已建立的秩序,对他而言,找到或创造他和他的容器能藉以拥有世界的一种新的秩序、一种神话是必然的了。奥登合成了(或多或少如同消化器官合成酶)自己的秩序,借助于多种资源:1、大体上的马克思-共产主义。2、弗洛伊德和格罗代克:大体上的,现代心理学冒险和非科学的、然而丰饶且富有想象力的一面。3、一系列相关资源:民间的东西,血统的东西,直觉,宗教和神秘主义,传奇故事,寓言,诸如此类——这里面包含着许多半法西斯因素。4、科学,特别是生物学:这些对他而言似乎是可利用的,因为它们只是部分地被资本主义文化同化,并且就像数学,实际上它们不能被它所腐化。5、所有男孩子的价值资源,飞行,极地探险,爬山,打仗,科学激动人心的一面,公共学校生活,运动,大尺度的恶作剧,“间谍生涯”,等等。6、同性恋:如果普通的性别价值观被视为消极而被拒斥的话,这作为一种积极的革命的价值观资源就能被接受。
奥登能建立一个我们(他与之联为一体——伴以拒斥)对立于敌人的他们,我们和他们都不是人们在政治或经济分析中找到的相对清楚或简单的实体,而是由诸多元素构成的各种庞大丛集,这些元素来自几乎每一种资源:奥登有兴趣建立一种二分法,在此之中,一方理所当然地获得所有它最坏的东西,而他想要这所有最坏之物尽可能的完整,以覆盖从帝国主义到在信中给太多的词划线的所有事物,读者或许冷漠于他们一些或大部分的腐坏特征(bad points),但他们被给予这么多东西以至最坚定的鸵鸟也会在某一点上崩溃继而认同奥登的拒绝。奥登需要一场全面的战争,一种全面的胜利;他没有犯那种政治错误,即占据一个清晰有限的位置而把其余的一切留给了敌人。他倾向于把他喜欢的一切给予我们,把他所不喜欢的一切给予他们,有时这种资质从灵巧的掠过变成确定的天才——或不真诚的东西。我打算在最大范围内处理这种我们-他们的对立——对它的一种处理实际上是对奥登早先位置的处理;我将搀杂在某种我已列出的价值资源的讨论之中。
他倾向于把他喜欢的一切给予我们,把他所不喜欢的一切给予他们,有时这种资质从灵巧的掠过变成确定的天才——或不真诚的东西
奥登是这样开始的:旧秩序的死亡不可避免;它在经济上已腐烂、道德上已崩溃、智力上已破产,诸如此类。我们=未来,他们=过去。(因此任何读者倾向于跟随我们和那持续的胜利者,未来。)当然,奥登从马克思主义获得这些;但任何时候他都不是一个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会意味着放弃太多东西给敌人。他保留着马克思主义者所拒绝的各种各样的东西,而他最珍惜的一些信条——正如读者会看到——和他的马克思主义有直接的矛盾。在信仰最终的强制性层面,他的马克思主义大部分一点点地消失(而在过去几年,已经消失);对奥登来说,他的精神分析的、含糊的医学信念是如此更加基本—— “医生与护士之子,承载着一个梦”——以致他或许想使之符合马克思主义要旨的诸多寓言一直证明是精神分析学的。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能量资源,作为一种积极而悲剧的洞察力的资源是不可估量的;极其需要它来抵制消极性,抵制对理解、爱和神的信任,后者在奥登看来是地方性的。马克思主义一直提供了他诗中的大部分恐惧;在最近的诗中,保留下来的所有东西是遗憾——一种病人的饮食,像牛奶吐司。
很明显,他们代表商业,工业主义,开发——而比这更坏的是,一种衰败的商业,一种其机器已经在腐烂的工业主义,奥登已经看到发生在漫长衰落期的英国的事情,而他对这种情况做出浪漫式的、美丽的、有效果的延伸,不仅仅进入衰落,而且进入了整个制造业实际的崩溃,一个韦尔斯式的国家,在那里,商业和运输业已支离破碎,在那里,船只“长,高而干燥”躺卧着,在那里,没人走得“比铁路终点或防波堤尽头更远?”在那里,专业旅行家“火炉边被询问……沉默无言,”这些诗最好的是《诗篇》中的第二十五首:大事件之前的历史,某人善感而奢侈的心告诉他。(偶尔,这种视野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在这里奥登找到了一个象征,其变体对他来说难以释怀的,对于读者、另一种机器的孩子来说,是适度地强制性的:长着草的矿坑,废弃的矿层,淤塞的港口,抛弃的产品——这些,连同没带来什么的电线,没人踏足的铁轨,对于奥登,一个想要成为矿业工程师、“爱一个水泵式引擎,/认为它处处/美丽如你”的男孩而言,完全是感人肺腑的。那些思绪,萦绕着被抛弃并腐烂在潮湿乡间的“从未讲话的、但让小男孩/崇拜它们的机器,” ——早期奥登甚至在乡村环境看到他的机器——可能(无意识地)就像一些政治或人道主义关怀一样影响深远。


奥登从那些不讨人喜欢或被轻视的东西中,选择了自己的先辈,创造了自己的传统




如果我们有邪恶的事物要说,糟糕地言说它们,甚至女童军也不受其害;但如果我们糟糕地言说“具有精神和价值的”东西,那我们不仅损害了它,而且有助于替代或怀疑我们希望保存的已表达过的善
所有力量崩溃,绝对力量绝对的崩溃。政府,一种必然的恶,摧毁了统治者
只是奥登是如何成功地从近乎共产主义者到相当的自由主义者转变的呢?他没有在环境的压力下转化;早在任何环境改变之前,他就通过一条古老而怪异的道路——神秘主义——做出他的进步。在奥登的中期,人们发现一种越来越集中的全神贯注,伴随着一系列相近的观念:所有力量崩溃,绝对力量绝对的崩溃。政府,一种必然的恶,摧毁了统治者。所有行动是恶的;意志是恶的;生命本身是恶的。唯一的逃脱在于避免行动,放弃意志。我不是说,奥登完全或实际上接受了所有这些东西——谁这样做了?但他或多或少为这样的理念(完全地与马克思主义对立;十分投缘于精神分析学的一种松散延伸)所迷惑并运用它们:如果所有政府是恶的,为什么我们还信任一种恶的选择,为它而死呢?如果所有行动是恶的,我们怎能信任做任何事情?如果意志本身是恶的,为什么选择、计划、行事?生命是恶的;对于理想终点的沉思,当然好过特定的意志和行事,好过如此频繁邪恶的手段。


我们是健康,他们是疾病,奥登从弗洛伊德和格罗代克获得的所有东西,被用来把他们放进病人的类别中,放进无意识地驱动自己的疾病的患病受难者的类别中。这让我们的反抗对他们而言不仅仅是善的,而且也是必要的——我们的暴力是医生的暴力,他们的对立是疯子面对精神分析家的对立。我们是生命,他们是死亡。死亡冲动对于他们的行动是基本的动机,奥登已说过或暗示过;如果他们否定它,他就反驳说,“当然你们不会意识到它。”

我们是生命,他们是死亡。死亡冲动对于他们的行动是基本的动机,奥登已说过或暗示过
我惊奇地看到了大多数重要的仪式因素(净化,再生,认同,诸如此类。)在早期诗歌中是被多么持续地发现的
需要死亡,谷粒的死亡,我们的死亡,
老家伙们的死亡;将他们离弃
在没有亲友的愠怒山谷,
春天时被遗忘的老家伙们,
无情的贱妇和骑马的大师,
直僵僵在地下;而在明澈的深湖,
新郎慵懒卧躺,无比俊美,就在那里。
Needs death, death of the grain, our death,
Death of the old gang; would leave them
In sullen valley where is made no friend,
The old gang to be forgotten in the spring,
The hard bitch and the riding-master,
Stiff underground; deep in clear lake,


二
在考虑奥登最早的诗时,人们很少找到什么来谈论特定类型的修辞,却有许多东西来言及一种特定的语言。(后来的诗恰恰相反。)人们看到,早期诗中最好的是多么有效果,多么具体,令人吃惊,完全实现它们的肌理;但经过分析后,人们发现它们令人吃惊地非修辞化,吸引人的、韧性的魔力效果不是由任何精细的修辞所完成,而是由各种各样的原因引起的,它们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语言——普通英语的一种具体的、简洁的、古怪的变体。(它或许来自在霍普金斯、乔伊斯和盎格鲁-萨克逊语言倾向的某些延伸。)甚至当奥登没有运用这种个人语言时,他规律性的言辞因为它而更坚韧、更紧张了。关于它更重要的特征,我列出一个名单: (1)冠词和说明性形容词的频繁省略。(2)主语,特别是“我”(“I”),“你”(“you ”),“他”(“he”),诸如此类的频繁省略。(3)“在那里”(“there”)和类似的介绍性词语的频繁省略。(4)并列连词、从属连词、连词性副词、诸如此类的频繁省略,甚至介词有时被省略。(5)关系代词的频繁省略。(6)助动词的频繁省略。(7)持续的倒置,正常的语序有意识又有效的改变。(8)不寻常的标点符号:一种决定性的隐性标点符号(underpunctuation) 是常见的。(9)为了指示习惯性行为,经常偏爱动词胜于名词。(10)减少副词、形容词或任何或许可被省掉的词,另一方面,有大量的动词、动词词组和名词。结果是一种强有力的言辞。(11)频繁的并置,通常是非语法性的。在这些诗中,奥登想要延伸或打破语法或句法规则。(12)运用虚悬分词和其他虚悬的修饰词。(13)一种混成词的生造——对于伊丽莎白时代人是普通的——在它之中一种限定词组关涉它前后的东西。(14)词的重复或词的部分重复;这与拟音词或同样生造的词有关联。(15)应用独立结构。(16)头韵、半谐韵、和韵的频繁运用,诸如此类。(17)非协调元素作为协调元素来运用。(18)运用不寻常的同位语或古怪得不寻常的同位语的。(19)古词或古文结构偶然运用。(20)频繁的歧义——通常有效,有时仅仅令人迷惑。(21)词序的省略,有时是大量的,有时在逻辑上频繁地跳跃,在那里人们要在没获得什么句法帮助下获得一个意义。(22)非常长的并列结构,通常是省略的;句子成份甚至可能被句点分开。(23)修饰语远离其所饰之物(有时相当远)。(24)一个同质的或有点专业化的词汇表的运用。(25)一种词性作为另一种词性的运用:形容词作为副词,副词作为形容词,动词或介词作为名词,诸如此类。(26)将与句子的任何部分没有惯常句法联系的成分插入到一个句子中。
有许多更为重要的特征。这是一份明显没有给读者关于这种语言的效果或价值的观念的名单;我希望读者自己会找到实例和较次要的特征——我没为它们留出篇幅,也没给予这语言及其效果任何完整的评价。对我而言,它看上去大体是成功的;在其最好之处,是杰出的。将它作为一种古怪的语言局限谴责是容易的;我打算将它界定为一种创造性的拓展。我想,人们可以显示,早期诗的力量和美好(通常原创到似乎有相当魔力)存在,是因为这种语言,或它在奥登有规律的语言上产生的效果,否则,便不可能被获得。这语言适合他要说之物(或产生新的合适的要说之物)。它是原创的,不仅仅是古怪的;它是“建构的”,不仅仅是为了打破而打破的转换。让我为它召来伊丽莎白时代人的防护盾吧。(如果有读者不熟悉早期诗的语言,我请求他不要仅凭我的特征名单就对这些意见做出任何评判。)
在奥登后来的诗中,语言变得较为虚弱。它相对地被动和抽象;充满副词、形容词、不及物动词,等等。和他辉煌的“动词年份”的言辞比较,它似乎苍白而无效。但这种修辞变得更强大了,在后来的诗中有一个修辞手段如此精细的系统,奥登或许把它列在资产之下,正如一个公司列出它的专利。我会分析这里面的许多手段;有时会给出许多与之相关的实例,既然我要显示它们是典型的,既然我想要读者欣赏这满满的分量和它们应用的范围。
奥登探索得最为全面的修辞准则(修辞家们应该用他的名字辨认它)之一,是一种演说家的喜好的倒置:一个令人惊叹的抽象词,被放入一个具体的诗意的语境
诗歌的肌理多大程度上依赖于诗人对词的不同层次和变动范围、对并置(有时令人震撼,有时几乎难以觉察,其词语来自不同领域或谈话的中转站)的最大敏感,几乎不能被夸大;不过要是能够,阅读奥登是这样做的一种方式,每个人会认出伊丽莎白时代人的“粗俗而充满面包”(gross and full of bread)公式和演说家的喜好——一个具体的词插入一个抽象语境;但许多表现更好的方案不被称赞不被分析,即使被感觉到。奥登探索得最为全面的修辞准则(修辞家们应该用他的名字辨认它)之一,是一种演说家的喜好的倒置:一个令人惊叹的抽象词,被放入一个具体的诗意的语境——一般来说,未被预料的抽象的、批评性的、“非诗意”的词语来自相对抽象的技术的、谈论的、“非诗意”的语域,替代被期待的、具体的姐妹们。这种技艺的持续使用,是让奥登的诗被攻击为放松或抽象的诸多事物中的一种。这种技艺,像它的对立面,是多种多样的不协调效果(Effect by Incongruity)。这里有一些——来自许多实例的若干例子,它们中大多数会相当明显,既然那些不太明显的,过于依赖一个大点的语境或确定的语调而不便引用:

奥登常用的另一个公式,是迥然相异的同等物的并置:这包括伊丽莎白体的形容词公式和它朝着三四个不规则的同等术语的扩展
这类事物并非奥登的发明,比重音诗行更多东西的是霍普金斯的诗;但它的官僚化,它作为一个重要修辞原则的系统运用,我想是新颖的。它是诗歌措辞的对立面,在那里抽象作为必要和正确的诗歌语言被想到;这里,效果依赖于对立的观念,依赖于诗的语境(基于与表达的形象的联系)仍然具体这个事实。

当然我们的城市——随着可怜的牛栏直至
河边,是教堂,引擎,狗儿们;
这里有世界性的烹调术
轻合金和玻璃
Certainly our city—with the byres of poverty down to
The river’s edge, the cathedral, the engines,the dogs;
Here is the cosmopolitan cooking


我们学会了我们以前会认为不可能或不存在的微妙变化或延伸;但我们在让我们一度充满恐惧的质与量上,不断地容许我们自己过度。那是许多风格——不仅仅是风格——退化的方式
关于这些修辞技巧,以及很大程度上构成风格的那些机制和持有专利权的识见的可怕的东西,是它们习以为常的,风格在数量的不断增加上的所需之物。我们学会了我们以前会认为不可能或不存在的微妙变化或延伸;但我们在让我们一度充满恐惧的质与量上,不断地容许我们自己过度。那是许多风格——不仅仅是风格——退化的方式。风格的纯正,像其他东西,是某种必须始终努力的东西,一种斗争——像睡眠、吃饭或生活——仅容许暂时胜利;没有什么比我们克服恶习的知识更易让我们受恶习的感染了(人们过去对之辩解,似乎以某种方式给予他们忽视它的权利。)。

这样的词有其魅力所在,它保留了经验真实的鲜活;也有一种真正振动与之相关


奥登身上大量的“早期浪漫主义”因素模糊地根植于某种类似于此的态度。我希望我阐述的语调,看起来没有否定它真实的不确定的效果;这是衰弱的、但不是因此魅力更少的危险技巧之一。这种词汇的运用后来退化成显而易见的感伤;同样的结局等待着奥登最初是小玩笑的爱鸽韵律(love-dove rhymes),这种玩笑在诗最后的语境有一种深思熟虑的可怜的决定性。


我现在来到某种可怕的机制,而我打算用更为可怕的称谓——不协调透视的官僚化——来压制它
我这么挥霍无度地、呆板又不协调地行文,因为奥登已如此;他完全到处官僚化他的手段——因而充满灾难——如任何效率专家可能希望的那样。它是一种可以运用在任何材料上的方法:一种有专利权的、在数量上可保证产生见识的过程。不幸的是,质量不能被保证。收益递减律非常快地到来;诗人的受众(其成员之一就是诗人),这么容易厌倦不协调,如同厌倦一种气味,诗人必须供应越来越大的数量,但那已越来越没有效果。读者在我早先的引用中,已看到奥登对这种手段的应用的许多实例;存在足够的例子给几代批评家;我将只描述一个,一种奥登用来表达人的空间隐喻。

子在此会需要做出这样的评论。
被朋友弃下,独自吃早餐,在意大利
白色的海滩,他那个可怕魔鬼
在他肩上浮现;深夜独自饮泣,
一个脏兮兮的风景画家憎恨鼻子。
残忍的好奇的他们军团
人数众多且壮硕如狗;德国人和小艇
扰得他心烦意乱;关爱有数里之远;
但经由泪水的指引,他成功抵达了悔恨。
欢迎仪式多么奇异。花朵们接过他的帽子
赢得了他,引介给火钳般的人群;
魔鬼的假鼻逗得一桌人大笑;一只猫
即刻带他疯狂跳起华尔兹,让他握紧她的手;
众声喧哗推使他到钢琴边唱滑稽歌曲;

Left by his friend to breakfast alone on the white
Itlalian shore, his Terrible Demon arose
Over his shoulder; he wept to himself in the night,
A dirty landscape-painter who hated his nose.
The legions of cruel inquisitive They
Were so many and big like dogs; he was upset
By Germans and boats; affection was miles away;
But guided by tears he successfully reached his Regret.
How prodigious the welcome was. Flowers took his bat
And bore him off to introduce him to the tongs;
The demon's false nose made the table laugh; a cat
Soon had him waltzing madly, let him squeeze her hand;
Words pushed him to the piano to sing comic songs;
And children swarmed to him like settlers. He became a land.
诗存在于两个层面上,像对位法——也就是,像一种对应,其中一个层面须由听者补充
我不会带着意见请教读者——不过我愿意提及我不能以斜体标出的虚悬分词。所有人会看到,这么一种修辞过程有多么机械,多么自觉地拥有某种意志;在以斜体标出这些词时我已没有对人不公——它们已被这位诗人用斜体标出来。现在随着奥登把人类看作英国乡村的两页的一个奇喻,我引用的名单抵达一个壮观的高峰。但——是两页啊!我不得不无力地终止于对《新年书信》一种最直白的提及。
到此为止,这种名单的采集对读者已必定暗示了一种归纳:即奥登在后来的诗中极大程度依赖于技巧。我现在可以把种种技巧的名目加到我的名单中;但我将发现的乐趣留给读者:奥登不仅仅模仿乔伊斯、惠特曼及其他人,而且甚至滑稽模仿一系列乔叟的技巧。另一种延伸的技巧,不完全是修辞的,决定性地影响了一首诗修辞的肌理。它或许是被称为固定风格的东西:一首诗老老实实地限制在某个相应的传统中。这或许甚至抵达它的限度,戏仿诗;无论如何,在原型和“副本”之间的互动是持续且自觉地产生效应的——如果读者不能意识到诗依赖于一个标准与其偏离之间的关系,诗将被严重地误解。诗存在于两个层面上,像对位法——也就是,像一种对应,其中一个层面须由听者补充。奥登,对一首诗的特别功能和惯有样式有着一种敏锐的感觉,没有迹象显示他幻想一首诗能作为诗人本人的诗或诗歌的范型,而他经常为了这些有限的成功而努力。当他写下一首大众诗歌,看到批评家发现他“受流行歌曲影响”总是一件乐事;这就像发现艾略特的法语诗“受法语影响”,或发现柴可夫斯基的《莫扎特风》(Mozartiana)“受莫扎特影响”一样。今天我们不擅长于惯有样式,我们更乐于要求讲道来自石头,书本来自溪流——从每一首诗中,获得“比它所给的更多东西”(那正是它的惯有样式妨碍它给出的东西);如果我们是诗人,我们甚至也许试图去提供那“更多东西”。奥登有八种或十种类型;读者会记得它们中的大多数,因此不需要另一个名单。(《新年书信》中许多偶然的效果,甚至来自于这种资源。)另一种喜欢用的而非常值得注意的技巧,是长长的、机械地采空了的奇喻。

但这种走向抽象的退化,对奥登来说是不可避免的,是他整个发展的反映。对一个熟知其作品的批评家来说,奥登的发展有如此多的因果统一性,如此逻辑地、适当地装配在一起,以致这位批评家难以忍受把这个整体打乱为分析的片断,而感觉就像叔本华所说的:所有这一切是一个单一的思想。对奥登而言,发展并依赖这整个修辞机制是必要的,因为他的诗歌,他的思想本身,已越来越抽象化、公共化和散文化了。这些修辞技法构成了一个准科学方法,借助它你能让任何素材获得修辞性效果,甚至已死的或半生不死的东西,也能被刺激成一个活体,(这种方式更适合于教诲性或阐释性的诗歌,而不是抒情诗:所以《新年书信》比起奥登最近的抒情诗更为成功——他在用宜人的主题和宜人的技巧工作。)最早的诗不需要、也不拥有这样一种修辞。
奥登想要让他的诗更好地组织化,更有逻辑,更为正统,更可以接近,诸如此类;怀着这些可真诚称颂的意图,从他早期的作品开始,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他试图奔跑着穿过一系列巨大的改变,如此之快以至他的抒情诗近乎被毁灭。是否我可以用一种散漫的比喻性语言来谈论,这语言适合这种感觉:这后来的技术和素材似乎是挪用的,而不是挣得的——一种空洞无根的后逐,没有必然给予它意义的前物。早期的许多诗由于奥登的整个存在而产生,无意识的东西像有意识的东西一样多,必需的制作犹如它们应当如此,它们中最好的有形状(就像木筏或鹅卵石),似乎是产生它们的力量的直接表达。后来的大部分诗犹如直接指向产生它们的力量:脑袋,脑袋,脑袋顶;准确的、推理的、理想主义的、感伤的智性。尼采说过可怕的一句话:欧里庇德斯作为诗人,本质上是他自己意识的一个回声。对奥登最近的诗来说,不采用这种判断是困难的。
尽你所能写一首好的朴素的诗歌,并发现它在大多数读者心中,是足够使人喜泣的
但分析,甚至对缺陷不友好的分析,是一种显示欣赏的方式

奥登已成功地让他的诗更为人所理解;但这种成功完全太昂贵了。意识到1920年代最好的诗歌过于难以理解,我们可能想要我们的诗歌可以理解——但在我们完成之后多少诗可以得以留存呢?我们的政治关注或人道主义关注,或许让我们想要我们的诗面向多数群体;努力使这些群体更接近诗歌,把这些关注转化为政治行动或人道主义行动,这样更好。最好的动机毁灭得同最坏的动机一样快;而通往灵薄狱的道路恰恰铺满因为最好的动机已做了一切的作家们——我抱以同情,而不是讽刺。所有这一切是一个困扰现今多数诗人的问题;尽你所能写一首好的朴素的诗歌,并发现它在大多数读者心中,是足够使人喜泣的。1920年代典型的解决方案(诗歌是必要的晦涩;如果读者不能获得它,让他去读勃朗宁夫人)和1930年代政治诗典型的解决方案(诗歌必须写的为人民所理解,否则就是颓废的逃避主义;诗歌是公共演讲——借用麦克利什令人厌恶的说法,因而让人想到伪君子们的公共祷告)是不恰当的无知,荒诞的半真半假的陈述。一种古典主义的理性而又荒诞的解决方案,是温特斯及其学派的解决方案,其想要的、小心限制的居高临下的说话,结果成了一种道德儿语。奥登更为吸引人的解决方案已运行得更好;它过于有意识、过于单薄、过于单一的理性:我们不信任它,正如我们不信任任何成圣的理性途径。我不打算试图告诉读者,这个方案是什么,但我可以告诉他在哪里找到它:在次一流诗人的作品中。对于奥登所写下的最好的诗,一篇如此的论文或许是一种不尊敬的回报;而我感到尴尬,在给出——即使在这样一篇有限的文章——这么多的分析和这么少的欣赏之时。但分析,甚至对缺陷不友好的分析,是一种显示欣赏的方式;而我希望在下一次尝试另一种方式。
❶ 贾雷尔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南方评论》(1941,秋季号),自那时就激起文学圈强烈而不同的反应,对此文中的不同看法也可见于许多人的文章中。此文在作者车祸去世(1965年)四年后,即1969年被收入后人所编的《第三本批评集》(The Third Book of Criticism,Farrar Straus and Giroux,New York,1969)中,本中译文即根据这本书译出。贾雷尔对奥登作品有着复杂的感情,对后者一直持续地阅读,在1951-1952学年,受约赴普林斯顿大学作关于奥登的演讲系列。在演讲过程中,贾雷尔曾将此文拆为两部分(即一部分论“态度”,一部分论“修辞”),作为其中两次演讲的主体部分。对比原初版本和后来的演讲稿可知,后版本对前版本有少量的改动和增删,主要在于时间表述的调整(如“最近的诗”改为“中期的诗”等)、个别词语的完善(如把一些“激进”用词改得稳妥周到)、某些段落的补充(如普鲁斯特小说里的话及里尔克的诗),删掉了若干内容(可能由于演讲需要),等等。由于贾雷尔的演讲稿晚至2005年才被整理为《贾雷尔论奥登》(Jarrell on Auden)一书出版,因此大范围的读者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接触到的是原来版本。我已译出贾雷尔的演讲稿,但鉴于对原版本的历史面貌(保留着一种“批评的激情”以及它对大部分读者的“震撼”效果)和相较后版本的某些价值(如对奥登早期语言特点的详细描述)的看重,故同时将它译出。由于这篇文章写于1941年或之前,贾雷尔的批评显然未涉在此之后的奥登作品,因此他在文中的时间表述(如“最近的诗”、“中期”)也应参照这时间点;而为了让读者对贾雷尔的所指有更准确的了解,我也根据后来的演讲稿,在某些注释中说明了它们后来相应的改动(个别时间表述所在的句子或段落后来在稿讲稿删去的,则未对之说明)。此外,为方便更进一步研究,注释中也参照了《贾雷尔论奥登》中的相应注释,其中EA、CP、Plays分别是以下书籍的缩写:The English Auden(London:Faber and Faber, 1977)、Collected Poems (New York: Vintage, 1976)和Plays and Other Dramatic Writings, 1928-1938, by Auden and Christopher Isherwood(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由于奥登早期诗最初仅以数字排列,收入《诗集》时才起名,我在标示贾雷尔引诗出处时,尽量注出它在《诗集》中的标题。本译文在奥登若干诗句或诗的题目的翻译上受益于马鸣谦、蔡海燕的译本《奥登诗选》(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在此致谢!
❷ 肯内特·伯克(Kenneth ,1897-1993):20 世纪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修辞学家。
❸ 格奥尔格·格罗代克(Goerg Groddeck,1866-1934):20世纪著名精神分析家,弗洛伊德的同时代人,他也是身心治疗法的倡导者之一。格罗代克把精神病人的外在症状比作未完成的艺术品;他通常会把病人的症状推至极端,以此迫使病人找到实现自己目标的更好渠道。
❹ 贾雷尔后来在演讲稿中,加上:“这是艺术,不是政治——让每一个相关的人有时感到困惑”。
❺ 来自奥登的《“地球翻转,我们这一边感受寒冷”》一诗,其准确的表述应是:“我,它们的作者,站在这些梦之间,/护士和医生之子,承担了一个命运。”见EA,145。
❻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通称H·G·威尔斯,英国著名小说家、新闻记者、政治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创作的科幻小说对该领域影响深远,如“时间旅行”、“外星人入侵”、“反乌托邦”等都是20世纪科幻小说中的主流话题。
❼ 以上所引的诗皆出自“《诗篇》中的第二十五首”,即“Who would endure”一诗(见EA,34-35),该诗后来收入《诗集》(Collected Poems)更名为《这地方没有变》(No Change of Place),有改动。❽ 这里出自奥登的诗《沉重的日期》(Heavy Date),见CP,261。
❾ 这里指死于一战的英国诗人爱德华·托马斯(1878-1917)。
❿ 贾雷尔可能记忆有误,据他后来的演讲稿版本可知,他这里指出的是《维纳斯此刻有话要说》(Venus Will Now Say a Few Words)这首诗,而它在《诗篇》(Poems,1930)中是第三首。《诗篇》中的第四首是“Watch Any Day His Nonchalant Pauses, See”(该诗后来在《诗集》(Collected Poems)中更名为《一个自由人》(A Free 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