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与世界名著《根》
2018-10-16
最近在做讲座的时候,我偶尔会提到美国黑人作家哈里的小说《根》,并说这本书与档案的关系可大着呢!如果不是因为完善的记录和档案保存,或者说哈里完全没有档案意识的话,那么世界上就不会有《根》这本书出现了。甚至,美国反种族歧视的运动也就难以巩固既有成果并形成足够的社会同情,因而黑人的地位也就难以发生持续根本性的改变,当然奥巴马是否能够当上总统也就难说了。讲到这里的时候,台下总会有疑惑的目光看着我,我想一定有人在心里嘀咕:胡扯吧,想说档案重要便吹得没有谱了。

◇《根》作者亚历克斯·哈里
只是,我是学历史出身的,讲什么都格外讲究证据。《根》,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不能说不深广,而档案,对《根》的出现不能说不关键。

◇198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中文节写本《根》封面
一
对《根》这本书,熟悉的人一定不少。四十多年前,该书就风靡美国,如今已是众所周知的世界名著。中文系的同志们大约还知道,当年这本书是作为“非小说类畅销书”走向公众的。在1977年4月,美国国家图书奖委员会还郑重地将历史类奖项授予了《根》,因为它本来就是一部“非虚构的历史作品”(亚历克斯·哈里著,郑惠丹译:《根》,译林出版社,1999年,“前言”)。
30多年前,本人在大学阶段曾买到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英语注释版《根》的节选本,记得开篇即是《根》的写作经历(其实是将原著的最后部分移到了最前面),因此对其中档案所起的作用有一个大致的印象。于是,刚开始给学生讲档案文献编纂学的时候,便拿《根》《红与黑》《基督山伯爵》这样的名著当例子,告诉同学们,不少有影响、有生命力的艺术创作也是受益于档案的。
节本的信息自然不完整,哈里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寻根之旅和心路历程?他在如何的情形中查阅到档案?又因为档案解决了写作中的哪些问题?会不会没有档案就没有《根》的问世呢?带着这些问题,我开始翻阅《根》的不同版本,包括中文译本和英文原版。在图书馆工作的弟子张艳很是支持我的工作,几次在校图书馆和湖北省图书馆为我检索相关文献。
我希望对其中情形有一个清楚的了解。以我无比低劣的英文水平,尚能对英汉本子的情况作些自己的判断。感觉1999年译林出版社的本子似乎更接近于原文,于是我据此先将《根》的故事又重温了一遍,在有兴趣的地方还会拿另一译本比较。
亚历克斯·哈里怀着身份迷茫的苦恼和强烈的认祖归宗意识,以及为上千万美国黑人同胞捍卫文化尊严的使命,通过十二年的不懈追寻,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根”。原来,他的第一代黑奴祖先康达·金特(即书中的“金塔”)是从非洲冈比亚河畔的一个村落被绑架并运抵美洲的。
可以说,这是一次艰难而奇特的寻根之旅,而哈里整个寻根的过程和关键节点,又完全离不开档案的助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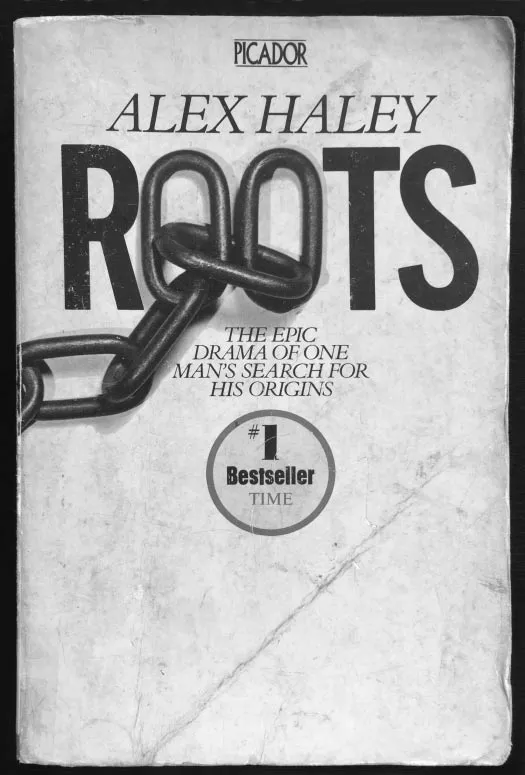
◇1977出版的英文版《根》封面
二
哈里从小就受到口述历史的熏染,“外婆和其他老妇女不断地灌输”“家族历史”给他(同前引,645页),这些不断强化的印象,成为他寻根的主要线索。
打小时候开始,哈里就发现外婆和姨婆们每次聚会都会重复谈论一些“相同的事”,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才意识到,这些或许就是“家族世代累积下来的历史”(同前引,628页)。这种历代口耳相传的习俗,这种独特的非洲家族记忆模式和文化传承,使哈里对家族史寻根有了越来越强烈的冲动。他清楚地记得,传说中的那个非洲人被海船运至美国的“纳波利斯”,然后被一个叫“约翰·华纳”的农场主买去为奴并取名“托比”,可每当其他奴隶这么称呼他时,他都会厉声纠正自己叫“金塔”。在第四次逃跑失败后,他被伤了脚,为好心的威廉·华勒医生所救,于是跛行的“金塔”得以长期在新主人的菜园里工作并获得信任,还能为主人驾车。“金塔”和一个叫“蓓尔”的厨娘结婚并生了“济茜”,他牵着“济茜”的小手到处散步,并用非洲母语指认不同的事物,譬如指着吉他叫作“可”,指着玛那波里河叫作“肯比·波隆河”等。后来,“金塔”开始用英语对女儿讲自己、非洲族人和非洲家乡的故事,告诉她自己是准备到森林里砍木头作鼓的时候被几个家伙掳走并运至美国为奴的。从此,“金塔”的后人便历代相传着同样的故事,直到哈里听到外婆和姨婆们谈论“同样的事情”。在“金塔”的后代中,有斗鸡界颇具名声的“鸡仔乔治”,他和一个叫“玛蒂达”的女人结婚,生养了八个孩子,其中第四个儿子汤姆因铁匠手艺为人称道。汤姆全家被卖到北卡罗来纳州阿拉曼斯郡一个属于“墨瑞主人”的烟草农场,之后与具有印第安血统的女奴“爱琳”结了婚。到哈里的父亲这一辈,已是俄亥俄州州立大学的硕士生,并且是农业机械大学的教授了。作者哈里则在大学期间(二战爆发)入伍美国海防队当了传令兵,在服役的二十年间,他因擅长写作而兼任“战地记者”,且“初期的写作都是以美国海防档案资料处的海事记录做基础”(同前引,645页),写一些海上探险故事。退伍后,哈里开始了职业作家的生涯,作品包括口述访谈和人物传记《马尔科姆·艾克斯自传》,这些经历无疑为后来《根》的写作打下文笔基础。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的中文译本《根》封面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的中文译本《根》扉页
三
真正促使哈里踏上寻根之旅的正是那些关乎档案的事物。
20世纪60年代初,哈里在伦敦地区参观,当他在大英博物馆里看到“罗塞达石碑”(Rosetta Stone)时,竟被它“深深地吸引”了,他立马“在博物馆内的图书馆借了一本书以便仔细地探讨研究”(同前引,633页)。“罗塞达石碑”(如今档案界将保存久远的理想载体称为“罗塞达盘”)于1799年由法国军人在埃及港湾城市罗塞塔发现,在英法两国战争中转到英国人手中,自1802年起保存于大英博物馆。石碑上刻有三种文字,一是为人所知的希腊文,一是当时无人认识的文字,一是认为已绝对无法译说的象形文字。但经法国学者商博良的配对解读,原来是三段内容一样的记录,这块制作于公元前196年的石碑,刻有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登基的诏书。
望着这块历时几千年却仍能被解读的“罗塞达石碑”,哈里在想,口传下来的远祖“金塔”这个名字,一定暗含着祖先所在的部落信息,还有他所讲的“可”“肯比·波隆河”,这些个语音尖高且均带有“K”字头的奇怪非洲音,究竟代表了何种非洲语言呢?虽然因时间的久远或许已在传播中失了些原形,但也应该遗传了祖先家乡母语中的语音片段,自己是否也可以用学者考释“罗塞达石碑”的方法去尝试解读这些带着先祖信息的“密语”呢?
哈里决定先去看望外婆辈唯一在世的表姨婆并确认那些尚存的重要非洲元素。当他说出寻根的愿望后,卧病在床的表姨婆深情地表示支持他的计划,并说“所有的祖先都会在天上看顾着”(同前引,635页)。在寻根的过程中,哈里的内心一直充满着对先祖的敬爱和对历史真相的激情。
正是早先的口述访谈和写作训练将哈里引上了一条正确的寻根之路——依据口述史查阅档案记录,通过档案记录印证口述历史。
不久之后,我到华盛顿特区的国家资料档案处,告诉阅览室的人员我想借阅南北战争北卡罗来纳州阿拉曼斯郡的人口普查记录,于是卷卷的缩微胶卷便送到我面前来。透过机器,我读着一千八百多名不同人口普查员用旧式文体所写下的一连串密密麻麻、排列无止尽的长串名字,这引起我相当大的好奇心。在看了几卷冗长又累人的胶卷后,我惊叫了,发现自己的眼睛正注视着:“汤姆·墨瑞,黑人,铁匠;爱琳·墨瑞,黑人,家庭主妇……”紧跟着是外婆姊姊们的名字——大部分我都已在前廊上听过外婆提了无数次。“伊莉莎白,六岁!”在普查的当时,外婆甚至都还未出生!(同前引,635页)
哈里从遥远的口述史中走来,仿佛眼前的迷雾正在消散,这些档案记录部分印证了外婆和其他姨婆所讲的那些事情,而此刻他正坐在美国政府的档案资料室里目睹着那些早已熟悉的名字(同前引,635页)。
这次查找档案的收获,无疑对哈里的寻根活动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于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他只要有空就会钻到档案馆和图书馆里,因此也使他迅速掌握了整个家族历史的主要脉络:
住在纽约时,我尽量挤时间到华盛顿去,在国家档案资料处、国会图书馆以及美国革命图书馆的各个分馆搜索资料。无论我在哪里,每当黑人图书馆员一知道我要查资料,我所需要的文件都以惊人的速度送到我面前。在一九六六年不断地查询后,我至少已能掌握整个家族历史的珍贵精华部分(同前引,635页)。
四
接下来,哈里将注意力集中到如何解密那些听了无数遍的非洲语音上,因为这决定了他是否能够尽量缩小寻找的范围并获得更多确切的信息。
他通过各种渠道联系上范纳西博士——从伦敦大学非洲与东方语言系毕业,并在非洲的部落做过研究的比利时学者,以及他的非洲史研究同事。在听到哈里所发的非洲语音之后,两人都确定这些非洲音当属曼丁喀语,并且说“可”指“可拉琴”,是一种曼丁喀族人最古老的弦乐器,而“肯比·波隆河”则当指冈比亚河,至于“金塔”,可能在古老的村落名称中仍有这样的保留。然后,哈里又在汉密尔顿大学找到一位熟悉曼丁喀语的冈比亚留学生埃布·曼根,并一同飞往冈比亚。在那里,此前的推断得到证实,根据现存的村名,“金塔”应为“金特”,而且在冈比亚是既古老而又有名望的家族。
令哈里格外兴奋的还有,在较为古老而且落后的非洲村落里有一些民间“史官”,他们称得上是“口述史的活档案”(同前引,638页),这些老史官往往可以讲述长达几世纪的村落、种族、家庭或伟人历史,哈里急切地想见到这样一位知悉其“金特”家族历史的“史官”。
要听懂这些“史官”的口述还须有相当的知识储备才行,哈里回到美国后,开始狂补非洲历史。作为非洲人的后代,他为自己长期停留在“人猿泰山”式的非洲印象而感到羞愧。在那些日子里,他“整天不断地啃食非洲历史后……夜晚都坐在床沿详究着非洲地图,记下每个国家的相关位置和当时奴隶船航行的河流”(同前引,639页)。
之后,哈里便再一次飞向那片神秘的故土,那些之前认识的非洲人帮他联系上最熟悉金特家族的乡村“史官”,他便带着翻译和为史官讲述暖场的乐师们,一起坐汽艇溯冈比亚河而上,只在英法两国当年用来转运奴隶的碉堡前稍微驻足一会儿,便直奔目的地——嘉福村。在这里,他听到史官的系统讲述,知道“大约在国王军队抵达的那年”“欧玛若的长子康达外出去砍木头后,就没有人再看到他了……”(同前引,642页)。当“史官”的这种讲述与哈里出示的口传史笔记惊人相合之后,他已身处族人的簇拥中,“触手仪式”表示了对他身份的确认和同胞归来的欢迎。
此刻,他正经历着人生的“高峰体验”,即终于找到了“根”的兴奋和感慨。他决定写一本书,一本以自己祖先的故事作为美国黑人家族史代表的书!
五
家族史写作要建立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哈里希望进一步寻找更多的证据。
他想,外婆和其他老妇人经常会提到奴隶船把“金塔”带到一个叫作“纳波利斯”的地方,这个“纳波利斯”应该就是马里兰州的安纳波利斯港。可当初是什么样的船从冈比亚河能漂洋过海航行到安纳波利斯港,而且上面正好载运了他的先祖“金塔”呢?

◇1999年译林出版社中文译本《根》的封面
弄清楚事件发生的确切年代成为关键。哈里记得那位“史官”用“国王军队抵达的那一年”来解释康达·金特被俘虏的时间。于是他再赴伦敦,并在第二个星期“搜检英国军队于一七六○年期间军事行动记录时”(同前引,645页),发现“国王的军队”其实是指一个叫作“奥哈尔上校部队”的军事组织,也就是这支部队在1767年从伦敦被派往并驻扎在冈比亚河上那个当时为英国人控制的“詹姆斯奴隶转运站”。
哈里紧紧抓住这条线索。接下来他去了趟伦敦的劳埃德保险社,并得到兰德斯总裁的全力支持,因而顺利地获准“在无数卷旧时大英帝国的海事记录中搜寻资料”(同前引,645页)。
在这些浩繁的史料中,哈里度过了一辈子自认为最为辛苦的六周时光。他夜以继日地翻看“一柜柜、一叠叠在英国、非洲和美国之间做三角航行的运奴船文件”(同前引,646页),有时也不免灰心,似乎想要的信息不过是大海捞针、徒劳无益的搜索。但他越看越气愤,因为从文件记录中,他感到贩奴行动显得和普通的买卖甚至运载牲畜一样的平常,这些记录也从未被人翻阅,因为并没有人会在意这些黑人从哪里来又被卖到了哪里。哈里在心里发誓,一定要找到运载先祖“金塔”的那条船的记录(同前引,646页),哪怕是“找到从冈比亚开往安纳波利斯港的任何船只档案”也行!
在第七个星期的一天下午,他开始“翻阅第一千零二十三张的运奴船记录,那是张宽大的四方形文件,上面记载着一七六六年至一七六七年之间出入于冈比亚河的三十多艘船只”,当看到第十八号船时,他终于发现:1767年7月5日,也就是“国王的军队抵达”的那一年,一艘叫作“里弓尼领主号”的船由船长汤姆土·戴维斯自冈比亚河航行到目的地安纳波利斯港。一开始他并没有太在意,只是消极地把资料记下来,然后把“记录簿”归回了原位。直到他在一家小咖啡馆坐下来准备喝茶时才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先祖“金塔”很可能就在这艘船上!(同前引,646页)
哈里立马冲了出去,并赶上当天回纽约的飞机,他要迅速看到华盛顿特区国会图书馆内那本他曾查阅的书——华格罕·布朗所著的《安纳波利斯港的船舶》。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找到了“里弓尼领主号于一七六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在安纳波利斯港报关”的记载。(同前引,646页)
信息被再一次证实了,但离最后的证据还差一步。于是哈里马不停蹄,着手查找当年有关先祖上岸的档案资料:
我立刻租了一辆车飞奔到安纳波利斯港去,到马里兰档案资料厅内要求档案处理人员菲比·约瑟森女士可否给我一七六七年十月第一个星期左右当地所出版的报纸。她很快地取出一卷马里兰官报的缩微胶片给我。透过投影机,在几乎看完一半十月一日的报纸后,我看到一则广告:“最新引进口,在戴维斯船长从非洲冈比亚河驶来的里弓尼领主号上装运着一批‘特选的健壮黑奴’将于十月七日星期三在安纳波利斯港以现金交易拍卖,该船将以一吨六的运费载运烟草至伦敦。”此篇广告是由约翰·里德奥与丹尼人所刊登。
1967年9月29日,正好是里弓尼领主号靠岸两百年整,哈里特意前往安纳波利斯港的码头,当他望着那片曾经把他的祖先带来的海水,眼泪悄然而下。
对于哈里的祖先“金塔”来说,这是一次猝不及防的、充满屈辱和死亡威胁的远行。哈里还想了解同船非洲同胞的命运,他开始继续查找相关的档案资料:
一七六六年至一七六七年之间,冈比亚河域上詹姆斯奴隶转运站的文献记载着里弓尼领主号载运了一百四十名奴隶。可是究竟有多少人在漫长的航行中存活下来呢?于是我为此任务再一次前往马里兰档案资料厅去查询。我发现资料登记着一艘抵达安纳波利斯港的货柜船,货单上以旧式的文字写着:“三千二百六十五枚象牙;三千七百磅蜂蜡,八百磅生棉,三十二盎司冈比亚金矿沙和九十八名‘黑奴’。”船在一路上损失了四十二名非洲人,大约是三分之一,这是当时运奴船的正常损失率。(同前引,647页)
发黄灰暗的记录,触目惊心的数据,血淋淋的历史!
至此,哈里关于祖先的信息已经越来越清晰了,如果能找到“金塔”在美国上岸以后的档案资料,那么整个寻根才算是真正闭环可靠的,他祈盼“这些真实的文件记录能够存在”。
因此,我去了弗吉尼亚的里士满,熟读里弓尼领主号一七六七年九月靠岸以后弗吉尼亚斯波特瑟尔维尼亚郡所签署的一切法律文件。我翻到一份日期为一七六八年九月五日的冗长契约,里面记载着:“约翰·华勒与其妻将下列之土地及物品所有权转移给威廉·华勒:二百四十英亩之农田……以及一名叫托比的黑奴。”(同前引,648页)
所有的记录都如此严丝合缝,一切已真相大白!哈里终于为他的寻根之旅打上了句号。
六
哈里在《根》中说,自从十二年前在大英博物馆见到“罗塞达石碑”后,他“起码旅行了五十万英里。在不断地搜寻、查考、筛选、核对再核对后,不仅找出越来越多的人证实了前人口述传下来的历史,更是把大洋两岸的关系牵连起来”。(同前引,648页)为了写作的纪实性,他甚至漂洋过海,以尽量还原的方式体验先祖当年屈辱和痛苦的行程。
哈里的《根》编撰了家族的七代历史。关于这本书的真实性,哈里写下了这样两段话:
在写此书的那几年当中,我曾在许多听众面前提到《根》这本书的故事;很自然地有人会问:“《根)这本书的真实性有多少?杜撰的有多少?”我可以说《根》里所谈到的祖谱都是我家族世代小心翼翼地口述传下来的,而且我也从史料中证实到许多。因此《根》内的灵与肉是我多年来在三大洲上走遍五十多个图书馆及档案资料室,不断地精密查询研究后所凝聚而成的。(同前引,649页)
他也并不讳言《根》的文学演绎成分:
由于故事发生时我并不在现场,所以大多数突发事件的对话和情节都是我在比对资料时灵感所及,再加上必要性的戏剧化所构成的。(同前引,649页)
七
其实哈里不说我们也知道,《根》的故事不可能完全真实。
以我亲自主持的几个口述访谈项目经验,即便是当事人亲口叙述,也未必完全贴合历史的真实。一定意义上说,完全真实的历史只不过是一种奢望。我们永远只能接近历史而无法还原历史。
口述史的总体意义在于口述本身,它可以补充一些历史细节,给我们一些历史线索,但也可能因为口述者个人的立场和认知而使历史在局部意义上失真。最好的方式,只能是在口述、原始文献的相互印证中去分辨、去谨慎地下结论。
哈里正是这样做的。因为早年在部队写作的经验,他似乎比一般人更具有档案意识,而且懂得档案不只是在国家综合档案馆收藏,还分散在历史发生的广泛区域。他充分利用可能记录历史的各种文献,包括图书、报纸,当然更重要的是原生记录和保存下来的档案。利用档案史料需要潜心静气,当哈里面对浩如烟海的档案史料,或文件表单,或缩微胶卷,再累也能坚持,成功在于他的执着。哈里对档案的利用很讲方法,他不仅懂得以口述史为线索,注重档案与访谈之间的结合,注重时间节点的意义和历史发生的空间,还能在相关文献的查阅上相互提示、相互补充、相互印证。因此,鉴于哈里在写作之前所做的访谈查证工作,有充分的理由肯定《根》在总体意义上的真实性和独特的历史价值。
更允当的说法是,《根》的纪实性特征和文学性特征是并存的。但之所以能产生巨大而持续的影响,首先还在于其作为可信的“家族史”典范。其中,历史记录和档案资料,在他的寻根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支撑作用。环环相扣的档案史料,印证了家传口述史核心信息的真实性,也不断增强着他的信心。也正是这些档案记录,一次次揭开历史的面纱,给哈里的前行指引了方向。
我们有理由说,是档案让哈里的心不再漂泊,不再彷徨。甚至可以说,没有档案,就没有《根》。
由于《根》不只是哈里家族的寻根,而且“挖掘了一条美国黑人之根”,甚至还必然地“触及美国白人之根”(同前引,“前言”),因而产生了众所周知的巨大而持续的社会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或许没有《根》,也就没有总统奥巴马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