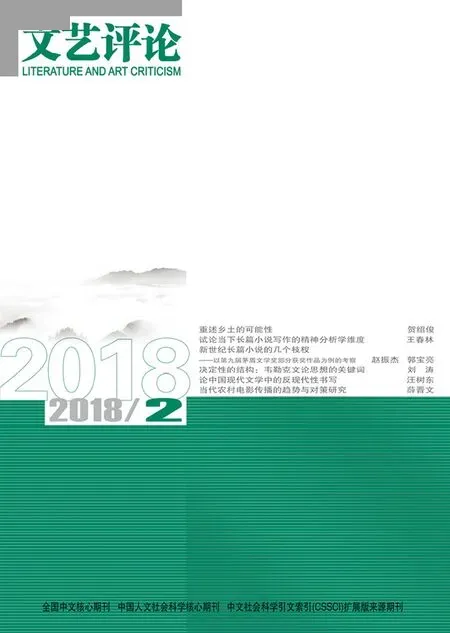新乡土写作,或“收拾残瓦时碰出的碎响”
——从六部近几年的乡土小说谈开去
2018-09-28谢尚发
○谢尚发
在罗伟章的小说《声音史》一开头,主人公杨浪带着他独特的耳朵,走进了一座千河口的空院子里,所见的景象乃是凋敝的乡村,废墟般的人家。他惆怅万千,落寞而寂寥,只能在回忆声音的聆听里,来重温昔日村庄的容貌——“房倒屋塌,瓦砾成堆,见缝插针的铁线草,盘盘绕绕地将瓦砾缠住……酸味儿,霉味儿,铁锈味儿,朽木味儿,各逞其能又交互渗透……先前,这里住着十余户人家,房屋倒塌后,瓦块混乱,他能从收拾残瓦时碰出的碎响,识别它们各自的主人,主人生活过的气息,已浸入它们的骨骼。”村庄容颜尽毁,声音断绝,任何生活在村庄或者重回村庄的人,都只能带着各自的记忆,还原逝去的旧日时光。这不仅仅是小说中的一幕,同时也在全国各地的乡村,争相被展览。引用这一段小说的原文,不是要评价它的好坏,而是要学着从小说“收拾残瓦时碰出的碎响”中,听出这个时代文学的心声。毕竟,他们所描述的东西,浸透着一个个即将逝去的乡村魂灵,书写下一段段历史流逝中残存的踪迹和印痕。
近些年来,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是,大约从2010年左右开始,更为年轻一代的作家,主要是“70后”作家,纷纷拿起笔来,仍旧作为“侨寓”城市的一员,凭借着故土生活的短暂乡村经验,以“重回故乡”的方式,书写当下中国的“新农村”。这一股潮流中,叶炜的《后土》《富矿》,季栋梁的《上庄记》,罗伟章的《声音史》,付秀莹的《陌上》以及叶凤群的《大风》等,是较为成功的作品,也因此常被谈论。在讨论他们的创作之时,评论家常常冠之以“新乡土写作”的名头,来概括他们写作的特征,以区别于“旧”的乡土文学。但“旧”在哪里?时间节点为何?又“新”在哪里?从何时开始“新”的?却都语焉未详,不曾触碰。为此,进入文本内部,寻觅“新乡土写作”的婉转心曲,披览其中被时代和历史湮灭,又复现于文字中的乡土性灵,是现下研究者应该努力的方向。
一、乡土“新常态”
2006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表决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在这个中央文件的第二篇,用了较大篇幅规划“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从此,关于“新农村”的各种讨论便层出不穷。但其时,作家们已经先知先觉地关注到了农村的“新常态”。贾平凹的《秦腔》等作品就首开先河,书写了当下乡村的种种新变。此后,为了贯彻规划纲要,新农村建设在文学上也得到了回应,一些期刊杂志开始推出“新乡土文学”的作品联展、征文大赛等,一时之间,“新乡土文学”的写作实践开始增温,一批作品不断涌现。大概是出于“提倡”的名目,随后的研究依旧未能“领会”到“新乡土文学”概念中,所包含的更复杂多元的意义,更多则是就作品讨论作品,“新”的一面远未彰显出来。即便是“新”乡土写作本身,也在“新”的理解上有着别样的追求。直到2016年,更多的“新乡土”作品问世,他们所关注的“新”才逐渐展现出独有的面貌来。
“新农村建设”既是中央政策,实际上也是大势所趋。快速城镇化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已经在全国各地热火朝天地铺展开来,新一轮城镇化进程对乡村的“蚕食”也迅速展开。作为乡村“新常态”之一,这一历史潮流也成了“新乡土写作”所处理的重要主题。在《陌上》中,付秀莹描述了一个全新的“权力阶层”——企业老板大全及其周围附着的官员、商人。于是,乡土文学中一贯的士绅、队长等角色,摇身变成了“老板”,资本和商业成为支配乡村的新权力,文化和政治的角色逐渐被经济的力量所取代,“新乡土写作”之新,也就于焉呼之欲出。整个芳村,因为有了大全的企业,许多人不再选择外出打工,而是就近入厂,从寄身于土地的农民,变成了土地抛荒的工厂工人,乡村的衰落便从土地开始,庄稼成荒原,书写的便是“新乡土写作”所寄托的哀愁。但身为大老板的大全,行事风格却依旧留下了“旧”的一面——村中的女人成了他性欲泛滥的牺牲品,有离婚而投其怀抱的,有被迫遭受奸污的,有上床谋取利益的。大全究竟还身处乡村,“旧”乡土文学中队长们干的事情,逐渐被转移到了他的身上,成就其为一个“新却旧着”的人物形象。但同时,乡村逐渐转变为城镇,工业生产取代了农业劳作,新乡土的面容发生着急遽的变化。类似地,叶炜的《富矿》中,城市对乡村的淹没,虽然并非是商业活动、工业生产的覆盖,但掏空了乡村内里的生产者,不但改变着乡村,还败坏了淳朴的民风。麻庄因为富含矿藏,开采队以公司的形式进入,导致麻庄土地塌陷,农业生产无法继续。村里人也都进入煤矿公司谋职业,村庄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工业附属物”。更其甚者,煤矿公司的员工们,以城市的奢华炫耀着身份的显赫和金钱的光芒,吸引着一批批乡村少妇少女委身其中,以至于麻姑最终转变为妓女兼老鸨,笨妮以各种变样的形式被强奸,甚至发生了幼女被矿工强奸致死的事情,对乡村的各种损害层出不穷。然而麻庄人却一日日生活于其中,须臾不可离之。“麻庄人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对钱的看法,他们越来越认识到钱的重要性,于是,他们也开始对钱有了依赖,他们也因此渐渐改变了对麻庄矿以及那些矿工的敌意,他们拼命想尽快加入到有钱人的队伍中来。”于此,也可以看出,在迅速城镇化过程中,乡村不但改变了容颜、身体,甚至连心理和灵魂也都随之而改变,昔日其乐融融的乡亲邻里,和睦古风的衣食住行,经历了巨大的时代断裂而入于作家笔下,“新乡土写作”之“新”,不可谓不触目惊心。如果再加上《声音史》中秋玲等人远赴东莞等地卖淫,用卖身的钱财投资乡村酒店,无形中把乡村小镇拉入到城市化的行列之中的书写,这种乡村的“新变”就显示出它更为复杂多样的一面来。
城镇化进程的另一面,则导致了乡村的凋敝和逐渐空心化。在《上庄记》和《声音史》中,这一“新乡土”变化的表现尤其醒目。《上庄记》以一个下乡驻村的扶贫干部所见所闻为线索,记录了一年里上庄这个村子的贫穷、衰败和逐渐空壳化的现状。一进村庄,已经七十多岁的老村长便介绍着:“孩子年龄大点,年轻力壮的就携家带口进城去了,边打工边供养娃娃读书,不农不工不乡不城的,打工挣下点钱,只有户口还在咱上庄。刚从村里走过你也看到了,许多人家都空壳了,村子里学生娃越来越少。”驻村扶贫干部便被请来当教师,把剩下的孩子们并在一起上课。在一年的时间里,扶贫干部既观察到了村子的贫困、生存环境的恶劣,也走进了留守老人和孩子们的家中,看到了他们的悲惨境况,但最令其动容的,仍旧是村庄的逐渐凋零以至于即将消失的命运。整个村子“就剩些女人、老汉、娃娃、痴傻、残障,没人操心,连要个救济都摸不着门。”(《上庄记》,第49页)然而,纵然如此,留下来的人除了等死一途,便是盼望着“进城”的一日。老村长以列数据的方式说,“上庄一共六百八十多户,有人的也就六七十户,十分之一,上庄一共八个自然村,但庄点有二十几个,有的庄点就剩一两户人了,有的一户占一个山头,还是寡妇站在大门口,有走心无守心的。”(《上庄记》,第10页)驻村干部进村所见,只有和《声音史》中杨浪所见一模一样的景致了。“有些院落箍窑塌了,由于长年累月烟熏火燎,在昏黄的阳光里黑乌乌的像山洞。有些院落院墙倒了几堵,就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脱落了牙齿,从豁口看进去,院里长满了干枯的荒草,在风中瑟缩,发出呜咽声。有几扇铁大门,风蚀雨浞的,脱落了铆钉,铁皮在风中发出巨大的哐哐声,锤头大的铁锁锈成了褐红色,被风曳动咣当有声。”(《上庄记》,第4页)以至于老马死后,竟然无人抬棺,只得把驻村干部叫去帮忙。等待村庄的命运,便是这些老人一死,村庄立马荒废,了无人烟,不复存在。用《后土》中的话来说,就是:“麻庄空了。麻庄是一点一点空起来的。最先走的是年轻男人,没娶媳妇的出去了,娶了媳妇的也出去了;接着是没说婆家的小姑娘,也去了城里。现在村里剩下的大都是老人和孩子,还有年轻的小媳妇。”《声音史》同样如此,讲述了老年杨浪,见证着千河口的衰败和最终的消亡——年轻的一代打工出走,挣钱后都搬迁到镇子上,他们从事着五花八门的职业,把小镇变成了城市,除了从千河口村掠夺野味,再也无人愿意重回村庄。“而今,除去夏青的儿子小栓和那些还没上幼儿班的小孩子,已经54岁的杨浪,是千河口最年轻的男人。同为光棍的九弟和贵生,一个比杨浪大四岁,一个比杨浪大七岁……他们三个,成了千河口光棍汉的绝唱”。(《声音史》,第 93页)不久,九第和贵生相继死去,村中其他的人也都搬迁到了镇上,整个村庄只剩下了光棍杨浪和离婚的夏青,“一个在田土上劳作,一个在山野间转悠”。当夏青从悬崖跌落,背她的只有杨浪,她也只有在杨浪模仿的众多声音中,回味千河口村的往昔存在。村庄从此消失,成为孤魂野鬼寄托魂灵的所在。“新”的乡土犹如一曲挽歌,唱给逝去的村庄,和出走与死去的乡民。
由此也可以看出,村庄凋敝和衰败的重要表征之一,便是人口的流失——他们一窝蜂地奔向城市,试图安享那里的荣华富贵。但对于出走乡村的人们而言,是“永远进不去的城市”,遭遇失败后,也只剩下“无法回去的乡村”。《声音史》中,张胖子的小儿子东升便是这样的代表。看着村里人出外打工,各个发家致富,在镇上买房子,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年纪轻轻的他放弃学业,奔赴城市。但他文化程度不高,只能干一些粗活、累活、脏活、重活,同时,不能吃苦的他被“农民工”的身份日夜煎熬着。他明白,“等到某一天,城市很可能就不需要农民工了,他们只能回去。但老家的房子垮了,土地要么抛荒,要么被征用,已经回不去了”。(《声音史》,第169页)这大概是村庄最痛苦的卑贱和最卑贱的命运混合而成的疼痛。无独有偶,《上庄记》中,为了孩子上学不得不进城的盼香也成了打工一族,他们在城市中的遭遇却是受尽了城市人的歧视、谩骂和污蔑——“死也不找个地方”,是公交司机骂一个横穿马路的农民工;“妈的,老子都进城十几年了,还把老子不当城里人”(《上庄记》,第197-198页),是一个和城里人在公交车上对骂了之后的农民工嘴中咕哝的抱怨。盼香费尽心力把儿子带到城市就读,然而“农民工子弟”的“群体显得孤独,胆怯,敏感,自卑,忧郁,有些小心翼翼,弱不禁风”。他们都知道,等待他们的命运,已经注定。“读到大学毕业,不但不能终结他们的苦难,反而延伸了他们的苦难,让他们不堪重负。”(《上庄记》,第210页)父母期盼孩子考上大学来改变命运,但阶层固化、利益分配完成等结构性的社会矛盾,使得他们看不到出路。大学毕业就等于失业只是其一,留在城市里,天价的房子、生活的尊严等,没有一个是有保障的。对于这一群人而言,注定是“进不了城,回不去村”的孤魂野鬼,漂泊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待到城市榨干了他们的劳动力,遣返回乡的只能是病体残躯,等待死亡。
前行无路,后退无门,“新乡土写作”仍旧努力地给它们提供着别样的出路——“新农村建设”的规划所造就的新景象,在叶炜的《后土》中得到了展现,虽然昙花一现,略带海市蜃楼的感觉,但那毕竟是念想的存留。麻庄老一代的村庄领袖刘青松和曹东风,见证的是村庄的苦难和逐渐凋敝衰败,以至于消失,但年轻一代的乡民,则带着从城市学来的知识、观念和新视野,让乡村看到了光明的前景。刘青松的私生子刘非平在其资助下顺利读完了大学,但他却并未留在城市寻觅活路,而是带着女朋友黄莉莉重回了麻庄,立志干一番大事业,从此改变乡村的老旧面貌——“我想在咱们麻庄开发农家乐,发展旅游业,争取利用上头的资金,大力开发小龙河,把村里的苇塘、果园、马鞍山和鱼塘连成一片,集观光、旅游、垂钓、娱乐等旅游开发于一体。具体说,就是建设小龙河观光带、苇塘观鸟园、果园采摘园、马鞍山野味馆、麻庄鱼塘垂钓中心等,以观光旅游带动麻庄的经济发展,带动麻庄乡亲共同致富!”(《后土》,第328页)这是一幅想象的“未来乡村蓝图”,充满了乌托邦的气息,美好到令人浮想联翩。但它终究需要实践的证明,而其所依仗的仍旧是城市的“猎奇眼光”和“别样体验”,更何况它的发展模式可复制性虽强,却不能全面铺开。等待乡村命运的开发前景虽美,但任重道远。不过在《后土》中,麻庄的“弃儿”王东周,在城市闯荡出大事业,带着雄厚的资金重回故乡,在资金和理念的双重驱动下,麻庄的确以旅游的方式,焕然一新。但愿这不是文学家虚构的伎俩,欺骗了众多渴求的乡民的眼神。
在这一批新乡土作品中,以乡村“新常态”作为主心骨,把城镇化的影响、乡村的凋敝和衰落、乡村在城市面前的卑微以及乡村未来发展的蓝图,统统作为一种“新”的面貌呈现出来,从而区别于“旧”乡土文学——鲁迅等人的残忍和阴冷,沈从文等人的浪漫和温情,十七年作品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色彩。这便让它们拥有了“新”的质地和风骨。时代的转变,历史发展的当下,不管是问题的呈现,还是蓝图的描绘,命运转变中乡村的故事,实际上开始逐渐变了本质,城乡差别、田园牧歌、落后先进等也逐渐消灭了裂隙。新乡土写作,在这一方面,实际上代表着当下生活的历史化的新方向。
二、“新乡愁”:从空间到时间
1935年,鲁迅在给《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小说二集写导言的时候,敏锐地捕捉到乡土写作的气息,并率先给乡土文学一个界定:“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在鲁迅的界定中,人“在北京”,“侨寓”的身份以及“隐现着乡愁”大概是“乡土文学”的“标配”了,至于还需要再加上地方的风俗、人性的美丑、命运的离奇,则都是“豪华版”的配制。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这几点都指向了“远离”而后带来的“乡愁”,虽没了“异域情调”的展示,也非“炫耀他的眼界”。因此,一代代乡土文学的写作者,拾起笔来所写的,都是远离故乡的愁绪,不管是用了批判的笔调,还是赞美的文字。这种乡愁的由来,和背井离乡,远居他地,有着密切的联系。于此,就可以看出,空间的阻隔与交通的不便,使得这种乡愁成为了异乡人惦念的永恒情思,但重回故里后,这种情思愁绪便能得到慰藉,只是情感上的缺憾实在难以弥补。实际上,鲁迅的界定直到今天,不管是“旧”乡土文学,还是“新”乡土文学,也还都是适用的,因为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仍旧远离故乡,站在外面重看故乡时,写下了饱含乡愁的文字。查看罗伟章、付秀莹、叶炜、叶凤群、季栋梁等人的生活轨迹,都可以看出这种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叶凤群更是从乡土脱离出来,远赴国外,空间阻隔的乡愁实在是他们不可避免的一环。但是让人颇为惊诧的是,一俟落实在他们的“新乡土写作”中,这种乡愁又实实在在变换了愁绪的来源,感情的别样,以及寄托的位移。
“重回故乡”被置换为“重回昔日的故乡”。往昔之不再,岁月不重来,带着浓重的感伤情绪,出现在这一批乡土作品之中。乡村不再,需要借助某种形式才能重新唤回逝去的那个乡村,是《声音史》的一大命题,也是其着重表达的内容。杨浪天生异才,能够分辨出诸种声音的细微差别,最特殊的是他还能够模仿各种声音。倘若只能够模仿自然的诸种声音,那也只是口技的一种,但杨浪可以把千河口众人的声音都模仿得惟妙惟肖,如同死去的人再世、离去的人站在眼前一般。五十多年过去了,杨浪成了老光棍,而千河口也在经历着空心化,死亡和离去是抽空这个山中村庄的两种最主要的形式。在岁月的历史中,村庄的东院、西院和中院居住的村民,以各种方式远离了千河口,还剩下的三个光棍,九弟瘫痪在床,贵生照顾他的饮食起居,杨浪加入之后,便用他的嘴巴开始复活整个村庄。“他喝了一口酒,从东院开始,一个一个学。每学一个人时,与之相关的声音也随之响起……当然那都是好多年前的声音了。那时候走亲戚是件相当慎重的事情……除了人声,还有年节烧爆竹的声音,打铁棍的声音,耍车车灯的声音,更有平日里的鸡鸣牛哞声,猪撞圈栏声,羊唤乳羔声,猫扑老鼠声,以及风声、雨声、鸟叫声……村庄在声音里复苏了。”(《声音史》,第 154-155页)只是,随着村庄一日日凋敝,人都消失不见,村庄也一去不复还,这些声音自然也都消失殆尽了。小说的末尾,夏青在骨折卧床之际,恳求杨浪做的事情,也仍旧是“学学志刚说话”,彼时,夏青的丈夫已经出轨,另外组建了家庭,两人已经离婚。她对杨浪说,“我只求你学这一回,随便学几句,我听听就好,听了这一回,我就把他丢开了……”(《声音史》,第241页)还仍旧惦念着前夫的夏青,希望通过对声音的唤回来重温往昔的美好时光,正如罗伟章试图通过文字的书写,来重叙与村庄的昔日姻缘一样。但声音中所透露的,则多少显示出一种凭吊和祭奠来,毕竟,“有些东西,一旦失去就无法挽回。”(《声音史》,第192页)在声音中被重构的过往,只是虚幻的一种,聊以自慰罢了。浓重的乡愁意绪,在杨浪的声音中被重新唤醒的记忆所烘托出,在消逝的村庄和性灵面前,惆怅的不仅仅是杨浪、九弟、贵生和夏青,还有罗伟章,以及这一代远离了正在消逝的乡村的人们。
回忆只是虚妄,记住也不切实际,于是寻宗问祖就成了“另类还乡”的精神寄托。这在《大风》中是最为明显的。家族第一代是显赫的地主出身,但在建国初期的土地革命中,不惜抛弃家财,逃命到了贫穷的乌源沟,装穷卖傻地终于熬过了被批斗的命运。家族的第二代,在表舅的撮合下,到了江心洲,娶了当地的一个女子。但这个从小“被迫”充当傻子的男人张广深,在艰苦的岁月中养成了“醉心于一件事而不能自拔”的习惯,他力大无穷又带着痴傻的干劲,在迷恋上妻子的身体后日夜折腾,于是就有了家族第三代张文亮的诞生。然而妻子产后即去世,留下鳏夫孤儿,贫穷地过着日子。但随着爷爷的到来,张文亮在爷爷的讲述中培养起了贵族的气质——“乖孙,老实跟你讲,你祖上是方圆百里最富庶的大户人家。我家有上百亩良田……乖孙,你祖上,一共有七七四十九间房屋。猪有猪屋,马有马屋,驴有驴屋,柴有柴房,还有一间专门放锄、犁、锹、镐头等干活的工具,一间房光存酒,一间房储粮食,堂屋里摆着八仙桌,睡房里有木箱衣橱……”以至于让那个被饥饿折磨得两眼放光、因居住狭窄而沮丧不已的少年,渴求万千,在一次邻居端来了一碗肉的时候,祖上“曾经”的辉煌再一次给了他自豪感——“这点猪肉算什么,我小的时候,一顿都吃一碗大肉,一点不掺黄豆,也不掺咸菜。”祖父如是说,给孙子虚构了一个“曾经”的村庄故事。若干年后,张文亮在和媳妇孙梅打工、拼搏之后,拥有了自己的企业,但这个“曾经”的村庄故事,根深蒂固,使他无法安于城市的富庶生活,患上了“夜游症”,没日没夜地要寻找那个虚无缥缈,仅存在于祖父口中的“颍上村”。以至于妻子抱怨道:“他所有开心的事情里都有他的老家,对老家的回忆,他回忆起过去那些辉煌,就会两眼放光。”“听他的意思,就好像那个地方是世外桃源,千年不变,他只要找对地方,往那里一站,一切疑问烟消云散,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一切贫穷结束,一切幸福来临。那简直就是天堂。”(《大风》,第286-287页)这个虚构的、想象的故乡,犹如人类的原乡,让张文亮日牵夜挂,想方设法要重回到过去。“重回往昔”和“寻找祖宗”挂钩,让逝去的村庄所勾引起的乡愁,显然多了另一分忧伤、惆怅的体验。这个不存在的“原乡”,就好像在时代变迁中被彻底变换了容颜的现实乡村一样,连年轻人梅子杰也如是惦念——“草垛是结实的,那时不烧煤气灶;庄稼是结实的,那时没有拖拉机,一寸寸土都是锄头在翻;房屋也是结实的,一到有个什么砖瓦碎了,有人补有人修;那时衣裳是结实的,你走几户就能看到女人们围坐在一起织毛衣、纳鞋底。可是现在,这些东西一样也没有了,地里还有庄稼。可是麦秆棉叶都不像是土里长出来的,而且没有味道,飘得也那么漫不经心、无精打采。房屋在那里,大门紧锁,无人居住。鸡呢,没有几只,鸭呢,没有几只,牛呢,没有几头,猪呢,没有几头。”(《大风》,第 271页)而这一切的原因,竟是“光阴像一把大剪子已经把江心洲剪成一个秃子了。”这不是远离故土而来的愁绪,因为梅子杰身在其中;也不是身在异地而心在故家的惆怅,这是岁月流逝中,时代转变带走的村庄历史所勾引起的回忆。往上,则是意味着逝去的村庄如同“祖宗”一样,需要人们去寻回。但张文亮终究也未能找到那个“原乡”颍上村,属于时代的乡村只能以消逝的命运,营造着无限的乡愁,环绕在“现代人”的心头,让一代人永久地成为“无根”的存在,飘荡在城市的上空。
也还有残存的“往昔”和“传统的习俗”,但那残存的苍凉里,是必然被岁月湮灭的惆怅,和无法存留的告别的哀伤。坟墓也可以见证过去,但死者无法重生,坟头的纸钱只能作为现代的乡愁,告慰过去的亡灵。在《上庄记》中,驻村扶贫干部在学校里教书遇到的第一个传统节日,便是当地“正月二十三”的“燎疳节”。“燎疳表达着人们驱邪除魔、保佑平安、庄稼丰收的祈愿。”只是,虽然传统节日还有,但已经大变了模样,“以前燎疳家家户户门上点堆柴火燎,真是万家灯火哩,现在没人了,过年连人七日都不过,初四五就都动身了,一家一户连个疳都燎不起,凑合到一起燎燎,就是应个节气事”。(第21页)似乎这传统节日的存在,比起不存在来,更让人心生悲凉,因为在一个“连狗都进城”(第256页)的时代,乡村残存的节日和剩下的生气,明证的乃是往昔不再的黯淡和今古对比的悲哀。无力维持的人们,只能“敷衍了事”,那存留下的风俗和传统,就更显得千疮百孔,卑微而可怜。类似的传统还包括驱鬼除魔的仪式、丧礼的考究等,但都被上庄人敷衍了事地进行着——既要保证规矩的存留,又不得不在匮乏的存在里偷工减料,由此而带出的惆怅让这分乡愁在时光的穿梭中,有了更多的别样滋味。当然,同样存在的还有过去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脉脉”,映照着如今冷冰冰的“货币关系”。季栋梁成功地塑造了老村长这一角色,他为了维护村庄的存在,不惜一次次拖着残躯,以扶贫的名义来维持乡村小学的存在,不顾年迈守护着村庄的存在,操心着留下来人的生老病死和日常起居。他充分理解了所有生活的不易,为村人争取哪怕一点点的好处,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子女都已经在城市安家落户,也召唤他进城生活的时候,他依然选择了拒绝,宁愿留在败落的上庄,守着贫瘠的土地、荒凉的人生和将死的命运。但随着老马的死去,宣布着老村长的“时日无多”,也同样象征着上庄的“大限将至”,无法抗衡的时光流逝和消亡的预言,让乡愁变成了永恒的存在,因为“再也回不去的村庄”将让所有村民必然领命如斯,把它当作珍藏的一部分,长久地惦念而无法释怀。扶老携幼、互帮互助的村庄精神,湮灭在现代交易的规则中,人间温情被冷冰冰的现代条款所吞噬,在这乡愁中被放大、提升。
探寻这种乡愁的存在本质,可以看出的是,相比较于“旧”乡土文学,新乡土的书写缓缓流淌着的乡愁,乃是一种被抽去了心根的乡愁,使得一种归返的情感无所寄托,从而让生命处于一种“无根的飘浮状态”。一己的生命无法安放,自然也就成了揪心的所在。《大风》中那个永远也到来不了的“祖先”,也无法寻觅到他的踪迹,这种“阙如”的状态,恰好是新乡土写作所要表达的新乡愁的本意。当村庄消失,单凭记忆所构筑的乡土,显然是脆弱且不切实际的,它永远处在一种被描述、被构建的状态,随着记忆者的死去而宣告永久消亡。但已经“进城”了的人们,却时时被刺激着这种“关于乡村的记忆”,因为对于他们而言,新的生活的建立是艰难的,无法融入城市,也无法重建自我生活的秩序,导致这种新乡愁必然愈演愈浓烈——“喊工派活就像吆牛喝驴,可那些工头骂起人来语言难听的,日妈喝爹翻先人道亡人的,啥话都能骂你,啥人都能骂你,受不了那口气,受不了那眼神。工地上丢了东西,第一个怀疑的就是你。”(《上庄记》,第267页)活着的尊严,让乡愁的存在成为必然,记住乡村似乎是要铭记和重塑自我的尊严的前提,乡愁里所涵盖的内容就别是一般模样。所以上庄小学剩下的学生们,开学一点不马虎,升国旗、开学典礼、颁奖和发言……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形式大于内容”是在乡村中得到最佳体现的规则。尊严得到保存的最卑微的形式,其所唤起的乡愁也更加充满了悲悯的气息。但随着这剩下的孩子也同样离开了上庄,转学到城市之后,那微薄又可怜的一点点尊严,该寄托在哪里呢?这不正是“新乡土写作”的“新乡愁”的全部要义吗?旧乡愁可谓是远离的乡愁,地理和空间的乡愁,而新乡愁则是消逝的乡愁,是历史和时间的乡愁,这种从空间到时间转换了的乡愁,恰好开启了新乡土书写的一个面相。
三、“收拾残瓦时碰出的碎响”,或新乡土写作的“文学命运”
在浓重的伤感和惆怅情绪中流淌着的“新乡愁”,似乎在时刻提请着阅读者明了:乡村的凋敝与衰落既是现实的呈露,也是历史的必然。但短短几年时间内,大量新乡土写作的涌现,大概不会让人产生这种“历史的必然”背后,所隐藏着的决绝与离弃。村庄虽然不在,但文字还在;村庄正在消亡,却在小说中被复活。只是,稍微用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这一波“新乡土书写”更像是乡村衰亡的前兆,是回光返照的刹那绚烂。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一波“新乡土写作”的主力军是“70后”作家,只有少量“60后”和“80后”参与进来。如果再加上非虚构代表作家作品,如梁鸿和她的《出梁庄记》《梁庄在中国》与黄灯的《大地上的亲人》等,那么这一作家谱系就更会向“70后”作家群倾斜。何以“70后”会对乡村有着如此之深的眷念?而只有到了他们四十岁左右才集中爆发了出来?这是一个需要处理的问题。从年龄构成上来看,这一代人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的包产到户历史,以及20世纪90年代乡土在市场经济冲击下逐步式微的过程,更对21世纪初农业税取消、城镇化快速推进、乡村凋敝等触目惊心的新现象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50后”作家和大部分“60后”作家,还沉浸在他们漫长的乡村生活而不能自拔,所以基本上以此为核心书写乡村的现状和历史、演义;“80后”和“90后”所经历的历史进程毕竟有限,即便历史时段已经够长,他们浸淫于城市的时间也远超过居留于乡村的岁月,对于城与乡的差别有着更为醒目的认知,却又因拔根过早而认同于城市文明。在这个历史的间歇段,便是“70后”说长不短,说短又不长的乡村经历,足以构成他们书写的资源,源源不断涌入到笔下。恰是如此,他们的书写显得紧凑、豪华,短时间内集中亮相,但却仿佛只是这一群人“收拾残瓦时碰出的碎响”,是短时段的历史线条的当下延伸。
城镇化的发展,是“新乡土写作”在题材上,最为致命的一个历史局点,它预示着乡村的“新常态”会在一个历史时段内,彻头彻尾地转换了它存在的容颜。毕竟,乡土写作并非是简单的小麦加收割播种、菜园加老谢老马,以及些许方言的装点、故事的地域背景等,因为在高度城市化的上海,这些同样存在,却已经被转换为是城市文学的一部分了。借用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的论述,这个“乡土”首先应该是“土”,在乎它的“土里土气”;也是“私”,在乎它的“自私自利”;更是“礼”,在乎它的“礼尚往来”,这其中包含着礼俗道德、宗族礼制、主宾礼让等。但在“新乡土”的世界中,抛弃土地变成“无产者”的人群是乡村凋敝衰落的第一原因。那种“‘土’是他们的命根”的历史样貌,已然被连根拔起,不复存在。传统的乡村礼俗礼制逐渐被新风气、新风尚所冲击。旧有的已遭破坏,而新来却远未建立,处在转型时期的“新乡土”,正是许多资本、商业等为非作歹、恣意猖狂的真空地带。正如麻庄的老领导刘青松所感慨的那样——“麻庄的风气真是越来越坏了!以前的淳朴越来越难觅踪影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了!……人心已经乱了,已经散了。”(《后土》,第302页)这在《陌上》中,有着更为集中的表现——现代法制制度的亏缺,导致了商人大全四处勾结,官商一体,裙带关系,以此来谋取利益。大全的行为破坏了乡村作为基本存在的礼俗道德,以工业的方式,在合情合理的存世法则下,褫夺了依靠土地来生活的农业生存规矩,却又未能及时建立一整套现代商业行为规则,因此整个芳村呈现出权力真空,他也就成了芳村的“真神”。乡村的城镇化进程,同样是褫夺着传统乡土存在的模式、生活的方式,从而使得乡村不再成其为乡村,对于它的书写,也多少以荒腔走板的格调,存在于文学的园地。但这或许是大势所趋,非但是一两个作家所不能扭转,就算是整个群体奔走争取,历史的车轮也无法扭转时代的格局。因此,将“新乡土写作”看作是“乡土文学”的“最后的挽歌”,既不是要凭吊乡土的不再,也不是要祭奠文学的寿夭,而是指认这种书写方式所指引的乡土写作,在短暂爆发后,将会遇到低谷或者瓶颈,顺带着,整个乡土的书写将会出现下滑。
不啻此,“新乡土写作”所面临的困境,还来自既往的乡土文学书写的经验的重压,和这种书写所自带的“自我重复性”的特性导致的审美疲劳。如果说“新乡土写作”在“旧乡土写作”的挤压下,实则匮乏创造和新意,那至少是掩耳盗铃的视而不见,但要说“新乡土写作”区别于“旧乡土写作”的重要症候,是超越和别开新面,也多少有些违心和不符事实。在“新乡土写作”中,许多作品试图以泼洒的方式,描绘鸡零狗碎的日常生活,试图从这种生活中找出“新乡土”的特质,但他们似乎忘记了,早在2005年发表出版,创作于2003年的《秦腔》虽不至于将这种书写方式耗空殆尽,但至少让后来的写作者,实在难以超越。所以看上去,《声音史》中的乡里乡亲、日常俗事显示出了乡村凋敝的一面,但读上去和《秦腔》就会慢慢混为一谈。虽然《上庄记》采用了“类非虚构”的方式,以外来人的眼光透析村庄的衰败,且写法结构上是“每日一记”的层层推进,但“上到塬上看贫穷、见到老汉问声好”的书写风格,也会让阅读者难以提起精神,从而产生审美疲劳。或许是得益于女性作家的独特感受,《陌上》某种程度上看似跳开了这种种写作的难题,但实则是“女版”的“故事重述”,是女人眼中“乡村生活的泼烦与拉杂”。总之,在上一代人对乡土进行勤勤恳恳的开掘之后,下一代人想要别开一途,实在是困难重重,一不小心就落入了前人的圈套之中。而所谓的“自我重复性”,也在在让人感到惋惜——就算《声音史》《上庄记》《陌上》与《秦腔》有着巨大的差异而不能混为一谈,但他们之间的那种写作风格,实则是难分你我。不能说是相互抄袭,但最起码在时代的共同性主题驱使下,他们未能在同中看到异,更未能塑造出这种异质性存在。同样是写“村庄空了”,麻庄是空的,上庄也是空的,千河口的院落街道同样是空的,连空的过程和途径,又几乎是毫无例外的“城市输出”,且城市以各种方式反过头来重塑着乡村。虽然《大风》用“痛说家史”的方式来追溯今日之所来,但其中夹杂的家族第四代,以目之所见而勾连起的乡村现状,也殊途同归了;虽然《后土》以展望未来的方式,给麻庄指引了一条大道,但也只不过是破砖烂瓦砾上,堆起的“乌托邦”。这里或许存在着一个“新乡土写作”的致命原因,那就是“命运的在地性”。浸淫于乡土越久的作家,把控乡土、认知乡土、感受乡土都会深入骨髓,因为乡土就是他们的命运,他只能在乡土中安放自我的生命存在。但“70后作家”的一群,居多都是“暂时性生活与逗留”于乡村,所获得的居多是“走马观花”的印象,写起来容易浮于表面,难以深入到“乡土的内心”,所以不能够感受到“乡土内在的心跳”“乡村灵魂的悸动与震颤”,更无法思考“乡土的命定性”与乡村的出路和希望。粗略地看上去,当下乡村千篇一律地千疮百孔,无一例外地被城市化进程所打乱从而凋败乃至于消失。倘若民政部的调查数据是真实的,“每天都有八十至一百个村落消失”,那么,就如同“每天都有八十至一百个新乡土作品诞生”一样,新而未新,旧却早已陈旧。如此,让人不得不相信,这一批“新乡土书写”的浪潮,几乎可以看作是作家们,各自在乡村,曾经居住过或者短暂停留过时,“收拾残瓦时碰出的碎响”。
还需要提及的一点是,“长篇小说”的书写模式,几乎构成了这一波“新乡土书写”潮流的固定格式。在无意于评价他们个人创作成就的高低情况下,哪怕是以“群体”的存在方式来看,这些作品都存在着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重复啰唆、冗长繁琐。作品中铺排开来的文字,虽然经过精心的妆点和修饰,但结构拖拉,故事琐碎,人物形象淹没在没完没了的叙述中,着实让作品本身的成色大打折扣。可以将这些作品归入到“好作品”“一流作品”的序列中,自然没什么问题,但要成为“经典作品”或“著名作品”,恐怕还有着不小的差距。更不要说在具体的叙述中,故事推进的浅层次化——反反复复,说着同一件事情,却总也说不清楚,还得继续说下去;思想的缺席和浅薄化——叙说现象大于冷静沉思,沉思所得又难以用形象化的文学方式表达出来;甚至于,文本内部的自我复写和重现,虽然也能将乡村的“新常态”和盘托出,但总觉得被“拉长”的篇幅,浓缩为精华的所在会更好。当然,不管是“最后的挽歌”,还是“收拾残瓦时碰出的碎响”,“新乡土书写”的命运,不会就此终结,它仍需要探讨最为适恰的推进方式,不但反映当下乡土的“新常态”,刻摹情绪的“新乡愁”,还能以“命运的在地性”或“乡土的命运性”为依归,感受“乡土的脉搏”、聆听“村庄的心声”,把自我不但置于“乡土之中”,还要“以乡土为命”,如此,“新乡土书写”的“天命惟新”和“天降大任”才能得到出色的体现和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