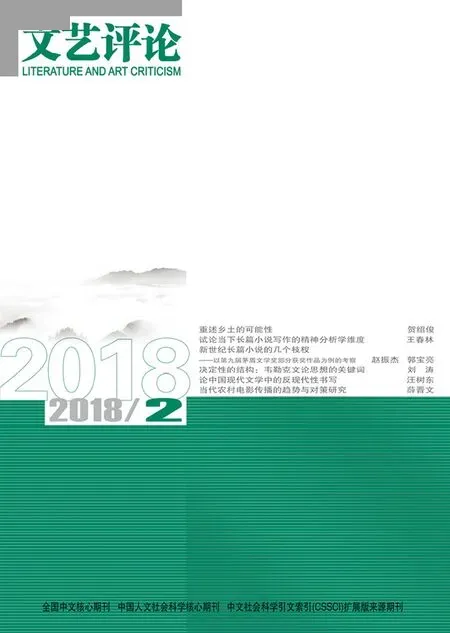论北大荒小说的叙事时间
2018-09-28姜深香周玉玲马广原
○姜深香 周玉玲 马广原
在北大荒博物馆的一块石碑上刻有这样一段文字:“五百年前有人说,北京往北是北大荒。三百年前有人说,关东就是北大荒。一百年前有人说,黑龙江是北大荒。如今人们都说,黑龙江垦区就是北大荒。”这段话其实孕育了一个非常简单而朴素的道理:即地域性与时间不可分离,时间是地域性存在的基本形式之一,时间的流动会引发地域文化属性的改变。因此,当下意义的北大荒具有鲜明的现实时间域——即从国家1947年试办国营农场开始,经历了1949年—1952年的荣军农场和解放团农场时期、1952年的大型国营机械化友谊农场建立时期、1955年—1956年的四川、山东等支边青年创建的农庄转变为农场时期、1958年的10万转业官兵投身农场开发的军垦时期、1968年54万知识青年加入的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生产建设兵团时期、1977年至2010年的曲折发展和改革开放时期、2011年至今的现代化大农业的生态文明发展时期等阶段。①在现实而客观的物理时间流动中,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北大荒的时间性从“过去”到“现在”,也必将进入到“未来”。这个真实存在的时间过程经过演化和变异被小说作者们切入转换到北大荒小说的叙事世界中,形成了北大荒小说地域性叙事要素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叙事时间。叙事时间是一切叙述文本的生命,任何叙事文本都会自觉地把叙事纳入到时间框架建构之下。作为叙述文本的北大荒小说也必然会包含一个故事发生、发展和结束的时间进程或者一个主体成长的时间历程,但不同的北大荒小说叙述者对文本中具体的叙述时间进程所采取的处理方式和表达形态不会完全相同。
一
从北大荒小说叙事时间所呈现出来的时态特征看,绝大多数北大荒小说的主体叙事时间指向了过去一般时或过去完成时,在时态上基本上是一个已然的过程,是一个已经过去、已经完成了的“那个”时刻、“那个”时间节点在现时状态下的一种回放。虽然一般过去时或者过去完成时意味着北大荒小说主体叙述事件的发生时间是在彼时的过去,但因为所有叙事性文本的叙事时间都具有交替性和延续性,所以北大荒小说的叙事时间的起始位置永远也不可能停滞于一个持续不变的固定时态。北京大学叙事理论与小说阐释领域著名教授申丹曾对此进行说明:“回忆的过程往往就是用现在的眼光来观察往事的过程。”②根据这一特征进行梳理就会很容易发现——绝大多数北大荒小说在总体叙事时间走向上仍坚持以立足于当前的时间节点为前提,在此基础上形成由此时到彼时再回到此时的相互循环、相互照应和相互平衡的时态结构关系。
尽管不能一概而论,但是从一个故事时间到另一个故事时间,北大荒小说的叙述者们还是比较普遍地站在了某一个具有“现在”意义的时间段内对他们“过去”曾经置身过的现场情境时间进行反思和再现。由于并置了“现在”和“过去”反复交替的时态关系,不仅扩大了叙事空间,而且也有益于转移和丰富叙事视角,使叙事时间的情境内蕴得到扩张和扩展。如,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知青》等系列知青作品,它们的时间情境价值绝不仅限于知青“下乡——开荒——返城——出路——选择”那么简单,其双重交替的时态关系和由此及彼的叙事视角的变化均使北大荒小说的情境内蕴具有无限的张力。在梁晓声的上述小说作品中读者体验到的不再是单一时态形成的价值内蕴指向,而是受双重时态架构影响的丰富的内蕴集成。它既包括过去的英雄主义,也涵盖了现实条件下的虚浮主义;既具有曾经的浪漫主义气质,也具有现时的情怀感伤;既有高度的集体主义意识,也不乏个人主义的迷茫;既有虔诚与理智,也有摇摆与徘徊;既有正直与正义,也有虚伪与奸猾;有高洁,也有平庸;有妥协,也有抗争;有怀旧、也有反思;有赞美,也有批判……在“过去”与“现在”的双重时态交互作用下,在叙述时间、被叙述时间、叙述行为时间的相互搅拌中,读者不仅能够体会到人物的性格、事件的发展具有了更为丰富的逻辑性,而且也能够感受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价值体系和不同的价值观带给人们思想上的冲击和影响。总之,在“过去”与“现在”不同叙事时态的相互穿插和变化中,梁晓声让读者感受到了他赋予作品鲜明的“过去”与“现在”的对比性观念预设。这种对比性观念预设的层次既包括土地,也包括人;既包括情感,也包括思想;既包括机制,也包括体制。通过对比,梁晓声的北大荒小说既能让读者产生富有正能量的强烈的充满理想的激荡,也能让读者沉下心来对现实的社会和人性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思考。梁晓声之外,韩乃寅的《岁月》、张抗抗的《隐形伴侣》等诸多作品也都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对比性成分,并在这个对比性的双重时态的框架下隐喻丰富的指向意义——即“过去”是理想的、浪漫的、荒凉的、落后的、单纯的、朴素的、粗放的、被动的、困惑的;“现在”是富足的、进步的、复杂的、矛盾的、细致的、集约的、主动的、明白的等等。
但是也应该明确的是:并不是所有北大荒小说的叙事时间的时态都采用“现在”——“过去”——“现在”的双重循环时态模式,有的北大荒小说文本整体或局部采用了无明显时态的叙事时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时间的界限,增加了小说叙事时间背景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二
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热奈特在他的《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一书中指出:时间是一种关系,是一种建立在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之间的相互比较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其中的故事时间是指故事发生的自然时间;叙事时间是指叙述故事的时间。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的长短距离并不完全等同,二者之间的长短差异就构成了时距。③虽然没有具体的量化标准,但叙事时间却总在试图改变故事时间,包括改变故事时间的起始位置、故事时间的原有秩序、故事时间的推进频率等。这在本质上都属于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的差距——即叙事时间长度的变化范畴。一般来说,叙事时间不一定要与故事时间完全一致或完全聚合。但每一部北大荒小说却都有自己的叙事时间长度,长的可能对应历史时间中的半个世纪,短的可以反射出某一具体历史时段。无论如何聚合、切割和变化,它们都自然地对应着或多或少的特定的历史内涵。因此,无论从哪一具体时间位置开始落笔,也无论选择何种接续方式对叙事时间范围内的不同时间位置进行衔接,最终都会形成长度差异化的北大荒小说的叙事时间特征。
从北大荒小说叙事时间长度的具体表现状况来看,北大荒小说的叙事时间绝大部分仍属于主流线性序列。尽管在叙事时间上北大荒小说存在取时跨度长短的不同,同时也客观存在不同作品在某一具体叙事时间段相重、相同的现象。但如果把每一部北大荒小说的叙事时间的长度按前后的顺序连缀在一起,读者就会很容易发现北大荒小说叙事时间的内在逻辑迁延线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序的、连贯的整一系统,这个系统自然地对应于北大荒客观现实的历史发展轨迹。如,林予的长篇小说《雁飞塞北》,它的核心叙事时间集中在1958年,这一叙事时段与现实历史时间相对应,时间顺序非常清晰,写完整的一年时间里以张兴华为代表的10万转业官兵开发建设北大荒的故事。而梁晓声的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的叙事时间长度则相对短暂,具体起始时间从当天下午写到晚上,然后再迁延到第二天下午。但最核心的叙事时间却只有一个晚上——那就是1979年春节后、一个大自然和人均陷于混乱状态的夜晚。这个夜晚既是一个自然界暴风雪肆虐的夜晚,也是一个北大荒四十余万知识青年在大返城关键时刻复杂人性尽显的夜晚。不同于一年、一个夜晚的叙事时间长度,韩乃寅的长篇小说《岁月》的叙事时间跨越了50年的长度。作者在叙事时间位置的选取上主要对应于20世纪50年代的10万转业官兵时期、支边青年时期、20世纪60年代的四十余万知青时期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8万大中专学生时期的三个大的子系时间系统。《岁月》近乎全景式的叙事时间长度,全面地覆盖了北大荒开发、建设、改革发展的不同历史进程,并同步再现了三代北大荒人的情感生活及精神样貌。尽管在叙事时间长度上存在不同,但无论是一年、一天抑或是50年,上述所列北大荒小说在具体的叙事时间节点上基本匹配于从“过去”到“现在”的线性历史时间,就像各历史阶段的一面面镜子,映射出其所处时代的特定的历史情境。尽管诸如《岁月》等作品也客观地存在局部叙事时间系统均衡性强弱的差异以及拓扑时间的交代和转换未必完全清晰和紧致等问题,但却不能因此而否认北大荒小说作家们在叙事时间长度上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主体历史意识。
但是,叙事时间毕竟不能等同于纯物理的现实时间,在完整的北大荒小说叙事时间长度里,时间流程变得交错复杂,一些纯现实时间有可能被压缩,也可能被延长,甚至被小说作者有意识地隐蔽起来。为了保证北大荒小说叙事时间长度的张弛有致与合理布局,北大荒的小说作者们充分利用热奈特所总结出来的“概述”“场景”“停顿”“省略”四种叙述时间的方法,并综合运用正叙、倒叙、过渡、错位等一系列叙事时间秩序的处理方式,并最终把富于变化的叙事时间长度协调统一在每一部北大荒小说作品中。
三
一个完整的故事是由一个起始时间状态和一个结束时间状态形成的,而一部小说却可能汇聚大大小小若干故事单位,自然就会包含若干不同的时间状态。从北大荒小说的叙事时间形态来看,“时间是立体的”④。首先,时间与事件相互依存,时间意味着事件状态的变化。其次,“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⑤。再次,时间是“主观时间”⑥呈现出来的样态,时间的运行方式和速度在本质上取决于人的时间意识。事实上,单一故事时间一般是一维的存在,而叙事时间则相对复杂,往往体现出多维特点。很显然,事件时间和人物时间等可以组成故事时间,而故事时间则必须受“主观时间”统摄才能形成叙事时间。因此,叙事时间形态的实质就是将一种时间状态转换成另一种时间状态,并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一维的、自然的故事时间会因叙述者设计的各种拓扑关系而形成倒错、变异的非完全线性时间。
根据北大荒小说叙事时间惯常使用的叙述方法,绝大多数北大荒小说的叙事时间着眼点是立足“现在”而回忆和反思“过去”,总体上呈正向线性形态。但也客观地存在时间剖面的选择以及时间方向和时间顺序的安排等叙事时间表现方式和形态上的差异。这些差异虽不能详尽,但却可以粗略地概括为以下两大类:
一类是以《雁飞塞北》《今夜有暴风雪》《岁月》《雪城》《破釜沉舟》等中长篇小说为代表,这些北大荒小说作品的核心故事时间剖面刻度非常清晰,叙事时间正向推进,反向拉伸,通过正向、反向时间的接续,延长了故事时间。如上述列举过的长篇小说《雁飞塞北》,它的正向叙事时间剖面明确为1958年,正向时间秩序清晰而严谨。具体叙事时间的起点位置是从1958年1月3日晚下半夜开始,然后逐步接续到1月4日、阳历一月末、初春二月、四月初、五月初、八月梢的一个清晨、金色的秋天、阳历十月初等。在正向推进的时间进程中,作者有意截断正向的叙事时间,进而逆向插入1958年之前系列人物的故事时间。如分场党委书记张兴华、捕鱼工王开富、军医刘玉洁、拖拉机二队队长罗海民等。仅以张兴华一人为例,作者就插入了他1937年冬北上抗日、1942年秋开垦南泥湾、1945年从延安到山东、1949年和女军邮员恋爱并结婚、1950年夫妻奔赴朝鲜前线、妻子牺牲等逆向时间故事。通过逆向时间的拉伸向读者展示了张兴华这一人物的来龙去脉,一旦插入叙事时间结束,正向叙事时间与逆向叙事时间粘合衔接在一起,就形成了完整的人物故事时间。既完成了对八一农场大雁分场党委书记张兴华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因人物时间、事件时间线的相互交织而使整部小说的叙事时间呈现出明显的动态变化性。
另一类是以《隐形伴侣》《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龙抬头》《远去的马群》《独船》《野狼出没的山谷》《北纬48°动物传奇系列》等系列作品为代表,这类小说的故事时间剖面基本上没有明确的年、月、日等时间标识。由于未指明具体的故事发生时间,虽然读者也能够通过阅读在心理上补充出大致完整的故事时间位置,但叙事时间的表现方式和所呈现出的时间状态关系却变得比较复杂和多变。
首先,由于时间剖面和故事时间的位置不再直接点明,所以小说中就出现了大量的诸如“ 那 天”“ 那 年 ”“那年深 秋 ”“那天 夜 里 ”“ 这 一年”“这几年”“一个多月过去了”“一年过去了”等模糊性的时间节点。尽管这些模糊性的时间词汇在小说中出现的频率以及承载的时间表述职能并不完全相同,但在解构现实时间的路标以及使叙事时间的节奏更富于变化等方面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从功能上来说,它们或用于一笔带过,或用于具体展开。
其次,模糊性叙事时间不等于彻底摒除时间,它只是表示叙事时间边界不够明晰。类似北大荒小说作品有刘海生的《远去的马群》、王凤麟的《野狼出没的山谷》等。这些作品并不直接点明故事发生的时间,加之叙事中大量使用倒叙、追叙、插叙等时间表述方式,这些做法都使得北大荒小说的叙事时间更加模糊多变。此外,模糊性叙事时间也常借助主观心理时间与客观物理时间的相互交融有意制造“时间的无形迷宫”,在展开情节的同时不忘解构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莫过于张抗抗的《隐形伴侣》,该小说因融入了相当数量的梦境和朦胧性的回忆,正常的叙事时间秩序被打破,故事中人物的时间感变得交错搭叠,形成了表面不合逻辑而实有逻辑的叙事时间顺序。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北大荒小说的叙事时间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回看走过的路,北大荒小说的叙述者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现在和未来永远比过去更重要,学会理性分析和总结过去北大荒小说在叙事时间方面积累的成功经验和得出的失败教训。在新时代的历史境遇条件下,用新的发展的叙事时间要素来反映新的时代生活和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