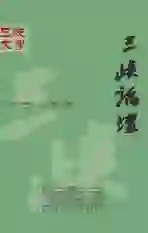《楚辞》版本六大谱系的考索
2018-09-10龚红林夏志强
龚红林 夏志强
摘 要:在追求“最全的”、“最真的”、“最好懂的”楚辞文献集成研究之路上,《楚辞文献丛考》在目前“最全的”《楚辞文献丛刊》基础上,考索出了“最真的”楚辞文献。《丛考》总字数约计一百八十万字,先有类别之“综论”,后为各版刻之“分述”,提炼出了两千余年来关于《楚辞》版本传承的两个轴心,考索了《楚辞》文献版本六大谱系,同类文献之继承与变迁,明晰可辨。而对首次面世的日本、韩国及美国所藏《楚辞》孤本的版本考索,是弥足珍贵的楚辞域外所藏文献的提要。因此,《丛考》可谓当前对《楚辞》版本谱系解读最深细、最有体系性的考述。
关键词:《楚辞文献丛考》;黄灵庚;楚辞;版本谱系
中图分类号: I2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8)04-0075-04
楚辞之学萌发于秦末汉初,然彼时距离屈原生活时代已有百余年,诸多名物及意蕴已然不易读懂,故汉武帝命淮南王刘安撰《离骚传》;加之秦火,地上之参考文献有限,致使汉人之间的《楚辞》文本阐释及屈原品评等,已彼此矛盾不一。故,学者们至今仍孜孜不倦于楚辞“疑古”、“考证”与“经义”之学。
两千多年的楚辞文献学研究铸就了《楚辞》刻印、校读版本千馀种。面对卷秩浩繁的楚辞文献,普通读者很难于诸多版本中看出“门道”,亦难以一时之间遍览全部古籍珍本,更不用说一睹域外收藏古代孤本之真容。于是,搜集“最全的”、“最真的”、“最好懂”楚辞文献丛刊,成为当代学界的期盼与学人为之努力的方向。
一、周详性
而要有“最好懂的”楚辞文献,需要以“最全的”、“最真的”楚辞文献为基础。于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今,学术界出现了各类楚辞文献集成的成果。一时间,有关国内外《楚辞》文献的版本丛考、影印编纂成果不断涌现,已出版了“楚辞”六大文献集成:(1)马茂元主编《楚辞研究集成》(共5册,含《楚辞要籍解题》、《楚辞注释》、《楚辞研究论文选》、《楚辞资料海外编》、《楚辞评论资料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2)杜松柏主编《楚辞汇编》台湾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出版,全书十册。(3)崔富章主编《楚辞学文库》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该文库共有《楚辞集校集释》(上·下)、《楚辞评论集览》、《楚辞著作提要》、《楚辞学通典》四卷五册。(4)周殿富译注《楚辞源流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含《楚辞魂》、《楚辞论》、《楚辞源》、《楚辞流》、《楚辞余》五种。(5)吴平等主编《楚辞文献集成》广陵书社2008年。包括注释类,收刘向、王逸、朱熹等诸家注释楚辞之作,共七十四种;音义类,收录有关研究楚辞的字音、字义、韵谱之作,共计十九种;评论类,收录有关楚辞的论人、论世、论义、论文之作,共计二十种;考证类,收征实有关楚辞的人物、名物、制度、史事之作,共计二十一种;图谱类,收有关楚辞的法书、图画、地图之作,共十种;札记类,收录诸家读书札记中考论楚辞的文字,共计六种。(6)黄灵庚主编《楚辞文献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出版。包含了中、日、韩所存《楚辞》重要版本、海内外孤本、研究文献二〇〇馀种,以“章句”、“补注”、“文选”、“白文”、“集注”和“楚辞研究文献”六类逐一影印,是至今最大、最齐全的楚辞文献丛刊。
可以说,在追求“最全的”、“最真的”、“最好懂的”楚辞文献集成的研究之路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楚辞文献丛刊》(黄灵庚主编)提供了周详的第一手楚辞文献资料,带给了研究者诸多方便。不仅如此,时隔三年,与《楚辞文献丛刊》既相对独立、又相辅相成的《楚辞文献丛考》(下简称《丛考》)亦面世出版。“原拟每书之首皆以‘考论,以其篇幅繁钜,则抽出别为一书。”[1]2《丛考》在目前“最全的”《楚辭文献丛刊》基础上,又呈现了“最真的”楚辞文献。
二、谱系性
《丛考》总字数约计一百八十万字,“考镜源流,辩章学术”,先有类别之“综论”,后有各版刻之“分述”,同类文献之继承与变迁明晰可辨。可谓当前对《楚辞》版本体系解读最深、最有体系性的考述。
首先,“提炼”出了两千余年来关于《楚辞》版本传承的两个轴心。
现存《楚辞》版本千余,但其源头无外乎“叔师”与“考亭”。正所谓“今读《骚》者,率祧叔师而跻考亭。”(明汪瑗《楚辞集解序》)“叔师”“考亭”即王逸、朱熹。汉代之后的整个楚辞文献体系可概括为“一祖二宗”。“一祖”乃王逸《楚辞章句》,所谓“《楚辞》不祧之祖”[2]、“叔师一笺,朦发万古”(明汪瑗《楚辞集解序》)是也。“二宗”乃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卫瑜章《离骚集释》例言:“传《楚辞》者,刘安而后,迄于隋唐,无虑数十百家,今多不传。最通行者,惟王叔师、洪庆善、朱晦庵之注而已。”[3]180按,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各有扩展,但均以王逸《楚辞章句》为祖本,对后世影响深远,可称“二宗”。
黄灵庚主编的《楚辞文献丛考》(2017年版)条分缕析地解读考索了《楚辞文献丛刊》(2014年版)中编纂出版的两百馀种楚辞文献,深度解读了各个《楚辞》版本间的传承体系,并凝炼为两个轴心。其《后记》中说:“回顾两千馀年的《楚辞》学术史,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与南宋的朱熹《楚辞集注》是两种标志性的文献著作。《楚辞》文献研究,南宋以前,基本上以《楚辞章句》为轴心,南宋以后至民国,基本上以《楚辞集注》为轴心。”[4]1985按,汉、宋确实是楚辞学术史上的“轴心期”。后代学者,或遵循王逸《章句》之传统,不断加入自己的创作,如清王夫之《楚辞通释》十四卷基本遵循此路,加入王夫之作《九昭》;或遵循朱熹《楚辞集注》,删去《七谏》《九怀》《九叹》《九思》,增加贾谊《吊屈原》《服赋》。如清人吴世尚、丁元正、郑知同、李文炤等。本套《丛考》将众多楚辞文献研究的“源头活水”归属于两个轴心,形象传达了《楚辞》版本的传承谱系,与历史上楚辞文献体系“一祖二宗”之事实一脉相承。
其次,《丛考》分“章句”、“补注”、“文选”、“白文”、“集注”和“楚辞研究文献”六类,考索了《楚辞》文献版本六大谱系。《丛考》在考索“章句”、“补注”、“文选”、“白文”、“集注”和“楚辞研究文献”六类版本之时,做了大量细致的校对工夫,十分注重比照彼此的关联,理清了各版的因缘关系,据之可以了解目前最完整有关现存国内外207种《楚辞》版本的谱系。
以“章句”谱系看,王逸《楚辞章句》明代单刻本版本传承的“祖本”仿宋痕迹明显,有故意在皇帝避諱上“做文章”的情况以显示是宋本翻刻。传承下来的明代单刻本系统有二:明正德高第、黄省曾刊刻宋本(下文简称“正德本”)和明隆庆五年朱多煃刊刻宋本(善本,下文简称“隆庆本”);这两个系统均曾传播到日本,但已经不是原貌。正德本、隆庆本虽同是据宋本翻刻,但是二本也有差异,是否用同一祖本,很难断定。其中,“正德本”之“明万历十四年俞初校刻本”域外传播较广,日本庄允益宽延安三年据之翻刻,且成为日本的几种主要《楚辞》版本之一,如西村时彦楚辞考异稿本、楚辞疏证稿本、楚辞王注考异(謄稿本)、王注楚辞翼(日本董鸥洲謄稿本)均以俞初校刻本为底本。“隆庆本”之“明万历十四年丙戌冯绍祖观妙斋校刻本”传播亦广,如:明万历十六年金陵益轩唐氏修版重印本、明万历金陵王少塘补版重印本、四库全书的《章句》抄本、明万历二十九年朱一夔、朱一龙刻本附西村时彦批校(翻刻本)、三乐斋书坊重印本、明万历十五年冯氏改刻本、明万历丁亥《楚辞句解评林》(托名冯梦龙,实为观妙斋翻刻本)、明毛晋汲古阁观妙斋翻刻本该校刻本,均是以之为底本;亦传播到了日本。
在详述了各版本情况时,《丛考》的有些结论也颠复了传统的说法。如,“日本国庄允益宽延三年刻本”的底本是“明万历十四年俞初校刻本”,绝非如学者(竹治贞夫、崔富章、饶宗颐等)所称是“夫容馆翻宋本”,即隆庆本。庄氏参校了朱一夔、朱一龙刻本、《补注》、《文选》等,和“明万历十四年俞初校刻本”虽有差异文字,但是整体上脱不尽其原貌。还有一些文字,是庄氏无版本依据而妄意增删的结果,因此,这个本子最不可信,非如学者所鼓吹那样“精善之本”。这个结论,颠复了有关“日本国庄允益宽延安三年刻本”的传统说法。
“补注”、“文选”、“白文”、“集注”和“楚辞研究文献”其他五类《楚辞》文献版本的谱系,均可从《丛考》中读出。且均指明了文献原本所藏地点,便于检索,惠泽学人,推动楚辞学之功,不言而喻。
《丛考》详细考述了日本、韩国及美国所藏《楚辞》版本,其中,许多还是首次面世的楚辞孤本的版本考索。
《丛考》解读了日本藏十七种《楚辞》文献,囊括了日本国现存文献的精华,非常珍贵。具体是:明万历朱刻本附西村时彦批校、日本庄允益刻本、楚辞疏证稿本、西村时彦楚辞考异稿本、楚辞王注考异、日本国翻刻楚辞笺注、金陵书局刊本附西村时彦楚辞集释手稿等。这些版本选自于日本明治汉学家西村时彦所购的《楚辞》类典籍百馀种,《丛刊》编纂中复制了十七种,《丛考》对其一一加以考异批校。对每一本文献流传之来龙去脉逐一考索,大致反映了现存日本大阪大学图书馆《楚辞》文献版本的谱系。如,明万历朱刻本附西村时彦批校本《楚辞章句》,现藏日本大阪大学图书馆,经考索,该本原为明万历朱燮元、朱一龙二氏校刻本,传日本西村时彦有朱笔批校,其刊刻祖本为明“隆庆本”谱系之“明万历十四年丙戌冯绍祖观妙斋校刻本”,文字有参洪兴祖《补注》校改,虽比不上隆庆原本,但仍是不可多见的明代单刻王注《楚辞章句》本。这些成果也是作者和日本著名学者石川三佐男长期合作的成果。
作者在具体考证这些域外文献时,十分注意国内学者和域外学者的学术作风的差异。如辨别董鸥洲《王注楚辞翼》时,发现其征引文献不甚规范,竟用明末袁黄《历史纲鉴》来作为考证岁星纪年的依据,这在清代作者身上是绝可能发生的。由此,《丛考》作者注意到董鸥洲的地望“北越”,发现竟是日本的古地名,董鸥洲实际是日本人。这个结论纠正了以往误认为清朝越人[5]332的结论。
三、创新性
历代书目著录《楚辞》,但对版本彼此的关联考论仍不完善。
有关《楚辞》版本体系的梳理,汤炳正先生《楚辞编撰者及其成书年代的探索》一文中描述了早期《楚辞》版本的承序:“《楚辞》一书,既非出于一人之手,也不出于一个时代,它是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人们逐渐纂辑增补而成的。”[3]4汤炳正先生的观点是,早期《楚辞》成书经过了宋玉、刘安之编辑,此后才成刘向《楚辞》之面貌。这一观点得到了学界诸多认同及引用。但有关《楚辞》成书之后的版本谱系,虽多有《楚辞》书目提要或要籍提要的编撰,鲜有系统精微的文本比较与有意识地版本传承关系的梳理,究其原因主要是文献实物的参照难度及卷帙浩繁。
文献记载,最早的《楚辞》总集始于西汉刘向编《楚辞》十六卷(佚)。《四库全书总目》一百四十八·集部一《楚辞类》提要称:“裒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刘向编《楚辞》十六卷辑录的作品有:《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辩》、《招魂》、《大招》、《惜誓》、《招隐士》、《七谏》、《哀时命》、《九怀》、《九叹》。但这个版本已经不存在。
现存最早的楚辞集是东汉王逸(约公元89-158年)的《楚辞章句》,作品选录中增王逸自作《九思》而为十七卷。姜亮夫:“若以刘安之附《招隐士》例之,则刘向续辑十六卷,有其自作之《九叹》,其事理至顺适,则王逸以十六卷本为刘向所定,为不诬。”[3]3-4这个版本比较复杂,异文多达六千多条。
此后历代书目均著录“楚辞”,梁阮孝绪《七录》始列“楚辞”类目[6]43,其后,《隋书·经籍志》等历代书目因之。“《隋志》集部以楚辞别为一门,历代因之!盖汉魏以下,赋体既变,无全集皆作此体者。他集不与楚辞类,楚辞亦不与他集类,体例既异,理不得不分著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八·集部一·楚辞类》)《宋史·艺文志》集部四类,“楚辞”居首:“集类四:一曰楚辞类,二曰别集类,三曰总集类,四曰文史类。”《清史稿·艺文志·集部·序》集部增为五类,“楚辞”仍为首:“集部五类:一曰《楚辞》类,二曰别集类,三曰总集类,四曰诗文评类,五曰词曲类。”
可见,要想读到“最真的”楚辞文献,必须是实物文献为参照的基础上,依据版本考索,方能找到最可靠的善本。今细读黄灵庚先生主编《楚辞文献丛考》时发现,如此有难度的课题已有了基本的答案与眉目。
注 释:
[1] 黄灵庚:《楚辞文献丛考·凡例》,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
[2] 姜亮夫:《楚辞通故·叙目》,齐鲁书社,1985年。
[3] 崔福章:《楚辞书目五种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4] 黄灵庚:《楚辞文献丛考·后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
[5] 饶宗颐引西村时彦辑本:“《楚辞翼》,清董鸥洲撰,鸥洲,北越人。”转引自姜亮夫编著《楚辞书目五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6] 熊良智:“言《隋志》别立“楚辞”一门,又不察阮孝绪《七录》之先。”见熊良智《阮孝绪<七录>楚辞分类著录的学理背景》,《文学评论》,2007年第6期。
责任编辑:杨军会
文字校对:赵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