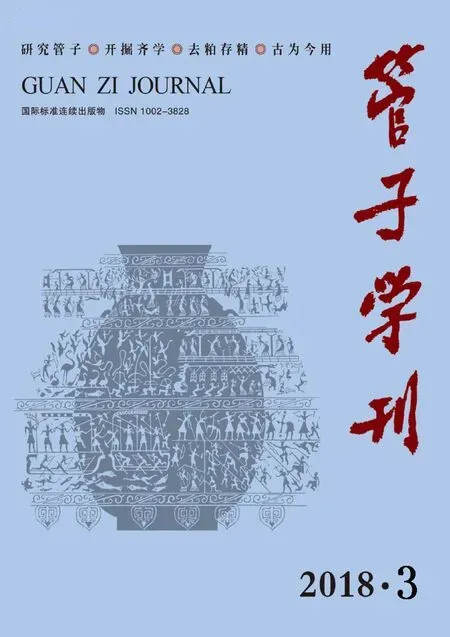考古遗址公园对公众考古的发展
——以日本飞鸟、英国弗拉格和我国大明宫遗址公园为例
2018-08-22孙悦
孙 悦
(山东大学 博物馆,山东 济南 250012)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快速发展,文化遗存保护与城化进程的矛盾也在逐渐加深,造成了保护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之间的矛盾凸显。在这样的时代环境背景下,迫切需要既可以能够保护大遗址,又能在不损害大遗址前提下适当地加以利用的一种大遗址保护方法,考古遗址公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与此同时,遗址本身的公共性特征也越发明显,仅仅依靠政府以及考古学家、文博机构等微薄的力量保护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在本身学术研究的基础之外,与社会公众建立良好的沟通,依靠全社会力量来进行保护,所以“公众考古学”也逐渐发展开来。本文就是希望通过列举国内外考古遗址公园对公众考古的发展,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和建议,以期能够引起大家对于公众考古学的重视,将公众考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更好的结合起来。
一、公众考古学及其发展历程
谈及考古遗址公园对公众考古的普及首先不得不提到的就是公众考古的提出。公众考古学的兴起,主要是在处理考古学、公众、国家政府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把考古学纳入到广泛的社会关系当中,并在考古学和社会紧密结合的基础上探讨考古学大众化的问题,调和考古与经济、社会效益之间的矛盾。思考考古知识传播问题,关注考古资源、文化遗产的管理保护和文化的传承[1]。公众考古学这一说法提出之前,考古学被认为是很神秘的一门学科,大家对考古学的了解非常少,到了20世纪60年代,英、美等国家对于考古学、公众、社会三者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在当时,美国的工业化进程正迅速发展, 工业化大规模的建设对于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造成了一定的威胁,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同时也催生了文化资源管理理念与实践的形成和发展。美国广袤的地域及其巨大的潜在考古资源都使人们认识到,要想使考古现场得到保护或者进行可靠的调查,必须要令非专业的公众参与到考古服务中来[2]。于是,美国考古学界开始考虑以往那种由专业学者和政府主导的文化资源管理模式,并不能更为有效地促进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需要公众的参与,通过借助非专业的公众对文化资源管理和考古学相关工作的广泛参与,来探索一条新的保护道路,同时能够推动立法及文化遗产管理体制的完善。所以说,在一定意义上文化资源管理(CRM)本身就是公众考古。学界现在默认的公众考古学概念,最早提出是在1972年,美国考古学家查尔斯·麦克基姆西在《公共考古学》一书中正式提出了“公众考古学(Public Archaeology)”的术语和理念。公共考古学的概念为两层意思,即“公共”和“公众”。公共是指具有公共性质的,与国家和社会机构相联系,如公共团体、公共建筑物、公共办公室、公共利益等[3],像一些公共机构来代表广大公众进行考古工作和文化遗产保护,而公众则是指多元的、但不以考古研究为职业的人群[2]。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大众,他们也有义务和责任对遗址和文化遗产等进行保护。公共基本理念与创新实践为“交流”和“阐释”,“交流”是考古机构、考古学者和公众之间的互动。要达成相互沟通交流的目的,考古学家必须了解公众的多样性和人们从考古材料中获取信息的方式。通过调查和研究,能够对公众的想法、兴趣、关注度、意见进行了解把握,为互相交流打下基础。“阐释”是对考古遗址、相关学科知识的解释。通过对考古的解释,用显而易见、通俗易懂的方式传递给公众,例如考古现场开放的方式,让公众有所了解,与公众进行文化协商,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查尔斯·麦克基姆西的公众考古学意在为了更好地实现考古资源保护和获得公众支持,并为考古资源研究、保存和发展开辟一条新途径[4]。
我国的公众考古始于19世纪50年代,半坡遗址博物馆的建立。张忠培先生,曾经参加过半坡发掘实习,他讲道“他们当年是一边做着田野发掘,一边向当地群众以及前来参观的人们做田野发现的讲解宣传”[5],这大概就是公众考古的萌芽了吧。1950年苏秉琦先生在天津的《进步日报》上发表了《如何使考古成为人民的事业》一文,提出考古是人民的事业这一观点[6],改变了以往考古学家个人自发普及考古知识的实践模式,号召全体考古从业者应当改变自己以往观念,让考古成为人民的事业,这标志着我国“考古学大众化的”正式开始。20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撰写科普读物依然是该阶段普及考古知识的主要方式。贾兰坡先生撰写了《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北京人之家》等文章,李伯谦、徐天进先生主编《考古探秘》,王仁湘先生策划并主编的“华夏文明探秘”系列丛书等科普读物[7],黄石林、朱乃诚著《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宿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考古发现》等都在一定意义上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非专业的公众普及一定的考古知识,讲述考古人的故事、阐释考古发现的发掘现场。1976年,我国在湖北的楚国纪南城遗址举办了面向工人、农民和文博从业人员的考古培训班,这在我国文博行业是首次。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大批“公众考古”译著和论文。苏秉琦先生在《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一书,收录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公众考古学方面的多次讲稿,其书写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更是展示出了考古公众化思想,集中反映了这个时代中国公众考古学所达到的理论高度和发展水平[8]。李零、陈平原、陈星灿、王巍等学者都写了相关公众考古学的文章,认为处理好公众与考古之间的关系是考古学发展必须要完成的一项重要使命。随后中国公众考古的发展由开始的普及考古知识、“考古学大众化”理念的提出转变为普惠大众的保护和利用[9]。 2002年,在杭州召开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颁证与学术研讨会”和 2003年在北京召开的“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传播学术研讨会”都以“考古学与公众”作为其核心的讨论内容,并提出尽快在中国建立公众考古学的必要性[10]。随后我国的公众考古也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政府、媒体、高校、考古机构等都以极高的热情投入到公众考古学实践中。国家文物局牵头,每年都举行全国十大考古发现评选活动,《中国文物报》《中国文化遗产》等报刊也开始刊登与公众考古相关的内容,文物出版社也出版了《少儿考古入门》《长江中游文明之旅》及其相关考古音像制品等系列产品。2007年,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作为国内高校,设立公众考古系列课程,给本专业研究生讲授“公众考古学”相关知识,后来还面向全校各院系非文博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开设“考古发现与探索”平台课程,激发了学生对考古的热情,提升了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之后北京大学等学校也开设了公众考古的相关课程。2008 年5 月,山东汶上南旺大运河保护公众考古实践的开展,让群众有组织地进入发掘工地参观,并请正在工作的考古人员现场讲解,这是我国首次公众考古实践活动。北大的公众考古与艺术中心考古夏令营活动、上海博物馆“博物馆之友”活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举办的考古探险活动、山东省博物馆的“国际博物馆日”活动、海昏侯墓发掘关键点现场直播等等,让公众考古更多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二、考古遗址公园对公众考古的发展
简单的梳理了一下公众考古的概念和发展历程,下面着重谈一下考古遗址公园对公众考古的发展。我国的考古遗址公园的概念初步提出,是在2009年6月召开的“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2009年12月17日颁布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中则正式提出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定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指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间”。 相比于我国的考古遗址公园还较为新兴来讲,考古遗址公园在国外早有先例。 美国在1916年的时候,由国会通过立法成立了国家公园管理局。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首先于1918年将卡萨格兰德遗址纳入了管理体系之中,该遗址是美国史前建筑遗址最突出的代表。到现今,有将近七万处古迹和遗址被包括在该体系之中。在国家公园管理局这个体系中有两个重要的遗址公园,一个是梅萨沃德国家公园,一个是查科文化国家历史公园。国家公园管理的模式对其他国家建立遗址公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随后,英国、日本、美洲、韩国等也都相继建立了考古遗址公园。这里不得不提到的是日本的遗址公园,日本建设遗址公园的保护方式则与欧美等国家大不相同,1965年以前,其考古遗址保护方针主要以“现状保存”为主。1965年之后,日本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全国都开展了土地开发运动,考古遗址保护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包括著名的平宫城遗址。在这种形势下,人们开始重视遗址的展示与利用,先后建立了很多大型考古遗址公园,例如大室公园、吉野里历史公园、飞鸟历史公园等等[11]。下面分别以飞鸟历史公园、弗拉格遗址公园、大明宫考古遗址公园为例,来谈一下遗址公园对公众考古的发展。
(一)日本飞鸟历史公园
飞鸟历史公园的公众考古有公众参与展示及多媒体展示等方式。它是以飞鸟地区考古发掘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营公园,位于奈良县高市郡明日香村,包括已基本建设完成的甘樫丘地区、高松冢周边地区、祝户地区、石舞台地区,还有正处于筹备和建设阶段的KITORA古坟周边地区。作为日本注重个人感官享受基础上的遗址公园,飞鸟历史公园的公众考古的展开也体现在该园内各个方面,其最主要的方式为公众参与展示。通过让公众参与园内设置的活动,满足了公众的求知欲望,以更好的了解历史,促进遗址的保护。例如在祝户地区设立用于为飞鸟观光的据点以及学习和研修的场所飞鸟只宿祝户庄,额外提供以被认为是古代飞鸟人食用的古代饮食特别料理“万叶飞鸟叶盛御膳”。住宿的古建筑是根据考古发掘复原而成,里面的食物也仿照古代而设定。这些别具特色的展示方式可以让公众更加直观地了解遗址当时的状况,比普通的图片和文字展示在一定意义上更能吸引公众的目光,有利于公众学习历史文化知识。这充分体现了遗址公园的知识性、趣味性、休闲性、娱乐性,能够达到教育公众、娱乐大众的目的,最重要的是可以让年轻的一代对遗址保护有兴趣,有利于青少年学习当地的文化,了解家乡的历史。历史公园内还专门设置了梦市茶屋、明日香民俗资料馆和犬养万叶纪念馆,这三个建筑内都举办以喝茶沙龙为主题的相关公众体验活动。例如,在日式客厅里喝抹茶模拟古代感官体验。
每一个遗址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属性和局域,飞鸟历史公园建设时也注意到了这方面。飞鸟历史公园的一大特点就是将周边环境与遗迹保护相融合,尤其是对植物的利用和开发,同时通过与周边环境相融合,以公众参与展示的方式促进公众考古的发展。园内在甘樫丘地区设立了长约2.3千米的“万叶”植物园路,可以一边观察一边欣赏万叶集、古事记、日本书纪上所吟咏过的40种“万叶植物”。这些“万叶植物”通过猜谜翻牌的形式与公众产生互动,使公众一边享受散步的乐趣,一边学习到相关植物的知识。
如今,正在筹备建设的KITORA古坟周边地区计划建设体验学习广场和里地里山体验原野,这更将公众参与展示发挥到了极致。体验学习广场设在户外,用来体验古代的风俗习惯和活动,以及相关天文图的天文观测等。而里地里山体验原野则设想游客和当地居民能够参加与学校有联系的环境教育活动,模拟一种情境,即通过栽培古代米,能让人联想起当时气氛,构成历史风土中的梯田景观保护和再生。
多媒体的展示也是飞鸟历史公园与公众考古相结合的一大特点。互联网的出现,大大方便了人们的沟通。我们发现互联网能够将各国家各地区之间不同的科技文化等快速的流通与交流,各阶层的人们也通过网络密切地关注着文化遗产、考古发掘等动向。飞鸟历史公园也充分意识到了互联网作为公众考古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媒体工具,因而建设了极为优秀的历史公园网站。网站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如遗址简介、遗址内出土的文物展出、公园规划、交通设施以及各种活动等。在网络平台中,该遗址公园利用文字、图片以及少量视频等对五个区域重要景点予以介绍,不仅吸引了更多公众的关注,还帮助公众在进入遗址公园前对园内有一个深入的了解,也提升了公众对考古、遗址保护工作知识的普及度。
(二)英国弗拉格遗址公园
在简单分析了日本飞鸟历史公园对公众考古的发展后,再以英国的弗拉格遗址公园为例,探讨一下英国公众考古的发展。相比于美国对文物的原貌保存较为重视并维持文物的现状的保护方式建立遗址公园,以及日本以“现状保存”为主要方式建立遗址公园,而英国与其他的欧洲国家一样,建设遗址公园的方式是注重遗址的本体保护,对出土文物的工艺方面严格把关并进行复原,比如英国的弗拉格考古遗址公园。弗拉格遗址,位于英格兰彼得伯勒这座城市的东部,是距今约3500年前开发掘的一个青铜时代遗址,该遗址是在潮湿的沼泽地上搭建,建立在一个名为Northey的小岛屿上,如今岛屿名称为Whittlesey。19世纪初考古学家在彼得伯勒发现了传统的陶器、Fengate器皿和青铜时代“烧杯”风格的陶器[12]。20世纪70年代后,在沼泽地附近进行了试探性的发掘。1984年弗拉格遗址开始正式发掘,在1990年的时候,发现了垂直和水平的木材、动物的骨头、青铜短剑、其他金属物品和碎片、燧石工具等等[13]。在后来的进一步发掘过程中,发现包括来自英格兰的现存最古老的木轮以及欧洲大陆的一些进口品[14]278-281。2001年到2002年期间又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在距弗拉格遗址约2000米的地方发现了8艘青铜时代的船只,这些船只是在一个较为狭窄的淡水古河道发现的,因为水涝而被保存下来,根据碳14测年,这些船只长达1000年左右的时间,最早船只可以追溯到1750-1650 BC[15]。在此次发掘中,还发现了青铜时代的木制鱼笼以及一些金属制品像刀、枪等等。
因为弗拉格遗址出土类似宗教碑以及木材平台等遗物和建筑,众多学者认为对于研究英国乃至欧洲的宗教文化和祭祀礼仪等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及其意义。比如该遗址发现了一些皮革和木材,由于在沼泽地区的土质缺乏氧气保持接近于原始状态,所以出土的文物是青铜时代的生活极为重要的反映。英国彼得伯勒政府以弗拉格遗址的考古发掘为基础建立了弗拉格遗址公园,该考古遗址公园对游客开放大约超过20英亩,也就是大约8公顷左右面积的园区,虽然相对于其他的遗址公园面积来说较小,但是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其遗址公园分为了两个主要区域,即户外区域和游客中心。户外区域主要包括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圆房子、一段罗马道路、花园农场等。游客中心主要包括博物馆、保护展厅和游客服务区域。
英国建立遗址公园的方式,是十分重视遗址的原真性保护,依照出土文物的工艺特点进行原真性复原。主要通过建筑复原、陈列展示、公众参与三种方式来对遗址公园进行展示。
弗拉格考古遗址公园对其公众考古的发展,最主要的体现在了园内举行的大量公众参与活动中。公众参与活动是该遗址公园进行文化展示的一大特色,使公众在亲身参与中感受到古代文化的魅力。遗址公园内定期开展讲座,例如实验考古行动中引人入胜的故事这种夹杂科普与趣味的讲座,引起公众的兴趣,而在儿童参与方面,园内结合不同年龄孩子的特点分别设置了多种层次的考古课程,让儿童能够充分了解古代的历史与文化知识。此外,为了让公众充分了解考古学家发掘的经过与实践的经验,遗址公园里还专门设置了发掘大帐篷这个景点,让公众明白了在古代人们是如何生活的。该遗址公园每周末还开办农夫市场,农夫市场设立在游客中心附近的草坪上,市场将有各种工匠食品工艺摊位。在公众参与方面,弗拉格考古遗址公园还有一个不同于其他遗址公园的独特之处,就是定期举办各种活动征集公众参与。例如园内曾经举办的“真实大小的恐龙入侵”活动,通过让公众自己进行化石的发掘,并参与化石的处理过程,来体验其自己动手的乐趣。
弗拉格考古遗址公园在建筑复原展示时,也充分考虑到了公众的感官享受(如图一)。通过对圆房子的建筑复原,一方面让公众领略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不同的建筑风格,另一方面因为屋子冬暖夏凉,可以让公众有室内室外不同的时差感受。此外,弗拉格遗址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木材结构,根据考古发掘学者分析,用木材铺制的堤道也存有祭祀的意味,所以该遗址公园在建立过程中对这个祭祀的堤道进行了复原,展示给公众观看。同时,遗址公园同样根据考古勘探复原建设了古代农场,其布局和设施均参考发掘结果和历史资料,在建设的农场中还饲养了一些家畜,例如古老神奇的索伊羊。更让人神奇的是在农场内还开辟了罗马香草园,来种植古代罗马花园时期相关的植物,使公众可以放松的享受并了解古代时期农场的模式构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公众考古的发展。

图一 弗拉格遗址公园圆房子的建筑复原
(三)中国大明宫考古遗址公园
在简单介绍了日本飞鸟历史公园和弗拉格遗址公园对公众考古产生的影响后,下面再以我国的大明宫考古遗址公园为例,探讨一下遗址公园对我国的公众考古的普及与发展。
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概念的提出,是在20世纪90年代,西安第三次总体规划中明确提出建立唐大明宫遗址公园的方案。2006年,国家文物局审批了《唐大明宫遗址保护总体规划》,西安市政府将计划进行公布。2007年,国家颁布了《国家“十一五”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规划中唐大明宫遗址成为大遗址保护展示的示范园区。2008年8月,经文物部门专家讨论后,《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总体规划》正式通过,公园计划建设面积大约3.5万平方公里,包含了大明宫宫城区以及部分夹城。2009年5月,《唐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总体规划》正式确定。2010年10月,国家文物局发布了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一共12个,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不负众望入围其中。2010年10月,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建成并向公众开放。主要包括开始的殿前区,中间的宫殿区和宫苑区,最后的北夹城以及翰林院[16]五个部分。大明宫考古遗址公园对公众考古发展主要是体现于大明宫遗址公园建造了一个占地四万三千多平方米的考古探索中心。
园内建设的考古中心是利用原有建筑来展现大明宫的考古、保护和修复过程的场所(如图二)。探索中心设置了陶艺展示区、音乐体验区、拓片体验区等供公众参与,例如在音乐体验区设置了三种乐器,钟、编钟和木琴,公众可以用乐器旁边的木槌来敲击乐器,体会钟、编钟和木琴不同的声色。而在拓片体验区可以根据老师的教导自己动手复制拓片。此外,在探索中心的展厅内还设置了众多的考古游戏供公众游玩,比如模拟“墓葬”遗址、模拟“宫殿”遗址,考古勘探游戏、文物保护与修复知识问答、瓦当和宴饮图知识拼图游戏等等。模拟的“墓葬”和“宫殿”遗址能够根据游戏了解唐代砖室墓和宫殿基址的发掘流程;考古勘探游戏分单双人游戏,可以使公众体验利用现代高科技手段进行考古勘探的乐趣;文物保护与修复知识问答则是学习不同种类的文物保护与修复知识;瓦当拼图游戏则是通过拼凑残破的瓦当,使公众注意到形状为圆形和半圆形的瓦当的圆形弧度走向及其纹饰的特征;宴饮图游戏则是根据1987年出土于陕西长安县南里王村的唐代墓室壁画为模板,公众通过玩这个游戏可以大体了解唐代的饮食、民俗、家具等知识。考古探索中心展厅里还陈列展出了与人们生活中息息相关的常用物品,如铜镜、钱币和服饰等,展现出同样物品在不同时期的形态,以他们的发展演变来展示考古学研究成果,帮助公众了解人类的社会生活的发展轨迹。

图二 考古探索中心考古勘探与发掘展示厅
另外,和飞鸟历史公园一样,多媒体的展示也是大明宫遗址公园与公众考古相结合的一大特点。考古探索中心内有众多的影像资料,甚至还有国内最大的IMAX电影院(如图三),供游人参观游览,比如播放3D电影《大明宫传奇》、环球屏幕电影《飞越大明宫》以及精心拍摄的纪录片《大明宫》供参观的公众观看。
大明宫遗址公园所设立的考古探索中心不仅可以让公众在放松、休闲的同时,近距离地感知考古信息,了解古代的历史文化,还可以使公众更多地关注文化遗产的保护,从不同的角度对考古遗址研究提供一定的帮助。

图三 大明宫IMAX影院
三、关于遗址公园和公众考古的几点思考
通过比较分析日本飞鸟历史公园、英国弗拉格遗址公园和我国大明宫考古遗址公园的展示方式对公众考古产生的影响和促进作用,借此谈点个人的见解。
世界经济的大融合大发展,各国资源的紧缺性稀有性和不可再生性,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不仅影响着各个区域经济的格局和未来的趋向,也直接或间接地对文化遗产发掘及遗址的保护产生重要影响。经济建设和城市化进程与文化遗存保护的矛盾是今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长期而又不可回避的矛盾,也是必须要科学对待和妥善解决的问题。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作为新的大遗址保护方式日益成为了今后的主流趋势,从以往的遗址公园建设来看,我国的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第一,遗址的保护与城市建设开发利用两者的关系并没处理好,大遗址地区居民的安置以及对大遗址的保护利用都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在一些观赏性不强、影响力暂时不突出的遗址地区,对大遗址保护重视的力度不够;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需要,往往只考虑眼前的利益,无视长远社会效益,偏重于对影响力大、欣赏性高的一些大遗址斥巨资进行投资,甚至违背规律,违反规定,盲目的过度开发利用,如在遗址保护区内建设了破坏遗址保护的一些违章建筑等。第二,遗址公园经营状况不良,宣传力度不够。目前国内现有的遗址公园建成后缺乏一定的知名度,主要是考古遗址公园的信息宣传力度不够,有的除了考古人几乎无人知道,因此导致游客稀少。许多公众不了解遗址公园的具体内容以及遗址概况,形不成公众参观群,更无法对公众产生浓厚的吸引力,连锁反应也就无法使遗址公园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目前一部分遗址公园甚至无法维持收支平衡,其日常的活动都难以经营下去,反而需要政府给予扶持。第三,遗址公园展示手法单一。目前的遗址公园的展示有些只是一些静态展示方式,对一些考古发掘出来的出土文物,如建筑材料、生活用具、生产工具等采取陈列展示的方式是合适的,但对一些活动、冶炼遗址仅采取这种方式是不够的,过于死板没有趣味性,无法让公众有更为直观的体验,更谈不上有精神上的愉悦感、满足感;而且主题性和科普性讲座、模拟考古、公众参与活动的体验也较少;另外大多数遗址公园仅仅只是注重最后呈献给公众的展示,而考古过程中难以保护的部分以及保护过程中所运用的保护技术并没有向公众详细解释,导致公众只观看了展示,但并不了解具体的操作措施。第四,有关配套项目及基础设施不完备,公交线路设置不合理,园内游客服务中心设置较少,有些遗址公园指示标志不明确,使公众无法及时找到想要观看的景点,耽误了公众的宝贵时间。此外,休息区域座椅普遍较少,一些公共设施如厕所、餐厅等也较少,不能满足公众的需求。
公众考古学虽然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出现萌芽,但是真正得到广泛的关注还是21世纪近些年来,所以如何把新兴的遗址保护方式与公众考古相结合进行普及与发展,笔者认为也是今后遗址保护建设面临的一个难题。
应当看到,在世界经济文化日益深度融合、互连互通、共享发展的今天,文化遗产的保护观念并没有从根本上深入人心。考古所发现的遗址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面向广大公众的,比如城市、乡村、道路的下面才有古代的遗存,这都是与公众息息相关的,需要唤醒全社会公众的保护意识,并使之形成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氛围。此外,考古行业毕竟不同于其他行业,是一个较为特殊的行业,从业人员较少,专业性较强。随着大遗址的保护以及城市化建设的矛盾的不断激化,仅仅依靠有限的考古行业及其相关机构的从业人员进行大遗址的保护是远远不够的,迫切的需要公众考古的发展,需要公众力量的支持。公众考古也正是在考古学专业化与文化遗产保护大众化的矛盾下兴起的[17],发展公众考古不仅能够有助于满足公众对于考古这个行业的好奇心,同时使公众更直观的了解考古知识,学习古代的历史,公众考古也有助于提升考古相关机构的知名度,促进文博事业的发展。尽管公众考古学如今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还受到很多因素制约,比如考古现场的开放受自身的限制以及处于遗址保护的需要并不能全部对外开放,而有一些公众考古也出于安全性和科普性的考虑,需要对年龄有一些限制。还有,进行公众考古的相关机构无强有力的资金支撑,公众考古的盲目性也导致公众的关注点错误反而起到反作用等等。因而,如何更好的发展公众考古学也是值得思考与探究的长远问题。
我国以往公众考古发展的模式大体分为以下几种:一是出版科普图书报刊、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的传播模式。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报社主办的《文物天地》《中国文化遗产》 《中国文物报》等考古报刊,还有现在的一些其他报纸开辟的文博考古专版,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众考古的发展。此外,考古文物类图书和考古学家的传记、游记、随笔,以及一些虚构类的考古小说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大众对考古的关注。微信公众号相关考古文章的宣传工作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众考古的发展。二是公众考古活动。参观考古现场是以往主要的公众考古活动的参与模式,一些正在发掘的或发掘完毕的工地有组织的定期给公众参观,让公众了解考古时所需要的工具,知晓考古的知识,普及考古与盗墓的不同之处,通过参观现场让公众有着更为直观的体验。其他的公众考古活动包括举办的文化遗产日活动、国际博物馆体验日活动、“全国十大考古发现进校园”活动、博物馆举办的面向公众的考古讲座、学校开设的校园讲座等模式,而新出现的遗址保护方式考古遗址公园则在一定程度上更加促进了公众考古的发展。考古遗址公园常见的公众参与展示、模拟现场展示、多媒体展等方式将不同的公众考古模式相结合,并能够把公众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让公众参与各类模拟实验考古,一方面近距离看到了该地的遗址情况,了解考古知识;另一方面能够通过考古遗址公园的模式,使公众对历史文化产生强烈的自豪感和认同感,增强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责任感。所以,将新兴的遗址保护方式考古遗址公园与公众考古相结合进行普及与发展,是今后遗址保护的趋势。
根据我国的考古遗址公园和公众考古发展的不足和优势,笔者认为:第一,在进行遗址公园展示规划时,考古学研究必须是遗址展示的基础,需要展示的遗址单位应当制定考古发掘规划,解决遗址展示中的需求,通过主动和有目的的考古发掘,来完善展示内容[18]。所以要充分发挥考古科研人员在规划和展示中的作用,在设定考古遗址公园规划时一定要与考古工作相结合,规划编制应采取合作的方式,要与进行遗址发掘工作的文物考古机构合作,也要倾听考古学者的意见,他们是最了解遗址的实际情况和文化特点的[19]。第二,进行遗址展示规划时要充分考虑展示方式的多样性,比如模拟实验、体验活动等方式,提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激发公众的参与热情,为科普考古学知识提供更好的平台。第三,要注重公众志愿者在遗址公园中的作用,通过选出一些文化水平高、喜欢考古、了解一定考古知识,乐于奉献的公众,通过做志愿者的方式,参与到考古工作中,根据其工作的亲身体验,慢慢感染渗透其他公众。第四,要完善遗址公园网站建设,加强网络的传播,定期发布一些活动信息、考古信息与相关知识,同公众进行互动,使公众更广泛的参与其中。同时,在遗址公园内定期举行一定的科普讲座,请发掘该遗址的考古人员或其他考古专家通过讲座的形式向公众传递正确、严谨的考古学知识,通过一系列的讲座,让公众了解考古学,了解遗址保护。
考古遗址公园以及公众考古学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今后去讨论。本文只是以日本、英国和中国的三个具有代表性的考古遗址公园的展示方式为例,简要阐释和分析了遗址公园对公众考古的发展起到的影响与作用,旨在抛砖引玉,引起更多方面的重视和关注、更大范围的研究共鸣,以期能够为今后我国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公众考古学的探索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启迪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