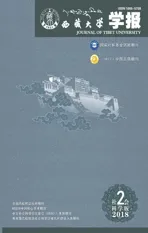20世纪迎来汉藏佛典翻译又一高峰
——追念汉藏佛学研究的三位大师
2018-07-24旺多
旺多
(西藏大学文学院 西藏拉萨 850000)
20世纪,世界形势风云变幻,一次次的变革,一次次的战争,一次次的呼唤,一次次的选择……就我国而言,经历了种种社会动荡与变迁,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王制,打着西方君主立宪制和民主的招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政治体制的进步。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和后天畸形发展,中国仍然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五·四运动”掀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热潮,是中国人民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举起了“科学”与“民主”的旗帜,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旧文化”,提倡“新文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为中国社会进步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伟大的一页。
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的佛学研究掀开了新的一页,像雨后春笋般,呈茁壮滋长之势,这种风气,一直延续了四、五十年。这种风气的形成有着深远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主要原因是太虚大师等提出了“人间佛教”“人生佛教”“人间净土”的主张,高喊“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的口号,认为佛教不仅要关照遥远的“来世”追求,更重要的是顺应时代发展,立足今生今世,解决现实实际问题。
当时,出现了一批佛学界的仁人志士,掀起了一场佛教复兴运动,既推动了我国的佛学研究,又呼吁整个社会关注和解决现世问题,包括个人、民族乃至国家的利益。“二十世纪的中国佛教,大体上沿着一条在厄难中图复兴的崎岖道路行进。从适应后期封建社会的明清佛教传统模式向适应近现代社会的新模式转型,可谓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的特质。”[1]
一、陈寅恪与汉藏佛学研究
陈寅恪(1890-1969年),江西义宁人,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和诗人。他从小学习国学,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数地理。1902年起游学四方,足迹踏遍日、美、欧各大学。1926年回国,与梁启超等一同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先后执教于清华、西南联大(昆明)、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和燕京大学。他在清华大学开设历史、语文、佛学等课程,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展开了研究。1939年,被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是第一位(西南联大)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同时他精通历史学、宗教学、突厥学、蒙古学、文字学,也涉足藏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带动了一批藏学研究学者。对他的藏学研究成就,先后有王尧、苏发祥、王川等发表过论文。
陈寅恪的藏学研究,首先是从语言开始的,他能畅读英、法、德文,又通希伯来文、拉丁文和蒙文,尤其曾刻苦学习了藏文。他在柏林留学期间接触到了藏文佛教典籍,如柏林图书馆藏藏文《甘珠尔》《丹珠尔》等。20世纪30年代,他利用拉萨长庆会盟碑碑文开始研究吐蕃历史。在清华期间,他曾采购大量藏文文集,北平(北京)图书馆馆藏藏文典籍也与陈寅恪有关,同时,他对英藏古藏文敦煌文献等极为关注。在抗日战争期间流亡云南时,为联大学生讲授《佛经翻译》,此外,以大量心血对勘汉、藏、梵原本、译本的异同。牛津大学所藏档案记载:“陈先生是目前中国唯一可以利用藏、蒙、满文原始文献去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的学者,他的成就,像《蒙古源流》等所展现出来那样,是西方汉学家难以超越的”。[2]他对藏学研究的兴趣,一是对藏族文化的真诚热爱,二是被博大精深的藏族文化所吸引,三是认为藏学研究领域广阔。陈寅恪先生是我国藏学研究的前辈学者之一,他的朋友和学生中也不乏有著名藏学家,如李方桂(美籍华人)、于道泉、王森和张怡荪等。
李方桂从语言学的角度深入研究了吐蕃碑文、汉藏佛学词汇以及历史人物,著有《古代学者碑文研究》《敦煌汉藏词汇》《马重英考》等。于道泉(1901~1992年),山东淄博人,通晓多种语言,如英文、法文、梵文、藏文、蒙文、满文等,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教育家和藏学家,是我国现代藏学的开创人之一。192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度人泰戈尔访华时,于道泉是翻译,后陪同泰氏拜访了俄国学者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1877-1937),由此得到了向钢和泰学习梵文、藏文的机会。他的藏学研究成果主要有:《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达赖喇嘛于根敦珠巴以前之转生》《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藏文数码代字》《译注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纪事及宗喀巴覆成祖书》等。王森(1912-1991),河北人,现代著名藏学家、语言学家、宗教学家、因明学家,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顾问和中国宗教学会理事等职。他的藏学研究成果有:《因明在西藏》《藏传因明》《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等。张怡荪(1893-1983年),四川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由于受陈寅恪先生的影响,他曾师从北京雍和宫的喇嘛学习藏文、藏族文化,后被邀请参加了《藏汉大词典》的编纂工作,并担任主编。
陈寅恪于1931年所著《〈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①上世纪80年代苏鲁格先生撰文否定陈先生的主张。2006年沈卫荣发表《再论〈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一文,认为《彰所知论》的确不是《蒙古源流》的直接来源,且“印、蒙、藏同源”并非始于《彰所知论》。指出:蒙古民族起源于天竺、吐蕃之说,受到了八思巴《彰所知论》的影响,思想观念和编制题材实取自《彰所知论》。《彰所知论》是八思巴为太子真金传授藏传佛教道果法修持要义的讲义,是蒙古人接受藏传佛教特别是萨迦派的重要标志之一。《彰所知论》共五品,其中“器世界”和“情世界”直接来自于佛教的《阿毗达摩俱舍论》,对蒙古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产生了影响。《蒙古源流》由萨冈彻辰写于1662年,后译为汉文和满文,定名《钦定蒙古源流》并被收入《四库全书》。
二、吕澂与藏传佛教研究
吕澂(1896-1989年),江苏丹阳人,中国现代佛教学者,曾任中国社学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14年,吕澂来到南京金陵刻经处,协助欧阳竟无筹建支那内学院①1922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国佛教学院和佛学研究机构,由佛教学者欧阳竟无创立。因古印度称中国为“支那”,“内学”为佛学,故名。其宗旨为“阐扬佛学,育材利世”。招收学员,学习法相、唯识典籍,编刻法相、唯识要典和注疏,后有校勘等。1937年被侵华日军毁,后迁至重庆(内学院蜀院)。欧阳竟无去世后吕澂担任院长,对佛学展开系统研究。1952年停办。,于1922年建成,担任教务长,并协办法相大学、勘印《藏要》等。1947年,恢复南京支那内学院,1949年更名为中国内学院,吕澂任院长。1961年,受中国社学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会委托举办了佛学学习部,重点培养佛教研究人才。他的佛学造诣很深,特别是对印度佛教、中国汉藏佛教有深入的研究。著有《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中国佛学源流略讲》《西藏佛学原论》《因明刚要》《因明入正理论讲解》等。在日本留学期间,专攻美术。
吕澂精通梵文、巴利文、藏文、日文、英文、法文等多种语言,凭借语言学的优势,他在解读、校勘梵、藏佛教原典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突破了中国学者向来依靠传统汉文译本大藏经进行佛学探源、研究的局限,被学术界称为“三藏兼备,五明俱通”的佛学大师。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在吕澂先生的追悼会上说:“(吕澂先生)于佛教学术事业,笃志精勤,超敏缜密,……他在佛学义理的研究和佛教典籍的校勘等方面,扶微阐幽,勘同校异,有着许多新的发现和独创的见解,是公认的具有卓越成就的当代佛学大师。”
《西藏佛学原论》②《西藏佛学原论》最早于1931年(民国1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一部有关藏传佛教发展史及汉藏佛学典籍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原书序论中写道:“吕澄依据西藏要籍二十种,分从渊源、传播、文献、学说四方面,推论西藏佛学之特质,兼与汉土所传对论短长期有裨于研学者,与此易得真正之认识,篇末别载藏译大小乘论典六百种之目录,比较参证,资益尤多。”近现代研究佛学的大部分学者认为,西藏有完美纯正之修证、藏译佛典浩繁精严,藏传各说富有精粹,多数学者非常重视西藏佛学研究。无可否认,也有对藏传佛教没有深入了解而造成的一些误解,其中一些是藏传佛教自身在异地传播过程中的一些消极因素所导致的。从20世纪初开始,又一次迎来了“西藏佛学”的研究热潮,开展了对西藏佛学的研究,特别在藏译典籍的挖掘、整理、对勘、考证、翻译等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就,引起了世人的关注。《西藏佛学原论》是国内最早直接利用藏文文献,并在藏、汉经典对勘基础上全面深入介绍藏传佛教的学术著作。该书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也为促进汉地佛教界、学术界全面认知藏传佛教、藏族历史文化提供了一部重要的参考资料。
从《西藏佛学原论》的目录(目次)中可以看出全书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1)渊源:主要对藏传佛教与印度佛教的渊源关系进行梳理和阐释;(2)传播:概述藏传佛教的发展历程;(3)文献:对藏传佛教的典籍进行梳理;(4)学说:对藏传佛教各教派形成、特点及其神学思想进行梳理。“《西藏佛学原论》一书不仅仅是对藏传佛教各种问题进行单纯的梳理和讨论,更多地是侧重于藏、汉佛教之间的比较性分析,以便于汉传佛教界能够更为准确地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为汉传佛教自身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参考依据,这恐怕是吕澂先生撰著此文的重要目的之一。”[3]
该书开头说:“今直接依据藏土资料,兼采时贤之言,就渊源、传播、文献、学说四端,推论西藏佛学之特质,俾其本真显豁可,是亦能与研学之士以一二基本概念矣,因名其篇为原论云。”[4]吕澂先生把“依据藏土资料”与书名中“原论”结合起来,表现了作者对藏文典籍的信心、熟悉程度以及作者深厚的藏文功底。1953年,吕澂先生撰文《汉藏佛学沟通的第一步》提出汉藏佛学沟通的必要性和汉藏佛典翻译研究的迫切性,他说:“随着中国佛协的成立,汉藏佛教界的关系日见密切,两地佛学的沟通也益觉其有迫切的需要。在佛协的成立会议上,代表们讨论到如何发扬佛教的优良传统,就已提出了汉藏佛典翻译的问题。但这问题过於专门了,一时难得有具体的结论。会後,我看到一些有关西藏佛敎文献的稿子,重新引起了注意,因而拟了这个「汉藏佛学沟通的第一步」题目来再发表些意见,以供当代汉藏佛学家的参考。”[5]诚恳地提出了以往工作中不够的地方,认为“沟通的第一步,应该是彼此的互相了解。但以往多少年来,汉藏学者在这方面所做的准备工作就很不够。”[6]
吕澂先生撰写《西藏佛学原论》时,引用了多种藏文原始文献资料,主要有三类:第一类藏文《大藏经》目录,包括《丹噶尔目录》《纳塘新版甘珠尔目录》《北京版丹珠尔目录》等;第二类是藏传佛教史(教法史),主要有布顿·仁钦珠的《善逝教法史》(布顿佛教史)、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罗桑曲吉尼玛所著《一切宗义明镜》(土观宗派源流)等;第三类是重要论著及藏译经论,主要有阿底峡尊者所著《菩提道灯论》及《菩提道灯论详释》、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及《略论》、觉贤所著《定资粮品》、月称所著《入中观论》、隆覩喇嘛所著《隆覩喇嘛全书》以及寂天的《入菩萨行所出愿》等,共有30余种重要典籍。同时,他在《汉藏佛学沟通的第一步》中指出,“至於有关汉地佛学文献《大藏经》方面,西藏也只有工布查的著述里做过《至元法宝勘同目录》的翻译。但至元录本身问题就很多。它的勘同,可说是流於形式的。”[7]
“西藏佛学之文献”是《西藏佛学原论》的重点内容,其中作者做了大量而细致的工作,经过吕澂先生的对勘比较,统计出藏、汉大藏经中收录经典的同异数量(见表1-2)。[8]
造成汉藏佛学典籍差异的原因,吕澂指出“盖密乘之学降至晚宋始见完备,其无汉译者,率皆时代之也”,“西藏藏经多出晚世之书(其显乘论典作者约有二百家,汉土所传仅二十七人而已)”。[9]认为藏传佛教明显受到了印度晚期学说的影响,这是造成汉藏佛典差异的主要原因。另外在《丹珠尔》中,藏、汉经典的差别则更为明显,藏传佛教经典中收录了大量的赞颂、咒语等,在汉译经典中基本上未译出。

表1 《甘珠尔》经律与汉译本对勘统计

表2 《丹珠尔》论著与汉译本对勘统计
在藏地显教推崇龙树、无著二人,龙树本论《七十空性》与《中观》并重,汉译仅存《中论》而其注疏佛护、月称之作均未传;无著所著《慈氏五论》,汉译亦缺其二;陈那继世亲之业,法称益推衍之,而于汉译一无闻焉。在藏地,龙树之中观实际是以月称学说为核心的中观学说;无著的瑜伽派实际上是以法称为核心的瑜伽学说;密乘是以印度超戒寺系统为主的无上瑜伽。而汉地只有于中唐以前流行的三部瑜伽,并没有无上瑜伽。
“虽然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同源于印度佛教,但两者在经典种类和数量、教理教义、修学方法上存在明显的差别,这正是由于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必然结果。这也是吕澂先生通过大量藏、汉经典对勘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10]
吕澂先生所撰《西藏佛学原论》是一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关于藏传佛教研究的学术著作。吕澂先生在动荡艰险的环境下,仍孜孜精进地开展佛学研究,并在佛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强调佛学研究要具有世界性的眼光。他以理性审慎的态度和独到敏锐的视角,对藏传佛教的历史渊源和宗派教理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梳理,极大地推动了近代佛学研究。吕澂先生通过研究所得出的很多结论,对于我们今天从事佛学研究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和指导意义。在藏、汉佛教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当我们回顾中国藏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时,吕澂先生及其对中国佛教的巨大贡献仍然是这一进程中为人仰望的里程碑。[11]
三、法尊法师与汉藏佛典翻译
法尊法师是现代著名的高僧、佛学家、汉藏佛典翻译家。法师为沟通汉藏文化、促进汉藏佛学交流、传播和弘扬藏传佛教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法师成果有论著、论文、译著、译文、讲记等共20余部(篇)。法师通过翻译,将藏传佛教的重要显密经典第一次介绍到了汉地,如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论》《密宗道次第论》等,促进了汉藏佛教界的进一步沟通和交流。同时,他十分了解和熟悉西藏的历史、宗教、风俗、语言和地理。《西藏民族政教史》是他的一部历史专著,也是一部较有影响和参考价值的藏传佛教史籍。《现代西藏》是一部好的教科书。
综观法尊法师一生,他在汉藏佛教典籍的互译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填补了汉藏佛学交流、研究领域的一些空白,是20世纪汉藏佛典互译的先驱者和榜样。
法尊法师所著的《善慧海》《西藏前弘期佛教》《西藏后弘期佛教》《嘉曹杰》《西藏佛教的宁玛派》《克主杰》《西藏佛教的迦当派》《律经》[12]等作品系统全面地介绍了藏传佛教的历史和主要教派、代表性人物、藏传佛教教义及佛教经典。法尊法师编写的这些关于藏传佛教的论著,至今仍然堪称权威而被教内外人士参考引用。
法尊法师圆寂后,整个佛教界处在悲痛和惋惜之中,时任中国佛协会会长的赵朴初为法尊法师写下悼词道:
溯自汉明西使,白马东来,士行、法显、玄奘、义净并能不惜身命,忘躯求法,高风卓行,百代钦仰。若法师者,诚可希踪先贤,比肩古德矣。方冀广翻要典,续补佚篇,光大释门,增辉四化,何期化缘已毕,溘然长往!痛哉无常,夺我法匠,天地易色,草木凄怆!同愿等万里来集,缘悭一面,瞻仰遗容,倍增悲感!择泪述赞,永志哀思。赞曰:[13]
象教东流,译业为先,名德世出,贤哲比肩。
赵宋而后,响绝五天,雪岭继兴,法炬复燃。
猗欤法师,挺生季世,抗心希古,游学藏卫。
译述等身,老而弥励,法称伟作,翻传功济。
法师之德,桂馥兰芳;法师之行,如圭如璋。
法师之功,山高水长。典型百代,释宗之光。
四害既除,法教日昌,方冀哲匠,长寿康强。
盛会伊始,痛失楝梁,缅怀功德,哀思不忘![14]
1988年,台湾文殊出版社编辑印行了当代中国佛教大师文集丛书,收有《法尊文集》。1990年,中国佛教协会佛教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印行《法尊法师佛学论文集》。《法尊法师全集》由著名学者、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吕铁钢主编,由上海文化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发行,共有10册。
结语
自7世纪以来,汉藏佛学交流源远流长,汉藏佛经翻译又贯穿于藏族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应该说汉藏佛学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和现实意义,其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应是汉藏佛经翻译方面的研究。从20世纪初开始又一次迎来了“西藏佛学”的研究热潮,开展了对西藏佛学的研究,特别是藏译典籍的挖掘、整理、对勘、考证、翻译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就,引起了世人的关注。20世纪掀起的汉藏佛学研究、汉藏佛经互译实践、关注汉藏佛经对勘等等,是历史上形成的汉藏佛学交流的延续、深化和发展,对当下进一步促进汉藏佛教界的交流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