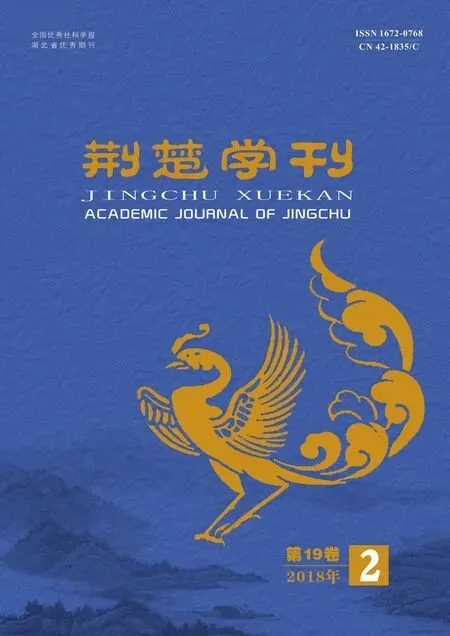内圣外王:《郭店老子甲本》的结构秩序
2018-06-19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郭店老子》于1993年出土于湖北荆门的郭店村,系战国时期的《老子》传抄本,《郭店老子》分甲、乙、丙三本,甲本的抄写时间早于乙本、丙本。学界有多名学者从文字特点与书写字体[1],以及内在思想[2]等方面论证了甲本早于乙本、丙本,甲本早于乙本、丙本的观点在学界已取得共识。《郭店老子甲本》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老子》传抄本。
《郭店老子甲本》由五组竹简拼连而成,《郭店楚墓竹简》[3]一书中的《郭店老子甲本》所拼连的五组先后顺序并不等于《郭店老子甲本》原抄本的顺序。韩禄伯明确提到这一点,“(郭店)《老子》甲组有5枚简以章首之文始录于简头,因而,39枚简可分为5个单元。……按《郭店楚墓竹简》一书所示排列,而非其原始顺序。……第19章(“绝智弃辩”章)未必就是(郭店)《老子》甲组的文首。”[4]但韩禄伯没有对五组的先后顺序进行重新调整。《郭店楚墓竹简》一书中的《郭店老子甲本》原第一组直接进入治国的内容,显得唐突。原第二组首章提出道,应作为第一组,道是治国的依据。《郭店楚墓竹简》一书中的《郭店老子甲本》五组组别顺序应进行调整,原第二组应作为第一组,原第三组应作为第二组,原第五组应作为第三组,原第一组应作为第四组,原第四组应作为第五组。对五组的组别顺序进行调整后,整本能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李零在《郭店楚简校读记》中“……依原简的篇章符号,参酌文义,重新排列”[5]3,也采取了同样的调整。原简的内容文义和篇章符号得到了吻合,这样的调整是颇有说服力的。郭沂在《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一书中也认同和采用了李零的调整方案[6]49-100。崔仁义也有自己的调整方案,调整后的前三组和李零的相同[7]。但李零和郭沂都未进一步揭示出《郭店老子甲本》的内圣外王的结构秩序,尤其未对具体的章与章之间的关联性进行揭示。
一、内圣篇与外王篇:《郭店老子甲本》的结构层次
内圣外王之道,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内圣就是成为圣人,外王就是圣人治国。前者是修身,后者是治国。前者是个人人格(境界),后者是社会责任(事功)。前者是个体性维度,后者是社会性维度。内圣外王在生活口语层面,就是常说的“先做人,再做事。”
一般认为,内圣外王之道只是儒家的传统,其实不然,道家是明确提出内圣外王之道的思想的,最早明确提出内圣外王之道是在《庄子·天下篇》里。《庄子·天下篇》是推崇内圣外王之道的,认为内圣外王之道没有得以彰显,才导致各派学说按照自己的意志和目的自作主张,“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有的学者把此句理解为是对内圣外王之道自身的否定,是一大误解。而在《郭店老子甲本》中,老子又是直接按照内圣外王的结构秩序构建自己的思想的。其实道家、儒家均有内圣外王之道的思想,冯友兰有过相关论述,“哲学所讲的就是中国哲学家所谓‘内圣外王’之道”[8]7,“道家同意儒家的说法:理想的国家是有圣人为首的国家。只有圣人能够治国,应该治国”[8]86。许抗生也明确表述过,“儒家道家都讲内圣外王之道”[9]。梁涛考究得出,“北宋时期是‘内圣外王’由道家用语向儒家术语演变的重要时期”[10]。也就是,“内圣外王”最先是道家的概念,其后才是儒家借用其概念。
李零认为《郭店老子甲本》有层次结构,“此组分篇甚有理致,上篇犹如《道经》,是以论述天道贵虚、贵柔、贵弱为主,下篇犹如《德经》,是以论述‘治道无为’为主,即以‘无为’治国用兵取天下为主,似乎是按不同的主题而编录。”[5]3-4李零敏锐地看到《郭店老子甲本》“分篇甚有理致”。李零认为上篇“论述天道贵虚、贵柔、贵弱为主”,其实就是内圣的维度;认为下篇“论述‘治道无为’为主”,其实就是外王的维度。但李零没有明确使用“内圣外王”的概念。另外,李零认为“似乎是按不同的主题而编录”,但未具体揭示具体主题以及章与章之间的具体脉络。
郭沂也认为《郭店老子》有层次结构,“简本《老子》从内容到形式皆甚有理致。……每篇都有自己的主题。第一篇着重讨论守道归朴的根据,第二篇着重讨论守道归朴的效果……。”[6]49-50郭沂认为“第一篇(即《郭店老子甲本》上篇)着重讨论守道归朴的根据”,其实就是内圣的维度;认为“第二篇(即《郭店老子甲本》下篇)着重讨论守道归朴的效果”,其实就是外王的维度。但郭沂同样没有明确使用“内圣外王”的概念。另外,郭沂同样也未具体揭示具体主题以及章与章之间的具体脉络。郭沂把不同时期的《郭店老子》三个文本作为一个完整的文本,忽视了《郭店老子甲本》自身是一个独立完整的文本,无需和乙本、丙本共同组成一个文本。高华平从文献学角度,也论述过乙本、丙本与甲本不是同一个整体,“通过考察郭店楚简《老子》的内容和文体特征,认为郭店《老子》文本显示《老子》一书原是经、传的混合体;郭店《老子》甲组属‘经文’,乙、丙二组属‘解说文’。”[11]邓球柏明确提出了《郭店老子》有内圣外王之道的主题,“我初步认识到内圣外王之道是《郭简·老子》的主题思想”[12]。但作者仅仅是认为《郭店老子》的内容里有内圣外王的主题思想,这一发现虽然也很重要,但忽视了《郭店老子甲本》的整体篇章顺序本身就是依照内圣外王的结构秩序布局的,也就是关注到了思想主题,而忽视了文本的脉络结构。邓球柏和郭沂一样,把不同时期的《郭店老子》三个文本作为一个完整的文本,而忽视了《郭店老子甲本》自身是一个独立完整的文本。
这个体系依照内圣外王的结构秩序展开,内圣即成为圣人,外王即圣人治国。《郭店老子甲本》共20章(1000余字),内圣篇是1至7章的内容,先后从人法天地、人法自然、人法道的途径进行论述(依照首章的末句的中心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展开);外王篇是8至20章的内容,先后从圣人欲不欲、圣人好静、圣人无为、圣人无事的途径进行论述(依照末章末句的中心句“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欲不欲而民自朴”而展开)。《郭店老子甲本》的释文和具体结构秩序如下:
(一)内圣篇(成为圣人的途径)
1.道(总纲)
一章:有将昆成,先天地生。悦穆,独立不改,可以为天下母。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国中有四大焉,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2.人法天地
二章:天地之间,其犹橐籥欤?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三章:至虚,亘也;守中,笃也。万物方作,居以须复也。天道员员,各复其根。
3.人法自然
四章:含悳之厚者,比于赤子。螝蠆虫蛇弗蠚,攫鸟猛兽弗扣。骨弱筋柔而捉固,未知牝牡之合然怒,精之至也。终日呼而不嚘,和之至也。和曰常,知和曰明。益生曰羕,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
五章: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厚藏必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4.人法道
六章:反也者,道动也;弱也者,道之用也。天下之物生于有、生于无。
七章:持而盈之,不不若已。湍而群之,不可长保也。金玉盈室,莫能守也。贵福骄,自遗咎也。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二)外王篇(圣人治国的途径)
1.圣人欲不欲
八章: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绝伪弃虑,民复季子。三言以为辨不足,或命之或呼属:视索保仆,少私寡欲。
九章:江海所以为百谷王,以其能为百谷下,是以能为百谷王。圣人之在民前也,以身后之;其在民上也,以言下之。其在民上也,民弗厚也;其在民前也,民弗害也。天下乐进而弗厌。以其不争也,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十章:罪莫厚乎甚欲,咎莫险乎欲得,祸莫大乎不知足。知足之为足,此亘足矣。
2.圣人好静
十一章:以道佐人主者,不欲以兵强于天下。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强。果而弗伐,果而弗骄,果而弗矜,是谓果而不强,其事好。
十二章:长古之善为士者,必微弱玄达,深不可识,是以为之容:豫乎若冬涉川,犹乎其若畏四邻,俨乎其若客,涣乎其若释,敦乎其若朴,沌乎其若浊。孰能浊以静者将徐清,孰能安以动者将徐生?保此道者,不欲尚盈。
3.圣人无为
十三章:为之者败之,执之者远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临事之纪,慎终如始,此无败事矣。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教不教,复众之所所过。是故圣人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能为。
十四章:道亘无为也,侯王能守之,而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将镇之以无名之仆。夫亦将知足,知以静,万物将自定。
十五章: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之。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
十六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也,恶已;皆知善,此其不善已。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是以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也,为而弗志也,成而弗居。天唯弗居也,是以弗去也。
十七章:道亘无名仆唯妻,天地弗敢臣。侯王如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也,以输甘露,民莫之命而自均焉。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卑道之在天下也,犹小谷之与江海。
4.圣人无事
十八章:其安也,易持也;其未兆也,易谋也。其脆也,易判也;其几也,易散也。为之于其无有也,治之于其未乱。合(抱之木,作于毫)末;九成之台,作(于垒土;百仞之高,始于)足下。
十九章:知之者弗言,言之者弗知。闭其兑,塞其门;和其光,同其尘;挫其锐,解其纷。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亦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
二十章:以正治邦,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也?夫天多忌讳而民弥叛,民多利器而邦滋昏,人多智而奇物滋起,法物滋彰盗贼多有。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欲不欲而民自朴。
内圣篇,论述成为圣人;外王篇,论述圣人治国。《郭店老子甲本》在整体篇章结构上,就是依照内圣外王的结构秩序所展开。在具体论述内圣和外王时,同样是有其结构秩序的。内圣篇先后论述了成为圣人的途径:人法天地、人法自然、人法道,而这样的具体论述,又是依照首章的末句的中心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展开的。外王篇先后论述圣人治国的途径:圣人欲不欲、圣人好静、圣人无事、圣人无为,而这样的具体论述,又是依照末章末句的中心句“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欲不欲而民自朴”而展开的。也就是内圣的三大具体途径和外王的四大具体途径,都有原文所明示,它是一个自洽的结构系统,而不是笔者强加的。
还有一个微观的问题,就是原文是否与这些具体途径具有一致性,也就是笔者的层次分析是否符合原文本意的问题,这仍然可以通过原文的代表性句子加以验证。
在内圣篇中,人法天地是二章、三章的内容。二章中“天地之间,其犹橐籥欤?”直接提到了天地;三章的“天道员员,各复其根”直接提到了天(这里的天道不是本原之道,而是天的法则)。人法自然是四章、五章的内容(人法自然是人以本然为法)。四章中的“含悳之厚者,比于赤子”论述了人的本然状态犹如初生的婴儿。五章中的“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论述了人的本然是人的内在生命——身,而不是外在之名货。人法道是六、七章的内容。六章中的“反也者,道动也”、七章中的“功遂身退,天之道也”都明确提到了道。
在外王篇中,圣人欲不欲是八章、九章的内容(圣人欲不欲也就是圣人以不欲为欲,即圣人不彰显欲望)。八章中的“视索保仆,少私寡欲”直接提到了寡欲;九章中的“以其不争也,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也是不欲的体现;十章中的“罪莫厚乎甚欲”,也直接提到了欲望的后果。圣人好静是十一章、十二章的内容;十一章的“以道佐人主者,不欲以兵强于天下”,论述了不妄动,不好战;十二章“孰能浊以静者将徐清”明确提到了静。圣人无为是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十七章的内容。十三章中的“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十四章中的“道亘无为也”,十五章中的“为无为”,十六章中的“是以圣人居无为之事”,都直接提到的无为的表述;十七章中的“道恒无名仆唯妻”是无为的具体表现。圣人无事是十八章、十九章、二十章的内容。十八章中的“为之于其无有也,治之于其未乱”,十九章中的“玄同”,是无事的具体表现;二十章中的“以无事取天下”明确提到了无事。
二、内圣篇:论述成为圣人的途径
《郭店老子甲本》内圣篇是1-7章的内容,一章即首章先提出了道,道是内圣外王的依据。因而首章既是内圣篇的总纲,也是《郭店老子甲本》整本书的总纲。
一章:有将昆成,先天地生。悦穆,独立不改,可以为天下母。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国中有四大焉,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郭店老子甲本》只有“有将昆成,先天地生”一句是本原之道的维度,其他章节不再提到本原之道,而五千言《道德经》有多章论述本原之道,并有玄虚的表述。《郭店老子甲本》在“有将昆成,先天地生”一句之后,接而从本原之道转化为治国之道。“悦穆”是讲道之容与道之静,容和静都有价值意义,这都不再是谈论本原之道,而是谈论治国之道。(悦穆:在《郭店楚墓竹简》中的释文是“敚穆”。“敚穆”其实就是“悦穆”,《文子·精诚》中的“老子曰:……夫道者……静漠恬惔,悦穆胸中,廓然无形,寂然无声”一句可证。王利器在《文子疏义》中提到,“悦穆在《淮南子·泰族篇》中是颂缪,许慎云,颂,容也,缪,静也。”[14]也就是悦穆就是容与静,这是符合老子思想的。悦(讼)即容,是老子的处下思想,与《郭店老子甲本》十七章的“卑道之在天下也,犹小谷之与江海”相照应。穆(缪)即静,是老子的虚静思想,与《郭店老子甲本》十四章的“知以静,万物将自定”相照应。)“独立不改”是论述治道之恒久性。“可以为天下母”,则直接点明这里的道是治道的维度,因为“天下”是政治概念。作者用大、逝、远、反四大特征来描述治道,是分别突出治道的四种可能性:完满性、消亡性、持久性、更替性。完满性,即以道治国就是完满的。消亡性,即老子说的“无”,“无”在《郭店老子甲本》的原文正好是“亡”。持久性,即老子说的“有”。治国面临持久与消亡两种状态,这就是反,有和无的更替,这和《郭店老子甲本》中的“有无(亡)之相生也”相验证。《郭店老子甲本》里谈论的有无(亡)问题,也就是谈论存亡之道。《汉书·艺文志》也认为,道家明存亡之道,“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易传》也认为圣人是知存亡之道的,“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把道的顺序放在天地之后,也是再一次说明本原之道已转化为治国之道,治道在天地之后,而不是“先天地生”的本原之道。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老子也是“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的顺序[15]。董仲舒讲“天不变,道亦不变”,这里的道也是治国之道,所以在天之后。五千言《道德经》把道的顺序放在第一位,则是把这里的道理解为本原之道而非治国之道了。“国中有四大焉,王居一焉”,进一步确立了王的地位,王与天、地、道同为大。王是圣人、圣王,也就是实现内圣外王之道的人。“国中有四大焉”,直接转到论述“国”,也是在突出治国之道。
老子以本原之道为起点,但最终归宿点是落在治国之道上的。而老子主张由圣人来治国,要实现圣人治国(外王),先得成为圣人(内圣)。为何要圣人来治国,圣人是依道而行的人,是完满的人,圣人也就是所谓的得道者。道是完满的,圣人又是通道的人,所以圣人是完满的。完满的人——圣人,在内在的境界上是完满的,在外在的事功上也是完满的,前者是内圣,后者是外王。也就是成为圣人后,圣人不是逃离社会,而是担当起社会责任,即圣人治国,这也就是所谓的内圣外王之道。老子说的王,也就是圣人,所以老子在首章表述为“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国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王(圣人)和天、地、道,都是完满的。《庄子·天下篇》里也认为圣和王同源,“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圣人是完满的人,是通道的人。圣有通的意思,《说文解字》说:“圣,通也”。王也有通的含义,董仲舒从造字的角度揭示了王字的内涵,“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第四十四)
首章末句提出了内圣(成为圣人)的具体途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一句的主语是人,人是主体,人有意识,是人法地、法天、法道、法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实际应为“人法地、法天、法道、法自然”。老子把“人法地、法天、法道、法自然”表述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表达的转换是修辞的需要,用前一句的尾字接后一句的首字(类似成语接龙),仅仅是一种语音节奏的需要,达到一种一气贯注的效果。(比如,“吾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正好还原为:“吾强为之名曰大、曰逝、曰远、曰反”,这就符合了老子的本意,是以为证。)也就是人不仅法地,还要法天、法道、法自然,这也符合老子的整体思想。如果简单的按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字面形式断句,而不做修辞的还原,即人只法地,不法天、道、自然,显然不符合老子的整体思想的。另外“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把地、天、道作为主语,是违背老子思想的,因为地、天、道是没有意志的,也就不存在去法的问题。因而,把“道法自然”作为老子的核心命题之一,显然是值得商榷的。人是主体,人有意识,是人法自然,指人以自身的本然为法。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实际应为“人法地、法天、法道、法自然”。老子在具体论述中,把人法天地进行合并论述,然后论述人法自然,最后论述人法道。也即在具体论述中,老子认为成为圣人的途径是:人法天地、人法自然、人法道。
《郭店老子甲本》二、三章论述人法天地,四、五章论述人法自然,六、七章论述人法道。
(一)人法天地:人以天地为法
人法天地论述的是人与天地的关系,即人以天地为法。相关原文为《郭店老子甲本》二、三章。
二章:天地之间,其犹橐籥欤?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三章:至虚,亘也;守中,笃也。万物方作,居以须复也。天道员员,各复其根。
二章中“天地之间,其犹橐籥欤?”直接提到了天地;三章的“天道员员,各复其根”直接提到了天,这里的天道不是本原之道,而是天的法则。
二章中的“虚而不屈,动而愈出”是为了突出虚静的力量,实际是为了言说不要发动权力意志。三章中的“至虚,亘也;守中,笃也”,至虚就是至虚静,守中就是向内守(《说文解字》:中,内也)。
(二)人法自然:人以自然(本然)为法
人法自然论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以自然为法。(自然是人之本然)相关原文为《郭店老子甲本》四、五章。
四章:含悳之厚者,比于赤子。螝蠆虫蛇弗蠚,攫鸟猛兽弗扣。骨弱筋柔而捉固,未知牝牡之合然怒,精之至也。终日呼而不嚘,和之至也。和曰常,知和曰明。益生曰羕,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
五章: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厚藏必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人法自然是人以自然(本然)为法。四章中的“含悳之厚者,比于赤子”论述了人的本然状态犹如初生的婴儿。五章中的“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论述了人的本然是人的内在生命——身,而不是外在之名货。
四章中的“含悳之厚者,比于赤子”,是突出人的自然(人之本然)状态,亦即人的原初性、本心,而这就犹如赤子(婴儿)状态。所以老子的自然,不是大自然,而是人的本然。老子用赤子(婴儿)作为比喻,是用赤子(婴儿)来比喻圣人的素朴,而不是巧诈之心,反对巧诈也就主要是为了反对权谋。而这种质朴之心,意味着人的自足自由。《说文解字》:“悳,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从直从心。”从直从心,即是本心、自然(本然)之心。“老子‘自然’的本义为初始的样子、本来的样子、本然。老子之所以用‘赤子’、‘朴’等来形容‘自然’,那是因为‘赤子’乃人之初,而‘朴’为未加工成器的木材,亦即未经雕饰、仍保持本来样子的木材。”[6]53五章中的“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是把身作为内在要素,把名货作为外在要素,是为了言说圣人的人格是超越名货追求的。(名是指社会名位,货指物质财富。)超越名货,是一种公心,超越了一己之私。身作为内在要素,名货作为外在要素,老子主张守身,也就是向内守,这和“守中,笃也”一句照应。《说文解字》:“中,内也”,守中就是守内。
(三)人法道:人以道为法
人法道论述的是人与道的关系,即人以道为法。相关原文为《郭店老子甲本》六、七章。
六章:反也者,道动也;弱也者,道之用也。天下之物生于有、生于无。
七章:持而盈之,不不若已。湍而群之,不可长保也。金玉盈室,莫能守也。贵福骄,自遗咎也。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六章中的“反也者,道动也”、七章中的“功遂身退,天之道也”都明确提到了道。
六章中的“反也者,道动也”,是用道来言说人之对反,而这个对反主要是有和无的对反:“天下之物生于有、生于无”。有和无的对反,具体指存在与消亡的共存,无的原文为亡,通俗地说就是人有生死。“天下之物生于有、生于无”,说明有和无的地位是并列的,与老子有无相生的思想照应(《郭店老子甲本》十六章有“有无之相生也”的原文)。而五千言《道德经》是“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其“有生于无”说明无的地位高于有的地位,这就会造成与“有无相生”的思想相互矛盾。当然,老子还用有无(亡)意指治道意义的存亡之道。七章中的“功遂身退,天之道也”,是对名货(名利)的超越,也是对六章中的“弱也者,道之用也”的进一步论述。老子之所以强调柔弱,是柔弱者不强制人,而刚毅者容易强制人,而不强制人是符合自由精神的,自由可以理解为不被强制。犹如哈耶克所说,“在这种状态下,社会中他人的强制被尽可能地减到最小限度。这种状态我们称之为‘自由’的状态。”[16]28
当人做到法天地、法自然、法道,也就成为了圣人,也就具有了治国的内圣条件。为何当人做到法天地、法自然、法道,也就成为了圣人呢?这是因为人法天地、自然、道,就是“以天为则”,是人合于“天”,其实达到了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天地、自然、道都是广义的“天”的范畴。在五千言《道德经》二十三章里则表达为“道者同于道”。《庄子》则表述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同样是在主张天人合一的境界。《庄子·天下篇》在表述何为圣人时,第一要义就是“以天为宗”。《史记》中提到“究天人之际”,也是把天人关系作为一个重要的起点。
三、外王篇:论述圣人治国的途径
完满的人——圣人,在内在的人格上是完满的,在外在的事功上也是完满的,前者是内圣,后者是外王。也就是圣人不是逃离社会,而是担当起社会责任,即圣人治国。(孔子也强调外王,孔子不仅讲“修己”,还讲“安百姓”。《大学》讲修身也是为了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外王意义。)
老子的治国思想,体现了老子对理想社会的构想。老子的思想是民本的,反对权力至上,反对权力对民进行干预与强制,而达到一种自由自治的秩序,这样的社会是民拥有充分自由的社会,老子把这样的理想社会称为:民自富、民自化、民自正、民自朴。四个“民”字,体现了民本主义;四个“自”字,体现了自由自治的秩序。要达到这样的理想社会,老子认为需要执政者依道而行,道是处下的,“道亘无名仆唯妻”,执政者为仆也就是执政者的角色是公共服务者。
外王即圣人治国,主要是处理好执政者与民的关系。完满的执政者是圣人,所以在老子思想里也就是圣民关系的问题,在圣民关系里,老子又是以民为本的,这是一种圣民合一的思想。在老子看来,人的自由是在人的关系里体现的。哈耶克也非常重视这一点,“自由‘专指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16]30而人的自由意味着不被强制,而来自强制的最大要素往往是执政者,所以老子最关注的人的关系是执政者与民的关系,而倡导以民为本的圣民关系,在这样的关系里是没有强制的:“我(圣人)无为而民自化”。
如何达到民自富、民自化、民自正、民自朴的理想社会,老子认为需要由合道的人来治国,即圣人治国,而圣人治国的具体途径,《郭店老子甲本》在最后一章末句概括为:“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欲不欲而民自朴。”也就是圣人治国的途径是:圣人无事、圣人无为、圣人好静、圣人欲不欲。在具体论述中,老子把顺序做了颠倒,先后按照圣人欲不欲、圣人好静、圣人无为、圣人无事的顺序进行。圣人欲不欲,就是执政者不彰显私欲;圣人好静,就是执政者不发动权力意志;圣人无为,就是执政者不强制;圣人无事,就是执政者不扰民。
《郭店老子甲本》八至十章论述圣人欲不欲,十一至十二章论述圣人好静,十三至十七章论述圣人无为,十八至二十章论述圣人无事。
(一)圣人欲不欲:民自朴
圣人欲不欲,即圣人不彰显私欲(以不欲为欲),而民自朴。相关原文为《郭店老子甲本》八章、九章、十章。
八章: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绝伪弃虑,民复季子。三言以为辨不足,或命之或呼属:视索保仆,少私寡欲。
九章:江海所以为百谷王,以其能为百谷下,是以能为百谷王。圣人之在民前也,以身后之;其在民上也,以言下之。其在民上也,民弗厚也;其在民前也,民弗害也。天下乐进而弗厌。以其不争也,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十章:罪莫厚乎甚欲,咎莫险乎欲得,祸莫大乎不知足。知足之为足,此亘足矣。
八章中的“视索保仆,少私寡欲”直接提到了寡欲;九章中的“以其不争也,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也是不欲的体现;十章中的“罪莫厚乎甚欲”,也直接提到了欲望的后果。
既然执政者为公不为私,执政者就不要彰显私欲。圣人欲不欲,八章表述为“视索保仆,少私寡欲”。也就是老子承认了合理的欲望,既不主张纵欲但也不主张禁欲。(五千言《道德经》里有“无欲”的表述,显然陷入了禁欲主义,与“少私寡欲”相矛盾。)而“少私寡欲”又具体表现为不争和知足,也就是九章和十章分别要论述的内容。九章讲的不争,是说执政者处下,不与民争利,体现了为公不为私的公共服务精神,也就是一种民本精神。十章讲欲望彰显的后果是罪、咎、祸,因而主张知足。
八章的“绝智弃辩”在五千言《道德经》里是“绝圣弃智”,如果老子一方面推崇圣人,一方面又“绝圣”,会导致相互矛盾,而“绝智弃辩”就不会有这样的悖论。八章的“民复季子”在五千言《道德经》里是“民复孝慈”,如果老子一方面解构儒家价值观,一方面又推崇儒家的孝慈,也会导致相互矛盾,而“民复季子”就不会有这样的悖论。季子即童子,意指童真。《说文解字》:“季,少称也。”有的学者把原文的“季子”释为“孝慈”,是受到五千言《道德经》的影响而采取了先入为主的做法。
(二)圣人好静:民自正
圣人好静,即圣人不发动权力意志,而民自正。相关原文为《郭店老子甲本》十一章、十二章。
十一章:以道佐人主者,不欲以兵强于天下。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强。果而弗伐,果而弗骄,果而弗矜,是谓果而不强,其事好。
十二章:长古之善为士者,必微弱玄达,深不可识,是以为之容:豫乎若冬涉川,犹乎其若畏四邻,俨乎其若客,涣乎其若释,敦乎其若朴,沌乎其若浊。孰能浊以静者将徐清,孰能安以动者将徐生?保此道者,不欲尚盈。
十一章的“以道佐人主者,不欲以兵强于天下”,论述了不妄动,不好战;十二章“孰能浊以静者将徐清”明确提到了“静”。
圣人好静,体现出老子的人类情怀和人文关怀,老子是反对倚强凌弱的丛林法则。十一章的“不欲以兵强于天下”,说明老子是主张和平而反战的,而这需要执政者去除征服欲。十二章里的“犹乎其若畏四邻”等描述,老子意在说执政者需要谨小慎微,去除权力意志,而不是狂妄自大;“孰能浊以静者将徐清”关于静的主张,同样是为了反对权力意志的发动,所以二十章提到“我好静而民自正”。
(三)圣人无为:民自化
圣人无为,即圣人不强制,而民自化。相关原文为《郭店老子甲本》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十七章。
十三章:为之者败之,执之者远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临事之纪,慎终如始,此无败事矣。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教不教,复众之所所过。是故圣人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能为。
十四章:道亘无为也,侯王能守之,而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将镇之以无名之仆。夫亦将知足,知以静,万物将自定。
十五章: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之。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
十六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也,恶已;皆知善,此其不善已。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是以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也,为而弗志也,成而弗居。天唯弗居也,是以弗去也。
十七章:道亘无名仆唯妻,天地弗敢臣。侯王如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也,以输甘露,民莫之命而自均焉。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卑道之在天下也,犹小谷之与江海。
十三章中的“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十四章中的“道亘无为也”,十五章中的“为无为”,十六章中的“是以圣人居无为之事”,都直接提到的无为的表述;十七章中的“道恒无名仆唯妻”是无为的具体表现。执政者无为,对民不强制、不干预,是防止公权力异化为私权力,体现主权在民、民自主,这是一种民本思想。执政者不强制,民就是自由的状态。犹如哈耶克所说,“在这种状态下,社会中他人的强制被尽可能地减到最小限度。这种状态我们称之为‘自由’的状态。”[16]28
老子把无为上升到道的高度,认为道是无为的:“道亘无为也”(十四章),这也说明无为之治确实是老子非常重要的思想,老子主张的道治也就是无为之治。《郭店老子甲本》用了5个章节的内容来专题论述(其中,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共4个章节都直接涉及“无为”的原文),是治国论中篇幅最长的一个专题。学界通常也认同老子的治国方略是无为之治,但学界对无为一词的理解颇有争议,解读得较为发散。其实,无为就是不强制,执政者无为就是执政者不强制民。“为”字的甲骨文是,从爪从象,原意是人对象进行驯化,驯化意味着改变本来状态,是强加人的意志,所以“为”的本义是意志的强加,故而无为也包含不强加意志的意思,无为也就是不强制。执政者无为,就是不彰显权力意志,对民不强制、不干预,是防止公权力异化为私权力,体现民自主的民本思想。《韩非子·扬权篇》也认为不彰显权力即是无为,“权不欲见,素无为也”。执政者不强制,民就是自由的状态。执政者处下,对民不干预和强制,从而突出民本的地位,实现自由自治的理想社会。
在老子思想里,对于“为”的问题,有的地方是反对“为”的,比如十三章中的“为之者败之”;而有的章节又是主张“为”的,比如十六章中的“为而弗志也”,十八章的“为之于其无有也”。出现这种情况,并非老子思想的悖论,而是“为”具有不同的含义。凡是老子在反对“为”时,这里的“为”是强制的意思;凡是老子在主张“为”时,这里的“为”是“做”的意思。
十三章提出“无为故无败”,表述的是无为之治的作用和意义。十四章的“道亘无为”,把无为之治上升到道的高度(突出了无为的重要性),也就是执政者实施无为之治才是符合道的。十五章的“为无为……是以圣人犹难之”,表述的是执政者不要轻易发动权力意志,而妄自尊大。十六章的“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旨在反对执政者采取意识形态驯化,反对推崇唯一真理,而是主张思想自由,具有怀疑精神,从而具有多元化的价值。十七章:“道亘无名仆唯妻”,则更加明确地突出了执政者的角色:执政者是仆(公共服务者)。
《郭店老子甲本》中有三处“仆”的原文:“道亘无名仆唯妻”、“将镇之以无名之仆”,“视索保仆”。学界普遍把“仆”通为朴,是受到五千言《道德经》的先入为主的影响,而导致两者的差异性被遮蔽。“朴”和“仆”,虽然音近,却不能随意互通,因为两个词各有其独特的含义。“朴”原文为樸,是素朴的意思,本义指没有加工的原木,《说文解字》:樸,木素也。而“仆”原文为僕,是为人办事的意思,《说文解字》:僕,给事也……,古文从臣。《郭店老子甲本》谈论的是治道,而治道是针对执政者而言的,“道亘无名仆唯妻”,也就是在说执政者是仆,即执政者是公共服务者,而不是主宰者、专制者。古代男权社会,妻子在家庭里作为服务角色,所以老子用妻来形容道之仆,“道亘无名仆唯妻”。“仆”在《说文解字》里是给事的意思,而妻在《说文解字》里有持事的意思,《说文解字》:妻,妇,与夫齐者也。……又,持事,妻职也。给事和持事,有相通性,仆和妻就有了可类比性。有的学者把“道亘无名仆唯妻”的“妻”释为“微”,也是因为忽视了仆的信息所致。老子说道是仆的,也就是在言说执政者是公共服务者,事于公,是处下的,执政者和民就犹如江海与百川的关系,“江海所以为百谷王,以其能为百谷下,是以能为百谷王”。
“道亘无名仆唯妻”中的仆,是从人,原文是僕。而“视索保仆”和“将镇之以无名之仆”中的仆是从臣,原文是,学界仍然把“仆”通为“朴”,是忽视了“僕”是“仆”的古文,《说文解字》:僕,给事也……,古文从臣。那么古文为何是呢?从臣呢?《礼记·礼运》:仕(事)于公曰臣。而老子里的仆,给事给的是公事,是公共服务,不是为人谋私利。
(四)圣人无事:民自富
圣人无事,即圣人不扰民,而民自富。相关原文为《郭店老子甲本》十八、十九、二十章。
十八章:其安也,易持也;其未兆也,易谋也。其脆也,易判也;其几也,易散也。为之于其无有也,治之于其未乱。合(抱之木,作于毫)末;九成之台,作(于垒土;百仞之高,始于)足下。
十九章:知之者弗言,言之者弗知。闭其兑,塞其门;和其光,同其尘;挫其锐,解其纷。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亦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
二十章:以正治邦,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也?夫天多忌讳而民弥叛,民多利器而邦滋昏,人多智而奇物滋起,法物滋彰盗贼多有。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欲不欲而民自朴。
十八章中的“为之于其无有也,治之于其未乱”,十九章中的“玄同”,是无事的具体表现;二十章中的“以无事取天下”明确提到了无事。
圣人无事,是为了防止执政者扰民,实现安民的状态。十八章的“为之于其无有也,治之于其未乱”,主要突出在无的时候为,在无的时候为就会显得无事,在有的时候为,就是扰民、瞎折腾。十九章的“玄同”,突出公正原则,不分亲疏是超越情感,不分利害是超越私利,不分贵贱是超越社会名位(世俗价值观)。二十章的“以无事取天下”,突出取天下的路径不是武力,而是无事。当时的历史处境是春秋末期,诸侯争霸,天下大乱。老子是写给诸侯王的,提出取天下(得天下)的方案,不是武力统一天下,而是“以无事取天下”。各大诸侯都试图以武力称霸天下,而这又是不得人心的。老子认为,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以无事的方式停止战争,更能得天下人之心。这与后来秦始皇的方案是截然相反的,历史已证明,秦始皇的武力取天下并不得人心,不可长久。
二十章的末句“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欲不欲而民自朴。”是对整个外王篇内容的概括。要实现民自富、民自化、民自正、民自朴的自由自治社会,需要圣人无事、无为、好静、不欲。圣人无事而民自富,圣人无为而民自化,圣人好静而民自正,圣人欲不欲而民自朴,阐发的是圣民关系,具体体现为圣民合一的理念,也就是反对执政者与民的对立。
四、《郭店老子甲本》与五千言《道德经》的关系
关于《郭店老子甲本》与五千言《道德经》的差异,之前学界做了一些相关研究,主要讲了两个方面,一是《郭店老子甲本》不像五千言《道德经》一样,有玄虚的表述;二是《郭店老子甲本》不像五千言《道德经》一样,反对仁义,通行本的“绝仁弃义”,在《郭店老子甲本》里是“绝伪弃虑”。《郭店老子甲本》与五千言《道德经》的差异研究还不够,应进行深入全面的比较。
笔者认为,从整体上看,《郭店老子甲本》比五千言《道德经》更富有理性。除了上边提到的两个方面,还有多个方面可以证明这一点。一是,《郭店老子甲本》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而五千言《道德经》是语录体。二是,《郭店老子甲本》不讲鬼神,而五千言《道德经》给鬼神留下了位置:“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虽然认为道高于鬼神,但还是承认了鬼神的存在。三是,《郭店老子甲本》不讲愚民,而五千言《道德经》明确讲到“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还讲到“常使民无知无欲”、尤其是“小国寡民”的思想:“使人复结绳而用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有复古色彩,是不利于社会进步的。四是,《郭店老子甲本》讲不欲,不彰显欲望,“我欲不欲而民自朴”,而五千言《道德经》讲无欲,“我无欲而民自朴”,陷入了禁欲主义,是一种宗教色彩。五是,《郭店老子甲本》不讲报怨以德,而五千言《道德经》讲到“报怨以德”、“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这是一种宗教色彩,主张邪恶势力,不利于形成正义社会。六是,《郭店老子甲本》是“天下之物生于有、生于无”,把“有”和“无”放在并列的地位,与“有无相生”的思想相验证,而五千言《道德经》是“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把无的地位优先于有的地位,导致与“有无相生”相矛盾。七是,《郭店老子甲本》有执政者作为“仆”的表述,“道亘无名仆”,这里突出了民是主的思想,也突出了执政者的职责是为民办事(公共服务者),《说文解字》:仆,给事也,而五千言《道德经》是“朴”,缺乏“仆”的明确的民主信息。八是,《郭店老子甲本》是以道为本原,以治道为归宿点,不用大量篇幅论述德,只有一处提到德(“含德之厚者,比于赤子”),全书仅从内圣外王之道的治道视角展开,而五千言《道德经》既论本原之道,也论治道,还论德,主题比较混乱。(《郭店老子甲本》是老子道经,而五千言《道德经》是老子道·德经。)
《郭店老子甲本》与五千言《道德经》有如此大的差异,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有的内容可能是老子后学逐步增改所致,比如从道经到道·德经的主题转化,增加了论德主题的不少内容;有的内容可能是宗教思想混入,比如鬼神的思想、无欲的思想、报怨以德的思想,以及那些玄虚的内容;有的内容是别的经典的混入,如五千言《道德经》中的:“谷神不死”一章,《列子·天瑞篇》引用此章内容时,说是出自《黄帝书》;还有的内容,可能是在汉代重建经典时,无意或有意的“改造”所致。在春秋末期至汉代期间,历经战乱、焚书、传抄等各种原因,造成先秦典籍遗失和缺漏,汉代进行了经典重建,这也是历史事实。汉代重建经典,一方面由于原始经典不详,一方面是当时意识形态的取舍需要,都必然造成汉代建立的经典与原始经典的不符。五千言《道德经》把《郭店老子甲本》中的“仆”改为“朴”,并增加“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常使民无知无欲”等内容,这些内容都有可能是统治者意识形态的植入。熊铁基也提到了郭店《老子》被汉人“改造”的问题,“新出土的文献,例如马王堆帛书中的《老子》、郭店竹简《老子》,应该研究,但它们与流传两千年的《老子》并不是一回事。先秦《老子》流传中有不同,汉人进行了较大的改造,这些问题也应该研究;人们为什么要‘改造’它?它的原来思想又有什么意义?等等。”[17]
《郭店老子甲本》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同时又富有理性色彩,应该是《老子》原著(老子元经)。高华平“通过考察郭店楚简《老子》的内容和文体特征,认为郭店《老子》文本显示《老子》一书原是经、传的混合体;郭店《老子》甲组属‘经文’,乙、丙二组属‘解说文’。”[11]既然《郭店老子甲本》是经,那就应该是老子本人所著。高华平是从竹简形制、内容风格等文献学的角度论证《郭店老子甲本》是经,笔者是从文本结构等义理的角度论述《郭店老子甲本》是经。由于《郭店老子甲本》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本文认为《郭店老子甲本》应为《老子》原著(老子元经)。谭宝刚在其博士学位论文《老子及其遗著研究》[18]的摘要里也认为,《郭店老子甲本》是老子原著,给出的理由是,唐代陆德明认为老子“为(尹)喜著书十九篇(章)”。(《郭店老子甲本》可以分为19章或20章,笔者本文采取20章分法,分为19章是“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一章和“罪莫厚乎甚欲”一章在竹简原文中是合并的。)当然,谭宝刚同样忽视了《郭店老子甲本》还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而有的学者认为郭店《老子》为摘抄本,但《郭店老子甲本》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章与章之间的先后顺序是按照思想脉络顺序展开的,行文一气呵成。如果是摘抄本,恐怕没有这么巧合,同时也没有证据证明老子本人写了数千言的内容。汉代五千言《道德经》应是逐步形成的,不全是老子原著。许抗生、熊铁基等学者,也认为五千言《道德经》的内容是逐步形成的。许抗生提到,“《老子》一书似乎经历了由简本向帛书本的转化过程”[19];熊铁基提到,“汉代曾经对先秦典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改造,其中,对《老子》一书的改造就很典型”[20]。有不少学者从五千言《道德经》的用词变迁上也进行了论证,比如五千言《道德经》有的用词是老子所在时代之后的特点。《郭店老子乙本》和《郭店老子丙本》的内容不同于《郭店老子甲本》,且在时序上又晚于《郭店老子甲本》,也说明内容在不断增加,五千言《道德经》是在老子原著基础上逐步增改完成的,而在汉代重建经典时得以定稿,形成传世本五千言《道德经》。(有的学者依据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老子思想的描述来确定老子的思想内容,忽视了司马迁所在的时代看到的内容是汉代传本的五千言《道德经》的内容,并非老子原著。)
《郭店老子甲本》如果是老子原著(老子元经),只有20章的内容,而五千言《道德经》有81章的内容。多出的61章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文本发展的文献线索呢?很巧合的是,《郭店老子乙本》8章,《郭店老子丙本》4章(不含与《郭店老子甲本》重复的“为之者败之”一章),《汉书·艺文志》记载的《老子邻氏经传》4篇(章),《老子傅氏经说》37篇(章),《老子徐氏经说》6篇(章),共计59章,与多出的61章数字相当,汉代五千言《道德经》分章是逐步形成的,有误差也在常理之中。(据《汉书·艺文志》,《老子邻氏经传》4篇,“邻氏传其学”;《老子傅氏经说》37篇,傅氏“述老子学”;《老子徐氏经说》6篇,徐氏“字少季,临淮人,传《老子》”。)
《郭店老子甲本》应为老子原著,五千言《道德经》应为老子学派的论文集。
五、结论
《郭店老子甲本》由五组竹简组成,对五组的组别顺序进行“还原”后,整本能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依照内圣外王的结构秩序展开,内圣即成为圣人,外王即圣人治国。《郭店老子甲本》共20章(1000余字),内圣篇是1至7章的内容,先后从人法天地、人法自然、人法道的途径进行论述(依照首章的末句的中心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展开);外王篇是8至20章的内容,先后从圣人欲不欲、圣人好静、圣人无为、圣人无事的途径进行论述(依照末章末句的中心句“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欲不欲而民自朴”而展开)。内圣篇里论述的人法天地、人法自然、人法道,阐发的是天人关系,具体体现为“天人合一”的理念,也就是反对天人对立。外王篇论述的圣人欲不欲(民自朴)、圣人好静(民自正)、圣人无为(民自化)、圣人无事(民自富),阐发的是圣民关系,具体体现为“圣民合一”的理念,也就是反对执政者与民的对立。也就是内圣篇论述的是天人问题,而外王篇论述的是天下问题。从内圣到外王,也就是从天人到天下,从修身到治国。从《郭店老子甲本》的结构秩序来看,老子是第一个明确把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一个完整体系来建构的,同时也可以看出,内圣外王之道确实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思维范式,老子、孔子等都有内圣外王之道的思想。
《郭店老子甲本》这一脉络结构,可以用四句口诀来概括:老子内圣与外王,人法天地自然道,圣人不欲与好静,圣人无为与无事。老子内圣与外王,是整体结构的两大层次。人法天地自然道,是内圣(成为圣人)的途径:人法天地、人法自然、人法道。圣人不欲与好静,圣人无为与无事,是外王(圣人治国)的途径:圣人欲不欲、圣人好静、圣人无为、圣人无事。
《郭店老子甲本》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是一个富有理性色彩的文本,我们可以把《郭店老子甲本》视为老子本人的原著,而可以把五千言《道德经》视为老子学派的论文集,老子学派的论文集是逐步完成而定稿的,是老子原著与老子后学的著作混合,并且在流传过程中把顺序给打乱了,从而遮蔽了老子本人有结构秩序的原初文本。也就是《郭店老子甲本》系一人所作,而五千言《道德经》是历经几百年时间由多人所作。我们看到的《庄子》《韩非子》等各种文本引用的老子言论,有的却在《郭店老子甲本》里看不到,那么这些言论引用的老子实际就是老子学派。五千言《道德经》和《管子》《墨子》《庄子》等类似,都是学派的论文集,《管子》是管子学派的论文集,《墨子》是墨子学派的论文集,《庄子》是庄子学派的论文集。
《郭店老子甲本》作为完整的思想体系,是一本完整的著作。这一事实,决定了我们可以重新审视一些传统共识。一般认为,老子的著作属于语录体,其章与章的顺序布局是跳跃的,而《郭店老子甲本》作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可以让我们重新对老子是语录体的说法进行审视。一般认为,先秦无体系性著作(1),而《郭店老子甲本》作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可以让我们重新对“先秦无体系性著作”这一说法进行审视。进而,可以得出,世界上第一本有体系性的哲学著作应该在中国,世界上有体系的著作没有比《郭店老子甲本》更早的。
《郭店老子甲本》比五千言《道德经》更富有理性色彩,但《郭店老子甲本》毕竟是时代的产物,也具有时代局限。“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我们可以从《郭店老子甲本》开拓出现时代所需要的新哲学。《郭店老子甲本》把内圣篇作为上篇,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展开,论述了人法天地、人法自然、人法道,突出了自然法的思想(广义的自然包括道、天地和人之自然),我们可以开拓出以法为根本精神的新道家——法道家,并结合黄老帛书“道生法”的命题,结合庄子“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反人治思想,再结合西方现代法治思想,进行整体的现代化转换,可以构建整全的新道家——法道家。严复从五千言《道德经》开拓出了民主思想,胡适从五千言《道德经》开拓出了自由思想。我们可以进一步突出《郭店老子甲本》中的执政者作为“仆”的独特思想,进一步开拓民为主的民主思想。《郭店老子甲本》把外王篇作为下篇,以“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欲不欲而民自朴”的思想展开,论述了执政者无事而民自富,执政者无为而民自化,执政者好静而民自正,执政者欲不欲而民自朴,突出了民自富、民自化、民自正、民自朴,都可以进一步开拓出民主思想。(在价值导向上,进一步开拓无为作为不强制之义的自由意蕴,与西方现代自由思想结合。)
注释:
(1)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页。
参考文献:
[1] 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8-9.
[2] 谭宝刚.老子及其遗著研究[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9:179-181.
[3]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4] 韩禄伯.简帛老子研究[M].邢文,改编.余谨,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6.
[5]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M].增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6] 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7] 崔仁义.荆门郭店楚简老子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8]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9] 许抗生.当代新道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51.
[10] 梁涛.北宋新学、蜀学派融合儒道的“内圣外王”概念[J].文史哲,2017(2):20-30.
[11] 高华平.对郭店楚简《老子》的再认识[J].江汉论坛,2006(4):93-96.
[12] 邓球柏.内圣外王之道:《郭简·老子》的主题[J].哲学研究,2004(1):25-30.
[13] 兰喜并.老子解读[M].北京:中华书局,2005:95.
[14] 王利器.文子疏义(新编诸子集成)[M].北京:中华书局,2000:60.
[15]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6] 哈耶克.自由宪章[M].杨玉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7] 熊铁基.抱道持身,履贱三宝——如何解读《老子》六十七章及其他[J].哲学研究,2017(12):53-58.
[18] 谭宝刚.老子及其遗著研究[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9.
[19] 许抗生.初读郭店竹简《老子》[M]//中国哲学:第20辑——《郭店楚简研究》.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93-102.
[20] 熊铁基.从《老子》到《道德经》[N].北京:光明日报,2007-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