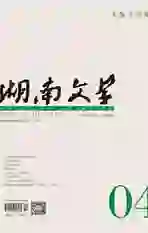红柳荡
2018-05-31王剑宁
王剑宁
骏马,要看一双眼睛;勇士,要看走过的脚印!都为自己打算的人群里, 啥时候都不会出现英雄!
——哈萨克谚语
一
豹子啊!你快来看看吧,家里出事了!
太阳刚刚挂在远处的乌孙山梁子上,奶茶还在铁皮炉子上熬着呢,艾尼瓦尔就匆匆穿上警服,骑着他那匹腿脚不灵的跛马,向红柳村赶去。
电话是舅舅打来的。舅舅在电话中心疼地说,昨晚还在圈里吃草的马,一早就不见了,日怪得很呢,那匹马的肚子里,可怀着小马驹呢,下崽的事情,就在这几天呢!
艾尼瓦尔听了,心里当时就咯噔了一下,附近的几个冬窝子连续发生了几起牲畜盗窃案,线索还在天上飘着呢,案子就又发生了,而且被偷的竟然是舅舅的马。艾尼瓦尔放下电话的时候,肚子里就骂开了,这他妈的贼娃子,日能到老子头上来了。
艾尼瓦尔身材伟岸得很,就像乔尔玛雪峰上的石头,结实得不得了——骑在黑马上,鞭子轻轻一挥,猎人的本色就摆在那里了。虽然还是初冬,但寒冷却像刚磨快的和田刀子,扎得人生疼,艾尼瓦尔早晨费了很大劲才刮去的胡茬子,借着初冬的风,一碗茶的功夫就又长出来了。寒风戳在脸上,胡茬子上就落满了霜,白晃晃的,很是显眼,这么看上去,艾尼瓦尔四十岁的额头上就刻满了沧桑。
艾尼瓦尔摸了摸腮帮子,心中的烦恼就飘了过来,心想牧区长大的人啊,命贱得很,就连这胡子都像那拉提的草,见风就长呢。艾尼瓦尔这么想着,禁不住打了个寒战,裤裆里就有了尿意。他索性翻身下马,痛痛快快撒了泡尿,这才重新坐在马背上向远处的红柳村走去。
大概一个时辰的光景,艾尼瓦尔来到了红柳村附近的土坡子上。这时,座下的那匹跛马突然变得不安起来,打着响鼻,步子也慢了下来。艾尼瓦尔愣了下神,脑子这才转过弯来,这畜生有灵性呢,十几年前的旧事还在肠子里放着呢!
十几年前,红柳村还荒着,只住着很少的几个猎户,由南到北几十公里范围内,都长满了红柳,浩浩荡荡的,就像是一条红色的河流。据说那时候很少有人敢只身穿越红柳荡,因为先辈们早就说过了,那里有狼。那里的狼被先辈们称作“红狼”,先辈们说,这红狼外形不同于一般的草原狼,一身红毛,像燃烧的火,极其古怪。草原狼虽然彪悍,但红狼却比草原狼更凶残,而且脑子贼灵,像人。先辈们还说,乌孙国的时候,那片浩大的红柳荡就是红狼的家,它们世居于此,很少离开,谁侵犯了它们的领地,离死就不远了。
老人们还说,曾经有一个外乡来的猎人,听了这个说法,死活不相信,笑着对牧民们说,你们嘛,沟子夹得紧紧的,这世上有黑狼灰狼,哪有红狼嘛?亏你们还是猎人的后代呢,胆子比狍鹿子还小呢!咱们猎人是干啥的?不就是狼的爷爷吗?
这猎人硬是不听牧民们的劝说,骑着马,背着猎枪,孤身进了红柳荡,进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后来就有人传说,那个猎人遇到红狼了,这红狼不喜欢吃人肉,但特别喜欢人的“下水”,就撕开猎人的肚子,将里面的物件吃了个精光——之所以有这么一说,是因为次年夏天有人在红柳荡边上看到了一具干尸,尸体被掏空了,只留下了一具皮囊,風干后挂在红柳枝上,随风飘着,显得极其诡异。村子里的老阿訇说,那猎人也是活该呢,红柳荡可是人间圣地,那猎人不知死活,亵渎了神灵,胡达(真主)因此派红狼找他算账了。这么一来,有关红狼的传说就更匪夷所思了。红柳荡也因此变得阴森古怪,令人望而却步。
艾尼瓦尔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红柳荡的传说了。那时候父亲还在世,经常吓唬他:巴郎子(小伙子),要听话呢,不然的话,就把你扔进红柳荡,喂红狼呢。
父亲是牧区远近有名的猎人,五岁的时候,艾尼瓦尔就开始随父亲进山打猎,猎人的所有本事都在他的血液里流着呢。在艾尼瓦尔眼里,父亲的能耐大得很。有年冬天,父亲带着艾尼瓦尔在村头玩耍,突然看到雪地上一串爪印,就对艾尼瓦尔说,有肉吃了。父亲观察了下地形,在一处凹地上下了套子,随后笑着对艾尼瓦尔说,走,回去把烤肉钳子拾掇一下,明天咱们烤狍子肉吃。艾尼瓦尔死活不相信,问道,你是在吹牛呢,就算这个地方有狍鹿子,你咋能断定它一定就会从那里经过呢?父亲微微笑着,说道,我是猎人嘛,猎人的眼睛,可以看到天堂呢。
艾尼瓦尔知道父亲是在说笑,可第二天早上当他和父亲来到那片雪地上时,真的看到一只狍鹿子被套住了!
回到家后,吃着烤肉,艾尼瓦尔就问父亲,你是咋知道狍鹿子会经过那里的?记得父亲当时吃着肉,喝着酒,并没有过多的解释,只说了一句话,你记住,我是个猎人,你是猎人的后代,咱们猎人,眼睛是不能被风雪迷住的!
艾尼瓦尔十岁的时候,父亲进山打猎时意外掉下悬崖,去见真主了。然而,父亲有生之年却从没有进过红柳荡,即使猎物受了伤,但只要逃进红柳荡,父亲就站在远处看着,停止了追捕。对此,艾尼瓦尔很难理解,追问原因时,父亲只是意味深长地说道,那里是个传说,我们就永远把它留在那里吧!
直到后来第一次走进红柳荡,艾尼瓦尔才理解了父亲那句话中的含义!
艾尼瓦尔第一次进红柳荡,是在追捕一个逃犯的时候。
那时侯,艾尼瓦尔二十岁,警校刚毕业,高个,阔肩,腰身颀长硬实,像是头豹子。猎人的后代里,艾尼瓦尔是第一个“公家人”,又是警察,牧民们就把他称作了“豹子”。艾尼瓦尔的性子也像豹子,行动迅捷、奔跑如飞,特别喜欢独自捕捉猎物。毕业分配到牧区派出所后不久,一个外地来的杀人嫌犯逃进了牧区,民警们前去追捕,没想到那家伙滑溜得很,躲进乌孙山死活不出来。当时正是晚秋,到处都飘着瓜果的香味,乌孙山脉里野物又多,人钻进去,不愁活不下来。艾尼瓦尔就对所长说,不急嘛,等第一场雪下来,我就把那个卖沟子的给你撵出来。
艾尼瓦尔清楚得很,山里只要下了雪,气温就会往死里降,乌孙山又是天山的余脉,一年四季气温本就低得让人心慌,只要一下雪,就是头真正的西北狼也耐不住那里的寒冷;何况有了雪,再狡猾的猎物都会留下印记,怎么可能逃过猎人的眼睛?那几天,艾尼瓦尔不急不躁,拿着酒壶,吃着冬肉,在山脚下的冬窝子里悠闲地转着,看上去就像一个闲得无聊的牧民。
十几天后,冬天第一场暴风雪下来,艾尼瓦尔这才揣上几块干馕,背着酒壶,准备独自进山。
所长不愿意,说,那家伙可是匹狼呢,一个人进去危险得很。艾尼瓦尔笑了,说,山里的事,你知道的少呢!人多了,目标大得很;山里和平原那是两码子事,人多了啥用没有,坏事却出来了呢!有经验的猎人,一个,足够了!
艾尼瓦尔没有吹牛,进山不久,嫌犯的踪迹很快就在他的眼眶子里了。艾尼瓦尔盯住不放,逼着那家伙无路可走,只好从山里窜了出来。
本来,盘羊只要出了山,屁股就在猎人的枪口下了,可那家伙出来后,艾尼瓦尔却突然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那家伙情急之下逃进了红柳荡。
那天,站在红柳荡边上,有关红狼的传说就在艾尼瓦尔的脑壳子里回响着。此时,广阔无边的红柳荡在寒冬里静默着,缥缈神秘,就像远古留下的一个狂野的梦,远离现实却又无法回避。云脚压得很低,天和地似乎站在了一起,这时的红柳荡漂浮在天地间,就像是一座悬挂在半空的城堡,里面住着的是神仙还是魔鬼,或许只有圣明的真主才知道。雪正下得猛,西北风“呜呜”地吼着,像狼叫。艾尼瓦尔觉得那一定是红狼,正藏在红柳荡深处等着他进去呢。
听说艾尼瓦尔要进红柳荡,村里的老人们匆匆赶来,说,豹子啊,进不成嘛,进去了,命可就没了!
进,还是不进?那一刻艾尼瓦尔现出了少有的犹豫,寒风刺骨,艾尼瓦尔的鼻梁骨上却挂满了汗。远古的传说就在那里,如果进去,自己很可能就像先前那个猎人一样,被掏了肚肠,只留下皮囊,挂在红柳枝上。可是,不进,嫌犯跑了,警察的脸就被扔进了特克斯河,这人丢不起!艾尼瓦尔最后决定进去,就算被老天爷收去也要死得像个猎人。
艾尼瓦尔最终骑着黑马进了红柳荡。
三天后,艾尼瓦尔出来了,带着逃犯的尸体。尸体冻得僵硬,面目狰狞。出来的时候艾尼瓦尔满脸都是冻疮,那匹马因为陷进沼泽里差点送了命,前面的一条腿被折断了,成了匹跛马。后来有人问艾尼瓦尔,这红柳荡里是个啥样子?艾尼瓦尔笑着什么也没说。又有人问,遇到红狼了吗?艾尼瓦尔仍然笑着,眼里的光无法捉摸。
有的时候当你什么也不说时,神话就出来了。
牧区的老阿訇说,逃犯死了,一定是被红狼吓死的,艾尼瓦尔肯定也遇见红狼了,可他有灵性呢,真主在旁边护佑着呢,红狼是真主的使者,当然不会动手。
神话就这样流传开来,艾尼瓦尔成了神话中受人尊敬的勇士……
就在艾尼瓦尔回想第一次进红柳荡的情景时,老马又发出了一声嘶鸣,将艾尼瓦尔从遥远的记忆中拉了回来。艾尼瓦尔亲切地拍了拍马头道:阿达西(朋友),现在红柳荡都没有了,你还怕个啥嘛?
如今,红柳村已经不算是红柳村了,因为那些红柳眼看就要没了。
艾尼瓦尔站在土坡上,放眼向远处看去。虽然已经入冬,远处的红柳荡里依然在施工,据说是要建一座现代化的煤化工厂。巨大的轰鸣声传来,红柳一片片倒下,红色的火焰渐渐熄灭,巨大的灰尘漫过了天际。看着那些灰烟,艾尼瓦尔的胸口有些堵得慌,内心突然感到一丝担忧,如此下去,喀拉峻的草会不会也即將消失?那些经年传唱的牧歌会否成为最后的绝唱?艾尼瓦尔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只几年的光景,红柳成片地被砍伐,成了打馕的木柴;放眼看去到处都是民居,只在村庄的边缘残留着部分红柳,没有了先前的气势,风刮过来,“呜呜”响。老人们说,那是红柳在哭泣呢!
艾尼瓦尔眯着眼忧伤地看着红柳村。
如今那些古老的传说还在西天山回荡,可现实已经把传说埋在了人的欲望深处。艾尼瓦尔悲伤地想,是不是传说一旦没了,人就失去了信仰,也就没有了畏惧?没有了畏惧,人的世界到底还能走多远呢?艾尼瓦尔突然想起了父亲的那句话,那些传说就让它留在那里吧!他仿佛明白了,也许有传说的地方才会有历史,才会有经年传唱的牧歌,也才会有让人发自内心的敬畏!
这么想着,父亲的影子就在艾尼瓦尔的眼前晃着,艾尼瓦尔的眼中有了泪。
艾尼瓦尔擦了擦眼睛,挥了挥马鞭,深吸了口气,努力把思绪拉回到现实中,悲伤还在头顶悬着,怒火就又燃烧了起来。过去牧区哪有什么贼嘛,人们单纯得就像特克斯河的水。可现在贼出来了,世道被人的贪念给弄坏了。艾尼瓦尔肚子里就又骂开了,他妈的,贼娃子们也太狂妄了,竟然偷了舅舅的马,真是丢死人了。想想看,自己是个警察,舅舅的马被偷了,不丢人才怪呢!艾尼瓦尔恨恨地想,不知是哪个卖沟子的干的?抓住了,皮子非扒了不可!
一边骂着,艾尼瓦尔一边催马下坡,趟过一条小河,走进了红柳村。此时下了雪,所有的故事都被掩埋在了苍茫的天地间。
二
远远的,艾尼瓦尔就看到舅舅正在家门口等着呢。
看到艾尼瓦尔,舅舅心急火燎地迎了上去,说,豹子啊你可来了,那匹马可是舅舅唯一的家产啊!舅舅拉着艾尼瓦尔的手,又说道,造孽啊,那马的肚子里小马驹可就要出来了。艾尼瓦尔拍了拍舅舅的手,安慰道,您老不急,贼娃子再日能,咋能跑出咱猎人的手?只要我艾尼瓦尔在,你就等着为小马驹接生吧!
艾尼瓦尔拉着舅舅的手,走进了他来过无数次的小院。
艾尼瓦尔和舅舅亲得很。舅舅家的院子里有一个很大的葡萄架子,用坚硬的红柳撑起,占去了半个院落,每年葡萄熟的时候,艾尼瓦尔都会和父母到舅舅家做客。舅舅家房屋是土木结构,显得很古朴,哈萨克风格浓得很。每次到舅舅家做客,舅舅的儿子马力克就在葡萄架下摆上一张圆桌、几把小椅,父亲母亲和舅舅舅妈就坐在葡萄架下,摇着扇子,喝着茶,悠闲地聊着天。每当这时,马力克就会弹起心爱的冬不拉——马力克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冬不拉,弹得也出奇的好。恍惚间,艾尼瓦尔就会有一种隔世的感觉,仿佛在听乌孙人歌唱,与乌孙人同舞,所有的奇思妙想都在枝蔓撑起的阴凉下滋长!一种久远的、自然而古朴的情感就会流淌心间。冬不拉只要响起,母亲和舅妈的屁股就坐不住了,情不自禁地就跳起了舞,很是热闹。每次从舅舅家出来,艾尼瓦尔就有了诗歌的感觉,艾尼瓦尔不是什么诗人,但他总觉得草原牧区人家天生就是与诗歌有缘的,不需要刻意地构思和铺垫,只要敞开小院的门,憨笑着往葡萄架下那么一站,就自成风景,天然成诗了。
可今天艾尼瓦尔却没有一点诗歌的感觉了,舅舅的牛被偷了,如果找不回来,自己的脸朝哪个地方搁嘛!
艾尼瓦尔埋着头,来到舅舅家的后院。马厩就在后院的角落里,不大,但很严实。现场十分简单,柱子上残留的马缰绳耷拉着,有明显的刀割痕迹。艾尼瓦尔拿起绳子,眯着眼仔细瞅了瞅,切口十分齐整,显然那把刀子极其锋利,只一下,缰绳就齐刷刷断了,很有可能是声名显赫的和田刀子。从马厩出来,艾尼瓦尔站在院子当中仔细观察着,雪还在下,地上除了自己和舅舅的脚印,啥都没有。
艾尼瓦尔皱皱眉头,暗暗骂道,这他妈的雪,下得真他妈的不是时候呢。
院墙虽是土坯子打的,却很高,艾尼瓦尔站在墙角踮起脚尖试了试,足有两米,一般人很难翻过来。艾尼瓦尔又前后仔细查看了墙面,没有爬越的痕迹。墙是土打的,又经过了雪的浸泡,如果翻墙过来,是不可能不留下痕迹的。艾尼瓦尔忍不住嘟囔道,卖沟子的,肩胛子上有翅膀呢,会飞呢!
在院子兜了幾圈,没发现什么特殊痕迹,艾尼瓦尔只得判断,贼娃子大概是从大门进来的。可到底是怎么进来的呢?真是匪夷所思。
大门是两扇,松木做的,高大得很。艾尼瓦尔把门关上,里外看了看,关得很严实,门缝很小,只有蚂蚁才能爬得过去。门内侧有个插销,钢筋做的,顶端有个弯钩,只要合上,就与里面的套圈钩在一起了,不熟悉情况的人,很难从门缝捅开。观察了许久,艾尼瓦尔这才折过身来,问舅舅,马,确定是昨晚丢的?舅舅说,谁说不是呢,怀着孕呢,每天晚上我都陪着它到天黑呢。艾尼瓦尔又问,门是从里面插着的?舅舅答道,就是嘛,喂完马,我亲自把门插上的,早上,门却是开着的,一定是贼娃子干的。艾尼瓦尔听舅舅这么说,就又站在门边,仔细端详着门插销,心想,看来是个高手呢,一般的贼,这样严实的门,从外面咋样也是捅不开的。
看样子,必须得从外围寻找线索了,艾尼瓦尔暗暗想着,眉头就皱成了山。
看到艾尼瓦尔为难的样子,舅舅的脸就掉下来了,问道,怎么样?豹子,那马,还能找回来吗?艾尼瓦尔笑了笑,努力把眉头松开,说,当然能找回来,不然,警察们还活着干啥?舅舅又凑近艾尼瓦尔,神秘地说道,听说了吗?老人们可说了,最近冬窝子丢了那么多的牲畜,据说都是红狼干的!
啥?红狼干的?艾尼瓦尔莫名其妙地问道。
舅舅说,是啊!老人们说了,现在,人把红狼的家毁了,红狼就化作“红魔”,报复来了!这红魔啊,听说神通大得很,会飞呢,做起事来,一点痕迹都不留呢。
艾尼瓦尔听了这话,心中暗想,如果真的有红魔,那倒是好了,人们有了畏惧,说不定红柳荡,就不会消失了呢,唉!
艾尼瓦尔深深地叹了口气,勉强笑了笑,又安慰道,你老人家担心个啥嘛,咱们都是好人嘛,就是有“红魔”,也不会拿咱们下手嘛,咱牧区不是有句老话吗?再狡猾的猎物,也斗不过有经验的猎人嘛,你老人家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马达(问题)没有嘛,过几天,我艾尼瓦尔一定把马给您送回来。
话虽然这么说,艾尼瓦尔心里却没有底,这个案子,做得干净,看来不简单得很呢,什么人干的?难道真的是“红魔”,艾尼瓦尔自嘲地笑了笑。
临出门时,舅舅突然想起了什么,喊道,巴郎子,你等等!随后,转身跑进了屋内,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把崭新的冬不拉,说道,这是马力克亲手做的,让我送给你。
艾尼瓦尔接过冬不拉,心头一热,就问道,马力克回来了?他还好吗?舅舅忧郁地点点头,说道,前天回来的,昨天走了,看样子,精神不好呢,这孩子,命苦着呢。说着话,舅舅的眼圈就红了。看着舅舅难受的样子,艾尼瓦尔揉了揉眼睛,故意玩笑着说道,这家伙,回来了,也不去看看我,下回见了,骂死他!
从舅舅家出来,雪仍然下着,原野上白茫茫的一片。
三
回到派出所,已是中午,雪却下得更大了。大西北的雪,总是这个样子,下起来,就执着得很。
艾尼瓦尔没心思吃饭,就坐在办公室里,卷了一根粗大的莫合烟,狠狠地抽着,他将脸埋在浓重的烟雾里,努力推测着案发现场的各种可能。随后,又把零乱的头绪集中在一起,肠子肚子都放了进去,各种可能,就都放在那里了,脑子里这才亮堂了许多。最近牧区发生的几起盗窃案,手法干净得很,会不会是同一伙人干的?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并案侦查了呢?这么问着,艾尼瓦尔猎人的自信,就又回到了宽阔的额头上。他相信,狐狸的尾巴藏得再深,终究是要露出来的。破案嘛,迟早的事。
这么想着,艾尼瓦尔心头的云,就慢慢飘走了,心情稍有好转,艾尼瓦尔这才想起了放在床边的那把冬不拉。
那把冬不拉做工精巧得很。冬不拉嘛,艾尼瓦尔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哈萨克的后代,谁不知道?冬不拉是哈萨克民间最流行的传统乐器,一般情况下,冬不拉大多是松木或者桦木凿成的。这把冬不拉,却是用名贵的天山云杉做的,这种木料,只有天山雪岭里才有。琴把上的三根弦,是品质优良的羊肠,韧性特别的强。椭圆形的音箱上,刻着哈萨克人喜欢的天鹅图案。
琴头上,拴着一个十分小巧的木饰,引起了艾尼瓦尔的兴趣。
艾尼瓦尔凑近看了看,木饰的样子竟然像一匹狼。如果哈萨克人也有图腾的话,狼应该就是哈萨克人的图腾了。不过,与蒙古人不同的是,哈萨克人是承接了古突厥人有关狼母亲的神话,以此来确立了自己的狼图腾,其他的动物,恐怕都算不上哈萨克人的图腾呢。再一看,木饰竟然是红柳做成的。马力克对红柳喜欢得很,这,艾尼瓦尔从小就是知道的。红柳坚硬,能用红柳做成狼的样子,真是非同一般呢。马力克喜欢冬不拉,手也巧的很,小的时候就追随有名望的哈萨克琴师学做琴,手艺精湛得很。可以看得出来,马力克做这把琴,是费了很多心血的,所有的情意,都在琴的骨架里呢。
看着那把精雕细琢的冬不拉,马力克红柳一样倔强的身影,就在艾尼瓦尔眼前晃着。一些往事,就飘了过来。
马力克的命,天生就与红柳连着呢。舅舅说过,舅母怀上马力克的时候,有一次在红柳荡边放羊,也许是劳累动了胎气,羊还没吃饱,孩子却早产了。舅舅说,小时候的马力克,就和红柳一个样子,粗粝、坚韧,脾气硬得很,撇也撇不断。想要干的事,就是八匹伊犁马也拉不回来。有一次,家里的一只羊被野狼吃了。这狼也乖张得很,吃也就吃了,还把个羊头撂在毡房前,向人示威呢。马力克见了,骂道,他奶奶的,狼这是要造反呢,骚情到猎人头上来了。骂完,喝了几口酒,只拿了个套狼索,放了个响屁,就一头钻进冰天雪地的黑嘴子沟,趴在雪窝里,和狼比起了耐心。那几天,雪大,没过膝盖骨。艾尼瓦尔在雪窝里一连守了十几天,球把子都快冻僵了,却硬是将那只狼给逮住了!
艾尼瓦尔和马力克从小就亲得很,像乌孙山上两块长在一起的青石。
那时,他们经常坐在村头的一排新疆杨下,看着远处的红柳荡,想象着远古的乌孙王朝。那时的红柳荡,旺得很,红柳漫山遍野,自由自在地长着,像火,映红了半个天空。鹰,在红柳荡上空盘旋着,翅膀上的故事,永远是那么高远。许多传说,在遥远的想象中,美好地活着。牧歌悠扬,花草流芳,红柳荡,在那些传说中,幽雅地站着,那样安静,处女般,干净纯洁。
看着那片浩大的红柳荡,他们的想象总是会走得很远。
马力克时常会对艾尼瓦尔说,你看嘛,只有在咱们天山的脚下,才会长出这样茂密的红柳,别处,咋会有嘛?艾尼瓦尔总是笑着,说道,是啊,牧民嘛,和红柳的骨头连着呢。每次聊起红狼,艾尼瓦尔就会问马力克,你说,这红狼,到底是有嘛没有?如果真的有红狼,咱们該怎么办嘛?马力克就笑着回答道,如果有,我嘛,绝不会害怕,我会和红狼成为朋友的,那种骨头和肉一样的朋友。艾尼瓦尔就又问,你说,人和狼,真的能做朋友吗?马力克就又笑着回答到,能呢,我相信能呢,只要心里没有怨恨,啥都可以成为朋友呢。艾尼瓦尔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就跟着憨笑了起来。
艾尼瓦尔觉得,如果真的有红狼的话,马力克说不准就是红狼的后代呢,他的魂和魄,就在那片红柳荡里呢。
马力克不止一次说过,如果我死了,你说啥也要把埋体(尸体)搁在红柳荡里,那个样子,我下辈子嘛,就会脱胎成红狼呢。马力克的这句话,戳在艾尼瓦尔心口子上,生疼。是啊!那片红柳荡,就是他和马力克生命里的归宿。自从第一次走进红柳荡,艾尼瓦尔就明白了,传说,是无形的,红狼也许就是个传说,是飘在红柳荡上空的传说,它在马力克和艾尼瓦尔的心中,就是个无形而永远的存在。
岁数一天天大了,马力克的心,也变得越来越宽广了,像看不到边的喀拉峻草原。
有一次,马力克对艾尼瓦尔说,长大了,我要出去呢,挣多多的钱,回来,让牧民们过上天堂一样的日子。马力克还说,你信嘛不信?我要把这片红柳荡买下来呢,就在那个地方放着,我们守着它,让它放开了长,长到天堂里去,永远是红狼一辈子的家。马力克说这话时,目光就像流动的伊犁河,亮亮的,让人十分的感动。艾尼瓦尔觉得,那应该是一种叫做信念的东西,是那种牧民才有的信念。艾尼瓦尔就抱住马力克,说,我相信呢,咱们的骨头在一起呢,死了,咱们就都埋在红柳荡里。
艾尼瓦尔脑子好使,转弯快,又特别喜欢学习。十八岁的时候,艾尼瓦尔考上了警校,进了城。
两年后的秋季,雨水猛得很,草疯了似的长。马力克早早开始备冬草,等到草剁成了山,马力克也决定下山。他在红柳荡边磕了个头,太阳般笑着,对父母说,我空着手出去,拿着钱回来,你们,等着吧,好日子在路上呢。说完,背着两块干馕,踩着雨水下山了。到了山脚下,马力克没有回头,他告诉自己,这一去,赚不到钱,绝不回头。那年,马力克二十岁,强壮得像一头犍牛。
城市很大,到处是楼,人在楼的缝隙中挣扎着,远没有草原那样辽阔。
马力克觉得,那些楼,就是钢筋水泥的森林。人,就好像是丛林中苦苦觅食的狼。在草原上,马力克不怕狼,在这里,他却有些迷茫。马力克先是在一家工地上扛水泥袋子。马力克长得硬实,又能下苦,一天干下来能顶几个人的活。原想,这个样子下去,很快就能挣上几个钱,自己的梦就在跟前了。然而,一年辛苦下来,骨头都扛烂了,马力克去领工钱时,昧了良心的包工头却想赖账,硬是不露面。
马力克的犟劲上来了,就装了一麻袋馕,坐在包工头家门口,不走。
包工头见了,骂道,狗日的,把这当驴圈了,想撒野,找死呢。包工头还说,在这里,收拾这样的毛驴子,简单得就像放个屁。包工头报了警。警察来了,马力克说,他们欠着我的钱呢。警察却说,钱不钱的,我们管不了,可你堵了人家的门,却是犯法的。马力克还没闹清是怎么回事,就被带到了看守所,拘了五天。出来后,工钱的事也泡了汤。听说这件事后,艾尼瓦尔心疼地对马力克说,回去吧!这里的土地硬得很,红柳,这里活不成呢。马力克却不依,笑着说,你等着看嘛,我就是要在这城市里扎根呢!我,马力克,儿子娃娃,裤裆里硬着呢。
留下来的马力克,伤还留在心里呢,希望却依然挂在脸颊子上,就又在城边的一个煤矿里做了“煤黑子”。
百米深的矿井,地狱般看不到光明,可那时的马力克心却仍然亮着。虽然过得辛苦,马力克却硬是立稳了脚跟。谁知天有不测风云,煤矿出现了塌方,十几个人被困在了矿井里。原本,马力克已经逃了出来,当听说有几个工友还在井里,就扭头又冲了进去。后来,工友得救了,马力克的右腿却被砸断了。闻讯赶来的艾尼瓦尔,在医院里看着失去了腿的马力克,禁不住痛哭失声。马力克却没哭,反而笑着说,啥事没有,哭啥嘛?骨头断了,筋在呢嘛。马力克还说,红柳虽然不值钱,可红柳有骨气呢,他长在咱们牧民的骨头里,硬实着呢。看着马力克,艾尼瓦尔相信,红柳即使不在了,根,一定还在乌孙山下的黑土地里埋着。只要下了雨,就会重新发出来呢。
这时,来看望马力克的工友们已经站了一屋。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乡里的,也有城里的。有哈萨克族,也有汉族,他们眼里噙着泪花,强忍着,没有一个掉下来。
那一刻,艾尼瓦尔突然发现,马力克已经不是一枝孤独的红柳了。在他的身后,红柳已经长成了一片林,红红的,像燃烧的火!出院后,马力克拄着拐杖,像一只受伤的野山羊,锐气依然藏在羊角里。失去右腿的马力克留在城里,在城边的一个小屋开了一个乐器店,专卖自己做的冬不拉!马力克告诉艾尼瓦尔,你等着,我一定会开一个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乐器店,我,马力克,说话算数呢!
想着马力克,艾尼瓦尔禁不住拿起冬不拉,拨弄着,唱起了他和马力克最喜欢的那首流行歌曲——《故乡》。
天边夕阳再次映上我的脸庞
再次映着我那不安的心
这是什么地方,依然是如此的荒凉
那无尽的旅程依然如此漫长
我是永远向着远方独行的浪子
你是茫茫人海中我的女人
在异乡的路上每个寒冷的夜晚
这思念它如刀让我伤痛
总是在梦中看到你无助的双眼
我的心又一次被唤醒
我站在这里想起和你曾经离别的情景
你站在人群中那么孤单
你是破碎的心
我的心却那么的狂野……
唱着唱着,艾尼瓦尔的眼泪就流出来了。风,正在远处深情地召唤着,神秘的天光落在雪山之巅,云朵正在踏歌而舞,轻灵的赞歌在空旷中游走。他觉得,自己的魂魄早已丢失在了梦和现实之间,就在那梦幻的高处,随着冬不拉疯狂而舞。他似乎看到了,天堂中的冬不拉正释放出历史的火焰,苍茫行走的岁月,就藏在冬不拉的传说中。他觉得,似梦似幻中,轉场的牛羊正走出天堂之门,岁月由绿转黄,南去的大雁在天堂之路上留下深情的一瞥,天堂之门关闭之际,牧羊人的鞭梢扬起一轮草原新月,托呼拉苏的梦就落入了冬窝子酣睡的馕坑里了。而此时的自己,正在梦的边缘,找寻着早已丢失的情缘!
那一刻,艾尼瓦尔回想起了小时候的故乡,看到了红柳荡边上,他和马力克年少时的身影……
四
案子的确不那么简单。
艾尼瓦尔经过外围侦查,发现近期发生在冬窝子的这些牲畜盗窃案,下手都出奇的麻利,线索很难找到。而且,很有可能是流窜作案,一个冬窝子只做一次。赃物出手也快得很,得手后,立刻就换个地方处理掉,屁都不多放一个。艾尼瓦尔往往刚发现点线索,紧着追,很快就断了!可以看得出来,贼娃子对牧区熟悉得很,很有可能是牧区走出去的猎手,下手又快又准,牧民们拉屎的功夫,牲畜就没了。那几天,艾尼瓦尔急得眼珠子血红,像阿拉山口的兔子,办法却象唐布拉山尖上的云,飘着飘着就不见了。本来,艾尼瓦尔的肠胃好得很,吃得多,拉得也快,可现在案子悬在半空中,拿不下来,他的胃口就跑没了,怎么也吃不下。就是吃了,屁眼子却不听话,屎怎么也拉不出来,憋在肚子里,折腾得艾尼瓦尔肠子都快断了。
就在这时,传统节日古尔邦节来了。
古尔邦节,是个吉祥的日子。很小的时候,每到古尔邦节来了,看到自己亲手养的牛羊被宰杀了,艾尼瓦尔就会哭得死去活来。那时,父亲还在呢,就笑着对他说,勺子(傻子),不哭呢,这是好事嘛,真主会感恩的。可为什么要宰牲呢?真主他老人家,为什么就不管管呢?那时,艾尼瓦尔怎么也想不明白。他觉得,好好活着的牲畜,就那么宰了,多么可惜呀?人怎么就这么残忍呢?
那天父亲抱着他,看着远处的红柳荡,给他讲了个故事。
父亲说,古兰经里有记载呢,先知伊布拉欣直到晚年也没个儿子,他就祈求真主安拉赐给他一个儿子。不久,伊布拉欣果然有了儿子,他对真主的恩赐感激得很。十几年后的一天夜里,伊布拉欣做了个梦,梦见真主安拉命令他把儿子宰掉,给自己献祭,以考验他的诚心。父亲伊布拉欣醒来后,觉得应该听真主的话,就决定宰儿子献祭。他懂事的儿子知道后,也毫无惧色,鼓励父亲说,动手吧,父亲,我不会怪你的。
听到这里,艾尼瓦尔由衷地说,这个儿子,真是孝顺得很呢。
父亲笑了笑,接着讲道,于是,伊布拉欣开始做起了准备,他把刀子磨得很亮,锋利得很。儿子躺下后,他就把刀架在儿子的喉头上。这时,他伤心地痛哭着,泪流成了河。第一刀下去,儿子的脖子上只留下了一个白色的印子。第二刀下去,只刮破了点皮。儿子看着父亲,说,我的父亲啊,你把我翻个身吧,让我趴着,看不到我的眼睛,你就可以狠下心来了。伊布拉欣听了儿子的话,就把他翻了个身,举起了刀。
听到这里,艾尼瓦尔就惊恐地问道,那个儿子真的被他父亲宰了?
父亲拍了拍艾尼瓦尔的头,不慌不忙地说道,这时,真主开口了,让他刀下留人,并派天仙背来一只黑头羯羊,作为献祭替代了儿子。伊布拉欣高兴坏了,拿起刀子,按住羊的喉头,只一下,羊便倒了。父亲最后说,后来,当伊斯兰教创立时,穆斯林们承认伊布拉欣的地位,并将他尊为圣祖。于是每年的这一天就形成了宰牲献祭的习俗,就这样沿袭到了今天。
现在,每到古尔邦节,艾尼瓦尔就会想起父亲讲过的那个故事,内心总是会想,这穆民们啊,忠贞得很呢,信仰,都在骨头里呢!
古尔邦节来临的那天,所长把艾尼瓦尔叫进办公室,说,你明天回家吧,节,总是要过的嘛。艾尼瓦尔就摇了摇头,说,这哪行嘛,案子在那放着呢,这时跑球掉了,还是人吗?所长笑了笑,亲切地说,弟兄们在呢,你就放心吧。不等艾尼瓦尔开口,所长又说,家里,只有老母亲一个人,工作是工作,这孝心,还得尽嘛。所长是个汉族,说这话时,脸上真诚得很。艾尼瓦尔有些感动,又想起了母亲,心头一热,就说到,那好吧,我早上回去,晚上一定回来。
牧区开阔得很。母亲的房子,虽然就在邻村,却离红柳村很远。第二天早上,风很大,下着雪,艾尼瓦尔早早动身,天刚亮就到家了。
还没到家门口,艾尼瓦尔就听到母亲的院子中传来了巨大的吵闹声。这是咋了?艾尼瓦尔加快脚步走进了院子。院子里,几个牧民围着一头公牛,正在对峙着。艾尼瓦尔发现,那头壮实的黑色公牛,虽然腿被绳子绑着,却仍然打着响鼻,目光凶悍,很难将其放倒。看到艾尼瓦尔,妻子阿伊古丽就喊道,啊,你可回来了,这犟牛,没法弄呢。艾尼瓦尔明白了,牧民们这是在宰牲呢。过去,牧民们过节都宰羊,后来就有人说,羊的骨头多得很,虽香,肉却少,填不满咱牧民们的大肚子。于是,牧民们就合起伙来,宰牛。牛大,肉多,一个节下来肉都吃不完,还可以做冬肉呢,划算。
可今天,那头公牛太彪悍,几个牧民一起上,都没办法把公牛日弄翻。艾尼瓦尔笑了笑,说道,你们嘛,怂得很,乖乖让开,看我的
随后,艾尼瓦尔脱掉大衣,吹着口哨,轻松地向公牛走去。公牛扭头看了看,并没在意。艾尼瓦尔接近了公牛,亲热地笑着,若无其事拍了拍牛角。牛摆了摆头,牛角闪着寒光,看艾尼瓦尔,似乎没有发现恶意,就放松了警惕。艾尼瓦尔微笑着,暗暗运着气,随后突然举起巴掌,在牛的肩胛骨处狠狠拍了一下。牛的眼睛,立刻就凝在了那里。
父亲早就说过了,牛的心脏离肩胛骨很近。
牛虽粗壮,心脏却特别的脆弱,受到重创,牛就不牛了。艾尼瓦尔手上的劲,可以劈开天山上最坚硬的石头,这一掌下去,牛的心脏就受到了重创,仓促间猛地立在那里,不动了。艾尼瓦尔深吸口气,两手用力,大吼一身,牛就被推翻在了地上,死命蹬着腿,就是起不来。
随后,艾尼瓦尔极其舒服地放了个响屁,活动了下腰身,问,刀子呢?母亲就把刀子递到了艾尼瓦尔的手中。
那把刀子是父亲留下的,是把真正的英吉沙刀子,刀把镶着金边,华丽得很,刀口闪着锋利的寒光。艾尼瓦尔把刀咬在口里,又喊,阿伊古丽,水呢?阿伊古丽慌忙拎着水壶赶了过来。艾尼瓦尔撸起袖子,净了手,暗暗做了祷告,这才摁住牛头,找准位置,口中念念有词,一刀下去,血就疯狂地喷涌出来。
牛拼命挣扎,艾尼瓦尔死死摁着牛头,就是不松手,不久,牛就彻底断了气。
艾尼瓦尔活动了下手臂,抓起一只牛腿,熟练地剔去牛毛,在血管上挑了个缺口,这才对着围观的牧民们喊道,你们这些赖瓜子就会吃呢,力气都被屁放走了,现在该你们了。几个精壮的牧民就慌忙答应着,凑了上来,抱住牛腿,鼓足了气,轮换着在缺口上猛吹。牧民们的气足得很,很快,牛的肚子就鼓了起来。艾尼瓦尔弯下腰,刀子舞得飞快,不大工夫,牛皮就被完整地剥了下来。有牧民拿起那张牛皮看了看,竟然没有一个创口,就咂巴着嘴说道,这手艺,真是邪乎呢,除了真主,恐怕谁也做不到呢。
艾尼瓦尔分好肉,阿伊古丽已在茶棚子下面架好了煮肉的大锅。肉下到水里,不多时,院中便飘满了牛肉诱人的清香。
此时,雪纷纷扬扬地下着,寒气重得很。
院外,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艾尼瓦尔愣了愣神,心想,这么早客人们就上门了?穆斯林的习俗,节日是要上门拜访的。情意都在那些問候里呢。因此,每到这个日子,穆斯林们你来我往,以最好的肉迎接客人的到来。听到有客人来,艾尼瓦尔立刻愉快地答应着,跑去打开了院门。
门口,站着两个陌生的中年男人。
艾尼瓦尔发现,这两个人的毡帽上,都挂满了雪花,脚上的毡筒上全是泥。凛冽的寒风,正不停地撕扯着他们破旧的皮大衣,两个人被寒冷打红的脸颊子上满是疲惫和惶恐,就连身后那两匹落满寒霜的马,也低着头,仿佛十几天没吃草似的,骨架子都塌了下来,显得没有一点力气。很显然,这两位是远道而来的客人!
色俩目尔来昆(穆斯林问候语:你好)!
虽然素不相识,艾尼瓦尔依然热情地问候着。双方握过手后,客人探寻着问道,我们远道而来,冷得很,能不能进去喝口茶啊?艾尼瓦尔微笑着,痛快地答应道,说啥话呢嘛,都是穆民,进来吧。
哈萨克人是一个热情好客的民族。
据说,曾经有一位内地来的汉人,在草原上游玩,不慎丢了钱物,虽然身无分文,却依然受到了哈萨克人的热情接待,在大草原上吃住了十几天,就再也离不开那个好客的民族,自愿留在了大草原,成了那个部落中第一位在草原上繁衍的汉族人。
看到客人仍然略显惶恐的样子,艾尼瓦尔又热情地说道,何况今天又是古尔邦节呢,好日子呢!
进了屋子,盘腿坐定后,艾尼瓦尔立刻招呼道,阿伊古丽,赶快倒茶呀,有客人呢。等到两位客人像沙漠里多日未见水的驼儿一样饮足了茶后,艾尼瓦尔才问,两位是从哪个地方来的呢?一个牧民答道,我们是从牧场连夜赶来的。艾尼瓦尔又问到,是来探亲的吗?另一个牧民答道,不呢,是来卖马的!
卖马的?
艾尼瓦尔略感惊讶,牧区这几天没有牲畜巴扎呀,何况按照哈萨克人的礼节,古尔邦节的第一天,都是要留在家里的。不然客人们来了,没人咋行?像这样连夜从牧场赶来卖马的,艾尼瓦尔从没见过。
想到这里,艾尼瓦尔在心中画上一个重重的问号。
那么,您的马一匹多少钱呢?艾尼瓦尔喝着茶,问道。一个牧民回答道,急等钱用呢,给上九百元也就行了!
九百元?
艾尼瓦尔感到震惊,哈萨克人爱马如子,自己喂养的马是决不可能折价处理的。何况艾尼瓦尔早就发现,门口的那两匹马是纯种的伊犁马,还是上等的跑马,怎么可能以这样低廉的价格出售呢?震惊之余,艾尼瓦尔稳稳地喝着茶,未露出丝毫的猜疑,职业的敏感告诉他,这两位不速之客一定不寻常!
两位客人先喝茶,我去看看,肉,在锅里呢。
艾尼瓦尔稳住两人后,来到院门口,观察着那两匹马。良久才返回屋内。
肉,马上就熟了,艾尼瓦尔说,随后给客人续着茶,好像自言自语地说到,门口那两匹马,可真是两匹好马呀!
谁说不是呢?要不是急等钱用,真舍不得便宜出售呢,一个牧民立刻附和道。
艾尼瓦尔不动声色,又不置可否地问道,那匹黑马,耳后的标记好像是新打的嘛?
另一个牧民赶紧回答道,是呀!新打的,丢了好找呢。这么回答着,两个牧民的脸上就突然出现了一丝迟疑。
阿伊古丽,怎么还不上肉啊?
艾尼瓦尔生气地呼喊着妻子,假借洗手,再次来到院门口,拿出手机给所长打了个电话。等到警车呼啸着停在门口时,艾尼瓦尔依然面带笑容,对两个牧民说,尊贵的客人们,肉,咱们就不要吃了,请到派出所坐一下吧。听了这话,两位客人顿时惊呆了。
事后,所长问艾尼瓦尔,你是怎么发现这两个人是贼娃子的?
艾尼瓦尔笑着说,也是碰巧呢。起先看到这两个人,我就觉得奇怪得很,过节呢,怎么可能出来卖马嘛?至于怎么识破的,艾尼瓦尔说,其实嘛,那匹黑马的耳后,根本就没有什么标记嘛。这两个贼娃子,掉进咱的套子里了。艾尼瓦尔还高兴地对所长说,没想到,过年呢,竟然抓了两个贼娃子,说不准与先前的案子也有关系呢,你们先审着,我随后就到。好事,看来有呢。
那天,雪一直下到午后。艾尼瓦尔怎么也没有想到,那个案子的背后竟然牵出了一个人。这个人,艾尼瓦尔是再熟悉不过了。
五
那天午后,艾尼瓦尔料理完家里的事,就急匆匆地赶回了派出所,
看到艾尼瓦尔,所长黑着脸迟疑着说道,艾尼瓦尔,这个案子真的不简单呢。说话间,所长打量着艾尼瓦尔,脸上分明有一种试探和狐疑。怎么?那两个撞在枪口上的家伙有什么不对吗?对所长的迟疑,艾尼瓦尔感到有些意外,对所长脸上那种不加掩饰的试探和狐疑,艾尼瓦尔也明显有所察觉。只是他无法理解所长为什么会露出这种神情,在他的印象中,所长一直是一个直言快语的汉子。
所长说,审讯结果出来了,有些出乎意料呢。
不等艾尼瓦尔开口,所长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道,开始我们也觉得这就是一般的盗窃案子,抓住那两个嫌疑人也纯属巧合,因此并没有太多的奢望。然而,随着审讯的不断深入,才发现这两个家伙背后还有一个组织者呢。最近发生在冬窝子的牲畜盗窃案都是这个团伙干的。所长说着,脸上的神情更加凝重了。
是吗?真是太出乎意料了,那些案子真就这样给破了?艾尼瓦尔高兴地喊道。冷静下来后,又问道,可是,那个幕后组织者,又是谁呢?
马力克!所长淡淡地说道。
谁?马力克?你是说,马力克?艾尼瓦尔猛地愣在了那里。
是马力克,最近发生的案子,都是他指使人干的,所长肯定地说道。
不,不可能嘛!怎么可能是马力克,他可是个猎人,怎么可能偷自家的马嘛!艾尼瓦尔大声喊道。所长拍了拍艾尼瓦尔的肩膀,说道,你,冷静点嘛,案子的确是马力克干的,错不了。
这时,艾尼瓦尔突然感到有些眩晕,胸口像被山压着,喘不过气来。
许久,艾尼瓦尔才从惶惑不安中清醒过来,喃喃地说道,真的是马力克?他现在在哪,我要亲自问问他。所长说,我们已经派人去找他了,可是没能找到,可能是听到了风声,跑了。
艾尼瓦尔不再说话,手顫抖着,卷了支粗大的莫合烟,埋头抽着。许久,艾尼瓦尔抬起头来说道,我知道他在哪。
所长就问,在哪?
艾尼瓦尔说,红柳荡。
黄昏的红柳荡在晚霞中显得十分凄凉。马力克,就坐在红柳荡里。不过,现在的红柳荡,已经不能称之为红柳荡了,它们已经被摧残得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当艾尼瓦尔走近马力克时,马力克没有动,他知道,能在这里找到他的,只有艾尼瓦尔。
你说,这里真的有红狼吗?马力克没有回头,凄凉地问道。艾尼瓦尔站在马力克身后,没有出声,悲伤地看着马力克的背影。
马力克自顾自地笑了笑,轻声说道,当然没有,怎么可能有红狼呢?我们应该早就知道,红狼就是个传说嘛。就算有,红柳荡都死了,红狼还会活着吗?
艾尼瓦尔依然默默地站着,看着日渐消失的红柳,悲愤地说道,是的,红狼可以没有,可传说还在呢,咱们的信仰还在呢!
信仰?信仰是个球嘛!我马力克的信仰,早就死了!马力克声嘶力竭地喊着,眼泪终于流了下来。
六
第二天,雪下得更大了,像是世界的末日要来了。
天还没亮,艾尼瓦尔就起床了,头发乱得像野草,眼睛通红,没有亮光。昨夜,艾尼瓦尔失眠了,牧区长大的汉子,这还是第一次。艾尼瓦尔走进所长的办公室,低着头问,他,交代了吗?所长给艾尼瓦尔递了根烟,说道,这家伙硬得很呢,死活不说。
艾尼瓦尔抽着烟,不知怎么就呛了一下,剧烈地咳嗽起来。
稍后,艾尼瓦尔才缓过劲来,喘着粗气问道,要不,我进去看看?
你?所长的声音有些怪异,似乎不大相信,沉吟片刻,这才接着说道,你们俩,从小长大的,我看你还是回避一下吧。
回避?你是说,回避?
艾尼瓦尔声音大了起来,喊道,所长,啥叫回避嘛?我,艾尼瓦尔,是怎么样的人,这么多年了,你是知道的嘛。法律,在我的心中,那就是良心嘛,我,猎人的后代,怎么能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呢?艾尼瓦尔的话糙,理却不糙。这么多年,艾尼瓦尔的确从没有干过对不住自己良心的事。最后,所长点点头,艾尼瓦尔就走进了审讯室。
审讯室内,马力克坐在暗淡的灯光下,冷漠,像黑山头的石头。
艾尼瓦尔记得,过去的马力克,眼光亮得很,极有神,像唐布拉的鹰。古铜色的脸,猎人的味道,足得很。现在,马力克的脸,苍白,暗淡,没有丝毫光泽。目光中,只有瘆人的冷漠。艾尼瓦尔看着带着手铐的马力克,内心说不出的凄楚。
为了什么?
不为什么!
你忘了吗?咱们曾经在红柳荡发过誓呢!
红柳荡,已经死了!
可是,咱们,还活着呢!
活着,又有啥用呢?
……
窗外,风雪更大了。审讯室内,任凭艾尼瓦尔怎么问,马力克就是什么也不说。艾尼瓦尔有些失望,走出审讯室,来到了室外。
雪,到处都是白茫茫的雪。艾尼瓦尔觉得,雪落的时候,空旷就会被激情填满,遥远就会被飘落阻击。艾尼瓦尔觉得,所有的视线都被风雪折断了,思绪正匆匆围拢过来,在咫尺之间,互相打量着敞开的胸膛。这时,艾尼瓦尔发现,雪地上,空旷的已经不再空旷,遥远的也不再遥远!看似微小却密集的力量,正在征服着一个自以为强大的世界!
艾尼瓦尔有些激动,又举目向远处看去。
风雪中,西天山昂首长空,纵横逶迤,它肌肉的伸缩,依然强劲!它骨骼的支撑,依然雄浑!它没有把高度作为炫耀,而是以一种眺望的姿态,在做着更多睿智的思考。艾尼瓦尔相信,在风刀雪剑的逆境里,只要情怀犹存,又何愁绿色不再?
艾尼瓦尔看到了远处雪地上的一棵孤树。
艾尼瓦尔走过去,抱着那棵树失声痛哭。那只是一棵树,在冬天里,它没有了繁华和茂盛,它的躯干没有一丝温度。在它孤独的翘望中,它又看到了什么?可是,它的腰身却是笔直的,它的脊梁是硬朗的,在肆虐的寒风中,它执着地坚持着,从没有失落,也从没有彷徨。时间之手可以折去它头顶上的一枝一叶,却无法撼动它深扎在泥土深处的根!艾尼瓦尔问自己,一棵树,都会如此,人呢?
再次走进审讯室时,艾尼瓦尔的手里,拿着那把精致的冬不拉!
天边夕阳再次映上我的脸庞
再次映着我那不安的心
这是什么地方,依然是如此的荒凉
那无尽的旅程依然如此漫长
我是永远向着远方独行的浪子
你是茫茫人海中我的女人
在异乡的路上每个寒冷的夜晚
这思念它如刀让我伤痛
……
艾尼瓦尔弹着冬不拉,轻声唱着,声音中满含悲凉。
在他的歌唱中,那些传说就站在远处,笑着。浩大的红柳荡,充满了血性。在他的歌唱中,雪山再高,都无法阻挡奶茶的醇香。哈萨克毡房里啊!母亲端起的茶碗里,翻动着哈萨克人滚烫的生活;他似乎看到了,广阔的草场上,牛羊走得再远,都离不开哈萨克毡房。哈萨克人即使走出了草原,心,却仍然留在了毡房里。回归的时候,总会跪倒在毡房前的草地上……
终于,马力克哭了!
马力克说,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一个人的奋斗是多么的艰难?没有钱,即使你的理想长出了鹰的翅膀,又能飞到哪里去?
马力克说,你知道吗?现实是多么的残酷,它会让你失去自己,失去草原,失去那些长在骨头里的东西!
马力克说,你肯定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它可以使你不再卑微地活着,可以让你像一只真正的鹰,在天空中无忧无虑地飞翔!
马力克最后说,那个东西,就是钱,有了钱,你才会有梦想,否则,即使你的骨头再硬,又能顶个球用?
……
在马力克的哭诉中,艾尼瓦尔震惊了,他怎么也无法相信,一个牧区走出去的人,骨头曾经是那么的硬,内心曾经是那么的干净,这么快,就成了金錢的奴隶。他更无法相信,曾经像红柳般那么倔强的一个人,会在欲望中变得这么无耻!
马力克终于说出了一切!
他说,起先他快乐地开着他的乐器店,梦想在他的心里头花一样开着。可当他发现这样开下去,他那微薄的收入永远也无法实现他的梦想时,他迷茫了。他内心的信仰滑落了,他看待这个世界的目光变得不再纯净。那一刻,他仍然记着他的誓言——他曾经说过,他要买下红柳荡,他要让所有的牧民都过上好日子……可是没有钱,一切就都是个传说,于是,他借了高利贷。然而直到把钱都花完了,也什么都没干成,债务却压在了他的身体上,像山。
后来,他碰到了一个外号叫“黑毛”的毒贩子。
黑毛说,钱,容易得很,你只要做一次就有了。他动心了,他决定试试,哪怕就做一次。有了钱,他马力克不就可以抬着头回红柳村了吗?可黑毛又说,做生意需要本钱呢,你,有吗?最后,为了本钱,他开始盗窃。当他和黑毛交货的时间越来越近时,钱仍不够,他最终偷了自家怀孕的马!
你和黑毛的交货地点在哪里?
就在红柳荡!
什么时间?
明天早上……
临近中午,艾尼瓦尔终于走出了审讯室,面色疲惫而又凄凉。艾尼瓦尔长出了口气,对所长说,都撂了,明天早上,咱们去抓黑毛。
这时突然就刮起了风,艾尼瓦尔看着远方,想象着红柳的样子,就有了要流泪的感觉。艾尼瓦尔极力闭着眼睛,泪水却还是流了下来。
艾尼瓦尔,你哭了?旁边一个民警关心地问道。只是一粒可恶的沙子,艾尼瓦尔说着用手背抹了一下眼睛,轻轻一甩。艾尼瓦尔,你本来可以回避的,另一名警察抱怨道。是的,可以回避的,艾尼瓦尔淡淡地笑了笑,说,有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回避的。我,是个警察嘛,警察能回避现实吗?
晚上,舅舅的电话打过来了!
舅舅在电话中说,豹娃子,案子办得怎么样了?艾尼瓦尔回答道,破了。舅舅高兴地问道,真的吗?艾尼瓦尔回答,真的!舅舅在电话中笑了,说,那太好了,马找回来了,下了马驹,卖了,马力克做生意就有钱了!舅舅又说,你不知道,马力克不容易呢。这几年,他受的累太多了。他是个有心的孩子呢,他的心,都在红柳荡里呢。可是,他是个穷孩子啊,没有钱,你让他咋办嘛?艾尼瓦尔叹了口气,是啊!钱,好东西呢!可是,钱这个东西,又是多么可怕啊!
外面雪花纷纷扬扬,下得很猛!
七
第二天早上,抓捕黑毛的行动,在红柳荡展开。
那天,艾尼瓦尔看到了红柳荡上空,一只孤独的鹰跃动于不可企及的高空,翅膀之上闪耀着金色的光芒。小的时候,父亲就对艾尼瓦尔说过,你知道吗?人们之所以赞美鹰的神奇和粗犷,都是源于它翅膀之下的那片琼宇。父亲说,然而只有鹰自己才知道,如果只是停留在高空之上,无论如何是不能被称之为鹰的,因为只有在低处的那片丘陵地带才有它赖以生存的能量。
那时,他还不能完全理解父亲的话。可现在,他明白了。
鹰,一生应该有两个高度,一个在云的肩上,那是它思考的地方;另一个,应该在宽广的土地上,那里才是它赖以生存的栖所。在无与伦比的高空,鹰的精神得到了升华,而只有回归到了黑色的土地上,鹰才会找回自己!艾尼瓦尔深深地意识到,人,应该也是这样。否则就会失去自我。
马力克答应,他去和黑毛接头。
马力克还说,他要找回做人的尊严,一个猎人应有的尊严,就是死也要死在红柳荡。天还没有亮,艾尼瓦尔就带着人,埋伏在红柳荡,伺机展开抓捕。
那天,黑毛如期来了。
黑毛来的时候,口袋里带着枪。交货的瞬间,黑毛发现了异常。枪,响了。当艾尼瓦尔冲过去时,马力克已经倒在了血泊中,双手,仍然死死抱着黑毛的腿。眼里,都是笑。
那天,天冷得很,风死命地刮着,红柳荡在风中,发出阵阵凄凉的呼喊声。
责任编辑:刘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