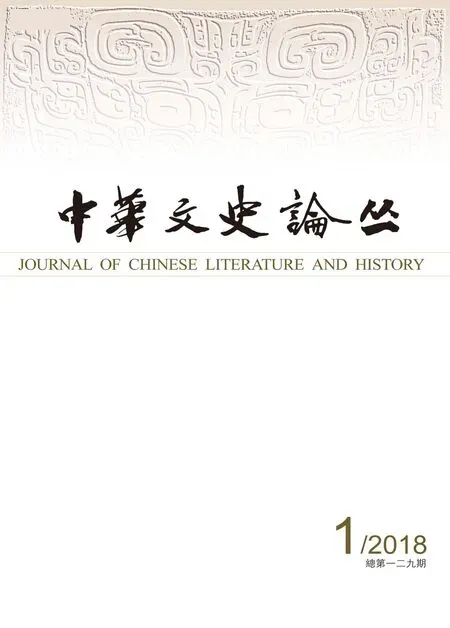漢初隸變楚辭與《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的材料來源❋
2018-05-28張樹國
張樹國
自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以迄清代,《楚辭》研究史上没有人否定屈原的歷史存在。東漢王逸《章句》、宋洪興祖《補注》、南宋朱熹《集注》、明汪瑗《楚辭集解》以及清儒王夫之《楚辭通釋》、戴震《屈原賦注》、林雲銘《楚辭燈》、蔣驥《山帶閣注楚辭》等著作對《楚辭》作品無論在訓詁、音韻還是藝術手法上都有詳細注釋和闡述,對屈原流放行蹤和悲劇命運都有細緻考證。但即便如此,《史記》仍有重要“異文”遺漏,如中華書局新版《史記·屈賈列傳》“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史記》(修訂本)卷八四,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3009。南宋黄善夫《史記》刻本作“屈平屬草藁二,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南宋刊建安黄善夫本〈史記〉》,臺北,臺灣藝文印書館影印,1966年,35册,本傳葉1A。揆諸上下文,“二”不能省,黄本於義爲長。雖然對個别《楚辭》作品的歸屬存在各種意見,但屈原是歷史人物,是一系列《楚辭》作品的創作者,這一點始終未曾改變。
但近現代以來,隨着西方思潮以及研究方法的引進,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疑古思潮”的影響下,廖平、胡適、何天行諸學者開始懷疑屈原的存在以及《楚辭》作品的歸屬等問題,這些問題體現爲:
(一) 否定屈原及《離騷》。據日本稻畑耕一郎《屈原否定論系譜》歸納,*載黄中模編《中日學者屈原問題論爭集》,韓基國譯,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年,頁295—316。原文刊載日本早稻田大學中國文學會1977年編印《中國文學研究》第3期,頁18—35。廖平《楚辭新論》力倡《離騷》爲秦博士之《仙真人詩》。胡適《讀〈楚辭〉》認爲“傳説的屈原,若真有其人,必不會出生在秦漢以前”,但如何來看待《漢書·藝文志》“屈原賦二十五篇”問題,胡適認爲:“屈原也許是二十五篇《楚辭》之中的一部分的作者。”*《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293。何天行《楚辭新考》認爲屈原這個人根本不存在,《離騷》爲淮南王劉安所作,《楚辭》皆爲漢代人所寫。類似説法見於衛聚賢《〈離騷〉底作者——屈原與劉安》、朱東潤《楚歌及楚辭》等。
(二) 認爲《屈原賈生列傳》中的材料不可靠。岡村繁《楚辭與屈原》認爲司馬遷寫作《屈原列傳》的材料來源主要分爲三部分: 一是對《楚世家》懷王十六年—頃襄王三年的“忠實的轉抄”,但有不一致之處,如《楚世家》懷王三十年:“昭雎曰: 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史記》卷四〇,頁2081。這裏勸諫楚王的是昭雎,而《屈原列傳》中卻將其改爲屈原;二是從淮南王劉安《離騷傳》中借用的文字;三是《漁父》之類“乃後人假托屈原同漁父論辯儒道思想優劣的虚構作品”。因此,岡村繁認爲《屈原列傳》“至少其傳記中的重要部分,是完全憑藉品質上缺乏可靠性的資料而編寫的”。*岡村繁《周漢文學史考》,陸曉光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50—81。
(三) 《屈原賈生列傳》作者不是司馬遷。汪春泓先生《讀〈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獻疑》認爲《屈賈列傳》爲西漢楚元王後人劉德、劉向所撰。*載《文學遺産》2011年第4期,收入汪春泓《史漢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119—153。
屈原與《史記》中諸多“當時則榮,没則已焉”*《史記》卷四七《孔子世家》,頁2356。的傳主不一樣的地方,是戰國楚辭文學的開創者,留下了彪炳史册的楚辭作品。《屈賈列傳》:“太史公曰: 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史記》卷八四,頁3034。但司馬遷所讀楚辭作品是戰國楚文字寫本還是漢初隸變文本?這是本文探討的主題。因此,要回答上述諸多爭議,還是要對屈賦文本作認真研究,而這恰恰是屈原否定論者的“硬傷”。《屈原列傳》收録了《懷沙》、《漁父》兩篇作品,與傳世《楚辭》(即王逸、洪興祖《楚辭補注》本)多有不同,而王逸《章句》本是劉向、劉歆以西漢晚期隸書整理後的本子,故《楚辭目録》下首稱“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劉向集,後漢校書郎臣王逸章句”。*洪興祖《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本文通過《史記·屈原列傳》及其收録作品,發現司馬遷研究過屈原作品,並用來敍述屈原的心路歷程。下文對《史記》本《懷沙》與王逸《楚辭章句》本作對比研究,以確定司馬遷爲寫《屈原列傳》而研讀的楚辭作品到底是戰國楚文字寫本還是漢初隸變文本,從而確定《屈原列傳》的可信性和屈賦作品的篇目問題。
一 《史記》本《懷沙》爲漢初隸變文本
《史記·屈賈列傳》敍述屈原來到江濱,與漁父對話之後,“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史記》卷八四,頁3015,3019。將《懷沙》視爲屈原的絶命詞,收録於《史記》屈原的本傳中。清陳本禮《屈辭精義·懷沙》箋云:“此篇當是絶筆之文。”*陳本禮《屈辭精義》,《續修四庫全書》,130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嘉慶裛露軒藏版,2002年,頁523上。筆者查閲宋、明、清以來《楚辭》刊本,發現《史記》本《懷沙》與今傳王逸《章句》、洪興祖《補注》本《懷沙》多有不同,據筆者統計,《史記》本《懷沙》與今傳《楚辭章句》本異文多達四十餘處,這些異文體現爲古今字和大量通假字。據蔣禮鴻先生説,構成古今字雖然有比較複雜的情況,但對形聲字來説,基本上是“初文加聲旁”和“初文加形旁”兩類。*蔣禮鴻《古漢語通論》,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28—29。《史記》本《懷沙》“易初本由兮”之“由”《章句》作迪,“誹俊疑桀”之“桀”《章句》作“傑”等;兩本通假字以聲同通假占多數,如“陶陶孟夏”,《章句》作“滔滔”;“眴兮窈窈”,《章句》作“杳杳”;“孔靜幽墨”《章句》作“默”等。值得注意的是,“修路幽拂兮”之“拂”,《章句》作“蔽”,張守節《史記正義》:“拂,風弗反。言拂鬱幽蔽也。”*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卷八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3238。《正義》此條今《史記》修訂本未引,注釋不是很準確。“拂”上古讀若重唇音“蔽”,《戰國策·趙策二》“趙燕後胡服”章:“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范祥雍《戰國策箋證》卷一九《趙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1076。《魏策四》“魏王與龍陽君共船”條:“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爲王拂枕席。”*《戰國策箋證》卷二五,頁1460。司馬相如《子虚賦》:“下摩蘭蕙,上拂羽蓋。”*《史記》卷一一七《司馬相如列傳》,頁3651。“拂”即“蔽”。“拂”又訓爲弼,《管子·四稱》:“近君爲拂,遠君爲輔。”安井衡云:“拂,弼也。矯過曰拂。”*黎翔鳳《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620。《史記·秦始皇本紀》:“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正義》:“拂,蒲筆反。”*《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頁325—326。疑劉向或王逸《章句》將“修路幽拂”之“拂”改爲“蔽”。
除古今字、通假字之外,還有很多形近而訛或意近而改而造成的異文,如“巧匠不斫兮,孰察其揆正”之“揆正”,《章句》作“撥正”,瀧川資言《會注考證》:“《正義》本作‘撥正’,與《楚辭》合,作‘揆’義長。”*《史記會注考證》卷八四,頁3850。“巧匠”,王逸《章句》、朱熹《集注》皆作“巧倕”,《章句》:“倕,堯巧工也。”清陳本禮箋:“言倕必斫而後知其巧,喻己不見用,無人知其才德也。”*陳本禮《屈辭精義》,《續修四庫全書》,1302册,頁523下。從文意來説,似以“巧倕”爲是,與下文“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之“離婁”相對應。但“匠”(從紐陽部去聲)與“垂”(倕,禪紐歌部平聲)形音相差太多,“巧匠”固然樸拙一點,可能更接近原本。筆者查閲南宋黄善夫本,亦作“巧匠不斫兮,孰察其揆正”。*《南宋刊建安黄善夫本〈史記〉》,35册,本傳葉5B。又如“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强”之“違”,《楚辭》作“連”,王念孫按:“違,恨也。言止其恨,改其忿,抑其心而自强勉也。《廣雅》曰:‘怨、愇、很,恨也。’愇與違同……《楚辭》‘違’訛作‘連’,王注以‘連’爲‘留連’,失之。”*王念孫《讀書雜誌·史記第五》,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影印,2000年,頁135下,136上。以上這些異文還看不出《史記》本《懷沙》的文字特徵,下面這條就很能説明問題,文云:
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史記》卷八四《屈原賈生列傳》,頁3017。
《楚辭》作“舒憂娱哀”,《章句》:“娱,樂。《史記》云: 含憂虞哀。”*《楚辭補注》,頁145。陳本禮箋:“以懷石爲舒憂,以投淵爲娱哀,命盡於此,天實限之,夫何怨哉?”*《屈辭精義》,《續修四庫全書》,1302册,頁524下。王念孫按:
“含”當爲“舍”,字之誤也。(隸書含或作含,又作舍,皆與舍字相似。)“舍”即“舒”字也,《説文》:“舒,從予,舍聲。”《小雅·何人斯篇》“亦不遑舍”,與車、盱爲韻。《史記·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聘·禮記》:“發氣怡焉”鄭注曰:“發氣,舍息也。”“舍息”即“舒息”。是舒與舍古同聲而通用。王注《楚詞》曰:“言己自知不遇,聊作詞賦以舒展憂思,樂己悲愁”,是“舒憂娱哀”義本相承。若云“含憂”則與“娱哀”異義矣。*《讀書雜誌·史記第五》,頁136上。
王念孫釋“含憂”之“含”當爲“舍”之誤,“舍”爲“舒”義,隸書“含”“舍”形近而誤,此説正確,具有重大意義。
首先,對“含”與“舒”這一異文現象的考證,是判斷《懷沙》文本究竟是戰國楚文字寫本還是漢初隸變文本的重要證據。“含”“舍”漢初隸書寫法可參見《銀雀山漢簡文字編》及《馬王堆簡帛文字編》:*陸錫興編著《漢代簡牘草字編》,上海書畫出版社,1989年,頁19,98;駢宇騫編著《銀雀山漢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頁38,185;陳松長編著《馬王堆簡帛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頁46,210。


“含”、“舍”在漢初隸書中形近易訛,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戰國楚文字中,“含”、“舍”寫法則差别很大:

從上例可見戰國楚文字“含”、“舍”字形差别很大,幾乎不存在互誤的可能。長沙馬王堆隸書“含”字係從戰國楚文字隸變而來,演進之迹甚明。除《上博一·孔子詩論》寫法之外(此字是否讀“舍”還有很大爭議),戰國楚文字“舍”寫法比較複雜,《上博三·用曰》簡1:
整理者釋作“豫”或“舍”。*《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圖版頁105,釋文頁286。據范常喜先生解釋,“縈”訓“營”,《荀子·宥坐》“言談足以飾邪營衆”,楊倞注:“營讀爲熒,熒衆,惑衆也。”*王先謙《荀子集解》卷二〇,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521。“豫”當讀作“舍”,“舍命”即“發號施令”,上引文句意爲“(心、目、口)三節如果不能相互配合默契,那麽發號施令就會混亂。”*范常喜《簡帛探微——簡帛字詞考釋與文獻新證》,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頁64,65。《上博三·中弓》簡10:“舉而所知,而所不知,人其豫之者(諸)?”*《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圖版頁82。今本《論語·子路》:“舉而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程樹德《論語集釋》卷二六,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1139。《上博三·周易》簡24“豫爾靈龜,觀我頤”,*《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圖版頁36。今本《周易》作“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周易注疏》,十三經注疏本(嘉慶本),北京,中華書局影印,2010年,頁82上。《清華三·芮良夫》簡15“天猶畏矣,豫命亡(無)成”,*《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圖版頁78。“豫”、“舍”、“施”通。傳本《楚辭》“豫”出現五處,兩處見於《離騷》,即“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楚辭補注》,頁33,36。“猶豫”爲聯綿詞,用法與今同。其他三處見於《九章》:
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讎也。一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惜誦》)
行婞直而不豫兮,鯀功用而不就。(《惜誦》)
余將董道而不豫兮,故將重昏而終身。(《涉江》)*《楚辭補注》,頁123,126,131。
其次,語助詞“兮”的使用,《史記》本比王逸《章句》本多出13處(51∶38)。王逸《章句》本“亂曰”以上,出句有“兮”,對句則無;“亂曰”以下,出句無“兮”,對句則有,比較整齊;而《史記》本《懷沙》“亂曰”以下句句有“兮”,如“浩浩沅湘兮,分流汩兮。修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朱熹《集注》:“《史》逐句有‘兮’字,自此至篇末並同。”*朱熹《楚辭集注》,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影印《古逸叢書》本,1990年,頁111。王夫之《楚辭通釋》認爲《懷沙》“蓋絶命永訣之言也,故其詞迫而不舒,其思幽而不著,繁音促節,特異於他篇云。”*王夫之《楚辭通釋》卷四,《續修四庫全書》,1302册,頁233上。此“繁音促節”當指“亂曰”以下“兮”連句而用。清劉淇《助字辨略》:“兮,歌之餘聲。”*劉淇《助字辨略》卷一,章錫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57。“兮”在先秦楚文字寫本中通常寫作“可”,上博簡(八)收録《李頌》等四篇楚辭作品,如“相吾官樹,桐且怡可。摶外疏中,衆木之紀可”,*《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八),圖版頁91。“可”今本皆作“兮”,其應用形式很有規律,《李頌》文本結構及藝術風格與今傳本《九章·橘頌》相似。但王逸《章句》本《懷沙》“兮”的使用這樣有規律,表明已經過後人整理。
《史記》本《懷沙》“兮”的連句用法表明這是一篇用於吟唱的楚歌體作品。清水茂《從誦賦到看賦》認爲:“辭賦本來是朗誦的,而前漢的大賦還保存着音樂性,以後漸漸地走向書面文學。”*《清水茂漢學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237。在漢賦之前,楚辭是用來吟唱的,並非“朗誦”而已。《史記》書寫於漢武帝時代,“楚聲”還在盛行。《史記·樂書》記載武帝得“天馬”而作《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貢兮天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爲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馬,又作《蒲梢馬歌》,歌曲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史記》卷二四,頁1400—1401。這兩首歌詩後被收入《郊祀歌十九章》,見《漢書·禮樂志》,但都被删去了“兮”字而成爲雜言詩,如《太一之歌》變成了三言詩:“太一況,天馬下。霑赤汗,沬流赭。……體容與,迣萬里。今安匹,龍爲友。”《蒲梢馬歌》則改動很大,增添了許多三言句式,如“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等。*《漢書》卷二二,頁1060—1061。另外《楚辭·九歌·山鬼》“今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等句,在《宋書·樂志三》中改作《今有人》“今有人,山之阿,被服薜荔帶女蘿”,題名《楚詞鈔》。*沈約《宋書》卷二一,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607—608。又如《漢書·藝文志》記載《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所謂“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清代學者曾根據這些楚歌被改爲三言詩的案例,推斷高祖唐山夫人所作《房中祠樂》實即“房中燕樂”,是楚歌形式。朱乾《樂府正義》認爲:“徐伯臣定以‘大海蕩蕩’四章爲房中燕樂,極是。”*朱乾《樂府正義》卷二,浙江圖書館藏乾隆五十四年(1789)秬香堂版,葉5A。這四章包括《大海蕩蕩》六、《安其所》七、《豐草葽》八、《雷震震》九,除《大海蕩蕩》爲雜言體外,其他均爲三言,當是删落楚歌的代表特徵“兮”後而成。除這四章之外,則爲齊言的雅樂作品。同理,《史記》本《懷沙》“亂曰”以下幾乎句句用“兮”,而到劉向、劉歆整理文獻後隔句刊落,就變成今本《懷沙》的樣式了,今本王逸《章句》采用的是劉向輯録的文本。
再次,在《史記》本《懷沙》“亂曰”以下出現兩組相似的語句,其一處於“修路幽拂兮,道遠忽兮”之下:
曾唫恒悲兮,永嘆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史記》卷八四《屈原賈生列傳》,頁3018。
司馬貞《索隱》云:“《楚辭》無‘曾唫’已下二十一字。”*同上書,頁3019。張守節《正義》云:“自‘曾唫’已下二十一字,《楚辭》本或有無者,未詳。”*《史記會注考證》卷八四《屈原賈生列傳》,頁3238。見於《史記會注考證》,《史記》修訂本未引此句。可見早在唐代就存在或有或無兩種《楚辭》抄本了。清沈家本曰:“萬曆本《楚詞》有此二十一字,而無王注,恐是後人據史文增也。”*沈家本《史記瑣言》,《諸史瑣言》卷三,《續修四庫全書》,451册,頁645上。《四庫全書·集部》收録《楚辭章句》,*《文津閣四庫全書》,354册,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頁19上。有此二十一字,未有王注。而明汪瑗《楚辭集解》、陸時雍《楚辭疏》*汪瑗《楚辭集解》、陸時雍《楚辭疏》收録於《續修四庫全書》,1301册,頁158上,398下。、清王夫之《楚辭通釋》、陳本禮《屈辭精義》則没有。*《楚辭通釋》、《屈辭精義》收録于《續修四庫全書》,1302册,頁232上,524下。其二處於“定心廣志,餘何畏懼兮”句下,“知死不可讓”句上:
曾傷爰哀,永嘆喟兮。世溷(《楚辭》有“濁”)不吾知,心(《楚辭》作“人心”)不可謂兮。*《史記》卷八四,頁3018。
傳世《楚辭·懷沙》版本一般都有此四句二十字。朱熹《集注》:“此四句若依《史記》移着上文‘懷質抱情’之上,而以下章‘死不可讓,願無愛兮’承‘餘何畏懼’之下,文意尤通貫。但《史》於此又再出,恐是後人因校誤加也。”*《楚辭集注》,頁112。劉永濟亦云:“當是衍文”。*劉永濟《屈賦通箋》,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80。王引之認爲:“‘曾傷爰哀’四句,乃後人據《楚辭》增入,非《史記》原文也。”又云:
“曾唫恒悲”四句即“曾傷爰哀”四句之異文,特《史記》在“道遠忽兮”之下,《楚辭》在“余何畏懼兮”之下耳。後人據《楚辭》增入,而不知已見於上文也。“浩浩沅湘兮”以下,每句有“兮”字,而“增(曾)傷爰哀”,“世溷不吾知”二句下獨無“兮”字,與《楚辭》相合。其增入之迹,尤屬顯然。“永嘆喟兮”,《集解》引王逸注曰:“喟,息也。”則後四句之增,蓋在裴駰以前矣。又案: 此四句,似當從《史記》列於“道遠忽兮”之下。今循其文義讀之,“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皆言世莫能知也。“定心廣志兮,餘何畏懼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皆言己不畏死也。其敍次秩然不紊。蓋子長所見屈原賦如此,較叔師本爲長。*《讀書雜誌·史記第五》,頁136下。
所謂“‘曾唫恒悲’四句即‘曾傷爰哀’四句之異文”之説,兩組雖然文意相近,但異文多達八處,聲韻亦有殊。“唫”即“吟”,古歸侵部,“傷”歸陽部,相隔較遠;“恒悲”、“爰哀”微部疊韻;“慨”、“喟”物部疊韻,“世既莫吾知”與“世溷(《楚辭》有“濁”)不吾知”區别顯然。《史記》本《懷沙》兩處皆有,重章疊唱,很具有感染力。陳子展《九章解題》認爲“兩者都可以有,而無一是多餘”,“頗疑《史記》係根據原始的《屈原賦》本子,和王叔師根據劉向校集的《楚辭》本子不同,非必異文重出,原爲同調疊詠,《詩三百》中多有之,古樂章亦有之”。*陳子展《楚辭直解》,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582。《史記》所依據的楚辭作品當爲漢初隸定文本,而王逸《章句》本則來源於成帝時劉向、劉歆整理過的文本,在整理《懷沙》之時,可能因爲“曾傷爰哀”與“曾唫恒悲”四句意思相近,而删去了“曾唫恒悲”四句,同時也删去了“曾傷爰哀”四句中作爲楚歌體標誌的兩個“兮”字。
《九章·懷沙》爲屈原絶筆,《史記·屈原列傳》云:“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史記》卷八四,頁3019。東方朔與司馬遷同時,所作《七諫·沈江》“懷沙礫而自沈兮,不忍見君之蔽壅”,*《楚辭補注》,頁242。《屈原列傳》“懷石”與《七諫》的“懷沙礫”是對《懷沙》篇名來源的一個重要解釋。另一影響較大的説法爲明李陳玉、清蔣驥以及近人游國恩提出的“懷念長沙”之説。關於“懷沙”命名的爭議,可參見金開誠《屈原集校注》中的綜述。*金開誠、董洪利、高路明《屈原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532—534。若没有楚系文字材料的新發現,“懷沙”題義之爭還會延續下去。楚簡“沙”有四種寫法:

①④ “沙”爲“一形多音”字,除“沙”外,還讀“徙”,如《上博四·柬大王泊旱》簡9、10、15三次提到人名“相沙①”,*《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203。李守奎《文字編》讀爲“xī”,*《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1—5)文字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年,頁417。這是有根據的。據李家浩《章子國戈小考》研究,“徙”字古文或寫作“”,从尾从少。少、小古本一字,甲骨文作三小點或四小點,像細小的沙粒之形,既可以表示“小”,又可以表示“沙”,“少”古有“沙”音。*李家浩《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李家浩卷》,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80。《清華簡(壹)·楚居》記載“徙”字凡三十六條,如簡2“穴酓遲徙于京宗”等。*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保護中心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年,頁181。學者已經注意到“懷沙”之“沙”字的楚系寫法與“徙”相同,禤健聰《懷沙題義新詮》認爲:“懷沙”即“懷徙”,“意謂傷懷流徙”,*《文史》2013年第4期,頁231。這是很有價值的新見。《懷沙》:“傷懷永哀兮,汩彼南土。”“傷懷”爲同義複詞。清林雲銘《楚辭燈》云:“言久放傷哀,欲沉於此。乘此水大之時,由遷所而往也。”*林雲銘《楚辭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29。從“懷沙”篇名來看,漢初對楚文字的隸定不算錯,因爲楚文字“”本來就具備“沙”、“徙”兩種音義,釋爲“懷徙”從而使篇題與文本結合得更爲緊密。但禤健聰認爲:“由《懷沙》篇題含義的確認,可知將《懷沙》視爲屈原的絶命詞是缺乏理據的。”*禤健聰此文原載《文史》2013年第4期,以同名收入氏著《戰國楚系簡帛用字習慣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年,頁555。那麽,除《懷沙》之外,還有哪篇詩爲屈原的“絶命詞”,禤健聰没有給出答案。《史記》本《懷沙》詩云:“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前文已論“含憂虞哀”之“含”當作“舍”,“舒”義。《集解》:“王逸曰: 娱,樂也。大故謂死亡也。”《懷沙》“亂曰”:“定心廣志,餘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嘆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史記》卷八四,頁3018—3019。可見屈原在詩篇中已經表達了決絶赴死的態度。禤健聰據楚文字將“懷沙”釋讀爲“懷徙”,是很有價值的新見,可證《懷沙》出自屈原手筆;但藉此否定《史記·屈原列傳》以《懷沙》爲屈原絶命詞的結論,就顯得證據不足了。
從對《史記》本《懷沙》與傳世《楚辭章句》本相關字詞的比較研究,可知司馬遷《屈賈列傳》采用的是漢初隸變後的楚辭文本,並不是戰國楚文字寫本。若以屈宋等戰國楚文字寫本爲“祖本”的話,那麽這一隸變文本充其量可稱爲“宗本”。
二 《漁父》體現了漢初輿論環境中的屈原話題
屈原在漢初輿論環境中是“話題感”很强的歷史人物。漢初思想比較自由,黄老思想盛行,“屈原話題”在黄老道家、儒家、忠臣列士、辭賦家如賈誼《弔屈原賦》以及隱士羣體中都有議論。賈誼《弔屈原賦》爲漢初作品,賦中慨嘆屈原“逢時不祥”,生活在是非顛倒、黑白不分的時代,“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史記》卷八四,頁3024。應像鳳凰一樣高翔遠引,而不是投江自殺。在漢代流傳的屈原史料中,有些與《史記》一致,如《鹽鐵論·非鞅》記大夫曰“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頃襄”,*王利器《鹽鐵論校注》卷二,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頁104。《屈原列傳》云:“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史記》卷八四,頁3014。有些材料則有别於《史記》記載,《鹽鐵論·訟賢》“文學”曰:“夫屈原之沉淵,遭子椒之譖也;管子得行其道,鮑叔之力也。”*《鹽鐵論校注》卷五,頁315。將屈原之死歸諸“子椒之譖”。《鹽鐵論》是漢昭帝始元六年(前81)二月召開鹽鐵會議的記録,其時《太史公》(即《史記》)尚未面世。大夫、文學關於屈原典故的引用或“索隱”自《離騷》,或許還有别的傳播渠道,這些談論側重義理而罕少事實。
《史記》記載譖毁屈原者早期有靳尚、上官大夫,後期亦有上官大夫及子蘭,未提“子椒”之名。關於“子蘭”“子椒”的來歷,《離騷》云:“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章句》:“蘭,懷王少弟司馬子蘭也。”《補注》引《史記》“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認爲子蘭“乃懷王少子,頃襄之弟也”,詩意爲: 本來還以爲子蘭是信得過的人物,誰知道他竟是内無誠信之實只是徒有其表罷了。《離騷》“椒專佞以慢慆兮,榝又欲充夫佩幃”,《章句》:“椒,楚大夫子椒也。慆,淫也。慢,一作謾,《釋文》作嫚。慆一作諂。”洪《補》:“《古今人表》有令尹子椒。”“覽椒蘭之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章句》:“言觀子椒、子蘭變志若此,況朝廷衆臣,而不爲佞媚以容其身邪?”洪《補》云:“子椒、子蘭宜有椒蘭之芬芳,而猶若是,況衆臣若揭車、江離者乎?揭車、江離皆香草,不若椒、蘭之盛也。”*《楚辭補注·離騷經章句第一》,頁40,41。王逸《離騷序》稱屈原“譏刺椒、蘭”,引自班固《離騷序》“怨惡椒、蘭”,*《楚辭補注·離騷敍》,頁49。由此可知,“椒”“蘭”實際喻指子椒、子蘭,非只“香草美人”之興寄而已。
作爲“好奇”的史家,司馬遷不可能無視這些“話題”而不爲屈原立傳。戰國乃至漢初,“楚才晉用”很普遍,據當時的輿論觀點,君臣與父子兄弟血緣關係不同,並没有什麽“君臣大義”,而是與朋友一樣的“選擇”關係。《郭店楚簡·語叢一》簡80、81“長弟,親道也。友、君臣,毋(無)親也”,簡87“君臣、朋友其擇者也”。*《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圖版頁83,84,釋文頁197。《史記·屈賈列傳》太史公曰:“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史記》卷八四,頁3034。這些“話題”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司馬遷的寫作風格,即抒情筆墨太多而事實不清,這似乎給“屈原否定論”留下了太多空間,《漁父》就是漢初“屈原話題”的反映。王逸序云:“《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間,憂愁嘆吟,儀容變易。而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濱,欣然自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楚人思念屈原,因敍其辭以相傳焉。”但洪興祖《補注》則謂王逸之説不可信:
《卜居》、《漁父》,皆假設問答以寄意耳。而太史公《屈原傳》、劉向《新序》、嵇康《高士傳》或采《楚詞》、《莊子》漁父之言以爲實録,非也。*《楚辭補注》,頁179。
《莊子·漁父》假托漁父給孔子上課,講授“聖人法天貴真”的思想;*郭慶藩《莊子集釋》卷一〇上《漁父》,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頁1032。而《楚辭》中的“漁父”則借黄老道給“狂狷”的屈原開出一劑“心靈雞湯”,《史記》本“漁父”云:“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隨其流”,《會注考證》:“按《楚辭》作‘搰其泥’”,今《楚辭補注》作“淈其泥”。*《史記》卷八四《屈原賈生列傳》,頁3014;《史記會注考證》卷八四,頁3232。“懷瑾握瑜”,《楚辭補注》本作“深思高舉”*《楚辭補注·漁父章句第七》,頁180。,但與《卜居》“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楚辭補注·卜居章句第六》,頁177。之“超然高舉”意思雷同,古書所謂“高舉”往往指隱居高蹈之意,而屈原未嘗有“高舉”之思。聞一多《楚辭校補·漁父》:“‘深思高舉’謂自放,與下文‘自令放’爲被放之意齟齬。《史記》作‘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於義爲長,當從之。”*聞一多《古典新義》,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年,頁443。《懷沙》“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史記》卷八四,頁3017。今本《楚辭補注》作“窮不知所示”,王逸注:“《史記》云: 窮不得余所示”。*《楚辭補注·九章章句第四》,頁143。漁父之語乃承此句而來。實際上,“漁父”講的是黄老思想的“貴因”精義。黄老學發源於戰國齊國,成爲漢初思想的主流,司馬談《論六家要旨》講論道家,云:“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又云:“其術以虚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史記》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頁3994,3997。黄老道與老莊道家是不同的,司馬談所説的道家實際上是黄老道。其主要精義爲“輕物重生”、“虚無爲本”以及“因循爲用”等。蒙文通《略論黄老學》認爲:“‘虚無爲本’是南北道之所同,故同稱道家。而‘因循爲用’則是北方道家所獨有之精義。可以説黄老之精華即在此,其最後起而能壓倒百家亦在此。”*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四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頁233。黄老道爲北方道家,老莊道爲南方道家。馬王堆帛書《黄帝書·行守》云:“直木伐,直人殺。”《稱》云:“環□傷威,弛欲傷法,無隋(隨)傷道。數舉參者,有身弗能葆(保),何國能守?”*魏啓鵬《馬王堆漢墓帛書〈黄帝書〉箋證》,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175,191。黄老教義在《淮南子·齊俗訓》中也有表述:“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于能,易爲也。矜僞以惑世,伉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爲民俗。”又云:“博聞强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敖世輕物,不污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爲民化。”*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卷一一,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417,443。“伉”同亢、抗,“高”義。屈原標榜“堯舜之抗行”,又“博聞强志,嫻於辭令”,自然成爲漢初黄老學派的輿論中心,並不爲黄老學所贊同。上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實際上是黄老道“因循爲用”的經典表述。
而《史記》本《漁父》中屈原對答體現了儒家思想因素,屈原云:“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晧晧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司馬貞《索隱》云:“汶汶,猶昏暗也。”又云:“蠖,音烏廓反。温蠖,猶惛憤。”《正義》:“温蠖,猶惛憒也。”*《史記》卷八四,頁3014。此段對答見諸《荀子·不苟篇》:“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己之潐潐,受人之掝掝者哉!”*王先謙《荀子集解》卷二,頁45。此句又見於《韓詩外傳》:“故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莫能以己之皭皭容人之混沄然。”“沄”舊作“污”,趙善詒云:“‘混污’當作‘混混’,《文子·上德》篇:‘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許維遹案:“混沄即混混也。”*許維遹《韓詩外傳集釋》卷一,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13。荀況與屈原時代相近,不可能存在某種影響關係。荀況曾授詩於浮丘伯,浮丘伯授詩於韓嬰而作《韓詩外傳》。今本《楚辭補注》下有“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四十字,*《楚辭補注·漁父章句第七》,頁180—181。太史公削之。瀧川資言《考證》云:“以直接《懷沙》賦,此文章剪裁之法。”*《史記會注考證》卷八四,頁3848。此《滄浪歌》出自《孟子·離婁上》:
孟子曰: 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樂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孔子曰: 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孟子注疏》卷七《離婁章句上》,十三經注疏本(嘉慶本),頁5914下。
據此可知“漁父”所歌“滄浪”即孟子所謂“孺子歌”。太史公之所以在引用《漁父》時删去此詩,因爲此詩出自《孟子》,不可能不爲人所知。戰國楚語與齊語語音差别很大,《孟子·滕文公下》記孟子與戴不勝談論,云:“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 使齊人傅之。曰: 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岳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莊岳”,漢趙岐注:“齊街里名也。”*《孟子注疏》卷六上《滕文公章句下》,十三經注疏本(嘉慶本),頁5898下—5899上。可見上古方音及語言環境關係之重要,而漁父歌孟子《滄浪歌》“鼓枻而去”,這種情形若出現在戰國時期的南楚就顯得有點詭異了。
據以上分析,可見《漁父》是由黄老道家及儒家著作《孟子·離婁》、《荀子》、《韓詩外傳》等書中語句雜湊勾兑而成,這一大雜燴似的散文作品怎會出自屈原手筆!王逸《章句》將其列入《楚辭》屈原賦二十五篇中很不正確。其寫作時間應在漢初,洪興祖《補注》所謂“皆假設問答以寄意耳”是一準確概括。《史記》在敍述屈原事迹時采用了這條材料,以增加敍事生動性,並不認爲這篇是屈原所作。
三 《史記·屈原列傳》的楚辭觀及闕失的記載
屈原楚辭作品早在漢初就已經“隸變”而爲人所知了,相對完整而系統的介紹非《史記》莫屬。《屈原列傳》“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史記》卷八四,頁3034。所悲之“志”當然指詩人“情志”而言。這四篇作品中,《招魂》存在諸多爭議,有屈原招懷王魂、宋玉招頃襄王之生魂以及宋玉招屈原魂,等等。但無論作者是屈原或宋玉,畢竟是戰國楚國文學作品。據筆者考證,漢初文人陸賈借鑑《招魂》中的一些手法而創作了《大招》,應用於漢高祖劉邦的大殮入殯禮上。*《〈楚辭·大招〉: 漢高祖喪禮中的招魂文本》,《文學評論》2017年第2期。《天問》可以看作長篇詩體自然史和興亡史詩,詩人面對自然、歷史接連發出一百七十二“問”,所謂“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楚辭補注·天問章句第三》,頁115。可以看作是詩人之“志”的直接表現。屈原、宋玉等詩人的作品是用戰國楚文字書寫的,在漢初經過“隸變”而成爲近體文字寫本,目前這些漢初隸變《楚辭》文句已經發現一些,如阜陽漢簡中有《楚辭》殘簡,其一爲《離騷》殘文四字,即“惟庚寅吾以降”中“寅吾以降”;其二爲《九章·涉江》殘文五字,即“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中間部分“不進旑奄回水”六字,這些字用秦漢古隸寫成。阜陽漢簡出自漢文帝時汝陰侯夏侯竈之墓。*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楚辭〉》,《中國韻文學刊》1987年總第一期。又如出土於臨沂銀雀山漢墓《唐勒、宋玉論馭賦》殘篇,整理者注:“疑爲宋玉賦佚篇。”*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貳),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頁6—7。文章開頭兩簡相對完好:
唐革(勒)與宋玉言御襄王前。唐革(勒)先稱曰:“人謂就(造)父登車嗛(攬)轡,馬汁(協)險(斂)正(整)齊,周(調)均不摯(縶),步騶(趨)兢久疾數(速),二一一三正馬心愈(愉)而安勞,輕車樂進,騁若蜚(飛)蠪(龍),免若歸風,反騶(趨)逆□,夜□夕日而入日千里。今之人則不然,白□堅二一一四……*《銀雀山漢墓竹簡》(貳),圖版頁123,《釋文》頁249。
篇題爲“唐革”(簡二一一三背)即唐勒,《史記·屈原列傳》:“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史記》卷八四,頁3020。本篇爲賦體,陳述唐勒與宋玉在楚襄王面前議論馭馬之術的高下,整理者認爲此賦爲“宋玉佚賦”。據《銀雀山漢墓竹簡情況簡介》介紹,銀雀山漢墓竹書字體爲早期隸書,估計是文、景至武帝初期這段時間内抄成的。*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頁5。《淮南子·覽冥訓》中的一段文字襲用此賦:“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爲整齊而斂諧,投足調均,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安勞樂進,馳騖若滅,左右若鞭,周旋若環。”劉文典《集解》:“王良,晉大夫郵無恤子良也,所謂御良也。一名孫無政。爲趙簡子御,死而托精於天駟星,天文有王良星是也。造父,嬴姓,伯翳之後,飛廉之子,爲周穆王御。”*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卷六《覽冥訓》,頁244。《楚辭》在《淮南子》一書中多處引用,是其重要題材來源。既然已經發現了漢初古隸寫本《離騷》、《涉江》以及《唐勒宋玉論馭賦》,清王引之已考證《史記》本《懷沙》“含”、“舍”因隸書形近而致誤,學界也應相信《史記》本《懷沙》來自漢初隸變文本。除全文照録《懷沙》文本外,《屈原列傳》對《離騷》之命名做出了最早釋義。
《楚辭》篇章往往取篇首或句中字詞來命名,如《九章》中的《惜往日》、《悲回風》取篇首字詞“惜往日之曾信兮”、“悲回風之摇蕙兮”名篇,*《楚辭補注·九章章句第四》,頁149,155。《抽思》,朱熹《楚辭集注》“與美人之抽思兮”*朱熹《楚辭集注》,頁106。以名篇,但此句《補注》本作“與美人抽怨兮”,王逸《章句》“爲君陳道,拔恨意也”。*《楚辭補注·九章章句第四》,頁139。但“離騷”命名卻不能在作品中找到直接證據。《史記·屈原列傳》所謂屈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史記》卷八四,頁3010。係出自淮南王劉安《離騷傳》。游國恩《離騷纂義》列舉自西漢司馬遷以至清代關於“離騷”的二十種説法,如司馬遷釋爲“離憂”、班固釋爲“遭憂”、王逸釋爲“别愁”等等。游先生以楚地樂曲“勞商”解“離騷”,認爲:“‘勞商’與‘離騷’本雙聲字,古音宵、歌、陽、幽並以旁紐通轉,疑‘勞商’爲‘離騷’之轉音,一事而異名者耳。”*游國恩《離騷纂義》,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6—7。“勞商”爲樂曲名,其義尚無從知曉。“勞”(來紐宵部)與“離”(來紐歌部)、“商”(書紐陽部)與“騷”(心紐幽部)雖然聲母相同或相近,但韻部遠隔,不能通轉。“離騷”之“離”通“罹”,與“離騷”類似的詞語結構如“離尤”(《離騷》“進不入以離尤”、《九章·惜誦》“恐重患而離尤”)、“離憂”(《九歌·山鬼》“思公子兮徒離憂”)、“離蠥”(《天問》“啓代益作後,卒然離蠥”,王逸注: 離,遭也。蠥,憂也)、“離謗”(《九章·惜誦》“紛逢尤以離謗兮”、《九章·惜往日》“被離謗而見尤”)、“離湣”(《九章·懷沙》:“離湣而長鞠”)等。*上引諸句見《楚辭補注》,頁17,127,81,98,123,150,142。可見釋“離”爲“罹”、“遭”都是正確的,解釋的關鍵在“騷”字上。


在《史記》中提到《離騷》、《天問》、《招魂》、《哀郢》四篇楚辭篇名,並全文收録《懷沙》文本,可見經過漢初“隸古定”以後,楚辭作品一般都有標題。余嘉錫《古書通例》認爲“古書不題撰人”,就已出土九册“上博簡”、七册“清華簡”以及馬王堆帛書等簡帛古書來看,此説很正確;但余嘉錫認爲“古人著書不自命名”則不完全對,*《余嘉錫説文獻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178,191。因爲出土戰國楚地文獻已經很多了,簡背題寫篇名如“上博簡”中的“訟成氏”(即“容成氏”)、“凡物流形”、“吴命”等都可證明先秦簡帛古書還是有篇名的,所以没有理由懷疑這五篇篇名爲戰國楚辭原有。
在參考資料有限的情況下,史家縱有“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雄才,在敍述屈原行狀及其作品時,亦難免有漏書之處,最明顯的闕失當屬於屈原晚年流放時間、地域及其楚辭創作問題。《屈原列傳》在“(懷王)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之後有一大段議論,接着敍述“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但“遷之”何處?《集解》引《離騷序》曰:“遷於江南。”*《史記》卷八四,頁3012—3014。《史記》緊接着敍述屈原在“江濱”與漁父的對話。但屈原遷所何在及遷徙時間有多長,存在大塊歷史空白。長期以來,學者相信《屈原列傳》遷於江南沅湘流域的説法,但清代蔣驥《山帶閣注楚辭》根據《哀郢》文本明確指出屈原放逐在寧州(安徽宣城)、池州(今安徽池州)之間的“陵陽”之地,“今按發郢之後,便至陵陽,考前後《漢志》及《水經注》,其在今寧、池之間明甚。以地處楚東極邊,而奉命安置於此,故以九年不復爲傷也。”*蔣驥《山帶閣注楚辭》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頁121。《哀郢》云:“當陵陽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楚辭補注·九章章句第四》,頁135。可見連屈原自己都不知道流放地“陵陽”在哪裏。據《漢書·地理志》“廬江郡”條注云:“故淮南,文帝十六年别爲國,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淮水出。屬揚州。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頁1568。陵陽漢屬廬江郡。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江南道四》“池州”條:“陵陽山,在縣北三十里。”*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八,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690。《哀郢》云:“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楚辭補注》,頁135。從詩中了解到,屈原在陵陽這個流放地一共消磨了九年時間。據游國恩先生《論屈原之放死及楚辭地理》所附《屈原年表》,爲頃襄王十三年(前286)屈原五十八歲至頃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屈原六十六歲之間。*《游國恩楚辭論著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302。這個《年表》可以看作是對其《楚辭概論》所附的那個年表的修改。*游先生早年著作《楚辭概論》有《屈原年表》的又一版本,將屈原流放陵陽的時間安排在頃襄王三到十一年(前296—前288)之間,見《游國恩楚辭論著集》第三册,頁70。游國恩先生認爲:“屈原之放,前後凡兩次: 一在楚懷王朝,一在頃襄王朝。懷王時放於漢北,頃襄王時放於江南。漢北之放蓋嘗召回;江南之遷一去不返。”*《游國恩學術論文集》,頁37。清代蔣驥認爲《哀郢》“江與夏之不可涉”實際上是頃襄王對屈原的禁令,“特逐之江外,不得越江而北耳”,*蔣驥《山帶閣注楚辭》,頁126。這是一個重大發現。不得“涉”江夏即不許回郢都之意。屈原在流放九年後,從陵陽逆江西上來到“鄂渚”之後未逾“江夏”以返回郢都,卻選擇了在沅湘流域流浪到投江自殺,可能與這條禁令有關。這一流浪蹤迹及心路歷程以及悲劇結局在《哀郢》、《涉江》、《悲回風》、《懷沙》中都有體現。《悲回風》一詩在歷史上充滿了爭議,筆者《揚雄〈畔牢愁〉與〈九章·悲回風〉的附益問題》認爲今傳本《悲回風》由兩部分組成,從開頭“悲回風之摇蕙兮”到“不忍爲此之常愁”爲屈原原作,表達歲暮飄零於沅湘流域的悽愴感受;從“孤子唫而抆淚兮”至結束爲揚雄《畔牢愁》。*《文學遺産》2017年第1期。《史記》依據漢初楚辭隸變文本及傳説材料對屈原晚年流放生活及創作情況敍述不準確,並造成了一定誤導。
四 對“屈原否定論”問題之辨正
由上文論述可見,司馬遷主要通過研究分析漢初隸變楚辭文本來寫作《屈原列傳》的,同時采用了漢初輿論環境“屈原話題”中的若干語料。除了《離騷》尚有淮南王劉安的解説,楚辭中其他作品除了文本之外就没有什麽材料可資參考了。這種情況一直到東漢王逸作《楚辭章句》時依然如此,據其《離騷敍》記載,在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之後,班固、賈逵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一作篇)闕而不説”。*《楚辭補注》,頁48。有學者竟然認爲《史記·屈原列傳》爲淮南王劉安所作,從而剥奪了司馬遷的著作權。如《史記會注考證》引董份曰:“《屈原傳》,大概漢武帝命淮南王安爲原作者也,太史公全用其語,班固嘗有論矣。”*《史記會注考證》卷八四,頁3223。類似説法又見前文引岡村繁《楚辭與屈原》之語。因此,有必要研究一下《屈賈列傳》與淮南王劉安《離騷傳》之間的關係。
淮南王劉安雅愛《離騷》,曾應武帝之請作《離騷傳》,應該説是楚辭最早詮釋者。據朱東潤先生研究,淮南王劉安來朝在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司馬遷時年七歲。*朱東潤《史記考索》,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239。《屈賈列傳》借用了一些《離騷傳》中的文字,如“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濯淖污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史記》卷八四,頁3010。班固《離騷序》云:“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敍《離騷傳》。”指出引文出自淮南王劉安手筆,評論説“斯論似過其真”,*《楚辭補注》卷一,頁1,49。又云:
“五子以失家巷”,謂五子胥也。及至羿、澆、少康、貳姚、有娀佚女,皆各以所識,有所增損,然猶未得其正也。故博采經書傳記本文,以爲之解。*嚴可均《全後漢文》卷二五《班固》,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頁611。
從引文斷定,班固讀過淮南王《離騷傳》,並截取文章段落加以評判。《史記·屈原列傳》從“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至“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史記》卷八四,頁3010。文意暢達,一氣貫注,顯係出自一人手筆。《漢書·淮南王傳》記載:“初,安入朝,獻所作《内篇》,新出,上愛秘之。使爲《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師古注:“傳謂解説之,若《毛詩傳》。”*《漢書》卷四四,頁2145—2146。《文心雕龍·辨騷》:“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頁45。然據王念孫《讀書雜誌·漢書第九》“離騷傳”條考證,“傳”當爲“傅”,“傅”、“賦”古字通,“使爲《離騷傅》者,使約其大旨而爲之賦也”*《讀書雜誌》,頁296上。。楊樹達《漢書窺管》認爲“王説非也”,“傳”爲訓詁學中“泛論體”之“傳”,“非賦體”之“傅”。*楊樹達《漢書窺管》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345—346。從班固《離騷序》引文判斷,楊説爲正。東漢王逸《楚辭章句》稱淮南王安《離騷傳》爲“《離騷經》章句”,説明這種“泛論性”的“傳”與訓詁“章句”之學基本上是一致的。《離騷傳》所謂“蟬蛻”、“浮游”實際上即方仙道所謂“尸解”“形解”,指肉體雖壞而精神解脱。《淮南子·精神訓》:“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蛻蛇解,遊於太清。輕舉獨住,忽然入冥。”*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537。王念孫考證,“住”當作“往”。*《讀書雜誌·淮南内篇七》,頁826上。淮南王劉安實際上是以神仙家思想來闡釋屈原,而在屈賦中並没有這種思想。由此看來,《史記·屈原列傳》借用了淮南王《離騷傳》的經典評述。需要明確的是,司馬遷是在評價屈原《離騷》作品時引用淮南王劉安《離騷傳》的,根本不足以據此懷疑《屈原列傳》的真僞問題。
其次,《屈原賈生列傳》是否爲太史公所作問題,須作進一步辨正。
胡適《讀〈楚辭〉》注意到《史記·屈賈列傳》“太史公曰”以上,有這麽一段話:“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史記》卷八四,頁3034。胡適認爲:“司馬遷何能知孝昭的謚法?一可疑。孝文之後爲景帝,如何可説‘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二可疑。”*《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上),頁291。汪春泓先生《讀〈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獻疑》認爲這段文字應是西漢晚期劉德、劉向等人所作的證據,“與余通書”之“余”蓋非司馬遷,而是漢昭帝時擔任“宗正”要職的劉德。*汪春泓《史漢研究》,頁147。該文徵引了一些有價值的證據,如論“三閭大夫”與“宗正”之間的關係,引述宋代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一一《考史》説:“王逸《注楚辭自序》云: 屈原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三閭之賢者,忠於宗國,所以長久。”*王應麟《困學紀聞》,翁元圻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1314—1315。與“三閭”之職相對應,漢朝爲“宗正”,而楚元王子孫劉辟彊、劉德、劉向都擔任過“宗正”一職。汪先生認爲劉向編撰《新序·節士》“屈原章”早於《史記·屈原列傳》,《屈原列傳》是劉向在此基礎上編撰的。*汪春泓《史漢研究》,頁143。認爲“今本《屈原列傳》卻存在背離司馬遷初衷的大竄改”,“從君臣觀看太史公與賈誼的分歧”、“從宣帝時代崇‘文’貶‘武’的思潮考察《屈原列傳》的作者”以及“從社會身份、經濟處境來分析漢代的屈原論”等,基本上屬於“推斷”,在政治思想史範圍内結合史料進行論述,也給人一些有益的啓發,但文獻證據卻嚴重不足。
前文研究司馬遷是根據漢初隸變楚辭文本來寫作屈原傳記的,《史記》本《懷沙》與在西漢晚期劉向整理基礎上形成的王逸《章句》本存在異文四十多處,前人忽略了兩種不同時期楚辭文本的差異,其懷疑論立場就站不住腳了。胡適所謂“二可疑”前人早已解釋清楚了,清代梁玉繩認爲:
此文爲後人增改。“孝武”當作“今上”。而中隔景帝,似不必言“孝文崩”,宜云“及今上皇帝立也”……“至孝昭時”二句當删之。《唐表》誼子名璠,璠二子嘉、惲。*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三一,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1307。
由此可知,“及孝文崩”一段當爲後人附益。事實上,《史記》中爲後人附益多處,然若探討這些附益之事,先要明確《史記》記事最終截止年限問題。《史記·太史公自序》云:“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黄帝始。”《集解》引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爲述事之端。上紀黄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索隱》引服虔云:“武帝至雍獲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故云‘麟止’。遷作《史記》止於此,猶《春秋》終於獲麟然也。”*《史記》卷一三〇,頁4006。《漢書·揚雄傳》云:“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漢書》卷八七下,頁3580。《後漢書·班彪傳》云:“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采《左氏》、《國語》,删《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黄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後漢書》卷四〇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1325。武帝獲麟在元狩元年冬十月(前122)。鄭鶴聲認爲:“孔子作《春秋》訖於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史記》竊比《春秋》,時亦適有獲麟之事,故所記以此爲終限。然則《武帝本紀》當敍至元狩元年十月止,年表、世家、列傳稱是,凡此年以後之記事,皆非原文,此標準宜爲最可信據者。”*鄭鶴聲《史漢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影印,2014年,頁30—31。
但《史記》記載“元狩元年”(前122)以後之事甚多,因此對《史記》敍事之最終年限尚有不同説法。據鄭鶴聲研究,約有三説:
(一) 訖太初(前104—前101)説。《太史公自序》最末一段云:“余述歷黄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史記》卷一三〇,頁4029。《漢書·敍傳》:“太初以後,闕而不録。”*《漢書》卷一〇〇下,頁4235。若訖太初四年,則逾麟止之限二十二年。
(二) 訖天漢(前100—前97)説。若訖天漢四年,則逾麟止之限二十六年。《漢書·司馬遷傳贊》云:“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校勘記引楊樹達説,“大漢”無義,當作“天漢”,天漢,武帝年號。*《漢書》卷六二,頁2737、2739。楊樹達《漢書窺管》,頁480。
(三) 訖武帝末説。《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末附“後進好事儒者褚先生曰”:“太史公記事盡於孝武之事,故復修記孝昭以來功臣侯者,編於左方。”*《史記》卷二〇,頁1257。武帝最末一年,爲後元二年(前87),若訖於此,則逾麟止之限三十六年。*《史漢研究》,頁31。
上述諸説,當以《太史公自序》所謂“余述歷黄帝至太初而訖”爲準,太初四年(前101),司馬遷時年四十五歲。朱東潤先生認爲:“班固、司馬貞、張守節並云‘止於天漢’,蓋讀後人改修之書也。”*朱東潤《史記考索》,頁247。《史記》一書漢宣帝時纔面世,《漢書·司馬遷傳》:“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佈焉。”*《漢書》卷六二,頁2737。書出以後,頗爲後人附益,瀧川資言《考證》卷末《史記附益》歸納有三十四處之多,其中就包括《屈賈列傳》卷末部分,《考證》云:“《賈生列傳》卷末‘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孝武’宜作‘今上’,‘至孝昭時列爲九卿’八字,後人附益。”*《史記會注考證》,頁4421。據此可知,胡適等人之説根據不足。
汪春泓先生《讀〈史記·屈賈列傳〉獻疑》一文主要論據與胡適相同,而認爲《屈賈列傳》爲劉向、歆所作,那麽就來探討一下是否存在這種可能性。
《太史公自序》:“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史記》卷一三〇,頁4022。《史記》初名《太史公》,《漢書·司馬遷傳》“爲《太史公書序》”下,王先謙《補注》引錢大昕曰:“案太史公以官名書,桓譚云: 遷著書示東方朔,朔署曰‘太史公’。署之者,名其書也。”*王先謙《漢書補注》卷三二《司馬遷傳》,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1236上—下。語見錢大昕《廿二史考異》“爲《太史公書》”條下,錢云:“‘史記’之名,疑出魏晉以後,非子長著書之意也。”*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五《史記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89。《漢書·敍傳》:“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漢書》卷一〇〇上,頁4203。“大將軍”即王鳳。《史記》有闕文,《漢書·藝文志》“春秋家”類:“《太史公》百三十篇。”自注:“十篇有録無書。”*《漢書》卷三〇,頁1714。《漢書·司馬遷傳》全録《太史公自序》及《報任安書》,云“《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又云“遷之自敍云爾。而十篇缺,有録無書”,張晏曰:
遷没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漢書補注》卷三二《司馬遷傳》,頁4352。
余嘉錫《太史公書亡篇考》*《余嘉錫論學雜著》上册,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103。基本就張晏所説“十篇”立議,未聞亡《屈原賈生列傳》者也。太史公所謂“《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是《史記》宏大敍事結構中的重要一環,史無記載這篇是由後人補苴的。若單純依據思想史的方法,推斷《屈賈列傳》爲劉向等人所作,可能會有很大局限。在文獻中還找不到直接證據足以否定《太史公自序》以及《漢書·司馬遷傳》中的相關記載。與此相反,文獻中倒有證據證明劉向、歆父子撰寫《屈賈列傳》之不可能。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云:
《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録。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至建武中,司徒班彪以爲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僞新,誤後惑衆,不當垂之後代者也。於是采其舊事,旁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劉知幾、浦起龍《史通通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314。
《後漢書·班彪傳》:“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録,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李賢注:“好事者謂楊(揚)雄、劉歆、陽城衡、褚少孫、史孝山之徒也。”*《後漢書》卷四〇上,頁1324—1325。由此可知,“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只是“上以續史公”即續《史記》,而對《史記》文字“無所增損”,《史記會注考證》列舉三十四處後人附益文字,可能出自這些“續史記”人物之手。劉歆曾被王莽封爲“國師”,班彪認爲“誤後惑衆,不當垂之後代”,爲世人不齒,若《屈賈列傳》爲其所作,班彪、班固豈有不知之理?因此,汪春泓先生所謂“《屈賈列傳》爲劉德、劉向或劉歆所作”這一觀點有待於文獻證明。
《史記·屈原列傳》是惟一一篇先秦楚國文學家的傳記,傳主屈原命運悲慘,幾乎一輩子處於貶謫流放途中,在原典性的戰國史書中基本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司馬遷生在屈原之後一百七十年左右,也没有見到過戰國楚文字寫本的楚辭作品,在漢初直至武帝時期的輿論背景下,通過研究漢初隸變楚辭文本資料敍述屈原行狀,在《楚世家》中適當安置了屈原“使齊”歸來勸諫楚懷王的情節,但這一安排是不可信的。同時,采用了淮南王安《離騷傳》這一最早闡釋文本,傳記中抒情議論的筆墨多而事迹敍述少。因此,《史記》屈原本傳雖然是最具原創性研究的傳記資料,但其留下的大量空白也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最明顯的就是屈原晚期流放到“陵陽”度過九年的生活和創作,史家没有記載。
宋代黄伯思《校定楚辭序》云:“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物,名楚地,故可謂之楚辭。”*黄伯思《東觀餘論》卷下,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0年,頁179。單憑所謂“楚語”、“楚聲”、“楚物”、“楚地”還不能斷定作品的時代是先秦屈宋還是漢朝人所作的,最重要的應該是“用楚字”,先秦楚文字與漢初隸變古文截然不同。現在戰國楚文字寫本文獻已經成篇成卷的出版了,學者對其已經有了非常直觀的認識,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那麽,司馬遷是否閲讀過戰國楚文字寫本文獻?答案應該是否定的。
《史記》史家論贊往往提到該傳記的材料來源,《五帝本紀》“而《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馴”,又云“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史記》卷一《五帝本紀》,頁54。《夏本紀》主要依《尚書·禹貢》來敍述。《殷本紀》“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於《書》、《詩》”,*《史記》卷三《殷本紀》,頁140。其敍述商代帝王世系多采《世本》。《秦本紀》以《秦紀》爲主。《吴太伯世家》“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句吴兄弟也”,*《史記》卷三一《吴太伯世家》,頁1781。《考證》云:“《春秋》古文即《左氏春秋傳》,劉歆《與太常博士書》、許慎《説文敍》可證。”*《史記會注考證》卷三一,頁2105。《衛康叔世家》“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云云,*《史記》卷三七《衛康叔世家》,頁1940。“世家”即《世本》。《屈賈列傳》“余讀《離騷》、《天問》、《哀郢》、《招魂》,悲其志。”*《史記》卷八四,頁3034。從上文對《懷沙》的分析,可以推測這四篇楚辭也應該是漢初隸變文本。從以上這些記載可以看出,除了提到“《春秋》古文”之外,司馬遷基本上是以漢初隸變古書傳抄而來的寫本文獻來展開《史記》寫作的,屈原作品也概莫能外。如果司馬遷能够閲讀到戰國楚文字寫本,其《屈賈列傳》的敍述一定會别開生面的。同理,我們今天能够了解到這些戰國寫本文獻,新材料帶來新學問,對屈原及其楚辭作品的研究也一定會有新的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