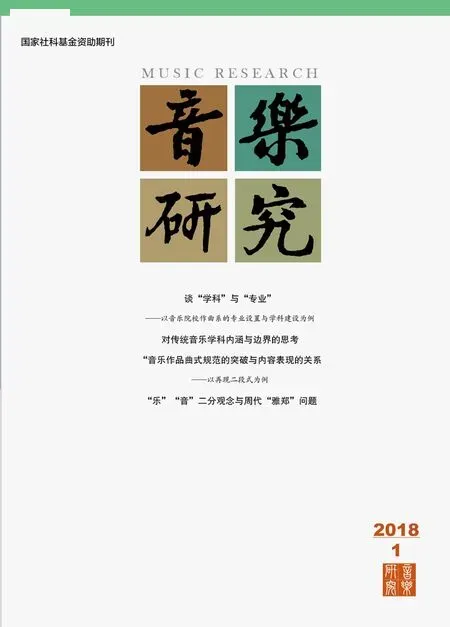“物”化的南音—印尼东方音乐基金会“南音人”口述史研究
2018-05-17陈敏红
文◎陈敏红
南音历史源远流长,主要流行于闽南及中国台湾、南洋群岛华人居住地区,被誉为汉族传统音乐文化的“活化石”。南音融合了中原宴乐、西域音乐及周边方国音乐的特点,是在汲取闽南地方性音乐文化特色基础上形成的,其特性之“和”决定了南音活动的集体性,它以“馆阁”的形式延续至今。近年来,相关学者已经对非物质文化与物质文化在边界、概念、定义上做了一定论述。本文的研究重点是把南音作为一种“物”,试图将物质文化研究的范式引入到南音研究中来。“物质文化”,从一开始就与物的言说者“人”产生了密切联系。20世纪初的社会学理论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确立了“礼物”之中蕴含的超越性意义,从而奠定了物的社会学内涵。①〔法〕马塞尔·莫斯著,汲喆译《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20世纪60年代,结构马克思主义者复兴了经典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见解,启发人类学家以物的生产过程来理解商品的内涵,重构对资本主义的反思。著有《消费社会》的让·鲍德里亚就是其中代表,他旗帜鲜明地宣称,“我们总是靠主体的光辉和客体的贫穷生活”却“没有人声称客体的命运”②〔美〕比尔·布朗《物论》,载于孟悦、罗钢主编《物质文化读本》,第81页。。物质文化的研究在20世纪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相继有学者如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和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等人,都试图在60年代理论反思的基础上复兴“物”的“社会生命史”研究。
笔者五次深度采访印尼东方音乐基金会,③五次深度调研分别是:中国·印尼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年11月7—10日);第二届世界联谊大会唱暨东方音乐基金会成立三十周年庆典(2013年10月29日—11月1日);2014年7月7日—8月3日,前往印尼东方音乐基金会进行田野调查;2015年11月2—4日,第十一届中国泉州国际南音大会唱暨永春南音大楼(陈秀峰纪念堂)落成20周年庆典,并随赴晋江、石狮、厦门等地进行社团交流;2016年2月12—16日,前往印尼东方音乐基金会进行田野调查。对基金会主席、资助人、社团创办人以及新一代南音人等代表性人物陈锡石、陈淑宝、蔡金娘、张武勇、李长旗、吴丽凤、吴文焕、洪清河和蔡宴莹等人进行了长时段跟踪采访。在基金会历史源流、发展概况、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印尼南音的局部传播、印尼南音教师基本情况、基金会的日常活动以及被采访者人生经历等方面获得了宝贵的口述资料。在海外南音传播的实地考察中,深刻感受南音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人”“物”的诸多联结,其在“人的书写”和“音声为记忆”的构建中,呈现“物的社会生命”。如同彭兆荣、葛荣玲在《南音与文化空间》一文中认为的那样,南音与其文化空间密不可分,“南音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表现非单一性类型的表述形态,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文化空间’案例。”④彭兆荣、葛荣玲《南音与文化空间》,《艺术探索》2007年第4期。然而,南音作为“物”的内涵不仅能够通过空间理论加以阐明,更重要的是,把南音视为主体的研究能够还原其独立自在的“社会生命”,从而使其具有深刻的社会学内涵。那么,如何透过“口述史”的方法论呈现“南音在海外传播的历史表述”,以此追溯“南音人”的生命历程,关注南音海外传播的路径、流变、精神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同时,在海外具体个案的社会情境中去看待南音作为“物”的社会生命历程,思考是什么因素决定其生命的流动,通过南音的交流和展示体现了什么样的社会价值,作为“物”的南音如何凝聚了社会和历史的变迁则是本文所关注的。
一、印尼东方音乐基金会“南音人”口述史
(一)漂泊的“南琶”情怀
东方音乐基金会会长陈锡石先生,⑤采访时间:2016年2月15日;采访地点:陈锡石于印尼雅加达的家中(JC.KANO INDAH 3 NO1-3)。1935年出生于福建永春,15岁时随母亲远赴南洋与父亲团聚。其父陈秀峰,1917年生人,19岁侨居雅加达,一生爱好甚广:擅歌舞,兴乐器,养信鸽,藏名画,下象棋……共获得过430多个奖杯,120多个奖牌。陈秀峰小学的时候在家乡学过南音,移民后经常在自家天台上玩南音。他擅于演奏南音琵琶,在雅加达,他的琵琶演奏是一流的,尤以“捻指”⑥捻指,南音琵琶基础弹奏指法之一。为佳;虽也会吹洞箫、拉二弦,后来由于肺部劳损,便不再吹箫。据陈锡石回忆,他父亲来南洋的时候虽没带手抄曲谱,但凭借良好的记忆力,虽远赴南洋十数载,《春今卜返》《梅花操》《四时景》等曲目无需曲谱仍可演奏。那时由于没有带“傢俬”,南洋的南琶质量较差,陈秀峰嘱咐陈锡石由家乡捎来南琶。遗憾的是,颠簸的路途造成这把南琶和漂泊的乡民一样命途多舛,先是在骑脚踏车的时候被碰断了南琶头,刚在厦门接好,又在赴印尼的途中碰断了“凤头”。这一事件成为陈锡石一生少有的憾事,也是陈先生开始执着于南音的一个重要节点。
1949年,陈锡石开始在印尼当地就学。家底殷实的他,后来兴办了染料、房地产和旅馆等产业。他曾在永春听过南音,但是没有机会学。50年代定居南洋后他参加了“同益社”(社里主要有南音、梨园、高甲、京戏、古装戏等),并学习笛子,演过《陈三五娘》《陈若霖斩皇子》《莲花庵》《十五贯》《红灯记》等,如扮演过《陈三五娘》故事中的林大、《陈若霖斩皇子》中的皇子、或者反派角色。1965年,囿于时局,“同益社”解散。直到1983年参加印尼东方基金音乐会,他才开始学洞箫,学会吹奏《出庭前》《鱼沉》《梅花操》《五湖游》《三台令》《走马》等,自己也会唱几首南音,但不太敢唱。1985年中风后,他没有继续吹奏和演唱,但他对南音的热爱却没有间断过。
东方音乐基金会从成立至今,除传承南音之外,还要做社会工作、慈善事业、免费医疗等。请了十几位南音老师,第一任是台湾的卓圣翔,然后是马香缎;紧接着是黄清标、吴淑珍,再后来是龚锦绢和江培玲;厦门乐团成员王小珠,因泉、厦两地唱法不同所以只教了大约一年;苏诗咏教得最久,长达六年多;接着是惠安杨秋兰、南安李真棉(在马来西亚教了两年);然后是丁信坤(早前在菲律宾任教),他会的很多,包括44套全部指、谱及曲子一百多首。东方音乐基金会的成立还得益于早期南音在印尼比较活跃,仅芭城就有15个南音会馆:万隆市、苏佳巫牟、楠榜、泗水、井尼文、三宝垄、玛琅、安班南、望佳锡等地都有。
(二)政策骤变的南音日常活动
东方音乐基金会副主席陈淑宝女士,⑦采访时间:2016年2月14日;采访地点:陈叔宝雅加达旧家(原印尼东方音乐基金会旧址:JC PEJAGALAN I NO:35C)。1930年出生于晋江安海,17岁时与颜呈茂结婚,次年丈夫独自先去印尼。颜呈茂长淑宝3岁,在中国国内时就喜欢南音,其三伯是“西垵”的“倚馆先生”,当时尚在读书的他,虽未习南音,但在田间劳作时耳闻伙伴念唱《听门楼》之类的南音,久而久之,也能哼唱一点,从而迈入了“玩”南琶和三弦的大门。1955年妻子陈淑宝侨居印尼后,他愈发喜爱南音,只要有“傢俬脚”就拉来家里玩,他还在工作和生活上支持、帮助他们,后来家里也越来越热闹,他也因此积累了很多曲目。1966年,政策骤变,按规定禁止两个以上中国人聚集。颜家隔壁的永定会馆虽被印尼海军陆战队占领,但因队员和他们关系极佳,弦友照例可以日日聚集玩唱南音。若有人阻止,海军便出面维护。在东方音乐基金会会馆成立之前,诸多弦友都是在颜家玩南音;遇上大日子,来者众多,淑宝还会和家佣煮“半瞑粥”(夜宵)招待,能坐满足足两桌。有时玩南音的“傢俬脚”太多,一直没有机会玩的人就会吵架,这时颜呈茂就会劝他们和好,一人再拉首曲子,大家又开心了。由于“唱脚”极其缺乏,所以大部分女人都只学唱,没有学乐器,当年痴迷于南音的廖大安、潘贵、林志良、王鱼颠如今皆已过世。
陈淑宝受丈夫的熏陶,35岁时开始学习南音。她的第一个南管先生是祖籍永春的廖大安,学的第一首曲子是《阿娘听女间》。年轻时学得勤奋,即使是多年不唱的曲子,直至今日仍能背唱,现还会唱的曲目有《听见杜鹃》《泥金书》《见只书》《梧桐叶落》《听爹说》《书今写》《赏春天》《莲步轻移》《不良心意》《年久月深》《随君出来》《我为乜》《孤栖闷》《一身》《直入花园》《风打梨》《于我哥》《但得强企》《当天下纸》《春光明媚》《我为你》《三更人》《三更时》《夫为功名》《一路安然》《冬天寒》《因送哥嫂》等。廖大安最初在同益社弹南琶,作为“倚馆先生”,到家中教学,从不收费,除了教南音,他还有另外的工作。第二个老师是祖籍南安的洪草茹,也有其他的工作。他们两个过世后,就没有老师了,所以会馆一直想从“唐山”找先生。
1983年印尼东方音乐基金会成立,成员中手头有钱的提议要购买一间会所,王仁忠、林志良、颜呈茂三人带头,在雅佳兰街道购买了一小块地并盖起房子作为会所,会员们延续中国人的传统供奉关帝爷。2008年新会所建成时,大家一致同意将关帝爷请到新址。林志良作为发起人被选为会馆的第一任主席,他痴爱南音,也非常热心,且号召力强,回中国的手续都是他负责张罗,并为许多经济困难的弦友解决了来回路费。会所成立前夕,回中国参加南音活动时,二十余人在香港入不了关,经林志良前后运作才得以顺利解决。陈淑宝回忆,1981年、1984年、1988年中国泉州国际南音大会唱,因其他人都是“傢俬脚”,唱曲的较少,每次她和深林婶及金娘都参加。在1988年的照片里,还能清楚看到泗水、东爪哇等社团的锦旗,如泗水的寄傲圣道社,现在这些馆都已消失。
(三)贯穿生命礼仪的南音缘
东方音乐基金会财务总监蔡金娘⑧采访时间:2016年2月15日;采访地点:蔡金娘于印尼雅加达的家中(JC MUARA KARANG BLOKJ 6S/14)。,1953年出生于印尼茂物,祖籍晋江紫帽。其祖父在年轻的时候开始下南洋谋生,先后娶了两位夫人(第一任夫人留在了中国,第二任夫人是其祖父下南洋后娶的)。父亲在中国出生,十几岁时被爷爷带至印尼,回到中国后与祖籍晋江池店的母亲结婚。金娘本名志亭,因命里缺金,小时候又经常生病,所以祖母将其改名为蔡金娘。她的丈夫来自汕头潮州,在印尼的加里曼丹岛出生,十八岁起在雅加达生活。
南音,可以说和蔡金娘的一生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她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的父亲虽不会南音,但喜欢听。九岁时她与母亲一同学习南音。第一位南音老师是蔡长庚。蔡老师会弹南琶,还会自己抄曲谱。他每周至少来两次,会馆现在还保存着他抄的曲本复印件。蔡金娘和丈夫是在淑宝家玩南音时认识的。他们的订婚仪式、结婚仪式和三个孩子的满月宴席,都有弦友到家里玩南音。蔡金娘擅于演唱,一个晚上可以唱好几首,而“傢俬脚”就要轮着来,或者同一种乐器一起演奏。
蔡金娘早前并不插手会馆的事情,专门唱曲。⑨目前还能演唱的曲目:《非是阮》《元宵十五》《拜告将军》《怜君此去》《看你行宜》《因送哥嫂》《为伊刈吊》《岭路崎岖》《告大人》《特来报》《遥望情君》《鱼沉雁杳》《春光明媚》《望明月》《出画堂》《把鼓乐》《三更鼓》《共君断约》《直入花园》《轻轻行》《听见雁声悲》《满空飞》《孤栖闷》《一身》《风打梨》《远看长亭》《见只书》《木兰词》《空思断肠》《汝因势》《花园外边》《鱼沉》《出庭前》《南海赞》等。后来由于母亲身体的原因,从旧馆搬迁到新馆时,她就开始帮忙处理会馆事务。金娘说“不帮忙的话,妈妈的心血就没了,二十五周年庆要建新工会时,买地、建房都是我在执行。”会馆的收入主要来自成员的月捐和农历五月十三的“选炉主”。月捐主要用于平时的开销,包括人工费、请老师费用、餐费、水电费、敬神、学生来学习的费用等。⑩每次签到,发人民币50元/月。炉主通过“博杯”选出,一般会有十几个。选出的炉主名单会写在红色的纸上,贴在关公旁边的墙壁上。2016年选的是陈锡石和魏耀坤。除此之外,还有应酬和“选炉主”。福建会馆活动、出国等大型活动费用主要用炉主的捐赠,以及会馆原有基金存款利息支付。
提起陈主席,金娘笑着表示,锡石先生热衷举办各式活动,已经在印尼和永春举行了三次南音大会唱。他对南音非常执着,每年都会列一份名单,交代给南音老前辈们(吴世安、陈育才、苏诗咏等人)汇钱,以感谢他们对南音的支持。同时,为了南音弦友能够经常相聚,他经常个人出资或集资举办大型南音活动,由蔡金娘和李长旗负责活动的具体事务。比如在家乡永春举行的第十一届泉州国际南音大会唱暨陈秀峰纪念堂⑪陈秀峰纪念堂是陈锡石为纪念其父,私人出资建造的。落成20周年庆典上,为助力此次活动,陈锡石个人出资四个M(约200万人民币)和政府联合举办活动。
(四)四代人的南音邂逅
东方音乐基金会总务李长旗先生,⑫采访时间:2014年7月20日;采访地点:印尼东方音乐基金会会馆新址(JC PLUIT BARAT IV NO.1)。生于1966年,经营和化学产品有关的公司。其父李增泉,1938年出生于峇眼,祖籍同安,现居井尼文,做食品生意。早期峇眼南音都是老人在唱,基本上唱大曲如《山险峻》《不良心意》《为伊割吊》,还有很多曲目晦涩难懂。李增泉由于父亲是看曲馆的,受南音影响颇深。起初主要听录音带,如《陈三五娘》《绣成孤鸾》《年久月深》《三哥暂宽》《早起日上》《共君断约》等曲子。1970年以来,于当地曲馆学南音演唱,《不良心意》《山险峻》《因送哥嫂》《出汉关》《元宵十五》《梧桐叶落》《班头爷》《早起日上》《阿娘听女间》《共君断约》《三千两金》等曲目信手拈来。由于井尼文没有社团,他就坚持坐三小时火车到会馆唱南音。2014年,吴重洋夫人逝世的时候,李长旗与父亲去殡仪馆奏唱南音,父亲唱了好几首,还演奏了指尾《出庭前》、谱《梅花操》等。
李长旗2010年开始学习南音,本来并不喜欢,但是每次要送父亲到会馆玩南音,有次因为下雨不得不留下来听,觉得南音也不难听,所以开始学习。李长旗先跟随苏诗咏老师学,会背十几首,如《阿娘听女间》《共君断约》《直入花园》《风打梨》《一间草厝》《望明月》《女间随官人》《元宵十五》《心头伤悲》《偷身出去》《劝爹爹》《鱼沉雁杳》《师兄听说》《看你行宜》《出庭前》《鱼沉》等。妻子吴丽凤,1973年出生于峇眼,祖籍厦门同安,不懂汉字,小时候也没听过南音,但2009年与三个儿子⑬李长旗有三个儿子,李恒龙、李恒吉和李恒文,均在学习南音。一同学习,慢慢地也喜欢上了南音。她先后跟随苏诗咏、蔡维镖、杨秋兰老师学习唱《劝爹爹》《直入花园》《偷身出去》《年久月深》《心头伤悲》《班头爷》《恨冤家》《正更深》等。
李长旗的妻子平时还负责会馆里的“佛”事务。每逢月初一、十五以及二月十九日、六月十九日、九月十九日“观音生”,吴丽凤会去买水果和鲜花,祀神之后把这些水果装袋分发给主席团和员工,以示平安。每年正月初九日,福建人“敬天公”,会馆会摆桌大敬;五月十三日是“关公生”;五月十二日会唱《南海观音赞》,会馆会买水果、鲜花、蒸发糕、甜品作为贡品。在活动开始一个月前,公会会先选拔“炉主”,到了“关公生”当日,会请和尚来念经,“做敬”,结束后同样把水果、发糕等送去“炉主”家里;二月十二日、八月十二日“郎君生”,也都会“做敬”。此外,如十二月二十三日“送神”、正月初四“接神”等一些传统农历节日,会馆也都保留得比较完整。
二、南音作为“物”的社会生命历程
每当问起印尼东方音乐基金会老一辈南音人为何学习南音、为何成立会馆,他们总是回答,“因为那是父辈从家乡、故土带来的记忆”。这种表达,反映了闽南人眼里视南音为“家族的音乐”“家乡的音乐”“家的音乐”,是联结家乡之“魂”。其作为“物的流动”,在交流、馈赠、互动中冲破音乐符号的界限,以闽南人特有的方式在印尼社会动荡的土壤中,得以固执地坚守和传承。
(一)会馆空间构建的多重功能
会馆一楼的“关帝宫”,供奉关公、菩萨、土地公等神仔,在佛堂的右侧还放有“签诗”的柜子,香客许愿抽签,可照签号自行找到签诗解签。会所佛务组逢每月初一、十五日,正月初九日、二月十二日、二月十九日、五月十三日、六月十九日、八月十二日、九月十九日等“天公生”“观音生”“关公生”以及“郎君祭”等重要日子,均会置办鲜花、水果,举行隆重或简单的祭拜仪式。2016年农历正月初九日,与“故乡”习俗一样,基金会举行“敬天公”仪式,首先对佛堂进行“布置”,在最大的香炉两旁绑上两根“有头有尾”的甘蔗,在神龛前摆上多张供桌,供会所及香客放置贡品。会所的煮饭阿姨蒸二十几个漂亮的“发糕”,准备“三牲”“红蛋”,佛务祖的吴丽凤夫妇购买水果,并将水果叠成锥状固定,做成一个个的水果塔,同时,购买一些包装及做工特别精致的闽南特色甜馃、碗糕等作为贡品。
“关帝宫”对于印尼东方基金会几位创办者来说是南音在印尼特殊时期承续的“幌子”。1966年印尼排华,取缔了华人社团,使许多印尼南音社团遭到重创,由显性形态逐渐转向隐性形态。1983年印尼排华结束,会馆以祭祀地方神的宗教组织和音乐会社的名义,向印尼文化部和宗教管理机构正式申请到“东方音乐社”和“关公宫”两个批文,后又改为“印尼东方基金会”。笔者透过两次直接田野观察,发现该“宫庙”的信徒并不多,甚至十几天也未见“抽签”的人。但采访中多位创办人均对“关帝宫”的“灵”性深信不疑—他们认为“关帝宫”是南音的“靠山”,是海外华侨“乡音”承续的关键。基金会举办两次南音大会唱 “请佛”踩街活动和“选炉主”仪式,此在发源地泉州以及流播地区比较少见。“迎神”“选炉主”是地方民间信仰的仪式,它保留了闽南地方民间信仰的基本符号。在印尼特定的地方社会中形成特殊的传播形态,为印尼东方音乐基金会筹集基金、开展南音活动以及慈善活动奠定坚实的基础。南音以关帝信仰、民间宗教仪式为依托得以生存和发展,体现了作为“物”的南音所具有的社会生命。它内化在民间宗教的周期性仪式活动中,寄托习南音者丰富而饱满的情感,传递着通天的“灵”性在音乐中的持久表达。

图1 “敬天公”仪式摆设
印尼教育体系中一个很特别的校外教育方式,就是寺庙承担教育的功能。每周日上午,一批来自学校的学生,在教师的带领下到会馆“念经”,每次有十几个学生参与,一般持续时间两个小时。他们摆上会馆为活动准备的贡品和鲜花,以及释迦牟尼造像,席地而坐就开始了。教师在这样的空间中进行人生教育和知识的传授,根据学生签到的次数给予分数或学分。社区或学校定期举办“念经”比赛,学生都积极参与,在刻有“Liam Keng”的奖杯上,我们看到了印尼人对闽南语音标识的认同。活动结束后,会馆还为学生提供午餐,接着二楼南音空间的南音常规活动就开始了。
“关帝宫”的慈善活动显示出当地华人与印尼社会之裂痕正逐渐被弥合,更多印尼当地人对华人华侨的接受度逐年提高。不管是特殊时期的“幌子”,还是“寺庙”功能,或者是印尼社会“传统”教育空间,抑或会馆“选炉主”场域,南音在带有庙宇符号的空间中与闽南人、印尼人、华人相互勾连,佛缘、音缘、亲缘、地缘在“关帝宫”多重功能下折射出南音作为音乐、作为文化、作为祖先“灵”的多面性,在其移居地和祖籍地之间摇摆前进。
(二)印尼南音的“生命”流动
“走回去”和“引回来”是印尼南音传播的一个特质。“走回去”,回到哪里?祖籍地。在口述中,金娘第一次通过林志良的安排,从雅加达到香港再转回华人口中的“唐山”,对其间所历千辛万苦的描述,那种不言而喻的兴奋洋溢在他们的脸上,带着在“异乡”学习的乡音,又回到家乡。就如基金会主席陈锡石所言:“在我心中,南音是一种很好的音乐。海外游子若能记得它,就会总想回家乡。”
自2012年以来,印尼东方音乐基金会每年都回到泉州,或参加大会唱,或参加表演,或与民间社团进行交流,他们走访与之联谊的社团,如安海雅颂南音社、鲤城区南音社、石狮南音研究社、同安银安堂南乐研究会、永春南音社、德化南音社等,并进行交流。这些社团均摆宴设席、互赠礼物,进行南音交流,在交流中形成良好的兄弟情谊,也在交流中完成“礼物”的馈赠。南音超越了“交流”意义的文化符号,成为文化通道,使得海外与故土的情感得以联结。南音也正是在这一文化通道的频繁“流动”之中形塑自身。1995年,会长陈锡石和其叔陈秀明回到永春,以父亲陈秀峰的名义建了一座纪念堂,成为永春南音社活动场所,还举办了世界永春南音大会唱。2015年11月2—5日,由陈锡石出资举办的“第十一届中国泉州国际南音大会唱暨永春南音大楼(陈秀峰纪念堂)落成20周年庆典”,有五个国家43个团体参加,改变了以往祖籍地南音大会唱由政府出资的局面。在他们的传承意识中,依然保持与发源地家乡的音乐内容、形态的一致性,使南音在异乡的传播,即使阻隔几十年,回到祖籍地依然无需排练,拿起各自“傢俬”就能开始合奏、吟唱。

图2 印尼东方音乐基金会参加第十一届中国泉州国际南音大会唱彩街活动⑭ 时间:2015年11月2日;地点:泉州永春。陈振梅摄。
第二个特质是“引回来”,从哪里引回来?从祖籍地引回移居地。为什么说“回来”?在田野过程中,我们已经深深感受到印尼华人华侨已将印度尼西亚作为他们的“家”的认同,无论从服饰、生活、交流、语言、行为,都体现出移居地和祖籍地的一致性。发源地泉州举办大会唱多为政府组织,而印尼东方基金会在传播地举办南音大会唱,更多依靠社团和华人自发组织。
2008年10月30日,印尼东方音乐基金会在移居地举办二十五周年暨新会所落成庆典,邀请八个国家的26个代表团超过300名会员参加庆典,并进行南音交流,这是东方音乐基金会第一次大规模邀请海内外南音社团参加的交流活动。
2013年10月29日,第二届世界南音联谊大会唱暨印尼东方基金会成立三十周年庆典在印尼举行,主办方邀请了七个国家的38个代表团超过500名会员参加。两次大型南音交流活动的举办,形成了印尼东方音乐基金会特有的南音文化,显现出华人在印尼社会地位中的独特镜像。
早期印尼东方基金会以“家”的形式聘请当地的廖大安、洪草茹为南音先生。自基金会成立以来,先后从发源地泉州,以及流播地厦门、台湾聘请十几位南音弦友到印尼驻馆教学。这些南音先生不仅带来了南音,也为社团带来更多交流的平台。来自中国的国家级传承人苏诗咏、黄淑英,省级传承人丁信坤,以及早期马香缎等人,或短或长在印尼东方音乐基金会进行南音教学,苏诗咏待了六年之久。
目前,师资不稳定是印尼东方音乐基金会传承面临的难题,也导致会馆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基金会虽采取一系列的举措来吸引学生,但老一辈坚守南音文化的这份精神并不能得到年轻一代华裔的理解。幸而,在良好社会环境与印尼华人的坚持下,有八位年轻一代的南音爱好者加入了基金会,他们从一开始的排斥,到接受南音,南音像一根长长的丝线,联结着“故土”“唐山”“印尼”“家庭”“家族”,呈现出不同的“家”的含义,展现了南音作为“物”的延续。南音正是通过这样的“走回去”与“引进来”,彰显其生动的社会生命。
三、集体记忆与“灵力”
南音在发源地泉州与传播地印尼均有“馆阁”和“家”的空间传承,在南音人眼里,“馆阁”即“家”,“弦友”即“兄弟”。但自从1966年“排华”事件发生后,印尼社会南音社团早期的十几所“馆”传承空间逐渐消失。在这个特殊的社会,南音以“和”为集体活动的特质看似不可能发生。所幸,“馆阁”即“家”,而“家”即“馆阁”,口述资料为我们呈现了华人摆脱困境的智慧,他们为南音的“生”与“隐生”提供了可能。在印尼海军陆战队的支持下,颜呈茂家中经常聚集南音爱好者进行南音活动,为弦友们营造了一个脱离时代背景玩南音的空间。同时,“排华”时期弦友订婚、结婚、孩子满月、丧葬等仪式,这些画面(图片见彩版)⑮蔡金娘(中)演唱《看你行宜》。三弦:许秀文;南琶:李长旗;拍板:蔡金娘;洞箫:吴建兴;二弦:王文焕。陈敏红摄。为我们呈现了南音如何冲破重重障碍,在印尼华人华侨的生活中扎根,以它自身的方式记录了这段印尼华人的艰难岁月。它凝结了共同体的集体记忆,是其社会生命的重要来源和动力。
“郎君祭”“踩街”“会唱”等一系列仪式活动(图片见彩版)⑯《风打梨》器乐大合奏、《直入花园》。时间:2014年2月8日。地点:印尼雅加达。陈敏红摄。,完成了南音作为“物”的生命。在南音活动中,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神之间互为依靠、互为对照、相互交流,从经济、精神、物质等方面完成“礼物”的流动,具有一定的“灵力”。王铭铭在《物的社会生命?——莫斯〈论礼物〉的解释力与局限性》一文中认为:“在莫斯心中,再复杂的社会,其基本的品质,都不过是在最简单的社会当中见到的那一人与物的‘混沌’,即使在现代社会中,人与物之间也难以割舍……《论礼物》处处表现出物在人与人之间的流动所带有的‘灵力’对于物自身的超越。也恰是在这个‘灵力’的超越中,等级得到诠释。”⑰王铭铭《物的社会生命?——莫斯〈论礼物〉的解释力与局限性》,载《人类学讲义稿》,世界图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53页。我们此次的调研虽然很难确定南音在其流动过程中,是否在海外及其故土之间形成某种历史性的等级关系,但是南音的流动确实带来了超越性的“灵力”,这是民族音乐所特有的属性,是音乐人类学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结 语
南音在印尼传播过程中那种人与物的情感常常让人不解。作为音声的南音,是如何在闽南人心里播下种子,并散播到他们移居的土地,生根发芽?是如何在祖籍地和移居地之间徘徊、漂移,进而深扎、联结?印尼东方音乐基金会向我们展示了印尼社会以建构人的方式同样建构着“南音”。因此,在南音人的口述史中,描述南音作为“物”的社会生命是可能的,南音悠久的音乐形态以及丰富的音乐文化在印尼社会的构建中,将会是作为理解侨居海外华侨在文化认知和社会形塑力量的精彩切口,其强调南音作为物与人连结的观点有着涂尔干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延续,以口述史来描述“南音”在海外的传播,呈现闽籍东南亚华人华侨在不同的宗教信仰、文化内涵、社会结构、文化变迁的巨大变革映衬下,南音透过人生礼仪、生活场景、社会联结、仪式过程镌刻于海外华人华侨的生命轨迹之中,是闽南人内在符号的重要标识之一,触发我们对南音与人生、南音与社团、南音与华人在异域文化之间的关系的思考。作为“物”的南音有着与社会生命的诸多联结,其在流动中交换,在流动中分裂,在流动中重组,在流动中牵引,这就是南音“灵魂”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