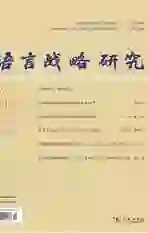中国语言教育政策百年演变及思考
2018-05-14周明朗
提 要 本文回顾、梳理了中国语言教育政策的演变过程,认为影响这个演变的两大主要因素是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建设。全球化直接导致了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造成了中国不同地区语言教育政策的分分合合,至今仍未取得理想的和谐与统一。百年来,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经历了4个不同的模式。 每个民族国家建设模式都有自己的语言意识形态,并以其意识形态为基础形成语言立法,制定语言教育政策,以建设有效的语言秩序。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清朝政府1911年通过的《国语统一办法案》仍是各届政府语言教育政策参照的蓝本。由于时代背景的限制,这个蓝本不能充分满足当代中国语言教育的需要。当代语言教育政策面临多重挑战:一要满足民族国家建设的需要;二要兼顾社区的语言多元现实;三要让国民有愉悦的语言学习过程,使他们成为忠诚的和合格的公民;四要培养国民的全球竞争能力。
关键词 语言教育政策;全球化;民族国家建设;语言意识形态;语言秩序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014(2018)05-0011-010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180501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ies in Greater China in the Last One Hundred Years
Zhou Mingl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and analyzes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ies in Greater China in the last one hundred years. It points out that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state building are the two most important factors that have affected this evolution. Globalization broke imperial China into separate lands, leading to diversity i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ies and unfulfilled wishes for the unification of these policies. In the past century, Greater China experienced four models of nation-state building. Every model had its own language ideology, and,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ies on the basis of this ideology, developed a corresponding language order. More or less, these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ies followed the Qing dynastys 1911 Act of the Unification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 However, with changing political landscape, the Qings plan cannot answer todays language education challenges. Now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ies must meet the needs of nation-state building, take into account the linguistic diversity in various communities, make language learning a pleasant experience for every student so that they become loyal and qualified citizens, and prepare citizens for global competition.
Key words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globalization; nation-state building; language ideology; language order
一、導 言
16世纪到20世纪初的全球化进程中,西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与传统中国发生了激烈冲突,使中国相继失去了台湾、香港和澳门。台湾17世纪先后被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占领,1895年又被迫割让给了日本,直到1945年才回到中国的怀抱。同样,香港在1842年鸦片战争后被割让给大英帝国,直到1997年才回归中国。1887年,澳门受葡萄牙殖民统治,中国政府到1999年才恢复行使主权。一系列的国土割让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备感国耻,痛定思图强,向西方寻求解药,以应对西方带来的全球化。从西方列强的崛起到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知识分子看到,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似乎都建立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语言的意识形态之上,从而把单语意识形态和单语秩序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直接挂钩。因此,他们责怪中国多言多语,也把中国的落后归罪于“过时”的文字,进而推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语言的意识形态(De Frances 1977:53~84)。经过这批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1911年8月清朝政府在濒临崩溃的前夜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案》(费锦昌1997:22)。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个办法案在顶层设计、教材建设、教师培训和语言规划诸方面为历届中国政府的语言教育政策提供了蓝图,成为了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元素之一。
建设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成为了中国20世纪初以来应对全球化的主要策略。民族国家建设包括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两个有机部分(Smith 1986)。民族建设主要依托于一种促进文化、语言、宗教、社会融合的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常常表现为民族主义。同时,国家建设着重于国家机器的建设,通过这些机器推动民族融合,保护领土完整,宣传爱国主义。民族国家建设就是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的相辅相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语言教育起着纽带作用,连接民族建设和国家建设,培养公民的国家语言意识形态,维护国家的语言秩序。因此,语言教育政策在民族国家建设中举足轻重。
本文旨在回顾、梳理百年来中国如何制定与执行语言教育政策,以满足现代民族国家建设需要,从而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
二、中国政府的语言教育政策发展轨迹
百年来,中国的人口从20世纪初的四亿两千九百万增长到了21世纪初的十三亿多。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汉民族,只有百分之八点几是少数民族。尽管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语言融合,中国现在仍有130多种语言,虽说其中一部分是濒危语言(孙宏开等2007)。这130多种语言分别来自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南亚语系和印欧语系。汉语除了使用当年被认为是落后的文字,还有若干方言和无数土语,而且有很多方言土语之间互不通话。受单语意识形态影响,这个语言多元状况过去一直被简单地认为是语言问题,阻碍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历届政府多与《统一国语办法案》的理念相近,推动汉语现代化,以此促进中国的语言统一。
中华民国自1912年成立后,试图以孙中山先生的“五族共和”为原则,建设第一个共和国,承认汉、满、蒙、藏和回五族公民,其中“回”是指西部操突厥语族语言又信仰伊斯兰教的各少数民族(李世荣2014;Zhao 2004:68~69)。按照孙中山的国家建设模式,民国政府主张有限多语秩序,采取两条腿走路的语言教育政策。首先,政府在汉族地区统一“国语”标准,推行汉字改革,支持白话文取代文言文(Chen 1999:13~23)。1919年公布以南北官话混合语音为基础的“国语”标准以后,1920年教育部就指令小学一、二年级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其他各年级逐步采用白话文教育。为了让这个改革顺利进行,教育部在北京和各个省会举办在职“国语”教师培训班,同时编辑了白话文的语文课本。新课本用日常汉语,如民谣、新闻等为课文,用注音符号辅助汉字标准读音和课文阅读。与此同时,“国语”标准化的工作仍在继续推进,1926年公布了以北京音为“国语”读音标准,1928年公布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不过民国政府对后者在中小学推行不力(费锦昌1997:42~44)。
其次,民国政府1914年成立了蒙藏院,通过该院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教育。蒙藏院既资助民族语言教育,又提倡“国语”教育,旨在促进五族融合。20世纪20年代末期,南京的民国政府通过了新的少数民族政策,在北方和西北兼容少数民族语言教育,而在西南强推“国语”教育(Mackerras 1994:49~78)。例如,1930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上通过的蒙藏教育计划包括了编辑民汉双语教材和民语教材、培养双语和民语师资等(内蒙古教育志编委会1995:142~151)。同时,民国政府在西南的贵州、四川等地的少数民族社区强推“国语”教育,排斥少数民族语言教育。
在20世纪40年代初,即抗日战争最激烈的阶段,蒋介石提出了中华民族论,让民国政府进一步实行民族融合政策,团结各民族抗日。按照蒋介石的中华民族模式,各民族来自同一个始祖,属于不同的宗支,由血统和联姻维系,通过融合和同化成为中华民族(Zhao 2004:171~172)。根据这个模式,民国政府主张单语秩序,加强了语言教育同化。民国政府教育部1941年在《边地教育视导应特别注意事项》的指令中强调,“边教应努力融合各地民族”,“边教应推行国语教育”(宋恩荣,章咸2005:584)。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笼络人心,采用了宽容的语言教育政策。國民党政府教育部1945年9月发布《边疆初等教育设施办法》,规定“国语与边地语文得视地方需要,同时教学或选择一种教学”(宋恩荣,章咸2005:584)。不过这个政策还没有得到真正贯彻,国民党就因内战失败,1949年退到台湾去了。
1949年初,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寻找适合中国的国家建设模式,决定“一边倒”,全面学习苏联模式,最终采用了苏式多民族国家建设模式(沈志华2003:52~62;孙其明2002;Bernstein & Li,2010)。 在语言方面,苏式模式提倡多语双轨制,汉语发展为主轨道,少数民族语言发展为卫星轨道(Zhou 2010)。汉语主轨推动汉民族的共同语——普通话教育。按照20世纪50年代的官方定义,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政策法规室1996:12)。所以,当年普通话并没有母语者,这对语言教育是一个巨大的挑战。1955年11月,教育部颁发《关于在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要求(1)全国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必须逐步用普通话教学,使学生学会说普通话;(2)各省市必须举办教师普通话培训班和普通话教学培训班,1956年夏完成对语文教师的培训,1958年完成对其他科目教师的培训;(3)地方教育部门和大学应该合作编写普通话教材,开办普通话培训班;(4)地方政府和学校要组织普通话演讲比赛,奖励说普通话的优胜者(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政策法规室1996:48~55)。与此同时,拼音和简体字也跟普通话一起在全国推广,全面实行汉语现代化。1956年2月,国务院发布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要求到1960年,三年级以上的汉族学生必须学会说普通话,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学生和学习汉语的少数民族学生也必须学会说普通话(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政策法规室1996:11~15)。当时计划推普分两步走,最终使普通话成为汉民族的共同语,以达到汉民族的语言统一。受经济发展水平和户口制度的限制,这个推普计划没有在指定的时间内达到预期目标。
按照社会发展理论,各民族到共产主义社会将融合为一个民族,说一种共同语(杨荆楚1995:46~47)。少数民族语言发展从各自的卫星轨道出发,最终都与汉语主轨道会合。根据苏式多民族国家建设模式,多语发展首先要给各民族选定他们的标准语,让标准语推动各种宗族语言向部落语言发展,再促使部落语言向民族共同语发展(谢尔久琴科1956)。这个过程主要借力于以民族共同语标准音为基础的拼音文字。各民族共同语共用同一个拼音文字,又通过这个拼音文字从汉民族共同语中大量借词,使各民族共同语的语音和词汇日趋大同。20世纪50年代汉语拼音被寄予了这样一个厚望,被广泛用于中国的新创少数民族文字和少数民族文字改革,被期待最终促进中国的语言大同。这个语言发展模式分两步走,第一发展各民族共同语,第二融合各民族语言为更广泛的共同语。但是,这个语言发展模式在实际执行中常受极“左”思想影响,时常两步并作一步走,直接过渡到汉语,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1958;Beckett & Postiglione 2012;Zhou 2003:62~68)。这个苏式多语发展模式对语言教育的直接影响表现为民汉分校教育。民汉分校分班教育不具备优化民汉双语教育的机制,加之又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所以这个时期双语教育算不上成功。
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苏式模式的弊病日益彰显。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在这些领域里逐步放弃或者改革了苏式模式。1991年底以来,中国深入地探讨了苏式多民族国家建设模式的经验教训,开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建设模式(果洪升1997;Shambaugh 2008)。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逐步从斯大林的民族问题话语转换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话语。例如,90年代初江泽民视察新疆,指出“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构成的,在我们祖国的大家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的新型民族关系,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李德洙1999:158)。“三个离不开” 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之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2002:18)。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加快经济建设,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成为了民族工作的重点。2003年,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强调,中国要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就是中国的各少数民族共同富裕,共同发展经济(毛公宁,刘万庆2004:14)。2005年,在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正式采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阐释中国的民族关系(金炳镐2006:926~941)。2014年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也进一步强调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源自费孝通1989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做的题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的讲座。讲座中,费孝通提出了3个理念,即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多元一体的格局(费孝通1999)。中华民族包含56个民族,但并不是56个民族的简单集合的总称。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實体,形成了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这个理念上的中华民族包含两个层次的身份认同,低层次是56个民族的各自族群认同,汉族只是其中之一;高层次的是每个中国公民都应该具有的中华民族认同。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念认为,两个层次的身份认同既不互相取代,又不互相排斥,而是在语言和文化的多元环境中共生存,共发展。
作为民族国家建设模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包容互补多语意识形态,支持分级多语秩序。这个语言意识形态既承认中国多语的存在与其必要性,又推崇普通话在中国的特殊历史意义和主导地位,认可普通话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语,行使促进相互交流、形成统一共识、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功能。与这个语言意识形态相呼应,最理想的语言秩序应该是以普通话为主,以各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为辅,主辅语言各司其职,各尽其能。
代表这个中国式互补多语意识形态和分级语言秩序的立法形式,是2001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该法律把普通话从汉民族共同语升级为国家通用语言,既规定每个中国公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与义务,又肯定各个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但是有主次之分,有语言使用域的分工。这个法律对汉族和少数民族语言教育政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汉语社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加强了中小学的普通话教学,大力推动了普通话的学习和使用,有效地为21世纪中国的崛起做好了语言准备。经济的高速发展,户口制度的松动,使中国流动人口每年多达2.5亿。流动人口创造了普通话使用的市场,同时说普通话又有助人们流动,就业,升职。毫无疑问,这个发展趋势很可能超过国家原来制定的2010年前初步普及普通话、2050年前全面普及普通话的计划(李宇明2005:4)。当然,这个发展趋势也让人担忧。不少弱势的汉语方言已经濒危或者接近濒危,即便强势的汉语方言,如上海话和广州话,也同样面临使用人口和使用域逐年减少的局面。
在少数民族社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对语言教育产生了3个重大影响。第一,学校的体制改革。民汉合校教育逐步取代了民汉分校教育,从教育制度上建设民族融合平台,优化民汉双语教育机制。第二,教学用语变化。少数民族语言在规定的期限内从主要教学用语转为辅助教学用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成为了主要教学用语。第三,加大学前双语教育发展的力度,大量开办学前双语班,实现双语教育从娃娃抓起。这3项变革无疑可以广泛促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让少数民族社区产生了一些顾虑(Guljennet 2008;Tsung 2009)。例如,民汉合校和主辅教学用语转换不宜限时“一刀切”,最好根据每个地区每个学校的师资准备、教材准备、学生语言能力等情况因地制宜,逐步施行。在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同时,学校实际上面临两个挑战,一是如何根据法律继续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教育,二是如何提供优质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应对好第一个挑战,能让少数民族学生和父母不必担心母语的传承,也能让学生无后顾之忧地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对好第二个挑战,于家,可不误人子弟;于国家,可培养优秀人才和合格公民。
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模式所推崇的互补多语意识形态和分级多语秩序开始产生国际影响。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开始竞争全球语言(global language)的地位。从2003年起,中国启动了“汉语国际推广”,后又名为“汉语国际教育”,西方有学者称之为“官话攻势”(Mandarin offensive)(Hartig 2012;Lo Bianco 2007)。汉语国际教育带动了汉语全球化。汉语全球化有三大特征:第一,海外华人社区从汉语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转用普通话;第二,普通话、拼音和简化汉字成为全球各级各类学校汉语教育的标准;第三,中国在世界各大洲建立了几百所孔子学院,上千个孔子课堂,派出了成千上万的汉语教育志愿者(周明朗2017)。无论利弊如何,这都是百年以来中国应对全球化的首次主动语言文化出击。
三、台湾地区语言教育政策的变迁
当今台湾地区的2300万人中,98%的人说汉语方言,主要是说闽南话(Wu 2011)。虽说官方认可的少数民族语有16种之多,但是说少数民族语的人仅仅占总人口的2%。1945年8月台湾光复时,由于半个世纪的日本殖民同化教育,大多数台湾民众都能讲一些日语。 不过,他们在日据时期私下都讲闽南话,强烈认同中国而不是日本(Wu 2011)。台湾光复后,台湾当局的语言教育政策经历了3个主要发展阶段,不断调整以期适合台湾的政治和社会变化(Tse 2000)。
首先是1945年至1969年的肃清日本影响及重建中华民族认同阶段。这个时期,台湾当局持续了其大陆语言教育政策,发动了“国语”运动,特别是在学校强化中华民族认同(Tsao 1999)。期间台湾地区民众与政府关系日趋紧张,以至于1947年2月爆发了民众与政府的激烈冲突,随即政府宣布台湾全岛戒严。1949年国民党退到台湾,全岛再次戒严。同时,语言教育政策进一步强调同化,指定“国语”为各级学校唯一合法的教学语言,明确规定其他语言不适合国民教育。根据台湾当局1966年颁布的《各级学校加强推行“国语”计划》,学校可以合法地惩罚在学校讲汉语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的学生(Huang 2000)。然而强制“国语”教育并没有培养出完全忠于中华民族的一代年轻人,反而在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台独”倾向,导致部分年轻人开始挑战台湾当局持续了近20年的戒严。
第二个阶段是1969年至1986年的“国语”推行期。这个阶段台湾地区取得了经济建设的成功,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建设的成功让台湾当局更有信心代表中华民族正统文化,更有决心推广“国语”为台湾地区的唯一公共用语。1970年,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颁布了《加强推行“国语”运动实施办法》,加强地方县、市“国语”推行委员会的地位和作用,提倡说“国语”、做优秀国民。次年,为了落实教育部门的《实施办法》,台湾当局制定了《台湾省加强推行“国语”实施计划》。计划十分全面,涵盖了小学到师范学校的“国语”教学法、“国语”培训、“国语”水平测试、“国语”辅导等。为了把“国语”推向农村,推向山地少数民族社区,台湾当局1973年制定了《台湾省各县山地乡“国语”推行办法》,旨在让少数民族转用“国语”,加强中华民族认同。随后10多年间,语言教育政策主要沿着这个方向发展,意在加强中华民族认同,复兴中华文化,但是高压之下产生了“国语”与闽南话的对抗,民间“台独”倾向日趋严重(Dreyer 2003)。
第三个阶段是1987年以来的“民主”与“多元”时期。1987年台湾地区解除了近40年的戒严后,“国语”作为学校的唯一教学用语的地位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受到了挑战,因为台湾地区宪制性规定并没有授予“国语”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地位。面对挑战,国民党执政的台湾当局开始考虑语言教育政策如何兼容语言多元。1993年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决定,学校可以开设地方语言选修课,包括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Wu 2011)。虽说选修课学时仍有限制,但事实上学校已经开始了双语教学。因此,教育部也鼓励学习当地语言,编辑当地语言教材。语言教育政策问题在民进党执政的2000~2008年变得越来越尖锐。2003年,陈水扁当局教育主管部门公布了所谓的“国家语言平等法”草案。该草案规定,闽南话(所谓的“台语”)、客家话和少数民族语跟汉语官话一样享受“国语”地位。由于这个草案代表“去中国化”,在立法机构没有被通过。这期间,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得到了改善。2006年,台湾地区少数民族事务主管部门制定了一个复兴原居民族语言六年计划(周惠民,施正锋2011)。这个计划有8个要点:(1)对少数民族语加强立法保护;(2)建立少数民族语言保护与推广机构;(3)编辑少数民族语言词典和课本;(4)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研究;(5)培训少数民族语言复兴工作人员;(6)促进少数民族家和社区使用母语;(7)充分利用多媒体和数字技术;(8)开发少数民族语言水平测试。2009年国民党重新执政以后,台湾地区的语言教育政策仍然朝多元化发展。同时,作为对大陆汉语国际推广的回应,台湾地区也在世界各地小规模地建立台湾书院,既推行“国语”教育又推广台湾多元文化。2016年民进党又重新执政,在蔡英文当局推动下,所谓的“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草案于2017年5月下旬在立法机构通过,少数民族语言正式成为官方语言。2017年7月,蔡英文当局又向立法机构推出了所谓的“国家语言发展法草案”。该法草案认定台湾岛内各种自然语言为“国语”,为其提供各级学校学习的机会,同时淡化原有的“国语”,以便实现语言“台独”。总之,台湾地区的语言教育政策的走向值得海峡两岸密切关注,因为语言政策是民族国家建設的指路灯。
四、香港地区的语言教育政策
香港主要是一个讲粤方言的社区。在香港的700多万人中,90%讲粤方言,1%讲普通话,4%讲其他汉语方言,3.5%讲英语,1.5%讲世界其他语言(Hong Kong 2011)。尽管被殖民100多年,香港居民传统上非常认同中华民族,不过他们中的部分人对大陆的政治制度仍有顾虑。20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后,香港居民除了中华民族身份认同,还拥有香港身份认同(Tsui 2003)。从19世纪40年代起,英国殖民当局仅承认英语的官方语言地位,直到1974年才追加汉语为官方语言之一。这里汉语指粤方言口语和现代汉语书面语。不过1997年香港回归以前,汉语对香港的语言教育政策并没有实际影响。香港主权回归的前几年,港英当局才开始正式把学校分为英语教学学校和汉语教学学校,给回归留下了后患,制造了一个撕裂社区的语言教育问题(Tsui 2003)。
1997年香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中回归中国。语言主权理所当然是回归的一个重要层面,涉及去殖民化和民族国家认同重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第九条规定,英语可以跟汉语一起作为特区的官方语言。同时该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特区有权制定香港的语言教育政策。基本法中提到的汉语,在内地一般指普通话或者国家通用语言,但是在香港传统上是指粤方言。两种不同理解可能导致不同的期待。为了保持平衡,特区政府于1999年制定了“两文三语”政策,“两文”指中文和英文,“三语”指英语、粤方言和普通话(Zhang & Yang 2004)。这3种语言代表着几种不同身份认同。英语标志着香港的国际地位和资本主义制度。粤方言代表着香港地域身份,而普通话比较复杂,有两种身份指向,即分别为中华民族和国家的社会制度。因此,英语无论是作为科目还是教学语言,都是社区和学生的首选。港人需要英语保持国际竞争力,也需要英语象征性地维护“一国两制”。按照前港英殖民政府遗留的教学用语分类办法,特区政府1998年制定了母语教学政策。这个政策巧借汉语这个词的歧义,绕开了普通话,直接把粤方言作为母语定位为仅次于英语的教学语言。因此,这个政策无论从教学法上来说,还是从政治上来说,都为港人普遍接受。在20世纪90年代,普通话在香港的政治功能是毫無疑义的,代表着去殖民化和国家认同重建;但是普通话的日用功能尚不明确。90年代末,把普通话作为教学用语的学校寥寥无几。然而随着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到21世纪初,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采用普通话教学(Zhang & Yang 2004)。2009~2010年,中小学学生对普通话的态度有明显的改善(Lai 2013)。对此,有人乐观,也有人悲观(Evans 2011)。乐观者觉得普通话会很快在香港学校普及,而悲观者认为普通话会把粤方言边缘化。其实,若考虑到近几年香港出现的学潮,无论乐观的态度还是悲观的态度都是没有依据的。普通话在全球日益扩大的实用性必定会推动香港各级学校的普通话教育。同时,部分港人对“一国两制”动摇不稳的信心则不利于学校的普通话教育的发展。因此,只要依法贯彻执行“一国两制”,在今后30年内普通话教育应该会在香港各级学校稳步普及,达到国家认同重建的目的。
五、澳门地区的语言教育政策
现在澳门地区的55.2万居民中,约83.3%说粤方言,5%说普通话,3.7%说各种福建话,2%说各种汉语方言,0.7%说葡萄牙语,2.3%说英语,3%说世界其他语言(Macao 2012)。在葡萄牙4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中,葡萄牙语一直是澳门地区唯一的官方语言。1987年中葡两国开始就澳门回归谈判时,葡澳当局才追加汉语为澳门官方语言之一。不过葡澳当局的语言教育政策一直是宽松的,仅仅要求几家公立学校用葡萄牙语教学(Mann & Wong 1999)。在葡萄牙殖民统治的最后10年,葡萄牙语学校的学生只占澳门学生总数的5.1%,葡汉双语学校的学生仅仅占2.8%。相反,中文学校的学生多达澳门学生总数的86%,英文学校的学生也有6.1%(Shan & Ieong 2008)。当然,中文学校大多用粤方言教学。澳门的中小学校实际上是实施“三文”(葡萄牙文、中文、英文)“四语”(葡萄牙语、英语、官话/普通话、粤方言)教育。
按照香港模式,《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九条规定,葡萄牙语与汉语一起作为澳门特区的官方语言;第一百二十一条还规定,特区政府有权决定学校教学用语。继续使用葡萄牙语只是“一国两制”的象征而已,因为葡萄牙语不像英语,不具备英语那种全球超级语言的地位。不像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不必为语言教育政策解释“汉语”这个词的歧义,只是继续实行“三文四语”的实践。首先受益于这个政策的是澳门的高等教育。回归20年以来,澳门的高等教育发展很快,国际地位也日益高涨(Shan & Ieong 2008)。直到2014年,澳门特区政府才规定,普通话必须用于中小学汉语为第一语言课程的教学,也可以用于中小学汉语为第二语言课程的教学。这个规定代表着进一步去殖民化和国家认同重建,但是并没有影响粤方言作为中小学教学语言的地位。同时,普通话在正规学校教育和夜校教育中都取得了可喜成绩。从2001年到2011年10年间,澳门居民会讲普通话的人数从居民总数的26.7%上升到41.4%,会讲英语的居民从13.5%增加到21.1%(Macao 2012:13)。同期,讲粤方言的居民略微从94.4%下降到90%,讲葡萄牙语的居民从3%减少到2.4%。从语言态度和能力来看,澳门的居民一方面强烈认同中华民族,另一方面拥抱全球化。在“一国两制”下,这个发展势头应该会越来越好。
六、几点思考
(一)政治上,语言可以说仅仅次于军事,是民族国家建设或者重建的重要手段之一。军事通过暴力方式铲除殖民主义,建立民族国家,维护国家领土统一。语言则用和平方式消除殖民主义,建立爱国主义,培养统一的国家认同,实现民族国家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与军事同为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工具,前者为柔性工具,后者为刚性工具。由此可见,语言政策,尤其是语言教育政策意义重大。
(二)在过去百年应对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经历了民族国家4类建设模式,见证了台湾、香港、澳门3个地区的殖民化和去殖民化过程。无论是民族国家建设,还是殖民化或者去殖民化,语言教育政策都是重要的工具,起到过重要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曾经左右过中国的语言教育政策,今天仍然影响着中国的语言教育政策的统一。全球化改变区域和全球语言秩序,既带来机会又带来挑战(Zhou 2011,2017a)。这个机会使汉语有可能上升为全球语言之一,成为全球华语;而这个挑战是在全球华语大同的趋势之下,中国如何取得政治大同。成功应对这个挑战取决于利益攸关各方的政治智慧。
(三)就国家而言,语言是工具。语言教育政策涉及民族国家建设,关系到中国建设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各个族群之间形成什么样的关系,每个公民拥有什么权利与义务,可以有什么身份认同。国家必须认识到,就家与个人而言,语言是生活。语言教育政策关系到他们如何学习,如何工作,如何生活,生活得如何,做什么人,是什么人。因此,语言教育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家的成败与人民的福祉。
(四)即使语言教育政策好,其成功与否在于细节,诸如政策执行的力度、节奏、资源利用的效率、教材编写、教师培训、教学法等。总之,成功的语言教育政策既要让每个学生享受愉悦的语言学习过程,又要让每个学生成为有理想的、有竞争力的、忠诚的公民。语言教育育人,应润物无声。
参考文献
费锦昌 1997 《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记事》,北京:语文出版社。
费孝通 1999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果洪升 1997 《中国与前苏联民族问题对比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1958 《为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民族语文工作方针而奋斗》,《民族研究》第3期。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2002 《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政策》,北京:民族出版社。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政策法规室 1996 《国家语言文字政策法规汇编(1949~1995)》,北京:语文出版社。
金炳镐 2006 《民族纲领政策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李德洙 1999 《中央第三代领导与少数民族》,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李世荣 2014 《民国时期回族及其伊斯兰教民族政策研究》,《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第5期。
李宇明 2005 《中国语言规划论》,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毛公宁,刘万庆 2004 《民族政策研究文丛》(第三辑),北京:民族出版社。
内蒙古教育志编委会 1995 《内蒙古教育史志资料》第二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沈志华 2003 《苏联专家在中国》,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宋恩荣,章 咸 2005 《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孙宏开,胡增益,黄 行 2007 《中国的语言》,北京:商务印书馆。
孙其明 2002 《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谢尔久琴科 1956 《苏联创立文字和建立标准语的经验》,《语言研究》第1期。
杨荆楚 1995 《毛泽东民族理论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周惠民,施正锋 2011 《我国原居民族教育之回顧与展望》,载《我国百年教育回顾与展望》,新北市:国家教育研究院。
周明朗 2017 《全球华语大同?》,《语言战略研究》第1期。
Beckett, G. H. and G. A. Postiglione. 2012. Chinas Assimilationist Language Policy: The Impact on Indigenous/Minority Literacy and Social Harmony. London: Routledge.
Bernstein, T. P. and Hua-Yu Li. 2010. China Learns from the Soviet Union, 1949-Present.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Chen, P. 1999.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 Socio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e Frances, J. 1977. Nationalism and Language Reform in China. New York: Octagon Books.
Dreyer, J. T. 2003.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policies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aiwan. In M. E. Brown and S. Ganguly (eds.), Fighting Word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Evans, S. 2011. Long march to biliteracy and trilingualism: Language policy in Hong Kong education since the handover.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33, 302-324.
Guljennet, A. 2008. Present state and prospects of bilingual education in Xinjiang. Chinese Education and Society 41 (6), 37-49.
Hartig, F. 2012.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the rise of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7, 53-76.
Hong Kong. 2011. Population Aged 5 and Over by Duration of Residence in Hong Kong, Ethnicity and Usual Language. http://www.census2011.gov.hk/en/main-table/A124.html.
Huang, S. 2000. Language, identity, and conflict: A case study of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143, 139-149.
Lai, M. L. 2013. Impact of medium of instruction on language attitudes: A case study of Hong Kong. Asian-Pacific Education Research 22 (1), 61-68.
Lo Bianco, J. 2007. Emergent China and Chinese: Language planning categories. Language Policy 6, 3-26.
Macao. 2012. Results of 2011 Population Census. Macao: DSEC.
Mackerras, C. 1994. Chinas Minorities: Integr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nn, C. and G. Wong. 1999.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education: Survey from Macao on its return to Chinese sovereignty. Language Problems and Language Planning 23 (1), 17-36.
Shambaugh, D. 2008.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ion. Washington, D. 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Shan, W. J. and Ieong S. L. 2008. Post-colonial reflections on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Macao. Comparative Education Bulletin 11, 36-67.
Smith, A. D. 1986. State-making and nation-building. In J. A. Hall (ed.) States in History. Oxford: Blackwell.
Tsao, F. F. 1999. The language planning situation in Taiwan.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20 (4-5).
Tse, J. K. P. 2000. Language and a rising new identity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143, 151-164.
Tsui, A. B. M. 2003. Medium of instruction in Hong Kong: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whose language? In J. W. Tollefson and A. B. M. Tsui (eds.), Medium of Instruction Policy: Which Agenda? Whose Agenda?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Tsung, L. 2009. Minority Languages, Education and Communities in China. New York: Palgrave.
Wu, M. H. 2011. Language planning and policy in Taiwa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Language Problems & Language Planning 35 (1), 15-34.
Zhang, B. N. and R. R. Yang. 2004. Putonghua education and language policy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In M. Zhou and H. K. Sun (eds.), Language Polic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ory and Practice Since 1949. Dordrecht: Kluwer.
Zhao, S. H. 2004. A Nation-state by Construction: Dynamics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Zhou, M. 2003. Multilingualism in China: The Politics of Writing Reforms for Minority Languages, 1949-2002.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Zhou, M. 2010. The fate of the Soviet model of multinational-state build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 P. Bernstein and H. Y. Li (eds.), China Learns from the Soviet Union, 1949-present.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Zhou, M. 2011. Globalization and language orde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L. Tsung and K. Cruickshank (eds.), Teaching and Learning Chinese in Global Contexts. London: Continuum.
Zhou, M. 2017a. Language ideology and language order: Conflicts and compromises in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A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243, 97-118.
Zhou, M. 2017b. Language policies and education in Greater China. In T. McCarty and S. May (eds.), Language Policy and Political Issues in Education, Heidelberg/New York: Springer.
责任编辑:杨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