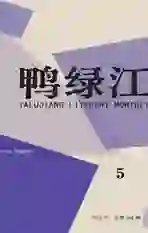文人情怀的映象诗篇
2018-05-08覃皓吕冰怡
覃皓 吕冰怡
2015年,曾七次冲击“金棕榈”大奖的侯孝贤终于得偿所愿,凭借《刺客聶隐娘》荣获68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自此,这部风格独特、气韵非凡的所谓“侯式”武侠电影,也如同该片的主人公一样,在隐逸神秘、功力莫测的传言中被颂为传奇。上映前,热盼中观众们几乎一头雾水,只能从影评人及媒体对该片的一派盛赞欢呼中,捕捉谜如烟云的破碎信息。不少影评人如此论断:大部分观众对侯孝贤并不了解,其个人风格实在太强,凭借个人趣味难评难断,将影片定位为“票房不乐观的杰作”。
果不其然,随着当年8月影片的上映,《刺客聂隐娘》随即成为话题之作。爱者甚爱,厌者极厌,迷者愈迷。影评网站上,该片从高度期待的高分一路走低,影院内许多观众一头雾水,怨声载道,甚嚣尘上,甚至笑称为“催眠神片”。紧接着,新一轮风评迅速逆转,支持者无不从文艺性、实验性角度力捧其文化高度。刹那间,掀起一场言论两极分化严重的文化怪谈。便有影人笑谈,时间终会给出客观的答案。有人拿影片和多年前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比量,可我却始终认为,每部电影都有自己的命运流转、前世今生,文人的浪漫更多是不可言说的心意。
如今《刺客聂隐娘》上映已近三年,关于本片的争论早已尘埃落定,孰是孰非我本无意判断。于我而言,侯孝贤的电影就如冰川一角,仅仅论断其表面的形貌有失公允,也难品奥妙,需要慢慢化解方能品得那份凛冽甘醇。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中,可谓借来了冰封千年的中华文脉精华,献祭了他近乎半生的才华与时间。
文人初心,文脉渊源
拍摄一部关于“刺客聂隐娘”的电影,是年近古稀的侯孝贤自学生时代开始便置于心头的夙愿,其文脉渊源亦堪称传奇中的传奇。原本的唐传奇小说《聂隐娘》初始文本仅仅1700字,以诡异的文风、离奇的故事、玄妙的意境与生动的人物而被称为唐传奇中武侠小说代表之作。侯孝贤从小痴迷武侠,无论是金庸小说还是功夫电影都广泛“研习”,唐人小说中的武侠传奇更是令他感到惊喜。虽然侯孝贤在此前的风格化、艺术化的影像风格,似乎与传统意义上的武侠片有着难以逾越的间隙,但他仍旧以自己的方式证明,武侠片其实还可以如此写意、深邃与真实。
影片遵循了原著的大部分设定,在删改剧情的同时丰富并延展了人物与故事,片中写实而严谨却又隐逸迷幻的表现形式,不仅高度还原了唐人小说中的风格气韵,更呈现出一副相对真实的唐朝风貌。在一些访谈中,侯孝贤曾反复提及他最希望的是能有一台时光机回到唐朝去看一看,如此便可以更加真实地还原那个他心驰神往的唐朝情景。也许就是为了那一眼的唐朝,才有了《刺客聂隐娘》的底蕴与纯粹。这同时提供给电影的创作者们一个新的思路,往前寻觅那些文化冰山中仍然沉睡有待唤醒的冰封宝藏,也许我们不必急于求成地非要而为票房标新立异,但求原汁原味、原汤原食。
“原来的唐传奇只有千余字,而且刺客杀人是不需要理由的。但是要把这个故事搬上大银幕,就一定要给‘杀人找到某种合理性。”编剧之一的谢海盟坦言,如何平衡原著故事与电影的冲突矛盾和人物性格,他们着实下了一番大功夫。而为了完美呈现本片,侯孝贤不仅自己通读《资治通鉴》、新旧唐书等各种唐代史料,更邀请阿城、朱天文、谢海盟共同参与编剧,这也令本片在兼顾真实的同时具备了一分难得的文气。
文人匠心,文气呵成
说这部电影是由文气一气呵成毫不为过。编剧之一的阿城是中国当代文坛家喻户晓的大家,其电影编剧方面的成就在作家圈内堪称卓越;朱天文则是台湾知名作家朱西宁与翻译家刘慕沙之女;年仅二十九岁的谢海盟更是享誉台湾文坛的“朱氏家族”第三代文脉传人,即朱天文的侄女。阿城曾如此评价朱氏文人:“朱先生有三个女儿,大女朱天文,二女朱天心,都是台湾最好的文学家……如果以为朱家有一股子傲气(他们实在有傲气的本钱),就错了,朴素,幽默,随意,正直,是这一家子的迷人所在。”
但就算有了如此强大的编辑团队打底,《刺客聂隐娘》仅是前期筹备阶段仍旧长达七年之久,就连剧本也八易其稿。“尽管影片中对一些人物的呈现是简约、片段式的,甚至可能给人跳动、破碎的感觉,但从编剧的角度讲,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前世今生、行事逻辑,而电影最终展现的只是他们在生活中的某个部分,某种状态。”谢海盟的言论似乎证实着侯孝贤一直以来严格遵循的一套“冰山理论”,即电影中的每个人物都如一座冰山,露出的只有一角而已,更多的隐情与秘密都埋藏在更深层次的情感中。
在编剧们扎实的文学功底与导演的严格把握下,影片在意象与细节上的精道处理细腻入微且意蕴深厚。“罽宾国国王得一青鸾,三年不鸣,有人谓,鸾见同类则鸣,何不悬镜照之,青鸾见影悲鸣,对镜终宵舞镜而死。”青鸾与凤凰之别在于“赤者为凤,青者为鸾”,同样是双生用典,比较广为大众所熟知的凤凰而言,以“青鸾舞镜”为征却更显得凄美动人,褪去了煊赫富华之感。而诸如“绝人以玦”的玉玦文化内涵,以帷幔拂动表现无形之风的精妙,少年所磨之镜的“心如镜像”心相意蕴,乃至繁如沐浴微若妆容的生活点滴细节,宫殿内小到配饰大到家装的各样细节,也都颇具匠心、令人叹服。据称这也离不开阿城在各类古董家具道具搜集时的帮助与古典文化细节上的顾问作用。
其实片中备受争议的台词并非纯粹的文言文,而是具有文言古风的口语表达,既能够较好地避免一众台湾演员口音带来的异样感,也符合戏中人物性格与复杂纠葛的矛盾,言简意赅的对话以“隐”的方式,反而能传达出更多耐人寻味、只可意会的弦外音信,这不仅让本片多了几分哲思意味,也更多体现出了文人电影特有的情怀余韵。
文人诗心,文化映像
作为侯孝贤多年来的朋友与搭档,朱天文评价侯孝贤为“抒情诗人”。她说:“他的电影的特质也在于此,是抒情的,而非叙事和戏剧。吸引侯孝贤走进内容的东西,与其说是事件,不如说是画面的魅力,他倾向于气氛和个性,对说故事没有兴趣。”从故事的角度解读《刺客聂隐娘》,与其说它是一部夺人耳目的武侠片,倒不如说是一部扎扎实实的文人映像。虽然其中有爱恨情仇、有武功玄术甚至还有政治惊悚等如此纷繁复杂的元素暗含其中,其主线故事却出乎意料的简单和纯粹,即:杀——不杀。所有的情感都隐而不发,一切的故事都如冰山般隐于更大的莫测之中,却更显出那个藩镇割据时代的厚重和恢宏。
单从拍摄角度看,《刺客聂隐娘》开篇纯粹的黑白画面中,那些粗粝的噪点凸显出的胶片质感不仅有种岁月美感,更是一种映像态度的人文情怀。当富有浓烈色彩感的宫殿堂皇与写意气韵的云墨山水交相构筑于眼前,那每一个空镜头内都仿佛是欲言又止的阐述,每一个人物的一举一动哪怕是轻功白刃都如符合自然道化,而那些微而可闻且贯穿全篇的风声、虫鸣组成的自然之音,都愈加映衬出那份人力难及的至尚至高之美。
侯孝贤曾说:“我觉得总有一天电影应该拍成这个样子:平易,非常简单,所有的人都能看。但是看得深的人可以看得很深,非常深邃。”在我看来,本片的意义不仅在于其文化溯源而上汲取文脉的智慧,也不在于其忠于创作初心与诚意宛如古儒般的品格,而在于一种引发电影创作者与观影受众们内心重新审视的角度。于对观众们而言,若只为休闲娱乐避暑纳凉,大可不必费尽心力攀登这座文化冰山的一角传奇;于导演们而言,若只为票房大卖谄媚观众,亦无须用心良苦糟蹋那片冰封千载的文化宝藏。时隔多年再看,无关技法,无关演员,仅仅是关于这个传承千年的故事,关乎这份文人情怀的坚持,影片便始终具有恒远的魅力。
有人说:“侯孝贤拍的就是自己,他是一个没有同类的人。”而谁又有真正的同类呢?千年来的文化冰山中封存的仍然是那份超越时间本源的人心共性,我们无非要寻找那个古往今来迷失的我们自身罢了,而每个时代的经典之作,终究又化作下一个时代攀登的冰山一角,如此轮回。
【责任编辑】 行 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