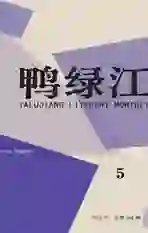丙申年
2018-05-08王明明
王明明
汽车在鄱阳湖大堤上缓缓前行。这一幕曾在我梦里出现过。马小鹏双手紧握方向盤,不经意脱口而出这一句。很怕被她听到,他向后视镜瞄了一眼,穆晓早已在后排昏睡过去,儿子的头偎在穆晓的怀里,两只小脚抵在车门上,就像两只猴子。
丙申年猴票的发行消息一出,马小鹏第一时间想到了赵阳。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他们二十年的缘分终归与邮票脱不了干系,以至于时隔多年,在马小鹏和赵阳鲜有联系的现在,当马小鹏试图为他们的关系找到一个分水岭,抑或说某种仪式的时候,邮票仍旧是他最佳的选择。于是,马小鹏早早地就跟集邮公司的同事打了招呼,能不能帮我留几套小本票?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东西就跟电影首映一样,总有个具体的时间,即便是点映,也要有个具体的放映时间,不是你想提前饱眼福就能饱得到的。况且,还限购。发行当天,马小鹏一大早就赶到了单位楼下的营业厅,假装集邮爱好者一样挤在人群当中,其实他至多曾经算是个发烧友,现在恐怕连发烧友也算不上。他备好零钱、排队、登记身份证,最终他得到了一个小本票和两张四方联。马小鹏原想将他老婆穆晓的身份证也揣着多买一套的,想想还是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马小鹏小心翼翼地打开小本票,这款邮票由两枚组成,咖啡色底的那张,红脸的黑猴子左臂正攀着树枝,右手举个红色的蜜桃;白色底的那张,土黄色皮肤的红脸猴子正盘腿稳坐,它正对着观众,左右各怀抱一只小猴子在它腿上,两只小猴子的嘴则正好亲在大猴子的左右脸上,可爱至极。马小鹏仔细端详着,这可是黄永玉老爷子时隔三十六年后的又一次猴票作品,1980年庚申年的那款猴票他们是没福气得到了。1980,多么遥远,那时他和赵阳尚未来到这个世界,而今那款邮票快成绝版了,不是他这经济条件的人想买就能买到的,这次的他们一定要珍藏起来。这一年,画家黄永玉老爷子92岁高龄了,极有可能是大师最后一次画猴子了。马小鹏想,他和赵阳,他们俩能活到92岁吗?简直不敢奢望。
买到猴票的第一时间,马小鹏就将这一消息告诉了赵阳,并打算立马将邮票给赵阳快递过去。他没想到,电话那头的赵阳却并没有想象中的兴奋。寄什么?你先放着就是,等什么时候见面了当面给我呗。
马小鹏犹豫了。他并不想见赵阳,他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见赵阳了。放着就放着吧。
这一年,集邮公司的活动还挺多。马小鹏所在的城市在历史上曾诞生过一位与莎士比亚、塞万提斯齐名的东方喜剧大师。夏末时,政府举办过一系列纪念活动,马小鹏所在的邮政公司也发行了一整套的首日封和明信片,他也给赵阳留了一份,盖上了漂亮的纪念邮戳。他在阳光下将明信片上邮戳的黑色油墨吹干,然后将它们夹在某本书里,准备一齐带给他。
现在,猴票装在塑料薄膜袋里,被放在了挡风玻璃前,邮票里两只猴子,噢,不,是四只猴子正随着坑坑洼洼的路此起彼伏,跳舞一般。马小鹏想,那只黑色的猴子就是赵阳,而另一枚中的土黄色猴子就是他,抱在他怀里的是穆晓和孩子。
穆晓唇齿间翕动一下,并未睡熟,她的一只腿从驾驶座和副驾驶中间的空隙搭了过来,险些踢到变速器上。马小鹏有些发火:多危险!她难道不清楚他这个新司机正驾车行驶在怎样的路上吗?进而他又想到,每次出来都是如此,她不是吃就是睡,把他们的新车弄得像火车卧铺一样乱七八糟,她怎么就能为了目的地而将沿途的风景统统忽略呢?出来玩,过程对于她究竟意味着什么?他甚至对穆晓对他十足的信任和依赖略感厌烦,长途旅行,她竟这么放心将自己交给他?而不是与他分担压力。
他的担忧,正随着脚下鄱阳湖的粼波一起翻滚,随着草洲此起彼伏。
马小鹏驾车行驶在有两层楼高的鄱阳湖大堤上,施工车辆不时交会而过,仅有两车道宽的大堤每有车辆交会似乎都在颤抖、在喘息,然后灰土漫天,接着,灰土在夕阳中变黄、变淡,直到眼前再次出现鄱阳湖的开阔。马小鹏一次次冲进漫天灰尘中,被包裹着,那种神秘感让他无所畏惧,等神秘劲一过,堤坝与湖面的落差赫然眼前,又让他意识到欣赏美景所要付出的代价,他一次次告诉自己脚下的路有多么艰险,稍有不慎,他将随着整辆车葬身此处。那样的话,穆晓一定会发疯,就为了送几张破邮票。简直不可理喻。倘若是在几年前,在他还没和穆晓结合、儿子还没降临时,马小鹏曾一度有些期盼生活中的“壮烈”或“戛然而止”的状态,起码比庸庸碌碌一辈子到头来再得个老年性痴呆、半身不遂等病症来得利落些,也干净些。后者他见多了,他居住的小区就有,还不止一个,他们借助轮椅或板凳行走,面目扭曲,鼻涕和口水左一把右一把。有一个老太太则要人从后面环抱着她,一点点帮着她练习挪步。他想,倘若有一天他变成这样,穆晓绝不会对他这么好。毕竟生活的境遇早已变化。成家以后,他越来越意识到作为父亲、作为儿子,自己肩上的责任,这种责任时常让他喘不过气来。儿子出生时得了两场大病,将他折腾得不轻,人一下子就老了。等这两年儿子大些了,他又陷入了另一种压抑中。好比这一次,赵阳在电话里激动地说,鄱阳湖的蓼子花开了,难得一见的“草原花海”,来看看吧?马小鹏想,机会总算是来了。他排队买的丙申年猴票,从春天拖到了秋天,连他盖了纪念戳的首日封也拖了整半年,还叫什么首日封了?都趁机带给他吧。他当真想去,毕竟有几年没见赵阳了。可是他休周末,穆晓也休,孩子幼儿园也放假,哪有不带她们一起的道理?那要如何给她们俩“交代”呢?他毕竟不是公务外出,是给他送邮票,是散心游玩。倘若真是丢下她们只身而去,好像证明了老同学赵阳在他心中比老婆孩子还重要似的,即便马小鹏不得不承认,多年以前,赵阳的确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马小鹏思忖了很久,最终也没能找到给她娘儿俩“交代”的理由,就只好带上她们一起。
眼下,这样的越野行令人狂喜,出来玩就是要舍弃高速、走乡村公路、走土路,这才有意思嘛!邮票里的猴子在挡风玻璃前跳跃,梦里曾多次出现的这一幕格外熟悉。在梦里,或许出现在车窗外的是湿漉漉的雾气,是裹挟着越野车的蓼子花海,而不是尘土。但其实,差不多是一个意思。
马小鹏是中午赶到赵阳所在的县城的。一下车,他就将邮票递给了赵阳,本以为赵阳一定会很激动地打开看,然后认真地将这份礼物收好。这礼物的难得之处他们都清楚,不光是猴票的问题,更是黄永玉的猴票。黄永玉的名气,学美术的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不承想,赵阳却并未打开看,他刚接过就又塞给了马小鹏,你先拿着,我没带包,晚点儿再给我。马小鹏内心百感交集,只得将邮票扔回了车里。
缘分这事真是奇妙。二十年前,他还在东北的边陲小镇里读中学,而赵阳的家却在这鄱阳湖滨。当时流行一时的“交笔友”的游戏将两个不相干的人联系到了一起,他们彼此都喜欢绘画、喜欢邮票,就在你来我往的信件中交流着他们共同的爱好。他们每次给对方去信都会选择不同的邮票,然后小心翼翼地将信封上盖了邮戳的邮票撕下来,夹到本子里。高考时,马小鹏成绩不理想,选来选去都找不到合适的院校,赵阳说要不来我这儿吧,我们一起读师范。就这样,马小鹏奔波了两千多公里、跨越了大半个中国来到江西,和赵阳一起读了师范学校的美术专业,成为同一专业不同班的同学。马小鹏清楚地记得,开学的第一天,他就急切地带着邮册跑到了赵阳的寝室,两个“笔友”终于从信纸里走到现实中。他们彼此翻看着对方的集邮成果,两个世界终于融合到了一块儿。在邮票盛行的时代,作为学生的他们并没有钱去购买新发行的邮票,说是集邮,于他们而言无非就是将旧邮票搜集到一起。
中午饭时,赵阳叫来了他一胖一瘦两个朋友作陪。这两个人长得实在有点丑,一胖一瘦、一黑一白,就跟《鹿鼎记》里的胖瘦头陀一样,马小鹏索性就在心里这么称呼人家。对于那个又白又胖的同事,马小鹏从第一眼见时便觉相熟,似乎在哪儿见到过,绞尽脑汁却没想起来,只得作罢。难得见到赵阳,平白多出来两个不相熟的人,马小鹏很无奈,却也没办法,到了赵阳的地盘,理应听他安排。马小鹏想,他这样安排自有他的道理。推杯换盏间,马小鹏总算听明白了赵阳的用意,赵阳是邀请他来鄱阳湖玩的,这两个朋友恰巧都在鄱阳湖旁的村子里工作,“胖头陀”考取了村干部,“瘦头陀”考取了乡村教师。赵阳介绍说,他俩都是我以前的同事。
马小鹏这才猛地想起来,我见过你。他指着“胖头陀”说,说完,心里咯噔一下,生怕被看出什么似的。
对方略显尴尬。是吗?我倒想不起来了。那胖子说。
马小鹏放下酒杯,心想这话要是反过来就对了,要是那胖子说见过他马小鹏,他来回应说想不起来确乎更合理,因为胖子的那张脸实在是不容易让人记住的类型。话到此处,多年以前赵阳在县郊那所私立中学做老师时马小鹏曾多次来找他的那些尘封往事似乎就将被揭穿。
马小鹏赶忙补充,也可能是我记错了,但我应该见过你,以前赵阳做老师时我来找他玩过。
本以为这么轻描淡写就过去了,谁承想赵阳来了一句,不可能吧?我记得你那时来找我时我宿舍已经搬到了一楼,没和他住隔壁了吧?
马小鹏说,不是那次,我记得是在顶楼,我们还在阳台写生——
对——我记得——胖子话到一半,趙阳立马打断了他,很羞愧似的,不可能,你就来过一次,那会儿我已经搬了宿舍。
马小鹏与赵阳对视了一眼,他本以为赵阳是在掩饰什么,不承想赵阳的眼神着实令他失望。马小鹏顿时失落起来。自己究竟来过几次呢?马小鹏在心里回忆着,不是两次就是三次,甚至四次,肯定不止一次。他清楚地记得有一回赵阳说想画画了。赵阳在电话里说,很久没画画了,学校周围的景色特别漂亮,好想画一画。马小鹏说那你就画呗。赵阳说一个人没意思呦。马小鹏由衷地喜悦,那周末我去陪你画吧。赵阳还是这副德行,以前在学校时他一旦想画画就会叫上马小鹏。他们的学校位于南昌的东郊,校园很大,景色宜人。赵阳偏偏说多数人都看得到的那就不叫景色了,他就带着马小鹏在校园的犄角旮旯里找旁人不容易见到的风景,去找那些值得特写的部位。马小鹏记得那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他带着画板就来了鄱阳湖边当时赵阳教书的学校所在地——白马镇白马中学。毕业后,他们都从事了跟绘画八竿子打不着的工作,马小鹏进了邮政企业,赵阳则回了老家,在白马中学里教语文课。他们将画板立在阳台上,随夕阳的光眺望过去,远处是金灿灿的麦田,再远处是烟囱里冒着烟的工厂,近处国道公路在蜿蜒,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凡·高的“麦田”系列。太久没动笔了,马小鹏明显不在状态,画了一会儿他就停笔了。再看赵阳,他竟然流出泪来,在泪水中,赵阳像一头疯狂的狮子,将画板和油彩踢翻在地。
鄱阳湖的水草正疯长。一行人选择在蓼子花开得最繁茂的地段停了下来,沿着堤坝小路向湖底走去。
时间已近黄昏,远处夕阳将天际和湖水染成了金色,金色再往上是白色泛蓝的天空,下方是受秋季枯水期影响,而裸露的大面积湿地、滩涂,近处才是成片的蓼子花。蓼子花是粉红色的,连成花海后颜色逐层加深,走进花海中才发现那些蓼子花正与滩涂上的白色芦花连成一片,粉中有白,像点缀的雪粒。蓝天,晚霞,滩涂,蓼子花海,这些颜色拼凑在一起,蔚为壮观,像一幅美妙的油画。只不过由于水汽和阳光的光合作用,加之大堤上弥散开的尘灰,竟将这幅油画的对比度调低,有了些中国水墨的朦胧味道。
这景致,真的该被画下来。马小鹏心想,倘若他的画功没退步,他一定会将这美景画下来。如果他梦想尚在,他也会期待将这美景画成一枚邮票,寄向远方。
赵阳拉着他那两个旧日同事,狡黠地对说,我们开个小会,你们先走。
马小鹏心里微微一颤,美景顿时被打了折扣。马小鹏不知道他是被美景所震撼,还是其他,比如浪漫、情怀……这些,显然与身边的人有关,并不是随便一个路人甲能给予的。这一次,不论是来看蓼子花,还是来给他送邮票,都不过是借口罢了,他只是觉得是时候见见他了。
赵阳的妻子领着女儿走在前,马小鹏则带着穆晓和儿子走在后,他们向蓼子花海深处走去。马小鹏回头看赵阳,透过蓼子花的缝隙,俨然可见三个男人的背影——在花海深处解开了裤腰带。马小鹏若有所失,赵阳没叫上他,甚至连问都没问一句。同时他又有点小高兴,在赵阳心中,他和别人终究是不同的。
一行人散漫地在布满蓼子花的草洲中间穿梭,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关乎鄱阳湖的话题。鄱阳湖的水运历史、干旱的季节、蓼子花和草洲的形成,他们乐此不疲,马小鹏却左耳进右耳出。水草繁茂,最深处有一人多高,马小鹏将自己隐藏其中,被柔软包裹着,格外安全。身为北方人的马小鹏,对赣鄱大地的历史可谓毫无所知。多年以前,对于大学生马小鹏来说,南方就等于一个赵阳,他的全世界也等于一个赵阳,他就这么一个朋友,这从他只身来到南方读大学那一刻就定下了。他心里清楚赵阳的世界却并非如此。现在,马小鹏的心思全在孩子身上,在陪伴赵阳的那女人身上,赵阳的孩子和女人,他都是头一次见。女人是小学教师,为人师表的她看上去细腻、知性、有素质,一脸旺夫相,不仅如此,在马小鹏看来更难能可贵的在于她没有90一代少妇那股娇滴滴的“作”劲,看上去是个过实在日子的好妻子。马小鹏心满意足。她挺着个大肚子,不时一手撑着腰一手抚摸着自己的肚皮,那里面是她和赵阳的第二个幸福的结晶,这让马小鹏的心底泛起一层苦涩的涟漪,他都有第二个孩子了。再看那女孩,倒比男孩子淘气,这一路,都是她领着马小鹏的儿子东跑西颠,一会儿看旱死的鱼,一会儿拿石子往水里扔,后来干脆扯着马小鹏的儿子朝不远处的渔船跑去,渔船上立着两只捕鱼归来的鸬鹚,也不知那两只鸬鹚彼此是什么伦理关系。
鸬鹚、渔船、草洲、蓼子花、孩子……马小鹏突然想到什么,趁大家伙没注意,他折身疾步返回到大堤上,打开车的后备箱,在里面拿出一块A3纸大小的蓝色画板,又翻出一张画纸,然后冲下大堤来。为避免尴尬,他将自己隐藏在草洲里,像个偷窥狂一样偷窥着眼前的美景,手中的2B铅笔尽可能飞快地在纸上飞舞起来。赵阳发现了他,赵阳看了他一眼,又回过头去,好在没被其他人发现。他的举动,明显不伦不类,在世俗生活里,他的疯癫足以被人耻笑。他也不允许他的画里有这些可能耻笑他的人,除了眼前鄱阳湖的美景外,有的只是两个孩子,他们站在渔船的船头,一个弯腰指着地面给另一个看着什么。铅笔勾勒出两个孩子的轮廓后,马小鹏眼角湿润了,这是他的孩子和赵阳的孩子啊!时光荏苒,在丙申年深秋的鄱湖岸边时空交错,让他一时缓不过神来。他记得当年是在学校图书馆的楼顶,他们翻着一本从图书馆借出的杂志,上面有一枚描述友谊的邮票,赵阳说起他最喜欢的两句诗,是杜甫的《赠卫八处士》里的两句:“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马小鹏清楚,当时赵阳就是说给他听的,如今全都应验了。准确地说,那时他就已经知道现在的结果,生活大抵如此。马小鹏不免伤感起来,想到赵阳结婚时他都没来,那时他在赌一口什么样的气,他早已不记得了。后來赵阳干脆说,不来就不来吧,等你结婚我也不去。赵阳说的却不是气话,赵阳理智地说,咱俩没必要非那样,谁都别给谁包红包,省了!也免俗了!
眼下,马小鹏却后悔起来,俗气有什么不好?他真想彻头彻尾做个俗气的人,跟赵阳变成金钱酒肉朋友,也省得心里这般难受。过去的岁月,他赌了太多的气。两个人最好时好得如胶似漆,他们挤在学生宿舍一米宽的单人床上翻看集邮画册,每次写生他们都相约一起去,他们画过山、画过水、画过天、画过地,甚至画过彼此的裸体,画裸体时他们开着下流玩笑让对方把自己的物件画大点儿,对方不服气,两个人竟都脱光了比起大小尺寸来……那时他们那么年轻。可后来竟变了,慢慢认真起来,变得凡事都过不去了。马小鹏对自己的付出越来越在意,对赵阳的反馈越来越在意,当感情逾越了友谊的界限,心里的重压总是让马小鹏无法喘息,他多次发疯一样地将赵阳的一切联系方式拉黑,他学会了在雨中奔跑,学会了抽烟,学习用一切方式让自己失忆。可事与愿违,每一次都过不去,就这么反复闹腾着。后来,当他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赌气竟变成赌着赌着就忘了。生活变得有那么多事情要他操心,他甚至都不知道还有什么事好值得生气的,等他再次接续上一次的气、上一次的故事,回想起来,日子已经一晃过去了几年,他们竟很多年都少有联络了。
他们沿着大堤走走停停,半天开了几十里,直到蓼子花海在他们身后隐退,变成了纯绿色的草洲。
你等过两个月再来,就更壮观了。鄱阳湖最好看的季节是冬季,候鸟都来这儿过冬,摄影家的天堂——也是画家的天堂。到时可热闹了。赵阳说着。
那你可以每年都来画画。马小鹏说。
我又不是画家。
不是画家就不画画了吗?
啧——早不画了。
那你还叫我来干什么?
马小鹏生气了。他没有再来的打算,甚至对于此次冒冒失失前来,都有些后悔。他想,这一次已经够热闹的了,他着实不喜欢这样的热闹。
晚饭是“胖头陀”安排的,在与鄱阳湖一堤之隔的另一侧的一个生态农庄。顺着堤坝走下去,农家乐建在一池人工湖之上,盛开在一池的莲花中间,集垂钓、野炊、唱歌、住宿等休闲娱乐于一体。倘若没有胖瘦头陀在场,人再少点儿,马小鹏会由衷喜欢这个地方。可现在,“胖头陀”的热情总是让马小鹏觉得尴尬,可毕竟“胖头陀”是好意,怕失了东道主的礼仪。“胖头陀”最先从赵阳以前所任教的学校辞职,之后考取了村干部,正好就是这一带管辖区域,到了他的地盘就只好听他的吧!赵阳用神情表示了无奈,他的无奈倒让马小鹏的尴尬烟消云散,喜悦由衷而来。马小鹏也就不在乎自己是否多余了。晚饭吃到一半,马小鹏就觉出了气氛的异样,大家都在聊赚钱、聊股票,马小鹏觉得自己格外可笑,他是给赵阳送邮票来的,一个丙申年的小本猴票不过十二元钱,在他们的世界里算什么?接着,这农庄的老板和老板娘过来陪酒,连小姨子和把兄弟都过来了,包厢里挤满了人。马小鹏意识到这是一场庸俗意义上的应酬,身为村干部的“胖头陀”只是以马小鹏一行为由头跟农庄老板要了一顿吃请。到头来,马小鹏一家只是陪衬罢了,赵阳也是。他觉得很可笑,又不得不逢场作戏地迎合着,将晚饭演绎成一处笑话。
他俩没吃几口,就从主桌上撤下来坐到旁边的沙发上唱起歌来,名义上为大家助兴。赵阳为马小鹏点了一首《兄弟》,马小鹏则给自己点了一首《十年》,都符合马小鹏的心境。鄱阳湖的夜,在喧嚣的歌声中变得更加静谧,静谧得让人欢喜。两首唱毕,马小鹏从屋里走了出来,钻进大堤上的车里。
马小鹏和赵阳年轻时曾梦想成为一名画家、或邮票设计师,其实差不多,也不冲突,黄永玉老爷子不就是嘛,人家还是作家。后来马小鹏逐渐认清了现状,梦想嘛,终究是个“梦”,能进邮政企业,他想着能在函件局设计个封片卡、台历挂历或宣传画之类的也行啊,可偏偏进了电商局。赵阳呢,一开始是老师,但不教美术,现在是公务员……他们离自己的梦想也越来越远了。马小鹏内心五味杂陈,邮票里那只左臂攀着树枝、右手举个红色蜜桃的黑猴子仿佛在笑他,那只土黄色皮肤、盘腿稳坐的红脸猴子也在笑他,连它怀抱中的两只小猴子也在笑他。马小鹏拿起它们,恨不得撕掉,又不忍心,只好将储物夹打开塞进去,不再看它们。
马小鹏从车里出来。深秋十月,从堤坝头顶吹来的冷风一下就将人彻底侵透。马小鹏忍不住将下午在草洲里画的速写画从包里掏出来,用铅笔在留白处题了几句小诗:
多年以后
我们终于沉入湖底
向鸟儿挥手
学着鱼,吐最后一个泡
与那喧嚣相忘于江湖
你看,水草茂盛起来
长出一把的年华
……
赵阳也走了出来,问,在干吗呢?
马小鹏鬼鬼祟祟地试图将画收起来,被赵阳制止了。赵阳将画展开,借着农庄湖岸的灯光,仔细端详着画的内容,又看了一眼马小鹏刚刚题上去的几句诗。
真好。赵阳说。
好什么?
你一点都没变,这么多年还始终保持着对画画的热爱呗!随车带着画板和画纸。
马小鹏有些羞愧。事实上,汽车里的画板和画纸只是一个巧合,一周之前他孩子所在的绘画兴趣班刚刚举办过一次写生,是孩子落在车里的。
你呢?马小鹏问。
你说巧不巧,赵阳说,我家着过一次火。
马小鹏着实吃了一惊。
赵阳不紧不慢地说,不要紧,人都没事,房子整体也没事,书房烧坏了,我的那些书、画,也包括邮票,烧得一干二净。
马小鹏伤心极了,他是替赵阳伤心。也替自己难过。也就是说,从他们少年时代开始,赵阳从寄给他的那些信上撕下来的各式各样的邮票、那些承载着马小鹏无数记忆的老邮票都没了。那些虽不是什么珍贵的票种,无非90年代普遍使用的八分的故宫邮票、长城邮票,再到后来的二十分的、五十分、六十分的……但對他来说,意义非凡。属于他的记忆,在赵阳的世界里消失了。对赵阳的记忆,在他的世界里抹也抹不去。
赵阳,那你——
不要紧。都过去了。人没事就行。跟人相比,这些都算什么呢?小鹏,邮票你带回去吧。我想了,我那些东西都没了,单独留本丙申猴票算什么?显摆吗?这也不值得一显摆!放你那儿,你帮我存着吧!——你说这个时代,这些都算什么呢?我上次去县新华书店转悠,想买本画册,书店里一个人都没有,跟鬼屋一样。现在人们拿在手里的是手机,满脑子想的是如何赚钱。
马小鹏不置可否。关于赚钱的事,穆晓也是多次提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二人沿着搭在水面上的木质走廊走到了水塘中央。荷塘月色之下,赵阳将双肘伏在栏杆上,马小鹏打量时,发现自己也正做着同样的动作。
这么多年你真是一点没变。赵阳打量着马小鹏,又重复了一遍这句。
马小鹏的心猛地紧了一下,“这么多年”的距离就在他的一句话里立马消解,仿佛昨天还见了面一样。马小鹏看着赵阳,对方眼里湿漉漉的,其实他自己也一样。
你也一样,没变。他说。
算了吧,我老多了。赵阳说。
除了头发少点儿。从一见面,马小鹏就发现了,以前赵阳的头发只是稀疏些,现在已几乎谢了顶。
其实我也老,我皮肤很差,细看很粗糙和松弛,毛孔很大。
赵阳没作声。
突然好想抽支烟。马小鹏脱口而出。
还有抽烟的习惯?
当然没有。马小鹏知道自己是没烟瘾的,以前是为跟赵阳的关系弄得自己不得安宁,他学会了抽烟。现在他则想叼着烟侃天侃地侃大山,最好说话间再蹦上几个脏字几句醉话不是更像男人间该有的样子嘛!偏偏他们都活得太细致。光细致倒也罢了,他们又熟得如同脱光了的人,脱光了也不尴尬,就像对方的影子。可问题是,这样的交流在外人看来,尤其是在他们各自家人眼里会不会显得有些怪异呢?
他们小心翼翼,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什么、隐藏着什么,他们的青春和梦想,诸如此类。在各自的家庭面前,曾经的青春翻篇到了另一个世界。
两个人就这么站着,也不说话,却胜过了万语千言。晚风从他们身后拂过,像在彼此耳间说着私话。远处的餐厅里推杯换盏声持续不断。看着远处草地中央燃起的熊熊火焰,赵阳说,篝火晚会还没开始。
马小鹏没吭声。
但恐怕我们赶不上了。赵阳说,预订的酒店在县里,现在已经很晚了。赵阳看看表。
事实上,马小鹏对所谓的篝火晚会丝毫提不起兴致,跟一些不熟识的人在一起假装热烈地狂欢,实在无法与跟赵阳这么在晚风里站一会儿相比。他此行的目的也绝不是吃喝玩乐、逍遥快活。他此行的目的,就只为这一刻。
多年以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再次有了微妙的变化,那份感情早已越过浓烈的坡峰,开始向另一种境界靠拢。马小鹏越来越珍惜赵阳这个朋友,跟他在一块儿的感觉就是一个词:舒服。
马小鹏嗤地笑了一声,刚才好尴尬。
赵阳眼睛瞄了一眼包厢,意思一下也就行了。赵阳说,我这次本来没想叫他,我只叫了那个瘦的同事,被他知道了非跟着来了。
嗯。马小鹏点点头。提起这个,我倒要纠正一下,马小鹏说,之前你在乡下的私立学校教书时,我的确见过这个胖子,就是你住在顶楼宿舍的时候,而且你住在顶楼宿舍时,我来过两次。这事我回忆了整整一下午。
赵阳没有吭声,他想了一下说,或许吧!你又认真了。
是的,他再一次认真了。中午说起这个话题,让他挺不高兴。
不一会儿,穆晓也从包厢里出来了,远远地,她一手拽着儿子、一手拿着饭碗,到包厢门口的椅子上给孩子喂饭。马小鹏瞥见穆晓带孩子出来,不由自主向反方向移动了几步,背对着他们。
这几年你过得怎么样?赵阳问。
马小鹏知道他想问什么,可这么假大空的问题该如何回答呢?只好说,挺好的。说完这话,自己心里又觉得够假的。
这么多年,马小鹏不止一次将自己关在屋子里,思考这段婚姻是否要继续下去。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他肩上的责任不允许他那么做。事实上,穆晓并没有错,只不过是跟他不合拍。在他看来,穆晓这女人总是那么强势,执拗,急性子……她身上有太多缺点,最让他不能忍受的就是她对待娘家亲戚、朋友、同事都要比对待他跟他父母要好。其次就是她的执拗,她实在是太有自我的想法和主意了,大事小情都是如此,她从不跟他说,很少征求他的意见,就好像那些事都是她个人的事而不是这个家庭的。或许,她觉得即便跟他说了也无法得到他的认同。他们像两条平行线,永远相交不到一块儿。
工作这块儿呢。就是天天下乡跑邮乐站点建设、搞金融客户引流和积分兑换。这些,他都无法跟赵阳说,说了他也不懂,还得从头将邮政业务给他解释一遍。可他做的这些究竟有什么用?起到了什么效果?恐怕有些事连他自己也解释不清楚。
你呢?马小鹏问。问完又故意补充一句,你挺幸福的!
赵阳唇齿间发出啧的一声,这是他的习惯,口头禅似的,也是他惯用的伎俩。马小鹏多是理解为一种标榜成熟式的默认,相当于“那还用说”。他突然觉得心里不是滋味。
月亮升高了。月光下,湖光粼粼,近处的草洲在夜色中疯长起来,似乎能听到拔高的声响。
人们从包厢里鱼贯而出。穆晓竟然醉醺醺的。
你怎么喝成这样?
不是你让我喝的嘛!
是的,马小鹏要开车喝不了酒,吃饭时就给穆晓开了一瓶啤的。他只是感觉不能无礼地辜负了“胖头陀”的一番好意,既然这聚会大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参加的,那他的家庭总该有个披挂上阵的。
可我没让你喝醉!马小鹏斜了穆晓一眼,像什么样子!说着,从她手里拽过孩子,还指望你带孩子呢!他小声嘟囔道,快步跟上了人群。穆晓则默默地跟在他身后。
是的。她连带孩子也不会。孩子长这么大,都是他跟他父母操持着。穆晓就是他心中有点“作”的女人,她唯一的优點或许就是尚有几分姿色,除此外,实在想不出其他的。事实上他心里清楚,她的姿色也不是他看中的,他对她最满意之处莫过于生了个可爱的儿子。
马小鹏最后一个来到堤坝上,却最先钻进了车里。安顿好孩子和穆晓,他没有再出来。他甚至连车窗也没摇下来。他看着窗外的人在寒暄着告别,自己是个局外人,他为这次前来与赵阳会面后悔不已。
在车子移动之前,他终究还是礼貌性地摇下车窗,与堤坝上送行的店老板挥了挥手。那老板一家同样假意挥了挥手,将更多的目光瞄向“胖头陀”的车子。
马小鹏再次摇起车窗,任由黑夜将自己吞没。
赵阳的车早已走远,尾灯越来越弱。
他看了看后视镜,出乎他意料的是,穆晓在流泪,她侧脸面向车窗,正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泪水。
马小鹏有些紧张,穆晓这是怎么了?她预感到什么了吗?他将目光与穆晓一起望向车窗外,车窗外是同样翻滚着的鄱阳湖和疯长的水草。
【责任编辑】 铁菁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