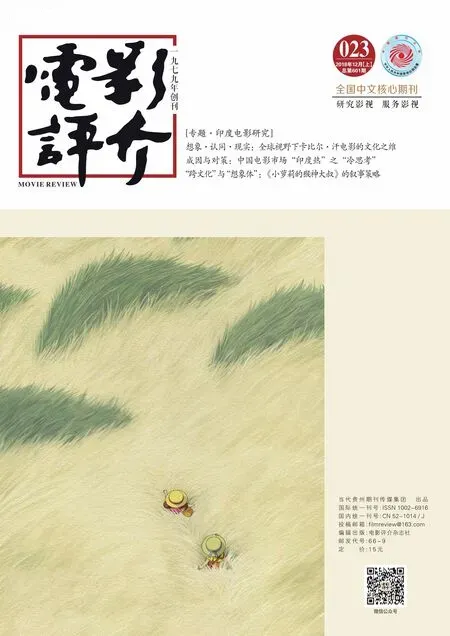想象·认同·现实:全球视野下卡比尔·汗电影的文化之维
2018-04-20
在全球化语境下,印度电影纷纷走出国门。针对印裔移民,印度电影输入至北美、南美,同时,2017年伊始,印度电影迅速打开了中国大陆观众观影的一扇窗,在对好莱坞大片的万分期待中,为印度电影留有一席之地。一时间,一股不同于大陆电影的印度电影潮流冲刷了观众对电影的认识,并愈发发酵升温。印度电影如《摔跤吧!爸爸》(2017.5.5)、《神秘巨星》(2018.1.19)、《小萝莉的猴神大叔》(2018.3.2)、《起跑线》(2018.4.4)、《巴霍巴利王:终结》(2018.5.4)、《厕所英雄》(2018.6.8)密集般地占据中国电影市场。印度电影的海外输出,不仅建立了印度移民观众的文化认同,也让中国观众在司空见惯的励志的,温情的,商业性的,娱乐性的影片类型中体味到不同的滋味——对男女地位、宗教冲突、教育等现实问题的揭示和批判,让观众在体验电影娱乐之时,不乏深思,逐步迈入与印度电影共建的情感圈中,大陆观众愿意体认印度文化并从中得到一定的精神满足,延伸与印度文化的想象性关系。印度导演卡比尔·汗的电影作品,在共性的电影叙事主题上不断尝试探讨印度文化想象的建构和传播,试图将印度电影的文化想象融入区域化、世界化中,其影片《小萝莉的猴神大叔》进军中国市场,又一次有力地验证文化认同的重要性。
一、全球性叙事主题与民族性叙事策略的缝合

电影《小萝莉的猴神大叔》剧照
在卡比尔·汗的电影作品中,导演思考了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反战、反恐、倡导宗教宽容不仅仅是印度面对印巴冲突时的内心祈祷,更是全球人类追求的和谐世界;男女平等、消除差别对待是人类世界中男性与女性之间一直追求的性别权利;彼此尊重、坚定信念更是各国电影所传达的人类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卡比尔·汗电影的叙事主题具有普世的价值,它给全人类带来了反思。影片《喀布尔快递》(2006)以“9·11”事件为背景,讲述恐怖袭击后,美国发动反恐战争入侵阿富汗,塔利班武装分子的“境遇”。不得不承认的是,恐怖事件的发生是施暴者与受害者共同的伤害,为从根本上遏制矛盾双方的冲突,卡比尔·汗尝试一种和平的解决方式,让两位印度记者以及一位美国记者“护送”塔利班分子回巴基斯坦;影片《纽约》(2009)探讨了尊严与信任,“9·11”事件发生后,美国FBI绑架在美的印度移民,主人公Sam 4岁定居美国,依旧无法逃脱这次残忍的扣押,历经9个月如动物般毫无尊严的生活,被迫走上恐怖分子的道路。显然,被尊重和信任才能化解移民的身份焦虑,才能立足于美国的现实生活中去;正如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存在的宗教矛盾和克什米尔问题,敌对在这个和平年代依旧存在,导演将宽容、彼此尊重、理解的思想灌输于影片《代号猛虎行动》(2012),印度对外情报局(简称RAW)特工与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简称ISI)特工之间忠贞的爱情示范了敌对双方互相理解的难能可贵;同样,影片《小萝莉的猴神大叔》(2015)中,哈奴曼神的信徒猴神大叔不顾艰难险阻,送小萝莉回巴基斯坦,导演将感人至深的温情缝合于宗教冲突的探索中,这不仅是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矛盾的暂时消解,更是全人类对各宗教间示以宽容和尊重;倡导公平、正义是影片《幻影》(2015)对2008年11月26日的孟买混乱,印度人民被恐怖袭击后的心声表现。卡比尔·汗创造了一位超级英雄,让他的无往不胜去制裁孟买混乱事件的袭击者——虔诚军,在超级英雄的车战追逐、徒手搏斗的挺身犯险又全身而退中,人们显然尝到了争取公平正义的自豪感与自尊感;影片《黎明前的拉达克》(2017)以一段感人诚挚的兄弟情,表达战争对人类的伤害,仇恨迷失了信仰的方向,只有大爱才得以保证家族小爱。
卡比尔·汗电影作品的叙事主题具有共通性,是全球人类一直以来竭力探索的命题,也是全球人类产生认同感的文化表现,蕴含普世价值。具有印度性的叙事策略以小见大,将印巴冲突、恐怖袭击、宗教冲突缝合于卡比尔·汗的马沙拉电影(融动作、喜剧、爱情等多种元素于一身的电影类型,伴有优美歌舞和华美场景,“马沙拉”本指印度美食中的香料混合物。),通过爱情、亲情、动作等因素激发人们的情感共鸣,完成呼吁公平正义、和平以及宗教宽容的全球性命题。同时,卡比尔·汗影片中运用影像语言再次碰撞人类心灵,电影使人类可见,“能对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团结,互相习惯和互相了解起些促进作用的也许还是电影艺术”。影像符号以其民族性、反复性潜移默化地侵占视觉,而影像符号的共通性,再次实现人们对影像所代表的文化的参与与认同。首先,卡比尔·汗的电影作品中,关于战争的影像呈现:战后残垣废墟、逃亡的山区、廖无人烟的沙漠、爆炸后的残车;战后受害者的画面:断腿少年、难民营、医疗救援营、爆炸受伤者;武器的呈现:坦克、随处可见的枪,这是一种恐怖氛围的渲染,一种赤裸裸的反人性的表征,也是无情战争的还原,意在以直接的视觉表现,冲击人类的惯性认知。值得注意的是,导演在影像呈现中的导向之意,敌对双方共歌,同吸烟,共谈板球的画面;神像、圣殿、清真寺等宗教建筑的空镜头;印度潜艇、印巴友谊快车、国家国旗、军人军礼的象征性镜头;万寿菊、婚宴习俗的镜头穿插,一方面是印度、巴基斯坦的文化表现,另一方面,这种具有文化象征的文化景观建构起本土人民、外国人民对于反战、和平、宽容、消除差异的一种想象性关系。“影像中对于印度民俗传统、理想化场景的描述,建构着跨国想象的‘文化共同体’,使得观众能够在集体想象中保持与印度的联系。”它不仅满足人们的审美期待,更重要的是,当影片人物与文化景观相融合,当真实与虚拟相辅相成时,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质被具体化,放大化,凝聚成世界人民的情感共鸣和强烈认同。当情感共鸣的基础建立时,卡比尔·汗电影中承袭印度电影本民族的歌舞表现特色,如同与电影人物一同唱赞歌般将感情由此升华。印度电影中歌舞是本民族的审美习惯,更是以歌曲、舞蹈这一世界通用语言传播民族形象,传播文化思想,可能再也找不到一种“华丽”,不晦涩苦闷的似政治课般常规的文化宣言,在欢愉的情绪下,共舞是团结,是包容,共歌是娱乐化的教化方式。它是似《黎明前的拉达克》中直白地阐明信仰的力量,也是《小萝莉的猴神大叔》中似上帝之音告以人间包容宗教差异,在爱中茁壮成长。
二、对立文化的理解对话与多元文化的认同
“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文化需要一个“他者”,才能更接近文化自我,建立身份的认可和确定。在卡比尔·汗的电影作品中,二元对立的人物身份设置肩负起对对立文化的探讨,导演着力实现跨越冲突的交流和对话。
一方面,电影中的根本矛盾多是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身份的冲突,然而两国本是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和宗教信仰的不同致使同一国家民族的分裂,影片突破了双方矛盾的白热化再现,从印巴人民相似的民族文化传统、神圣的爱情信仰、历史重述方面解构人物身份的冲突,建立文化身份认同,洋溢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影片《喀布尔快递》中,塔利班分子劫持两位印度记者和一位阿富汗司机向导把自己“送往”巴基斯坦边境。初始,塔利班分子持枪威胁记者,狰狞可怕的面目让印度记者害怕不已,紧张恐怖的氛围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当不同身份的四人处于一个封闭的空间内(行驶的车中),冲突显而易见,尤其是阿富汗向导司机随时找机会反抗塔利班分子并施以暴力。渐次,在封闭的空间内开始有语言沟通,来自不同国度的三人,语言沟通完全没有障碍,并不自觉地开始带有独特文化色彩和民族特色话题的争执和讨论,如板球运动员谁最厉害?印度的烟抽起来不伤嗓子;是谁挑起的战争?此时,拿枪的塔利班分子不再是暴力、权力的掌控者,而是沉默者。最终,封闭空间被打破,一行人突遇阿富汗士兵的围堵,闯入一位美国记者,枪的使用者转移了,记者们与阿富汗司机向导成为权力的掌控者。但此时当众人目睹塔利班分子对女儿隐忍的父爱以及凌驾其身上的不公平的说法和看法时,在车上共听印度歌,同抽印度烟时,枪的地位发生改变,成为保护这位心中有正义、有爱的塔利班分子回家的武器。劫持—交流—护送是不同身份、敌对身份交流的方式过程,也是不同文化彼此尊重、彼此认同的过程。
影片《代号猛虎行动》中尝试用爱情化解身份冲突,实现双方用感性替代理性,寻求双方的融合。Tiger和佐雅各为印度RAW、巴基斯坦ISI工作,两国为研制导弹而监视加达维教授,Tiger和佐雅在此次任务中相识,双方故意隐藏特工的身份,却在伪装的身份中相处,共沐爱河。当两人一起出现在加达维教授的书房中时,彼此真正的身份真相大白。面对天然的敌对身份,Tiger和佐雅因爱卸下伪装,也因爱决定离开印度RAW和巴基斯坦ISI。此时,不仅是特工身份的抛弃,也是敌对身份的认同。“当我爱上她的时候,没人告诉我她是敌人,当我已经爱上她的时候,我不理解她为什么会是敌人。”在Tiger的话语中,敌人的概念已经消解,先入为主的敌对身份并不会磨灭双方内心散发出的爱意。爱解构仇恨,面对印巴冲突的历史隔阂和宗教信仰的矛盾,导演试图用爱化解身份冲突,影片结尾处,在Tiger和佐雅共同捍卫两人的爱情时,目标一致的合作成为获得最终胜利的唯一方法。
身份的二元对立不仅是敌对身份的体现,也是不同文化下风俗习惯的差异、宗教信仰的区别,卡比尔·汗在影片《小萝莉的猴神大叔》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文化的相异性,而磨灭不同文化的排斥性,文化宽容才会得到圆满的结局。影片中莎希达是一个6岁仍不会说话的巴基斯坦女孩,帕万是一个极其信仰哈奴曼神的信徒,大家称他猴神。莎希达与母亲走失无意间来到印度德里,遇见了猴神大叔。莎希达失语的身份,避免了两人之间的直接性冲突,不带国家标签的莎希达让帕万放下防备之心以及对巴基斯坦敌对的惯性认知,愿意帮助莎希达。在两人的相处过程中,莎希达不吃素食,跑到穆斯林家吃肉;自然地行伊斯兰教宗教的礼仪;并在巴基斯坦板球队获胜时兴奋无比,隔着电视亲吻巴基斯坦国旗。无疑,流淌在莎希达血液里的文化印记暴露了她的真实身份,暴露了她所在的国家,这是帕万猜测莎希达家在何处时,唯一没想到,甚至不敢想到的国家。对于极度信仰罗摩神的帕万来说,伊斯兰教让他惊恐和排斥。伴随帕万的是,拥有不同宗教信仰,固有的印巴冲突的考验,莎希达与帕万的相处进入另一个模式,有区别的,或妥协或彼此尊重。帕万送莎希达到巴基斯坦驻印度大使馆却无法拿到签证,反而遇到印度人民对巴基斯坦大使馆的一次暴乱,而后帕万被骗,差一点把莎希达卖进不正当的场所。哈奴曼神的教义使帕万点燃心中善良之火,强烈地渴望亲自把莎希达送回家。帕万真正意义上开始走进巴基斯坦,不仅是用坚定的信仰感染印巴边境的军官,准许帕万的“非法”入境,更是印度教教徒走进穆斯林的生活中去。帕万被清真寺的阿訇帮助,在沙哈神殿祈福,聆听伊斯兰教的教义,汲取继续前行的力量。帕万从抗拒走进清真寺到亲身了解体验过后,对穆斯林的接受和尊重,双手合十的罗摩神万岁到真主保佑,帕万完成了对不同宗教文化的尊重和包容。莎希达被安然送回家后,帕万被当成印度间谍,印巴两国的仇恨依旧是最大的阻碍,是凭借个人力量所无法超越的,唯有印巴两国人民一致的呼声和强烈要求,让帕万重回印度。在卡比尔·汗的镜头下,印巴人民完成了一次颇具仪式感的合作,体验到了放下仇恨时共同的,强大的力量,这种爱的力量让莎希达不再失语,终于大声呼喊“罗摩神万岁”时,新生一代终可以在充满爱的环境下,茁壮成长,并开始学会尊重别国宗教文化。
在影片《幻影》中,卡比尔·汗导演选择一种最为激进的方式解决敌对矛盾,血腥复仇是影片中名叫幻影(达尼亚·汗)特工的首要任务,导演放弃与敌对方的交流对话,着重书写了尊严和责任的重要性。影片主人公幻影不顾一切地刺杀操控11月26日孟买袭击案的虔诚军创始人和首席教官,他没有得到国家真正的承认和认可,但为了重拾身为军人的尊严,毅然豁出性命报复伤害印度人民的恐怖分子,寻求印度人一直呼吁的公平正义以及唤回一位军人的职责使命和尊严。幻影的报复行动是印度人民对2008年11月26日的恐怖袭击一次情绪宣泄,也是恐怖袭击7年后,袭击策划者没有受到任何制裁的一次自我尊严的重建,尽管这次复仇行动是属于电影艺术中的假想,却“把它的观众联结在一个集体的梦幻中,一个对他们自己的文化经验理想化的幻景之中”。印度人民终于得以在幻想中真实地触摸正义之枪,以击碎敌人的头颅,寻回自尊,寻回对印度满怀的希望,建立民族自豪感。
另一方面,导演在影片中模糊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之间二元对立的界限,同时将战争是非对错,公平与否的争辩从暴力的思维方式转变为人类化敌为友的信仰力量的探讨上,战争的真正意义是人类对和平的向往,不是恶性循环般地伤害与残暴。此时,和平成为联结印度人民、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的纽带,建构起一致的文化认同。信念是每个人可以掌控的,化敌为友会愈发使自己的信念强大,“只要相信,一切皆有可能”是影片《黎明前的拉达克》与敌人交流的方式,内心对和平的极度渴望才会没有战争,相信和平才会是永远的停战。影片讲述中印边境关系紧张,弟弟离开哥哥去打仗,哥哥陷入无尽的牵挂之中,哥哥拉克什曼面对进入村里的印裔中国人李苓母子倍感气愤又十分恐慌,一度将中印边境的战争归结于中国人的错,而去报复李苓母子。但当拉克什曼尝试放下敌意,逐渐消除内心的仇恨时,发现印度人和中国人竟可以成为好兄弟,化敌为友的信念使得战争结束,中印和解。直接冲突——弱化冲突——消除冲突是卡比尔·汗面对身份冲突时的解决方式,也实现了建立友谊,终止战争的和平梦想。在影片《纽约》中,导演对“9·11”恐怖袭击后的在美印度移民进行探讨,暴力是“9·11”事件般的噩梦,也是“9·11”事件后恐怖分子的蠢蠢欲动。美国FBI特工Roshan和恐怖分子Sam同是印度移民,身在美国的他们有着不同的境遇,两人的身份也是敌对的,特工Roshan为了捍卫在美移民的尊严不惜一切调查所有可能有恐怖分子嫌疑的移民,Sam为尊严而战斗被迫成为恐怖分子。特工Roshan和恐怖分子Sam在一定程度上有着相同的文化身份,同时移民的身份又迫使他们备感焦虑,渴望外来文化被尊重,当他们在美国获得如英雄般的崇拜时,身份才得以认可。恐怖事件才能真正的就此罢休。尊重和尊严成为不同文化下人类的呼声和渴望,成为不同人种共同的文化想象。
显然,卡比尔·汗通过设置身份冲突的矛盾双方,与对立文化进行交流对话,在展现文化异质时,又找到一个平衡点,一种解决方式,在重述历史以及传统文化、人类信仰的寻求中,建立本民族的自豪感和满足感。同时,响应全球化语境下,人类对反战、和平、彼此尊重、宽容、坚定信仰的文化尊重,在试图承认文化的杂多性及内在的文化矛盾中,诉诸文化的多样性,建立多元文化下的构想,以期达到印度人民对本土的身份认可,文化认同,以及全球人类对于多样文化的认同。
三、主流文化想象的消费与文化现实的关注
在全球化语境下,随着好莱坞所建立的电影业霸权的地位,其他国家、地区纷纷联合,共同抗衡好莱坞电影的全球化,并努力将本国(本地区)电影推向世界舞台,同分全球化下电影经济、电影文化的一杯羹。当电影承载本国文化,本国主流价值观影响到全世界时,它已然成为不同于一个国家文化建设的软实力,却不得不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传播民族特色,适应全球化电影潮流。美国这一大国形象显然以其在电影中正面化的形象灌输于世界各地观众的意识中,对美国的崇拜也已离不开对美国超级英雄的想象性满足。“不论它的商业动机和美学要求是什么,电影的主要魅力和社会文化功能基本上是属于意识形态的。”美国导演在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日常生活之间找到一种相关性,不得不承认的是,美国主流价值观显然影响到颇多观众,美国的“梦工厂”为观众创造了太多奢华的梦幻,挣足了观众的电影消费。
在印度导演卡比尔·汗的电影作品中,同样看到影片中塑造了印度的正面形象,充满着理想主义,乐观主义,积极向上的精神,在文化层面上维护了民族国家,在深深的民族自豪感中让本土人民,印度移民、他国人民建立身份认同和文化归属感,由以获得电影的高票房,将印度电影传播至各国各地。甚至,当这种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文化随着时间得到良性反馈时,印度电影就获得了一个优良标签,个体与主流文化的想象性关系会持续延续下去。不可否认的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而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正如阿尔都塞提出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区别于强制性和暴力性的国家机器,把个体“询唤”为主体,使其绝对服从主流意识形态,比如宗教、艺术、文学、广播、电视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询唤’,意识形态剔除了主体对于社会的不满因素,使其产生归属感,参与感,安全感和荣誉感……绝对服从权威”。此时,“意识形态是一种‘表象’,在这种表象中,个体与其实际生存状况的关系是一种想象关系”。在电影中建立的文化想象,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在电影艺术中的外现。一方面,电影作为舆论工具,发挥着文化政治的功能,一方面,电影中的主流文化成为满足观众参与感和荣誉感的消费手段。
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体和文学,艺术等文化手段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把个体“询唤”为主体,获得想象性满足,“这个‘询唤’过程即是一个‘镜像’过程,是通过拉康意义上的‘误识’来完成的,并保证‘误识’不被识破”。在卡比尔·汗的电影作品中,通过媒体的作用,再次强化了电影本身所建立的文化想象,使观众获得一种对镜中的自己虚假的完满感。影片《喀布尔快递》中,两位印度记者和一位美国记者为报道“9·11”事件发生后的新闻,生死置之度外地寻找塔利班分子,并设法采访他,摄影机自然地成为弱势群体得到公平正义的“武器”,又自然地成为恐怖分子残暴的见证。拿摄影机的人,作为事件的外来介入者,围观塔利班分子被群殴而成为照相的旁观者,也是保护塔利班分子回家的参与者,记者承担了世人构想的残暴事件的还原和传播,又隐藏了亲身经历的关于塔利班分子的非残暴的一面。
影片《小萝莉的猴神大叔》中,在网络视频的帮助下,小萝莉回到家乡,猴神在电视新闻的舆论导向下,成功返回印度。在影片中,电视新闻成了唯一反抗警察的“武器”,洗脱猴神被冤枉的“印度间谍”身份。电视中对爱的正能量的报道,打动了影片中的巴基斯坦人民,也感染影片外的观众。《幻影》中,导演通过电视媒体实现了影片的最终目标,“为了世界和平,那(有意伤害)将是一场意外”,利用电视媒体告知公众,恐怖分子头目的意外死亡,从而隐瞒他杀的事实真相。此时,为了安抚大众,电视是假象的传播者,真相的掩盖者。电视的背后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导向,卡比尔·汗影片揭示了大众传媒一定程度上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保护和传播,为使“误识”不被识破,有效维持个体与其实际生存的想象性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讲,印度现实中的,历史遗留的问题,如宗教矛盾,种姓制度,婚姻平等等得以和解,其实是一种构建性的假想,由而引发了对于文化现实的辩证性思考,即文化想象与文化现实关系的思考。
卡比尔·汗的电影中,导演着力将民族性融合于全球性中,全球性叙事主题、议题的普世意义为大众构建和平,宽容,彼此尊重的文化认同,而民族的本土化促使印度人民再次获得身份认同和民族自豪感。在面对不同文化的冲突时,卡比尔·汗尝试寻求一种交流的对话方式,以期达到在文化自觉基础上的多元文化的尊重和认同,满足大众对自身文化的参与,获得文化归属感。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印度电影文化想象的建构与电影经济相辅相成,塑造了印度的大国形象又得到海外更多观众对印度电影的热捧。与此同时,卡比尔·汗找到一种方式或是一个平台,去表达现实,去关注文化现实——文化想象中已建构的平台:“多元文化的尊重,认同,承认,在此基础上才能更接近文化现实,即“为承认而斗争。”只有承认他者,才能承认自己,达到真正主体间的对话,不抹灭文化冲突,以更好地在承认中发现自身的独特性,实现冲突间的理解和对话。卡比尔·汗意在指出印度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用一种引导,教化的方式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他不完全遵从现实,赤裸裸地批判现实,现实之于真实,不能排除主观因素的存在。反之,卡比尔·汗通过架构矛盾冲突间的对话,试图勾勒一方蓝图,提供一种尝试的可能性,一种解决方法,以完成对印度文化现实的另一种关注,从意识形态的想象性建构上,塑造一个民族团结的大国形象。文化想象,并不是趋同,趋同一个乌托邦式的世界,而是为了更加全面认识世界,认识世界的主流文化,反思世界中不被关注的非主流文化,认识世界比直接批判世界更显冷静和客观。在“为承认而斗争”中形成多元文化的认同,实现真正主体间的对话,并非是相互对抗的价值取向,才会更好地维护自身的独特性和特殊性,良性循环之下,现实表达才会在文化想象的浸润中愈发客观,才能以平和的心态关注文化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