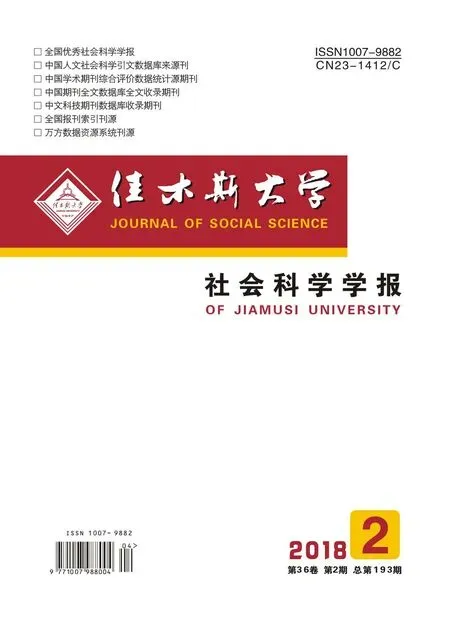魏晋南北朝僧医考论*
2018-04-19高祥
高 祥
(西华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印度,两汉之际传入我国境内。随着佛教的传入也带来了璀璨的佛教文化,佛教医学作为佛教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传入中国后很快与中国传统医学联系在一起,进而形成了佛教医学。作为“佛、法、僧”三宝之一的“僧”又是佛教医学文化的直接传播者,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僧医群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了诸多影响。本文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涉医僧人概况,探讨此阶段的僧医的具体医疗活动以及产生的影响。
近年来关于佛教医学研究颇多,但多主要集中在佛教医学的理论、内容以及与传统医学的交流等方面,而对僧医群体以及僧医具体治疗行为方面研究较少。在僧医研究方面,孟海贵[1]在《佛陀 佛学 佛医》中从对医学认识的角度对僧医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对古印度僧医对待疾病的态度与治疗方法进行了阐述;李清[2]对不同时期的来华僧医与汉地僧医进行了研究,对比其不同的诊断、治疗方式以及产生的社会影响;邵佳德[3]在其文《从借医弘道到悲田养病——试论汉唐之际中国佛教医学的发展及其贡献》中,论述了佛教从汉代传入僧人借医弘道到唐代僧人建立悲田坊利用不同的医疗救助方式达到争取信众的目的,同时也促进了佛教医学的发展。在专著方面李良松编撰《中华佛医文化丛书》中《佛医人物传略》《佛医知识问答》《佛陀医案》《佛医观止》等对古代佛医人物事件进行总结,为研究佛教僧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另有薛公忱[4]在《儒道佛与中医药学》中详细论述了魏晋僧医的群体构成、产生的原因以及治疗方式,并对僧医的社会贡献与局限性进行了分析。还有一些硕博论文对僧医人物进行了研究,如李红的《中国古代僧医综述》从僧医与贵族、文人和世俗医生交往的角度,探讨他们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分析僧医群体带来的社会影响;李清在《中国古代佛教医家的医学成就》一文中总结中国古代佛门医家,对佛门医家的医德理念、医术水平、养生与著述等方面进行研究,认为僧医的医药学活动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总体来看,学者们更多关注僧医的产生与发展,而对具体的各个阶段的僧医及其医疗方式研究较少。魏晋南北朝时期僧医作为独特的文化群体,在早期佛教文化传播中产生了诸多影响。因此,了解早期僧医的医疗活动以及产生的社会反应很有必要的,本文重点即在于此。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涉医僧人概况
佛教自创立发展的过程中,要求佛教徒善习五明①,《大乘庄严经论》卷五云:“若不勤习五明,不得一切种智故。”而作为五明之一的医方明又是僧人必须了解学习的。另外大乘佛教“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理念也要求佛教徒能用自己的技能来解决众生疾苦。佛教传入中国后,尽管并没有强制规定僧尼需要学习医药学,但宗教历来有“借医弘教”的传统,无论是道教还是佛教都希望“藉此宣扬他们的教义以吸引信众……可以激发一般民众的信心与热枕的”[5],在社会上活动的僧人可以以“借医弘教”、“借术弘教”的方法吸引信徒,例如佛图澄善于医术以致于“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与出家。”[6]卷95:2487另外在佛教当中有自己的一套戒律,规范佛教徒的衣食住行,保证自己的个人卫生。佛教徒自觉站在佛教的立场上看待医疗救助,给予足够的重视也对僧医群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从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到公元589年南朝陈国灭亡的369年期间活跃了大批的与医学有关的僧人,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通过翻译佛经间接与医学产生关系的僧人;另一类是直接通过医术治病救人的僧医,而僧医从其治疗方式上也可分为两种:一是僧人懂得医术;二是以佛教理论来治病救人。②对于第一类通过翻译佛经与医学产生联系的僧人大多出现在佛教发展的早期阶段,早在东汉末年时期,就有安息国太子安世高就将包含医学内容的佛经翻译流传。至魏晋南北朝佛教发展需要大量的佛经满足僧众的需求,大批佛教医经也被翻译成中文。在《开元释教录》中,在汉末至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共翻译出佛经一千六百二十一部、四千一百八十卷。而在《大藏经》中记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所翻译的佛教治病经典有21部之多,[7]实际数量应在此之上。如《佛说佛医经》(吴·竺律炎)、《佛说胞胎经》(西晋·法护译)、《佛说咒目经》(东晋·昙无兰译)、《治禅病秘要经》(刘宋·沮渠京声)、《禅秘要法经》(后秦·鸠摩罗什译)等。另外还有在战乱中失佚的《龙树菩萨药方》《龙树菩萨和香法》《龙树菩萨养性方》《西域诸仙所说药方》《婆罗门诸仙药方》等。而关于后一种僧医的记录较多,但大多零散见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正史以及《高僧传》《续高僧传》等著作笔记中,因此笔者将其主要信息搜集汇总以便一览全貌。

表 魏晋南北朝僧医汇总表
二、僧医的特点与治疗效果
材料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僧医有29位之多,实际数量必然是在此之上。在构成上汉地僧医较多,其中有17位是国内的僧人,4位是外来的僧人,还有8位由于资料较少而未见其籍贯。在这些僧医中有的是活跃在历史当中的得道高僧,例如佛图澄、支法存、于法开等,也有很多只是在史书中留下数笔的僧人,甚至有的少有姓名。在时间分期上更多的是在晋到南朝时期,而曹魏由于时间较短未见相关资料。就性别而言,比丘尼资料较少,故不在此论。总体来看,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僧医,无论是异域僧人还是国内僧人其医疗活动大体以具体治疗疾病、提供社会医疗救助和著术传术三种方式来表现,在具体治疗方面主要以传统医术方药为主,另外掺杂异术、禁咒、忏悔的方式;社会保障方面则更多地体现在设立“药藏”、“散药”、“祈祷避灾”等方面;最后,僧医总结方书、传授医术也成为其社会活动的一个形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僧医特点更多体现在其社会医疗活动中。首先,在具体治疗上,从时间跨度上看在佛教传播的前期异域僧人更多的偏向于借用异术来展示宗教魅力,具有神异特色的僧医大多使用神咒、异术使人病痛痊愈。至于中国传统医学色脉诊、针灸在早期阶段较少见于资料,在佛教传入前期翻译了诸多咒禁治病的经书,例如《佛说咒齿经》《佛说咒目经》《佛说咒小儿经》《佛说疗痔病经》等也可说明此点。尽管异域僧人带来的异术以及良好的治疗效果更多的是为了传播宗教,但是这些神异的异术背后往往具有丰富的医疗知识,也影响到后来的汉地僧人,在后期汉地僧人也并不介意借助这种外来医术附会于佛教理论。由本土僧人主导的佛教医学更突出其实际性,更多的是将佛教医学融合于传统医学,在后来的发展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中国传统医术的影子,例如针灸、养生等内容也被僧医所使用。对于内地僧医,范家伟先生就认为“他们在中国文化环境中成长,受中国医学思想所影响,在观念上虽主张佛教理论,但在治疗上则不一定完全依照印度医疗之法”,[22]更多的是将佛教医学理论与中国传统医学进行融合,借鉴传统医学的诊断之法、养生保健等内容形成独特的佛教医学体系。另外,佛教医学认为人有“身”病与“心”病,身病需要药物医术,而心病则需要咒语、忏悔的方式治疗。与传统医学相比,佛教医学对于疾病的治疗侧重于“心”的治疗,[23]这也影响到了僧医。通过忏悔等心理学治疗方式对缓解疾病以及战争对人产生的心理创伤是极其有帮助的。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是战争与疾疫流行的一个高峰期,[24]因此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佛教能够在3世纪到9世纪在中国逐渐盛行,与它为暴力和疾病的受害者所提供的慰藉和救助有密切关系。[3]其次,魏晋南北朝时期医疗资源更多地服务于上层阶级,也造成底层民众医药的匮乏。古代宗教寺院往往具备普世救助的社会保障功能,僧医也愿意通过设药藏、帮助疫疾之人实现普度众生的愿望,如安惠则祈祷天神降神药帮助百姓;法颖在寺内设药藏;慧达散药于金陵。虽然中古佛教兴盛,但寺院设立药藏等福利设施单独依靠佛教徒、僧祇户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国家支持。例如,石虎资助单道开“甚厚”,开则“皆以惠施”;刘宋太宗欣赏释道猛就“月给钱三万……车及步轝一乘”,释道猛“皆赈施贫乏”。尽管单道开和释道猛并未直接建立医药机构,但也可以预见寺院是社会救助的重要一环。也由此可见,僧医以其医疗资源在给予上层社会的医疗保障后,也兼顾到下层民众的生活,保证下层民众的稳定,成为联系统治阶级与下层民众的纽带。最后,僧医总结方书,保留其著作也成为此时的重要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传统医药学的总结阶段,包括药物炮制、针灸腧穴的总结以及对疾病认识等方面,医学家们也更愿意将其记录在册。僧医也更可能借鉴到传统医学的发展模式,在解散、脚弱等方面加以总结,例如《申苏方》《脚弱方》《解散论》等。同时在前期未见僧医著作,尤其是外域僧人,尽管有精湛的医术与丰富的药物知识,也很少见到留下著作,更多的是汉地僧人在后期对社会疾病、方药进行总结。
关于僧医的治疗效果,在统计数据中僧医治疗效果大多较为神异出众,例如,后赵石虎儿子石斌暴病,佛图澄“乃取杨枝咒之,须臾能起,有顷平复”;耆域在治疗衡阳太守滕永文时“取净水一杯杨柳一枝来。域即以杨枝拂水举手向永文而咒。如此者三。因以手搦永文膝令起。即时而起行步如故”;诃罗竭以咒术治瘟疫,“十瘥八九”等。但也不乏有治疗失败的事例,如《高僧传》中“太子季龙太子邃有二子,在襄国,澄语邃曰:“小阿弥比当得疾,可往看之。”邃即驰信往视,果已得疾。太医殷腾及外国道士自言能疗之。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圣人复出,不愈此疾,况此等乎!后三日果死。”尽管佛图澄治疗效果出众,但也不能保证都能取得效果。杯度、僧慧也被视为神医,但是杯度在治疗黄门侍郎孔宁子时,云:“难差。见有四鬼,皆被伤截。……宁子果死。”这样的情况也让杯度束手无策了。而僧慧更多的采用面诊,“在荆州数十年……往至病人家,若嗔者必死,喜者必差。”可见,面对恶性疾病僧慧也没有“奇效”了。另外,从佛教信徒在治病的选择上也可以看出佛教在医疗市场上的地位。《梁书》中记载一向尊崇佛教的史学家沈约因言得罪梁武帝“约惧……因病,梦齐和帝以剑断其舌。召巫视之,巫言如梦。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称禅代之事,不由己出。高祖遣上省医徐奘视约疾,还具以状闻……约惧遂卒。”[25]卷13:243在此期间,巫、医、道都参与了沈约的诊病,唯独没有最受梁武帝尊崇的佛教。另外,当时人们批评沙门参与到世俗生活中“或垦殖田圃,与农夫齐流;或商旅博易,与众人竞利;或矜持医道,轻作寒暑”[26]卷第6:2,可见僧人行医或许并不被大众所接受。
三、僧医群体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僧医群体是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流的结果,其出现与发展对中国传统医术、社会文化都产生了诸多影响。
(一)对中国传统医术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传统医学在认识疾病、治疗手段以及药理学等方面都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首先,在认识疾病上,僧医在认识疾病方面与中国传统医家不同,提出与五行学说类似的“四大元素”理论,即地水风火构成世界万物,即“人身有四病,一者地,二者水,三者火,四则风……四大各有一百一病,合为四百四病”,这种“百一”学说被医家所借用,如陶弘景在《补阙肘后百一方》中自序道:“人有四大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后至孙思邈《千金方》中也将五行学说与四大学说杂糅一起并用。另外,“百一”学说中“四百四病”皆有药方,也促进了医家搜集方书,整理医学古籍的习惯,使得魏晋南北朝成为盛产方书的时代,其方书不仅限于世医之方书,还有佛家与道家的方书。[27]其次,在治疗手段上补充传统医学的不足。魏晋南北朝时期,僧医在治疗“脚弱”、“眼障”和“心理疾病”方面有独到之处,是汉地医家不可比拟的。在眼病方面,慧龙道人的“金针播障术”是有史记载的最早手术治疗白内障的史实,[28]后世医家多有记载;在脚弱方面,支法存、仰道人等都善于治疗,并留下方书供后世医家学习;在心理治疗上,僧医利用忏悔、祈祷等方式缓解心理压力。因此,僧医提供的新的治疗手段尤其是外科和心理疾病方面补充了传统医学不足,而魏晋南北朝频繁的战争也为后来传统医学的发展建立发展提供契机。最后,在药理方面更多地体现在来自异域药物的使用以及“药王”思想的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异域僧人从天竺或西域携带相关药物来华,结合汉地药物丰富了传统医药学。在制药上,僧医更多的使用酥、蜜、糖、石蜜以及芳香制剂来合成药物,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记载:“婆罗门胡名船疏树子,国人名药疗病,唯须细研,勿令粗。皆取其中仁,去皮用之。”在药物使用上,佛教禁止杀生普遍使用草木与矿物类药,阿魏、龙脑、木香、郁金等运用到传统方药上。天王补心丹以及印度和西域香药的大量引进并形成活血化瘀、芳香开窍一类治疗则就是僧医临床药物使用的明证。[29]另外,佛教僧医重视药物的使用,很大可能影响到后世的“药王”崇拜。“药王”一名最早出现在魏晋时期佛经译本,《妙法莲华经》中《药王菩萨本事品第二十三》《佛说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中都有药王名号,僧医树立药王菩萨施医给药的信仰在民间有很大影响,后来民间将此种信仰扩大化,使得神农氏、扁鹊、孙思邈等都被称为“药王”。
(二)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在社会文化方面,僧医的医疗救助为社会下层民众提供医疗保障,也成为联系统治阶级与下层民众的纽带。一方面僧医利用其医疗救助和宗教信仰稳定社会,传播宗教;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也愿意通过佛教安抚民众,而民众也成为了社会福利的受益者。僧医所倡导的心理疗法,利用“来世”、“轮回”学说给予饱受战乱疫疾的民众心理慰藉,在社会上形成一种追求来世幸福的潮流。另外,药藏、六疾馆、隔离所的设立以及僧医的存在使得古代寺院成为“医院”雏形。患者前去求医,寺院提供场地与药物,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医院的起源,恐与佛教寺院有关。[30]魏晋南北朝时期,倡导养生服气,僧医在保健养生方面也多有影响。在生活习惯上,僧人素食斋戒、静心养性与魏晋时期士人清谈淡泊的思想不谋而合。单道开、昙鸾都是注重养生的僧医,在当时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另外,僧医在解众生疾苦时更怀有慈悲精神,这不仅是宗教信仰的要求,更是一种对自身道德的肯定。孙思邈吸收佛教伦理规范提出治病应“发大慈恻隐之心”,为后世医德的培养与建立奠定基础,补充我国医疗文化的不足。同时,与传统医学封闭性学习不同,僧医并不介意将医术传授他人。北魏名医李修的父亲李亮“就沙门僧坦研习众方,略尽其术,针灸受药,莫不有效”[15]卷91:1966,造就了李亮、李修、李元孙世家行医的事迹;另名医崔彧也是跟随隐逸沙门学习《素问》《甲乙》成名的。僧医传授汉地医家的医术诸多古印度与西域的医药学知识,也丰富了传统医药学体系。
四、总结
佛教文化在产生发展的过程中就与医学关系紧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医学就传入我国,并产生了大批与医学有关的僧人。这些与医学有关的僧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翻译了大批佛教医经的涉医僧人;另一种直接以看病救人的方式与医学产生关系的僧医。僧医群体由外域僧人与内地僧人组成,在前期域外僧医通过异术治病救人吸引信众,而在后期以汉地僧医为主体,吸收佛教医学的内容形成具有佛教特色的中国传统医学模式,从而也给传统医学带来新的活力。僧医的医疗活动影响着传统医术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医学理论、治疗手段、药物使用上,而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社会医疗救助机构的设立、服气养生以及后世医德文化形成等方面。尽管僧医的社会医疗活动主要以传播宗教为目的,但也客观地促进了中国传统医药学体系的完善,其博大精深的佛教医学文化也更加需要我们去研究探讨。
[注释]
① 五明亦称五明处,包括声明、因明、医方明、工巧明、内明。参见陈兵.现代佛学小辞典[M].成都:成都出版社,1996:68。
②僧医的定义也有人将其分为僧医与医僧,认为僧医当是以佛事为主,兼行医道,而医僧则是以医为主,信仰佛教而已。如胡世林.试论汉化佛教对中医药学术的影响(下)[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1996(05):18-20。
③关于深师的活动记录尚存争议,详见靳士英.岭南医药启示录[M].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12:180。
[参考文献]
[1]孟海贵.佛陀 佛学 佛医[J].五台山研究,2000(1):3-16.
[2]李清.魏晋南北朝僧医的医学成就[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09(2):24-26.
[3]邵佳德,王月清.从借医弘道到悲田养病——试论汉唐之际中国佛教医学的发展及其贡献[J].医学与哲学,2009(10):71-73.
[4]薛公忱.儒道佛与中医药学[M].北京:中国书店,2002.
[5]蒲慕州.追寻一己之福——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281-282.
[6](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蔡景峰.唐以前的中印医学交流[J].中国科技史料,1986(6):16-23.
[8](南朝梁)慧皎.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
[9][日]冈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169.
[10]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15.
[11]《中医大辞典》编辑委员会.中医大辞典·医史文献分册(试用本)[K].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20.
[12](唐)孙思邈.千金方[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133.
[13](唐)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4](唐)道宣.续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4.
[15](北朝魏)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6](唐)释道世.法苑珠林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3.
[17](唐)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8](唐)魏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9]张志哲.中华佛教人物大辞典[K].黄山:黄山书社,2006:377.
[20]张勇.傅大士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0:499.
[21](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198.
[22]范家伟.晋隋佛教疾疫观[J].佛学研究,1997(00):263-268.
[23]梁玲君,李良松.试论汉魏六朝时期佛教医学成就[J].中医文献杂志,2016(1):11-13.
[24]张志斌.古代疫病流行的诸种因素初探[J].中华医史杂志,1990(1):28-35.
[25](唐)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6](唐)释道宣.弘明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27]孟庆云.魏晋玄学与中医学[J].江西中医学院学报,2004(1):5-9.
[28]傅芳,倪青.中国佛医人物小传[M].厦门:鹭江出版社,1996:14.
[29]胡世林.试论汉化佛教对中医药学术的影响[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1996(5):18-20.
[30]全汉昇.中古佛教寺院的慈善事业.印顺中国佛教和慈善公益事业[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