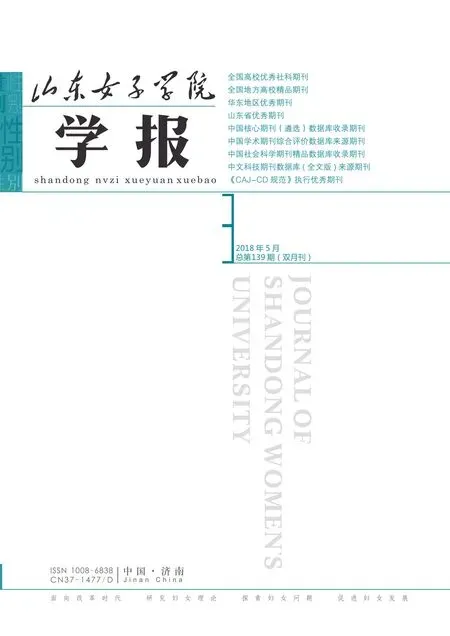文学伦理学视野下的《洛丽塔》
2018-04-03吴琳,杨帆
吴 琳,杨 帆
(中南大学,湖南 长沙 410083)
俄裔美国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是其流传最广也是争议最大的作品,之所以争议不断,是因为它讲述的是一个中年男人与一位未成年少女的畸形之恋。在当时的社会环境看来,这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甚至是一部反美学的小说,所以其最初在美国曾被禁止出版,一年后才在法国由巴黎奥林匹亚出版社出版。直到1958年,本书才在美国本土出版,一经出版,立即成为畅销书,更是被英国评为“二战后影响世界的一百部书”之一。许多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热衷于这部作品,从不同角度、不同视野探讨研究,形成新的文学批评热潮,使得《洛丽塔》这一作品更加开放和饱满。2004年,聂珍钊教授在南昌外国文学会议上提出了中国原创性文学批评理论——文学伦理学。“21世纪初在我国迅速发展起来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就是在西方多种批评方法相互碰撞并借鉴吸收伦理学方法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用于研究文学的批评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出现在西方批评话语中增加了我们自己的声音,为我们的文学研究方法提供了新的选择,尤其是它对文学伦理价值的关注,更使这一方法显露出新的魅力。”[1]聂珍钊教授力图通过这一独特理论的建构,向国际文艺理论界传达中国的学术声音,改变当今西方文艺理论主导中国文艺批评的局面,展现中国的学术创新能力。自此以后,中国批评界逐渐开始使用文学伦理学进行文艺批评,对不同的文学文本进行分析和探讨。本文便将从文学伦理学这一批评视角,来探讨《洛丽塔》中伦理环境、伦理意识、伦理禁忌、伦理悲剧等文学伦理问题,分析《洛丽塔》中伦理现象及其产生原因,从而得出与一般的道德批评不同的价值判断,展现《洛丽塔》内在的独特情感张力。
一、伦理环境之形成
纳博科夫出生于俄国圣彼得堡一个富裕而显赫的贵族家庭,但由于沙皇时期国内革命的影响,纳博科夫一家在他18岁时就离开了俄国,从此开始了20年的流亡生涯。纳博科夫先后去过英国、德国、法国、美国,背井离乡、颠沛流离的经历使得纳博科夫一直有着文化上的困惑和身份上的焦虑,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在他的作品中有所显现。《洛丽塔》中的亨伯特就是一个从巴黎移民到美国的教授,而且是一个混血儿。“我的父亲很文雅且平易,他是个种族杂烩:瑞士籍、法国、奥地利混血,血脉里还有少许多瑙河的气质。”[2](P15)他的母亲则死于一次意外的雷击,那时亨伯特3岁。虽然童年的亨伯特生活富裕,但母亲的死亡使他在成长中缺失了一部分情感。母亲死后,亨伯特这样说道:“我记忆中童年的太阳已经从记忆的洞穴和幽谷上沉落”[2](P16)。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关于童年的记忆有着这样的言论:童年记忆与成年期的有意识的记忆全然不同,它们不是被固定在经验着的那个时候,而是在后来得以重复,而且在童年已经过去了的后来时刻才被引发出来。在它们被篡改和被杜撰的过程中,实现着为此后的趋势服务[3]。亨伯特这些童年的经历对他之后的思想和行为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在后来的岁月中逐渐显现。
13岁时,亨伯特遇见了自己的初恋——阿娜贝尔,年少萌动,两个青春期的小孩就此坠入爱河,体味着魔法般的梦幻世界。但好景不长,4个月后,阿娜贝尔永远地离开了少年亨伯特,他们的爱情画上了悲惨的句号。阿娜贝尔是亨伯特少年时期的初恋情人,是第一次情感大悸动,这让他记忆深刻并且在多年以后还不断追忆和幻想。女友的突然离世,使得少年亨伯特的内心备受打击,留下了深深的悲痛,一生都无法释怀。“我是一个健壮的少年,我活了下来,但毒素却在伤口,伤口永远裂着”[2](P27),这种毒素一直存留在亨伯特的体内,并且不断强化、生长,最后连他自己也无法摆脱这种伦理意识的混乱。成年后的亨伯特也曾不停自问:“是否在那个遥远的夏天的光辉中,我生命的罅隙就已经开始,或者对那孩子的过度欲望只是我与身俱来的奇癖的首次显示?当我努力分析自己的欲念、动机、行为和一切时,我便沉湎于一种追溯往事的幻想”“我相信了,就某种魔法和命运而言,洛丽塔是阿娜贝尔的继续”[2](P21)。可以说,母亲和阿娜贝尔的死亡,给年少的亨伯特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创伤,使得亨伯特在之后的爱情中,用时间概念代替空间概念,对女孩的情结永远停留在9到14岁的漂亮女孩,这是《洛丽塔》伦理叙事中的一个伦理结。文学伦理学认为,“通过对文学文本中伦理结的生成过程进行描述,对生成或预设的伦理结进行解构,从而接近文学文本、理解文本和批评文本”[1],我们通过对这一伦理结的分析与解构,了解亨伯特的童年经历,掌握其最初的伦理生成状况,也就能够对之后亨伯特所做出的伦理行为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批判。
二、伦理意识之争斗
亨伯特在产生乱伦意识之前,还是一个沉于幻想的诗人,不断寻找着安娜贝尔一样的性感少女,填补那未曾得到满足的欲望。他跟社会上的成年女子保持着所谓的正常关系,但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幸福和满足,相反的是憔悴不堪,万分痛苦。他对身边的每一个“小仙女”都怀着热烈的欲望之火,近乎疯狂,不过他没有伸出自己罪恶的双手,因为成年后的亨伯特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伦理意识,明白与少女发生关系是社会所不允许的。他为此感到羞怯、恐惧,“精神分析学家用伪解放论和伪性本能讨好我”[2](P28),他后来结婚,也是为了缓解这种“不道德”的伦理意识所带来的痛苦和恐惧,“即使不能涤除我可耻的危险欲望,至少也许能帮我将它们控制在平和状态”[2](P37),此时此刻的亨伯特,希望通过外在的环境和内在的反省来调整自己的伦理意识,使之回归到正常的社会秩序之中,表现了亨伯特作为人的自我控制和理性思维的斗争。文学伦理学认为,“斯芬克斯因子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这两种因子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其中人性因子是高级因子,兽性因子是低级因子,不过前者能够控制后者,从而使人成为具有伦理意识的人”[4]。
直到遇见洛丽塔,亨伯特才彻底将自己的幻想从安娜贝尔转移到洛丽塔身上,并逐渐开始步入伦理禁忌之中不可自拔。为了得到洛丽塔,并且永久地和她在一起,亨伯特同夏洛特结婚,成为洛丽塔的父亲。在之后的生活中,亨伯特时刻关注洛丽塔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欣赏她美丽的胴体,观察她不羁的言行,并在日常生活中爱抚她、拥抱她,做出一连串隐蔽的小动作。新的快乐感充溢着他的内心,但同时他也为自己感到可怜,他不得不费尽全力地控制和压抑自己内心深处那热烈、疯狂的情欲,以此来保住12岁的洛丽塔的纯洁。作为一个有着伦理意识的成年人,亨伯特知道自己这些想法是不道德的、肮脏的,不被世俗所允许的。于是他不断自我反省,试图用理性战胜感性,他担心自己如果任由这种意识发展下去,兽性因子便会战胜人性因子,最终突破伦理禁忌而走向乱伦。为此,亨伯特被伦理的疑惑和恐惧所缠绕,陷入了无法脱身的伦理困境。作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现代大学教授,亨伯特清醒地认识到被欲望驱使最终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自己又将面对怎样不堪的局面,但他对洛丽塔的爱恋又让他一步步陷落,沉沦在情欲之中,个人的生命本能和社会秩序之间形成了强烈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内心深处伦理意识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故事将要朝着不可挽回的局面发展。
三、伦理禁忌之突破
在亨伯特逐渐陷入情欲之中,想要进一步占有洛丽塔时,他突然意识到一个伦理问题:即夏洛特阻碍了他和洛丽塔的结合,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让夏洛特消失。但亨伯特并未付诸实践,他知道那是犯罪,只是在潜意识中谋划了一切而已,是一场“想象式犯罪”。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夏洛特无意中发现了自己的日记,知道了他不为人知的秘密。夏洛特因此痛哭一场,发疯似地冲出家门,在过马路时被车撞死。这是《洛丽塔》故事情节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作者极其巧妙的一个设计。亨伯特与夏洛特的结合,使得他与洛丽塔有了伦理关系,而夏洛特的意外死亡则是排除了一切现实阻碍,使得亨伯特有了最大可能与洛丽塔结合,同时使得亨伯特不用践行自己的“想象犯罪”,背负法律责任和道义的谴责。
按一般的逻辑来说,既然一切障碍都已经排除,那么亨伯特即将有着令人兴奋的前景,去享受无穷无尽的快乐,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新的伦理困惑和恐惧扑面而来:他该如何定义自己与洛丽塔的关系?虽然他可以为此“摆脱”与洛丽塔的父女关系,但他依然不能和洛丽塔名正言顺地在一起。以当时的社会文明和伦理环境来说,向一个12岁的少女求婚是被看作“不伦”,是不被社会所接受的。为此,亨伯特甚至翻阅相关的法律条文和书籍,期望在法律允许的婚姻框架中确定自己的可能。在带着洛丽塔出走的路上,亨伯特企图通过安眠药让洛丽塔沉睡,以便自己能近距离欣赏洛丽塔,更加自由地感受美丽的小仙女。此时的亨伯特还没有占有她的想法:“趁黑夜对那个已经完全麻醉的小裸体进行秘密行动而不侵占她的贞洁,抑制和尊崇仍然是我的箴言。”[2](P175)亨伯特对洛丽塔并不是普通意义上性的欲望和占有,而是对自己幻想中美感的追求,是对狂热的欲念的着魔。最后是“她诱惑了我”,玩了一出“小孩子的游戏”。无论是评论家所说的“古老的欧洲强奸了年轻的美国”,还是“年轻的美国诱惑了古老的欧洲”,亨伯特最终迈开了那一步,突破了伦理的禁忌,和洛丽塔开始了“不伦之恋”。
在这一场性经历之后,他们慢慢确立了情人关系,然后开始了他们的全美旅行。亨伯特之所以要带着洛丽塔到处旅行,是因为亨伯特的伦理意识告诉他,这是一场乱伦,是不道德的,不被社会所接受的,他的内心有着很深的负罪感,并且为此感到焦虑和恐惧。他不得不辗转于各地的汽车旅店,编织不同的谎言,掩盖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伦理真相,企图通过不断的旅行来逃避这一切。倘若安定下来进入社会生活,承担自己的社会角色,他便会坐立难安,心神不宁,有着绝望般的恐惧,所以他宁愿开始流亡生活也不愿意回到正常社会生活中去。亨伯特企图在二人世界中确立自己的情人身份——这样一种没有忤逆道德的伦理身份,来抵抗乱伦禁忌的批判和社会道德的责难。
四、伦理悲剧之毁灭
随着洛丽塔年龄的增长,洛丽塔开始厌倦他们的流浪生活以及两人的不伦关系,她开始悄悄攒钱,并计划逃跑。由于道德的责难使得亨伯特对洛丽塔有着很深的依赖,与洛丽塔的不伦关系是他逃避社会的港湾,所以洛丽塔的出逃对亨伯特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使他本来就不稳定的安全感一下子荡然无存。他便开始疯狂地寻找,过上了一段新的漫游生活。三年后,他收到洛丽塔的求助信,此时的洛丽塔已为人妻,形容枯槁,面容憔悴,是一个苍白臃肿的妇人,生活潦倒凄惨,再也不是那个美丽动人、梦幻般绚丽的小仙女了,但他依然爱她。“你知道我爱她,那是一见钟情的爱,是矢志不渝的爱,是刻骨铭心的爱。”[2](P375)同时他了解到当年是流氓剧作家奎尔蒂诱拐了洛丽塔,并且让她拍摄色情电影,在利用玩弄之后,离开了洛丽塔。被抛弃的洛丽塔后来嫁给了朴实的狄克,生活凄苦。知道这一切的亨伯特五味杂陈,梦中诗意的消亡和情人的凄惨遭遇一起袭来,他不知道自己此时该以何种身份面对这个局面,是继父还是情人?伦理身份的困境让他感到无所适从。他本来想要杀死狄克的,却又没有动手,是因为他感到年轻朴实的狄克带给洛丽塔正常的快乐的生活,他没有妒忌,还慷慨地给了洛丽塔嫁妆。此时的亨伯特以父亲的身份出现,履行着一个父亲的职责,他希望帮助洛丽塔,并希望她过得快乐幸福。之后他寻找奎尔蒂,并枪杀了他,此时的亨伯特是以情人的身份出现,他杀死的是自己的情敌。枪杀奎尔蒂之后,亨伯特感到“舒服”“懒洋洋”,这是因为他终于摆脱了困扰自己许久的伦理困境,不再为此而饱受折磨和痛苦。奎尔蒂在书中一直是以一种神秘的身份出现,直到最后才道出了他的身份和行径。这是象征着另一个亨伯特,是黑暗、堕落的自己,书中亨伯特一直把他当作势均力敌的情人佐证了这一点。“这场闹剧实际上是亨伯特对自己的决斗,是他在正视了洛丽塔已为人妇的现实而消灭自己非正常的、黑暗一面的行为。”[5]这也就是说,奎尔蒂是亨伯特黑暗形象的一个化身,是那个与洛丽塔发生乱伦关系逃离现实社会的人,是饱受伦理困惑和道德恐惧的灵魂。亨伯特枪杀的实际上是自己罪恶的一面、黑暗的一面和自己痛恨的一面,这是他对自己的理性裁决和最后审判,这也就是为什么最后亨伯特选择让奎尔蒂来宣读死亡审判书的原因所在。其实从一开始,亨伯特的伦理意识和伦理处境就暗含着毁灭,他一步步走入伦理的漩涡中不能自拔,最后,这场伦理悲剧以生命的代价凄惨收场。
五、结语
乱伦一直以来都是文学作品表现的一个主题,许多作家都曾以此来创作自己的文学作品,如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王弑父娶母,最后惨遭天谴;福楼拜著名小说《包法利夫人》中爱玛婚后出轨,同赖昂、罗道弗尔通奸;《金瓶梅》中潘金莲与西门庆通奸,并合谋毒死自己的丈夫武大郎。这些作品都表现了人物内心伦理意识的混乱与挣扎,这些人最终因触犯伦理禁忌而导致了悲剧命运。纳博科夫却有所不同,他试图在人类生命本能与伦理道德底线之间,寻求一种别样的美感,一种审美的福祉,而不是简单的道德批判。纳博科夫在《洛丽塔》的后记中曾经说道:“对我来说,虚构作品的存在理由仅仅是提供我直率地称之为审美狂乐的感觉,这是一种在某地、以某种方式同为艺术(好奇、温柔、仁慈、心醉神迷)主宰的生存状态相连的感觉。”[2](P7)在他看来,《洛丽塔》不是一部色情小说,更不是一部道德小说,他也无意于此,他所要表现的是一种诗意精神,性不过是艺术的附属物。严歌苓曾评论道:“他(纳博科夫)写了这样一种非常不道德的一个成年男子的最诚实的对于少女的一片黑暗的诗意。”[6]我们从文本中可以看到,亨伯特对洛丽塔肉体的占有其实并没有多大兴趣,他的情欲是童年的移情,而且随着故事的发展,他对洛丽塔的爱始终真挚热烈。面对苍白凄苦的洛丽塔,他给了她嫁妆,告诉她好好生活,他在审判席上的小说,要等到洛丽塔死后才能出版。正如他引用的那句诗行:“人性中道德感是义务,我们必须向灵魂付出美感。”正是亨伯特这种黑暗的诗意带给读者不一样的阅读体验,让我们有了更多有关审美的思考,也让我们重新去定义后现代的伦理价值和道德批判。
参考文献:
[1]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1):12-22.
[2] 纳博科夫.洛丽塔[M].于晓丹,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7:达·芬奇对童年的回忆[M].长春:长春出版社,2010.86.
[4]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J].外国文学研究,2011,(6):5.
[5] 于晓丹.《洛丽塔》:你说是什么就是什么[J].外国文学,1995,(1):79.
[6] 严歌苓.严歌苓谈文学创作[J].世界文学评论,2012,(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