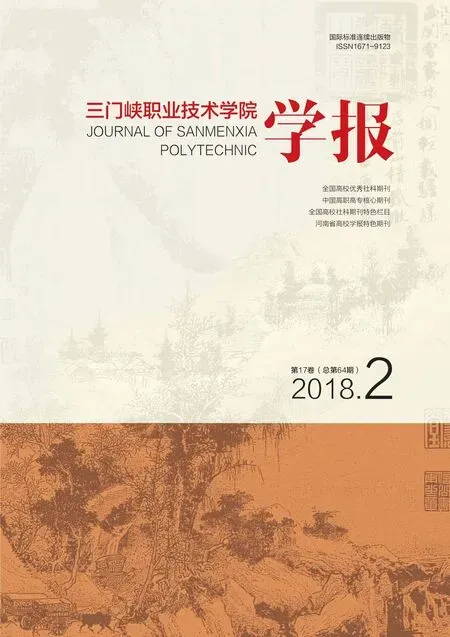《妻妾成群》中的“新女性”形象
2018-04-03李冀宁
◎李冀宁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西安 710119)
《妻妾成群》发表于1989年岁末,是苏童创作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篇小说。这不仅由于它是苏童“妇女生活”系列的开山之作,更是因为它于1991年被著名导演张艺谋改编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而“一朝成名天下知”。这部小说讲述一个“受过新时代教育”的女学生颂莲,自愿嫁到高墙深院的封建家庭陈府,最终又在“妻妾成群”明争暗斗中走向精神崩溃的悲惨命运。苏童在字里行间揭露着传统封建礼教“吃人”的黑暗本质,流露着对一夫多妻制的旧式婚姻下妻妾们无法逃脱的悲剧命运的深切同情。然而,更为难得的是苏童以一种全新的女性视角,从勘察女性生存的角度出发,尖锐地指出以颂莲为代表的“形新神旧”典型形象特征,也正是这种徒有虚名的本质使得如颂莲一般的“新女性”在与“旧女性”的对抗斗争中败下阵来,甚至同流合污,走向毁灭。可见,所谓的“新女性”光鲜亮丽的新外表下所隐藏的粗鄙落后的旧本质,亦是陈家大院里的妻妾们难逃悲剧命运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恰恰是小说主题的点睛之笔,引人深思。
一、“新女性”典型形象特征分析
《妻妾成群》讲述了一个女性所遭受的婚姻悲剧、甚至人性摧残的故事。小说以四姨太颂莲的视角描述了陈佐千的妻妾侍女为了各自的名分与宠幸,而展开一场又一场你死我活的明争暗斗,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我国历史上曾长期存在过的纳妾现象,以及在这旧式宅院里无法突围的女人们的悲惨命运。苏童在小说中巧妙地塑造了典型的“新女性”形象——四姨太颂莲,即“新人身份,旧人命运”,从独特视角审视她的革新之路,剖析她无法彻底革新的症结,塑造她“形新神旧”的典型形象特征。
(一)单纯天真,不谙世事
《妻妾成群》所描绘的时代背景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正是大力倡导妇女解放的一个时期。颂莲是全篇中唯一上过一年大学、穿着白衣黑裙的“女学生”,她沐浴过“五四”新风,也秉承了“新女性”的单纯、敏感和对生活理想的追求。从小说开头对颂莲出场和她刚到陈府时的一些细节描写中可以看出她当时单纯天真的模样:“那一年颂莲留着齐耳的短发,用一条天蓝色的缎带箍住,她的脸是圆圆的,不施脂粉,但显得有点苍白。”[1]颂莲刚入陈家时清新秀丽的模样跃然纸上,“她抬起胳膊擦着脸上的汗,仆人们注意到她擦汗不是用手帕而是用衣袖,这一点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这时的颂莲显然没有一丝太太的架势,自然朴实的动作使其邻家女孩的形象楚楚动人;小说也交代了颂莲在和陈佐千第一次见面的场景,“陈佐千第一次去看颂莲。颂莲闭门不见,从门里扔出一句话,去西餐社见面”[1]。没有哪一个传统女性敢在这种情况下将自己未来的丈夫挡在门外,而且约在西餐厅约会。陈佐千自然觉得颂莲不同寻常,而“打着一顶细花绸伞姗姗而来”的颂莲更给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心动。可见,颂莲的新潮举动和婀娜身姿都时时刻刻表现着自己与封建保守时代的区别,带来一股清新之气;当颂莲见完大太太后,“就挽住陈佐千的手臂说,她有一百岁吧,这么老?”[1]而当她在二姨太卓云那里受到了热情的礼遇时,就很快地改口喊卓云姐姐了。此时,颂莲不谙世事、调皮活泼的本性展露无疑。然而颂莲身上天真活泼、不谙世事的自然天性显然与阴沉压抑、封建腐朽的陈府格格不入,想要在陈府活命甚至得宠只凭借年轻貌美是绝不可能的。颂莲的人性之美在那个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世界里,若不是同化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境界就是沦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下场。在陈府里颂莲明显是求生的,而且要活得漂亮,于是她也从当初初入陈家单纯直率的“新女性”变身为残忍冷酷的“旧女性”。颂莲的人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注定她难逃重复前人悲剧的命运。
(二)现实,报复心强
颂莲在父亲死后,得知灾难临头的她并没有哭泣,也没有一般女孩的怯懦和恐惧。她很实际,知道父亲死后,她必须自己负责自己了。“所以当继母后来摊牌,让她在做工和嫁人两条路上选择时,她淡然地回答说,当然嫁人。继母又问,你想嫁个一般人家还是有钱人家?颂莲说,当然有钱人家,这还用问?继母说,那不一样,去有钱人家是做小。颂莲说,什么叫做小?继母考虑了一下说,就是做妾,名分是委屈了点。颂莲冷笑了一声,名分是什么?名分是我这样的人考虑的吗?反正我交给你卖了,你要是顾及父亲的情义,就把我卖个好主吧。”[1]在现实面前人人都是脆弱的。当父亲去世时,颂莲深知自己的继母不会帮助她而她自己也无力继续完成自己的学业,在无情的现实面前她只能实际地去选择一条对自己更有利的道路。选择做工,对颂莲来说只是一条艰辛困苦而前途黯淡的道路。于是,颂莲考量了自身的条件:商人门第、接受过高等教育又年轻貌美,于是颂莲以此作为资本精明地选择嫁给一个有钱人做小,想通过这样的途径继续自己衣食无忧的生活作为自己生存的保证。
颂莲同样是一个心狠手辣,报复性强的女人。当颂莲卷入陈府女人之间你死我活的斗角中时,她已经褪下了天真单纯的本性,工于心计来赢得胜利才是她所在乎的东西。譬如当颂莲发现雁儿在一张草纸上画自己的样子弄成纸团扔在马桶里诅咒她时,颂莲立刻把那张草纸捞起来,把草纸往雁儿的脸上摔过去,甚至惩罚丫鬟雁儿吃下草纸时说:“你也别怨我狠,这叫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书上说的,不会有错。”[1]颂莲身上极强的报复心直接导致了雁儿惨死。颂莲由令人同情的受害者变成了血淋淋的施暴者这一现实,也引起了对“五四”女性自我解放运动实际效果的深刻反思。
(三)从封建传统观念的受害者到内心精神世界的崩溃者
“颂莲”这一人物形象的设定和其他中国传统女性人物形象一样,自身深深受到封建传统观念的浸淫,潜意识里或多或少带有落后的封建传统文化。随着她在陈府时间的推移和女人斗争的不断深入,这种潜在的思想就被一点点激发,致使颂莲在内心精神世界中不停挣扎彷徨,逐渐焦虑惶恐,又不得解脱。最终,三姨太梅珊惨死如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颂莲的心理防线,彻底逼疯了颂莲。
这种封建传统观念在颂莲的脑海中时刻存在着,也束缚着她的一生。颂莲的父亲生意失败且自杀身亡,这不仅导致颂莲家境败落,同时也中断了自己的学业。当继母让其选择“做工”或“嫁人”时,颂莲则选择了结婚“嫁人”,甚至是做小妾。作为一个五四时期的女性,颂莲没有试图通过做工或是别的方式把握自己的命运,却自愿选择进入陈家当小妾,希望以此改变自己窘迫的人生现状,继续过着安稳富足的生活。只是,颂莲没有意识到选择嫁人也就同时选择了依附屈从男人来重塑自我价值,富足的生活中同样有她无法接受也难以逾越的身份界限和男女界限,她的选择无疑注定了她日后不可承受的精神与肉体双重痛苦。颂莲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新人这看似务实的选择实际上源于她身上挥之不去的封建传统观念,她并没有因为接触过新思想而彻底革除旧女性对男人的依附性,只是新皮装饰了旧瓤,颇具虚假性。无论何时,这都是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
无论如何,作为小说中突出塑造的“新女性”形象,苏童还是寄予颂莲一丝时代新气象,毕竟她是以女学生的身份背景出现,“五四”所倡导的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的时代风尚仍在其身上有所显露。颂莲正值花季嫁给已年过半百的陈佐千,除去对安逸物质生活的赤裸追求,毫无感情基础可言。当颂莲与陈佐千之间的激情慢慢褪去,陈佐千开始厌倦又难以满足颂莲的需求时,颂莲身上潜在的新人细胞开始躁动不安了。这时的颂莲将目光投向了这个宅子里同她年龄、秉性相仿的陈飞浦,不同于梅珊肉体与精神毫不掩盖的出轨,颂莲时刻克制着自己的身体,但精神却一次次出卖着自己的灵魂。当颂莲终于勇敢地给予陈飞浦以暗示希望得到对方回应时,陈飞浦的软弱与退缩也将颂莲最后的希望击灭。此时,颂莲没有三姨太梅珊那死而无怨的胆量与豪情,她甚至不敢继续追求自己的幸福,相反她内心经过激烈斗争终选择了妥协认命。当陈佐千到她房间来的时候,“颂莲又跳起来,勾住陈佐千的脖子说,老爷今晚陪陪我,我没人疼,老爷疼疼我吧。”[1]狗般转向讨好陈佐千,寄托自己空虚的精神又希望换来陈佐千的无限宠爱。梅珊为情所死或许是死得其所,颂莲为情所困倒有点疯的可悲。面对爱情与自由,苏童将两人进行鲜明的对比,作为“新女性”代表的颂莲却比不上梅珊的万分之一,令人唏嘘不已的同时又重重揭露了“新女性”的劣根性与软弱性,颂莲在向封建旧制度妥协低头的一刹那,其自身无法挣脱的“旧神”注定了悲剧命运。
四姨太颂莲是贯穿《妻妾成群》始终的人物,也是陈佐千所有妻妾中受到最集中精神伤害的。无疑,五四新风与封建传统观念的双重夹击是导致颂莲精神分裂的真正原因。正因为颂莲是一个接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女性,她身上所带的某些“新女性”的品格与封建势力残余严重的陈家始终格格不入。颂莲不肯放弃自己,又不得不放弃自己,因为在她拒绝封建家庭诸多无理要求的同时也必然失去万千宠爱。但颂莲又毕竟是一个接受过新式高等教育的且有思想的人,她做不到大太太毓如的麻木不仁,做不到二姨太卓云的两面三刀,更做不到三姨太梅珊的以身试法,没有能力却有思想,渴望挣脱又无力挣脱。在这种内心极度矛盾和精神高压状态下,梅珊被投井惨剧的发生,无疑是压倒颂莲精神支柱的最后一根稻草:颂莲曾经偷偷羡慕着梅珊,因为梅珊实现了她内心深处欲望的释放,在亲眼目睹梅珊因为反抗而遭杀害后,颂莲自我怀疑、自我否定,自身的压力和外界的压力共同钳制等一系列的变故后终于迫使其走投无路,精神崩溃。这时,崩溃与疯癫似乎成为了她唯一的活路。更加可悲的是,颂莲在自己最后时刻也没能走上“新女性”的革新解放之路,她没有试图去打破这种“吃人”的封建旧社会,打破这口随时无情吞噬女性生命的“井”,而只是念念有词“我不跳,我不跳”,企盼自己不要成为下一个梅珊而苟活着。颂莲,这位“新女性”再一次选择向命运低头妥协,她在命运的安排面前选择逃避,选择忍让,选择不作为,她终被这个黑暗的社会所吞噬,“新人”形象的崩塌和“旧人”精神的毁灭在所难免。
二、“新女性”形象悲剧原因分析
苏童在小说中着力塑造的“新女性”,即四姨太颂莲,最终以悲剧结束一生。究其原因恐怕不外乎两点:客观因素“新不了”;主观因素“不思新”。客观社会环境没有为她谋求革新解放的种子创造肥沃滋润的生存土壤,这就注定了她发育畸形,成长艰难;主观精神没有反抗强暴、斗争到底的思想与意识,这就使得她遇难则退、妥协退让,最终选择向残酷命运低头的结局。内因外因均显疲软态势,“新女性”彻底与旧社会、旧势力告别从而走上真正的革新解放道路自然变成无稽之谈,“新女性”只得流为一个幌子,“形新神旧”的本质特征也预示了悲剧的最终发生。
(一)客观因素“新不了”
小说中陈佐千是封建残余严重的男权社会的典型代表:他为了满足自己贪婪的性欲,使一个又一个女人成为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他的喜恶决定着一个女人一生的命运,就算已经失宠的人也要绝对臣服于他的意志;他的欲望是逼迫压抑几个女人直至她们心灵扭曲变态的直接原因。风雨飘摇的封建社会仍旧在苟延残喘,一夫多妻旧式婚姻制度仍旧彰显着男性的特权地位,“夫为妻纲”的封建理论仍旧占据着女性的头脑,纵使“五四”新风已经吹来,封建政治和落后文化依然牢牢控制着人们的所作所为,一切不合理的旧制度依然合理地存在且延续着。政治、文化等社会客观因素构成了阴冷糜烂的社会现状,虽惨白无力但却根深蒂固,想要打破千百年来固有的封建伦理社会,可谓困难重重。
颂莲所处的正是这样一个阴森恐怖、钩心斗角的生存环境。陈府中上至太太,下到丫鬟,通通都携带着传统封建旧伦理、旧道德及旧思想。在这样地家庭中想有立足之地,颂莲必须将自己的才智用在对付同类上才能赢得平稳富贵的日子,但也注定了她将被腐朽的封建大家庭吞噬的命运。陈府中的女人们直接构成了颂莲所面对的现实环境,也将“新女性”的出路扼杀:毓如是陈佐千明媒正娶的大太太,在陈府这样的封建大家庭中,毓如的唯一优越性就是正室地位。所以她在陈府里的各种场合都尽情地扮演着女主人的角色,管理着大大小小的家务事。毓如,无疑是一夫多妻制旧时婚姻的受害者与施害者,她倾尽全力为家庭付出所有,但人老色衰之后就遭到丈夫的无情冷落,同时,她又始终坚守封建礼教倡导的妇道,而且竭力维护着各种清规戒律。在她身上积淀着“旧女性”传统且固有的悲剧因素;说到二姨太卓云的话很是精确,“卓云是慈善面孔蝎子心”。如果说毓如是封建家庭制度的顽固尊崇者,卓云则是中国“阴性文化”的典型代表:她表面为人和善,实则笑里藏刀,让人防不胜防。毋庸置疑的是,卓云这刀刀见血的诡计帮助她成为了陈府妻妾斗争中的胜利者,她将梅珊告密致死,间接逼疯了颂莲,可谓一石二鸟之计;雁儿,小说中着力描写的一个“小人物”:她在陈府里是一个无名无分的、身份低贱的小丫鬟,一方面要受姨太太们的驱使,稍有不对便被无情指责,另一方面又要受到陈佐千的玩弄。但也是在这种环境的熏染下,雁儿变得趋炎附势且俗不可耐,甚至具有极强的报复心,如颂莲刚进陈家时嘲笑颂莲的穷酸模样,在草纸上画人形咒颂莲。此外,雁儿虽是一个卑贱的小丫鬟,可她却懂得运用自己的身体去吸引陈佐千对她的注意,进而实现荣升太太的美梦。然而,这一切只是雁儿的天真幻想,她最终没能“飞上枝头变凤凰”,只是卷入了一场又一场的妻妾争斗中,最后沦为毫无价值的牺牲品,梦醒时分也是她殒命之时;如果说雁儿还算是女人战争的直接参与者,那么小说中的另一个“小人物”——宋妈则是旧社会中众多冷漠残忍的旁观者的代表。当颂莲问起从前死在废井里的女人时,宋妈有模有样地谈论了起来,说到精彩之处还不时咯咯笑起来,甚至笑得前仰后合。显然,宋妈所代表的旁观者并没有对曾被投井的女人抱有丝毫同情心,更难以认识到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以及这种荒唐残忍的做法对女性所造成的极大残害。同时,宋妈津津乐道的言行无疑带给颂莲巨大的精神压力,这是一种旧思想与旧观念扑面而来的精神重压。
可以想象,陈府的女人思想落后且言行鄙夷的“旧人”仍充斥于社会的各个角落之中,并占据着大多数比例。整个大家庭,乃至整个大社会都难逃巨大的封建残余势力,政治腐败、制度残缺、文化落后等所构成的客观环境严重束缚着人们的双手双脚,难以走向真正的文明与革新,更别希望千百年来依附男人生存的、足不出户的小脚女人能彻头彻尾走向解放,走进新时代了。种种人性之恶体现了女性悲剧的生存环境,在这样的生存境遇中,人性被扭曲、被扼杀,客观环境没有为“新女性”的发生发展提供健康充足的养料,也就在根本上决定了其“新不了”的结果,人物的悲剧性也是必然的。
(二)主观因素“不思新”
整个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严重制约着“新女性”的发展道路,也从根本上否定了其出路,但是,若“新女性”勇于反抗、敢于斗争,坚决同旧势力相争斗,日趋落后腐朽的封建社会必然被破出一个大缺口,“新女性”的胜利也将指日可待。怎奈这时的“新女性”,群体并没有如此顽强的战斗力,甚至本身就是封建落后因素的继承者。颂莲,作为一个“受过新时代教育”的“新女性”显然应与这样腐朽的社会、家庭划清界限,但却不能否认其从小的生活环境、从小接触的人和物就自始至终充斥着这些不堪的、腐朽的旧因素,难逃潜移默化的不良影响。久而久之,这也为以颂莲为代表的“新女性”的产生与发展造成了不可忽视的阻碍与制约,使她们无法与当时仍旧占据社会主流的诸多落后因素完全割裂开来,甚至在自身的成长中会带有“旧女性”的影子,造成自身发展“形新神旧”的两面性。可见,“新女性”的种子犹如萌发在一滩又黑又臭的烂泥里,破土前难以汲取足够的养分,破土时极其吃力,破土后这烂泥又粘在幼苗的茎叶上。“新女性”的种子从萌芽时就包裹着封建落后势力所派生的腐烂物,沾满茎叶,难以一刀两断、彻底革新,而“新女性”的“新”也只是停留在嘴边,说说而已,并无实质。以颂莲为代表的“新女性”其自身就带有不可逆转的劣根性,她们名义上是新人,骨子里却植满了旧人的落后成分。她们生活在封建大家庭中,虽以新人的身份进入家庭,但获得的新知识最终只沦为向旧人谄媚、讨好的新工具,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在肮脏的旧社会中苟活下去,并非摆脱它。更致命的是,“新女性”自小生长的环境就已经有意无意地让她们形成了牢不可破的旧观念,她们向黑暗现实社会妥协时是那么自然而然,现有生活的残酷迫害在她们看来也合乎情理。当她们遇到悲惨命运降临时首先想到的不是顽强的反抗和积极的斗争,而是如何明哲保身、苟延残喘,显然她们遇难则退,主观上是“不思新”的,固有的落后意识无疑加剧了自身的悲剧性命运。
三、“新女性”形象悲剧意义分析
《妻妾成群》的发表极具轰动效应,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小说成功塑造了包括主人公颂莲在内的封建大家庭中各种各样的悲剧型人物,特别是富有浓厚悲剧色彩的女人颇具意义,发人深省。
(一)无情揭露鞭挞封建“旧社会”
以二姨太为代表的封建“旧女性”们因其自身的落后腐朽性自然早早注定了万劫不复的悲剧命运,她们可谓“死得其所”:她们始终都是封建旧伦理家庭的积极拥护者和尊崇者,她们俨然是封建“吃人”制度的帮凶,最后成为已经腐烂的社会的陪葬品自然不足为奇。但也应该认识到这些“旧女性”苦情的人生同样是苏童对一夫多妻制的旧式婚姻下妻妾们无法逃脱悲剧命运归宿的严肃控诉与无情的指责,她们的奸恶、她们的冷漠同样是中国千百年来封建社会对她们长期摧残迫害的结果,在她们身上所发生的一切无疑是不计其数的悲剧重复上演而已。封建社会中的“旧女性”固然是黑暗社会的牺牲品,但较于“新女性”的存在她们反倒以主人翁自居变成了旧制度的坚决拥护者与信奉者。卓云以一招一石二鸟之计害死了梅珊又逼疯了颂莲,似乎成为了妻妾斗争中最大的受益人,也将“新女性”的前程彻底断送。此时的卓云以及大宅里仍苟活着的女人们必然沾沾自喜,殊不知这只是风暴暂时平息而已。陈府作为这些自觉不自觉踏进这座宅子里的妻妾们无法突围的围城,等待她们的不是瓦罐里自相残杀的蛐蛐们的命运,就是那口阴森可怖的欲吞下背叛者的古井,至于在二者之间颤巍巍地巧走钢丝绳的“卓云们”的命运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吧。这样看来,无论是现在洋洋得意的“卓云们”,还是疯疯癫癫的“颂莲们”,如果不试图打破旧有的封建制度终究只是困兽犹斗,无法拥有真正美好的生活。苏童直观展现着“新女性”悲剧命运,同样暗示了“旧女性”也将迎来悲剧性归宿,从而尖锐地揭露父权制社会中妇女命运悲苦且只是男人权欲殉葬品的沉重主题,进一步痛斥了旧社会及其旧制度摧残人性、迫害生命的罪恶,强烈地鞭挞着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
(二)热切企盼呼唤光明“新时代”
当然上述形象意义的分析,是以四姨太颂莲为代表的“新女性”悲剧命运的直观感受,也是苏童毫不掩藏传达给读者的主题。换一种角度分析,或许“新女性”悲剧形象的设定还另有新意。颂莲走向疯癫纵然与其自身“形新神旧”的劣根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愈大的压迫必然受到愈大的反弹,苏童在小说中仍赋予“新女性”无尽的希望与肯定。“新女性”的血泪悲剧史具有催化剂般的作用将唤醒更多的有识之士,他们在这血淋淋的现实面前必有醍醐灌顶之感转而如雨后春笋般奋起反抗,或为女性同胞、或为自己的母亲、或为自己的妻女争得一片自由祥和的天地。正如苏童在小说结尾处的安排:颂莲疯癫后的第二年春天,在一个同样的季节里懵懂无知的五姨太文竹悄然来到了陈府。或许,这恰暗示着五姨太文竹的命运会重蹈覆辙,继续被丑陋罪恶的父权制社会所吞噬。又或许这时在文竹的视线里已不再有带着古旧气息的深宅和阴森森的古井,而只有神色黯然的疯女人颂莲。曾经作为“新女性”标志的颂莲已沦为“旧女性”逐渐走向衰亡,正如封建父权制历史必然崩溃的趋势,陈府里的一切也都行将就木,气数已尽。此时健康活泼的“新女性”文竹恐怕也会好奇地问起陈府当年的是是非非与恩恩怨怨,而她却已沐浴着“五四”新风走向了同过去彻底决裂的真正意义上的“新女性”时代。
四、结语
中篇小说《妻妾成群》塑造了以主人公颂莲为代表的“新女性”形象,她是以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学生身份进入陈府,但却在言行举止中散发着封建旧人落后腐朽的气息,集中体现了“新女性”形象“形新神旧”的典型特征。而致使小说中“新女性”畸形发展并最终走向悲剧结局的原因,可归结于客观因素“新不了”和主观因素“不思新”的双重合力。在这种令人窒息的糜烂环境中,“新女性”最终都如昙花一现般凄惨凋零。探究其悲剧命运的意义,这是苏童对一夫多妻制的旧式婚姻无情的抨击,是他对封建礼教迫害生命且摧残人性强烈的控诉,更是他对黑暗旧社会深切的诅咒与唾弃。当然,苏童对这残酷吞噬生命的可憎生活仍寄予了希望与憧憬,他坚信“新女性”的血和泪不会白白牺牲反而会唤醒和激励更多的有志青年挣脱渐趋颓势封建社会的桎梏,建立一个崭新又美好的“新女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