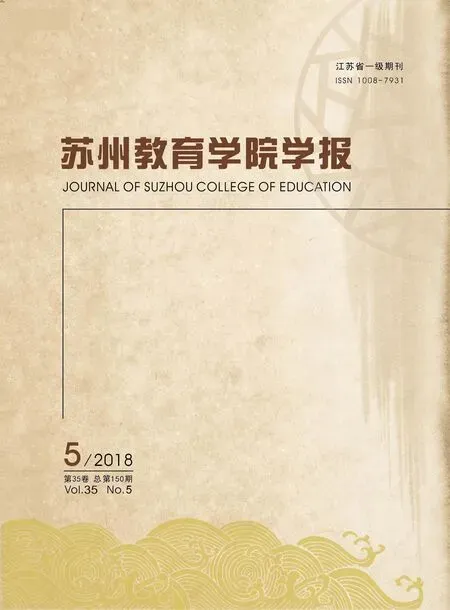赛博时代的多重世界互动叙事—中山大学“南方文谈”沙龙发言摘编
2018-04-03刘倍辰牛国庆吴东紫方锦彪录音整理
凌 逾,刘倍辰,牛国庆,吴东紫,黄 越,李 立,方锦彪(录音,整理)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2017年11月10日,中山大学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举办第23期“南方文坛”沙龙,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凌逾教授带来题为《赛博时代的三重世界互动叙事》①凌逾:《赛博时代的三重世界互动叙事》,https://mp.weixin.qq.com/s/WjoK5amcvNSqqZ-1TrG6BA。的学术分享,随后中山大学中文系张均教授、暨南大学文学院讲师郑焕钊博士、华南农业大学中文系王瑛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陈瑜副教授等嘉宾围绕演讲内容进行研讨。此次学术讨论精彩纷呈,特摘编如下。
主题讨论
陈瑜:关于香港文学,我在硕士阶段研究过黄碧云,但对董启章了解不多。在我看来,董启章和黄碧云一样,都是极具探索精神和革新意识的作家。我之前没有读过董启章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在凌逾教授的推荐下,我觉得有必要借来学习一下。说实话,刚开始阅读的时候,我也没读懂,但在作者建构的叙事空间中,我还是挺快乐的,因为就如凌逾教授所说,作家在小说中尽可能地“玩弄”、尝试各种叙事元素,包括时间、“实然”、“或然”、“应然”等多重世界。我并没有带着预设性的读者身份去阅读,而是以批判的视角进行一场阅读游戏,因为作家在“玩儿”,我也在“玩儿”。我是从所谓的“实然世界”—“我”所在的有13种物件的叙事空间—中开始读的,从“电报”开始,一直读到爷爷奶奶的故事,我觉得没劲了,就回到开头来读栩栩诞生之初的部分,再沿着这条线索读下去。也就是说,我是分为两个“声部”来读的,感觉差不多了,就开始看两者之间的对话。
这其实是一种扑克牌式的读法,整个阅读过程就是在玩。有很多小说家进行过各种叙事方面的尝试,如博尔赫斯在《交叉小径的花园》中畅谈且部分实践了对小说叙事题材中“时间”问题的思考;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创新了对空间的叙事和想象,《寒冬夜行人》则挑战叙述者、作者和读者的身份限定,探索书写世界和阅读世界的沟通。
我十分欣赏董启章的是,他在这部作品中已经跳脱出以往作家对时间、空间等叙事技巧的尝试和创新,直接触及文学创作曾经的基石—“真实”,并将“真实”的底线都消解了。有一类作家将“写实”作为追求的最高境界,后来也有对这种观点的反拨,但董启章不仅以叙事行为创建了多重世界,更重要的是,他在消解“真实”。那什么是“真实”?传统观念认为叙述者是真实的,创作出来的作品是虚构的,但在董启章的作品中,真实和虚构完全是交错的,就像凌逾教授所说的,叙述者可以和他创造的人物有直接的交流,这种交流是否真实我们无法确定,但他所创造的虚拟人物可以通过他的书写能力来获得所谓的真实性。所以,董启章不仅在“玩弄”叙事时间,“玩弄”叙事技巧,他同时也在反思,我们用文学去建构一个世界时,我们的文学行为、写作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否也是一种虚拟和自设。
另外我想请教凌逾教授两个问题,第一是序言《完整与分裂•真实与想像》的作者署名是“独裁者”,我在查阅资料时发现,王德威提到过“我”是这部作品的叙述者,但作者似乎并不是这个“独裁者”,是不是后面所说的一个叫“黑”的人?第二是我认为董启章这部小说不是科幻小说,在我看来科幻小说大部分是对未来的想象,可董启章反而在创设一个可能的世界,一个可能的叙述,那这属不属于我们所界定的科幻小说?还是另辟蹊径了?
凌逾:刚刚陈瑜教授说这部小说不是科幻小说,它确实不是,应该称之为“可能世界小说”更合适。《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其实是在实验各种可能的集合,比如真实与虚构的集合,写实、现代、后现代、后设小说的集合,男人与女人的集合,同性恋与异性恋的集合,又囊括了科幻小说、哲思小说和侦探小说等各种元素,可以说是将各种小说门类进行了结合。董启章的小说作品中有很多人物都反复出现,构成了多面的人物王国,倪匡称之为“连坐小说”。比如董启章多部小说中都出现过“独裁者”和“黑骑士”,其实都是隐喻“我”的多重化身和多重面具。《贝贝的文字冒险—植物咒语的奥秘》中,黑骑士自命为邪恶的文字魔法师,唯一嗜好就是收藏世界上最美妙的文字,所有被他诅咒过的人都要不停写作,直至他满意为止。其实,黑骑士是善良的魔法师。因为邪恶魔法师想限制和禁闭别人的力量,善良魔法师则是追求解放和开启的人,把公主从堡垒中救出,把精灵从山洞里释放,让想象力从黑匣子里飞升到天空中。黑骑士、独裁者形象也反映出作者的创作野心,独裁者创造性地书写了“婴儿宇宙”—一个仿若全知全能上帝眼中的世界。董启章近年生了一场大病后,写了《心》和《神》两部作品,可算是对独裁者形象的反思。
王瑛:凌逾教授的研究有两个吸引我的地方,一个是跨媒介,另一个是叙事。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跨媒介,尤其是我们学中文的同学。文学起初就是诗乐舞相结合,所以文学本身就是跨媒介的。跨媒介本身不是新鲜事,董启章运用跨媒介也不是新鲜事。大家都看过穿越小说吧?这种人物的穿越也不算新鲜事,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小说中已经能看到人物的穿越,人物走出来向作者要求了解自己的历史,要求了解自己的未来,甚至要求和作者谈一场恋爱等。
我没看过董启章的小说,但我从凌逾的研究中看到了许多有意思的东西。大家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今天凌逾教授给大家开启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就是跨媒介叙事学的前奏。为什么叫前奏呢?因为我国目前还没有跨媒介叙事学这个学科。跨媒介叙事从文学起源时已经存在了,那为什么到21世纪我们才开始研究?刚刚说凌逾吸引我的两点是跨媒介和叙事,其实我更关心的是跨媒介叙事学。我注意到凌逾说的两个词—“野心”和“开创”。实际上,从凌逾的研究中,我看到了她不想言说的野心,因为我从她的作品里看到了非常新的东西。《跨媒介香港》这本书很厚,有45万字,我当时想凌逾为什么不把它分成两本书,这样就有两部成果了。凌逾在书的后记里写到:“在书桌旁坐成一棵树。”这就是一种特别踏实的学术态度。像董启章的作品十分难读,我不想读,但是凌逾读下来了,她从发现西西开始,到发现香港,我相信她最后也会发现跨媒介叙事学。
跨媒介叙事学作为叙事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离成熟还很远。现在凌逾的研究,都是她自己原创的方法论,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新的概念和术语互相碰撞。如果你不了解叙事学,如果你没有看过很多作品,可能会听得一头雾水。但正是在什么都没有的状态下,凌逾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就目前叙事学的理论研究而言,不管是经典叙事学还是后经典叙事学,其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已经不能满足跨媒介叙事现象的研究。既然一种理论不能满足新现象的研究,那么新现象就会要求一种新的学科和方法论的出现。其实我一直没敢问,凌逾教授是不是想要建构这种新的学科,在叙事学的荒漠里生长出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
凌逾:王瑛教授提到了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跨媒介自古有之,如诗乐舞一体,古人看了场舞剑,因此诗兴大发,又或者是书法家从武术中得到灵感。但是古人的跨媒介多偶尔为之,而这个时代的跨媒介却多是有意为之。为什么跨媒介在这个时代突然迸发出来?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互联网的普及,过去没有那么丰富的可能性来承载它、拓展它,但是现在有了更多的可能。麦克卢汉认为古人是部落化的人,仿佛十八般武艺都要精通,才能生存下来,后来发展为非部落化的人,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如今人类又进入了一个重新部落化的时代,尤瓦尔•赫拉利就认为人类日益从智人走向智神时代。当前,认知科学和脑科学研究的急速发展,更要求我们成为全知全能的全才,这就是跨媒介叙事、跨媒介艺术一下子被提出来的原因。越来越多的人自发、自觉、集体式地进入这个领域,使之成为热点,成为潮流,而不是局部、个体、偶发的行为。现在的微信公众号就是极具跨媒介属性的载体,还有立体多维的动图诗歌,文字会漂流、转圈、变色、扭动、消失,随着情感的波动而变换形状,各种创意实验匪夷所思,很有冲击力。相较于传统诗歌,网络图像诗更立体、丰富、多元。
郑焕钊:今天很荣幸能向凌逾教授学习叙事学,凌逾教授把叙事学放在一个比较复杂的文本里讨论,对我很有启发。许多人在写作中会遇到一个问题,当他们将叙事学理论—如叙事视角、叙事形式、叙事结构—运用于文本创作时,写出来后很难找到文本中的灵魂,这与运用文化批评的方法相比会有不同的效果,后者带有抒发情感的人文气息,而叙事学理论较为形式化、抽象化。我们应该如何把理论与文化的研究,或者把叙事创作和社会现实的研究结合起来?这是个很难的过程,20世纪有西方理论家在做这两方面的研究,像詹明信和巴赫金就做得很好。其中还涉及一些需要讨论的问题,如叙事的形式是什么?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叙事方式的转变过程中,不只有故事讲述方法的变化,更多地涉及故事背后世界的变化,或者说读者如何理解这种世界的变化。任何一种新叙事方式的产生,比如后现代叙事,都反映了哲学层面我们对现代性和现代理性主体之间关系的反思,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封闭的因果关系等叙述模式就被解构了。像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的小说中蕴涵着多种偶然性和可能性,使读者在理解世界本体的过程中获取新的认知,这些新的认知同时也会导致读者理解现实世界方式的转变。
董启章的这部作品非常契合今天沙龙的主题。这部作品的特点是体现了我们时代的现实,这种现实被称为后人类主义或超人类主义,也就是“赛博格”(Cyborg)。“赛博格”起源于生物科学、航空技术等领域,是指为了便利宇航员在外太空的生活而给他们接上一些器械,这种方式逐渐普及到其他领域,如人工器官技术的飞速发展。这就带来一些问题,人还是原来那个人吗?现在人类的边界是否还是传统意义上人与世界的边界?在人和动物、人和自然、人和物质的边界已经处于不断模糊化的状况下,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上述问题?这是今天的现实之一。另一种现实体现在斯科特•拉什的《全球文化工业:物的媒介化》中,这本书研究全球化时代的创意产业及其背后的文化背景。在现今的文化工业时代,我们对社会结构的传统理解已不再适用。传统理解是指在马克思的建构下,社会结构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这种结构中,所有符号的意义建立在人类物质生活的基础上。但是在全球文化工业时代中,虚拟现实和仿真世界的出现,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辩证关系开始走向坍塌,文化下沉到物质中,物质也上升到文化中。在这种社会结构中,我们不再仅仅是体验文化、思考文化,不再是通过凝视一幅画,使我们的精神世界与图画中的艺术世界进行交流,从而获得感悟。今天的社会现实需要我们的参与,小到一篇微信推文需要我们去评论和投票,大到游戏需要玩家浸入式地参与其中,还有比如现在的3D电影比2D电影更能使观众沉浸其中,当画面中有一颗子弹飞来,我们的身体自然会躲避,身体和影像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是传统的观众凝视电影银幕而已。虽然AR(增强现实)和VR(虚拟现实)等技术在不断发展,但在现实运用层面依旧存在障碍。人们期待的VR电影是可以进入其中随意行动,与虚拟人物进行互动,自己创造故事。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改变我们与虚拟仿真的关系,改变我们的感知和互动,进而改变世界,给现实提供无限的可能性。
在《开工开物·栩栩如真》中,董启章通过虚构栩栩这个赛博人的形象,表现或然世界和实然世界的平行,又比如作品中的爷爷奶奶可以不借助任何接收设备,只靠耳朵接收电波信号,十分神奇,这在《超时空接触》《信号》等影视剧中也出现过,这些作品都体现出声波在传播过程中可以发展无数的世界。我们对外星世界的幻想大多也建立在对声音想象的基础上,如科幻小说《三体》中,主人公也是通过无线电波来召唤外太空的文明,声音中有无限平行世界的可能,这也是董启章在小说中用电波的意图,他想要寻找更多新世界的可能。
我觉得很奇妙的一点是陈瑜刚刚提到的一个词—“消解真实”。叙事本身磨灭了真实,实则就是作者提供了叙事上的可能,也就构成我们谈论的赛博时代、多重世界、跨媒介叙事的基础,他通过多声部和多重关系的互动,给予我们无限想象和思考的空间,比起一般的互动叙事能提供更多的信息,如最早用超链接进行的网络游戏,包括时下的橙光游戏,就是互动叙事的代表,但它只能提供有限的线索和选择,而小说能提供无限的可能。
张均:我今天听完感觉像坐过山车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写论文这么多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些方法和特点,所以当我面对一个与自己的研究完全不同的领域时,我会受到很大的冲击。我听凌逾老师分享的时候就受到很大冲击,因为我看了董启章的小说后,我写不出有关它的文章,不知道从何下手谈论我的感受。我以前写文章,比较强调作者与现实世界的对应关系,关注作家为什么写这篇文章,是否在回应社会向他提出的问题,这是我长期以来想问题的思路。今天听了凌逾老师的介绍,我觉得这种写作方法放在董启章的身上,是很难操作的。我感觉董启章写作不是为了呼应香港的社会现实,他似乎没有这种强大的动力,我们很难明白他那些叙事元素创作背后的现实契机,如果让我总结对董启章的感受,我肯定无话可说。我所研究的“十七年作家”都比较老实,他们只生活在一个实然世界里,没有或然世界和应然世界,所以如果让“十七年作家”看到这样一个作品,有着三重世界,而且读者和叙述者之间还能互相交流,他们肯定认为是天书,是荒谬的。我感到很困惑,如果有一天这个世界上全都是类似董启章的小说家,我该怎样生存?
前几年我跟同学们说过,你们爱看的东西我一无所知,我阅读的作品却逐渐消失在你们的视野里,总有一天我真的会失业,董启章的作品大概就适合现今这个年代。但当我心情很失落的时候,听到郑焕钊老师的发言,又燃起了一丝希望。他告诉我们,即使是如此技术化、后现代、赛博格的作品,仍然在回应当下的现实,呼应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叛逆的、不可预测的世界。这个世界重视主体对世界的参与,它不太强调我们对这个世界真理的占有,而是强调我们每个人都参与到这个世界中去,比方说游戏、互动叙事等。我还没有完全理解郑焕钊老师发言的精髓,不过总算看到一个方向,就是一个如此高度技术化的叙事分析,仍然可以和我们的意识形态建立逻辑关系,仍然可以用我熟悉的方法找到落脚点。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凌逾老师,就是郑焕钊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一种新的现实,但我总觉得他讲的现实放在今天的社会中,还不是完整的社会现实。打个比方,虽说虚拟世界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但把电脑一关,我们立刻又回到了现实,我们知道明天要上班,要买房子,要还贷款,这些事情不会因为作品中的主人公有多么自由、多么多元互动而产生改变。也就是说,“十七年作家”曾面对的、陈旧的社会问题仍然存在,并没有因为现代技术的突飞猛进而有什么不同。在技术如此先进、全球网络化的时代,我们所看到的现实和一百年、两百年前看到的现实还是相似的。我想知道,当我们的现实有百分之八十的因素仍然被这些传统的现实所占据的时候,这种现实与董启章的小说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董启章也是在现实中间,他并没有出于现实之外。我习惯的写文章方法就是文本内外的相互对照—文本内部的叙事与文本外部的社会意识之间的对话,但董启章这种超越现实的叙述手法与现实本身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想问凌逾老师,这能对我们有什么启发?
凌逾:多谢张教授的提问。其实董启章的作品中有写实主义,他一方面是很接地气的,致力于借助小说来切实地展现香港的发展史、百年史,不仅书写人物史,更是创造性地开拓出物件史、物的叙事学;另一方面他也是很不接地气的,作品中尽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董启章的接地气具体体现在讲述百年来香港的日常人事、物件用品、街区地图;讲述人与人的争斗,人怎么生存,怎么顺应或反抗时代的发展;讲述香港在不断上升发展的过程中,科技进步同时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董启章从个人的成长经历中窥探家族的成长、历史的成长,讲的一切都与我们息息相关,所以他没有脱离现实,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有血有肉的东西,他笔下人物也会谈恋爱,也需要吃喝拉撒,这一方面和“十七年文学”差别不大。
我在新书《跨界网》中,想象未来的全息世界,是受众进入虚拟世界后,就像进入了完全真实的世界,跟虚拟人物互动就像跟真人互动,如可以挑选多个恋爱对象进行一次次尝试,最后总能找到自己满意的。但这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面临更多选择的时候,我们其实更没有选择的空间;存在更多的可能性时,其实更没有可能。我今天讲了那么多,其实也有困惑,就是今天的小说到底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当各种叙事方法都用尽的时候,无穷的可能性都穷尽了之后,当达到了叙事的一个极限之后,该怎么办?
学生提问环节
学生:老师您好,这本《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我翻了二十几页后发现有点晦涩就放弃了。我在网上看过一些日本轻小说,也看过一些推理小说,可以说是各种套路都看遍了。但我第一次看见董启章这种反套路的作家。在我看来,他的作品除了带有科幻色彩以外,其他方面似乎有点浅薄,更像是一种人文哲学心理小说。我们常说“文以载道”,相比马克•吐温、欧•亨利等作家的创作,这部作品并没有一种非常接近现实的感觉,反倒是很虚幻,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新时代、新媒介产生的必然结果。这种写法是为了表达对网络时代物质发展和现实社会的担忧?还是在书写自己理想的社会结构,想要来改造这个社会?这是我的疑惑。
郑焕钊:有本书叫《论无边的现实主义》,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什么是现实主义?比方说在当下的中国,我们所呼唤的现实主义是人民群众伟大实践的现实主义,这跟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实主义中包含的内容非常复杂。至于写实,它写的是一种怎样的“实”?是外部的社会现实还是人的心理现实?这又是不同层次的现实。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网络小说其实也没有脱离现实,穿越小说、耽美小说有没有脱离现实?它们同样没有,所有网络小说的背后都有一个核心结构叫“屌丝逆袭”,就是主角在书中不断“开挂”,最后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为什么是“屌丝逆袭”的结构呢?我们有数亿网络读者,而且他们的购买力很强,去年中国网络文学的市场规模接近200亿元,为什么网络文学会有那么大的吸引力,而且美国也有不少人喜欢看中国的网络小说,这些现象反映了什么?反映了心理现实,这些网络小说满足了读者的欲望需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越压抑,就越希望在网络小说中实现自己的欲望。所以网络文学的写作有一个基本公式,就是要按照马斯洛的心理需求层次理论来写作,对于许多网络文学作家和读者来说,他们需要的不是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的满足,他们只停留在第一层次,即生理层次的需要。
我们在各种场合会面临各式各样的心理压力,这些都可以在小说中表现出来,所以董启章的这部作品表面上离现实很远,但恰恰离每个人的内心很近。回到刚刚的问题,我们如何理解现实?你刚才所说的要干预社会,要促进社会的进步,那是一种现实,但实际上文学中有很多不同的现实。比如我们要如何理解意识流小说,它的现实在哪里?它其实写的是人内心的一种心理真实。你能说意识流小说起到干预社会、干预现实的作用吗?未必。然而他实际上也写出了人,人本身就是复杂的、多样的,我们以前常说一句话,文学是人学,假如这句话成立的话,那么文学能把人的各个层面都写准确,这也是一种现实。
凌逾:有些书我们看不下去,也很正常,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菜”,都有自己的心头好。我们说“文以载道”,以前我们认为“道”只有一种,但这个“道”其实有很多的层次和面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自己的生存方式、自己的想象空间、自己的心理需求。在董启章的小说里恰恰没有固定的、统一的、一元的“道”,男人与女人、少年与老人的需求都不同,它能满足不同层次、不同族群的不同需求,所以它的现实部分也是非常丰富的。如今的社会太复杂了,以前几个月、几年才能抵达异国他乡,现在乘坐飞机几个小时就能到达,而且借助网络,我们几秒就能了解到地球上任何有网络地方的事情。庞杂的信息同时涌进我们的视野,作家怎样才能展现出这么复杂的现实?如此繁复的社会才会产生出如此繁复的小说,董启章写这篇小说就像耍口技一样,把各种元素和现象同时铺展出来,因此产生了层层叠叠的叙事效果,就像画家拿画笔反复涂抹一样。
学生:当我们提到“信息时代的文学”时,这个短语至少有两种内涵,一种是信息时代使文学产生一种新的实验性的可能,董启章就呈现了这种可能,即把人在信息时代中的体验用文学的方式表现出来,像老师提及的最早运用超链接的网络小说,就是用网络这种新媒介进行新的叙事尝试;另一种是以网络为写作平台,将网络文学发展为写作工业的文学。最早的一批网络文学倡导者更强调前一种以网络为实验的文学,但近几年大家熟悉的网络文学其实是后一种。老师您怎么看待这两种网络文学之间的关系?
郑焕钊:网络文学刚出现的时候确实给人们带来了很多惊喜,人们认为网络这种新媒介可能会给写作带来更大的自由,包括写作本身的自由、小说形态的自由和读者接受的自由。写作的自由我们都能理解,网络写作本身是没有门槛的,我们在什么平台都可以写,跟一定要经过编辑审查才能发表,投稿可能还会被退稿的写作相比,今天的写作很自由,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写作,作家的身份也就下降了,作家变成了写手。对小说形态而言,我们一直期待网络可以改变封闭的写作载体,比如董启章的作品再复杂,也是在有限的物理载体中呈现的,但是互联网技术可以带来互联互通的效果,这种互联互通可以发展出不同的故事线索、情节和结局,这是它故事形态本身产生的变化。从读者的角度来看,我们能够不遵循作者的写作顺序,作者对人物情节的安排,而是按自己的想法来选择阅读,这是我们一开始对网络文学寄予的厚望,但事实上,世界上这类网络文学体裁的存在仍然是少数。
中国早期的网络文学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探索,但在这个过程中,很快就有资本涌入,从而使网络文学变得商业化,虽然充分挖掘和利用了互联网平台的大众性和市场化的特征,但这样下去必然背离原本的发展方向,所以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到现在变成了网络类型文学,实际上它比较接近我们传统所说的通俗文学,区别仅仅在于—比传统的写作门槛更低,跟读者的互动度更大,读者群体更巨量。那么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技术性?有,互联网确实改变了文学的传播形态,改变了读者和作品之间的关系。
所以,对于网络作家来说,最艰难的事情就是和读者的博弈。在写作过程中,读者会不断提出他的意见,会不断干扰你的写作,你又要不断地和读者博弈,你既要满足他,又不能完全满足他,这个过程就反映出新媒介与传统媒介相比,对作者的要求不一样了,这种改变和我们一开始想象的不同,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这恰恰就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比如说一次社会变革会引发非常极端的口号,但这种口号是不可能被采纳的,可是你要实现变革就必须要有口号,于是那些相对可行的口号就会被采纳。互联网本身就有着极端自由的状态,但在人类社会制度之下又很难实现,于是我们就会采用相对妥协的方式,这种妥协有技术的因素、资本的因素、大众的因素,这些因素的博弈就造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结果。
凌逾:郑老师说的这点很有意思,就是网络文学沿着超链接的方向本来应该变成很精英的、具有高级叙述性的互动小说,变成网络作家的作家;但现在却因为商业化和资本的介入往低端走,使网络文学变得低俗、艳情。曾有人告诉我,有个网络作家,一年可以写几十万字,赚几百万,我说太牛了,然后一看他的作品,都是色情、武侠、玄幻类型的小说。虽然迎合了大众快餐式的口味,但能否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笔,这是存疑的。所以像你刚刚说的满足和不满足的博弈关系就是董启章的心理,他不愿意成为写言情、武侠等类小说的通俗作家,他想做一个更高级的作家,一个曲高和寡的作家,成为作家的作家,所以他不是刻意地去寻求某一类读者。如何在大众化与精英化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是一个难题。
王瑛: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就像我们今天读到古典诗词其实都是被筛选过的,在我们看到的作品之前一定有大量的赝品,大量的垃圾。我非常喜欢苏轼,大家读读苏轼就会发现,他的作品中也会有一些色情的诗词,换言之,网络文学也是一样的,网络文学在今天肯定是有良莠的,可能是莠的更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网络文学中肯定会出现精品,不会全部都是垃圾,全部是平庸之作,但在此之前,肯定会有垃圾的存在。
学生:老师您好,我是个本科生,今天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到这里,感谢老师们给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我有一个疑惑,我们之前研究二十世纪文学的时候,注意到它跟大众的关系,但类似今天说的三重世界这种复杂的新形态的叙述模式出现之后,很多读者可能觉得难以接受,就像当初先锋文学兴起也是很难让人接受的。我们应该怎样看待绝大多数读者难以接受新形态文学出现的现象呢?
凌逾:其实这很好理解。因为内地读者有口味偏好,多喜欢波澜起伏的、故事性强的、多讲恋爱与悲情的故事,很多获奖作家的作品都是这类。为什么说香港作家很难进入内地市场呢?因为他们不玩这一套,他们玩自己的一套,自成体系,20世纪中后叶香港社会发展比内地快些,我们的创意文化很多都赶不上他们。等我们的经济发展加速,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视野开阔了,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读者能接受这些新形态的文学。
王瑛:可能还是要看读者群体到底是谁,当下大众对文学的接受主要来自于影视剧、网络小说,称其为大众观者或手机阅览者可能更合适。真正有兴趣读文学作品的人是我们在座的这些人,这些文学专业的人,我们从严格意义来说已经不属于大众读者了。对专业的文学研究者来说,董启章创作的这类新形态小说,我们会渐渐养成阅读习惯的。
学生:我想接着上一个同学的话题提问,像董启章这类作家的作品技巧性太强,普通读者难以接受就会放弃,作品就无法获得读者,那这种脱离社会现实的叙事写作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比如我读过马原的《西海无帆船》,就觉得它像是一个游戏,跟反映心理、反映社会现实是没什么关联的,给人一种他就是写着好玩,为了展示技巧的感觉。
凌逾:有人说董启章不现实,其实他很现实。他从一开始就在探讨“我城”“V城”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香港会发展到今天,香港人的心理转变等问题。董启章写过一部小说叫《地图集》,研究香港从英国殖民开始一百多年来的所有地图,把它们全部整合在一起,通过形形色色的地图符号、有形无形的争战去解读香港的故事,他关注香港那些边边角角非常细致的东西,那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并把它们挖掘出来,我有一篇论文《后现代的香港空间叙事》专门分析这部作品。大多数小说可能就写日常的生活,但是董启章喜欢书写蹦极和过山车一类的极限感觉,他不断地跨越小说的边界,不断地去实验,以达到叙事的巅峰。这和别人的玩法是不一样的,这是一种生存的方式,也是一种拓展的可能性,大家永远都在某个平面层次里玩,他却往高处走,我觉得他的意义就在这里。
郑焕钊:我补充一下。你们读过康德的作品吗,觉得难不难?读过爱因斯坦的著作吗,看得懂吗?他们的东西能不能抵达大众?对于人类突破极限去认知这个世界、认知人与宇宙更大的可能性有没有意义?那是不是任何一个作家写作的目的都是面向大众呢?比如卡夫卡的《变形记》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这类小说,有多少人能认同,但它们对于我们认知人类的精神世界有没有价值?有些小说的读者注定是少数的,但这些少数人能够继承它的精神,人类的极限就在这里被突破,所以不是所有的小说都一定要面向所有的读者。
学生:再补充提问一下,我的视角可能比较狭窄,因为我会对照过去发生过的文学现象。如果拿董启章跟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实验派相比,前者发生在香港,后者发生在内地,他的作品有没有类似先锋派小说由于受众的原因而发生转向的可能性呢?
郑焕钊:董启章对小说形式的探讨跟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先锋派小说的形式探讨不是一回事,董启章是理解和把握了一种新的现实之后创造小说,而先锋派小说更多的是模仿和学习,也就是说,这两者面对的是不一样的现实,他们的结果自然不同,并不能直接作比较。
凌逾:郑老师谈得好,先锋派小说比较西化,学习借鉴了魔幻现实主义、荒诞派这类的作品,经历过模仿的阶段。而董启章的小说作品恰恰跳离出这种模仿,香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到七十年代西西《我城》的出版,本土意识逐渐增强,从也斯到黄碧云,再到李碧华,现在到董启章,香港作家已经形成了很强的本土意识。虽然董启章是香港大学英文系比较文学专业的硕士,他的硕士论文是全英文写作,研究的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但是他没有刻意地去模仿西方,没有那么多西化的东西,更多的是从香港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原生态的东西。
张钧:先锋派小说中有一种潜在的对话,对话的是我们曾经的历史,而香港文学发展的背景是香港的环境,是虚拟时代、电脑时代。他们的社会发展更快,自然走得更远,所以这两种文学形式没有太大的亲缘关系,区别很大。再说先锋派小说的转向是有争议的,在研究界有两个说法,一个是转向,这是在文学史的课堂上经常说的;另一个是制衡,是指他们的题材选择表面看起来有很大的转变,但基本的精神和叙事技巧仍然保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