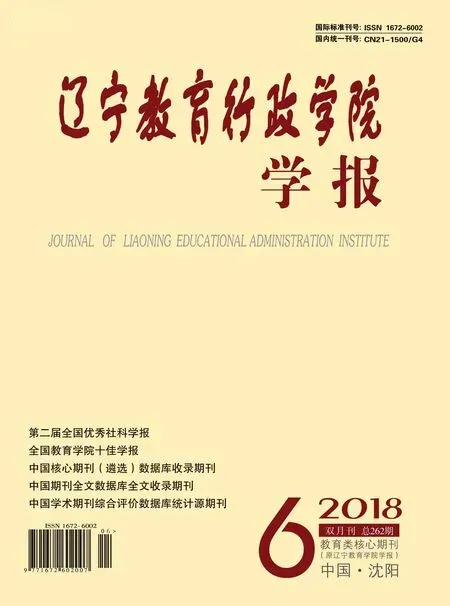论刑法中的原因自由行为
——兼论“醉驾型”犯罪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合理性
2018-04-03姜梦
姜 梦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 100089
在“醉驾型”犯罪之中,我国刑事司法实务界有判处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惯例。前段时间,发生于安徽省的“陈运醉驾案”终审被判处死刑,但被最高人民法院发回后改判无期徒刑,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在“醉驾”类犯罪当中,处罚的基础是刑法上的“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由于该理论在我国刑法实务与学术界是否得到承认尚存争议,因此,对牵涉“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相关类型的犯罪,在对其解读时亦常常存在困难。
一、域外刑法对原因自由行为的规范
基于责任原则之下,“实行行为与责任能力必须同在”这一原则是刑事处罚可罚性的基础,因此,当实行行为进行时、责任能力已经在客观上确实减弱的情况下,不寻找此种情形下的处罚逻辑,就会破坏责任原则之下的可罚性基础,由此而诞生的“原因自由行为”一直为域外刑法学理论所关注和探讨。
最早能够找到的类似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论述,源自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当中的内容,其指出:“将饮酒行为视为罪恶中,忽视其对责任能力作用,在此情形中得以加重处罚之事由。”②[P24]而后,这一问题又经托马斯·阿奎那和普芬道夫进行过讨论,并最终由克莱恩施罗德确定以“原因自由行为”作为概念标志以表达使用。③[P600]而在该概念为学界所接受并广泛使用后,对于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同样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19世纪中叶,在萨维尼等法学家的力主之下,《德国刑法典》并未对于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进行详尽的规定。④[P25~26]但是,这种过分苛求责任主义的观点逐步为司法实践认识到与公众观念上的不符,更是在刑罚导向上使得法律引导公民为自险无责任能力的行为。因此,责任理论开始异化,主张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逐渐变得有力,进而发展至今已成为通说观点。④[P25~26]
现代大陆法系各国刑法典对于原因自由行为的规范并不相同,比如,《意大利刑法典》上对于原因自由行为基本上在总则规范当中予以明确,该国法律规范对于原因自由行为的规定大致为:当陷入风险的原因是由于行为人自身可控制的行为所引起的,则不能以行为时无责任能力而寻求罪责的减轻。但是,产生于偶然事件或者不可抗力的醉酒、使用麻醉药品的状态,而导致危险行为最终发生的,要减轻行为人的罪责。但是,对于主动自陷无责任能力的行为,能够证明自陷无责任能力是为事后所脱罪借口的,刑罚得以加重,并且对于行为人属于惯常醉酒的情形而言,由于经常陷入醉酒状态,对于严重的后果而言有预见性,因此,在惯常醉酒状态下实施的犯罪行为,刑罚同样予以加重。⑤[P32~33]
《德国刑法典》对于原因自由行为采取了分则立法的模式,《德国刑法典》第323条a表述为:“(1)行为人故意地或者过失地通过酒精饮料或者其他醉人的药物使自己处于昏醉状态的,处5年以下的自由刑或者金钱刑,如果他在该状态中实施违法的行为却因为他由于昏醉已是责任无能力或者因为没有排除责任无能力而因此不能处罚他的话;(2)其刑罚不得重于对在昏醉中所实施的行为所威吓的刑罚;(3)该行为只有根据要求、授权或者刑罚要求才予追究,如果昏醉中的行为只有根据请求、授权或者刑罚要求才能予以追究的话。”⑥[P195]
瑞士对于原因自由行为采取了总分则相结合的立法模式,《瑞士联邦刑法典》第12条规定为:“(例外情况)如果严重之精神障碍或意识错乱是由行为人自己故意造成,并在此等状态下实施犯罪行为的,不适用第10条(责任能力、无责任能力)和第11条(限制责任能力)的规定。”⑦[P4]该法第263条规定为:“(在自己造成的无责任能力情况下实施的犯罪)1.因自己造成醉酒或麻醉,且在此等情形下犯重罪或轻罪的,处6个月以下监禁刑或罚金。2.行为人在此等情形下实施了只规定科处重惩役的犯罪的,处监禁刑。”⑦[P86]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域外刑法学理论上对原因自由行为的探讨留下了相对丰富的学术资料,但大陆法系刑事司法实务对于原因自由行为而言,其态度是比较暧昧不清的,在接受原因自由行为的问题上,大陆法系的刑事司法实务界仍然比较保守。比如,德国联邦最高法院1996年8月22日的判决对于酒后闯入过境检查处撞死两名官员的行为,该判决对于原因自由行为而言持有相对意义上的否定态度,仅肯定了部分过失的行为,而否认对于危害道路交通和无证驾驶两个行为的故意行为,特别是否定了在原因自由行为当中构成要件的延伸。⑧[P91~93]
二、关于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探讨
虽然大陆法系许多国家在刑法典中均部分承认了原因自由行为理论,但是,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尚不能明确地解释其为如醉酒等丧失罪责能力的状况下提供可罚性的依据。大陆法系的许多学者同样对于原因自由行为理论提供的可罚性依据进行了探讨,具体来说是以下两个方面:
(一)构成要件行为(实行行为)为根基的可罚性论
在“行为与责任必须同时存在”的责任主义语境之下,讨论原因自由行为必须建立在如何解释“同时存在”这一命题。由于醉酒或陷入心智缺失的状态后,显然已不具备认识事物的前提,故而必然不能具备责任能力,因此,责任能力(认识)在客观上只可能存在于因醉酒或其他原因造成心智缺失之前。基于这一客观事实出发而形成的考虑,如果需要寻找“行为与责任必须同时存在”的理据,就只有将构成要件行为适当地提前(实行行为提前),才能够寻找到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依据。具体来说,刑法学家主要认同的理由存在于“原因行为时的责任理论”与“类间接正犯”的理论二者。
“原因行为时的责任理论”,是指“具备责任能力的原因行为是追究责任的对象,如果能够肯定原因行为同结果行为(结果)之间存在一定的构成要件关系的,即可对原因行为追究刑事责任”。⑨[P36]而“类间接正犯”理论是指将陷入心智缺乏而造成责任能力缺失的情况,与间接正犯中“利用无责任者为犯罪行为”进行比较,试图援引间接正犯的可罚性根据反过来适用于原因自由行为当中。由于二者均是试图将原因自由行为的责任处罚对象(即构成要件行为)对于常见的犯罪构成而言适当提前,因此,均是扩张了构成要件行为的范围,是试图在构成要件层面的基础上来解决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问题。
但是,笔者认为,无论是“原因行为时的责任理论”,还是“类间接正犯”理论,均存在其致命性的硬伤。具体来说,“原因行为时的责任理论”的问题在于,行为人所为的原因行为在这一理论的框架下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刑法的处罚对象,但是,这些行为本身可能根本不具备违法性。通俗地说,行为人即便是大量饮酒,或者服用精神类药品等等行为,均不是刑法所禁止的行为。德国刑法学家洛克辛教授就指出:“反对行为构成模式的一种主要论点在于,对一种结果故意进行的原因设定,还没有表现为法律所要求的那种构成的行为(Tatbestandshandlung)。”③[P601]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强行将这一类行为纳入主观目的性的思考中进行评价,进而以其行为所具有的、可能的目的性来评价为犯罪行为的对象,有严重的不当扩张构成要件范围的嫌疑,构成要件本身的客观性主导地位,事实上,也可能已经不复存在,并且也会丧失构成要件的规范属性与犯罪圈的厘定属性。另外,这样一种对于所谓的“原因”的追索,事实上是首先设定了结果的必罚,而后再寻找责任最后存在的节点,并直接“不分青红皂白”地将这个节点作为处罚的基点的,显然与犯罪论整体上证成犯罪的逻辑不通。如果始终坚持客观主义的刑法理论并坚持“违法是客观的”这一基本立场,这样的对构成要件行为(实行行为)进行的任意扩张,很难令人接受。
与之相对,“类间接正犯”理论同样具有很严重的问题。具体来说,“类间接正犯”还是援引的间接正犯的理论而寻求的处罚逻辑,但问题在于:首先,间接正犯本身即是一种对犯罪构成的修正,而原因自由行为本身还没有完全地离开基础的犯罪论层面。根据笔者的观察,在以“违法——责任”为框架的基础的犯罪构成当中,特别是在违法的阶层之上,并不能够存在对犯罪构成行为就可以大肆进行修正的情形。换言之,修正的犯罪构成应当至少是在犯罪构成完全结束之后的问题,而不应该在基础的犯罪构成还没有能够尽善尽美的前提之下,就直接援引修正的犯罪构成来解释基础的犯罪构成的问题,这种对“犯罪构成的提前修正”同样有肆意之嫌。其次,间接正犯理论本身恐怕尚不能完全解释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问题,具体来说,“类间接正犯”的理论只是注重了间接正犯理论当中间接正犯的“工具性”这一面,而未能注意到间接正犯理论当中“教唆性——支配性”的另一面,其后果是造成“类间接正犯”体系的片面性。如果行为人在醉酒之后完全丧失了责任能力,按照“类间接正犯”的逻辑,行为人应当负完全的刑事责任。但间接正犯在很多时候只能存在至教唆的程度,如果未能够达到对实行行为人的支配,则很难承认间接正犯。换言之,当行为人自陷无责任能力、心智缺失的程度尚未达到意识完全丧失、但意识已经有所减弱的程度之下,行为人不能按照“类间接正犯”的逻辑来成立原因自由行为处罚,同时,原因自由行为本身更构不成一个教唆行为,使得行为人再承担教唆的罪责,在这种情况之下,行为人就只能被减轻甚至免除刑事责任。这与客观公正显然不符。⑩[P258~259]
(二)责任修正理论
由于在构成要件的层面上,需求可罚性根基的尝试并不能够尽善尽美,因此,也存在对立的责任层面上的修正理论来寻求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根基。具体来说,责任修正理论与构成要件模式之间共同的认识前提还是“实行行为与责任能力必须共存”这一前提,但对于实行行为本身并不加以改动,而是在责任的层面上,责任修正理论认为,对原因自由行为下的行为人的责任能力是一种修正。换言之,刑法在原因自由行为当中,例外地承认了客观上、实际生活的认识上不具备责任能力的行为人具有责任能力。这是对于责任概念本身进行的一个修正,因此,在责任的层面上,为原因自由行为本身寻求到了可罚性根基。
责任修正理论的提出同样备受质疑,具体来说是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责任修正理论同样是对犯罪论本体进行的修正,在基础的犯罪论尚未完成的情况下进行的修正同样是肆意的;其次,责任修正理论动摇了故意与过失同构成要件行为之间的关系,③[P600]并且有动摇了“故意”这一概念的嫌疑;再次,责任修正理论同实际的、客观的责任意识是完全对冲的,没有认识到原因行为同结果行为之间的关联性,更没有注重对于原因行为本身的评价,其评价的对象还是在客观上无责任能力下实施的、触犯构成要件的行为本身;最后,对于这一责任修正理论在实定法(总则)与习惯法(与总则相关的判例)上,均找不到相对应的法规与判决的必要支持,这一所谓的对罪责的修正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嫌疑。③[P600]
笔者认为,上述对于责任修正理论的批评有一定道理,但该理论仍然可行。
第一,针对责任修正理论是对于犯罪论本体进行修正、基础的犯罪构成与犯罪论尚未完结的情况下的修正这一质疑。笔者认为,这一批评对于维护犯罪论本体,特别是积极的犯罪构成的稳定而言,具有一定的地位,但是,笔者同样认为,基于原因自由行为已经属于犯罪论进入到责任是否予以排除的临界点上进行考虑的问题,原因自由行为之前,所有的积极的犯罪构成均已基本完成且不存在明显的修正之处(特别是故意和过失已经判断完毕),因此,需要指出的是,在原因自由行为之后的责任阶层当中开始对犯罪构成进行必要的修正,相比较直接修正犯罪构成要件阶层而言,是一种代价较小的对犯罪论阶层的修正。且这种修正是基于对朴素的公平正义的理解而必然进行的一种结果,修正的阶层越靠后,对犯罪论的影响自然也就越小,是对犯罪论特别是基础的犯罪构成的“最小伤害”。
第二,针对动摇故意与过失概念本身的质疑。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将故意与过失作为优先阶层判断,并试图在优先层级上建立与实行行为之间关联的一种认识而产生的结果,对于故意或者说认识的一种例外性的承认,并不一定会动摇故意本身的概念,且从原因自由行为的概念上考虑,认识仍然可能在原因行为时无可争议的存在,而这种认识与控制能力本身随着原因行为的延展,虽然在客观上消落,但在法律上仍可以被认为是行为人应当提高对自我的控制的一种要求,而认为应当加强对此种情况下行为人的自我监督。笔者认为,这并不会导致故意与过失这一概念的瓦解,相反会强化故意与过失概念当中,行为人的自我控制的意志属性这一面,对故意与过失概念本身而言,反而是一种增强。
第三,针对后两项质疑,笔者认为,对于批评责任修正理论仍然是处罚的构成要件行为本身这一问题,是没有真正地认清原因自由行为的处罚,根据仍然是站在客观主义刑法的立场之上。客观主义刑法的立场之下,实行行为有故意规制与犯罪圈公示,这两个重要的属性。肆意地修正一个属于客观的、公示属性的实行行为显然不妥当。因此,建立在实行行为本身不能够动摇的前提之下,修正相对主观化较强的责任阶层还是妥当的。而对于实定法依据的问题,德、日刑法典总则虽然可能在一定的时期之内缺乏足够的依据,但这并不能够成为阻却责任理论本身的依据,相反,法律及判例大量地为原因自由行为提供可罚性依据,无论在构成要件层面上的修正,还是责任层面上的修正,其实均已不存在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这一层面上的问题。
当然,对于修正责任阶层,也有观点提出了处罚原因自由行为的故意,需要具备“二重的故意”这一理据。⑽[P258~259]同样,我国学者陈兴良教授也指出“在存在双重故意的情况下,即醉酒是故意的,对于结果发生也是故意的,认定为故意犯罪当然没有问题。在存在双重过失的情况下,即醉酒是过失的,对结果发生也是过失的,认定为过失犯罪也没有问题。在故意醉酒后过失造成结果,或者过失醉酒后故意造成结果的情况,我认为应当根据对结果的心理态度分别认定为过失犯罪或者故意犯罪”。⑪[P183]但是,这样一种认识却可能存在着真正的、动摇故意概念的风险。换言之,在自陷无责任能力的前提之下,考虑着例外地承认存在责任能力,还有政策性和公正性的支持,虽然例外地修正了故意的概念,但基于对犯罪论本体的最小伤害还能够为公众所接受;因此,在已经过失地陷入到无责任能力的前提之下,即便因醉酒、精神疾病发作等原因导致对结果的追求的产生,倘若还以故意犯罪追究责任,显然对于公民本身而言,已陷入到巨大的风险当中,公民本身在责任层面上尽到的可防范的义务只能存在于尚可控制自身意识之时,不可能强求公民在已丧失意识之后再产生对结果的不追求,这显然不切实际。换言之,责任修正理论能够被承认,不仅仅是因为其是对基础的犯罪构成的“最小伤害”,其可罚性的原因还在于未能尽到防范自险无责任能力的发生,从而触及了刑律上对于罪责的延伸条款而成立了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
三、我国刑法上的原因自由行为
我国《刑法》第18条第4款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这一条款被我国部分学者视为是我国刑法承认原因自由行为的法理之一。周光权教授曾特别指出:“醉酒的人通常是在某种程度上减弱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但并非完全丧失这种能力。行为人以酗酒壮胆作案,即便犯罪时辨认、控制能力降低,也必须受到惩处……如果行为人已经预见自己醉酒后会陷入丧失辨认、控制能力的病理性醉酒的境地,而故意饮酒,最后造成犯罪结果的,则应当根据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确定责任。”①[P171]
根据周光权教授对此部分的解读可以发现,事实上我国《刑法》第18条第4款之规定存在两个方面的探讨。一是,我国刑法的立法者认为,行为人虽然醉酒当时丧失了一部分的辨识能力,但并未丧失全部的辨识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的行为仍然有成立责任的可罚性空间,故而肯定了在醉酒状况下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能力。二是,当行为人自陷无责任能力之时,行为人的行为因原因自由行为而入罪,亦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不过,即便是按照对我国《刑法》第18条第4款之规定进行“两面性”的解读,亦可以发觉这样一种解释的方法其结果上是我国刑法系不承认原因自由行为的基本法理。换句话说,在“实行行为与责任同在”的语境下,原因自由行为理论本身的探讨,在于首先确认行为人已不具备责任能力,在这一前提之下,进而才考虑以“原因自由行为”这样的概念架构来寻求处罚的逻辑合理性。而我国《刑法》解决这一前提的方法是立法者首先肯定了在该前提之下,行为人具备责任能力,从而肯定承担刑事责任。这一对《刑法》第18条第4款之解读,也在事实上与我国刑法学界抛弃原因自由理论的呼声不谋而合了,⑫[P49~57]其结果都是拒绝适用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逻辑框架。这样一种解释看似既不违反“实行行为与责任同在”的基础处罚法理,更解决了原因自由行为之下的理论窘境,看似有极强的合理之处。
但这样对我国《刑法》第18条第4款的“两面性”解读、甚至于在实质上是“抛弃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做法,在具体案例当中可能会导致显失公正的情形发生。比如,行为人酒力很差,只喝一杯就会有嗜睡、乏力等严重的醉酒反应;而该行为人在携带其未成年的子女、参加某次聚会时,被不知道其携带了未成年子女的他人所恶作剧,在其饮料中倒入了一杯高度白酒,行为人喝了该饮料后果然出现醉酒反应,在回家的路上其未成年的子女恰巧无意落入水中,而此时行为人因醉酒竟躺在路旁呼呼大睡(即:在过失醉酒的状况下发生的不作为犯罪)。在这一案例中,显然恶作剧者适用间接正犯的理论有极大的不合适。且在我国《刑法》第18条第4款并未对“醉酒”限定在故意醉酒的前提之下,如果拒绝适用“原因自由行为”的理论,而以对我国《刑法》第18条第4款的错误的“两面性”解读的话,那么,其结果必然是行为人应当因不作为行为而明显地构成故意杀人罪。但很显然在整个的案例当中,行为人在正常状况下根本不可能不想营救自己的子女,完全不可能放任子女死亡的结果发生。其不营救子女的原因,只能是因为醉酒导致的认识能力和意志能力的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强行地要求行为人承担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显然有违社会的一般认识与朴素的公平正义观。更何况,事实上在整个案例中,行为人实际的罪过,可能仅仅只是在携带未成年人参加聚会的情况下,喝下所谓的“饮料”时未能及时、审慎地察觉出该饮料可能暗含的酒精成分,造成了对未成年子女的管控能力下降。这样一种主观上的罪过,显然具有意外事件的成分,至多只能停留于过失的层面之上。但由于行为人罪过的产生时,与实行行为完全分离,实行行为的产生完全位于主观罪过之后,因此,在酒精辨识上的错误根本不能够成为行为人主观罪过为过失的处罚理由,这样在“两面性”的解读之下,行为人实际上还是只能承担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这很不合适。
笔者认为,想要解释我国《刑法》第18条第4款之规定,依旧只能以原因自由行为理论本身来寻求解释的空间。换言之,如果单纯地将《刑法》第18条第4款认为是“两面性”地承认了醉酒状况下行为人在客观上就具备责任能力,而将《刑法》第18条第4款作为法律的提示性规定进行理解,在实际的处罚逻辑上会常常陷入困境。因此,理解《刑法》第18条第4款之相关规定,只能是认为醉酒的人犯罪的,在我国刑法上例外地承认了具备责任能力。换言之,《刑法》第18条第4款在实质上并非是法律的提示性规定,我国法律也不能因此而被理解成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肯定行为人在客观上、实际上就具备责任能力,而只能适用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认识,认定该条款系对责任能力的修正条款或者拟制条款。即采用“责任修正”的理论对本条款进行解读。
采用“责任修正”的理论对《刑法》第18条第4款进行解读具备一定的理论优势,首先,它在客观上保证了犯罪论体系的基本稳定,而使得犯罪论的运转体系同社会实践的一般认知相同,不使犯罪的认定与社会认知过分分离。其次,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处罚的公正性,在理论上对于“实行行为如何同责任能力同在”的问题,在逻辑上进行了尽可能尽善尽美的安排。最后,采用“责任修正”的理论在我国更是避免了“无法律规定或先例”的问题,使得“责任修正”的理论在我国可以找到实定法上的依据,避免了原因自由行为在认定中对于“责任修正”理论找不到实定法上依据的尴尬。
四、以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看“醉驾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合理性探讨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法发[2009]17号)》中指出:
“刑法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行为人明知酒后驾车违法、醉酒驾车会危害公共安全,却无视法律醉酒驾车,特别是在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造成重大伤亡,说明行为人主观上对持续发生的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对此类醉酒驾车造成重大伤亡的,应依法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2009年9月8日公布的两起醉酒驾车犯罪案件中,被告人黎景全和被告人孙伟铭都是在严重醉酒状态下驾车肇事,连续冲撞,造成重大伤亡。其中,黎景全驾车肇事后,不顾伤者及劝阻他的众多村民的安危,继续驾车行驶,致2人死亡,1人轻伤;孙伟铭长期无证驾驶,多次违反交通法规,在醉酒驾车与其他车辆追尾后,为逃逸继续驾车超限速行驶,先后与4辆正常行驶的轿车相撞,造成4人死亡、1人重伤。被告人黎景全和被告人孙伟铭在醉酒驾车发生交通事故后,继续驾车冲撞行驶,其主观上对他人伤亡的危害结果明显持放任态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二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⑬
根据该意见,我国刑事司法实务界确立了在醉驾导致严重车祸、造成公共安全和人员的重大损失的情形下,判处行为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审判趋势。对于这一趋势,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均作出了许多解释。比如,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方文军曾撰文指出:
“行为人醉酒驾车肇事,一次性撞击造成特别严重的伤亡后果,说明行为人醉驾程度严重,基本丧失对车辆的控制能力,且多属于严重超速行驶,对公共安全的危险程度高,故应当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这种意见有一定合理性……《意见》以黎景全案和孙伟铭案作了说明。这两个案例的被告人都是在严重醉酒状态下驾车肇事,连续冲撞,造成重大伤亡,说明二人主观上对他人伤亡的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故二人的行为均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应当说,对于类似孙伟铭案、黎景全案这种有连续冲撞行为的案件,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已基本形成共识……对于行为人高度醉酒后明显控车能力不足,又有超速、逆行、闯红灯等其他违法情节,肇事时一次性多点撞击,造成重大伤亡的,鉴于这种情形下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放任心态的理由较充分,故可以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如果行为人醉酒后没有明显降低控车能力,肇事前也没有其他交通违法情节,因一时疏忽而违章肇事,即使肇事时一次性有两个或多个撞击点,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的,也不宜简单地为了体现严惩而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该认定为交通肇事罪的还是应当依法认定。”⑭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对于这一司法认定趋势的解读,仍然是基于对《刑法》第18条第4款之“两面性”解读之下的结果。换言之,论者仍然认为,行为人在醉酒的状态下,仍然具备责任能力,故而确立了对其可罚的地位。可是,《意见》又指出:“一般情况下,醉酒驾车构成本罪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并不希望、也不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属于间接故意犯罪,行为的主观恶性与以制造事端为目的而恶意驾车撞人并造成重大伤亡后果的直接故意犯罪有所不同,因此,在决定刑罚时,也应当有所区别。此外,醉酒状态下驾车,行为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实际有所减弱,量刑时也应酌情考虑。”⑬又在量刑的阶段,似是而非地承认行为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实际有所减弱,如果按照“两面性”解读来看,显然在统一性上难以令人满意。
但是,基于前文已经论述了认为《刑法》第18条第4款“两面性”认识的错误问题,在此可不做重复论述。但援引原因自由行为理论而言,是否具备对于现在司法实践操作的合理解读?笔者的答案仍然是肯定的。具体来说,责任修正理论下的原因自由行为,可以承认的是行为人在自陷无责任能力的情况之下,对于进行实行行为时,例外地肯定了存在责任能力,而这种责任能力不必然一定在醉驾当中是故意或者过失。换言之,行为人在喝酒前已认识到自己有可能会在之后去闹市区开车并丧失控车能力,仍然选择自陷无能力的前提之下,考虑对其责任上非难是合理的(但非难的不能是喝酒行为本身),从而,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后果,在事实上成为了行为人已丧失控车能力的重要证据,进而有承认行为人有危害公共安全故意(放任)之空间。而相反的一点是,倘若行为人在酒后尚未完全丧失控车能力,也就说明行为人尚具备一定的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适用原因自由行为,但对未造成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可以适用交通肇事的罚则,考虑行为人在主观上仍有“过于自信”而成立的空间;或者根本没有适用原因自由行为的必要,因为行为人的责任能力仍在承担刑事责任能力的底线以上。
当然,我国学界也有学者提出观点认为,可以参考德国模式在刑法分则当中就特别罪名承认原因自由行为理论。⑮[P109~114]但笔者认为,基于笔者前文已论述的就我国《刑法》第18条第4款的解读而言,我国《刑法》在事实上,已有承认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特别条款,按照此认识来看,在分则当中再对原因自由行为理论进行明确,虽然有尽到法律提示性义务的需求,但多属于“叠床架屋”,只需要加深对于现有条文的理解即可完成,而没有在分则中重复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必要。
笔者认为,对于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基础,应当按照责任模式(责任修正理论)进行理解。同时,我国《刑法》第18条第4款已可以被认为是承认原因自由行为的基础,在此前提之下,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的内容,同样具备合理性。
注释:
①周光权.刑法总论(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②胡印富.论原因自由行为[J].法制与社会,2011(12).
③克劳斯·洛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一卷)[M].王世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④何庆仁.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困境与诠释[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2(2).
⑤黄风.意大利刑法典[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⑥冯军.德国刑法典[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⑦徐久生.瑞士联邦刑法典[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
⑧克劳斯·洛克辛.德国最高法院判例刑法总论[M].何庆仁,蔡桂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⑨钟连福.德国刑法中的原因自由行为理论[J].德国研究,2005.
⑩山口厚.刑法总论(第二版)[M].付立庆,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⑪陈兴良.规范刑法学(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⑫梁云宝.犯罪论视域下的“原因自由行为”理论之否定[J].法学,2012(1).
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网,(2010-02-10)[2018-01-20].http://www.court.gov.cn/shenpan-xiangqing-79.htm l
⑭方文军.醉驾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条件[N].人民法院报,2014-05-14(6).
⑮于改之.论外国刑法中的原因自由行为[J].山东大学学报,2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