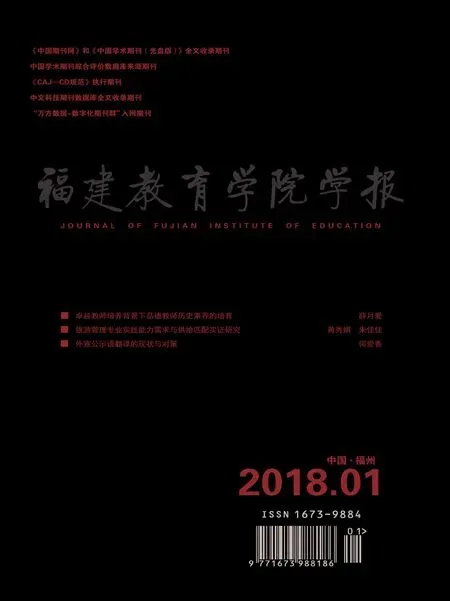浅析九十年代余华的归去来兮
——以《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为例
2018-04-03章立群
章立群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福建 福州 350108)
一、前言
余华是20世纪80年代先锋时期的代表作家,他在先锋创作高潮时期发表了《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往事与刑罚》《河边的错误》《世事如烟》《古典爱情》《此文献给少女杨柳》等一系列引人深思的作品。这些作品风格特征、叙事方式、创作思想等相差甚微,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共性:血腥、冷漠、暴力。
然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环境的逐渐确立,政治意识形态与商品意识形态的逐步融合,曾经风靡文坛的先锋派叙述革命、语言实验逐渐消退。以余华为代表的先锋小说家不得不思考:文学要走向何方?最终余华将方向转向了本土和现实,风格也回归温情、善良、包容。[1]《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可以说是余华90年代创作理论与实践的代表作,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回归:对现实的回归、对过去的回归、对美好的回归。进入新世纪后,余华又开始尝试改变,以《兄弟》为代表。但这次改变有些刻意,重形却轻质,当然这已经不在文章的撰述范畴之内了。
笔者尝试通过《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三部长篇小说,分别从语言运用、叙事方式以及人物情感三个角度分析90年代余华的归去来兮。
二、语言运用的回归
很多人都将《在细雨中呼喊》视为余华创作由先锋实验向朴素回归的一个转折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部长篇有效地限制了暴力性的叙事话语,将以往那种令人兴奋的血腥气,彼此杀戮的痛快感,赤裸裸的人性攻击欲剔除在外,而代之以温情和悲悯的意绪。[2]
如在《在细雨中呼喊》孙光林不再留恋的过去,语言平实有序,还有一丝丝淡淡的感伤:
于是我怀旧的目光逐渐抹杀了作为工厂的南门,石头砌成的河岸,以及我站立其上的水泥桥,我重又看到了南门的田野,长满青草的泥土河岸,脚下的水泥桥转换成了昔日的木板,我从木板的缝隙里看河水的流动。[3]
又如《许三观卖血记》:
坐在叔叔的屋顶上,许三观举自四望,天空红彤彤的越来越高,把远处的田野也映亮了,使庄稼变得像西红柿那样通红一片,还有横在那里的河流和爬过去的小路,那些树木,那些茅草和池塘,那些从屋顶歪歪曲曲升上去的炊烟,他们都红了。[4]
余华不遗余力地用沉甸甸的意象及精致的笔力为我们构筑了一个个艺术与生活交织的独特世界:看似真实,实则虚诞;看似虚诞,却又真实。其中更弥漫着对于农业文明的无限眷恋之情,对于土地的深沉至爱。[5]
再如《活着》,福贵儿子由于血型不幸与临盆的县长夫人相同,他竟是因为抽血过多而夭亡的。文章的语言极具生命张力,有一种竹子般的柔韧感:
我看着那条弯曲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洒满了盐。
月光照在那条儿子经常跑过的路,路好似他的伤口,月光满满,都像盐洒在他的伤口上。没有一字说悲伤,但细读下确实无尽的悲伤。这与之前先锋派恨不能用最夸张冷酷的文字完全不同。然而越是如此,文章反而显得更有内在的力量。
三、叙事方式的回归
叙事形式的回归,是指小说舍弃了一些写作上的技巧,转而用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来叙述故事,它应该是最直接的回归,也是最容易看出的变化。从余华这三部长篇可以看出,他逐渐舍弃了早期写作的一些技巧,如并置、错位、预述、时间的分裂等,不再过分迷恋形式,文风转向更写实。虽淡化了写作技巧,但却显现出更丰富的蕴含,让读者体验到更饱满的情感张力,感受到生存的挣扎、困惑与感动。对余华创作而言,这是一种诗意的回归。
《在细雨中呼喊》可以说是余华承前继后一部作品,残留着余华早期小说独有的叙事特点,阅读的感觉像是记忆被刻意断开一样,不连贯不顺畅。在小说里作者采用了一个循环往复式的开放空间结构,通过被世界冷落的孩子孙光林的眼睛来描绘生存的现实与荒凉。小说一开始叙述了一个让人意味深长的噩梦,梦里的“寂静无比的黑夜”“细雨飘扬”“雨中水滴”“幽静的道路”“哭泣般的呼喊声”“嘶哑的声音”等意象无不让人感觉一阵战栗和惊悚。这个梦就好像是小说的一个引子,预示着文章的主要内容就是一个人痛苦的呼喊与无人应答的恐惧,就像孙光林那躁动不安的心灵一样;这本书容易让人想到余华早期的作品:迷乱,不同的是,多了一些简朴和清晰。
《活着》虽然名为活着,其实是由一连串的死亡故事组成的,儿子为县长夫人输血而死,女儿难产而死,妻子得病而死,女婿出事故意外而死,外孙吃了太多黄豆而被撑死……这一系列的死亡都是非“常态”的,因此更让人觉得悲哀。小说里没有了太多的叙事技巧和刻意的雕琢,行文反而像流水一样自然顺畅,就像生老病死那样,正是这样的平常与自然更让人觉得那些死亡的触目惊心。
《许三观卖血记》写了一个小人物许三观一生不断卖血的故事,小说回归到了最初形态,即简单化线条化的讲述,注重的是文本的内容,而不是技巧的运用。这是余华所有小说里最没有展示叙事技巧的一部。正如作者所说的:“这本书其实是一首很长的民歌,它的节奏是回忆的速度,旋律温和地跳跃着,休止符被韵脚隐藏了起来,作者在这里虚构的只是两个人的历史,而试图唤起的是更多人的记忆。”[6]
四、人物情感的回归
这三部作品中都体现了余华对人在苦难中的挣扎与反抗的一种关怀与同情,他让这三个主人公都或多或少获得情感上的回归。
《在细雨中呼喊》中的孙光林一直在行走着。孙光林在自己还不谙世事的时候被人带离了故乡,又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回到故乡,五年中断的不仅是他对南门的记忆,对亲人对故乡的记忆,还有亲人和故土对他产生的一种隔阂与疏离感。回到五年后的故乡,他享受的不是被中断的亲情,而是长久的孤单和被冷落,这也使得他在村里似乎不再作为一个人而存在,反而像个影子一样飘忽,当他发现被故乡和亲人彻底遗忘的那一刻,竟然是如释重负的。
孙光林游走于城市与农村之间,关于爱关于回归的需求在他的记忆里渐渐消失掉,他被城市和农村同时抛弃。身份的尴尬,甚至说缺失让孙光林显得那样的灰色与黯淡,生命没有光彩,成为一个无意识的、永远在出走的形象。
《活着》小说中的主人福贵的出走与回归都是有意识的。从最开始逃离家乡,到小说结尾他用家人的名字叫着那头老黄牛,“今天有庆,二喜耕了一亩,家珍,凤霞耕了也有七、八分田,苦根还小都耕了半亩。你嘛,耕了多少我就不说了,说出来你会觉得我是要羞你。话还得说回来,你年纪大了,能耕这么些田也是尽心尽力了。”这让人觉得他与黄牛已经成为一家人,福贵的情感已经完全回归到那片土地上,让人感觉温暖。
这三部小说中,《许三观卖血记》底色最为明朗,只有在许三观身上,真正的乐观主义基调才得以确立,这意味着人对痛苦的超越。许三多一生在卖血的路上,他从容的享受着自己的生命旅程,去时满怀期盼,回时也是满怀喜悦与兴奋,那份对生命的透彻与平淡不似孙光林的无奈和凄凉,也不似福贵的悲伤与冷清,而是有一种生命的淡定在里面。再如,许三观一生最为耻辱的事是妻子被何小勇占有过,并生下一子。但在何小勇病危需要这孩子为亲爹喊魂时,许三观反而劝说儿子帮助仇人。在他最可能践踏他人的时候,他却选择了仁慈,因而正如作家王安忆评价的那样,“从一个普通人的境界跃升到了神的境界”,在更高层面上体现出存在的勇气。[7]
可以说,孙光林是无奈地接受命运的安排;福贵则是顺从地接受了命运对他所有不公平;到了许三观则是积极地面对了,每当遇到苦难,想的不是逃避,不是逆来顺受,而是怎么样去应付,让生命可以更好的延续下去。这三部长篇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与他的命运之间的关系,最初是被动的,然后是无奈的接受,最后是积极面对的。这是一种回归,对生的一种热切的渴望,对现实的一种有意识的改造,在他们身上流动着一些很美好的东西,让人感动。
五、关于回归的思考
早期的余华作为先锋派的代表人物活跃于文坛,从叙事革命、语言实验、生存状态三个层面进行颠覆创作。因为作品总是那样直接、那样血淋淋,余华被誉为“残酷的杀手”。但经过一段时间的体验后,特别是整体中国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时,它不得不引发思考:我们到底要怎样的思想大行其道?人们到底要从这些思想呈现(比如小说)中吸收怎样的营养?是残酷的、冷漠的、争夺的、绝望的;还是温情的、充满希望、有力量的、和谐的?
余华的归来,是这种意识形态选择、调整后的一个结果。余华本人曾说过,他的作品最先是“源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的关系”、是一个“愤怒和冷漠的作家”才有的作品;而之后归于理性的余华意识到“作家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