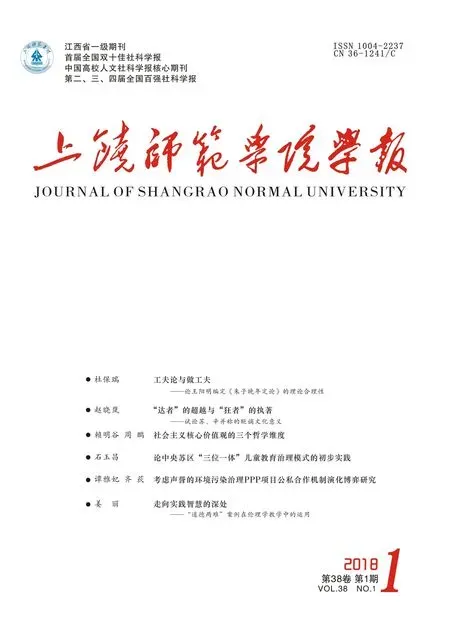姚名达“史理”说初探
2018-04-03
(上饶师范学院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江西分中心,江西 上饶 334001)
姚名达(1905-1942),字达人,江西兴国人,号称“中国目录学之父”。他极推崇“浙东史学”一派,发愿为程颐、刘宗周、黄宗羲、邵念鲁、朱筠、章学诚等学者做年谱,曾自叙:“著者籍隶赣南,于浙东之学,初无所知。其始觉也,盖自髫龄读《人谱杂记》与《王学渊源录》始。迨夫耽思史学,致力古书,气味相投,竟以《史学史》为其专门事业”[1]182。其“史学史”研究除了构成“事实”部分的诸年谱,作为“理论”部分的史学原理则受章学诚“史意”说之启发,并提出了建立“史理学”的设想。名达先生作为江西民国时期著名的学者、教授,以江西人而究心浙东史学,纯粹是出于对史学的见解与爱好,诚为“学者必有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2]606的示范。
一、“史理”说
“浙东史学”或“浙东学派”一名,较有影响力的提法应出自章学诚《浙东学术》一文,其中以黄宗羲、顾炎武分别为浙东、浙西之学,称:“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2]606。实斋之学生前影响力有限,民国时期因胡适等人的提倡而成为学术热点,其“浙东学术”的提法逐渐被大家认同并光大,大体以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三位学术史家作为浙东学派的中心人物。而由实斋上溯其学之源,逐渐延伸“浙东学术”的谱系,也是这一研究必然的结果之一。
胡适先生的《章实斋年谱》在学术界引起了热议,而姚名达先生的成名作便是补订、重写的《章实斋年谱》。之所以要重写,因为“胡适之做《章实斋年谱》,未尝道及其学之渊源,故似有不能彻底了解之处。名达之作《邵氏年谱》,盖有鉴于胡先生之失也”[1]68。进而追溯其源:“章实斋之史学,根柢于邵念鲁,而邵学,则又出于刘蕺山。刘则本王阳明致良知之教,发诚意慎独之说,而集宋明儒之大成者也。故欲穷章氏史学之渊源,非追求邵刘之哲学不为功。”[1]68考察学术背景,探源为学宗主,这是名达先生一贯重视的史学方法。
刘宗周、黄宗羲的传承是显见的,章学诚《浙东学术》中亦说“梨州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2]606,这是“浙东学派”较公认的几位大家。但实斋之学实出自邵念鲁,钱穆先生曾指教余英时先生说:“实斋常推邵念鲁《思复堂集》,弟治实斋之学,此集须翻检一读,可窥实斋学术之渊源。”[3]236这是名达先生说“欲穷章氏史学之渊源,非追求邵刘之哲学不为功”[1]68的原因。
民国是史学昌明的时代,传统学术中的很多问题曾以史学的面目而有新的表现。廖平《今古学考》中列一《今古学宗旨不同表》,其中提出经今古文的宗旨差别:“今是经学派,古是史学派”[4]。若经古文学派转变为史学派似是理所当然,但理(道)学传承亦有相应的史学派谱系,则不易理解。持这一观点的著名学人,以何炳松与姚名达为著称。何炳松先生《浙东学派溯源》一书中指出:
初辟浙东史学之蚕丛者,实以程颐为先导。程氏学说本以无妄与怀疑为主,此与史学之根本原理为相近。加以程氏教人多读古书,多识前言以往,并实行所知,此实由经入史之枢纽。传奇学者多为浙东人。故程氏虽非浙人,而浙学实渊源于程氏。……迨明代末年,浙东绍兴又有刘宗周其人者出,“左袒非朱,右袒非陆”,其学说一以慎独为宗,实远绍程氏之无妄,遂开浙东史学中兴之新局。故刘宗周在吾国史学上之地位实与程颐同为由经入史之开山。其门人黄宗羲承其衣钵而加以发挥,遂蔚成清代宁波万斯同全祖望及绍兴绍廷采章学诚等之两大史学系;前者有学术史之创作,后者有新通史之主张,其态度之谨严与立论之精当,方之现代西洋新史学家之识解,实足竟爽。此为浙东史学发展之第二个时期。[5]307-308
“远绍程氏”,就是何先生的结论。地域性学派谱系的复杂性,导致类似的结论往往很难解释清楚。于是对类似观点就有这样的疑问:“但究竞是如何‘近承’,又如何‘远绍’的?比较而言,‘远绍’的学脉梳理和贯通当比‘近承’更难。……对浙东学派而言,除了应该充分关注这一‘近承’关系之外,还有‘远绍’的问题,这是一种超越直接师承关系、出于同代甚至不同时代之问的学统认同,是一种‘虚拟’的传承关系,需要细加辨析。”[6]程颐与浙东学派之间的关系不易理解,何炳松先生的意见核心在于“由经入史”的命题,程颐与刘宗周在其看来都是引导“由经入史”这一学术理路转向的代表人物。于是何先生以程颐为儒家史学之代表,而以朱熹为道家儒学化,以陆、王为禅宗儒学化:
吾国学术思想至北宋末造经一番融贯之后,大起变化。儒释道三家思想,至此皆面目为之一新,各成为极有条理之派别。释家思想经儒家之陶冶,成为陆王一派之心学;道家思想经儒家之陶冶,成为朱子一派之道学;而儒家本身则因程颐主张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之故,蔚成浙东之史学。故吾国学术至南宋而后成三大宗门,吾国史学亦至南宋而后始独树一帜,南宋之世,实为吾国文化史上最灿烂之时期也。[5]307
以程颐开史学派,以程、朱为两派,这似乎不合于一般的认识,因为程、朱尊经抑史的立场是很明显的。以钱钟书先生评阳明“五经皆史”的观点为例:“阳明‘五经皆史’之说,殆有所承,而与程、朱之论,则如炭投冰。……盖以经与史界判鸿沟也。”[7]643所以如何理解何先生“远绍程氏”之说,涉及不同学者们对“史”“史学”“史料”等概念之认识的根本不同。
何先生的上述观点被姚名达先生引用在其《刘宗周年谱·序》中,并称赞道:
自来谈浙东史学,未有若柏丞先生之深切著明者也。其所给予宗周先生之位置,尤确定而不可易。观乎宗周先生祀尹焞于证人社,目为程颐之正传,拳拳服膺,备致推崇,可以知其思想渊源之所自矣。[1]182
名达先生以刘宗周祀程门高足尹焞为证,说蕺山之学为程颐正传,支持了何先生的观点。然何、姚二先生观点的根本,是“其思想渊源之所自”,即名达先生所说的“史理”的一贯。具体的师承,则实斋之学可关联邵念鲁、朱筠,对程颐、刘宗周学说的关联,只能是依于“史理”的“远绍”了。为了辩清这一谱系,名达先生发奋做了程颐、刘宗周、黄宗羲、邵念鲁、朱筠、章学诚等学者的年谱,但其实际的研究顺序恰是从实斋倒叙的,所以是一“史理”的追溯。
姚名达先生所撰的一系列年谱(黄宗羲谱毁于战乱),构成了其史学史研究中的“事实”部分。按其史学史研究分三方面,另外尚有“理论”部分与“著作”部分。其“理论”部分的大纲写着“研究史的起源及史学的大势”“研究专家和各家的关系”[1]173,这一部分阐明了名达先生基本的史学观和研究立场。又创造了“史理”的概念说明其纲领在此:“特提史理一词以与地理对立,事属首创”,因为“欲提倡史事原理的研究,必须另定一个学科名词。”[1]477
名达先生所构想的史学史,应该是“事实”“理论”与“著作”三部分诸多系列著作的统一。这一宏大设想是效法他所崇拜的章学诚先生的“通义”之意,其在《〈章实斋遗书〉叙目》中指出:
所谓《文史通义》者,即文史的普通意义,亦即史意,是乃实斋性命之文所尽萃,可概校雠而不可相与对立者也。……观实斋四十二岁以后,著书稿册,有《癸卯通义草》,《庚戌钞存通义》诸名,其各篇皆隶文史:而一切单称《通义》者,又皆指《文史》而言:则《文史通义》实为实斋著书唯一之名,益可知也。[1]111
实斋本意,《文史通义》实为其著书之总名:举凡平日所为文章,悉加甄别熔铸,编排定著为一首尾完具篇章清晰之大著作。[1]113
按名达先生的考证,实斋“文史通义”之名实则指其全部著作而言,但可惜未能完成其体系。撰写其史学史系列著作亦即名达先生的夙愿,但身逢乱世赍志而没,这一构想终未能展开其全景。
“事实”“理论”与“著作”三部分或内容有异,但“理论”为贯穿全部史学史之“义”,是名达先生得之实斋的“史义”。其考察学术史的推本溯源之工作,也是以“意指”作为贯穿,体现了实斋“学者必有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2]606的精神:
实斋之于学术也,溯其源,能知其浑然本一;析其流,能知其厘然有异:所谓“为学之要,贵乎知类”,实斋实已握捉要领,擒纵自如。故其论编次文集也,不可拘于文体之形貌而贵能求作者之意指。[1]116
古人论学术史,大抵是以汉宋之分或今古文之分来看待,如《四库提要》之论:“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8]民国学人受西学冲击,有世界学术的视野与观念,不局限于汉宋今古之间的取舍,如名达先生自命是以“科学的”史学观念来整体看待全部古代学术。这一整体的视野实是实斋“通义”之意的演变,所以名达先生对实斋推崇备至,曾反复称赞:“实斋于是力究纪传之史,而辨析体例,遂若天授神诣,竟成绝业。”[1]82。
因为受近代的“科学的”观念影响,以实斋的“通义”精神再加嬗变,于是有名达先生“史理”说的提出。传统学术以经学为主,大约在名达先生看来,自实斋提出“通义”的精神之前,“理”的解释总是被经学主导的。名达先生热烈拥护民国以来学术分科的制度,在“史理”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史理学”,认为“如有原理,便可仿物理、心理等科之例,名此科学为史理学”[1]481,并指出:
只有史事才是史理学研究的对象。只有史事原理才是史理学研究的目标。只有研究出史事发展的原理来此可促进者学科成为科学。史观、史法、史料、史书,都不是史理学的用人或用具,都不足以代表史理学。执一不化的,所谓历史哲学与只知方法而不知原理的所谓历史科学,皆不是史理学。[1]481
梁启超称赞章学诚为“历史哲学家”[9]200,然而“历史哲学”一词虽然为姚名达所使用,却并不完全认同,他认为:“所以不采用历史哲学这名词,一则以这名词的含义不明显,易流于反科学的迷途;二则以这方面的哲学家还没有解答这问题的力量,他们自身意见尚未一致。”[1]478名达先生是以爱国气节闻名的,在学术上强调“科学”的精神,无疑也是受西学刺激后而欲奋发图强的回应。
二、史理与史料的辨析
姚名达先生“史理”之说的提出,是以民国时候的史料学作为背景。民国时史学大家辈出,然而诸位前贤对于“史学”的理解却往往不同,甚至大相径庭。以章学诚研究为例,梁启超先生称赞章学诚为“清代唯一之史学大师”[9]466,而挖掘出这一学术热点的胡适先生却不无惋惜地指出:“实斋终是一个‘文史’家,而非‘史’家”[10]78。钱穆先生更直白地说:“实斋提倡史学,实于史学无深入,无多贡献可言。”[3]236章实斋的学说在其生前影响有限,伴随着民国史学的兴盛而逐渐显示出其独特的价值来。关于实斋是否能视为一“史家”,其著作究竟有怎样的史学价值,不同的观点反映出民国诸位史学大家们关于“史学”的认识与立场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
姚名达先生因胡适先生的《章实斋年谱》而受到学术启发,又跟随梁启超先生做章实斋研究,最终反对胡适先生的意见而另做新谱。正是在批评胡先生“史料”之说过程中,名达先生才明确了其“史理”的观念。名达先生“史理”之说因为受胡适先生影响太深,时时有 “史料”的影子。
何炳松先生称程颐之学为“由经入史”,至实斋则以“六经皆史”作为其学术的核心命题。胡适先生认为这一命题“其实先生的本意只是说‘一切著作,都是史料’。如此说法,便不难懂得了。先生的主张以为六经皆先王的政典;因为是政典,故皆有史料的价值”[10]114-115。然而实斋在历史考据方面实无多少成果,这是胡适先生认为实斋“非史家”、钱穆先生认为实斋“无多贡献”的原因。于是“六经皆史”就仅是一口号,恰与民国时候整理国故的运动相适宜。
但以“史料”解释“六经皆史”之“史”,这恐非实斋本意。何炳松先生指出:“他们所赏识的是《文史通义》中的事和文,我们所赏识的却是义。”[10]6又:“我以为章氏的供献,并不在事,更不在文,实在在义。这个义就是他对于史学的卓见。”[10]7此“义”或“意”,才是实斋“六经皆史”的感慨所由发,他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11]何炳松先生此说正是与姚名达先生相与论学的重要话题,名达先生便指出:
以愚观之,胡先生于章先生所用学语,若“史”“史学”“著作”等字,殆未彻底了解。章先生书,“史”与“史学”,意义截然不同。史为纪事之书,对象也。以学著为史,是为史学,造诣也,乌可混为一乎?至于目著作为史料,尤与章先生本意剌谬。章先生书,著作二字之价值极高,非同凡物也。……是本乎学问乃为著作,不本乎学问者非著作也。[1]63
在实斋的话语中,“著作”是很重要的概念,涵义完全不同于“史料”。名达先生认为其“著作”之意必须“本乎学问”,非一般史料所能当,他以为“本乎学问”,即“史义”之学问,认为“必先有学而后有史”“章实斋之言史学之意义也,盖本其言史与学之意义而言之。故曰:‘嗟乎!道之不明久矣。六经皆史也。’……是实斋意中,固以为必先有学而后有史,始可谓之史学矣”[1]102,又:“史之要素有三:实斋曰:‘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1]103
辩胡适先生为代表的“史料”说,申明实斋的“史义”说,这是名达先生所以提出“史理”的重要原因。名达先生多次在书信中感念过胡适先生对自己的奖掖提携之恩,但其学术立场很坚定,认为必须为实斋重新作谱:“适之先生自有他的见解,我不能阻止他参加己见,但我已见得有好几处,适之先生的解释或批评失了章实斋的本意。”[1]120又:“章实斋‘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一语,名达已有殊异之解释,仍目胡先生之解释为误,将诠入拙著《章实斋之史学》中,今兹不欲露其璞。”[1]69
考据训诂、搜罗材料,这不是“史学”,此实斋以“史学”补救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术所提出的意见。何、姚两先生以古论今,则针对民国的“史料”之学而言。名达先生指出:
整辑排比,参互搜讨,皆非史学。以博稽文笔故实议论体裁言史,皆不得为史学。则真正之史学,必有近乎斯数者。此一义也;至唐而史学绝,则自唐以前,我国固自有其真正之史……真正之史学,非能著几部之史而已。必有精深之造诣,学问已卓然成家,然后出其心得,著述成书,庶几或有当也。[1]97-98
正是基于“史义”的角度,名达先生认为胡适先生不知“史学”之义,所以失去了实斋的本意:
若以今语译之,则实斋所谓比类之书,正吾人所谓史料。史所不离乎史料,而史料终不可以尸史学之称。而胡适之先生著实斋年谱,释实斋“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一语,为“一切著作,都是史料。”则与史学史料之分际,尚未能深察。读古人书,心知其意,固若是其易易也耶?[1]105
“史料终不可以尸史学之称”,这是名达先生最终立志作“史学史”巨著的重要动机。他曾称赞过何炳松先生的著作为“深得章实斋之遗意”:“大著《五代时之文化》及其附论,名达与任公先生同其赞仰。盖以治史为作史,深得章实斋之遗意,虽资料集纂非难,而义意贯穿不易,非具史识而知史义者不能,而先生倡创之功为甚伟也。”[1]69在名达先生的叙述中,他认为梁启超、何炳松与自己为倡导“史义”说的一派。
以材料为“史”观念民国以来深入人心,这是很多学者解释“六经皆史”的基本前提。比如钱钟书先生亦以为“实斋仅识经义之为政典”:
典章制度,可本以见一时之政事;六经义理,九流道术,徵文考献,亦足窥一时之风气。道心之微,而历代人心之危著焉。……阳明仅知经之可以示法,实斋仅识经义之为政典,龚定庵《古史钩沉论》仅道诸子之出于史,概不知若经若子若集皆精神之蜕迹,心理之徵存,综一代典,莫非史者,岂特六经而已哉。[7]645
钱先生将经史关系置换为心迹关系,进一步指出所有文献不过皆“精神之蜕迹,心理之徵存”,是以“史料”与“史义”可以对立而言。名达先生所倡“史学”概念,便是要在其中预含“史义”,以“史义”为“史学”的先决。两种意见强调的侧重点不同,是由章学诚研究而显出民国史家的不同流派的又一例证。
三、史的意义
史家对“史”的认识各异,固然可以概念的梳理探其端倪,但根本在于人生的立场不同。实斋一生感受到戴东原的压力,所以有“六经皆史”的提法,钱穆先生指出:“实斋《文史通义》唱‘六经皆史’之说,盖所以救当时经学家以训诂考核求道之流弊”[12]。名达先生再三致意实斋的“史义”之说,并进而提出“科学”的“史理”之说,亦饱含其经世之意。所以名达先生指出:
惟有历史才能供给人类以最渊博的知识,惟有历史才能保存人类所曾创造的事迹。玄妙的哲学也许只能供少数有闲阶级的玩味,雕垛的文学也许只能供少数有闲阶级的吟咏,唯有历史是和报纸一样能够影响到人生的本身。它的真伪良窳直接牵连到人生的善恶,国家的安危,社会的治乱。[1]219
正如名达先生对“历史”一词有特别的见解,其使用“哲学”“科学”等概念亦呈现时代、个人理解所造成的殊相——以今天看,其“史理”的学说恰近似哲学。名达先生将“历史”与报纸的作用并称,是因为他一贯认为所有的今时俱为“历史”,我们似可以换言之:所谓的“历史”也不过只是今时。这是名达先生所辩的古今关系:
无古无今,学之对象,乃为人生中之种种事物。学之目的,乃在于人生之种种自然法之中,思其所以然而求其是。所谓求道也。人生只有过去今古绝无分界。知时博古,初非截然冰炭。且惟能知时者,始可与言博古。[1]102
所以治历史只在求道,求道只在解决人生的问题,这是名达先生推崇实斋“史义”的心理动机。所以名达先生述及自身事业时,常常从少年时读《纲鉴易知录》的启蒙开始,认为历史赋予其人生的意义,所以为妇女解放、民族解放热血奔走时以此自勉。“历史”的全部意义在名达先生便如此:
史的境界,弥满在人生,而史的意义,钟郁在有意义的人生……没有意义的人生,便不合史的意义。……史家的责任:要在全部的人,挑出有意义的人生,用文字纪载下来,留给当时此地以后的人看,使他们知道:人生究竟是怎么样?人生为什么发展到这样?能够保存有意义的人生,能够使人知道有意义的人生,这便是史家的成功,这便是史家唯一的目的。[1]73
从学理上可以说名达先生的经世精神得之实斋的求道精神,但也是民族危亡的客观现实所致。人生的气节与选择,在20世纪30、40年代是非常现实、切己的问题。这也导致了名达先生以人生境界的高低来理解学术问题,如章学诚与戴震的公案,名达先生也有一番见解:
实斋目学为求道之资,而非人人可得而自私。探求义理,考订名数,闲习文章,皆求学之一事。途辙不同,而同归于道则一,不应妄生轩轾也。……实斋论学,最重专精,非涉文史,少加评议。……实斋史家,最重史德。[1]87
名达先生曾回忆自己“起了一个信念,以为:研究一个人的学术,必须了解他所以成学的原因”[1]159。实斋有《史德》一篇,名达先生以引申为戴、章二人高下的寓意在其中。后来有余英时先生《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其中以实斋《朱陆》篇寓指戴、章,皆知人论世之言。不论名达先生对于实斋、东原的评价是否全部中肯,此由“史德”而上升至人生境界的意见,是其一生内化、践行的根本观点。
于是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则程颐之“无妄”、蕺山之“慎独”可以作为浙东史学谱系的“远绍”之说,根本原因在此。名达先生指出:
当明之季叶,王学末流,入于狂禅。理障,殆不可救。东林诸子,矫之以气节,已宗朱子而掊阳明。刘蕺山取长弃短,集宋明儒之大成,本良知而发慎独。入清而有黄梨州、邵念鲁相为羽翼。[1]91
学术家的学说,不仅是学理使然,社会环境的剧变带来的刺激更加直接。其作《刘宗周年谱》正是以明末的“天崩地解”比附民国时期的民族危亡,以蕺山的气节砥砺自己的人生境界:
时代背景,学术潮流,无往而不牵涉学者之思想;先生思想之成立,所感受与时事尤多;旧谱有昧于此,所纪多略;此宜用新史学之眼光,作科学的探究与纪载者,……先生之学,又实有其不朽者在,于今日时势,适如切症之药石,著者不敏,窃欲化专门为普及,变艰深为浅易,治文集为传记,使先生之学得广播于天下,而天下仰其赐,则著者之心愿偿矣。[1]179-180
黄宗羲曾说“遗民者,天地之元气也”[13],可知“元气”不只是一理学概念。名达先生的“史理”之说,其意义亦在此经世的一面。名达先生的兴趣在于研究历史,但短暂人生的后半期始终为实业奔走,办刊物、设基金,为妇女、学生的权益奋斗。
[1] 姚名达.姚名达文存[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2.
[2]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4.
[3] 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4] 廖平.廖平选集[M].成都:巴蜀书社,1998:44.
[5] 何炳松.何炳松文集:第四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6] 梅新林,俞樟华.浙东学派的学术谱系建构及其路径选择[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10-26(7).
[7] 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8]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65:1.
[9] 梁启超.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10] 胡适.胡适文集:7[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外编卷第十六[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552.
[12]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30.
[13]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