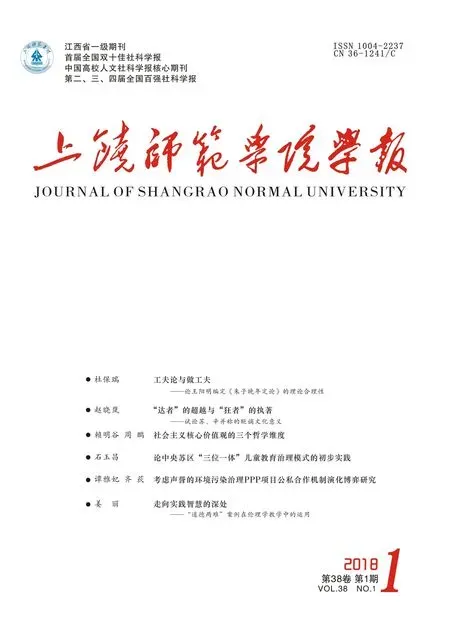从私人性到公共性:西方语言观流变的哲学分析
2018-04-03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上个世纪初的西方哲学发展中,语言问题日益凸显成一个重大主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就是有关私人语言是否存在的分歧。一般的观点认为,洛克肯定私人语言说,维特根斯坦则断然否定有私人语言存在的可能,而这两种语言观几乎代表了在语言问题上古典和现代最为显著的差异。在是或否这种二元断定中,二人之间理论上的深刻的连续性甚至是相似性往往被深深地遮蔽,我们不能否认从洛克到维特根斯坦300年的时间里,语言学及语言哲学的发展,但是把两者用二元界定豁然割裂开来,无益于问题的澄清。本文认为,语言观的历史不是一个个色调独立的补丁,历史及其承载的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前后相继的内在关联,它们与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相关,语言从私人性到公共性的流变就蕴含着哲学与自身所处时代的历史性关联。
一、关于洛克的私人语言观
生活在17世纪的洛克显然没有现代后来者们对语言之地位的自觉性,在写作他的《人类理解论》之初,洛克甚至没有觉得在考虑人类理解的重大问题时,关注语言问题有什么特别的需要。在该书第二卷末他写道:“我们既然叙述过我们观念底原始的种类和范围……,按照我原定的计划,我应该立即来指示出,理解怎样应用这些材料,……我亦原想照这样作,不过在我较进一步以后,我又看到,在我们的观念和文字之间,实在有一层密切的联系,而且在我们底抽象观念和概括的名词之间,还更有一种恒长的关系,因此我们如果不先来考察语言的本质、功用和意义,则我们便不能明白地清晰地谈论我们底知识。”[1]382这段自述表明,语言之重要性不仅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普遍的理论关注(同时期鲜有专论语言的著作),而且语言问题的重要性在洛克思考写作该书之前也并没有被特别关注。随着对人类认识能力和知识形式的逐步深入考察,洛克才意识到语言问题的重要性并于那个时代率先展开研究,因此可以这样说,20世纪发生的语言学转向是对这一发现的响应和继续,只不过其隆重程度大大超越了洛克的初见。当然,既然是初见,也可以说洛克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对语言的认识还远谈不上深刻,同时洛克的语言研究也只是另一个重大主题考察中的副产品。洛克的语言观严格地奠基于他的认识论之中,与其说洛克是通过认识论考察才发现语言问题,毋宁说他是通过语言的说明来进一步阐述他的认识论,语言问题从没有成为洛克讨论的中心,所以正确地理解洛克的语言观必须回到他的认识论基地上。
洛克所理解的语言并不是后来者主张的那样具有一种超越个人的先验的本体性存在,对他来说语言只是人类认识的一个工具,它之存在的意义是外化观念,或者说作为观念的外在表达以给人们提供在日常生活中交流观念所得的工具,观念是语言的本质,语言是附属于观念的,它的构成和联系都依赖于观念的形成方式和连接方式。
洛克的观念论受当时机械论和原子论的深刻影响。就像一般的物质一样有它的基本单位、结合方式,比如原子。语言同样可以分解到它的基本单位,人们使用语言也就只是使用这些组成部分在进行不同的化合作用而已,而洛克主张语言的基本单位就是词汇,人们谴词造句,总是谴词在前,语言的使用过程就是把词汇调动起来。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讨论语言的专章第三卷的标题是“on word”,而不是“on language”。词汇来自观念,它只是通过对观念的命名而附着在观念上,观念才是词汇的意义和本质,理解词汇的一切努力都必须回到观念上来,有多少观念就有多少种词汇。
洛克认为,作为人类理解的真正对象观念,它来自于人们的感觉,不同的感觉产生不同的观念,人类获得观念的渠道有三种:外感觉产生诸如光、热、平之类的简单观念;内感觉产生愤怒、忧虑、高兴之类的简单观念;而心灵黑箱的加工能力在把这些最基本的简单观念加工成房子、电影、信念之类的复杂观念。从起点上说,这些内外感觉和思维过程都是私人性的,那些感觉敏锐的人分辨出不同的内外感觉,那些心灵聪慧的人加工出不同的复杂观念,他们率先通过词汇来给以命名。所以顺理成章,那些附属于观念的语言从源头上就是私人性的。它总是由那些心灵和感觉明锐的“私人”来推动、发展,然后被众人接受并惠及众人。
虽然语言起于私人,但毕竟涉及众人,所以洛克并没有全然忽略语言的公共性,尽管他把这种公共性仅限于工具性。对洛克而言,语言是人类理解能力的副产品,语言的功能只有两个,一是记录:对理解到的观念的固化;二是交流:在不同的人们之间交换、传递观念上的新发现。相对于后者,前者更加重要,它直接参与了人类的理解过程并使之简化,而后者却并非必然需要,一个聪明人并不必然需要与他人交流一切发现,理解首先发生在个人的心灵之中,以个人为本位,语言也必定首先专属于个人。在此,洛克鲜明地展现了他的个体主义的唯名论的本体论和心理主义的认识论特征。真正的理解活动只发生在个人之中,心灵在理解活动中占据中心地位,至于为什么会有人类,人类为什么会有心灵的理解能力,洛克并没特别说明,但这些都有不言而喻的定论,那就是神恩,就像世界中有老虎,老虎有尖牙厉爪。
洛克说道:“物种的本质是由人心所形成的,——我们纵然假设人们如果认真来探究各个实体的实在本质,就会真把它发现出来,可是我们仍然不能合理地假设所谓分类命名不是根据于明显的现象,而是根据于实在的内在组织,……因为在一切国家中,各种语言是在各种科学以前久已确立的。……在各民族间,那些较为概括的名词都是由无知的文盲产生的。”[1]437对理解而言,观念是真正的对象且持续发展,而对交流而言,语言必不可少且相对稳定。语言(词汇)和观念之间并不是准确的对应关系,在观念的发展中,聪明人之所以要用那些文盲产生的词汇也只是交流的方便而已,他完全可以重新命名。可见,词汇只在个体的自我意识中被理解和生产,其私人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在洛克看来,一切语词包括语言本身的产生都可以追溯到某个私人性的个体。洛克所继承的唯名论传统只承认这种个体的真实性而否定类的实在性,因此语言只在私人的理解活动中才具有真实性。而他所开启的心理主义语言学影响持久而广泛,一直延续到索绪尔。
二、索绪尔的新语言观
索绪尔是西方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在索绪尔之前,欧洲流行的新语法学派受到发端于洛克的心理主义语言学的影响,侧重于从个人言语的各种事实出发研究语言,表现为以词汇和言语事实为重心的原子主义、实证主义[2],难免琐碎零散。在德国“格式塔思想(gestalteinheit)”的影响下,索绪尔试图开辟一条不同于新语法学派的语言学研究道路,把语言学研究建立在一种更系统、更完整的理论格式塔之上,使之科学化、系统化。语言研究的系统性统一性问题是索绪尔开始其语言学研究的初衷,索绪尔为自己的语言学研究设定了三个方面的任务:(a)整理各语系的历史,尽可能重建每个语系的母语;(b)寻求在一切语言中永恒地普遍地起作用的力量,整理出能够概括一切历史特殊现象的一般规律;(c)确定语言学自己的界限和定义[3]26。三方面共同的原则就是统一性,在索绪尔看来,寻找普遍、一般的语言规律的可能性只能寄托在语言学的系统性之中,这也是语言学科学化的唯一可能的方向。
为建立这种统一性,索绪尔区别了语言和言语,区别了共时态语言和历时态语言,从文字、语音、地理、历史等方面为语言学划定了清晰的范围、独立的问题域,这些成就为语言作为“科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促进了对语言公共性的认知。语言现象为人类所共有,突破个人观念的自我封闭的壳体,寻找一般语言学得以可能的条件无论如何是对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促进。但这种努力显然表现出与洛克迥然不同的旨趣和方向,它可能源于欧陆的唯实论传统和英伦的唯名论传统之间的差异。
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瑞士出生的索绪尔深受德国思想传统的影响,这种传统典型地体现在康德的这句话中:“系统的统一性就是使普通的知识首次成为科学、亦即使知识的一个单纯聚集成为一个系统的东西。”[4]这种体系化偏好也体现在黑格尔统一西方哲学史的努力之中,虽然语言从地理和历史方面表现为民族性、历时态性,但是同其他欧陆哲学家一样,索绪尔坚信其背后仍然有着普遍性、一般性、永恒性的东西,如科林伍德对历史哲学的论断那样:哲学“对伏尔泰,意味着独立的和批判的思想;对黑格尔,意味着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对19世纪的实证主义,意味着发现统一的规律”[5]。欧陆哲学中体系性偏好非常普遍,欧洲大陆也是盛产体系哲学家的地方,像沃尔夫、康德、黑格尔,更早的托马斯·阿奎那等等,其背后蕴含着对哲学及各类学科(包括语言学在内)真理化、科学化的预设的形而上学原则。黑格尔骄傲地把这个原则当做西方文化之优越于其他文化类型的最突出的特点,这个特点的确贯穿在西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知识传统之中。通过各个学科的西方学者身体力行,这一倾向以其浓墨重彩的理性主义的自我标榜而几乎成为西方文化的标准符号。
系统性和科学化的要求促使索绪尔必须裁剪掉私人语言说的纷乱无序,为此索绪尔分别了语言和言语,而把洛克的基于私人活动的语言归入后者,把语言学定义为纯粹的公共性的普遍学科。这样就像动物分类学方法一样,私人语言活动的多样、凌乱也就不再影响语言学的稳定普遍的科学意义,偶有不同也只是特例而已。这一区分终结了所有私人语言观,因为索绪尔在“语言”这个概念中就包含了公共性、普遍性的预设。与洛克不同,索绪尔把语言只看做统一的整体相关的符号系统,“就所指和能指而言,语言不可能有先于语言系统而存在的观念和声音”[3]167,他主张语言的一切历时态的变化都以语言符号之间的共时态的整体性联系为前提。符号先于观念和声音,符号的整体性也就先于个人的语言活动。索绪尔的语言观深刻地影响了维特根斯坦。
三、前后期维特根斯坦与私人语言说
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把20世纪西方语言学研究转向推向一个节点,成为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一主张也远远突破了语言学架构,弥漫到哲学研究的所有领域。
他说道:“‘语言游戏’一词的用意在于突出下列这个事实:即语言的述说乃是一种活动,或是一种生活形式的一个部分。”[6]17这是个语言学生活化的宣言。他进一步说道:“动物们不说话——它们只是不说话而已。更恰当地说,它们不使用语言——如果我们把最原始的语言形式排除在外,(语言)同走路、吃喝、游玩一样是我们自然史的一部分。”[6]19语言作为自然史,这就是维特根斯坦的语言研究的原则,这意味着像一切自然现象一样,语言研究要从语言活动的经验事实出发,维特根斯坦后期著作中充斥着这种语言事实的考证。
维特根斯坦的自然史化的语言观表现出对洛克基于内在心理事实的经验主义语言观的呼应和继承,但是并不像洛克那样主张语词起于命名,在他看来,我们通常叫做名词的那些词汇在语言活动中完全突破名词的传统划分,它们与使用的环境和使用者的不同结合将产生完全不同的意义效果,这种语用学的态度完全颠覆了传统语法学关于名词的定义,也表明了他与洛克之间的分歧。他保留了用实指的方式定义一个事物的可能性,这种语词的产生过程接近于洛克的命名活动,但这不能决定这个“被命名”(或被实指)的语词被置于何处、何用,语言游戏的活动性特征决定了任何语词的性质、意义都因其参与游戏的方式、位置、目的等等而产生变化,因此,对于任何语词来说,使用者的观念在先就被语言活动中的应用在先所取代了。维特根斯坦这个主张与洛克的分歧是根本性的,因为在语言现象层面上,他排除了洛克所确信的那种自我意识独立完成的观念及其命名活动,语词的使用总是对接受这个使用的另一个主体来进行,重要的是使用、沟通能否完成,而并不是语词与观念是否准确对号。甚至包括痛感这种极其私人性的感觉观念其表达也必定是在公共语言空间中进行,要成为有意义的、别人能接收的表达,就必定经由某个已经为人所知的公共语词。
继而对于私人语言,维特根斯坦说道:“让我们回忆一下,在一个人的行为中,有某种标准可以判别他不懂得某个词,该词对他来说一无所指,也一无所用。还有一种标准可判别他自以为懂,给这个词附上某种意义,但不是正确的意义。最后,还有判别他正确理解这个词的标准。在第二种情况中,我们可以说是一种主观的理解。我们可以讲其他任何人都不懂而我‘似乎懂’的声音称为一种‘私人语言’。”[6]141-142这段表述设想了一种“私人语言”可能的情形,这种情形会实际发生,只是这种“私人语言”是似是而非的语言,是语言的另类或畸变,是人们使用语言的不当情形。在洛克看来这种文字的滥用由文字的缺陷所致,是不可避免的,它可以通过观念的理解得到纠正。而维特根斯坦虽然没有说明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误用,以及这种误用的后果有哪些,但是他认为语词的“正确”使用取决于语言游戏中的长期训练,这甚至无关理解。显然在这个问题上维特根斯坦留下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这种训练可以不经由使用者的理解,语言如何作为人类现象得以可能?也许在维特根斯坦看来狮子通过训练可以按指令行事,也是对一种符号系统的掌握,只是不同于人类的语言而已。但是显然符号使用者的理性活动对训练的结果是有根本影响的。这是人类语言现象的根本特征,所以撤除这一根基讨论语言必定是有缺陷的。语用语言学或许只是马克思这段话的一个不完美的注脚:“语言是一种实践,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7]34
在排除语言私人性上后期维特根斯坦与索绪尔相近,但讨论语言的方法并不相同,因为他所反对的不仅仅是私人语言,而且也包括索绪尔所依赖的系统性的理性主义原则。早期维特根斯坦也坚信存在一个逻辑的公共性空间,“在逻辑空间中的诸事实就是世界”,而对于这一世界的存在,逻辑是必备的要件,并且为一切发生未发生的事实所共有,“每个事物都像是在一个可能事态的空间里。我们可以设想这个空间是空的,但是我不能设想没有这空间的事物”[8]。这种逻辑的理性主义“空间” 是他在早期同索绪尔一起继承于康德的共有的信念,后期维特根斯坦多少受到意向性学说的影响,对语言的阐述与哲学的态度交织在一起,并越来越倾向于在语言研究中来解决哲学问题。后期维特根斯坦带来的不是一个索绪尔式的科学的语言学,但给哲学带来了新的视角。某种意义上说,索绪尔是透过哲学看语言,而维特根斯坦却是透过语言看哲学,二者在语言观上交叉多于分歧,而在哲学上则反之。
四、语言私人性和公共性的再讨论
国内著述关于私人语言的讨论多集中于维特根斯坦,也多偏重于语言私人性是否存在的论证问题,这种讨论不无意义,但是,笔者觉得维特根斯坦通过语言私人性的讨论并不只是要提出这个结论,而是要通过这个观点透视更广泛的哲学空间。单单就语言公共性来说,17世纪的洛克也并没有忽视。洛克说道:“上帝既然意在使人成为社会的动物……还供给了人以语言,以为组织社会的最大工具,公共纽带。”语言为人类特有,并且是人类连接的纽带,虽然洛克认为“任何人都有一种不可侵犯的自由权利,任意使各个字眼来表示自己心中的观念”[1]383-384,但同时也强调要使用人们约定的“惯常习用的字眼”避免语言的误用。如果我们把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训练”同洛克的约定的“惯常习用”替换一下,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妥。
当然两人的区别依然是鲜明的。洛克认为语言有“自然的和后加的缺点”[1]498,需要哲学的改进;维特根斯坦则把语言活动的现象当做“我们的自然史”来考察,并不认为那些误用是语言现象不可容忍的缺陷,而哲学的参与非但于事无补,相反会增加语言的困难。他认为,“哲学不应以任何方式干涉语言的实际使用;它最终只能是对语言的实际使用进行描述。因为他也不可能给语言的实际使用提供任何基础”[6]75,而“哲学家的工作就在于为一个特定的目的搜集提示物”[6]76。值得思考的是维特根斯坦为哲学设定了什么“特定的目的”?以及搜集到哪些“提示物”,通过这些提示物,我们能得出些什么?维特根斯坦勾勒的哲学又是什么?在他看来,哲学是一个问题或病症,“当语言休假时,哲学问题就产生了”[6]29。语言疗救哲学,而不是哲学疗救语言。
相反,洛克对哲学是抱有信念的。他说:“用文字来传达思想,则他们有两种用法。第一是通俗的,第二是哲学的。”“所谓哲学的用法就是要用它们来传达事物底精确观念,并且用普遍的命题来表示确定而分明的真理,以使人心在追求真理时,有所依着,有所满足。”[1]462-463洛克心目中哲学的思想应当有两个特点,一是精确性,二是普遍性。这两个特点在索绪尔的语言学中也是得到贯彻的,可见虽然语言观上索绪尔不同于洛克,但在哲学的信念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寻求精确的具有普遍性的真理。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则大相径庭,他说:“哲学问题具有的形式是:‘我不知道出路何在。’”,这意味着哲学只是用来提出问题,而问题的解答则是一个悬疑。哲学并不回答关于本质的问题:“本质对我们是隐藏着的”[6]65,他把传统哲学习用的“本质”置换为“家族相似”;他否认精确和科学的定义的可能性:科学定义具有摇摆性,“今天被当做现象A的某种经验上的伴生现象,明天就会被用来定义A”[6]56;他要把哲学习惯使用的 “词汇”或“观念”,请回“语言游戏的老家”去。非常明显,维特根斯坦完全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语言和哲学的关系,不再是哲学指教语言,而是语言医疗哲学,“哲学的成果是使我们发现这个或那个明显的胡说,发现了理智把头撞到语言的界限上所撞出的肿块。正是这些肿块使我们看到了上述发现的价值”[6]73。
维特根斯坦为语言松绑,颠覆了哲学,这种反叛态度让我们不禁想到胡塞尔的口号:“回到事实本身去”。虽然胡塞尔的“事实”是纯粹经验,而维特根斯坦的“事实”是语言游戏活动,二者的哲学方法及对待本质的态度也多有不同(从渊源上说维特根斯坦接近洛克,而胡塞尔则源于康德),但二者都表现为反本溯源、重塑哲学,以反对黑格尔式的理性主义大全哲学的倾向。二者的关联或许要从他们共同面临的历史政治背景中寻找:二战的伤痛记忆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理性主义—集权主义联合体的思想反叛,胡塞尔死在二战之前,反叛的强烈程度远远比不上后来的哲学家们,包括维特根斯坦。
这个反叛运动一直延续到伽达默尔。就语言观而言,从“家族相似”的亲近程度说,维特根斯坦明显更接近伽达默尔,这并不奇怪,两人生活在同一时代,《哲学研究》同《真理与方法》的成书前后相距十年之内,而对待语言的态度上两个人也表现出惊人的相似。维特根斯坦剥离私人语言之后的语言游戏是一个“私人”缺位的语言,而伽达默尔的语言则是本体论化的语言:“虽然我们说我们‘进行’一场谈话,但实际上越是一场真正的谈话,它就越不是按照谈话者任何一方的意愿而进行”[9]387,“讲话并不属于‘我’的领域,而属于我们的‘领域’”“进入语言的解释,就意味在这个世界中成长”[10]65-66。这些经典的伽达默尔名句都分明表示,语言是从私人那里脱位的;两人也都试图用游戏图示来说明语言,语言产生着意义,语言回答着问题,语言通过游戏和融合扩大着人们的精神领地,所有的私人都是游戏的棋子,按照限定的规则来铺展语言,或者说语言按照自己的规则通过匿名的私人来铺展自己,这个私人缺位的语言像一个幽灵,漂浮在人类上空,不断活动、不断伸展、不断制造着“精神科学的真理”和人类的生活世界,这就是伽达默尔和维特根斯坦共有的语言观。语言从言语和私人活动中的这一脱位从索绪尔开始,并在维氏和伽达默尔的语言观中进一步体现,成为海德格尔所言的“诗意栖居”的存在之家园,它不再是逻辑的强制必然性所搭建的“坐架(gestell)”,而是人类自然生活史或历史的精神展开所沉淀下来的公共场域和精神家园。这种转变终结了单个人的个体主体性的独自做大、吞天夺地的超人属性,强化了人们相互依赖又相对自由的主体间性,为人类的共生共存提供某种具有先验意味的共同图景。
私人缺位并不意味着个体缺位,只是原本在洛克那里作为观念和语词的源头的个体不再是语言发展中独自发挥作用的原生性力量,而是作为游戏参与者加入并塑形于公共领域,成为在公共空间里由公共的交互性牵动着的活动者,语言给个体规定了法则,也规定了个人与公共性不可剥离的联系,维特根斯坦或伽达默尔的语言充当着人际间的纽带,不仅构筑了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和生活世界,也决定了作为游戏共同体的社会共体相对每一个体的优先性地位,从而从根本上排除了超人凌驾于其上的可能性。扩张的个体主体性让位于语言这种公共的主体性交互活动,只成为公共性场域的有限参与者,并时刻以他者的公共场域为限界。这里所折射出的个体在语言中的不同地位是二战以后哲学发展最具伦理和政治意义的变化之一。作为一种哲学的努力,这种语言观的转变已经渗透到西方现代文化的各个领域,成为一种借以消磨个体主体性那种排他性棱角的有益的尝试。当然,公共性、本体性的语言能否成为人们诗意栖居的家园可能并不仅仅取决于语言本身,它和客观存在及现实利益之间不可避免的刚性联系常常使得语言成为一种弱电流而无法像哲学家所期待的那样正常工作。限于篇幅笔者难以断言这种哲学努力成功的可能性,也无法从政治和社会影响的角度来说明其实际意义,但它的确已经引发了巨大的后果。
[1] 洛克.人类理解论[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2] 李冬冰.新观念新道路[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152.
[3]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明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4]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28-629.
[5] 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M].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7.
[6]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4.
[8]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贺绍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5-26.
[9]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387.
[10]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M].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6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