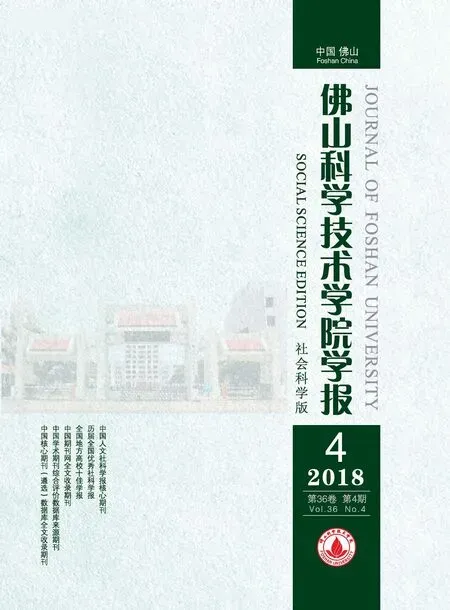人物核心与情节驱动
——中西戏剧中的叙事要素差异
2018-04-03廖艺舟
廖艺舟
(集美大学文学院,福建厦门 361021)
有一场发生在3000多年前的战争,起因是一位王子通过机敏判决赢得当世最美女性,激怒了海峡彼岸的强大国家联邦发兵征讨,拉锯式的攻城战延续十年。另一场发生在近2000年前的战争,大陆上军事力量最强的诸侯假托皇命挥师南下欲一统天下,双方各据长江南北,群雄汇聚、谋略不断,事件层出不穷、战场恢宏复杂,在几位核心人物的合力之下,最终凭借一场东风与一把燎江大火以少胜多。这两场战争分别是中西历史上家喻户晓的重大事件,历来均为文学作品所喜爱的取材源头。前者为发生在地中海沿岸的特洛伊战争,对其最完整的记述出自《荷马史诗》;后者是发生在中国汉末的赤壁之战,对其最精彩的演绎出自《三国演义》。若一场战役仍不够明显,不妨将外延扩展至全书,分析比对其叙事特征,能够清晰地看出:《荷马史诗》侧重人物本位,以人物为核心串联情节,在英雄的沉浮经历中渲染史诗的厚重;《三国演义》的众多诸侯势力与核心人物只是散布在张弛有度的故事画卷内的妙笔,人物为情节服务,以跌宕相扣的情节制胜。
一、中西叙事类文学的差异
从战争原因和目的上看,《伊利亚特》采用的设计方式是帕里斯通过判决金苹果归属哪位女神赢得了海伦,故而激怒了斯巴达王墨涅拉奥斯,其兄长、迈锡尼王阿伽门农召集各部族首领攻打特洛伊,消解了掠夺财富的历史实质。另一方面,从战争走势看,则是因为阿伽门农强行占有阿喀琉斯心爱的女俘布里塞伊斯,阿喀琉斯愤而不出战,使得希腊联军节节败退,死伤无数;《三国演义》中大大小小的军事战争,如曹魏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孙吴的“保全江东”,刘蜀的“匡扶汉室”背后均是掌权者的政治斗争,都讲求出师有名。个体英雄的表现在三国中可歌可泣,但无法影响战争的走势。
观其对于战场的具体刻画,《伊利亚特》着墨较多的是双方一刀一枪的杀戮过程,掩书过后血腥、残忍、野蛮的场景仍然历历在目,战争如“炽烈的火焰”,将士们如“蜂拥般厮杀”。“这种程式化、单一化的战争便是西方人“尚武”之英雄史观的一种反映”[1]。除尾声的木马计外对智谋运用显得单薄,描写英雄重在斗力、斗勇。《三国演义》的主要特色是着墨于战前两军力量对比、战略决策、战前准备等筹备活动,继而衬托出扣人心弦的战争紧张气氛。全书俨然一部兵书智典、谋略手册。在作为西方叙事文学滥觞的《荷马史诗》和作为中国古典小说集大成者的《三国演义》里,能够清晰地看到两者最突出的差异:西方的叙事文学重视个体,以人物为核心营构作品;中国的叙事文学重视情节,以情节的波澜演进讲述精彩的故事。
漫溯中西叙事作品的发展历程,这一内在规律均在文本之下发挥着隐微却深远的作用。从《俄狄浦斯王》到《哈姆雷特》,从《堂吉诃德》到《安娜·卡列尼娜》,从骑士小说到后现代的诸多流派,西方的人本主义传统从被发现到被隐藏再到重新高扬,“人”一直是历代文学巨著着力表现的永恒母题。而中国的小说、戏剧至元明方才走向成熟,从市井勾栏的说唱话本发展至由文人独立抒写的鸿篇,一向以情节吸引读者。诚然,这并非是在妄断其中某一方缺失哪项要素,人物与情节均是叙事类作品不可消弭的重要环节,但分别作为“核心内驱力”在中西文学中占有不同的比重。
阿契尔曾对三种基本的叙事结构设喻:“葡萄干布丁式的一致,绳子或链条的一致,巴特农神殿式的一致。”[2]128“链线式”即为珠串式一线到底,与中国古代若干文艺理论家的论述不谋而合:李渔的“立主脑、减头绪、密针线”,毛宗岗的“针线”说,吴梅的“线索纡徐”说,许之衡的“草蛇灰线”说等,均为线性设喻,形象阐释了中国叙事作品的结构形态。中国叙事作品往往具有完整的情节结构,多为连贯的单线叙事,侧重故事本位,又常“呈现出一种大故事中套着小故事的奇特艺术格局”[3]。如《西厢记》几大名段佛殿奇逢、月下联吟、席上赖婚、长亭送别起承转合明晰,首尾呼应浑然一体;如最常采用的章回体层次清楚脉络分明,《西游记》共写了14年零8天,共5048天,时间线索一目了然;如《水浒传》中的“武十回”“宋十回”等均构成独立的叙事单元,《聊斋志异》等短篇集合更不遑多论,每篇独立但连起来又是完整的整体。“正因为是线性结构,故而不是讲冲突、讲碰撞、讲对峙,而是讲曲折、讲波澜、讲起伏。”[2]129显然,冲突、碰撞、对峙必须以人物为主导,而曲折、波澜、起伏则必须以情节为主导了。
与之相对,西方的叙事作品喜用横截面式、片段式的结构,常有多线交织、蛛网密集式的线索安排,现代以来则擅以人物心理与意识流动作为情节主线。这种结构形同建筑体般错综复杂,是为“巴特农神殿式”,亦即“团块状冲突型结构”。比起中国“绵长延宕的渐变艺术”,这是一种“紧逼急促的激变艺术”,相对时间的重要性远高于绝对时间,讲求在短瞬之内集中呈现矛盾与冲突。如《俄狄浦斯》主故事时间在一天之内,《伊利亚特》聚焦十年战争的最后数十日;如《尤利西斯》中充斥着倒叙、插叙和交叉叙述,情节依循着人物的心理流动。
中国古典的小说、戏剧中,擅长描摹“类型化群像”[4]98,即运用刻意强化或夸张渲染的艺术手段,突出人物思想性格的某一侧面。因而在不同的作品中很容易发现一些具有相同特征的人物:神机妙算、运筹帷幄的诸葛亮、吴用、徐茂公;英勇粗犷的张飞、李逵、牛皋、程咬金;巾帼英雄的花木兰、穆桂英、梁红玉等等等,偏重于写英雄的共相,戏剧里则以不同颜色的脸谱将其具象化。而在同一部作品中,主要人物往往为单一性格特征的扁平人物,在作家的强化下甚至成为某种概念的化身。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评“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慨时时如见。”已对此做出最贴切注脚。
西方的小说、戏剧则热衷刻画“个性化英雄”,主要人物往往富有个人魅力。堂吉诃德挥剑纵马、横冲直撞,捍卫自由意识,闪耀着人文主义的光辉。人物的张力则通常来自内省而非外力的强加,核心人物往往是性格有多个侧面的圆形人物。譬如具有平等意识和反抗精神,又在野心的驱使下一心上爬、容易屈服、信奉虚伪道德观的于连,自认是信念、秩序、伦常的捍卫者,最后在暴风雨中发了疯的李尔王等等。
具体的人物塑造技法上,中国的叙事作品擅用白描,用行为动作来突出性格思想。如《三国演义》对于人物形象的勾勒,通常都是寥寥几笔“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声似巨钟”或是“身长八尺,浓眉大眼,阔面重颐”,用凝练简洁的语言让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水浒传》中写武松面临老虎的内心恐惧,是以“化作冷汗出了”的方式来表现。而在西方则善用心理刻画,重视情感描写,常用大段的独白来体现人物内心的纠葛变化。如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等都用第一人称。这在戏剧尤其近代话剧中体现更为明显,比如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便以普洛士帕罗的一段长达20行的独白作为全剧收尾。
值得一提的是,《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顶点,打破了前代对心理描写的粗略简括,其中人物的比重倒是大于情节的。这或许恰能解释它拥有无可比拟的学术地位却在民间的受欢迎程度稍弱,以及其在艺术上的世界普适意义。
二、立人物与讲故事:在戏剧文类中的取舍
“叙述与对话(展示),是中西戏剧比较的逻辑起点”[5]56。从文本形态学上讲,交流的话语形式有两种:其一是(代言性)叙述,话语关系体现在剧作者、演员与观众之间;另一种是(戏剧性)对话,话语关系表现在剧中人物之间。前者对应中国戏曲,是一种外交流系统。后者对应西方戏剧,是一种内交流系统。“叙述描述事件,对话展示性格”[5]73,叙述与对话是中西戏剧的根本性差异,也对应着两者对于人物与情节的不同侧重。
度过漫长的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戏剧中“人”的地位愈发被凸显出来,莎士比亚的戏剧以冲突性的对话为主导,塑造了一批足以立于世界文学长廊的经典人物,从《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麦克白》《李尔王》《奥赛罗》这些标题设置上都可见一斑。以易卜生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剧作家则致力于将人物置于典型社会环境,用人物的成长和内心冲突来体现社会的变迁。至现代派戏剧,人物的地位也从未降低,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中没有情节,仅有人物的零碎式对话,阿尔比的《动物园的故事》中杰利的一段独白竟达8个汉字印刷页之多。总之,纵观漫长的西方戏剧史,在越来越多的冲突性对话与精湛细腻的内心刻画背后,“人物本位”一直纵贯其中。
中国戏剧因为诸多原因成熟较晚,且文本中的叙述因素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究其渊源中国戏曲文化的“血统”是多元的,具体来说,民间“社火”是其土壤,宗教仪式直接影响,宫廷俳优予以催生,外来文化补充营养。明代曲论家王骥德认为,成熟的戏曲应具备以下两个条件:第一,“并曲与白而歌舞登场”;第二,“习现成本子”。按照这一尺度去衡量,他认为古代俳优、宋金杂剧和诸宫调都不算成熟戏曲,一直到元代“始有戏剧”。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得出了和王骥德类似的结论:隋唐时代的歌舞戏,“与其谓之戏,不若谓之舞之为当也”。宋金杂剧“非尽纯正之剧”,“而论真正之戏曲,不能不从元杂剧也”[6]。应当看到,元杂剧的前身,流行于宋金时期的诸宫调是一种说唱文学,它与民间说话是孪生的艺术种类。说书艺人为了谋生,为吸引更多受众来听,除了本身能说会道,靠的便是故事本身峰回路转的精巧结构,跌宕生姿、妙趣横生的情节,以及不能割舍的悬念。这种传统理所当然地浸润到了元杂剧当中,呈现出明显的“故事本位”。
中西戏剧分别侧重人物与情节,在若干经典作品中均有体现。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戏剧《哈姆雷特》被誉为“欧洲戏剧史”上的奇观,纪君祥的元杂剧《赵氏孤儿》在1735年被译成法文刊载在《中华帝国志》上,是第一部传入西方的中国戏曲。“同一性是比较的基础,异质性是比较的价值所在。”[7]两部剧对于中西戏剧传统有一定的代表性,且拥有共同的“复仇”主题。然而它们各自叙事的核心要素却具有显著的差异。
《哈姆雷特》全本共五幕二十场,《赵氏孤儿》一个楔子加五折,统计其篇幅体量,前者几乎是后者的五倍。按理《哈姆雷特》有更大空间讲述更复杂的故事,实际呈现却并非如此。戏剧开场即是一场鬼魂事件,由霍拉旭与马西勒斯发现了“像我们的国王”的幽魂。他们将这件事告诉了沉浸在丧父之痛的哈姆雷特,于第一幕第五场哈姆雷特便与父王的鬼魂见面,由此哈姆雷特便知晓了杀父仇人是谁,复仇的决心却已然在此立下。后文哈姆雷特反复挣扎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间,成为“延宕”的王子,而对于“复仇”这一核心情节,从一开始就是没有“悬念”的。莎翁的笔触多用在勾画哈姆雷特的内心,也正是复仇行动上的犹豫让这一形象显得深刻而复杂。哈姆雷特从高呼着“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快乐王子,变为愤慨地倾吐“这个泥塑的生命算得了什么”的忧郁王子,体现着哈姆雷特对于世界对于人性的思考与幻灭。作为绝对核心人物的哈姆雷特,其形象是立体的、变化成长的、多层次的。
《赵氏孤儿》的主角,则压根不是题眼中的“孤儿”赵武。楔子中屠岸贾借“神獒”奸计将忠臣赵盾抄家三百口,第一折里派韩厥上府欲将刚分娩的孤儿杀死,当门客程婴到来时公主以死相逼,程婴最终带走孩子。后来围绕杀死婴孩,上演了“程婴与韩厥对峙韩厥却倒戈放行并自刎谢罪”“屠岸贾再出恶招要抓全国半岁以下婴孩”等戏码,第四折二十年后揭开谜底,第五折赵武手刃仇敌。全剧跌宕起伏一气呵成,充斥着意料之外的险情,用悬念调动观众的情绪。对峙随处可见,观众与剧中人很难预料下一秒的情节,直到看到高潮弑仇、皇帝奖赏才拍手称快。
总体上看,首先,《哈姆雷特》中除主人公外还有若干形象鲜明的配角,类似雷欧提斯和福丁布拉斯还各有故事构成另外两条复仇的副线,《赵氏孤儿》中先后为婴儿丧生的公主、韩厥、公孙杵臼等等均只是功能性的角色。此外,中国戏曲一大共性是:不论文本还是剧本,从来只写“旦”“正末”等,类型化倾向相当明显,这正是“角色”而非“人物”,“所谓生旦是角色类型,叙述并对话的代言者。他们的性格跟话语没有关系,或者说他们的性格在戏曲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因此他们怎么说没关系,关键是说了什么。”[8]74西方戏剧则会在剧本上明确地写出人名。
其次,对于读者、观众来说,《哈姆雷特》的结局只需缓缓等待,他们会更关注人物的心理变化与煎熬,从而获取共鸣。《哈姆雷特》不缺乏“冲突”,但多为正面、直接的戏剧冲突,并非情节上的“悬念”。反观《赵氏孤儿》,整场戏,都会使人迫切地想知道下一幕发生什么,结局会是如何,会有酣畅淋漓的观感和愉快欣悦的满足感。
再次,《赵氏孤儿》的台词与唱词符合戏曲一贯采用的“代言性叙述”,对话成分占比远低于直接向观众讲述故事的部分。《哈姆雷特》中不仅有紧张的对话更有大段的独白来辅助塑造人物。
最后,在人物与情节的关系上,以《哈姆雷特》为代表的西方戏剧,是“意志决定情节”,而以《赵氏孤儿》为代表的中国戏曲,是“情同境转”[5]316。
西方戏剧突出自由意志的作用,认为人物的行动和情节发展决定于自觉的主体意识。这一传统历史悠久,亚里士多德早在两千年前就说过“行动由人物来表达”。人是戏剧的主人公,情节的下一步走向,通常会由人物事先的权衡与决策决定。为此,西方戏剧会严格控制人物数量,并保证情节整一性,以免剧情超越主人公意志。中国戏曲中人物的情感则受制于事态的发展,心境随着故事的发展而变化。情节上也常显得“节外生枝”,会有诸多巧合乃至完全超出人物预料的非自然因素出现。
试再举一例:中国名剧《窦娥冤》与希腊悲剧《安提戈涅》都是关于弱小女子出于传统伦理而献身的故事。安提戈涅在戏剧的开头就下决心要不惜牺牲性命去埋葬违法而死的哥哥,甚至意料到了行动的过程与结果,后来的剧情基本就是她意志的展开。可见与《哈姆雷特》类似,这也是一部典型的西方戏剧。相比之下,窦娥不是左右事态发展方向的决定人物,她只是被动地卷入。她所遭受的前几件悲惨的大事都毫无准备地到来,虽然在事出之后她都回肠荡气地抒发了自己的感情,但始终没有深入地分析原因并积极地寻找对策。故而,这些段落只是为抒情而抒情,而非自由意志的形成。
三、从文本到文化:对因由的立体观照
以戏剧为代表的中西叙事文学在人物与情节侧重上的差异,具有深层次的传统与历史根源,这一差异现象的形成,首先与作品的叙事主体即作者,以及作品的接受主体即读者有关。
在中国,戏曲也好,小说也罢,均是伴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和发展而兴盛的。就戏曲的文学因素而言,它是“言志”的诗词、“述事”的史传和娱情的说唱的交汇融合,假如从戏曲的艺术构成着眼而上溯寻源,着眼于诗者,认为戏曲乃诗词之遗;着眼于史者,认为戏曲乃“稗官野史”,是史观文化的庸俗化;着眼于歌舞者,认为戏曲的目的是“谐谑滑稽供人嬉笑”。而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之所造也。”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
尽管这些叙事类文学一向试图改变“小道”地位,剧作家们也希望甩开“小道”的标签往正统上靠,强调戏剧同样具有美育功能,但不可否认的是,既然受众群体是普罗大众,作为“俗”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作家的主观创作空间便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会不可避免地考虑到受众的需求。”[9]读者和听众,更关注通俗易懂的故事性内容,更容易被曲折动人的情节所吸引,更倾向悬念迭起的单线叙事。
在西方叙事类体裁才是文学正宗,古希腊的史诗与悲剧是后世文学的滥觞。戏剧的地位和中国大相径庭,深受统治者重视。“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僭主庇西特拉图为了赢得城市自由民(而非奴隶、女人)的支持,将戏剧作为教育市民的手段,兴建可容纳万人的露天剧场,每年举办两次戏剧比赛。莎士比亚时代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也很重视戏剧,伦敦有五个固定剧场”[10]162,很多戏剧就是专为君主而写的。到了近代资产阶级议会同样鼓励戏剧创作。从一开始西方的叙事文学就是供上层阶级乃至贵族、王室所欣赏的,剧作家能够得到上流社会的资金支持,创作空间自由,观众和读者的接受度和审美能力也较高。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中国上古时代便建立了以家庭为基础、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制度,没有个人主义的传统,不注重个人情感与内心世界的独立性。“传统并不是过去时间中客观的事件,而是一种先在经验结构,是无数的文本在精神中整合沉淀成的一种类型与形式的观念,一种‘集体的意识形态’。”[8]127而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从“认识你自己”到“超人”学说,无须赘述。这种差异自然也就造成了擅长写群体和擅长写个体的差异,以事件为中心和以人的性格和精神为中心的差异。“传统就是某种必然,传统中的任何艺术现象都不是偶然出现的,它是所谓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折光。”[8]95文本与文化之间,往往存在同构关系。
西方戏剧强调人的作用、强调主观意志的作用,是“主客二分”的文化的必然要求。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设想的“理念”开始,他们孜孜不倦地追寻着“终极真理”,认为在“行为”“在场”“现象”“感性”之上,存在着更高一级的“精神”“不在场”“本质”“理性”的世界。深受这种二元对立思想影响的西方人,倾向于将自己看作独立的主体,把世界看作外在的客体,而主体能够对客体进行认识和改造。“主客二分的文化是一种‘重智’的文化”[4]194,西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正好体现了西方人的知行观。他们心中一旦有了坚定不移的意志,就必然付诸行动,并且使整个情节以这个行动为中心,因此人物的意志会主导情节的走向,人物成为作品的核心。
相反,中国戏剧体现着“天人合一”的文化观。庄子所追求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典型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理想。道家如此,儒家也是如此,只是“他们在天人关系中加入浓厚的伦理色彩,予以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先灵内涵更丰富的诠释外延,进而扩展至与社会合为一体。”[10]180无论是纯粹的天人合一,还是带有道德意义的天人合一,在主客浑然一体这一点上是相一致的,只是对客体有着不同的解释。这可算是一种“重情”的文化,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熏陶的中国人一般不会采用对抗性的行动,特别是暴力型的行动去改变社会,他们希望与外在世界之间是和谐共生的关系。中国叙事文学中的人物也反映着这种思想,他们往往缺乏否定的精神,只能在无法控制的事态面前抒发情感。因此人物的形象由动作和事件来体现,情节设计会出现各种巧合和超出人物意志的进展,这样的写法更容易营造悬念。人物在情节中展现,情节成为作品的核心驱动力。
若再往前进一步,这两种文化形成的缘由恐怕很大程度上要归于地缘差异。中华民族在农耕社会、远古时代靠天吃饭,风调雨顺自然国泰民安,稳定的环境更容易滋养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西方文明的源头更容易培养出崇尚理性、勇于探索和冒险的民族精神。可见,文学的背后闪耀着文化的光辉,从文本到文化都值得我们用更专注的精神、更长久的时间继续上下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