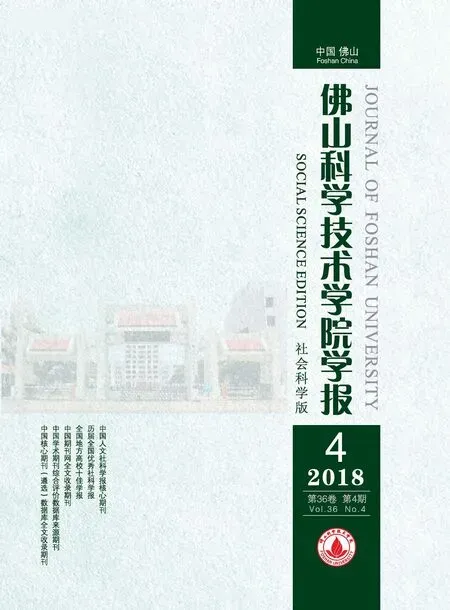遗骸犯罪所侵犯法益之探讨
2018-04-03彭鹏
彭 鹏
(湘潭大学法学院,湖南湘潭 411105)
我国《刑法》第302条盗窃、侮辱、故意毁坏尸体、尸骨、骨灰罪(以下简称遗骸犯罪)所侵犯的法益决定了该罪名的规范目的及刑事法网幅度,从而深刻影响本罪的定罪与量刑。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刑法理论通说将本罪所侵犯的法益归结为内容空泛的“社会良风美俗”,使得该罪名所保护的社会关系之实体内容难以得到全面的保障。因此,全面梳理当前关于遗骸犯罪所侵犯的法益,并从遗骸犯罪所真正侵害到的权益出发,探求本罪客体要件的应然内容,对于更好地完善我国学者对该罪的法理研究十分必要。
一、国内学术界关于遗骸犯罪所侵犯法益认识之梳理
(一)公共秩序说
这种观点从遗骸犯罪的同类客体出发,认为遗骸犯罪与《刑法》分则第六章的其他犯罪一样,对社会管理秩序造成了妨害,由此决定该犯罪所侵犯的法益是国家对社会风尚的管理秩序[1]或社会良好的道德风尚[2](依照我国刑法理论,将作为法益的社会关系划分为三个层级,只有为某种行为所侵犯的具体社会关系才能充当特定犯罪的客体要件)。根据这种学说,社会良风美俗对于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秩序抑或公共秩序是“通过一定社会结构中的人们共同遵守的生活规则来维持社会公共生活的有条不紊的状态……对公共秩序的破坏,实际上就是对社会生活规则的违犯”[3]10。而良风美俗显系这种社会生活规则的组成部分,于是违反良风美俗很自然地和破坏社会秩序联系起来。
(二)公民私权说
这种观点从遗骸本身的性质出发,认为逝者一旦死亡,其民事主体即告消灭,遗体等在法律性质上只能是作为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物,并且是代表亲属人格利益的特殊之物,“应以尸体之埋葬、管理、祭祀以及供养为目的,不得自由使用、收益及处分”[4]。因此侮辱、故意毁坏遗骸,“就无疑会侵害到专属于近亲属对死者的称谓权、尊敬权等永恒的精神性权利”[5]。对于这些权利,也有论者称之为祭奠权[6]或祭祀权[7],在性质上它们均属于具有身份性质的人格权利[5]。据此,针对遗骸实施的犯罪,实质上侵害的是作为私权的逝者亲属人身权利,并未破坏社会秩序。
(三)折中说
这种观点系“公共秩序说”与“公民私权说”的折中,认为遗骸犯罪所侵犯的法益系复杂社会关系,例如认为遗骸犯罪侵犯的社会关系是“社会风尚和死者及其亲属的名誉权”[8]或者“社会秩序以及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利”[9]。折中说无疑是在肯定遗骸侵犯了社会公共秩序的同时,认为这一认识有失片面,故而主张遗骸犯罪还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利。同时,由于遗骸犯罪规定在《刑法》分则第六章,故其侵犯的主要法益仍然为社会公共秩序,公民私权只能充当次要方面。
二、遗骸犯罪所侵犯法益诸种认识误区之剖析
(一)侵犯法益系社会公共秩序之证伪
根据我国学者的认识,作为社会秩序基础的社会公共生活规则,主要包含三个层次:第一,旨在保护人的安全和尊严的规则;第二,旨在调整公共场所秩序的纪律规则;第三,旨在维持日常生活中的稳定联系和习俗风尚的交往规则[3]12。良风美俗显然与第三层次的社会生活规则存在关联,但是是否一切不符合社会良风美俗的行为均是值得科处刑罚,需要纳入犯罪圈的行为?回答是否定的。社会学原理告诉我们,一切“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和社会共同生活,调节人们社会行为和社会活动的规矩和准则”[10]266均属于社会规范,其构成了现代社会控制的基本机制。其中,道德系一种源于风俗习惯却又高于风俗习惯的社会规范。[10]267然而,一方面,并非一切道德规范均与社会秩序存在关联,只有社会公共道德规范(如等候需排队等涉及社会公共生活的规范)才属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社会规范;另一方面,即使是违背社会公共道德的行为,也并非一概需要刑法介入,只有那些对社会秩序造成明显而现实的破坏,从而危及社会存续根基的那些违背社会公共道德的行为(如重婚行为严重危及婚姻家庭制度,进而有导致社会出现一定范围动荡的危险)才能被纳入犯罪圈。对遗骸实施的盗窃、侮辱以及故意毁坏行为,从根本上说,伤害了生者对于逝者的思念、哀悼等的情感,并无危及社会存续根基的可能性,因此其没有也不可能对社会管理秩序造成破坏,故良风美俗或者社会良好的风尚并不是遗骸犯罪所侵犯法益的内容。
(二)侵犯法益系自然人私权之证伪
1.逝者丧失权利主体资格
我国《民法总则》第13条规定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逝者既然已经丧失民事主体资格,显然不享有《刑法》分则第四章的所保护的公民人身、民主权利。尽管《民法总则》第185条、最高法《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3条规定:行为人侵害逝者的名誉、隐私等人格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然而无论前者关于“侵犯公共利益”的表述还是后者“近亲属因下列侵权行为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规定均表明:与逝者相关的人格利益的权益主体并非逝者本人。因此,法律保护遗骸以及附着于遗骸上的精神利益的趣旨之一在于维护生者的精神利益,救济亲属所遭受的精神损害。总而言之,法律保护遗骸及附着于其上的人格利益,并非是保护逝者的利益,而是保护亲属或社会公共利益,遗骸仅仅是法律关系的标的物而已,其并无成为法律关系主体的可能性。因此,前述认为遗骸犯罪的所侵犯法益系逝者的名誉权的观点,与遗骸的法律地位格格不入,不足为取。
2.逝者亲属人格利益具有片面性
固然,针对遗骸的侵害行为直接侵犯逝者亲属的人格利益,然而将这一社会关系界定为遗骸犯罪所侵犯的法益,仍显片面。首先,针对遗骸的犯罪只能侵犯到某些而非全部逝者亲属的人格利益,因为就人格的本体而言,系“满足其人之为人的利益”[11]44,而以人格为内容的人格权的存在价值则在于“促进人性尊严及人格的自由发展”[11]43。从权利的发展源流轨迹上看,“人格权概念乃是现代社会人的伦理价值范围扩张以及支配需要的结果”[12]。由此,人格权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权利群:既涵括具体化、类型化的具体人格权,亦囊括作为“以民事主体全部人格利益为标的的总括性权利”[13]的一般人格权。遗骸犯罪侵犯的显然是类似于祭奠权所包含内容的亲属人格利益,并无侵犯亲属之隐私权、名誉权、姓名权等具体人格权的可能性,因此以人格利益这一宽泛概念来统摄遗骸犯罪所侵犯的法益有失宽泛。其次,遗骸犯罪所侵犯的社会关系并不仅仅限于亲属的人格利益,还包括以社会情感为形式的社会公共利益,例如,侮辱、故意毁坏孤寡老人的遗骸同样会引起社会民众的普遍愤慨;同样,侮辱革命烈士的遗骸不仅会造成其亲属的精神损害,同样也伤害到全体社会民众对于革命烈士崇敬的感情。这种感情,显然不能被作为私权的人格权所涵盖,更接近一种社会公共利益。
3.遗骸不具经济学意义上财产价值
有论者认为,就性质而言,“尸体是一种能带来经济的特定物……盗窃尸体的民法意义上的结果,就是侵占公民的合法财产”[9],由此,就《刑法》第302条中的盗窃尸体罪而言,其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利。事实上,对于遗骸是否属于财物,国内外学者对此都有争议。在德国,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遗骸不具有物权法意义上的物的性质,而是死者人格的残存,另一种观点也把遗骸看成“物”。在日本,一些学者的观点认为遗骸是物[14]。我国学者对遗骸性质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有的认为,遗骸是一种特殊的物,遗骸不能买卖、先占或继承,公民依法对自己生前身体和死后尸体享有充分的支配权、控制权、处分权,公民生前对其死后尸体享有的处分权在其死后实际上由其近亲属加以维护和代为行使[15]。也有的人认为,尸体的本质在民法上一概表现为该种身体权利的延续,也就是在该身体权所有者(权利主体)死亡后的延续利益[16]。对于遗骸在法律性质上属于财物的认识,本文不敢苟同。通说认为,作为侵犯财产罪犯罪对象的财物在客观上要具有经济价值。[17]有无经济学上的价值,是划分财物与非财物的总括性标准,具体而言,指其是否凝结了人类无差别的抽象劳动,能否用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加以衡量。遗骸在法律性质上固然属于作为权利义务指向对象的物,但其仅在用于医学教学研究事业时才具有使用价值,且根据我国相关法规,遗体只能通过逝者生前书面签署的无偿遗体捐赠协议才能流转至医疗机构。可见,遗骸在法律上属于限制流通物。同时,遗骸的存在价值并不能用货币加以衡量,因为遗骸具有高度的人身专属性,人们只能通过土葬、火化等殡葬形式所留存的亲属遗骸来寄托哀思,慎终追远。由此,遗骸是不可替代物,一旦遗骸灭失,将给逝者亲属带来永久无法挽回的遗憾。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有学者所主张的具有主观性价值的物品能够作为财产犯罪对象[18]的认识,本文认为这是对“价值”理解的文义混同。在文义上,价值不仅可以从经济学角度理解为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同时也可以在一般意义上理解为“用途或积极作用”[19]。前述学者所主张的“主观价值”显然是从第二重意义上理解“价值”,而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实际上是特指“商品生产者相互交换劳动之社会关系”[20],主观价值显然不能用于商品交换,故其与财物所具有的价值之内涵相去甚远。既然遗骸不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那也就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财物,认为盗窃尸体、尸骨、骨灰罪侵犯了公民财产权利,是对“价值”一词不同意义混用的结果。
三、遗骸犯罪所侵犯法益为对遗骸虔敬感情之提倡
(一)中华民族“孝道”文化传统积淀
古人认为:“亡灵能够感应到祭祀者的哀思,那么在祭祀时就要恭敬虔诚,要事死如事生,要像父母祖先还在世一样去尊敬他们……在祭祀父母祖先时,要肃在祭祀父母祖先时,要肃穆诚敬,不能随随便便流于形式,而应该发自内心去祭祀”[21]。由此,中国古代社会形成程序复杂的丧礼,并成为中华民族“孝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学派从仁爱的角度出发,认为孝不仅意味着对父母的物质供养,更在于发自内心的敬畏[22]。因而,“送终”与“养老”共同构成传统中国社会子女孝敬父母长辈的道德暨法律义务,其不仅要求按照“丧礼”的程式为长辈操办丧事,而且发自内心地对逝者表示哀恸和不舍。根据儒家传统,父母逝世,儿女应当居丧三年,并且居丧期间的居处、饮食、容体、言语均有具体而严格的规定[23]。可见,体现在丧礼中“孝道”,以对逝者的虔敬感情为主要内容,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对逝者虔敬感情需要来自刑法的保障
不可否认,尊重亲属及社会公众对逝者的虔敬感情是来自道德的要求。然而,能否因此认为刑法保护生者对于逝者虔敬感情的保护,实质是对伦理规范的维护,进而,使得这一犯罪客体内容遭受“缺乏真正损害性因果关系[24]”的诘难?事实上,并非如此。刑法保护生者对于逝者的虔敬感情,并非缘于侵害这种感情之行为的反伦理性,而是由于这种情感本身是一种值得刑法保护的利益与社会关系。在现代社会,公众在满足基本生存需要之后,则产生感情的需要和被尊重的需要[25]。这些需要不仅通过被民法上的人格尊严权及一般人格权所部分涵盖,当民法上的恢复原状、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救济手段不足以弥补被害人情感上的创伤(如几年前,全国多地数次出现的盗窃逝者骨灰盒事件,民法救济手段就存在明显局限性,被害人因为不清楚加害方的身份,缺乏提起民事诉讼的可能性),就产生刑法介入的必要性。通过“刑修九”完善后的《刑法》第302条,扩展遗骸犯罪的客观行为方式及行为对象,能够更周延地保障遗骸,从而为保护生者对于逝者的虔敬感情构筑坚实的最后一道防线。
(三)作为法益之社会关系能够涵盖对逝者的虔敬感情
根据无法益侵害则无犯罪的观点,侵犯法益是犯罪成立的必备条件。对于法益的含义,刑法理论认为是“我国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26]95而所谓社会关系,不外乎是“人们在共同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相互关系的总称”[27]。在外延上,其不仅包含物质关系,亦包括思想关系[26]95。对逝者的虔敬感情无疑属于其中思想关系的范畴,是作为物质关系的婚姻家庭关系及社会交往关系在主观世界中的体现。由婚姻家庭关系所决定的亲情以及社会交往关系所决定的社会基本伦理决定生者对于逝者抱有的虔敬感情;同时,中国近现代历史还决定了我国人民群众对于革命烈士所怀有的崇敬和哀思。感情作为思想关系,对于稳定社会基本结构,淳化社会风尚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系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
(四)相关立法例的合理借鉴
在日本、德国,遗骸犯罪与宗教犯罪被规定在刑法典分则同一章节中,即日本刑法典第十八章名为“对于礼拜场所及坟墓的犯罪”[28],德国刑法典第十一章名为“有关宗教和信仰的犯罪”[29]。对于规定遗骸犯罪一章的共同法益,日本学者认为其系“国民宗教生活中的风俗、习惯,以及国民对死者所一般具有的虔诚、尊崇之情”[30],即对逝者虔敬的感情。由此可见,在域外的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地区),刑法典在不同程度上重视对公众情感的保护,从而不仅完整地保护了国民的精神需要,更是对社会文化的维护。在司法认定过程中,法官应当秉持《刑法》第302条之犯罪客体要件为逝者虔敬感情的认识,对于因为家庭贫困,无力承担相对昂贵的殡葬费用,而采用江河沉尸葬母[31]或自行燃火火化父亲[32]的行为,尽管从外观上看是对逝者的不敬,但是在贫穷的境况下不得已而为,并没有侵犯亲属本人及社会公众对于逝者虔敬的感情,据此不得认定为侮辱、故意毁坏尸体罪。
四、“对遗骸的虔诚感情”与“社会风尚”之区别
有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本文提倡的遗骸犯罪所侵犯的法益是对死者虔诚感情,那么对死者的虔诚感情与国内有学者提倡的公共秩序中的社会风尚有何区别呢?提出此种疑问的人认为对死者的虔诚感情其实就是公共秩序中的社会风尚,但是笔者并不赞同此种观点。
一方面,从概念上来说,社会风尚即为我国法律中确定的公序良俗中的一部分,公序即公共秩序,谓“社会之存在及其发展所必要之一般秩序”。良俗,即善良风俗,谓“社会之存在及其发展所必须之一般道德”,且须为“社会所行的一般道德”。[33]由此概念我们可以发现,对于社会风尚的内容界定过于广泛,而且在学理上也存在多种解释。法益本来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然而作为法益内容的社会风尚也是一个内涵以及外延很宽的概念,从而导致很难确定该罪所侵犯的法益。而对遗骸的虔诚感情内涵就比良美风俗要简单一些,就是对遗骸恭敬而有诚意,由此可见其内涵比善良风俗要容易确定。
另一方面,对于司法适用而言,根据“无法益侵害则无犯罪”的观点,法益的确定对于定罪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因为社会风尚的内涵过于宽泛,从而可能导致许多不应当被规定为犯罪的行为被作为犯罪进行论处,例如文章前述所说的“沉尸葬母”案就有此种嫌疑,这有违刑法中罪刑法定的原则。故而,明确该罪的保护法益对于司法实践的益处也是不言而喻。笔者认为,将该罪保护法益确定为对遗骸的虔诚感情,一方面可以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吻合,另一方面可以减少司法实践中的主观随意性。
结语
如果说人类意识是地球上最美的花朵[34],那么人类的感情则是最为夺目的花瓣。从某种意义上讲,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均是依靠美好的人类感情加以维系的,没有感情,整个社会共同体行将土崩瓦解。对于逝者的虔敬感情,不仅是表现为中华民族传统“孝道”的善良人性真实流露,更是现代社会人类的高级精神需要。在统一的法秩序框架内,不仅民事法律应捍卫这种感情,当这种感情遭受显著的破坏,民事法律的调整失灵时,刑法的介入也就成为必要。因此,遗骸犯罪的客体并非某种抽象的社会秩序抑或良风美俗、社会风尚,而是实实在在的亲属及公众对于逝者的虔敬感情。确认遗骸犯罪的这一客体内容,不仅彰显了刑法的人文特质,更是对现代人类文明精神的确认和维护,让《刑法》第302条的字里行间洋溢人性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