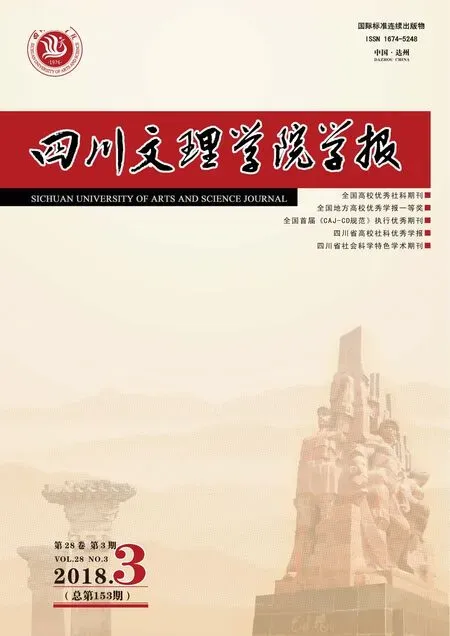论格非“江南三部曲”中百年知识分子的乌托邦建构
2018-04-03文婷
文 婷
(阿坝师范学院 学报编辑部,四川 汶川 623002)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一个人文理想大行其道、从胜到衰的年代,大多走过这个年代的作家们都怀揣着对理想和乌托邦的信念,乌托邦的书写在他们的作品里也屡见不鲜,如陈忠实《白鹿原》、王安忆《乌托邦诗篇》、王小波《白银时代》《黑铁时代》《未来世界》《2015》,以及20世纪初阎连科《受活》等,这些作品或多或少都表达出作者对乌托邦的思考。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是对乌托邦书写的经典之作,寄寓知识分子格非对乌托邦的热烈情感和真切希望。从宏观上来把握“江南三部曲”,即是讲述了发生在百年的中国历史中,三代知识分子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乌托邦的建构与建构失败的故事。格非一改过去以形式为重心的叙事模式,在“江南三部曲”中将着力点放在叙事内容——乌托邦母题,从历史和现实出发对乌托邦进行深度探讨,试图在发现问题的同时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展现出一个知识分子作家对当代乌托邦精神失落的缅怀与拯救。在“江南三部曲”中,不管是革命历史时期的张季元、陆秀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谭功达,还是欲望时代的谭端午,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身份除了乌托邦建构者外,他们还是作为文本当下时代的知识分子所存在。在作品中知识分子的身份和乌托邦建构是始终融为一体的,与此同时,乌托邦的解构与他们也息息相关,处处体现着知识分子如何参与乌托邦建构,如何忠于理想面对现实,如何在乌托邦建构和解构的过程中进行自身反思和救赎。
一、 知识分子与乌托邦的共生
从《迷舟》为代表的短篇小说开始,到“江南三部曲”的最终完成,格非之所以对乌托邦母题如此迷恋,与他典型的学院派知识分子身份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华东师范大学是批评家的圣地,尤其是由徐中玉和钱谷融先生所培养出来的王晓明、徐子东、李劼、南帆、胡河清等批评家都是成长与此,从80年代一直持续至今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也是首先发轫于此,当时的华东师大占据了“先锋批评”的半壁江山。作为在华东师大中文系土生土长的格非,对前辈们的文学坚守和人文理想信念一脉相承,这或许就是程光炜先说所说的格非“何以要用‘过来人’”的视角,重叙这二十多年时光岁月的缘由之一”。[1]
90年代的新生代作家毫不避讳地在公共场合表达自己对“知识分子”身份的厌恶。韩东曾说:“对于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我也是极端的反感,我从中读到了某种精神等级的东西,说白了就是他们自我感觉站在知识的立场上高人一等。”[2]韩东的此种观点与当时的社会转型不无关系。在当下消费主义时代,物欲金钱高涨让知识分子的身份发生了转变,他们对现实的挣扎和反抗越来越微弱,逐渐安于接受市场经济大潮下新生活的既得利益。知识分子不再是时代精神的启蒙者,开始成为消费文化的被启蒙者。但是这种观点仅仅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面向而已,因为当我们回顾新世纪以来的知识分子在遭受精神创伤和希望落空的时候,应该反思的是:大家在看到历史、时代、以及政治经济等意识形态的坚不可摧时,是否选择性地忽略或低估了知识分子在面对时代中的艰难困苦时所展现出的坚韧性格和顽强的生命力。
从词源学的角度考察,“乌托邦”(utopia),这一词语是根据古希腊文虚构出来的,既可以理解为“没有”(ou)的“地方”(topos),也可以理解为“美好的地方”(entopia)。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于1516年著的拉丁文航海小说《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简称《乌托邦》)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乌托邦”这一概念。由此,乌托邦进入文学和思想研究视域,并衍生出一系列的内涵:“虚无之乡”“乌有之乡”“极乐岛”“乐土”“理想国”和“桃花源”“世外桃源”等。
在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中,乌托邦的书写可以追溯到中国诗歌的源头——《诗经》。早在《诗经》中就有不少诗篇表达了中国先民们关于“乐土”的乌托邦想象,如《硕鼠》中的“乐土”“乐国”“乐郊”,《老子》中“小国寡民”的设想,《论语》《孟子》中所极力推崇的“礼乐制度”,这些都是一种乌托邦思想的表达,《老子》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庄子》的“建国之德”“至德之世” 更是从生存和统治问题出发去建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国度。因此,不管是老子的《老子·小民寡国》、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近代康有为的《大同书》以及建国后一系列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关于乌托邦的书写均与当下的社会政治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知识分子一词始于19世纪的俄国,当时俄国存在着一批出生上流社会,接受西方先进知识教育的进步青年,他们与俄国落后的专制制度格格不入,对现实社会和现存秩序出现了疏离和反叛,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因此被称为知识分子。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表明:“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不能只化约为面孔模糊的专业人士,只从事自己哪一行的能干人员。我认为,对我来说中心的事实是,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代表、局限、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3]刘易斯·科塞认为“知识分子必须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思想而生活的人’”,法兰克福学派坚持知识分子“应该是每一个时代的良知”。[4]国内著名学者许纪霖先生也指出知识分子就是 “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5]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士”是一脉相承的,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公共关怀和参与意识也是同传统的“士志于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着相同的精神契合之处。由此源流我们可以看出, 知识分子从一诞生开始就具有强烈的现实和道德批判精神,并且与乌托邦理想建构的责任和使命是共生的。
二、不同形式的乌托邦建构
在“江南三部曲”中,每一代知识分子都面临着自身的历史使命,并以他们自己不同的方式对待、履行各自的责任和使命。《人面桃花》中的张季元是接受过先进思想文化教育的近代青年,留学日本回来后成为隐藏在普济的革命党人,暗中与小驴子进行地下革命工作。陆秀米是扬州府官员之女,早期念私塾对古典诗词烂熟于心,后期留洋日本后回到普济进行革命运动,陆秀米和张季元都希望通过革命暴力实践建构一个理想的田园乌托邦和大同世界。《山河入梦》中的谭功达曾任新四军挺进中队普济支队政委,建国后出任梅城县县长,作为社会现代化建设的领导者,谭端午一直希望建一个人人相亲相爱的人民公社。作为最接近我们当下时代的《春尽江南》中的谭端午,他1985年从上海一所师范大学毕业后继续攻读了哲学硕士学位,是八十年代众人追捧的诗人,研究生毕业后迫于各种原因委身于鹤浦市地方志办公室,他用不作为的方式来坚守理想、抵抗社会的疏离。从“江南三部曲”这些主人公的人物形象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知识分子的身份,以及在不同时代下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构建和精神诉求。
(一)“性和革命”欲望的觉醒者——陆秀米
对陆秀米的乌托邦建构进行分析之前,不得不对秀米的启蒙者张季元进行简单的介绍:一方面张季元是秀米的革命启蒙者。张季元是作为秀米母亲的表兄出场的,秀米见他第一面,看他翘着二郎腿,抽着烟,一幅志得意满的样子,就铁定他“又是一个疯子”,正如秀米的父亲陆侃被称为疯子一样,文本提早暗示了张季元不同寻常的革命者身份。张季元实质上是“朝廷通缉的乱党要犯人,他来普济,原来也不是养病,而是暗中联络党羽,密谋造反”。[6]70随着夏庄薛祖彦的死去,张季元身份暴露惨死。另一方面,张季元是秀米的性启蒙者。文章一开始,秀米是一个不谙世事的懵懂小女子,把初潮的来临误以为是自己得了血流不止的大病即将要死去。张季元出现后,她不自觉地参与到张季元和母亲、翠莲之间的暧昧关系中,这恰到好处地唤醒了隐藏在秀米内心深处的欲望,促使她萌发了一系列关于情爱和性的幻想。在《人面桃花》中,“张季元不过是一个恰好出现、也正可以借用的替身和符号而已”。[7]尤其是张季元死后留下的日记,里面所记叙的大量关于革命过程和对秀米性幻想的文字,使秀米的爱情和革命启蒙开始步入正轨,并不由自主地开始投身到这场乌托邦的建构中。
把秀米的乌托邦建构概括为“性和革命”欲望的觉醒者,源于秀米在很大程度上尤其她前期的乌托邦思想是隐性存在的,是不自觉的,从日本归来后她才作为一个觉醒者开始进行自在自为地乌托邦建构。格非在文本的始初就对秀米后来的实践从性格方面埋下了伏笔,“每当她看到戏文中的‘黄沙盖连尸不全’的时候就会激动得两腿发颤,涕泪交流,既然要死,就应该轰轰烈烈”。在看到官兵的马队后,她觉得自己的脑子里也有这样一匹骏马,“他野性未训,狂躁不安,只要她稍稍松开缰绳,它就会撒蹄狂奔,不知所至”。[6]19这里,秀米所感受到的轰轰烈烈的人生以及狂躁不安的骏马均是对自己心中革命无意识的隐性表达。随后,当秀米目睹王观澄所建立的桃花源——花家舍土匪窝分崩离析,韩六直接道出了秀米的内心“这个王观澄这般的无能,这花家舍要是落到我的手里,保管叫它诸事停当,成了真正的人间天国……”[6]143从这里开始,秀米把自己变成了另一个张季元,真正的乌托邦实践开始。她留学日本回来后,在普济进行放足会(不让大家裹小脚)、成立普济地方自治会,设立育婴堂、书籍室、疗病所和养老院,她要把普济建成一个理想的大同世界,秀米的身份从大家闺秀的小姐、初潮来临时惊恐不安的羞涩少女变成了“校长”。最后由于翠莲与朝廷官员的联合,秀米的乌托邦实践终于梅城监狱,出狱后成了一个革命失败的“禁语者”。在这一漫长的实践过程,秀米深刻地体现出了一个“性和革命”的觉醒者敏感纤细的神经,无法抑制的情欲以及失败后的感时伤怀,秀米的一生也被后世传唱为一首慢悠悠的歌谣。
“使人扰乱和惊骇的,不是物,而是人对物的意见和幻想。”[9]秀米的乌托邦实践便始于她对性和革命的幻想,性和革命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性意识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革命启蒙的作用,性的懵懂和暴动充当了革命的原动力。根据弗洛伊德的学说,人性本能的激情和冲动指向快乐原则——本我。本我是每个人体生而有之的本能冲动,它是为了满足本能欲望的感性追求,遵循快乐原则,因此本我是个体最基本的表现,它处于弗洛伊德人格区别的最底层。正是由于对这种自身快乐的追求,个体身体所具有的性本能变成了实践力量的发源地,因此秀米革命实践的能量从初潮开始就悄悄聚集在身体的某个角落,等待着一个强烈的释放,于是,张季元和王观澄的出现便为她“初潮”式的革命激情提供了喷发的出口。正如张清华先生所说:“她的‘性启蒙’和‘革命启蒙’是同时完成的,这使得她的革命倾向一开始就与来自生命与血液之中的原始记忆与‘本能冲动’挂上了钩。”[7]秀米关于性和革命的实践并不是孤证,在许多的文学文本中,革命不仅仅是关于阶级斗争,不只是发生在政治、经济和历史领域,革命也发生在个体的身体内部,个体的性欲是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源,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文学史中会形成“革命+爱情”的经典小说叙事模式。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里也曾谈到:“在今天,为生命而战,为爱欲而战,也就是为政治而战。”[10]在马尔库塞这里,爱欲和性不再是闭门造车,不再是纸上谈兵,爱欲已经加入到了政治,成为了革命实践的一部分。这也就是为什么秀米在革命失败后变得更为轻松,什么烦恼和担心都没有了,脸上有了笑容,身体也好了起来,还能睡得着觉了,她感觉自己从记事起还没有这么舒畅过,根本原因就在于秀米内心的性和革命激情已经释放完成,她在由性和革命欲望所引导的乌托邦建构过程中回归到最原初的本我,成为了一个真正快乐的人。
(二)“堂吉诃德式”的行动者——谭功达
自塞万提斯《堂吉诃德》问世以来,堂吉诃德这个形象就以其“典型时代里的典型人物”成为各个时代争先研究的对象。在16世纪中期的近代欧洲,“将在行为和信仰高度上的个体性视为人类特有的条件和人类‘幸福’的主要成分的倾向,成了近代欧洲特性的重要倾向”。[11]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堂吉诃德不满社会的“世风日下、邪恶横行”,[12]84希望建立一个理想的黄金时代,在这个理想的国度“东西全是公共的,没有什么‘我的’和‘你的’”,“一切都是和睦的”,[12]85“一片和平友爱,带出融融洽洽……表达爱情的而语言简单朴素……真诚还没有和欺诈刁恶掺杂在一起,公道还有它自己的领域……”[12]87
堂吉诃德所描述的这一切不能不使我们将它和乌托邦、理想国联系起来。然而,堂吉诃德对未来世界不仅仅是简单的设想,他是一个“行动上的巨人”,他在行动上努力实践着自己关于理想国度的建构。面对黑白颠倒的社会,堂吉诃德在现实中找不到行动的方向,于是戏仿骑士小说里的人物,单枪匹马去与一切仇视人类的“巨人”进行搏斗。尽管他三次出行看起来荒唐可笑,他帮助一个挨打的小孩,却将小孩陷入更糟糕的境地;他把风车当成巨人与之搏斗,把自己摔得遍体鳞伤;他把修士当做妖魔,与比斯盖人进行恶战,把羊群当成军队,释放一群恩将仇报的囚犯……但是堂吉诃德从不怕人们的背后议论和当面嘲笑,哪怕在乌托邦的实践过程他四处碰壁,他始终忠于自己的理想。
谭功达就是一个和堂吉诃德相似的乌托邦建构者。在五六十年代,“革命既非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为,也并非秀米时代的秘密行动,此时的革命俨然已是一种积极支援革命建设即建立现代化国家的巨大热情”。[13]身处这样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谭功达站在梅城县县长的位置上,手拿梅城县行政区域规划图,俯瞰普济,深感梅城现代化建设的落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缓慢,他希望能建立斯大林集体式的高级社,实现他心中家家户户花放千树、灯火通明的美好蓝图。于是开凿大运河、建大坝发电、提出村村通公路计划,建造集体居民点,丧葬改革,沼气推广等,他进行了一系列与堂吉诃德相似的荒唐行动,是个典型的理想主义实践者。在这些过程中,很多人提出反对的意见,副县长赵焕章认为“眼下连年饥荒,财政入不熬出”,办公室主任钱大钧用“掏心窝子的话”好心规劝:现如今,解放不久,百废待兴。就眼前这些鸡零狗碎、焦头烂额之事都不遑应付,何苦无风兴浪,做那吃力不讨好的事?水库大坝……伤筋动骨,吉凶难测,万一弄出个三长两短,只怕是不好收场……”[8]12谭功达根本没考虑这些现实因素,一意孤行地秉持自己对乌托邦的坚定立场。哪怕最后他因为大坝决堤发难和官场政权的倒戈被革职查办,他仍然想着要在梅城修建下水道工程。正如高麻子骂谭功达的话:“最可笑的,这世上还有一类人。本是苦出身,却不思饮食布帛,反求海市蜃楼。又是修大坝,又是挖运河,建沼气,也做起那天下大同的桃源梦来。”[8]151革职后的谭功达去了郭从年所建立的花家舍人民公社会,这里呈现出来的状态是他一直所梦寐以求的社会形态,然而当他发现隐藏在乌托邦背后残忍的人性机制后,一切归于荒诞,留下的仅仅是他一个人才看得懂的梅城规划图,天下山河终入梦中。
不管是事业上还是生活中,谭功达都败给了臣服于权势的实用主义者和利己主义者,但谭功达如堂吉诃德一样选择了一种“孤独骑士”的方式,让自己成为一名永不妥协的战士,努力建构着心中的理想之地。如果说秀米的乌托邦建构满足本我的快乐原则,那么谭功达和堂吉诃德的行为便是建立在超我的“至善原则”上,并且“自我总是无一例外地实行压抑,以服务、听命于超我”。[14]在他们进行实践的过程中,潜意识不断地对自我进行规范和约束,如谭功达对姚佩佩的爱情以及面对政治高压偶尔想要逃离现实的冲动,堂吉诃德对心爱的杜尔西内亚的感情,这些潜在的情感都在对自己的监督下被压制,他们遵循“至善原则”,他们关于人民美好未来的艰难奋斗和理想社会的不懈建构使他们自身处在社会道德的高层。
根据此逻辑,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乌托邦不仅仅是人类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和追求,乌托邦是存在于超我的潜意识,它位于社会道德的制高点,是一种超验性的存在。“乌托邦理应隶属于人的纯碎精神领域或深层的情感体验,是无法完全还原到现实世界或当下历史经验中的特定社会阶段的。”[15]因此,不管是16世纪中期西方的堂吉诃德,还是20世纪中期东方的谭功达,他们关于乌托邦的建构注定了都只能是南柯一梦。
(三)“哈姆雷特式”的思想者——谭端午
哈姆雷特是与堂吉诃德同时出现在文坛上的经典人物,他们同属于理想的人文主义者。如果说堂吉诃德是 “行动上的巨人”,那么哈姆雷特就是典型的“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一个勇往直前,一个瞻前顾后,“屠格涅夫说:‘这两个典型体现着人类天性中的两个根本对立的特性,就是人类天性赖以旋转的轴的两级。’”[16]哈姆雷特呈现出这样的性格特质是与英国的现实环境息息相关的。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哈姆雷特身为王子,他鄙视英国当时等级森严、权恶相争的封建关系,他拥有诗人的美好理想和秉性,他渴望人与人之间真诚平等的关系。在哈姆雷特的理想世界里,父亲英明治国,父母相亲相爱,朋友相伴,自己和奥菲利亚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这就是他想要的一切。然而在他目睹母亲和克劳狄斯的一切苟行之后,他成了一名忧郁延宕的王子。他反复思考着“to be or not to be ”的问题并耽于“负起重整乾坤”责任,对自己为父报仇的行动迟迟未实施。黑格尔曾经指出:“哈姆雷特固然没有决断,但是他犹豫的不是应该做什么,而是应该怎样去做。”[17]哈姆雷特并不是要放弃复仇,他的犹豫和延宕是因为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他将自己的个人复仇同时代的责任联系在了一起。哈姆雷特看到了当时社会的现实,要想实现他心中理想的关于政治和道德的乌托邦国度,他需要复仇的对象并不是克劳狄斯一个人,而是克劳狄斯这样的一类人。因此,在面对这样巨大的现实面前,感性的哈姆雷特在复仇行动上所表现出来的深思熟虑、犹豫不决和瞻前顾后是十分合理的。
“迄今为止,格非小说中最主要的人物几乎都有一个‘哈姆莱特式的性格’——这个说法是我专门为格非小说‘发明’的。”[7]在张清华先生看来,从格非早期《追忆乌攸先生》中的乌攸先生,《迷舟》中的萧、《傻瓜的诗篇》中的杜预,再到“江南三部曲”的陆秀米、谭功达、谭端午,他们都爱幻想,身上有一种哈姆莱特式的悲剧性格。如果张清华先生是从一种精神内核的敏感与多疑来解释“哈姆莱特式性格”的类型,笔者却认为在《春尽江南》中谭端午与哈姆雷特性格的相似之处恰好在于他们都是“清醒的思想者,理性的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表现得谨小慎微,尽量掩藏着自己真实想法和真实自我,他们的痛苦不在于外在物质的匮乏,而在于自我对思想的深度麻醉,他们并非没有意识到当下生存状态的不完善,而是在意识到这种无力改变的现状后,他们对现实既介入,又疏离,“剪不断,理还乱”。他们的思考主要囿于看清现实后面对无路可走的生活该怎么做,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导致他们采取了延宕地安于现状,使自己成为 “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的大潮引起了中国现实社会的深刻巨变,市场经济的初步形成导致金钱和物欲成为大家争先追捧的对象,文化和精神则退居次要的地位。此时尽管陆秀米所构建的“大同世界”和谭功达所构建的工业化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完成,但是“真正的问题都出现在‘革命的第二天’”,[18]在“革命之后”(或者“革命的第二天”)世俗世界不断侵犯人的意识,人们发现道德理想已经无法革除倔强的物质欲望,乌托邦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一切面目全非。“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矣”,作为乌托邦实践者的知识分子身份也发生了极大变化,“大众”开始成为革命的主体,而知识分子则被设定为“尴尬的甚至是危险的角色”。[19]
谭端午作为上海一所师范院校毕业的硕士研究生,他的“诗人”身份在这个时候也被消解,他以冷眼旁观的态度被动地接受着一切:工作时,他整天面对的是鹤浦地方志办公室的家长里短和无所事事;生活中,他需要处理的是母亲和妻子的婆媳关系,儿子的教育问题,自己和妻子的情感问题。当然所有这些生活的日常问题谭端午都没有处理好,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和朋友的酒桌饭局,和家里的一本《新五代史》上。正如妻子庞家玉对这个丈夫的评价:“端午竭尽全力地奋斗,不过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无用的人。一个失败的人。”这是她心情比较好的时候所说的话。在心情不那么好的时刻,她的话往往就以反问句式出现,“难道你就想心甘情愿,这样一天天地烂掉?像老冯①那样?嗯?”[20]13谭端午对生活的态度和哈姆雷特是一样的,他看清在这个时代里知识分子力量的渺小和乌托邦理想的微不足道,于是采取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生活态度和建构方式,他的生活被推着走,他的每一步都是被动的,这是无奈的反抗也是彻底的屈服。
汪晖在《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里谈到,在中国20世纪八九十的历史境遇中,由于消费主义文化进入了大众生活的日常琐事之中,改变了大众的对当下生活的价值判断,因此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事件,而不仅仅是经济事件。他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大众文化与官方意识形态相互渗透并占据了中国当代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而被排斥和喜剧化的则是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的意识形态,在有些后现代主义者所采用的学院政治式的批评方式中,隐含的是他们的文化政治策略:用拥抱大众文化(虚构的人民欲望和文化的市场化形态)拒斥精英文化的姿态返回中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21]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中,精英知识分子身份被边缘化,处境艰难,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遭到来自金钱暴力和意识形态的双重挤兑,因此谭端午已经没有 “解答一切难题,克服一切障碍,完成一切探索”的自信,[22]而是选择无可奈何地面对自身的“无力感”。
从弗洛伊德精神学分析的话,谭端午和哈姆雷特对待理想和现实的态度,既不是本我的“快乐原则”,也不是超我的“至善原则”,而是一种来自自我的“唯实”原则。他们面对社会现实,既能压抑本我的欲望,又能在压抑的同时尽量满足自己的快乐,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从当下的现实出发,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处理好本我、超我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他们是处于本我和超我之间的一层。因此,哈姆雷特对于如何进行复仇和重整乾坤一直处于犹豫不决中,而谭端午对于自己失掉知识分子光环后的生活安之若素,他感觉自己现在的状态“置身于风暴的中心,同时又处于风暴之外”。[20]24端午甚至暗暗期盼着,能一直这样生活下去。面对这一现状,王岳川先生如是说:“当前最大的问题是知识分子生活在道德沦丧的环境中,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口不应心对知识分子来说已习以为常。知识分子已学会不相信任何人,不再关心别人,而只顾自己。”[23]
三、 乌托邦建构失败后的禁语和流放
“从长期来看,历史可以被看成是一系列试验和错误的试验,其中既是诗人的过世也有试验的价值,而且在这种实验过程中,知识分子由于在我们社会中的无归属性,最容易遭受失败。他们不断试图认同于别的阶级,却又不断受到拒斥,这必然使知识分子最终更清楚地看到他们自己在社会秩序中地位的含义和价值。”[24]乌托邦失败的原因除了曼海姆谈到的知识分子的自身身份以外,他所忽略掉的一点是进行乌托邦实践的知识分子所强调的独立、自由等思想和乌托邦世界中所强调“统一思想”“集体意志”等思想是相矛盾的。这使我们看到不管是在进行近代革命、社会现代建设还是在物欲横流的当下社会,知识分子们进行乌托邦建构所面临的失败结局具有必然性。
在“江南三部曲”中,乌托邦建构失败后,陆秀米变成一个“禁语者”,谭功达“流放”至“花家舍人民公社”,姚佩佩开始颠沛流离的逃亡,诗人谭端午却在众声喧哗的时代一言不发,因为“在政治话题沦为酒后时髦消遣的今天,端午觉得,可以说的话,确实很少了。他宁愿保持沉默”。[20]236这里知识分子的“禁语”、沉默、“流放”、逃亡即是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和身份问题。
话语权是法国思想家福柯提出的一个具有后现代性的概念,“话语是一种权力关系。它规定谁有发言权,谁无发言权……语言系统在情感和思想的层面上会产生压制;尽管它是一种隐蔽的,表面上无行为人的控制系统,然而它在社会中是一种真实的权利”。[25]从这个意义来理解,话语权便是确认知识分子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知识分子身上所肩负的“时代鼓手”和“时代传声筒”的责任和义务。秀米的禁语便是革命失败后,她觉得自己丧失了传统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感和实践能力,她在用禁语的方式遭受革命失败后对自己的惩罚,就如丁师母所说“让你变成哑巴,就是刑罚的一种”。[6]257因此,闹饥荒时,秀米得到一布袋白花花的大米后情不自禁地开口说话了,因为她现在又有了进行“达则兼济天下”的能力和权力。她把大米熬成粥每日一次地分给本乡人,甚至包括外乡人和乞丐,看着眼前的一幕,秀米想起了张季元未完成的大同世界,自己夭折的普济学堂,以及父亲出走时带走的桃源梦。
秀米的禁语方式跟自己乌托邦建构的成败直接相关,谭端午“保持沉默”的方式则有着更为深层的复杂原因。在物质不断发展消费文化逐渐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过程中,曾经的价值关怀和乌托邦理想等渐渐消退,大多数知识分子在这样大量创作物质财富的活动中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和“时代代言人”的话语权和身份。蔡翔曾生动地描述了这种状况:“接踵而来的市场经济,不仅没有满足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想象,反而以浓郁的商业性和消费性倾向再次推翻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26]因此,知识分子口中的“人文精神”“个体价值”“乌托邦理想”等思想和追求变成了大众们调侃的对象,精英文化的崇高在无形中被消解,代之而起是灵与肉的分离和“三俗”的价值取向。正是在这样的当代境遇中,谭端午自觉地选择了沉默,他不再去关心“铁屋子”里的动静,也不愿去唤醒“铁屋子”里沉睡的人,因为此时清醒的知识分子们已经变成无力唤醒沉睡者的孤独者和边缘者,知识分子式的努力只会加深他在这个时代的痛苦,“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个人”。
“禁语”表明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那么“流放”则说明知识分子为调和这种关系所做的努力,他们试图在永无归期的流放中找到知识分子的自我镜像。不管是姚佩佩还是谭功达,他们作为国家政治权力阶层一直在一座钢筋混泥土所建造的建筑物里从事高级的“脑力劳动”,他们在从事低级“劳力劳动”的大众心里都是一个“他者”,他们被大众设定为二元对立关系中更为尴尬的一方。因此,姚佩佩在杀死金玉后成为了社会最底层的逃犯,谭功达在革职后成为花家舍的巡视员,开始关注比现代化建设更为实际的大众生活,他们的“流放”就是一条知识分子开始向大众靠拢的路,谭端午甘愿保持沉默的姿态也是一种将自己的立场转到大众阵营中的表现,即知识分子开始“接地气”。
因此,在知识分子话语权和身份问题逐渐淡漠的今天,把知识分子绑架在道德制高点对他们进行批判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辩证地看到这些所谓的乌托邦建构的“失败者”为时代和大众所做的不同努力,他们并没有忘却自己的使命,只是换了另外的一种方式而已,或“禁语”,或“沉默”,或“流放”。
知识分子与乌托邦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在这复杂关系背后便是乌托邦建构定会失败的不二结果。不管是革命历史时期的陆秀米、陆侃、张季元,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谭功达,还是欲望时代的谭端午、庞家玉,他们“你方唱罢我登场”,均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乌托邦建构为我们呈现出了百年中国历史中个体存在尤其是知识分子与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他们的失败暗藏了知识分子不得不生活在永恒的个体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两难中,不管在何时,真正成功的革命者改造者唯有时代本身。因此格非才会深谙其道地说:“所有的成功者都是肤浅的,只有失败者肩负着反思的重任。”[27]
注释:
① 老冯,是端午所供职的地方志办公室的负责人。他是鳏夫,有点洁癖,酷爱庄子和兰花。他有句名言,叫做:得首先成为一个无用的人,才能最终成为自己。句式模仿的是马克思,弹的还是“君子不器“一类的老调。
参考文献:
[1] 程光炜.论格非的文学世界——以长篇小说《春尽江南》为切口[J].文学评论,2015(2):108.
[2] 韩 东,张 军.时间流程之外的空间概念[C]//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44.
[3] (美)爱德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台北:麦田出版局,1997:48.
[4] 陶东风.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226.
[5]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4.
[6] 格 非.人面桃花[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7] 张清华.春梦 革命 以及永恒的失败与虚无——从精神分析的方向论格非[J].当代作家评论,2012(2):6-12.
[8] 格 非.山河如梦[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
[9]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 阳,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06:45.
[10](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1966年政治序言[M]//爱欲与文明.黄 勇,薛 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1.
[11](英)欧克肖特.整治中的理性主义[M].张汝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89.
[12](西班牙)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上[M].杨 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13]段 曦.百年中国:理想的悲歌——论格非江南三部曲的主题意蕴[D].海口:海南师范大学,2013:1.
[14](奥)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M].林 尘,张呼民,陈伟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75.
[15]张彭松.乌托邦语境下的现代性反思[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94.
[16]易晓明.关于堂吉诃德形象的几点思考[J].语文文学论集,1987(1):95.
[17](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11.
[18]蔡 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1.
[19]南 帆.后革命的转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6.
[20]格 非.春尽江南[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21]汪 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M].上海:三联书店,2008:84.
[22]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M].上海:三联书店,2002:232.
[23]王岳川.世纪之交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态问题[J].科学中国人,2001(6):39.
[24](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黎 鸣,李书崇,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159.
[25]郑乐平.超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论新的社会理论空间之建构[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65.
[26]许纪霖,陈思和,蔡 翔,郜元宝.人文精神寻思录之三——道统、学统与正统[J].读书,1994(7):48.
[27]格 非,张清华.如何书写文化与精神意义上的当代——关于《春尽江南》的对话[J].南方文坛,2012(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