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之“恶”,成我之“识”
2018-04-02闵雪飞
《隐秘的幸福》是巴西女作家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代表作品,既是一篇短篇小说,也是作者一部小说集的标题。对于中国读者,李斯佩克朵也许不是一个熟悉的名字,但在世界范围内,她早已令人瞩目,这是一位能够达到文体、思想与生命意识高度统一的作家。

李斯佩克朵(1920-1977)
《隐秘的幸福》小说集出版于一九七一年,其中的小说,虽然主题不同,但隐约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方向:探寻自我,建立自我意识,亦即个人成长。《隐秘的幸福》同时也是一部具有很强自传性的作品,尤其是《狂欢节琐忆》《隐秘的幸福》与《索菲娅的祸端》这三篇代表性作品,某种程度上,是作家根据真实的童年生活写成的。因此,本文将以“存在”为基础,从“善”“恶”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出发,对《隐秘的幸福》略作解读,试以阐释一条不同于男性的女性成长之路。
李斯佩克朵童年时,母亲病得很重,家中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这一点可以在以第一人称叙事的《狂欢节琐忆》中清楚地看到。这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八岁的小女孩的成长故事,她希望通过装扮成玫瑰参加舞会来获得成长,然而母亲突然病重,她无法完成装扮,成长的美梦就此破灭。这个充满期待却又不得不接受苦涩宿命的小女孩正是李斯佩克朵贫苦而又不失温暖的童年的真实写照。通过这个短小的故事,作家也揭示了一个小女孩“自我之识”的过程。小女孩具有很强的成长欲望,渴望被装扮,渴望成为一朵玫瑰,因为她已经无法忍受小女孩的处境,对童年感到羞耻,意欲长大成人:“我迫不及待地要从这弱不禁风的童年里走出,她用鲜艳的唇膏涂我的嘴唇,往我的脸上抹胭脂。这样,我觉得我自己又漂亮又女人,我从孩童里逃了出来。”面对母亲病情突然加重这一起偶然的不幸,小女孩精心策划的成长之梦只能暂停,接受依然停留在童年时刻的现实。“我跑着,身上穿着玫瑰,脸却没来得及戴上少女的面具,把我暴露于众的童年生活遮隐。”这是一个心酸的瞬间,在小女孩最接近幸福的时候,幸福却迟迟不至:“我跑着,跑着,在拉环、彩带与狂欢节的喧闹之间,我茫然无措地奔跑着。其他人的欢乐吓坏了我。”这种突如其来的挫败与旁人的快乐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很显然,有着这样生活经历的李斯佩克朵必然会对庸常的幸福概念产生怀疑,她不禁质问:“命运掷出的骰子有道理可言吗?它太无情了。”通过书写童年的真实经历,作者质疑了幸福的终极性,重申“偶然性”才是一种必然的人生命题。

李斯佩克朵小说集《隐秘的幸福》闵雪飞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這部小说集还收入了另外一篇与“玫瑰”相关的小说,这就是《百年宽恕》。在这两篇小说中,“玫瑰”都是成长的象征。小女孩的童年是“蓓蕾”,而盛开的“玫瑰”则代表着成长。在《狂欢节琐记》中,小女孩渴望通过装扮成玫瑰的方式,实现自我变形,生成一朵玫瑰,从而获得个人的成长与认同。在《百年宽恕》,也是通过“玫瑰”,小女孩实现了个人成长与认同,但与《狂欢节琐记》略有不同,整个过程被具体化为小女孩的“偷花”行为,至此进入了李斯佩克朵对“恶”的书写之中。“偷花”属于偷盗行为,无疑是一种“恶”。然而,在李斯佩克朵的笔下,“恶”并不具有道德判断价值,而是促发“自我意识”产生的最主要的因素。与“恶”相联系的是“欲望”。在小女孩这里,“长大成人”的渴望首先表现为对“玫瑰”的觊觎,可以看一下文中的这个场景,女孩发现:“花坛里有一支孤独的玫瑰半开半合,颜色是娇嫩的粉红。我呆住了,艳羡地注视着那朵高傲的玫瑰,她还没有长成女人。就这样,我发自内心地想要这朵玫瑰。我想要,哦!我真的很想要!”女孩急于在自己与玫瑰之间建立联通的关系,从而让自己内化成“玫瑰”,而实现成长:“我想嗅她的香气,直到感受到浓郁馨馥里的黑暗。”之后,女孩下定决心,要去实施“采撷”这种实质上属于“偷窃”的“恶”的行为:“现在我终于站在她面前。我停了片刻,这真危险,因为近在咫尺的她更美丽。我终于折断了花茎,玫瑰刺破了我的手,我吮了吮指头上的血珠。”通过“恶”,女孩终于“拥有”了玫瑰:“我对玫瑰做了什么?我让她成了我的。”通过“偷花”这种特殊的“恶”,她最终实现了成长的欲望。并且,“我不后悔:偷玫瑰和番樱桃的小贼可以得到一百年的宽恕。就像那番樱桃,她宁愿等别人摘下,也不愿贞洁地死于残枝”。

巴西儿童文学作家蒙特罗·洛巴托(1882-1948)
从《百年宽恕》中,可以注意到李斯佩克朵的写作特点,她并不愿意具体地描写成长的完整过程,而是喜欢选取一个关键性时刻,或者说,一个具有神秘性的突发事件,用以凝缩成长过程中的种种心理矛盾。
“偷书”也是李斯佩克朵经常书写的“恶行”。一如“玫瑰”是成长的象征,书籍作为承载知识的物体,象征着“识”。对书籍的占有,某种程度上,是获得“自我认识”能力的重要途径。在李斯佩克朵的处女作《濒临狂野的心》中,女主人公约安娜便是一个偷书犯。约安娜从小父母双亡,被叔婶收养。叔婶企图将她培养成如同自己的女儿阿曼达那样循规蹈矩的堪称模版的女性,但是约安娜却从心底拒绝。她更期待认识真实的自己,并以此为基础,自主决定今后的生活,而不是被种种社会规范所定义。在书店里,她和婶娘之间爆发了一次激烈的冲突。婶娘发现约安娜若无其事地拿了一本书,没有付钱,不禁大骇,质问她为什么要偷书。在婶娘的眼里,“偷盗”是十恶不赦之事,规矩的女孩子不能做。然而约安娜却回答婶娘,偷书只为“快乐”,想做就做了,也不觉得是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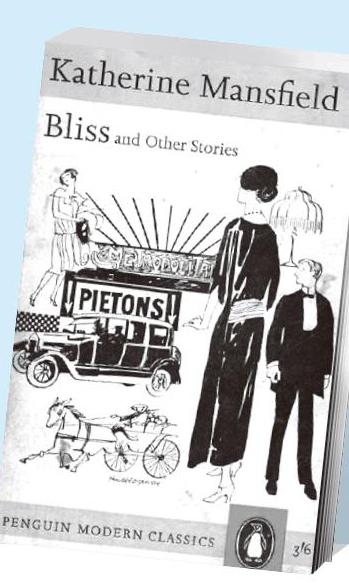
曼斯菲尔德《幸福》1962年企鹅版
实际上,一如小女孩通过“偷花”而实现成长,在约安娜的“偷书”行为中,体现了她对知识与知识权力的渴求。首先,她的目标不是其他宝贝,而是书;其次,她的目标不是具体的哪一本书,而是任何一本书都可以,这就使得这种行为从不可饶恕之“罪”变成了一种为了获取知识权力而实施的譬喻性挑衅行为。“偷窃”这个词,对于约安娜和婶娘,具有不同的意义。对于婶娘,亦即约安娜想挑战的世界的代表,“偷窃”是一种恶,一种罪,需要上帝宽恕,这是一个具有伦理价值的词。婶娘对这个词非常害怕,以至于说不出口。然而约安娜却可以平静地毫无愧疚地说出“偷”这个词,因为她“因为喜欢,所以去偷”,而这个行为“并没有什么不好”,而且她“只有在想偷时才偷”。通过僭越性的“偷盗”,以及轻飘飘地说出“偷”,约安娜打破了约定俗成,消解了“偷窃”在传统社会中所被规定的负面意义,从而建立了一种新的可能—可以利用平凡的词汇,开创出未知的新意义。
《隐秘的幸福》和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主要讲一个买不起书的瘦女孩如何占有一本书。在解读这篇作品之前,需要先来了解一下对李斯佩克朵少年时代影响最大的三个作家:首先是巴西儿童文学巨擘蒙特罗·洛巴托,就是《隐秘的幸福》中瘦女孩特别想读的那本《小鼻子轶事》的作者;接下来是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在读了他的《荒原狼》之后,李斯佩克朵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个职业叫作作家,她想:那我也可以成为作家;最后是新西兰的女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也就是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徐志摩的密友“曼殊斐儿”。
李斯佩克朵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偶然”结缘对《隐秘的幸福》的写作有着巨大的影响。她年少时因为家贫,只能借书,无法随心所欲地购买书籍。十五岁时,她做家教,第一次挣到了钱,平生第一次萌发了想买书的欲望。突然,她无意中看到了柜台上摊开的一本书,里面有一句话立即攫获了她,使得她完全不能停止阅读,而且让她觉得:“这本书就是我的!”这便是曼斯菲尔德的名著Bliss,中文译作《幸福》。李斯佩克朵的短篇小说《隐秘的幸福》可以视为对曼斯菲尔德的《幸福》的致敬之作。在这部作品中,李斯佩克朵依然用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位穷困而瘦弱的女孩的故事,某种程度上,依然是她的自传:无钱买书的瘦女孩酷爱读书,因此备受同班的胖女孩的折辱。在胖女孩的母亲发现这一切后,瘦女孩终于拥有了书,并感受到极其强烈的幸福。
我回到家,却没有立即开始阅读。我装成没有这本书的样子,这样,待一会儿我才会大吃一惊。几个小时之后,我翻开书,读上几行美妙的文字,又把书合上,在家里转了转。我又拖延了一会儿,去吃了些黄油面包,装成想不起书放在哪里了,接着找到了它,打开它看了一会儿。为了这隐秘的东西,为了这幸福,我制造了并不存在的困难。对我而言,幸福总是隐秘的。好像我已预感到这点。费了我多少功夫啊!我生活在云端,又是自豪,又是羞愧。我是一个娇贵的女王。

黑塞《荒原狼》李雙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
对于瘦女孩,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呢?经过长久的折磨,她终于占有了这本书,也就是说,占有了“知识”。虽然与约安娜相比,“瘦女孩”占有知识的手段不是通过偷,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隐秘的幸福》依然是一篇关于“恶”与“识”的作品,更确切地说,是不同寻常的“善”与“恶”之间的故事。表面看来,胖女孩是“恶”的,瘦女孩是“善”的,两者之间是对立关系,但实际上,她们共同构成了孩童的世界,代表的是同一种欲望:渴望拥有不拥有之物。她们彼此既对立又依存:胖女孩是加害者,她施恶的起因在于嫉妒,她嫉妒瘦女孩与其同类,因为她们拥有她不拥有的东西:消瘦与一头柔顺的头发。这是一种欲望,渴望拥有不曾拥有之物的欲望。而瘦女孩是受害者,是善与无辜的象征,但受苦的原因也是因为欲望:她希望拥有胖女孩才有的那本书。最终,在胖女孩母亲的帮助下,她拥有了自己想拥有之物,内心的欲望获得了满足,认为:“我不再是一个有了书的小女孩,而是一个有了情人的女人。”李斯佩克朵通过这个结尾,将瘦女孩的欲望实现打上情色的标签,瘦女孩也因此完成了从女孩到女人的全过程。
除去胖女孩的“恶”之外,瘦女孩的“善”也很特别,这是一种具有强烈的救赎意味的“善”。瘦女孩每日到胖女孩家去报到,除去无法遏制地想要获得书籍这一原因外,也因为自愿受苦是一种具有宗教意味的牺牲。通过承受胖女孩的“恶”,瘦女孩受苦来拯救他人,而这种痛苦也是“快乐”或是“幸福”的来源。在这篇小说中,作家通过亲身的经历,又一次探讨了“幸福”的主题。“幸福”这个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那里继承来的主题,被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赋予了“隐秘”的特征:幸福本身并不具有稳定性,实际上,幸福的程度是与期待得以实现的困难程度高度相关的。幸福是一种拥有,也是一种承受。在后期的长篇小说中,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以更多的笔墨展开了对“受苦/快乐”这个主题的讨论,“幸福”这一主题得到了拓展与深化,形成了她所追求的“真实存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此时,我们可以转向对《索菲娅的祸端》的解读,因为它既涉及对知识的占有,又有“善”“恶”“识”之间的转换,而且最重要的是,涉及对于真正想做之事的庄严选择。这篇同样具有自传特点的短篇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了小女孩索菲娅的成长故事。“索菲娅”这个名字本身便承载着独特的意义,其希腊词源意味着“智慧”,并直接指向德尔斐神庙中的著名神谕:“认识你自己。”小说的核心是九岁的索菲娅与已去世的老师之间的往事。尽管老师颓唐且丑陋,但幼小的索菲娅却被他吸引。这是一种奇异的爱,表达爱的方式是破坏课堂秩序与不认真学习。索菲娅以为老师很讨厌她,然而有一天,一件事情的发生改变了两人之间的关系。老师给学生们讲了一个勤劳致富的故事,让学生们写成作文,索菲娅为了快速交差,改变了这个故事的道德主旨,将这个故事写成了一个“不劳而获”的故事,没有想到却因为丰富的想象力而获得了老师的赞赏。对于年幼的索菲娅,这个事件的发生使得她真实感受到了存在之价值以及随之而来的快乐与痛苦。而且,也让她认清了自己的使命与志愿:成为一名作家。因此,《索非娅的祸端》是一个三重认同的成长故事:认同为人,认同为女性,认同为作家。
刚才我们提到了李斯佩克朵的三位文学先师,其中一人是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大约十二岁时,她读到了《荒原狼》,获得了神秘的阅读体验。她后来回忆说:“我原以为书籍是像树木与动物一般自然生长的事物。我不知道这一切之后竟有作者的存在。读了很多故事后,我发现了这一點。我说:‘我也要当作家。”黑塞让她萌生了当作家的想法。之后她便马上写了一篇小说,但是没有完成。
《索菲娅的祸端》的书写既是对黑塞的致敬,也补足了自己年少时未完成作品的遗憾。索菲娅对于作家身份的认同依赖于对创造之“恶”的完全承认。对于索菲娅,文本,或者文学生产,所产生的后果完全出乎她的意料。索菲娅改写故事的初衷有两个:一为迅速交差,二为激怒老师,这两个理由都是恶的,而且,从伦理的角度而言,索菲娅改写后的故事鼓励不劳而获,也是恶的。但是老师却对她说“你的作文很好”。索菲娅因这句话而进入了恐惧和惶惑之中,这是一种猛醒,因为她对于“小说”或“虚构”的“邪恶与诱惑之能力”有了顿悟。这些恶之因素结出了善之果实,索菲娅与老师的身份又一次发生了互转,老师成为了诱惑者与拯救者,索菲娅成为了被诱惑者与被拯救者。“顿悟”之后的索菲娅又恢复了平静,但这种平静与顿悟之前的平静有着重大的区别。通过书写提供的诱惑,索菲娅意识到自己的“利爪”或自身的恶所能带来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使她成为了“造物之王”。以此,索菲娅完成了自我救赎,对于写作的本质与其后果具有了自觉的意识,并凭此认识到了自己的最后一个身份:作家。在这部小说的结尾处,当索菲娅感觉到在自己身上,有尖利的爪子正在生长之时,索菲娅的形象便和荒原狼重叠在一起。当那只原始而又野性的狼在她的身体里塑形时,她坚定了从事文学的志愿。
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一生中创造了无数的女性形象,在《隐秘的幸福》中,我们见识了想化装成玫瑰的女孩,偷玫瑰的女孩,为了阅读而忍受侮辱的瘦女孩,以及为了拯救老师而被老师拯救的女孩索菲娅。她们以童稚的“僭越”之恶,撬开了那扇阻隔她们认知自我与世界的沉重的大门。李斯佩克朵还创造了青年的约安娜与洛丽,中年的G. H和安吉拉,等等。这些不同年龄的女性,绝不甘心循规蹈矩,而是以“僭越”谋求真正的自由。当僭越之“恶”被引向真实,它便变成了真正的善,从而导致完全的幸福。幸福是一种拥有,也是一种承受。“幸福”不全是接受,也是施舍。当李斯佩克朵忍受着指尖里长出利刺的痛楚,写下这些文字时,她感受到了施与的隐秘的幸福。而我,将这一切传达给大家的人,也是幸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