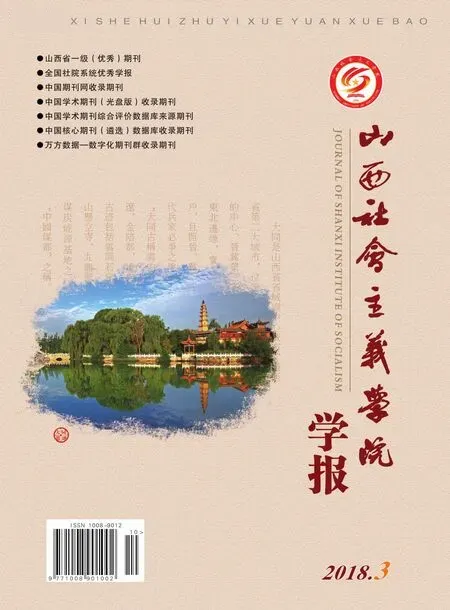王阳明乡村治理思想和实践对新时代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启示
2018-04-02黎文雯郭诺明
黎文雯 郭诺明
(江西省社会主义学院, 南昌职业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06)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今年,国家出台了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指明了方向。夯实基层基础工作是进行乡村有效治理的固本之策,是实施乡村振兴的强根之土。乡村基层民主建设关系到新时代农村工作的改革、发展、稳定全局,如何坚持走好“三治结合”的道路,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是新时代中国乡村实现社会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核心命题。历史上,无数有识之士在乡村治理方面进行过多种尝试和实践。五百多年前,王阳明受朝廷之命巡抚南赣(明朝的南赣是当时江西南安、赣州两府的合称),以其成熟的心学思想、卓越的管理才能在当地开展了一系列乡村治理改革举措,彻底改变了南赣地区的乡村面貌。他的一些经验和做法仍能为探索新时代乡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发展路径带来启示。
一、王阳明乡村治理思想和实践
明朝中叶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乡村秩序面临崩溃,江西匪患严重,尤以南赣最烈。首先,南赣地区处于我国江西省南部,属于福建、湖南、广东三省交界处,地貌以丘陵连片围绕为主要特征,该区域的原始山林自然结构相当险峻,当时自然地理条件之恶劣可见一斑[1];其次,赣南地区的地质地貌并不适宜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水利体系的兴修也存在较大困难,继而导致“靠天吃饭”的现象较为普遍;再次,土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统治阶级企图从土地上获取更大的收入,加大了对失地农民的盘剥;最后,赣南的地理区位决定了统治集团的控制力相对薄弱,政府暴力机构对该地的威慑效果十分有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王明阳巡抚赣南。他在巡抚南赣汀漳等地时深刻认识到:要想从根本上消除祸患,维护地方稳定,必须重视社会基层组织建设和加强社会道德教化的作用。王阳明通过深入民间调查走访,决定推行“十家牌法”,颁布《南赣乡约》,以保甲乡约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模式来加强地方管理,维护地方治安;推行乡民自治与政府监管双重管理制度,形成相对稳定的基层治理结构,充分发挥基层政权的作用;设乡学、兴社学,重视民间教育,教化民风,开启民智;主张“施政以德”,宽恤百姓、轻徭薄赋、赈济灾民以改善民生。王阳明在南赣治理中展开一系列乡村治理的实践与探索,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涉及社会治安、社会基层组织建设和管理、社会监督、思想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这些举措对净化社会风气、安定一方、发展社会经济建设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王阳明在南赣的乡村治理思想以“万物一体”“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哲学思想为根据,并从政治体系改革和教育系统升级两个方面开展具体乡村治理措施。
从政治体系改革层面来看,王明阳提出了蕴含着人人平等意识的具有现代民主思想萌芽的“万物一体”思想。从思想的本质角度来看,王阳明高度认可乡村自我管理的合理性,即承认乡民在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上的主体责任与平等地位。落实到实际举措中,王阳明在南赣推行乡约,设立保长,实行乡村自治组织领导的民主选举,更是非常有益和可贵的民主实践探索。习近平总书记说:“王阳明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王阳明以“知行合一”的理论来指导实践,既要求为政者不断提高自身修养,也强调人民群众的社会治理能力,这种方式减少了人民群众对为政者的依附性,提高了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能力,同时也表明了人民群众作为国之根本的重要性。以当代的视角来看,这一整套政治制度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王明阳所提出的政治体系建设思想从根本上肯定了乡村自我管理的科学性与可行性。通过民间推选的方式确定乡村治理体系具有独特价值,一般来说,被推选者一般是在当地具有一定的知识水平和经济实力,同时具有能够获得大多数人民认可的家族代表。[2]这些人一方面自身具有对家乡发展的强烈意愿,另一方面在知识与经济层面也具有与之匹配的相关能力。事实上这是此项改革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
从教育系统升级层面来看,“致良知”是王阳明对于如何破“山中贼”的体系思考,即通过对人心的治理来达到对国家的治理,强调为政者在德治中的主体性担当,公民在德治中的普遍性自觉,并强调通过“致良知”而开显“体用一源”的生命智慧以促进德治之道。在教化世人方面王阳明具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对儿童的教化是对全社会教化的重要举措,这不仅代表着未来一段时期内全体民众的教化水平,同时在对儿童的教化过程中能够潜移默化地对家庭以及家族产生显著的影响。王阳明在巡抚赣南地区时写的《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对当时的教育制度表达了担忧与不满,并直指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持拘囚”。王阳明认为当时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人性本善的培养,试图通过强制性或者惩罚性的手段来进行教育,使得儿童像囚徒一样被囚禁在学校而无法产生兴趣,这是与人性相违背的。在此基础上,王阳明结合自身的感悟与理解给出了可行的建议,认为“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提出了“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次习礼,或作课仿,次复诵书讲书,次歌《诗》。凡习礼歌《诗》之数,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倦,而无暇及于邪僻”等。[3]这些观点在当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也被现代教育制度所广泛吸取。
王阳明的南赣治理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不仅解决了南赣地区长久以来令人头痛的社会治安问题,恢复了乡村秩序,淳化了民风,并且对我国近代乡村建设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从社会学角度概括王阳明的乡村治理体系,即“把乡里体制、保甲制度同乡约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集政治、军事、教育功能于一体的乡村社会共同体,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农村基层控制体系”。王阳明基层自治思想、民本德治思想和地方法治思想对当今乡村治理、基层民主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发展历程
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是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历史发展过程。纵观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农村民主的萌芽阶段(1978-1982)。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村政策采用生产大队与人民公社制度,村民的治理以及日常劳作被紧密地连接成为一个整体,由生产大队以及公社书记等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进行领导。改革开放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大幕,原有的生产结构和权力运行架构发生了嬗变,如何实现农村集体的自我管理和自我发育成为当时急需解决的问题。1980年,广西宜山县下辖的若干公社纷纷成立了村民委员会,被公认是最早一批农村自治团体。1982年,广西宜山、罗成等地的农民自发地组织起村委会、村管会、议事会等,制订规章条约对村里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村民自治逐步形成了一定规模。
第二阶段为农村民主的宪治阶段(1982-1988)。1982年底,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的合法地位,正式确立我国农村民主自治结构的宪治阶段,即通过宪法的形式确定了此种治理模式的合法性与科学性。《宪法》第111条第一次规定了村民委员会是“群众性自治组织”,负责管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自此,我国村民自治组织的地位获得了法律上的确认。1987年11月,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该法的实施进一步规范了农村自治组织的产生方式和运作模式,使其从法律地位过渡到法律实操层面。从相关的法律角度来看,其规定了自治组织产生的基本方式、组织的基本构成、工作的一般模式与流程等基本事务,为该制度在全国范围有效推广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阶段为农村民主的发展阶段(1988-1998)。从1988年后半年起,我国广大农村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实施后,逐步开始了第一届村委会的民主选举工作。1994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通知》,要求农村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着重抓好村委会选举制度、村民议事制度、村务公开制度和村规民约制度建设。到1997年底,全国80%的村委会进行了两届以上直接选举,全国村委会建设进入规范化、程序化阶段。这一阶段,在相关法律不断细化过程中,我国村民自治组织蓬勃发展,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得到有效落实。各地的农村基层组织能积极适应国家发展需要,在政策指导下通过主动作为,为农村的发展保驾护航。这一时期,各地村委会在农资物品的集中采购、公共基础设施(含水利)的集资兴修等方面表现亮眼,使得村民看到自治组织在“管理与协调”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也使村民更加信赖和依靠农村自治组织。
第四阶段为农村民主的法治阶段(1998-2005)。1998年11月4日,在充分总结、吸收村民自治十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它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农村基层民主已经初步形成一套制度化的运作模式。截至2001年7月,全国共有23个省、市、自治区制定了《村委会选举办法》,大部分省(市、自治区)确立了村务公开的规章制度。村民自治在发展进程中,广大农村群众充分发挥聪明才智,进行多层面的机制创新,如“村民代表会议、‘海选’、‘两票制’、‘五人提名,代表预选’、村民参政议政小组等具有可操作性和合理性的村民自治机制”。这些新机制的创造与实行使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朝着良好的方向稳步推进,尤其是在具体民主法治建设上的不断探索为后续规范选举方式提供了必要的经验。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2003年,全国村务公开协调小组正式成立,对各地村务不公开、管理不民主的现象进行有效监管。2004年6月22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健全与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自此,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已经形成完善的从中央到地方、从母法(宪法)到子法(选举办法等)的全部法治建设,基层实践也能够在基本法的保障和监督下顺利进行。
第五阶段为农村民主的现代化阶段(2005年至今)。2005年以来我国农村民主治理体系多次进行微调。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内容,村民自治地位得到了重大提升。后续在2009年、2010年、2012年等年份均对相关法律体系进行逐步的完善,各地也在法律的框架下,结合本地实际不断地对自治方式进行细化,如辽宁省在2012年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办法中对集体土地、教育公共设施、自然资源等村委会行使职权的范围进行了细化;对村民大会召开的时间、频次、人员要求、通知方式进行了规定;对需经村民大会表决的事项进行了扩充;对政务公开要求进行了落实等。这一系列举措都为我国农村民主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必要基础。
三、王阳明乡村治理对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启示
王阳明在南赣的乡村治理思想和实践对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第一,以乡村多元力量观照乡村基层民主建设。王阳明在治理南赣期间,无论是推行十家牌法还是《南赣乡约》,都要依靠德高望重有影响力的公众人士及其宗族势力在地方的影响力。当代要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积极引入各方力量参与其中,培育各种类型的新乡贤,依托他们在基层民主建设中的独特作用,提高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水平。可以说,利用王明阳的基本治理理论,坚持当代基层选举制度,完善乡村的自我调节与管理,有助于构建现代和谐社会。当然,我国农村治理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面对的社会成分更为复杂,如城中村、留守村、空置村、移民村等时代性问题。[4]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基层的乡村治理所面对的是“如何办”的问题,不可能依靠文件与政策实行“一刀切”的治理方案。[5]为此,有必要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加大对乡村自治的扶持力度,鼓励新时代《乡约》《村约》的制定。村规民约以道德教化、舆论、惯例等方式,充分发挥道德在乡村基层治理中的价值作用,这将成为基层治理的一种可行模式。
第二,以乡约、牌法观照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通过梳理王阳明的地方治理思想,可以发现王阳明很注重条文规则对于人的规范作用,他制定的乡约、牌法和保甲制对基层民众的政治社会生活作了严格规约,具有约定性与强制性、自律性与他律性相统一的特征。这也是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法治建设需要着力加强的地方。通过完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相关法律条文,规范村级自治组织各项内容,对基层组织进行调节与引导,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切实保障农村基层民主工作的公正、公开,进一步推动法治乡村建设。
第三,以乡村文化教育观照农村基层民主道德建设。大力推进和普及乡村文化教育,加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这主要是解决村民对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心理认同”问题。制度功能的发挥不能单靠国家强制,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文化自然地蕴含在制度的运用之中。农村基层民主建设要求村民具有相应的政治素养,文化教育可以提高村民的现代化素质,培育符合现代民主要求的公民意识,对加强基层道德文化建设、发展新型人际关系、处理日常矛盾纠纷不无参考价值。事实上,明代的一些教育问题在当代也同样存在,甚至是更为严重。[6]如王明阳提出的“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持拘囚”,现在人们在重视知识教育的过程中并没有对德育教育引起足够的重视。针对这一问题,在教育资源进一步平衡的基础上,要形成对乡村文化教育的一体化建设,逐步将我国传统文化、社会公德、法治教育等融入基础教学,形成新的基层教育体系,培养更多的合格有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