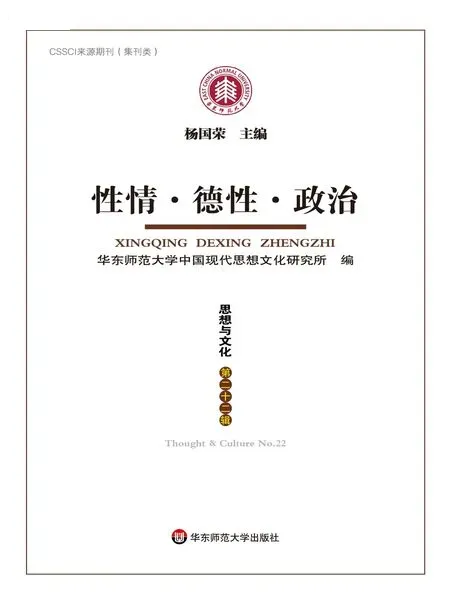怨慕 :孟子对“《诗》可以怨”的回应与转化*
2018-04-02
●
治孟学时,我们很难忽略孔孟之间的思想脉络问题。孟子自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对于他与孔子关系的“私淑”定位,孟子也明确地说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孟子·尽心上》)焦循曰“私淑艾犹私淑也”,又释其义为“未得为孔子之徒,而拾取于相传之人”。[注]焦循 :《孟子正义》,北京 :中华书局,1987年,第942页。则孟子推崇孔子且自认得孔子之教明矣。司马迁《史记·孟轲列传》言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赵岐《孟子题辞》言其“师孔子之孙子思,治儒术之道,通五经,尤长于《诗》《书》”,皆源于孟氏自述,又及孟子在经典尤其是“《诗》《书》”上的造诣。孔子极为重视《诗》,《论语》中可管中窥豹。孟子亦长于诗学,《孟子》中可见一斑。那么,孟子在经典问题,尤其是诗学问题上,是否受到孔子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性质,似有可探讨的空间。
日本学者铃木虎雄1925年初版的《中国诗论史》应是现代学术中最早讨论孟子诗学的著作,其对孟子诗学的全部论述都基于孔孟异同,他指出孟子诗学大体不脱孔门诗教,即主张诗参考政治和代用历史,唯有说《诗》方法即“以意逆志”逸出了断章取义的诗学旨趣,是其异于孔门诗教者。[注]见铃木虎雄 :《中国诗论史》,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7—29页。此外,朱东润1943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亦论及孔孟说诗异同 :同则皆以应用即就功能言诗,异者乃孔子取言喻而意得,孟子取以意逆志。[注]见朱东润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7页。言喻而意得,是言此而意彼,根植于春秋朝聘盟会的需要和断章取义的传统。以意逆志,是对诗本义的逆推和忠实,针对的是战国诗学的过度附会。二氏眼中的孔孟诗学关系大体一致,孔孟之同在于对诗的功能论的坚持,孔孟之异在于断章取义和坚持本义之别,皆未及其余。铃木虎雄和朱东润开启了以孔孟沿袭和异同入手论孟子诗学的路径,但后鲜有论此者,更遑论探讨的深化。这可能部分地基于在整个孟子文本中,孟子受孔子诗学影响的程度、性质与细节并不够明确。
我们注意到《孟子》中有关于《诗》与怨的相关讨论,而孔子曾提出“《诗》可以怨”的论断,这是两者唯一明确的相同议题。无论这种相关性是否刻意,它确然造成了孟子对孔子诗学的直接回应。如此,通过孔子和孟子对于《诗》和怨提法的个案探讨,或许我们可以更为清晰的揭橥孔孟诗学之间的沿袭与变革。
一
子曰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
传统注疏主要从三个方面解读孔子的“《诗》可以怨”。首先,孔安国的“刺上政”说揭示了“《诗》可以怨”的政治生活指向,虽然《诗》参与政治的方式变成了下对上的单向运动。其次,朱熹的“怨而不怒”说厘清的是《诗》表达怨的限度问题,其背后是对诗教温柔敦厚之义的恪守。此外,刘宝楠《论语正义》引焦循《毛诗补疏序》言 :“夫《诗》,温柔敦厚者也。不质直言之而比兴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务胜人而务感人。”[注]程树德 :《论语集释》,程俊英、蒋见元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1990年,第1212页。同样是对温柔敦厚的持守,焦循更注重“《诗》可以怨”的“微言相感”之义。简言之,以上三种诠释分别给出了“《诗》可以怨”的范围、限度、方式。那么,是否这就是孔子“《诗》可以怨”的全部含义呢?经学注疏总是受到当时的政教境域和思想取向的影响。在纵向梳理之后,我们还可以从横向的角度展开。
《论语》中“怨”出现20次,从其中对怨的使用与讨论,我们可以明了在孔子那里怨有何指。首先,孔子注意到怨的发生学问题,怨的发生几乎不可免除。孔子言“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则求不得有怨生。子又言“放于利而行,多怨”,则重利欲而怨生。子曰“不念旧恶,怨是用希”,则被恶劣对待而有怨起。子曰“劳而不怨”,“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则劳不以其法而有怨生。子曰“贫而无怨难”,则境遇悲惨有怨生。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则道德修养不够,自然会因为上述欲求的不能自洽、处境的不能自得而滋生怨愤之情。如此,境遇恶劣、欲求不得、修养不够等等人生状态的常常存在,导致了怨的发生近乎必然。其次,孔子注意到怨的特质,即怨是隐匿且不断积聚的破坏性因素。孔子有“匿怨”之说,这与《尚书》“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一脉相承。王夫之解“匿怨而友其人”言 :“有诈以成柔者 :与某人有怨矣,念不能报之,始则姑欲忍之,继则且与周旋焉,终则安之而怨隐矣……勿论其思报与不思报,当其匿怨之时,不复有生人之气矣。”[注]王夫之 :《四书训义》,长沙 :岳麓书社,2010年,第420页。怨因种种内外在因素不得不发生,却因主客观原因可能没有得以及时发泄与疏通。怨始终都有一个报的指向,怨的隐匿与报的拖延违背了感情自然生发的本性,怨的潜伏有使人非其所当是的危险。《左传》言“怨之所聚,乱之本也”,当其因长期的压抑与聚合而终报之,必然因怨愤的叠加与放大而有极大破坏性。再次,因为怨是政治与社会生活中不得不慎重面对的现象,怨的治理或“使不怨”便是重要且困难的政治和伦理活动。对孔子而言,仁的表现之一便是“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不怨天,不尤人”。不怨包含了使己无怨和使人无怨两个向度。前者是个人修身的内在要求,后者是伦理和政治生活的必然诉求。原宪问“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孔子的回答是“可以为难矣”。保持无怨的状态即使是对有志于成就君子人格的士大夫都是极为困难的事,更何况无强烈道德追求的一般民人呢?良好的政治生活要求“诸侯无怨”、“民无怨心”,这显然更为难以抵达。《左传》在引上述《尚书》之言后特意说“将慎其细也”,在怨念初起之时便审慎对待与疏导当是良策。子产就乡校议政事言 :“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从这一意义看,古人采诗亦有知民怨之生发并防微杜渐之义。
“可以”的提法,明确了“《诗》可以怨”指向一种方法论。结合“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等等关于学《诗》的说法,可见它是《诗经》应用论,对应的是朝聘盟会的礼乐制度和断章取义的诗学传统。在“《诗》可以怨”中,“可以”等同“以……可”,“可”即我们日常所谓的可以,“以”指向方式的给出,如此“《诗》可以怨”意即以《诗》的方式来对待、治理怨,当是一种可以采纳且效果有保障的治怨方式。
“《诗》可以怨”,在孔子这里,就变成了以《诗》来治理怨。这种治理的开端便是怨的抒发或宣泄。抒发或宣泄导向的结果便是无怨。如此,孔子“《诗》可以怨”从过程看是怨的抒发,从结果看是怨的消解。通过《诗》来怨,通过怨的表达实现怨的终结,是孔子“《诗》可以怨”的根本诉求。因此,怨与无怨内在统一在“《诗》可以怨”中。
“《诗》可以怨”蕴含个体怨的抒发和他者怨的展开两个向度。对保持个体的无怨状态而言,学《诗》和用《诗》使个体的怨念因同情、共鸣和感应的发生得以宣泄与疏通。这种疏通是温和无伤的,因诗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思无邪”的。《诗》自身怨念的表达是有限度的,通过《诗》的使用,个体的怨愤不再压抑和隐匿,且得以适当的发散,从而可至无怨而“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事父”同时意味着对一切家庭人伦关系(包括夫妇、兄弟诸伦)的妥善安顿,“事君”同时意味着对一切社会政治关系(即君、臣、民关系)的妥帖安置。对孔子而言,个体修养问题从来都关联社会伦理问题和政治生活问题,因此“《诗》可以怨”还有使人可怨然后无怨的维度。如何使人无怨?就庶民百姓而言,《诗》的自然生发是人情的舒展,通过《诗》的方式表达怨从而怨得以纾解。通过官方整理而返归民间的风诗之流行,怨得以节制。在这个过程中,君子通过观他人对《诗》的使用而知人间之情、人心之思,知怨而怨可息。
在孔子的“《诗》可以怨”的论断中,还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怨的“可以”是以兴和观为基础的。个人对《诗》的理解在极大程度上以兴(感发—兴起—通达)为基础。这种“兴”贯穿在孔门的所有诗学解读中,它从不拘泥于所谓的《诗》本义。子贡“始可与言《诗》”是因为他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应用到个体修身的不断进益。子夏“始可与言《诗》”是因为他的举一反三,将赞美美人动静结合美态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变成“绘事后素”的本始质朴论再变成“礼后”的伦理学解读。曾子将“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敬用到人的自我保全和孝的完成中。子路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的善德之言学到随顺泰然的生命状态。孔子从“岂不尔思,室是远而”的思念之情看到“仁远乎哉”的自修功夫。这些由此及彼的推演与会通是《诗》落实到个体道德修养的前提,正是有见于此,孔子在论及个人自我德性的成就时,采用的是“兴于诗”之说。兴是对“正墙面而立”的破除,是通路的给出。在《诗》从个体修养扩展到社会活动时,观的作用也变得重要起来。“授之以政,不达”,朱熹注为“《诗》本人情,该物理,可以验风俗之盛衰,见政治之得失”[注]程树德 :《论语集释》,程俊英、蒋见元点校,第901页。,其中“验”、“见”之说正有见于“《诗》可以观”之于《诗经》政治学的意义,观的内容自然包括观怨。“专对”作为观的结果的正确反映,自然也涵盖了对怨的觉知、应对和疏通。
简言之,在孔子这里,“《诗》可以怨”是一种《诗经》应用方法,它既用于个人的修身活动,也指向伦理生活和政治生活;人们使用《诗》来抒发并纾解怨,达成对怨的治理,怨和无怨不断生成;“《诗》可以怨”是以《诗》的兴和观的运作为基础的。在这里,《诗》是活泼泼的、运行着的经典。
二
在具体分析孟子关于《诗》与怨的表述之前,我们可以按照之前的方法梳理下《孟子》中“怨”的使用问题,由此察知《孟子》中“怨”的意义问题。[注]计《孟子》中共用“怨”25次。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孟子的大多数使用都属常规使用,即与孔子的使用几乎无别。其言“构怨于诸侯”,沿袭旧用,此怨产生于利益纠葛。其言“内无怨女”,这是习惯用法,其指向的是因无法进入常规生活而产生的求不得之怨。其言“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此为引用,此怨偏中性无褒贬,同样有求不得之意。其言“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此为常规用法;反观之,常人怨人胜己,亦基于欲求。两用“遗佚而不怨”,此用亦如前人;反之,若德性不够,不见用而怨,亦因他人对待不如期望、求不得。其就家庭生活言“劳而不怨”,就政治生活言“虽劳不怨”,先秦多有此论,孔子亦有,孟子用同。“自怨自艾”,沿袭旧用,自责之意。“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其中“宿怨”义近孔子“匿怨”。可见,孟子在怨的发生、特质和危害等认知上多与孔子相同。
其次,孟子认为怨的产生机制在于仁道原则,这是对怨之基础的思考。他说 :“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孟子·告子下》)爱之深,痛之切,陌生人的伤害与亲人的伤害相比,亲人之伤更让我们伤怀。因为我们天然地对亲人怀有亲爱之情,自然也期望亲人对我们有同等的亲爱之心。一旦现实截然相反,我之亲亲换来的是亲之不亲,怨油然而生。这里,怨念的产生与关切和期望的程度相关,简而言之,由亲亲的对等性决定。而“亲亲,仁也”,亲亲是仁的表现,由此,是否有怨基于仁的原则。亲者有怨、疏者无怨强调的是亲亲或仁之于情感构成的基础性。这与现代人的观点显然不同,一个他者无端伤害你,岂能无怨?虽然有轻重多少之分,伤害一般皆会导致怨念之起。回归到孔子的语境看,孔子在评论管仲时说,“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在被剥夺、被损害是合理正当的情况下,可以无怨,反之还是有怨的。无怨和可以无怨还是有差别的,这点容后再书。从这一点看,孟子将怨与亲亲或仁直接关联,与孔子不同。亲亲之外,孟子还说“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杀之而不怨”。这里,他以“义”作为衡量是否怨的标准,近上言孔子“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然更凸显“义”原则之于怨的意义。不义而有怨,与《小弁》章不亲而有怨有怎样的关联?杀之而不怨,并非基于亲亲,然“亲亲而仁民”,此义仍指向仁。以义为质乃是亲亲之仁向外推扩到政治生活的条件。如此,怨的产生与否仍基于仁的原则。那么,我们如何理解仁道原则及由此展开的亲疏关系在怨的发生机制中的意义呢?一个陌生人,按照仁道的遍及性,仍然是会和我发生关系的,是仁指向的对象。疏者无怨,无怨首先取决于爱有差等。“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建基于亲亲之上的仁道可以推扩乃至于涵盖一切人我关系。但基于自然天性的亲亲之义和因其合宜而展开的友好的他者关系是有本质差异的。其次,无怨也因怨自身的隐忍特性。上面我们提到孟子亦说“宿怨”,这界说了怨恨的隐忍特质。马克斯·舍勒关于怨恨的现象学描述指出,作为怨恨出发点的报复冲动有两个特点,一是对反抗冲动的隐忍,二是无能体验。对于陌生人,显然不需要因种种顾虑而刻意忍耐和压制感情的爆发。如此,如果有相关的情绪表达,不当是怨。在亲亲之怨和疏者无怨中,孟子给出了怨的正当性限度,即无怨基于亲亲关系的彻底终结,怨是对亲亲之道根本的守护。
再次,孔孟关于怨的分歧还在于,怨是否关联修养功夫。对孔子而言,无怨是个体修身的诉求与结果,并非情境的当然。“无怨”更准确的表述当为“远怨”,是始终有修身功夫在内的过程性或生成性的状态。而在孟子的表述中,不见无怨与修养的关联。怨更多的是一种现成状态的描述,他并没有区分无怨和可以无怨,这弱化了个体的道德生成和怨之间的关联。固然,他有将怨与修身关联的用法,然多是因袭之,少了怨之于成己的内在性。对孔子而言的疏者可以无怨,到孟子就置换成了疏者无怨。怨仅作为一种情绪构成,已经变成一种现成之物。因此,怨在孟子这里成了纯粹外向之物。与修养功夫相关时,无怨意味着对一切外在境遇的克服,且此克服指向自我的内在圆满。失去了修养和生成向度的无怨,则似乎更多地关注外在境遇的实显与对待的折射,于遭遇中不能得其所欲,则怨。这里并没有个体内在对怨的克服与化解。因此,怨的内在向度的缺失,意味着孟子“《诗》可以怨”的修养工夫的缺失。如此,《诗经》不再是面对自我的方式,而是面对世界的方式了,《诗经》之于我们生命的意义已经削弱了。
三
曰 :“《凯风》何以不怨?”曰 :“《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孟子·告子下》)
这里要注意的是,孟子完全是在《诗》本义与《诗》本事的意义上谈论诗篇是否有怨的,而对《诗》本义的重视必然意味着对作者和诗歌创作的关注。此两篇的本事使用当和后儒说诗有一脉相承性。《小弁》本事,按《毛诗》的说法,是“《小弁》,刺幽王也”。[注]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正义 :《毛诗正义》,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73页。朱熹《诗集传》更为详细 :“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废宜臼。于是宜臼之傅为作此诗,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注]朱熹 :《诗集传》,《朱子全书》第1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04页。按赵佑《四书温故录》的说法,高子、孟子、《毛诗》等取同种《诗》说,即太子宜臼被迫害事。[注]焦循 :《孟子正义》,第817页。《凯风》本事,《毛传》说 :“《凯风》,美孝子也。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尽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尔。”郑笺曰 :“不安其室,欲去嫁也。成其志者,成言孝子自责之意。”[注]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正义 :《毛诗正义》,第157页。朱熹等亦宗此说。亲亲之情不能对等并合乎情理地自然流转,且此亲亲的不能成就是因所亲者的不亲,是二诗共性。此不亲因具体事情和情况的差异而呈现不同的后果,似乎过大过小取决于个体遭遇的艰难程度与后果的严重程度。
何谓过大?何谓过小?似乎并无统一准则。魏源曾言 :“昔人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士庶人守一身,与天子守天下无异。论者乃谓卫母辱止于一身故小,幽王祸及天下故大,是庶人终古无大过也。”[注]王先谦 :《诗三家义集疏》,北京 :中华书局,1987年,第155页。这看似否定了以过错大小作为评判标准的合理性。然而,我们可以看看孟子给出的可以怨的典型案例。前述的“其兄关弓而射之”可以怨,因兄不念亲亲之天然而欲置弟于死地。《小弁》之怨,孙奭疏言 :“是亲之过大者,以其幽王信褒姒谗言,疏太子宜臼之亲,非特放之,又将以杀之,是以《小弁》为太子之傅作焉,而着父之过为大者也。”[注]赵岐注,孙奭疏 :《孟子注疏》,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82页。父将杀子,是其过大。在此章的最后,孟子提及舜“五十而慕”,在《万章上》的首章有相关讨论 :
万章问曰 :“舜往于田,号泣于昊天,何为其号泣也?”孟子曰 :“怨慕也。”万章曰 :“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然则舜怨乎?”曰 :“长息问于公明高曰 :‘舜往于田,则吾既得闻命矣。号泣于昊天于父母,则吾不知也。’公明高曰 :‘是非尔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为不若是契。我竭力耕田,共为子职而已矣,父母之不我爱,于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廪备,以事舜于畎亩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将胥天下而迁之焉。为不顺于父母,如穷人无所归。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忧。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忧。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贵,人之所欲,贵为天子,而不足以解忧。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
关于舜是否有怨,当然有诸多争议。传统注疏多主张舜乃怨己而非怨亲。万章亦先将舜不得其亲放在“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的类别之中。的确,在儒家经典中,面对父母的不爱、不慈、漠视、苛责乃至鞭挞,奉行孝道的君子常常是要“劳而不怨”的。《凯风》中孝子自责且不怨其母之过正是这种劳而不怨的典型表现。然而,不怨其不亲并非绝对原则。即使对于作为圣王的舜,不怨也是艰难之事,万章以“然则”发问,颇有玄机。“然”乃对前述事实或情境的确认,如果完全确证其“然”的实用性,则不当有问。“则”本应顺承而下,和“有怨”连用,却表明了万章对似乎不当有怨状态下舜亦有怨的困惑。万章“然则舜怨乎”之问恰恰证明了在“劳而不怨”的要求之下,舜仍是怨的。万章问的是 :在不得怨亲的大背景之下,作为孝道楷模的舜为何有怨?我们还是回过来看看舜面临的生存境遇,此篇第二章中的“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瞍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拚之”,第三章中的“象日以杀舜为事”都道出了其父母兄弟屡屡欲杀之的事实。“关弓而射”也好,太子宜臼也好,舜也好,都有被父母亲人杀害之虞。被杀显然是一种极端情境,这种极端意味着什么?
一般情况下,孟子说 :“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孟子·离娄上》)亲者不亲,我当自省自己有没有做好,正是孔子“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表现。这也是历代多以自责之意解读孟子“怨”的思想根源。孟子极为重视亲亲之道的施行。他说 :“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事亲是最大也是最根本之事。他又说 :“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尽事亲之道是人道之本。事亲的一个方面便是持守亲人之身。守身首先表现为养身,养身又包括养口体和养志。故而朱熹言“一失其身,则亏体辱亲”[注]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朱子全书》第6册,第347页。。《凯风》中孝子之自责当在不能养母之志,守母之身。然守身还包括自守其身,因为我们的身体来源于父母,是父母祖先身体的展开。故而孙奭言“以其守己之身为大也……所谓身安而国家可保”[注]赵岐注,孙奭疏 :《孟子注疏》,第244页。,此出自“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人皆以一身系天下,若身之不存,亲亲安能?仁道何存?“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啐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我所持守之仁义,存于我一身,通过我身而呈现、展开。一切皆以我有身为本,古人言“安身立命”无疑有守身之义。孟子曰 :“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事亲仍以诚身为本。真正的孝或亲亲之义必然建基于有身、守身、诚身之上。个人置身于死亡的威胁中,当然是亲亲之道的根本动摇。且“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身且终结,何况其后。故而杀身之境当是亲亲之道的彻底切结。《小弁》之怨的正当性正在于其对作为亲亲之道基础的守身之维护。舜不告而娶是以损害孝道的具体规定性而抵达孝之根本的方式,同样,《小弁》之怨亲正是以不亲其亲的方式对亲亲之道的根本坚守。故而舜的怨慕(有怨亲向度)恰是“大孝终身慕父母”的表现。在守身之外,是劳而不怨。如此,其亲过之大小与可怨与否的衡量准则在于是否守身。我们还可看孟子的另一表述 :
孟子曰 :“吾今而后杀人亲之重也。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知也,一间耳。”(《孟子·尽心下》)
杀人,实际上是自杀其亲,甚至自杀。孟子关于杀人的最终戒律仍落实在亲亲之道的守护之上,可谓旁证。
一言以蔽之,是否可以怨,取决于这种怨是否是对仁道的守护。破坏仁道的,可以怨,这种怨正是更为深切的亲亲或爱慕之情。在这里,孟子通过对《小弁》可怨和《凯风》不怨的比较,首先承认《诗》是可以怨的,然后展开了对“《诗》可以怨”的内在机制(亲亲之道亦即仁道)及其最终限度(对仁道的守护)的论述。
四
公孙丑问曰 :“高子曰 :《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 :“何以言之?”曰 :“怨。”曰 :“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曰 :“《凯风》何以不怨?”曰 :“《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孔子曰 :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孟子·告子下》)
在《孟子》关于《诗》怨的讨论中,我们先注意到了作为其观点对立面的高子言论。传统注疏或以高子为孟子弟子,或以其为孟子同时之齐人,或言其稍长于孟子,毋庸置疑的是,高子显然是一个坚定的儒家学者,这一点从他以君子小人之辨界说《诗经》也可确证。“高子曰 :《小弁》,小人之诗也。”很明显,高子将《诗》区分为小人之诗与君子之诗,他认为有怨之诗为小人之诗,君子之诗至少当是无怨的。问题是,就后世对《诗》本义的解读看,除了正风、正雅和颂,占《诗经》多半篇幅的变风变雅差不多都含有幽怨之情和怨愤之意。由此反观,或可能对于高子而言《诗经》多有小人之诗。高子明确的反小人立场很可能极大地削弱、撼动了《诗经》的经典地位。以有怨为小人,以有怨而否定《诗》的价值,否定怨与君子生活有关,这一切都与早前的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观点相左,从这一点看高子似乎完全没接受孔子诗学的影响。如此,对高子诗学思想的批驳,一方面捍卫了《诗经》之教,另一方面呼应和接续了孔子诗学。
通过上文对怨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孟子以“慕”作为怨的内核。我们通常会将怨落在欲求之不能满足和报复行动之不能施行的基础之上,前述舍勒的报复冲动和行为无能等亦如是。孟子将《小弁》之怨与舜之怨归于同类,并以“怨慕”来界定舜之怨,进而近乎取消“怨”而只言“慕”。他以“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终结关于《诗》怨关系的讨论,以“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结束对舜“号泣于昊天”的怨之表现的评论。这种小心的概念转换,一方面与儒家对无怨的强调和对怨的审慎戒惧有关,另一方面,恰是因为在孟子看来“慕”是“怨”之合理性的最终落脚之地。
慕从心,心为身之主。孟子曰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身具形色,英华外发,有践形之功。由此,慕虽为情感体验,然可涵养之。《说文解字》言“慕,习也”,习正是学和效的功夫。当怨慕连用,本已抛弃生成之义的怨似乎有了功夫论的加持。也因此,他反复强调慕与“五十”、“终身”的关联。慕以莫为声旁和形旁,而莫本同暮,有幽暗之义,故慕又有隐秘并于幽暗中向往光明的义项。怨同样有隐忍向度,然与慕恰为正负两端,则孟子在对怨的弱化与对慕的强调中,未始没有以慕化怨之义。慕最常理解为“思”与“爱”,朱熹言 :“慕,向也,心悦诚服之谓也。”它往往比思与爱更深刻、迫切,指向性更为明确、坚定。更值得注意的是慕自身对于推扩的内在要求。孟子曰 :“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慕可以自然推扩,因心有同然,心之所向。如果说怨强调爱之差等的话,慕使得差等之仁自然扩散。“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如果说怨更多地执着于亲亲之义的展开,慕的加入使得亲亲之义可以推扩到夫妇与君臣之义上,从而使以亲亲为基础的仁道得以遍及。也因此,孟子“怨”表面上的狭隘化问题似乎得到解决和扩张。
舜“号泣于昊天”,是感情浓烈到一定程度的不容己的宣泄抒发。《毛诗序》在谈及诗的生发之时说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舜之号泣,未始不是他的歌哭。这样情动于中的抒发,与诗同情,与诗同理。“《诗》可以怨”,以慕限定,以爱为义,也就意味着它以情为基。而通过言情之诗来抒发宣泄怨或爱,便成了孟子的“《诗》可以怨”。如此,如果说孔子的“《诗》可以怨”中怨的抒发是基于诗的温柔敦厚,那么在孟子这里,怨的抒发是基于《诗》和情的契合。
结语
孟子以“怨慕”言怨,从而孔子的“《诗》可以怨”转化成“《诗》可以怨慕”。当然,怨慕之说是否就是对“《诗》可以怨”的回应,仍有可质疑的空间。常见的“《诗》可以怨”的解释路径的转化一般都从司马迁“发愤著书”说谈起。但从孔孟关系和孔孟对《诗》的重视看,这种关联从逻辑上看相当大。而且在很多当代学者关于“《诗》可以怨”的论述中,多有以孟子《小弁》之论为证者,亦可见这种关联的可认定性。
简言之,孟子回应并转折了“《诗》可以怨”。从前文中可见,孔子的“可以怨”着眼于通过对怨的合理而有限度的抒发从而达到无怨境界,孟子则通过对怨的内在机制的揭示和界定来化怨为慕。孔子的怨以兴、观为基础;孟子的怨以《诗》本义为基础。孔子关注的是 :《诗》如何怨或我们如何通过《诗》来纾解怨;孟子回答的问题是 :《诗》是否可以表达怨及这种表达是否正当。
在孟子,怨的表达是《诗》本身的、是《诗》作者的。我们可以通过它是否合乎亲亲之义来评判它,从而无论是怨也好,《诗》也好,都只是作为对象之物存在。如此,《诗》之于我们生活、生命的切身性就削弱了。他说“知人论世”,《诗》变成了知和论的对象,而不再是感和兴的载体。这当然与战国时期礼乐生活的崩坏和《诗》经典地位的降格有关。但是,他对“《诗》可以怨”的再度承认,对孔子诗学的再度回应,使诗教再度可能,使《诗》重新焕发生命。在《诗》权威不再的情况下,这种解释和回应,使《诗》再度鲜活。由此,这种对经典的再诠释,对我们今天的经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因为我们同样是在经典濒死的状态下重建或复兴经典之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