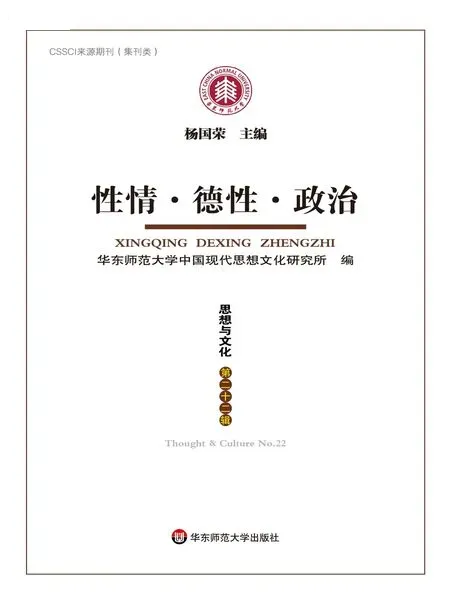因情而有义
——论斯洛特与梁漱溟的交集与分离*
2018-04-02
●
斯洛特构建的情感主义因其强调情感在道德、认识以及心灵结构中的重要性而得名。也正因为对情感的重视,斯洛特对中国哲学褒奖有加,认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哲学没有犯西方哲学割裂情感与理性的错误,在未来哲学的发展中必将发挥重要作用。斯洛特对中国哲学(儒家思想)的发掘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孟子和王阳明的思想。对于现当代中国哲学,斯洛特罕有提及。如果斯洛特将目光移到现当代中国思想界,他将会发现,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现当代中国思想家中的代表性人物更能在中西文化的冲撞比对中发现中国哲学的优良特质,他们的很多观点与情感主义有着更明显的交集。其中,梁漱溟恐怕更能被斯洛特引为知音。本文拟探讨斯洛特与梁漱溟在道德哲学上的交集,并讨论二者思想在相似背后的差异。
一、 因情而有义
梁漱溟有最后的儒家之称,在早期热衷于佛学之后,梁漱溟转向儒家,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推崇备至。他对儒家思想的解读曾被李泽厚认为是抓住了要害。在梁漱溟的眼中,儒家的道德哲学可以用“因情而有义”来概括。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或言中国哲学,其主要内容实在道德。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融国家于社会人伦之中,纳政治于礼俗教化之中,而以道德统括文化,或至少是在全部文化中道德气氛特重,确为中国的事实。”[注]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0页。主要着眼于人生问题,是中国文化的特点。而儒家思想无疑又是中国文化中最关注道德问题的。在梁漱溟看来,孔子思想的最大特点是专注于人的情感方面,这与西方文化恰成对照。“孔子两眼只看人的情感。”[注]梁漱溟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5页。引文中的黑体字是原文所有。下同。“孔子是全力照注在人类情志方面的;孔子与墨子的不同处,孔子与西洋人的不同处,其根本所争只在这一点!”[注]梁漱溟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162页。为什么要着眼于情感呢?因为伦理道德都与情感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因为有情才有道德。
梁漱溟从两个角度对儒家的伦理道德进行了解读。一是从生命的角度,另一是从社会的角度。
从生命的角度看,梁漱溟认为道德就是生命的展现与不断翻新。梁漱溟认为人类位于生物发展进化的顶端,因而能够摆脱本能的束缚,“其生命重心好像转移到身体之外:一面转移到无形可见的心思;一面转移到形式万千的社会。”[注]梁漱溟 :《人心与人生》,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页。因此,“人类生命所贵重的,宁在心而不在身,宁在群体而不在个体。”[注]梁漱溟 :《人心与人生》,第9页。
“心与生命同义。”[注]梁漱溟 :《人心与人生》,第28页。因而讲到人生,讲到道德,都与人的生命特性息息相关。生命的本性其一是生生不息。“一切生物的生命原是生生不息,一个当下接续一个当下的。”[注]梁漱溟 :《人心与人生》,第30页。、“生命本性可以说就是莫知其所以然的无止境的向上奋进,不断翻新。”[注]梁漱溟 :《人心与人生》,第32页。儒家所看重的正是这不断翻新的生命。“这一个‘生’字是最重要的观念,知道这个就可以知道所有孔家的话。孔家没有别的,就是要顺着自然的道理,顶活泼顶流畅的去生发。”[注]梁漱溟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117页。流畅生发的生命也就是不断向上翻新,能实践这一生命本性的就是道德。“生命本性就是莫知其所以然的向上奋进,不断翻新,人在生活中能实践乎此生命本性便是道德。‘德’者,得也;有得乎道,是谓道德;而‘道’则正指宇宙生命本性而说。”[注]梁漱溟 :《人心与人生》,第186页。道德就是依据生命的本性在实践中使得生命自新不已,而人的生命在这一本性之上又有其特殊性。人的生命的特殊性表现在人的生命的不断翻新是自觉的,亦即人的生命不断翻新是在人的意志指引下的不断翻新,是人主动争取而来的。由此,情感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因为,只有无私的情感才能以生命自身的自新不已为目的,除此以外别无所为。
所谓无私的情感,就是与理性(即梁漱溟所说的理智)相融合的情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谈及孔子思想的特点时,梁漱溟指出,孔子虽然是一任直觉的,但这一一任直觉是需要有一个补订,即孔子的一任直觉还需要有理智的回省。“孔子差不多常常如此,不直接一个直觉,而为一往一返两个直觉;此一返为回省时附于理智的直觉。”[注]梁漱溟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137页。换言之,在梁漱溟看来,孔子的直觉、情感都是不离理性、理智的,是与理性、理智相融合的直觉、情感。“又如孔子之作礼乐,其非任听情感,而为回省的用理智调理情感。”[注]梁漱溟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138页。听任情感,实际上是指任由情感服从于本能,因而其目的是为了利害得失而有所为的。“一切伴随本能而与之相应的感情亦皆有所为而发(从其利害得失而发)。不论其为个体,抑为种族,其偏于局守一也;则其情谓之私情可也。”[注]梁漱溟 :《人心与人生》,第64页。梁漱溟与通常的观点大异其趣。一般认为为自己的是私,为他人、为群体的是无私,是公。而在梁漱溟看来,所有一切为了利害得失的都是私,只有那种超越了利害得失的才能称之为无私。“若求真之心,其求真就是求真,非别有所为者,虽不出乎两点方向,却与利害得失无涉,我们因谓之无私的情感。”[注]梁漱溟 :《人心与人生》,第64页。无私的情感何以产生?因为有了理智的发展。理智的特点是反乎本能,人类与其他生物的一大区别就在于人类的理智发达。而“理智的发展却又是越出两大问题之外不复为其所纠缠的;尽管事实用心在应付和处理问题,却可不受累于任何问题。所谓不受累于任何问题,即不以任何利害得失(诱惑、威胁)而易其从容自主自决之度也”。[注]梁漱溟 :《人心与人生》,第63页。这一由理智调理的情感,或言之与理智相融合的情感,即是无私的情感。“当人类从动物式本能解放出来,便得豁然开朗,通向宇宙大生命的浑全无对去;其生命活动主于不断地向上争取灵活,争取自由,非必更出于有所为而活动,因它不再是两大问题的机械工具,虽则仍必有资借于图存与传种。原初伴随本能恒必因依乎利害得失的情感,恰以发展理智必造乎无所为的冷静而后得尽其用,乃廓然转化而现为此无私的情感。”[注]梁漱溟 :《人心与人生》,第64页。这种超乎利害、与理智的发展相联的情感,是“人类之所以伟大;而人心之有自觉,则为此无私的情感之所寄焉”[注]梁漱溟 :《人心与人生》,第64页。。梁漱溟有的时候直接将它称作“理性”。此一理性实即情感,也就是所谓的“情理”。
由上可见,无私的情感的特性在于“它恰是主宰而非工具手段”[注]梁漱溟 :《人心与人生》,第12页。。无私的情感使得人能以自身的不断向上、不断翻新为目的,将自己的生命活动置于自己的主宰之下,正是由于无私的情感的这一特性才使得人的生命的不断翻新是人的自觉活动。“行止之间于内有自觉(不糊涂),于外非有所为而为,斯谓道德。说‘无所为而为’者,在生命自然向上之外,在争取自由灵活之外,他无所为也。体认道德,必当体认‘廓然大公’,体认‘无私的情感’始得。”[注]梁漱溟 :《人心与人生》,第190页。
从社会层面说,人是群体、社会的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质是情感关系,因此,伦理道德、义务是因情而有的。
“孤单的个人是不可想象的。人只有在社会生活中才有可能;社会是人作为人的存在所必需的形式。”[注]梁漱溟 :《人心与人生》,第95页。生活与社会之中的人,也就是生活在与他人的关系之中,此即人伦。传统的人伦偏于人对人的关系,梁漱溟扩充了传统的五伦,将所有相互依存的关系都称为人伦,由此,个人与集体、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也属于人伦。有人伦,即有人伦应遵从之理,即伦理。“既然同是在生活上相互依存的两方就同属于伦理,都有彼此顾及对方,尊重对方之义。都有道德不道德问题。”[注]梁漱溟 :《人心与人生》,第193页。那么,伦理从何而来呢?对于这一问题,梁漱溟非常明确地肯定,伦理即情谊。人们之间关系的根本在于相互之间的情感关系,亦即他所说的相与之情。“一个人的生命,不自一个人而止,是有伦理关系。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注]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第121页。为什么伦理关系是情谊关系呢?这与情感的一个特性密切相关。理智与情感(理性)具有不同的特点。理智的一大特点是分别。“我看了近代西洋人——他们恰是以理智胜——由其所谓‘我的觉醒’以至个人主义之高潮,虽于其往古社会大有改进作用,但显然是一种离心倾向(对社会而言);使我体会到明晰的理智让人分彼我,亦就容易只顾自己,应当不是社会的成因。”[注]梁漱溟 :《人心与人生》,第10页。而情感则具有连接、联通的功能,它是使人与他人、万物连接为一体的关节与纽带。“人与人之间,从乎身则分隔(我进食,你不饱),从乎心则虽分而不隔。……人类生命廓然与物同体,其情无所不到。凡痛痒亲切处就是自己,何必区区数尺之躯。惟人心之不隔也,是以痛痒好恶彼此相喻又相关切焉。”[注]梁漱溟 :《人心与人生》,第84页。
既然伦理关系是人们之间的情感关系,那么,人们对他人的尊重、照顾之义都源于情。“吾人亲切相关之情,发乎天伦骨肉,以至于一切相与之人,随其相与之深浅久暂,而莫不自然有其情分。因情而有义。父义当慈,子义当孝,兄之义友,弟之义恭。夫妇、朋友乃至一切相与之人,莫不自然互有应尽之义。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即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伦理之‘理’,盖即于此情与义上见之。”[注]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第72页。在这段文字中,梁漱溟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观点,伦理道德产生于人们之间的情感关系,是由人们相互之间的情感关系所决定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道德要求都产生于此。情与义几乎可以说是同义的。所谓道德也就是对情与义的实践与发扬光大。“所贵乎人者,在不失此情与义。‘人要不断自觉向上实践他所看到的理’,大致不外是看到此情义,实践此情义……不断有所看到,不断有所实践,则卒成所谓圣贤。”[注]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第121页。
二、 斯洛特与梁漱溟的交集
斯洛特的情感主义发轫于道德情感主义,始于其著作《出于情感的道德》。经由《关怀伦理学与感同身受》和《道德情感主义》,斯洛特道德情感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基本完成。斯洛特的道德情感主义以感同身受的心理机制为核心,阐明了利他的行动是如何在对他人的情感、感受的感同身受中实现的。而同样借助于感同身受的心理机制,人们形成了对某些行为的赞成与对某些行为的不赞成,这也就是人们对行为的道德判断。“感同身受是道德的生活的所有这些方面的关键,这是我把它称作道德世界的纽带的主要意思。”[注]Michael Slote, Moral Sentimentalism,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3.简而言之,道德的行动是出于情感的,善与恶的概念、道德判断等莫不基于情感。斯洛特的这些主张如果要一言以蔽之的话,似乎也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因情而有义。
由此可以看出,斯洛特与梁漱溟在道德哲学最根本的问题上有着极为相似的观点,他们在伦理学上也就存在着较多的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道德是一任直觉而非诉诸理智的。既然道德是出于情感的,那么道德自然不需要依赖于理智。道德既不需要如康德所认为的那样需要诉诸理智,也不需要像功利主义那样诉诸计算。“我们人的生活便是流行之体,他自然走他那最对最妥帖最适当的路。他那遇事而感而应,就是个变化,这个变化自要得中,自要调和,所以其所应无不恰好。”[注]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121页。“美德要真自内发的直觉而来才算。”[注]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126页。而且,由于理智是分别人我、分别物我的,且是计算、计较的,因而道德与理智是不相容的。“最与仁相违的生活就是算账的生活。所谓不仁的人,不是别的,就是算账的人。仁只是生趣盎然,才一算账则生趣丧矣。”[注]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129页。在这一问题上,斯洛特有着相似的观点。斯洛特认为人的道德行动是出于利他的动机的,而这一利他的动机来源于对他人的情感的感同身受。因此,道德的行动是与理性的思考无关的。“如果仁慈意味着(本能地)关心他人的福祉并且不要求仁慈的人使用特定的道德理论和原则以解答道德问题(这是休谟将仁慈称为自然的动机的部分原因),那么人们会问为什么仁慈的人需要诉诸道德理论、原则或怀疑自己行动或动机的正当性,而不是仅仅是去帮助他人。”[注]Michael Slote, Moral from Motive, p.41.斯洛特多次使用了伯纳德·威廉斯的“想一想都太多”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一个丈夫在妻子和陌生人同时掉进水中,都面临着淹死之危险的情况下,一个“好”的丈夫会自然而然地、不假思索地救妻子而不是救陌生人。一旦他在行动前需要诉诸道德原则,去思考他应该在救妻子和救陌生人中如何进行选择的话,他就不是一个“好”的丈夫。而且,斯洛特也像梁漱溟那样,认为不去为自己的行动做理性的辩护,恰是显示了道德的意义。“我认为我们道德地行动,而没有诉诸理性和/或自我利益的术语对我们所做的进行辩护,这一事实表明我们认为道德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如此重要以致某事是否在自我利益方面对我们有帮助这类重要的事情被弃置一旁。”[注]Michael Slote,From Enlightenment to Receptivity : Rethinking Our Values,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123.
二、 道德是相对的。道德是生命的不断翻新,而生命又是活泼流动、生生不息的,因此,道德自然也就无绝对,是相对的。“我们人的生活便是流行之体”,流行变化的生活遇事不是诉诸确定的原则,而是随感而应的。“他那随感而应,就是个变化。”[注]梁漱溟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123页。基于这一理由,梁漱溟反对将道德理解为好的习惯,因为“一有习惯就成了定型”,就会“拘碍流行,淹滞生机”,而“害莫大于滞生机,故习惯为孔家所必排”。[注]梁漱溟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126页。而只有一任直觉,才是“活动自如,日新不已”的。而就伦理而言,义务都是相对于关系而言的,离开了关系,也就无从谈及义务。“不把重点固定放在任何一方,而从乎其关系,彼此相交换;其重点实在放在关系上了。”[注]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第84页。从关系而言义务,义务也就是相对于关系而言的,没有所谓绝对的义务。“根本不应当定义客观标准令人循从。话应当看是谁说的,离开说话的人,不能有一句话。标准是随人的,没有一个绝对标准。此即所谓相对论。相对论是真理,是天下最通达的道理。中国伦理思想,就是一个相对论。”[注]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第84页。斯洛特虽然没有直接论及道德是相对的,但是,对理性主义的拒斥使斯洛特实际上也反对普遍的、绝对的道德,他同样认为道德义务感的强烈与否、对他人关心程度的大小是和对象与能动者之间的关系亲疏远近相关的。人们对于在自己眼前落水的儿童有一种强烈的救助义务感,而对于遥远的国度因遭受饥荒而生命垂危的儿童,人们的义务感则要淡得多。
三、 道德既然是因情而有义的,那么,我们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是善的,关键是看动机而非结果。从不计较的态度可以很自然地得出孔子不注重行为的结果而只看动机的结论。梁漱溟引用胡适的话来说明这一点。“儒家只注重行为的动机,不注重行为的效果。推到了极致,便成董仲舒所说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只说这事应该如此做,不问为什么应该如此做。”[注]梁漱溟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127页。胡适的态度是倾向于墨子,而梁漱溟则认为孔子代表了中国,而墨子则代表了西洋。斯洛特的道德哲学同样是从动机的角度来界定道德行为的。出于利他情感的行为是善的,而不关乎这一行动最终的结果如何。“德性论聚焦于有德性的人和那些使他有德性的内在特征、性情和动机。”[注]Michael Slote, Moral from Motive, p.4.一个人是否是有道德是根据其内在的动机、品格来判断的。同样,一个行动是否是正当的,也要由动机来衡量。“当且仅当它是出于好的,或与仁慈或关心(他人的福祉)有关的、有德性的动机,或者至少不是出于坏的,或与恶意或对人性冷漠的低劣动机时,行动才是道德上可接受的。”[注]Michael Slote, Moral from Motive, p38.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斯洛特的道德哲学不看重实践智慧,因为实践智慧是关于如何做,如何达到好的结果的,而这无疑是与一个行动是否是善的无关。出于善的动机的行动如果带来了好的结果固然好,如果它没有带来好的结果,也无损于它是善的。
四、 伦理道德是利他。在梁漱溟看来,伦理道德主要是一种义务。情感具有的一种特质,是“人在情感中,恒只见对方而忘了自己”[注]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第80页。,所以在情感关系中,“在母亲之于儿子,则其情若有儿子而无自己;在儿子之于母亲,则其情若有母亲而无自己;兄之于弟,弟之于兄,朋友之相与,都是为人可以不计自己的,屈己以从人的。他不分什么人我界限,不讲什么权利义务,所谓孝弟礼让之训,处处尚情而无我”[注]梁漱溟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145页。。因情而有义的伦理道德因此也就主要是对他人的义务。“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各负有其相当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他有伦理关系之人,亦各对他负有义务。”[注]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第73页。一言以蔽之,“伦理关系即表示一种义务关系;一个人似不为其自己而存在,乃仿佛护卫他人而存在着”[注]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第81页。。那么,是否中国文化与权利观念就不相容了呢?梁漱溟并不这么认为。梁漱溟认为权利的本义是正当合理,与中国人所推崇的并没有什么两样。不同的是,西方的权利是自己主张的,中国人的权利则体现在他人对自己的义务之中。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表现在父母“我应给你们相当教育”的义务之中。“各人尽自己义务为先;权利则待对方赋予,莫自己主张。这是中国伦理社会所准据之理念。而就在彼此各尽其义务时,彼此权利自在其中;并没有漏掉,亦没有迟延。”[注]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第83页。在将道德看作是利他的这一问题上,斯洛特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据梁漱溟的观点,利他主要是从人伦角度而言的。如果从道德是生命的不断向上翻新这一角度来看,道德是可以将人自身的完善纳入其范围的。而在斯洛特看来,道德就是利他。“道德的(善或者体面的)生活依赖于我们利他地考虑他人并避免做伤害他们、对他们不正义的事情。”[注]Michael Slote, Moral Sentimentalism, p.14.斯洛特在构建了他的道德情感主义的理论体系后,就放弃了他还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时所持有的观点,即道德是我他对称的。出于情感动机的道德与利他是同义的。其根本原因在于感同身受的心理机制只能是对他人情感的感同身受,并由此而产生利他的动机与行为。对自己的感受、对自我利益的考量与感同身受这一心理机制无关。这样一来,自我的完善与发展也就被排除在道德的范围之外。
五、 道德不是不偏不倚,而是有差等的。道德、义务有亲疏远近之分。人的情谊关系最亲近的是骨肉之情,由是道德也以孝悌为本。“孝弟实在是孔教唯一重要的提倡。他这也没有别的意思,不过他要让人作他那种富情感的生活,自然要从情感发端的地方下手罢了。人当孩提时最初有情自然是对他的父母,和他的哥哥姊姊,这时候的一点情,是长大以后一切用情的源泉,绝不能对于他父母家人无情而反先同旁的人有情。《论语》上‘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一句话,已把孔家的意思说出。”[注]梁漱溟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134—135页。在这一方面,斯洛特的观点也极为相似。斯洛特认为直接性与能否感同身受以及感同身受的强度密切相关。直接性分为两种,一种是空间上的直接性,一种是时间上的直接性。斯洛特则认为,当一个儿童在我们面前即将落水时,我们感到的救助义务感要远远强于救助遥远国度的饥饿儿童。其原因是,具有空间上直接性的对象,更容易通过我们的感官对我们产生影响,我们对它们更容易感同身受。斯洛特又将空间上的直接性称为知觉上的直接性。“我们所感知到的需要的直接性或生动性使人的感同身受更深或更有力。”[注]Michael Slote, The Ethics of Care and Empathy, New York : Routledge, 2007, pp.23-24.除了空间上的直接性以外,斯洛特认为直接性还体现在时间上,即在时间上离我们近的对象比在时间上离我们远的对象更能被我们感同身受。“知觉的和时间的直接使得人们对处于困境中的人们有更强的感同身受,并且与我们提供援助的义务感的强烈程度相关。当某人的难题是看不见的,并且/或者是在遥远的未来,它好像,或在隐喻意义上,要比那些我们知觉范围内并且/或者正在影响我们的难题离我们更远。”[注]Michael Slote, The Ethics of Care and Empathy, p.26.除了时空上的接近或直接能影响感同身受以外,斯洛特认为关系的亲疏远近也是影响感同身受的一个重要因素。人际关系上的亲近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朋友和伴侣,另一类是家庭。关系亲近的人之间更能感同身受。“朋友和夫妻分享价值观、活动和经历,这使得相互间的感同身受比陌生人之间更加容易且深入。”[注]Michael Slote, The Ethics of Care and Empathy, p.26.概而言之,人们更愿意帮助、关心与自己关系亲近的“dear”或“near”,而对于那些与自己关系疏远的人,对他们的关心与爱则要淡得多。
三、 东西学术分途
当中西文化与思想发生碰撞交流时,对两种文化或者其中的一些思想进行比较,以发现各自的优劣以及是否存在、存在多少共同语言是在所难免的。中西比较的意义与价值自不待言,但在比较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却值得注意。其中的一个问题是有些时候人们会因为两种不同的思想间存在着一些相似或共同点,就断言这两种思想是相似的或相通的。曾几何时,有人将诸子百家分别贴上了西方语言学派的不同流派的标签。在斯洛特的道德情感主义逐渐为国人所知后,也有论者因此给孟子贴上了情感主义的标签。原来曾广泛被用西方的理性主义来比附的儒家思想,突然转而成了与之对立的情感主义。这不禁让人思考到底应该如何比较中西文化或思想,是要从整体框架上进行比较,还是从一些观点、结论上进行比较?这一问题恐怕不是一个新问题,在中西文化发生碰撞以后,人们就面临这一问题并给出了不同的回答。梁漱溟在当时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冲突的情况下,对这一问题有着自己的回答。在梁漱溟看来,中西文化是两种异质的文化,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就分别了中西文化。“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注]梁漱溟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58页。“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注]梁漱溟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59页。中西文化的不同是根本路向上的不同。“中国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条路线。”[注]梁漱溟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67页。由此,中西文化在形而上学、人生态度等问题上有着根本的区别。在《人生与人心》中,梁漱溟依然坚持这一观点,认为东西学术是分途的。“向外致力、向内致力只是东西古今学术界大端风气有分殊。”[注]梁漱溟 :《人心与人生》,第131页。那么,这是否就是说中西文化、思想间不可能有相似之处呢?当然不是这样。问题的关键是要看这些相似是根本问题框架、根本路向上的相似,还是某些具体观点上的相似。如果仅仅是一些具体观点上的相似,那么是不能因此而判定两种思想或文化是相似的。对于这一问题,梁漱溟说得很清楚。“大家总有一个错误,在这边看见一句话,在那边看见一句话,觉得两下很相像,就说他们道理可以相通,意思就是契合了。其实一家思想都是一个整的东西,他那一句话皆于其整的上面有其意思,离开整系统则失其意味;若剖析零碎则质点固无不同者,如果不是合成整的,则各人面目何其从见?”[注]梁漱溟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118页。如果双方在根本问题与路向上存在相似之处,就可以认为二者是相似的。基于这一原因,梁漱溟没有断言中西文化不同的思想间就不可能有路向上的相似,他曾认为柏格森也窥见了宇宙奥秘,只是所见不深罢了。
如果梁漱溟所言不虚的话,那么,我们似乎就不能因为上文所列举的斯洛特与梁漱溟思想之间存在的种种相似之处,就得出他们之间道理相通的结论来。我们固然可以看到,梁漱溟在与西方文化重理智的对比中,清楚明白地得出中国文化专注于人生之理,而人生之理是情理的结论。他的这一结论可以说要比以往的儒家都更为清楚明白地突出了情感的地位与作用。这一点从表面上看,似乎和斯洛特极为相似,但是在这表面的相似这下,我们也要看到斯洛特与梁漱溟实际上也存在着许多根本性的区别。梁漱溟道德哲学的逻辑起点是人的生命。基于生命的特性,道德是人生命的肯定、生长与实践。社会生活中的人生则是处于人伦关系之中的,伦理也就是人伦情谊之理。而在斯洛特那里,这一深层的背景是没有的。斯洛特既没有将道德与人的生命联系在一起,也没有将人理解为社会的人。斯洛特构建其道德哲学的核心基础是感同身受的心理机制。在理论的出发点上他无疑要比梁漱溟狭窄得多。二者在理论根基上的不同导致了他们在很多问题上存在着差异。人的生命是活泼生动的有机整体,是融合了知情意的。情感与理性并非是分离对立的,而是融合在一起的。既不能离开了情感来谈理性,也不能离开了理性来谈情感。而斯洛特的情感主义是西方理性主义的反动,他所要做的是,将理性主义建基于理性之上的道德大厦颠覆为建基于情感之上的道德大厦。但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斯洛特构建道德情感主义的思路是在分别了情感、理性的前提下,突出情感的重要性,并通过论证原来被认为是纯粹理性的领域其实是有情感因素或与情感相关的,以此来批评理性主义。例如,在认识论领域,斯洛特的工作主要是要论证原来被认为是纯粹理智的、与情感无涉的认识过程——梁漱溟也认为西方文化中的认识论是理智的活动,是与情感无涉的——是与情感密不可分的。“我想要论证的是与感同身受相关的情感和/或感情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根本性的部分。”[注]Michael Slote, From Enlightenment to Receptivity : Rethinking Our Values, p.65.换言之,斯洛特在构建其理论体系时,他所说的情感是与理性分立的,他的情感主义与理性主义恰成两极。从这一角度来看,斯洛特的道德情感主义还是在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框架中展开的。而儒家思想则是与之不同的另一种路向。这种路向上的不同使得梁漱溟与斯洛特的一些相似之处也只能是差异中的相似。例如,儒家的爱有差等是基于人与人、人与群体关系的亲疏远近而来的。而斯洛特的爱有差等则是基于感同身受的心理机制所产生的亲疏远近而来的,虽然结果都表现为有差等的爱、关心,但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却不相同。
但是,斯洛特与儒家、梁漱溟的不同却并非不可弥合。因为斯洛特在构建其理论体系的过程中,逐渐走向了主张理性与情感融合的路向。将道德建基于情感之上,需要用情感来说明道德判断、道德原则的产生,其结果必然会认为情感与理性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离“情感与理性本来就是融合的”只有一步之遥。在对启蒙的批判中,斯洛特所采取的方法是论证理性中本来就蕴含着情感的因素,这实际上已经走向了情感与理性的融合。基于这一发展的逻辑,斯洛特在近两年开始转向中国哲学。其原因正是在于中国哲学不刻意区分理性情感的特质。“儒家以及一般意义上的中国思想家没有像西方思想家那样很自然地从概念上区分认知和情感。”“与中国哲学家没有将人类心灵截然二分为认知与情感的作法相应,儒家传统也没有像康德或亚里士多德那样单纯从理性出发研究伦理学。”“中国从来没有像西方那样以一种不健康的、至少是受蒙蔽的方式贬低情感。”[注]迈克尔·斯洛特 :《重启世界哲学的宣言 :中国哲学的意义》,刘建芳、刘梁剑译,《学术月刊》,2015年第5期。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斯洛特开始对中国哲学中的阴阳概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近年来,古代中国阴阳所具有的既区别又互补的关系还没有引起伦理学家们的足够重视。笔者以为这种忽视是不幸的,需要予以补救。我们所有人——比如,中国和西方哲学家——都应该认识到互补性对于阐明伦理问题的巨大潜力。”[注]迈克尔·斯洛特 :《现代伦理意义下的“阴阳”概念再认识》,郭金鸿译,《齐鲁学刊》,2015年1月。
一旦斯洛特的这一发展路向得以进一步推进,无疑他与中国哲学的相似就开始更多地是神似而非形似。这样的话,斯洛特似乎也可以归属于梁漱溟所说的窥见了宇宙奥秘的西方思想家中的一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