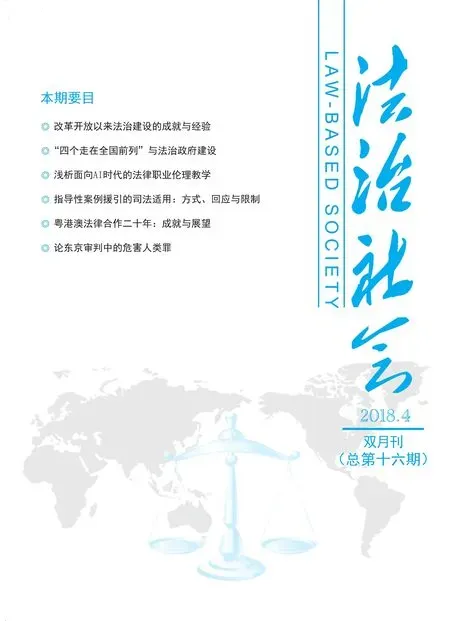特免、恶意和意图
2018-04-02霍姆斯著
[美]霍姆斯著 姚 远 译
内容提要:一旦证明被告的行为结果给原告造成现时损害,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被告能否预见该结果。此处涉及的恶意、意图、过失均指向外在标准或通常经验。特免是被告在明知的情况下施加被指控损害的主要免责理由。但是否准予特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准予特免,则属于政策问题。一旦面对政策问题,我们会发现无法经由一般命题作答,而必须根据案件的特殊性加以判定,即便人人均就应然答案达成共识。虽然不打算罗列或者概括应予考虑的所有事实,但显然要把结果的价值 (或曰准许作出该行为所得到的利益)同它造成的损失做一番比较。因此,结论将根据事情的性质而取决于不同的理由。对于诸多生活利益的体验,教给人们各种政策观点。生活利益都是斗争场域。无论作出什么样的判决,都必定有违一方当事人的愿望和意见,作为判决基础的各种区分将是程度的区分。并不试图证成特定学说,只是要分析据以形成法律判决的一般方法。
目前施行的侵权法已经基本上形成一套一般理论。下面我将稍稍总结该理论的第一部分。人们就现时损害 (temporal damage)提起侵权诉讼。法律承认现时损害是一种恶果,并在合乎下文提及的那些最重要考虑因素的范围内,致力于防范或补救这种恶果。一旦证明被告的行为结果给原告造成现时损害,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被告能否预见该结果。如果通常经验 (common experience)表明,某种此类结果在行为人的已知情况下,很可能随着该行为而发生,那么该行为人就被判定为知情(with notice)而为,①“notice”(知悉;知情)指某人已获得通知的状况,无论其实际是否知道。它与 “knowledge”(明知)有所区别,明知即实际意识到某一事实状况,而知悉仅指有理由意识到某一事实状况。——译者注因此被判定承担法律责任,除非他按照我已经提及和稍后提及的那些特定理由进行开脱。此处所适用的是外在标准,其中恶意、意图、过失这三个词也指向外在标准。如果损害的概然性极其显著并且损害随之发生,那么我们就说这是出于恶意或故意;如果损害的概然性并不极其显著但仍然相当大,那么我们就说这是过失致害;如果表面看不出致害危险,我们就称之为不幸。
再者,鉴于行为责任仅仅取决于它的概然后果,假如概然性的程度足以引起被告的合理警觉,则行为责任通常不受概然性程度的影响。换言之,就足以引起被告合理警觉的目的而论,该行为之被称为出于恶意抑或出于过失,一般说来无关紧要。就初步推定侵犯或书面诽谤而言,如果对原告人身施以强力或者使其遭受蔑视的可能性,达到前述过失一词所表达的程度,那就不需要达到更高程度了。例外也是有的,至少在刑法中是这样。明知情况下的危险程度可以区分谋杀和一般杀人。②Bigelow,Fraud,117,n.3;Commonwealth v.Pierce,138 Mass.165.试比较Hanson v.Globe Newspaper Co.,159 Mass.293.但规则如我所述。对于前面谈到的一般原则,我想不必进一步论证了。③See The Common Law,ch.2,3,4.
不过,明显危险程度这一简明尺度并未穷尽侵权理论。在某些案件中,一个人不对极为明显的危险承担责任,除非他确实意图作出被指控的侵害。在某些案件中,他甚至可能意图侵害而仍不用为此承担责任;按我的想法,至少在后面这类案件中,实际的恶意可能使他承担责任,而没有实际恶意的时候就不必承担责任。这里我所谓恶意是指行动的恶毒动机,而不虑及由意图侵害他人所导致的远期获利的希望。④See Rideout v.Knox,148 Mass.368,373.此种意义上的恶意是否影响到被告权利和责任的范围呢?这个问题已经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比如众所周知的以某种明显有害于邻人的方式使用土地。联合抵制以及出于或多或少类似目的的其他联合行动,也涉及这个问题并使其凸显出来,尽管在此类案件中所施加的损害只是手段而已,并且所寻求达成的目的通常是被告的某种获利。但在讨论该问题之前我必须考虑,撇开行为恶意问题不谈,一个人在上述案件中基于何种理据免责。
你们会注意到,假定我们已经越过了外在标准这一尺度所回应的问题。被告行为的明显倾向就是对原告造成现时损害,这一点不存在争议。总地来说,结果是预料之中的,而且至少常常是有意的。冒出来的第一个问题是:若这名被告就此而论不用承担责任,理据何在?如下老生常谈向我们提示了答案,即假如没有正当理由,蓄意施加现时损害的行为 (或者某种明显可能造成现时损害并且也确实致人损害的行为)就是可诉的。⑤Walker v.Cronin,107 Mass.555,562;Mogul Steamship Co.v.McGregor,23 Q.B.D.598,613,618.如果法院认定被告的行为出于正当理由,那么被告免责。证成理据可谓五花八门。此类情况下的证成理据是,被告具有在明知的情况下施加被指控损害的特免 (privileged)。
但是否准予特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准予特免,则属于政策问题。政策问题乃是立法问题,法官羞于将此类理据作为推理的出发点。于是,各种支持特免或反对特免的判决,虽然明明只能立足于此类理据,却常常表现为依据空泛的命题——例如,不得以损害他人的方式使用自己的财产 (sic utere tuo ut alienum non laedas),这不外乎教导人们心怀仁义——得出的空洞演绎,抑或所作出的那些判决仿佛本身蕴含着法律的先决条件,并且不容进一步的推演,比如判决有云,尽管存在现时损害,但 [被告]没有不法行为;而要查明的事情正是有没有不法行为,以及如果没有的话理由何在。
一旦面对政策问题,我们会发现无法经由一般命题作答,而必须根据案件的特殊性加以判定,即便人人均就应然答案达成共识。我不打算罗列或者概括应予考虑的所有事实;但显然要把结果的价值 (或曰准许作出该行为所得到的利益)同它造成的损失做一番比较。因此,结论不是千篇一律的,将根据事情的性质而取决于不同的理由。
例如,一个人想在小村子里面开办一家商店,而这个村子只能支撑得起一家这样的商店,尽管他预料到并且有意击垮当地一名亟需扶助的寡妇正在经营的商店,他依然有权开办自己的商店。他有权在自己的土地上建一座房子,尽管其位置会遮挡附近一座远为昂贵的房子的视线。当有人向他打听一名仆人的情况时,他有权如实作答,尽管他意图以此妨碍该仆人的出路。但这几种特免的理由是不一样的。第一种特免取决于一条经济学假定,即自由竞争对于社会来说利大于弊。第二种特免取决于如下事实,即必须在相邻所有权人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划定界限,而这必定限制每个人的自由;⑥See Middlesex Company v.McCue,149 Mass.103,104;Boston Ferrule Company v.Hills,159 Mass.147,149,150.也取决于不可避免的市侩品味,它在考虑整个片区内土地的最有利可图的运营方法时,认定用处优先于美观;也取决于被告实际上并未逾越自己的边界;还取决于稍后提到的其他理由。第三种特免取决于如下命题,即在某些情况下且在某些界限内,自由获取信息的益处超过了偶然不幸者遭受的损害。我不知道是否有人适用该原则来支持仆人品评主人的情形。
是否存在特免,以及特免的范围或程度,都会随着案情而变化。人们在谈到某些特免时仿佛那些特免是绝对的 (套用一下口头诽谤中的常用语)。例如,撇开制定法上的例外情形不谈,在任何普通情况下,改造自家土地或者在自家地里捣腾新花样的权利,不受此类做法的动机影响。如果采用相反的学说且将其推至逻辑极端,那就有可能因为陪审团裁决认定恶意运营而拆除一处昂贵的仓库,由此造成大量劳动的浪费和损失。即便法律不走到这样极端的地步,鉴于该建筑物的运营动机可能发生改变,问题将始终悬而不决。兴许另有其比这里提到的理由和前述理由更好的理由,或者这些理由可能不充分。⑦See 1 Ames&Smith,Cases on Torts,750,n.我并不试图证成特定学说,只是要分析据以形成法律判决的一般方法。
因此人们现已认为,一个人如果租用 [身为地主的]原告的房子或者与原告交易时,拒绝雇佣某个 [佃户],是有绝对特免的。⑧Heywood v.Tillson,75 Me.225;Payne v.Western&Atlantic R.R.,13 Lea,507.See Capital&Counties Bank v.Henty,7 App.Cas.741.在此要平衡如下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不予缔约的无限自由所带来的益处,另一方面是以特定方式行使该自由所可能造成的损害。
重要的是注意到,这里的特免不是一般性的 (即恶意拒绝与原告缔约),而是针对所运用的特定手段。不论是出于恶意,即为阻止他人与原告缔约,抑或出于其他无伤大雅的动机,被告本人都有拒绝缔结某种契约的特免。更重要而且更为切中本文宗旨的是,尽管有诸多相反的一般表达,结论却并不基于如下抽象命题,即恶意并不能使人对一种在其他场景合法的行为承担责任。据说倘若并不如此,那么一个人就会因其动机而受到指控。但这一命题和下述命题一样并非不证自明,即对于行为发生之时的情况的认识并不能影响责任,否则一个人就会因其认识而受到指控——该命题显然是错的。严格来说,人的意识状态对于其责任而言总是具有实质意义;当我们考虑一个人在有意对邻人造成金钱损失方面具有多大程度的特免时,我们会发现在某些情况下正是动机造就了世上一切差别,而不会感到大惊小怪。接下来我要探讨的问题是,特免是否至少在有些时候并不取决于被指控行为的动机。
我要举的例子里面,被指控的损害和前面一样也是恶意的商业干预,但所用手段 (即被告的行为)不同。我假定法律将该损害认定为现时损害,因而损害认定的问题在此不予讨论。我还假定,被告的行为只是因为所提及的特定后果以及被告对该后果的态度,才成为非法行为或者诉讼事由。最后我还假定,被告所招致的第三人的作为或不作为是合法的。假如可以找出这样一件案子,即除了 “人们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吧”这条一般理据之外,别无更特殊的或其他的政策理据为被告行为提供正当性,那么这件案子就涉及我希望提出的争议点。我发现很难设想这样一件案子,但假如它真的发生了,我想法院将会认定它所招致的损害超过了自发的收益。⑨或许如下判例符合我们的设想:Keeble v.Hickeringill,11 East,574,n.,and Tarleton v.M’Gawley,Peake,205——我们可以想得到,人们因为被告恶意开枪 (该行为在其他场合是合法的)而不得不远离原告。你们可在如下著作里找到这些判例,see 1 Ames&Smith,Cases on Torts.该书包含着与本文主题相关的精选判决。(Keeble v.Hickeringill是18世纪初英国财产法和侵权法的著名判例,案情如下:原告拥有一片地产,其中有个池塘配有若干捕鸭设施,他使用一些经过驯养的真鸭子作为诱饵,诱使野鸭自投罗网,但是被告先后三次向池塘开枪吓跑野鸭。该案原告胜诉,赢得20英镑。Tarleton v.M’Gawley是18世纪末涉及第三人干扰预期合同关系的著名判例,案情如下:原告派商船前往非洲进行贸易,商船抵达非洲海岸后,一群非洲人乘着独木舟前来交易,此时另一艘商船向独木舟开火,致一名非洲人死亡,成功阻止原告本可实现的交易。——译者注)因为使坏而感到痛快固然可被称为一种收益,但另一方的痛苦是更重要的损失。否则为何允许因受殴击而获得赔偿金呢?没有任何一般政策允许一个人仅仅为着为非作歹的快乐而侵害邻人。
但是我们不必虚扯这些事。让我们设想另一件案子,其中被告的商业干预行为得到了某些特定政策理据的支持。例如,一位权威人物建议别人不要聘用某位医生。允许人们相互自由地提出建议,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可取的。另一方面,让一个人失去生意,这通常是不可取的。两种利益相互对立,我们必须划定它们的分界线。建议他人不要缔结前述某些契约,这种做法不宜获得如此绝对的优先通行权。于是,人们很可能会说,如果听众相信该建议是出于好意,是为了保护听众的利益,那么被告就不承担责任。但如果听众不相信该建议是为他们的利益着想,而相信那是为了抹黑那位医生,那么医生就会胜诉。⑩See Morasse v.Brochu,151 Mass.567;Tasker v.Stanley,153 Mass.148;Delz v.Winfree,80 Texas,400,405.这些判例在行为的准确定性方面常常模棱两可,而这一点在我看来乃是重中之重的事实。在Lumley v.Gye,2 El.&Bl.216里面,当事人主张被告 “唆使和劝说”第三人违约。在Bowen v.Hall,6 Q.B.D.333里面,被告霍尔 (Hall)说服别人不履行他的契约 (p.338,339)。在Old Dominion Steamship Co.v.McKenna,30 Fed.Rep.48里面,被告 “劝说原告的员工”离开工作岗位,等等。如果听众相信该建议出于好意,可是被告仅仅为了施加损害而自愿提出该建议,那么各家法院可能作出不同判决,但肯定有的法院会认定不适用特免。①See Stevens v.Sampson,5 Ex.D.53.没有恶意的不诚信 (bad faith without malice)会引发怎样的效果,不在我讨论范围内。
可见,为查明被告是否知悉自己行为的概然后果而适用的外在标准,与特免问题无关或者关系不大。人们假定被告事先知悉其行为的概然后果,否则就谈不上特免的问题了。一般说来,被告不仅预见而且有意造成被指控的损害。如果不存在特免,那么知悉后果和恶意之间的区分便无关紧要。如果特免是绝对的,或者说囊括了恶意行为,那么它显然也囊括了非恶意行为。如果特免是有限度的,那么支持被告自由行事的政策一般说来就会限定在如下范围内,即禁止被告出于侵害的目的而使用行善条件下被允许的自由。我们不妨设想,被告给出的建议明显趋向于 (tend)损害原告,但被告事实上并没有想到原告,那么除非被告出于不诚信或恶意而明确针对着原告,否则该建议将获得特免。若要认定该建议是针对原告的恶意行为,只能是要么被告确实想到了原告,要么原告属于被告确实想到的那一类人。
法官为何不喜欢讨论政策问题,或者说不喜欢根据他们作为造法者的观点来判案呢?其原因之一或许在于,一旦你离开了纯逻辑演绎的道路,你就丧失了确定性的幻觉,这种幻觉使得法律推理看起来像数学演算。然而确定性不过是一种幻觉。对于诸多生活利益的体验,教给人们各种政策观点。生活利益都是斗争场域。无论作出什么样的判决,都必定有违一方当事人的愿望和意见,作为判决基础的各种区分将是程度的区分。就连前述关于自由竞争益处的经济学假定,也遭到一个重要流派的否定。
让我进一步举例说明。如下做法在英格兰是合法的,即为了阻止原告成为竞争对手,商人联合起来向发货人报出不盈利的售价和回扣,正如原告有权去做的那样,并且也会采取没收回扣和威胁解雇的方式防止代理人与原告往来。②Mogul Steamship Company,Limited,v.McGregor,1892,App.Cas.25;23 Q.B.D.598.See also Bowen v.Matheson,14 Allen,499(1867);Bohn Manufacturing Company v.Hollis,55 N.W.R.1119 (Minnesota,1893).但如下做法似乎是非法的,即工会主管责令工会成员不得为原告的供货商工作,以迫使原告戒绝他本来有权做的事情。③Temperton v.Russell,1893,1 Q.B.715.
在后一种情况下,被告的行为严格说来是在发布命令,而不是在拒绝缔约;但即便工会一致表决通过采取那种手段,法院的判决或许也不会改变。④See Carew v.Rutherford,106 Mass.1以及下文涉及联合行动的判例。亦参见文末的进一步评论。就商业干预而言,拒绝缔约的权利并不是绝对特免的。单纯的联合行动和侵害原告的意图,似乎并非裁判理据之所在。这两个因素以同等程度出现在莫高汽船公司案 (Mogul Steamship Company’s case)里面。诚然,当时陪审团裁决认定了恶意。但是请看看案件证据、法官指示和判决,显然人家的意思不是说被告不以利己为最终动机。被告想通过使原告屈服的方式获利,正如在另一种情况下,被告想通过排挤原告的方式获利。或许可以说被告有拒绝缔约的自由,但他们没有权利建议或劝说本打算同原告交易的承包商放弃交易,而一旦向承包商传达工会的缔约意愿 (前提是承包商不跟原告交易),那么被告就是在进行此类劝说。但假如这番详尽阐述 (refinement)不是在拐弯抹角地否定不缔约的自由——因为除非一个人能够说明他打算在什么情况或条件下拒绝[缔约],否则很难说他可以自由地拒绝[缔约]——那么同样的推理模式无论如何可以适用于被告免责的案例。裁判理由在此实际上回到一条相当微妙的政策命题(该命题关乎被告自己意图获得的特殊利益的价值),并启人疑思:具有不同经济学取向的法官们会不会在遇到这个问题时作出不同判决?
不妨用其他关于联合抵制的案件继续举例说明。同样的行为若由一人为着特定目的作出则可能得到特免,而若出于为着同样目的的联合行动则可能被判定违法。⑤See State v.Donaldson,32 N.J.L.151;State v.Glidden,55 Conn.46;Crump v.Commonwealth,84 Va.927;Lucke v.Clothing Cutters’ &Trimmers’Assembly No.7,507,K.of L.,26 Atl.R.505;Jackson v.Stanfield,35 N.E.R.345 (Indiana,1894) ;Mogul Steamship Company v.McGregor,23 Q.B.D.598,616;1892,App.Cas.25,45.这些案例并不是完全意见一致。Bohn Manufacturing Co.v.Hollis,55 N.W.R.1119 (Minnesota,1893).当我们区分若干重要权力在单一资本家 (且不说一家公司)那里的联合与其他形式的联合时,很容易发现困境之所在。⑥23 Q.B.D.617.除非快刀斩乱麻地说哪怕最微不足道的联合也是不法的,否则多大的联合才够称得上不法行为就是个程度问题。所有这些的背后是这样一个问题,即法院会不会公然违逆这个世界日新月异的组织方式及其必然后果。我的以上看法不是为了批评判决,而是为了提醒人们注意那些不得不加以权衡的、非常严肃的立法性考量因素。若这些考量因素竟以无意识的偏见或半清醒的倾向等模糊形式发挥权重,那正是危险之所在。要公允地权衡这些考量因素,不仅需要有法官的至高权力和法律实务未必能够保障的训练,还需要免除先入为主的成见,这是极难达到的境界。在我看来可取的是,应在明确承认其性质的前提下开展这项工作。法律仅作为共同意志之无意识体现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法律已经成为有组织的社会对自身作出的有意识回应,而这个有组织的社会明确寻求决定自身的命运。
我们总结一下这部分的讨论:如果应负责任的被告力图开脱自己对于某种行为的责任——他明知该行为可能给他人造成现时损害,且确实造成了现时损害——那么他必须给出证成理由。最重要的证成理由就是主张特免。单单考虑损害的性质和行为的效果并对二者加以比较,这对于判定特免主张来说还是不够的。通常还必须考察行为的准确定性和行为的情势。例如,只说被告劝诱公众(或一部分人)不跟原告交易还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知道他的劝诱方式。如果劝诱方式是拒绝让他们占用某栋建筑或是拒绝雇佣他们,那么答案可能是 (且不考虑其他条件的话)断然支持被告。如果劝诱方式是采取就其他理由而言的不法行为,那么答案超出了我的讨论主题。如果劝诱方式是建议或者并非在其他场合违法的联合行动,那么动机就可能是最最重要的事实。完全可以想见,在某些辖区,动机将左右所有的或近乎所有的特免主张。我以例证形式援引的上述案例来自不同的州,而且或许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能被认为彼此协调一致。但所有这些案例的裁判理由都是政策;一方面和另一方面给共同体带来的益处,是真正值得权衡的唯一事项。我只希望补充一点:到目前为止,当第三人的行为比被告的行为更靠近损害时,我假定第三人行为合法。我尚未谈到与他人不法行为相联系的特免。我也暂且搁置了如下例外情况:要是第三人明知的话,被告所劝诱的那种行为将是侵权或者犯罪,比如清白地给予一个毒苹果。如果损害在性质上比丢了生意更加严重,那自然而然会限缩特免,但在我前已想到的案件里不太可能如此。
我接下来谈谈完全不同的一类案件。在这类案件中,被指控的致害意图固有其重要性,一方面有别于知悉危险 (notice of danger),另一方面有别于实际的恶意。先从稍远的地方开始说起,无论谁在思考责任的外在标准时,都会遇到这样一种难题:假如被认定的知情是一般理据,那么销售军火的人为何不对自己卖出的手枪造成的死伤负责呢 (因为他势必被判定为知道如下概然性,即一个人早晚都会出于非法目的从他那里购置手枪)?我不认为此类问题的全部答案都在于特免学说。我也不认为应从关于原因的老生常谈中获得 [解决问题的]指示。有人说,谁的不行为最靠近损害,谁就是损害的唯一原因。但正如海斯诉海德公园案 (Hayes v.Hyde Park)所指明的那样,⑦153 Mass.514.谁的行为最靠近损害,谁就是致害原因之一,无论该行为正当与否。然而,他人介入的行为不见得使被告免责。
以下原则看起来至少在我国深得人心:每个人都有权依赖其同胞以合法方式行事,于是,如果他在行为时假定其同胞将会合法行事 (不论该假定有多么不可思议),他都不因此承担责任。在一些有说服力的案例中,该规则的边缘可能遭到小口啃噬,比如,轻微过失的第三人介入,或者第三人的过失仅发挥次要作用,但该规则很少引起争议。该规则在适用时既支持不法行为人,也支持其他人。经典例证便是:一个人若是口头诽谤另一个人,不对他人未经自己授权而不当重复该诽谤之辞的行为负责;但该原则是一般性的。⑧Ward v.Weeks,7 Bing.211,215;Cuff v.Neward&New York R.R.,6 Vroom,17,32;Clifford v.Atlantic Mills,146 Mass.47;Tasker v.Stanley,153 Mass.148,150.倘若他人的重复得到了特免因而是正当的,并且明显有可能发生,那么法律大概会作出另一种安排。⑨Elmer v.Fessenden,151 Mass.359,362.以及引证的案例。See Hayes v.Hyde Park,153 Mass.514.
但假如被告并不止于说:“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我周围的人会遵守法律,当我随性而为的时候,我不会以他们的违法行为可能酿成的危险来约束自己”;假如被告反倒不仅预见了违法行为,而且在行为时有意引发若无他人违法行为的帮助则不会出现的后果,那么情况就不一样了。该差别可由如下两方面的对比得到说明:一方面,土地所有人拥有为防范入侵者而按其心愿改造自己土地的一般权利,另一方面,他要为捕人陷阱或刺狗装置而甚至对入侵者承担责任。在后一种情况下,他明确地思虑过他原本有权假定不会发生的事情,而所造成的损害处于一种仿佛他本人就在现场亲历亲为的状态。他的意图可以说使他成为最终的侵权人。⑩Bird v.Holbrook,4 Bing.628,641,642.See Jordin v.Crump,8 M.&W.78;Chenery v.Fitchburg R.R.,35N.E.Rep.554,555.
因此,如果所预见的不正当行为是第三人的行为而非原告的行为,那么被告可能要对该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当然,一个人毫无疑问可能在民事和刑事方面因他人的违法行为而承担责任,而且人们现已达成牢固的共识,即一个人可因他人的违约行为以及侵权行为而承担责任。①Lumley v.Gye,2 El.&Bl.216;1 Ames&Smith,Cases on Torts,600,612,埃姆斯 (Ames) 教授的注释。如果他仗着自己的权威而命令他人作出违法行为,他就得承担责任;如果他用说服的方式劝诱他人作出违法行为,他可能会承担责任。至于他通过什么方式而在明知的情况下向他人提供违法行为的动机,是通过恐吓、欺诈抑或劝说,只要该动机奏效,方式问题在我看来就无关紧要。但若要剥夺他依赖他人合法行为的权利这一保护屏障,你就必须证明他意图招致违法行为势必引发的那些后果。通常来讲,这等于说他必定已有该违法行为的意图。让我们把这里的事情总结成一条规则:当你力图让某人对损害负责,且第三人行为比被告行为在时间上更靠近损害时,假如第三人的行为是合法的,那么该损害好像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于是问题就在于被告应否合理地预见或期待该损害;但假如第三人的行为是违法的,那么你必须证明被告已经意图达成这些若没有第三人行为便不可能发生的后果。②我冒昧地援引一系列将会佐证我观点的案例。Hayes v.Hyde Park,153 Mass.514;Burt v.Advertiser Newspaper Co.,154 Mass.238,247;Tasker v.Stanley,153 Mass.148(须注意,在该案中,根据被认定为建议基础的事实来看,被告所建议的行为亦即原告妻子的离去,似乎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构成违法行为);Elmer v.Fessenden,151 Mass.359,362;Clifford v.Atlantic Cotton Mills.,146 Mass.47.
尽管实际的故意是此类案例的必备要素,但恶意通常说来并不如此,除非是否对介入的不法行为人承担责任的问题与特免问题纠缠在一起。我们认定被告以违法方式施加损害,因为最靠近损害的第三人行为被认定违法。如果被告并不知悉第三人行为将会违法或可能违法,那么根据一般原则他就不承担责任。虽然鲍温诉霍尔案 (Bowen v.Hall)提出了保留意见,③6 Q.B.D.333,338.但如果被告明知第三人将采取违法行为,那么看来被告显然要对劝说第三人这样做的行为承担责任,无论被告是否出于恶意。我相信,恶意建议他人采取某一合法行为以显著损害原告的做法,以及善意建议他人采取某一违法行为以显著损害原告的做法,都不应获得特免。当然,我所谈论的是奏效的建议。在我看来,法律很难认可一种劝诱违法行为的特免。但无论是否存在这样的特免,我这里试图说明的是,除了特免以外便不存在答辩理由;也就是说,当基于特免之外的理由时,在是否对他人不正当行为承担责任的问题上,恶意不具有实质意义。
于是我们在此又一次回到了特免问题。如果被告的行为目的是借助第三人违法行为造成被指控的结果,那么相比于他仅仅有意劝诱合法行为的情况,被告在前一种情况下的特免范围更窄。如前所述,我认为,诚恳劝说他人以合法行为损害原告的做法所得到的特免,不会延伸到诚恳劝说他人以违法行为损害原告的做法。我们来谈谈得到更大特免的行为。一个人能以A对B违约作为己方与A缔约的条件吗?按照一些可敬的法院的判例,答案似乎是他不能这样做。④Temperton v.Russell(1893),1 Q.B.D.715.我在前面出于另一目的援引过该案。在该案中,多了一个联合行动的要素。参见前引⑤援引的案例。我到目前为止所称的不予缔约的特免,其实只是缔约特免的否定方面。我以否定的形式加以陈述,是为了让绝对特免的主张更貌似合理。但不是说只要协议在表面上不违法——亦即只要协议未必总是倾向于造成法律希望防范的结果——就有签订此类协议的绝对特免。如果一份协议尽管通常说来无害,但在特定情况下倾向于造成法律希望防范的结果,那么该协议就可能违法。
于是问题就来了:协议 (例如销售)和法律力求防范的结果之间须有多么紧密的联系,我们方可判定该协议违法?我不揣冒昧地认为,倘若涉及的结果是侵权行为,那么可以形成法律因果链的那种联系紧密度就将使人判定出售者承担责任。在格雷夫斯诉约翰逊案(Graves v.Johnson)里面,⑤156 Mass.211.当时发现有人在马萨诸塞州出售烈酒并且是 “为了”(with a view to)购买者在缅因州的非法转售,多数主审法官在解释这里的 “为了”时,认为它是指出售者意图见到购买者违法转售,且购买者也把出售者的行为理解为出于该目的的协助,因此判定该销售行为违法。但我们不妨揣测,倘若出售者仅仅知道购买者的意图,但既没有怂恿也不以为意,那么判决结果或许不同。
在特免的问题上,被告的行为性质、后果的性质以及该行为和后果之间的联系紧密度可能变化莫测。我们可以设想一种享有最高程度特免的行为 (例如使用土地),而它是在要求出租房屋或者拆除阻挡视线的建筑时必须符合某些条件。我们可以设想当事人在说明这些条件应予满足时是有意而为,但既不是在劝说也不是在建议,并且我们可以设想这些条件可能是五花八门的错误行为,上至谋杀,下至在借阅一个月的 《先驱》的事情上违约。人们大可在模拟法庭上设计此类有趣案例,尽管我很难指望在实务中碰到。不过,如前所述,我的目的不是判决案件,而是把案件的判决方法稍加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