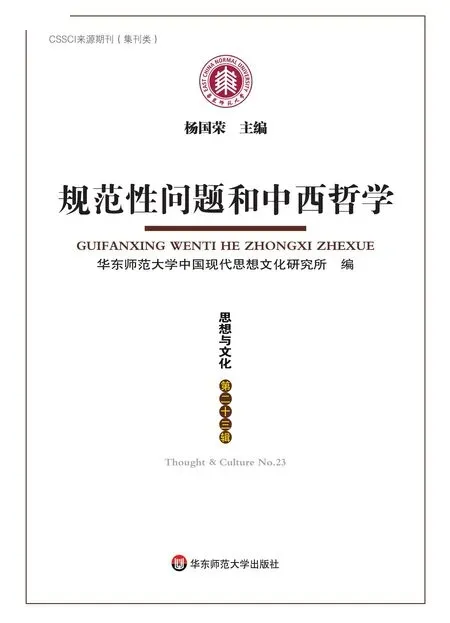论唐君毅、牟宗三对《起信论》之不同诠释
2018-04-01
●
一、 问题的提出
《大乘起信论》是佛教中国化的标志性论典,开启了天台、华严、禅宗等中国化宗派。自古以来注疏者不少,争论也不少,如吕澂认为《起信论》是二心,不符唯识传统思想,清净心孤悬。但《起信论》地位、价值之高举世公认,如牟宗三就认为“一心开二门”是“普遍性共同模型,适用于儒释道三教,亦可笼罩康德系统”,属于“实践的形上学”。[注]牟宗三: 《中国哲学十九讲》,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258页。他将《起信论》及“一心开二门”提高到前所未有之高度。而与牟宗三同时代,且同为熊十力弟子的现代新儒家唐君毅,对《起信论》思想作了不同诠释,二人相得益彰、互相发明,有彼此相似、印证之处,但也差异极大。牟宗三与唐君毅均对佛学有深度理解与研究,二人佛学立场不同,根本上,唐君毅趣归华严,牟宗三旨宗天台。唐君毅以中国哲学为立场,牟宗三则在理解“一心开二门”价值基础上,对中西哲学作分析比较,以“一心开二门”对治康德“感触界”(sensible world)与“智思界”(intelligible world)不能沟通之弊,认为中国哲学有“智的直觉”,成圣成佛是良知的“自我坎陷”(self-negation),他试图将西方理念“设准”(asumption)转变为“呈现”。牟宗三与唐君毅如何诠释《起信论》思想?二者思路有何不同?了解不同角度和观点的诠释,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研究《起信论》思想,以及如来藏与阿梨耶识[注]注: 因沿用不同文本说法,故本文中阿梨耶识,时而也作阿黎耶识、阿赖耶识。《起信论》之阿梨耶识或阿黎耶识,与唯识阿赖耶识意义有细微差别。一般地,阿梨耶识或阿黎耶识可通真如,是如来藏系统;阿赖耶识不通,是阿赖耶系统。笔者自行使用阿梨耶识,以示与阿赖耶识区分。关系等问题。
二、 真伪之辨与思想特点
关于《起信论》真伪问题,唐君毅与劳思光观点相近。劳思光在《新编中国哲学史》中说:“但有两点是无问题者,即第一,此书出自南朝末年。第二,此书思想属真常之教一系,与般若之学不同,与摄论、地论二说,则有近似处,亦有殊异处,可说代表一颇为特殊之态度。若以思想之深度言,则此书应成于摄论及地论二宗立教之后。”[注]劳思光: 《新编中国哲学史》(二),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221页。虽不表明定为中国人所著,但本着客观精神,依照其思想内涵及其出现年代与当时佛教思想相对比印证,可知《起信论》思想分类、归属。唐君毅在《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中也认为:“若起信论为国人所伪造,则其旨盖在综合当时之摄论师与地论师之争。……今起信论以如来藏为第一义之心,则近宗十地经论之地论师之说,亦通接于印度言如来藏、如来性,为第一义之心之诸经论,如‘胜鬘’、‘宝窟’、‘如来藏’、‘不增不减’诸经,……起信论以如来藏为心真如、亦即法性,则又通于南地之说。其以阿梨耶识为杂染所依,更言其为由第一义之如来藏,而衍出第二义之心,则显然意在综合北地与摄论宗之义。”[注]唐君毅: 《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下册,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761—762页。唐君毅是以“本觉”、“始觉”等名词概念源于魏晋玄学来推导、假设《起信论》为中国人所作,也肯定其理论精神有合于印度如来藏之处,但更多的是综合地论宗与摄论宗的结果。
牟宗三则大胆得多,直接承认是伪造。他认为《起信论》“考据上可以说”中国人伪造,但“思想却并不假”,其思想仍是依据印度佛教真常经《胜鬘经》、《楞伽经》、《涅槃经》及其他如来藏经典。[注]牟宗三: 《中国哲学十九讲》,第247—248页。他甚至大胆推论,《起信论》“其实就是真谛三藏所造”,“被标为马鸣菩萨所造,其实这是假托菩萨之名,以增加论典之权威性”,因为真谛的思想是“想融摄赖耶于如来藏的,而《大乘起信论》正是这种融摄之充分的完整的展示”。[注]牟宗三: 《中国哲学十九讲》,第251页。唐君毅与劳思光对于《起信论》真伪源流态度比较模糊,但比较客观;牟宗三则直接、具体得多,直指真谛,一方面显示出他对佛教思想内在脉络的熟稔,一方面也突显出他对自己理论水平的高度自信。
同时,针对吕澂认《起信论》为对《楞伽经》的反叛,视“本觉”为《起信论》之发明,牟宗三对此指出,返本还原是真常心派共有之义,不是《起信论》新发明。他认为吕澂不过是沿袭无著世亲赖耶缘起的思路,而忽视本性清净,而其实应该以如来藏思路来理解,赖耶与如来藏是两个系统。[注]牟宗三: 《佛性与般若》(上),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349—356页。这一点唐君毅没有指明,即前人以赖耶系统理解《起信论》导致理解进路不对,而应该以如来藏思路来理解。
《起信论》具有包容性与进步性特点。唐君毅指出了其包容性与进步性,其进步性是从真常经角度出发,看《起信论》“一心开二门”思想对于《胜鬘经》、《楞伽经》如来藏思想的升格。牟宗三没有指出其包容性,但却肯定其进步性,其角度是从宗派思想出发,认为《起信论》思想代表的真常心系是对唯识宗的进步。
首先,包容性。唐君毅认为: 以起信为名,自信是信己性;成佛赖诸佛菩萨外缘,类似唯识宗圣教外缘,慈悲愿护,不只表现于言教,亦可神通感应,这是信佛者所共许;起信论之成佛因缘,既许众生有如来藏成佛正因,自信自力,又有诸佛菩萨慈悲护念,兼信他力,自信兼信,起大乘之信。[注]唐君毅: 《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下册,第762页。可见其观点之包容,自信己性不废兼信他力,开禅、净土之先河;既蕴涵禅宗自力救度意味,又暗含净土宗他力救度思想,自力他力不二。
其次,进步性。唐君毅指出: 以二门摄空、不空义,是对于《胜鬘经》、《楞伽经》之进步。无垢即如实空,毕竟清净即如实不空;藏识是生灭门,如来藏是真如门,于是概念上明白划开,这是进步。[注]唐君毅: 《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下册,第764页。唐君毅以二门对真如空、不空义的摄取与对应,并使二者在概念安置上有对应关系,认为这是对《胜鬘经》、《楞伽经》如来藏思想的概念明晰化。
对此,牟宗三不是从空、不空义出发,而是以宗派思想的进路阐释其进步性。他认为: 《起信论》的出现,是在空宗(以《般若经》等为代表)和有宗(以《摄大乘论》等为代表)之后,其目的在于整合、融摄空有二宗,以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统摄一切法。《起信论》依《楞伽》、《胜鬘经》、《涅槃经》等经典对如来藏的诠说,提炼出真心,比印度空有两宗更进一步,唯识有宗比《中观论》般若学更进一步,《中观论》无对于流转还灭作根源说明故;《起信论》比唯识宗更进一步,唯识以阿赖耶识为中心,以正闻熏习为客,成佛根据不足,《起信论》提出真心,始有成佛的超越性根据,真心既是成佛的可能性根据,又是一切染净法之所依止。[注]牟宗三: 《佛性与般若》(上),第372—373页。并且牟宗三对《起信论》进行定性: 《起信论》是“真心为主虚妄熏习是客”的系统,“顺阿赖耶系统中无漏种底问题(正闻熏习是客)”,要“通过一超越的分解而肯定一超越的真心,而此真心不可以种子论”,此真心作为一切法之“依止”,且是“成佛底真实可能之超越根据”。[注]牟宗三: 《佛性与般若》(上),第356—357页。依牟宗三,空宗经典并未指明生死流转的根据,而有宗针对空宗特点,指出生灭门的根据,但成佛需要正闻熏习,正闻熏习需要佛现世、能听到佛说法,这不是凡夫众生能控制的,也就是没有主动性,是被动的条件。这样成佛不具备自己的内在根源,只能委之于外在客观条件。《起信论》则又比唯识有宗更进步,认为人人具有自性清净心——成佛依据,人人有如来藏,只要返本还原即可,这是内因、主因。牟宗三从空宗、有宗的思想特点与《起信论》相观照,指出《起信论》的思想是因病施药、对症下药,对治有宗的内在根源不足问题,并综合了空、有二宗思想,以“一心开二门”的思想融摄之。
三、 真如、生灭与熏习
(一) 心真如门: 无垢清净与无执无漏
心真如门,有空不空二义,唐牟二人所诠释角度不同,唐侧重于无垢清净的否定与肯定层面,牟侧重于现象与本体的属性差异。唐君毅认为:“无垢,即如实空,而毕竟清净,即如实不空也。”[注]唐君毅: 《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下册,第764页。他是从无垢、清净的角度来诠释空与不空二义的。而牟宗三则认为:“空是远离妄念所起的一切计执——差别相。不空是真心这个法体恒常不变,而且具足无量无漏性功德。”[注]牟宗三: 《佛性与般若》(上),第361页。牟宗三则是以离相离念说空,以法体恒常并具足无漏性功德来说不空,来诠释二者的。唐君毅的诠释角度是: 无垢,其实即是清净,不过从否定的一面来确定空,从肯定的一面来肯定不空。牟宗三诠释角度的不同在于,妄念与差别相是现象的、无常的,其本性是空的,法体却不是现象,具足无量无漏性功德,却又不是空的。
(二) 心生灭门: 藏识所覆之如来藏与生灭心双重性
心生灭门,既有生灭(妄心),也有不生不灭(真心),生灭门中又包含真如,其实是反映真妄二者在一门中之互动关系。相对来说,真如门是不动门,生灭门是起动门,因此所有活动皆从生灭门入手。对此《大乘起信论》云:“心生灭者,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所谓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非一非异,名为阿黎耶识。”[注]马鸣: 《大乘起信论》,真谛译,《大正藏》第32册,No.1666,第576页中。而冯友兰侧重讲阿黎耶识与真如的非一,而没讲非异,他在《中国哲学史新编》里说:“如来藏就是心真如门。真如心是宇宙的本体,所以生灭心要依靠真如心。照《起信论》所说,生灭心就是阿赖耶识。”[注]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41页。劳思光则较全面,认为阿黎耶识是“‘真我’之一状态”,生灭心依如来藏而有,“主体作如此迷蔽之活动时,就此‘迷蔽’境界说,非主体自由纯粹之境界,故云‘非一’;但毕竟迷蔽乃主体自身生出,作迷蔽活动者仍是此主体,故云‘非异’。‘非一非异’,乃称‘和合’”[注]劳思光: 《新编中国哲学史》(二),第226页。。与冯友兰、劳思光都不同,唐君毅、牟宗三各有其独特思路,也就是要解决阿梨耶识与真如的关系问题。
对于阿梨耶识与真如、觉的关系问题,唐牟也有不同的诠释。唐君毅认为,《起信论》之阿梨耶识“不同于唯识宗阿梨耶识,只是藏染净善恶种子,其自身无善恶染净而为无记者”,此和合的阿梨耶识,与《楞伽经》“为藏识所覆之如来藏”相同,而正是“生灭心所依之不生灭之如来藏”,才有所谓“本觉”,才有成佛的根据。[注]唐君毅: 《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下册,第765页。唐君毅辨别了阿梨耶识与阿赖耶识、如来藏的异同。唯识宗的阿赖耶识根本上则是杂染法,是有善恶染净之分的。《起信论》的阿梨耶识则是生灭与不生不灭的和合,其中含藏真如无明,与《楞伽经》如来藏相同,自身无善无恶无染无净。而《起信论》的生灭心(妄心)是以不生灭心(真心)为依止的,正因如此,妄心不知本来真心才有“不觉”,到知道真心才有“始觉”,最终不断熏习去妄成真而成“究竟觉”,而这一切的根据是因为人人本有成佛内在依据的“本觉”,否则人不能成佛觉悟。
对此,牟宗三有不同诠释。他指出,生灭心有“双重性”,“超越的真性”是其“觉性”,“内在的现实性”是其“不觉性”,所以生灭门是要“说明流转与还灭之可能”的。从内在的现实性而言,它是生死流转之因,叫阿赖耶缘起,但生灭心是“凭依如来藏真心而起现”,“阿赖耶必须统属于如来藏”,只是方便说为如来藏缘起,即“如来藏真心并不直接缘起生死流转,直接缘起的是阿赖耶”,换句话说,生死流转的直接生因是阿赖耶识,而如来藏则只是其凭依因,而不是其生因。[注]牟宗三: 《佛性与般若》(上),第362—363页。牟宗三将生灭心分为两种,一种是无明妄心,其归结为内在现实性,即不觉性,另一种是真如,归结为超越的真性,即觉性。之所以真如、真心也包含于心生灭门,是因为心生灭是依止于心真如的,本无自性;妄心是因无明依止真如忽起而成,所以心生灭门中,其实是含有真如的,真如无所不遍。生灭门就有两种发展方向,一种是无明熏真如,那就是流转,一种是真如熏无明,就是还灭。对于不觉性(流转)而言,称为阿赖耶缘起,因为无明熏真如,直接作用的是阿梨耶识(阿赖耶识),但阿梨耶识是以如来藏真心为依止的,所以如来藏缘起只是对阿赖耶缘起的一种方便权说。如来藏只是阿赖耶存在的依据,但后者并非是如来藏直接生出来的。阿赖耶缘起是以阿梨耶识(阿赖耶识)为重心,是唯识的或杂染法的系统;如来藏缘起以真如为重心,是真常唯心的系统。而《起信论》是真常唯心系的,所以不说阿赖耶缘起,而说如来藏缘起,主要诠释的是真如“不变随缘,随缘不变”、“染而不染,不染而染”的,显然这与阿赖耶缘起有着显著的区别。
(三) “生”义: 依傍不相离与凭依因
既然无明、不觉依真如而生,则“生”是何涵义?唐牟都有论述。唐君毅认为,无明、不觉依心真如而生,“非即在世间中某时,由之直接生出”,而是“傍之而生,以之为缘而生”,“所谓依傍,即不相离之意”,不相离“只是现象学地说,亦可以说是经验地说”。[注]唐君毅: 《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下册,第767—768页。无明不觉依真如而生,不是在世俗时间概念内由一物生出另一物的生出,无明只是与真如不相离,有真如则有无明,没有真如则无明也不存在。所以无明只是“依傍”真如而存在,而不是直接由真如生出。
对此,牟宗三认为,因“无明之插入,间接地说如来藏缘起”,是“不染而染”,而真心本性“自性本净”,不随之改变,是“染而不染”,如来藏“间接地为生死之凭依因”,“直接地为无漏功德之生因”。[注]牟宗三: 《佛性与般若》(上),第363页。在牟宗三看来,真心、真如本来清净,只是因为无明的插入,真心受无明所熏而现缘起相,所以如来藏本不缘起,只是间接地这样诠释为缘起,而真心即使受熏而仍为真心(即“染而不染”)。如来藏有空、不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是因为具有无漏功德性,是生无漏功德的直接原因,但不是生无明妄心的直接原因,而是间接原因,因为如来藏不直接生无明妄心,只是无明妄心的“凭依因”。唐君毅是现象学地、经验地诠释“生”即“依傍”、“不相离”;牟宗三是从如来藏空不空、染不染角度诠释“生”即“凭依因”。
(四) 真如熏习: 能现行与能熏习
无明能熏真如当无异议,而《起信论》的熏习特色在于真如能熏无明。对此唐君毅认为,唯识染净法不能互熏,而《起信论》真如熏无明,有“分别事识熏习”、“意熏习”、“真如自身之熏习”三种,第三种还有“自体之相熏习”与“用熏习”;真如“能自己熏其自体之存在”,“有力有用”,“自具一能现行之义”,这是内因,但不废“慈悲愿护”外缘。[注]唐君毅: 《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下册,第774—775页。唐君毅认为真如熏无明是熏习自体,是“返本还原”,自我现行。他主要侧重于从真如自身的能动作用、自我现行的角度来诠说。关于体相熏习与用熏习,牟宗三则指出,内因为“真如自体相熏习”,外缘是“真如用熏习”;用熏习分两种,“差别缘”和“平等缘”,前一种是针对无生法忍菩萨以下境界直至凡夫而说的,后一种则是针对已得无生法忍菩萨而说的。[注]牟宗三: 《佛性与般若》(上),第366页。牟宗三是从境界论的角度来区分真如用熏习的,因为对待不同境界,所应用的缘法不同,这是符合佛教“契理契机”精神的。
在牟宗三看来,“觉”是就“真心法体即阿赖耶之超越解性”(离念)而说的,“不觉”是就“阿赖耶和合现实迷染性”(在念)来说,《摄论》侧重于“正闻熏习”的“外缘”,是“后天的、经验的、偶然的”,而《起信论》更侧重于内因“本觉”——“真如是真心”,“心始有活动力,故它亦自有一种能熏力”,“为无明所熏,不染而染,它亦可以染而不染,能熏无明”。[注]牟宗三: 《佛性与般若》(上),第364页。在牟宗三看来,“觉”与“不觉”是心的超越性与现实性的分野,前者源于是纯真心之体性,后者源于被无明所覆之阿梨耶识。唯识宗阿赖耶识依靠后天听闻佛法熏习熏成清净种子,并非内心先有一清净真心,所以只能等待外缘,缺乏内因的主动。《起信论》则是一种对治,以“本觉”的内因为成佛可能的依据,且既能熏无明,又能被无明所熏。牟宗三认为心有活动力,并非只是死理,呆板不动,而是具有自己涌现的能力。
(五) 不觉到觉: 反本还原与自我涌现
生灭心要从不觉转向究竟觉,不是要外求,像唯识宗那样依赖正闻熏习等外在条件,而是人人内在自心本具有其潜能。唐君毅认为,我们所做的,“不外自呈现其本觉之事,则成佛之事,只是反本还原之事”,而无需增加其他论述,“本觉心真如,即人本有之佛性”,本觉佛性与始觉、究竟觉佛性相同。[注]唐君毅: 《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下册,第766页。即是说,本觉即始觉、究竟觉。在形上学与工夫论的先后问题上,唐君毅认为《起信论》与智顗相反,《起信论》是“先肯定此一真如心或本觉之真实,而后更依之以起修”,而智顗是先“透过止观之修习而见”,而后“显诸法实相或法性者”,没有以心真如作为基础,所以《起信论》采取的是“形上学为先,修行功夫论为后”的思路。这一思路的形成,是对“修行之功夫之究竟处,加以悬想”,“即在人之成佛处看”,故得以建立形上学,而要化除生灭心、显现真如心,只有依赖修行。[注]唐君毅: 《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下册,第766—767页。唐君毅将形上学(真如本觉)作为工夫论(反本还原修行)的基础,而同时又强调,工夫论也是形上学的实现手段。本质上,本觉、始觉、究竟觉、不觉都是一个东西,只是人未成佛前的不同阶段表示。既然是反本还原,则一开始就已确定了一个真如心,而后进行熏习、去妄归真,所以《起信论》的理论建构思路是先建立真如心为本的形上学,而后围绕如何反本还原进行工夫论建构。唐君毅比较天台宗智顗与《起信论》二者思路,在形上学与工夫论关系上,二者先后顺序相反。
依牟宗三,熏习可由不觉转向始觉,“正闻熏习”只是“外缘”(后天的、经验的),而“真如熏习”是“内力”,真如非“无性之空如之理”,而是真心(心有活动力、能熏力),“真如心不可以种子说”,种子是一种“潜能”,只能“受熏”而“起现行”,而真心有“自己涌现之能力”。[注]牟宗三: 《佛性与般若》(上),第364—365页。真如心的起现是“起而无起”,只说性起,而缘起是“生灭门之流转法”,真如门便不能这样说,只好说“性起”。[注]牟宗三: 《佛性与般若》(上),第369页。他认为缘起不是本体论的生起,是通过无明妄念(阿赖耶识)缘起流转法,“本身并不起现这一切”。[注]牟宗三: 《佛性与般若》(上),第376页。牟宗三将《起信论》的熏习义与唯识宗的熏习义相比较,认为唯识宗的正闻熏习需要后天的闻佛说法才能养成成佛清净种子,无异于成佛依赖于外在条件;而《起信论》不求之于外在,当然不废外缘,只是将主因由外在转向内在,自身便具有这种成佛因子,依靠人人本具之“心真如”,使得被无明覆盖之真心能“自己涌现”,如阳光直透云层,能直接自我显现。而唯识宗的种子是潜能,需要接受外在条件对其施加熏习才能激发而起现行,不能自己涌现。所谓真如缘起,真如本身并不缘起,而是受无明所熏而成妄心的缘起,所以“起而无起”。
四、 判教差别: 圆教与别教
关于《起信论》思想的判教,唐牟二人有不同意见。由于唐牟意趣不同,唐君毅将《起信论》判为圆教,牟宗三判为别教。
唐君毅认为,唯识真如不随缘,是“凝然真如”,华严判为始教,天台判为通别教,“唯承认此真如之随缘不变义者,方为圆教”。[注]唐君毅: 《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第152页。可见唐君毅是将真如随缘义作为圆教的标准,则华严宗及华严以之为标准的《起信论》也自然划入圆教范围(即使按照华严判教法,《起信论》至少也是大乘终教,其中也含顿教、圆教成分,断不至于成为别教)。他将起信思想与唯识思想比较,发觉唯识的真如不生,是凝然不动的,没有随缘意义。而唯识宗看待《起信论》,也认为后者错在真如能生。但唯识宗不能理解《起信论》的是“生”是何义。“生”非在时间范围内出生、产生之意,而是依傍、不相离、凭依因之意,这在前已述。或许不同理解方式导致唯识、起信走向不同道路,同理,华严与天台亦然。暂且不管华严与天台二者对于唯识的判教分别,有一点是明确的,唐君毅对《起信论》的判教,更倾向于圆教。而且联系唐君毅倾心于华严,更能明确这一点。
而牟宗三在判教的问题上,与唐君毅分歧最大,他判起信为别教。牟宗三认为“真如用不是存有论地分析地必然的”,只是“随感而应”(“自然地或神通作意地”),所以《起信论》超越的分解“虽高于以阿赖耶识为中心者,然仍是别教,非圆教”。[注]牟宗三: 《佛性与般若》(上),第372页。《起信论》真如缘起思想高于唯识赖耶缘起,对于此点牟宗三无疑问,只是,他认为《起信论》仍未脱离别教范畴。不仅如此,牟宗三将华严宗与《起信论》都判为别教,因为华严的“法界缘起”是基于《起信论》“唯真心”,一切事只是佛法身的示现,“随众生之所乐见而示现,而自身却无此等事”,佛法身、真心的“孤悬性”造成的“紧张相”没被打散,而至天台才将“紧张相”打散,归于“圆实佛”、“平平佛”。当然他也坦承:“凡一切大教皆非无真处。判教可,相非则不可。”[注]牟宗三: 《佛性与般若》(上),第377—378页。华严与《起信论》思想是同一路径,一切现象都是真如随缘示现而已,但其实真如本身还是高高在上、清净无染的,根本不造作,这即是牟宗三认为的“孤悬性”导致的“紧张相”。在个人宗派(不是宗教皈依,而是思想意趣倾向)归属上,牟宗三与唐君毅不同,唐君毅赞同华严,而牟宗三倾心天台,所以在《起信论》判教问题上,二人有极大不同,前者判为圆教,后者判为别教。后者对天台的喜好,影响了他的思想模式,认为天台才是最佳解药,将“紧张相”打破,使高悬的真如回归“平平佛”。天台主张性具思想,真如即无明,无明即真如,善恶兼具,没有《起信论》、华严的真如那种纯净、孤悬性。当然牟宗三也承认,判教判成哪种都无不可,因为所有教派理论都难以保证面面俱到、无懈可击,理论会有弱点,但不能因判教问题大加挞伐、彼此相非,争得你死我活实无必要。
同一思想,被判结果不同,那么别教与圆教区别何在?牟宗三指出,无明覆真如,“必须破无明,真心始显”,即“异体无住”,是别教;而“法性即无明,无明即法性”才是圆教,是“同体无住”。[注]牟宗三: 《佛性与般若》(上),第396页。所以华严是别教,天台是圆教,因为华严走的路径是沿《起信论》的破无明显真心路数,无明真心二者相异,虽然无住,却是“异体无住”;天台却二者同体,无明真心相即,是真正“同体无住”。无住是相同的,这里可以明确两点: 第一,真如与无明在《起信论》与华严是异体;第二,真如与无明在天台是同体。牟宗三对于华严与天台、真如与无明的判别思路,由此可见。当然,这是牟宗三一家之言,真如与无明到底是同体还是异体,由于无明“忽起”的难以解释、“生”义导致的复杂性,尚无定论,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五、 思想合理性: 契合性善论与沟通康德
《起信论》思想有何内在合理性?其思想为何与中国人契合?
唐君毅认为其与中国本土思想契合,清净心之说与儒家孔孟性善说相通。他说:“(起信论)如来藏之名,乃初出自楞伽、胜鬘等经,……当佛初说法,固可只标示此寂净之涅槃,为修道之所证,未必言其即为此心之本性。……然人在其修道、求道之心中,……必须同时自信其有能证涅槃之心性。……亦已为一念之清净心,……此如孔子之言我欲仁而仁至,即必引出孟子性善之说也。”[注]唐君毅: 《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53页。即是说,众生都具有此清净心,成佛即是证得自性清净心,使其呈现展开。清净心是先在的,不是后天的、经验的,人人皆有,理论上说人人皆可成佛。而儒家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说“性善”、“人人皆可为尧舜”,意象仿佛。在此儒佛两家都是先有一清净心、善性,人人都能成佛成圣,所要做的就是熏习、反本还原、求其放心、扩而充之而已,即是将自性呈现出来。
对此,牟宗三指出,一般人学佛,是为了学佛或修道,而不是当作哲学来看待,所以中国人“重经不重论”,而且国人对理论“兴趣不强”,“分析性也不够”,所以“主张直接读佛经”。而真常经特别得到中国人喜欢,因为其“蕴涵的义理,很合乎中国人的心态”,“真常经所主张之‘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或‘一切众生皆可成佛’的思想,很容易了解,因为《孟子》一开始即强调‘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同时更指出‘人人皆有圣性’”,而“性”(即“圣性”)是“通过道德实践而呈现”的,“最高境界即是成圣人”,“圣性”“是指成圣所以可能之根据”。[注]牟宗三: 《中国哲学十九讲》,第250页。圣性与佛性相似,二者都是人人成就最高境界之根据,圣人与佛也是成就最高境界之目标。值得提出的是,这里真常经或真常唯心系(以真如、真心为中心)才与儒家类似,需要与其他宗派思想区分开来。
可见,唐君毅认为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与孔孟性善说相类似,而牟宗三也提出过类似观点。只不过二人的区别在于,唐君毅是从如来藏的源头开始,证明清净心的正统性,说明印度佛教与中国儒家心性论上本来相似,并非中国佛教捏造。而牟宗三则是从中国人的心态、性情角度出发,认为中国人相比较其他类佛教经典,更喜欢真常经,而这种贴合性不仅在喜好上,也在义理上得到证明。
更进一步,牟宗三指明了“一心开二门”的优越性。他认为,天台宗批评唯识宗阿赖耶是妄识,只能生生死流转法,生不了一切法;而“一心开二门”,“先肯定有一超越的真常心”,真常心再开出真如、生灭二门,并且“一心开二门”是公共模型,有普遍适用性。[注]牟宗三: 《中国哲学十九讲》,第252—253页。唯识宗阿赖耶识是妄识,因为它不能是清净法,只能生杂染法,根子上它不清净。而“一心开二门”这一创造,先立一真心,再从真中立妄,妄法以真心为依止,最终扫妄归真、反本还原即是还灭过程。牟宗三把“一心开二门”当作公共模型,这一点唐君毅并没有提到。牟宗三认为康德哲学在“智的直觉”方面存在缺陷,需要与中国哲学沟通,以“一心开二门”架构弥补其不足。
牟宗三将“一心开二门”归属到“实践的形上学”范畴。他指出,“一心开二门”是“普遍性的共同模型,可以适用于儒、释、道三教,甚至亦可笼罩及康德的系统”,属于“实践的形上学”(practical metaphysics),不是“理论的(知解的)形上学”(theoretical metaphysics)。而康德哲学的诸多理念如“第一因”等“在思辨理性中是毫无客观真实性可言,它只是个空理”,无法证实,由此“必须经由实践理性才能得到客观的真实性”;牟宗三还将“一心开二门”从形而上学上进行定位,“形而上学以道德为基础”,而“‘一心开二门’是属于道德的形上学或超绝的形上学的层次”,他认为只有在这种程度上说“一心开二门”才有意义。[注]牟宗三: 《中国哲学十九讲》,第258—259页。这即是说,牟宗三认为康德哲学中的理念属于空理,无法实践证成,而无所着落,而“一心开二门”恰是需要实践证成的,属于道德的形上学,因此可以弥补其缺憾。
牟宗三直陈康德哲学是“设准”,只是一种假设的理念,而缺乏实践,需要中国哲学“直觉呈现”来弥补,而其工具,则是《起信论》之“一心开二门”架构。他说: 康德的上帝等理念只是“设准”(假设),知识无法达到,其问题在虽强调人的“实践理性”,却不认人有“智的直觉”、“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康德说行动属于“感触界”(相当于生灭门),行动原因属于“智思界”(相当于真如门),行动本身亦当上通“清净门”(真如门),却被康德漏掉;“现象与物自身只是一物的两面”,“不同的呈现而已”,以“一心开二门”架构来消化康德哲学系统,是中国哲学对西方哲学的贡献。牟宗三宣称,“只有依据中国的传统”,才能看出康德哲学“不圆满、不究竟之处”。[注]牟宗三: 《中国哲学十九讲》,第259—261页。牟宗三将《起信论》“一心开二门”视为解决康德哲学问题的钥匙。
同时,牟宗三既看到其问题根源,也提出了解决方式。“或许问题就在于康德把‘自由意志’这个理念只当做设准看。既是设准,则不能被直觉,也无法呈现”,解决方式是将“设准”转变为“呈现”,“如王阳明所说的良知,本身即是一种呈现”。如果“理念只是个假定,永远无法呈现”,讲理多、讲心少,道德实践力量微弱,则理论容易落空;要能“当下呈现”,否则,“永远无法成圣成佛”,成佛只是一个理想。康德哲学里行动只是现象,而“一心开二门”,行动是由本心发动,“本身即物自身”。[注]牟宗三: 《中国哲学十九讲》,第262—263页。将行动贯穿真如与生灭,人才有可能成圣成佛,否则依康德哲学,法性本体永远无法企及,人与圣、佛境界存在天然鸿沟。
鉴于此,牟宗三提出西方康德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相互促进性。“康德哲学再往前推进,则必须与中国哲学互相摩荡,互相结合;同时,要使得中国哲学更充实,更往前推进,亦必须与西方康德哲学相接头,如此才能往下传续。这种文化的交流,正显出佛教‘一心开二门’这一架构的重要性。”[注]牟宗三: 《中国哲学十九讲》,第266页。牟宗三认为中国哲学,既是现象,也是物自身,只是透过现象呈现出来;尤其“一心开二门”架构,圆满对接了现象界与本体界,并解决了“智的直觉”这一“设准”问题,将“设准”转变为“呈现”,从哲学假设转为道德实践,使“理论形上学”变为“实践形上学”或“道德形上学”。当然在某些方面,中国哲学也需要吸收康德哲学的正面积极性。牟宗三在《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中说: 佛教说生灭门是从负面说,康德说人生问题是从正面说,以实践理性说,因此生灭门是积极的,但儒释道则显得比较消极。[注]牟宗三: 《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85页。另外,佛教缘起法,例如生灭常断,是执着,而康德不说是执着,而说“知性的先验概念”,是以正面方式说,其实“由不相应行法可把佛教之知识论说出来,以康德所做到的来补充它,使原来是消极的转成积极的”。[注]牟宗三: 《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第95页。牟宗三站在中西哲学文化之间,以佛教“一心开二门”架构对应康德现象界与本体界,力图以中国哲学之“呈现”消弭西方理念“设准”之弊端,并引进康德在知识论方面的正面积极性来消除中国哲学言说的消极性,虽一家之言,但有一定道理,其言可贵,而其情怀更可佩。
六、 结语
综上,唐君毅和牟宗三对《起信论》理解与诠释有同有异,某些具体问题观点类似,但在判教根本方向上不同。从相同处看,例如有: 真如“生”无明之“生”义,是依傍(唐)或凭依(牟),意义相近;《起信论》真如心与中国孔孟性善说、“人皆可为尧舜”等观点相近,等等。然而二人判教观点大相径庭。从判教而言,唐君毅认为《起信论》是圆教,而牟宗三则认为是别教,天台才是圆教。总结唐、牟诠释相异点,主要有三方面: 一、角度不同。唐君毅看问题的角度倾向于体认、反省、反观式,比如“修行之功夫之究竟处,加以悬想”,“在人之成佛处看”等。而牟宗三则更倾向于义理分析,将他人观点拿来比较,比如吕澂、康德等。二、观点不同。比如判教相异,一个认为圆教,一个认为别教。三、立场不同。唐君毅倾向于华严宗思想,牟宗三倾向于天台宗思想,他们对“真如缘起”的理解不同,这才是导致二人判教方向不同的根本原因。试究其诠释不同之原因,有三点。一、归趣不同。这是根本不同,决定了其他走向不同,唐归华严,牟属天台。二、知识范围不同。唐君毅主在中国哲学范围,牟宗三则不拘束于中国,而是学贯中西,以“一心开二门”架构沟通康德,试图以“呈现”转变“设准”,使“理论形上学”变为“实践形上学”或“道德形上学”。三、理解方法与表达方式不同。唐君毅更倾向中国式反省、推想、体认,如修道观念、成佛观念、反观理解;牟宗三更倾向概念分析,作中西概念对比,并试图沟通中西。当然二人都有分析与体认,只是比较而言,取特色鲜明处对比。
唐君毅认为“真如缘起”代表了中国佛教的圆融性,而牟宗三则认为“真如”还是过于纯净、孤悬(不接地气),其紧张感没有打破,不如天台“性具善恶”那么究竟。正是他们对“真如缘起”的理解不同,导致他们对很多思想的看法不同。通过对比就会发现,他们二人不只是在《起信论》这里产生异见,在其他部分的思想中,处处可见这种理念差异,而这种差异来源就在于此。
将唐君毅、牟宗三对于《起信论》的理解和诠释进行对比,有一定学术意义。正是他们二人的这种差异,反而有利于我们对《起信论》思想加深理解、全面把握,并丰富思考维度,扩充问题视角,增加诠释资源。这种不同诠释,为我们理解真如与无明、阿梨耶识关系等问题提供重要参考,对于我们理解唐君毅、牟宗三思想差异之由来,也有一定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