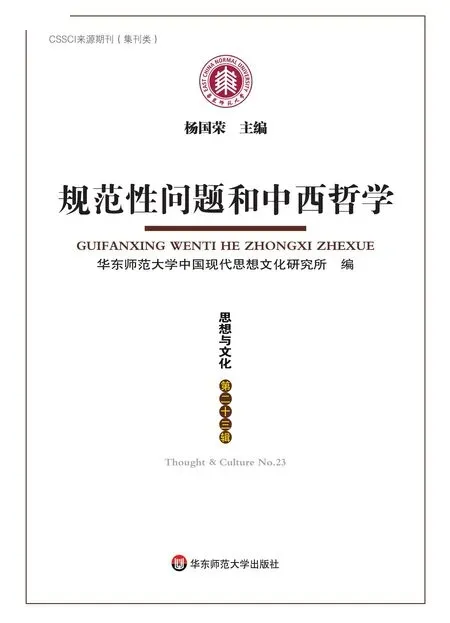儒家的自我修养与孟子的扩充概念*
2018-04-01
●
导论
当代道德哲学家,甚至是那些主要关注德性伦理学的哲学家,都不会花太多时间或提供很多细节去关注自我修养问题。然而在道德上改善自我的能力恰恰是他们所提方案的核心。我们能够改善我们自己,并且在某些情况下确实设法改善了我们自己,这种印象是我们的普遍经验,也是我们关于自己与他人的道德生活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注]对这一问题的一种现代亚里士多德主义进路,参见由Brad K. Wilburn撰写的尚未发表的博士论文: Moral Self Improvement, Stanfo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February, 1992)。另参见Myles Burnyeat, “Aristotle on Learning to Be Good,” in Essays on Aristotle’s Ethics, Amelie Oksenberg Rorty (ed.),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69-92。
中国的哲学家们,尤其是处于儒家传统中的那些哲学家们,已经对道德的自我修养问题给予了大量关注。绝大多数哲学家将他们有关自我修养的观点与一种相应的人性论联系起来,而这些理论极大地影响了这些思想家如何看待道德上自我修养的必要性,或者如何看待这种自我提高的最有效方法。然而,所有哲学家都相信道德自我修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还是好生活的关键性构成部分,并且它也是他们的大量伦理反思的主要焦点。
这篇文章关注一位早期中国儒家思想家孟子(公元前390—前305年)的思想。首先对他有关自我修养过程的一般结构的观点作一简短描述,但是我的主要关切点是孟子在如下问题上的看法,即一个人应当如何开始“扩充”(extending)本身固有的道德情感过程?[注]西方哲学对孟子道德扩充概念的研究肇始于倪德卫影响深远的文章,“Mencius and Motivation,” in Henry Rosemont, Jr. (ed.),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Thematic Issue S, Vol.47 No.3 (1980): 417-432。他在那个时候的立场由下文所讨论的第一篇信广来的文章所发展,并被随后的万白安的文章所批评。我们要考虑的下一篇文章,由黄百锐撰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倪德卫早期工作的启发。在他的被收进上述文集的文章中,黄百锐提供了对其观点的一个新解释,它显示出与我在此处所考虑的解释极大的不同,而似乎与我所提供并捍卫的解释更加接近得多。近来,倪德卫又再次回到这个主题上。在一篇经过重大修订和扩充的文章中,他展示了他的新解释,见“Motivation and Moral Action in Mengzi,” in Bryan W. Van Norden, (ed.), The Ways of Confucianism (Chicago: Open Court Press, forthcoming)。他的最新立场似乎更加接近于此处所维护的观点,尽管他对扩充的理解在细节上仍然是不清晰的。我将考察《孟子·梁惠王上》第七章,这段文字展示了这种扩充的一个著名实例。我将从我自己所知的哲学上最具重要性的一些解读来展开分析,并继续提供我自己的一个新解读。在结论中,我提出了一些方法,依据这些方法,从事于自我修养的早期中国人就能够被赋予有关道德生活的更加精确更为丰富的说明。
由于我的主要兴趣是对孟子扩充概念的初始阶段提供看起来最具合理性的解释,因此在文章开篇和最后部分我所提供的只是一个梗概,而不是一幅完整的画面。然而,我相信这些部分的内容能使主要的计划更多地面向那些不太熟悉孟子哲学的人。我还希望它们将证明,研究这种能使人获得更宽广的伦理领域的问题,其兴趣和价值是有启发性的。
孟子有关人性和道德自我修养的观点
孟子首先论证我们所有人都天生拥有端芽般的道德倾向或道德感(nascent moral inclinations or senses)。他称这些是我们的“端”——“道德上的萌芽”(moral sprouts),这一意象是极其重要的。[注]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上》第六章反复使用了“端”这个词。但是他也用其他词来揭示这一相同观念。例如,他在《告子上》第八章中使用了“蘖”和“萌”,以及在《告子上》第九章单独使用了“萌”这个词。他还使用其他的比喻来描述相同的一般观点。对孟子思想这一方面的讨论,参见我的Ethics in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The Thought of Mengzi and Wang Yang-ming, Revised 2nd Edition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pp.15-28。像其他的萌芽一样,这些道德倾向是自我的幼小柔弱而非成熟强大的部分。它们极易被忽略、被践踏或被连根拔除。它们也像初生的嫩芽那样充满活力,引人注目——不是潜伏的和隐藏着的——而且要是我们保护并供养它们,它们也会像嫩芽般成长和繁荣。这些相关的信念构成了孟子“人性善”主张的核心。他并没有做出我们已然是善的这样一种单调乏味且明显是错误的主张,而是认为我们生而好善,拥有一种向善的倾向性(a tendency toward the good)。
在这个阶段上,孟子的主张是相当谦逊的: 他只是表明,作为其本性的一部分,人们拥有某种道德敏感性(moral sensitivity)。这并不会给我们太大启示。一个人可以承认这样一种感觉是存在的,并且还可主张它对于行动而言是如此微弱的一种动机,以致它几乎从不引导我们的行动。然而,在我们进一步考察孟子如何继续论证之前,牢牢记住两件事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件事是早期中国人相信,心,“心智”(heart and mind),是这样一个器官,它包含认知(比如推理)能力、情感(比如情绪)能力——包括特定的道德敏感性——还有我们的意志力(volitional abilities,某种类似于但却不同于我们通常的意志概念的能力)。[注]孟子没有以任何令人满意的方式对这些能力加以分类,而且关于他的道德心理学的重要方面,例如像心灵受好的倾向所影响或牵制那样,其能够受坏的倾向影响或牵制到何种程度这一点也不清楚。他有关意志力的观点很粗糙,即我们拥有掌控心智的不同部分并集中注意力于其上的能力,从而在自我之内约束(或释放)不同的情感和意识因素。孟子论述道,正是这个器官必定引导着我们的生活道路。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这个“心智”拥有思考、衡量和判断我们所面对的各种抉择的能力。这是它的自然功能。如果想要了解我们真实的本性(nature),我们必须依据其自然功能运用我们的每一部分。[注]参见《孟子·告子上》第十四章和第十五章对这一论证的一个简明陈述。关于孟子思想的这个方面的更为完整的说明,参见我的Ethics in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pp.19-20。我们必须反思我们做出的选择和我们完成的行为,并准许心灵引导我们。
第二件需要记住的事情是,孟子有关所有人都拥有道德端芽的主张是一个“普泛的”(generic)主张。[注]Julius E. Moravcsik, “Genericity and Linguistic Competence,” Theorie des Lexikons, Arbeiten des Sonderforschungsbereichs 282, No.54 (Dusseldorf: Heinrich Heine Universitat, 1994).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有关我们称为人的这一类生物的正常、健全的典型主张。它并不意味着可被运用于在生物学意义上是人的每一个体之上。那些天生就有某种内在缺陷的人,抑或那些遭受某种外在伤害事件或在孩童时期就受到系统性虐待,结果在其行为中一向反社会的人,不能代表孟子主张的反例。这样的人并不是正常、健全人类的代表性范例。考虑一下像这样的主张:“海狸建造水坝”或“海狸在危险时就用尾巴拍击海水”。这些就是有关正常、健全的海狸在它们的自然环境中倾向于做什么的普泛性主张。如果你指出一只天生就没有尾巴或在某次事故中失去尾巴的海狸,抑或你指出一只生病的海狸,或者指出一只正处于沙漠环境中的海狸,而你又主张,这些是关于海狸“依其本性”倾向于去做的事情的两个较早主张的反例,那么你就恰恰误解了这种普泛性表达的特征和力量。孟子的如下主张,即要是突然看到一个快掉进井里去的小孩,所有人都会感到惊恐和担心,即是关于人的本性的一个普泛性主张。[注]孺子入井的例子,参见《孟子·公孙丑上》第六章。如果我们同意正常的人拥有这种善的端芽,并赞成孟子的功能论证(function argument)——这种论证把心智确立为自我的自然主宰——那么他只需更进一步为他的“人类显示了一种向善的自然倾向”这一主张举出一个貌似合理的实例即可。这个更进一步的主张关涉到道德行为的喜悦(joy)。孟子论证到,如果我们运用心智,依据有关我们行为的当前和更长距离的后果的充足知识,去对我们所做的事情进行衡量和判断,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每当做了一件善事,我们就能体验到一种特殊种类的喜悦和满足。反之,在相同条件下,每当我们反思自己干了一件不道德的事,我们将会体验到一种厌恶和羞耻的感情。孟子相信这种道德行为的喜悦将会滋养我们的道德端芽。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培育它们,随着其不断成长,它们就会授权我们去做越来越困难的善行。[注]例如,参见《孟子·离娄上》第二十七章和《孟子·告子上》第七章。因此,通过遵循本性,我们就倾向于善。
需要注意的是,正是对我们实际上所做的善事的沉思导致道德端芽的增长。仅仅思索善好的思想并不有助于它们的发展,尽管那可能会帮助我们搞清并领会在特定情形下我们应该做的事。同样的区别对于身体锻炼或掌握一种像拉小提琴这样的技巧也是真实的。思考俯卧撑永远也不可能使一个人更强壮,思考练习音阶也永远不可能使一个人成为鉴赏力高超的小提琴手。一个人必须去从事这些练习以便体认并领会它们的善好价值。就一种高水平的有判断力的意识是成功的必要条件而言,道德行动的情况在这方面更接近于演奏小提琴而不是做俯卧撑。一个人必须不仅要恰巧做得好,他还必须认识到他正很好地在做,以便感受道德行动的特殊喜悦。[注]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知道一个人正很好地在做,其确切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我的观点是,它在最低限度上需要这样一种认知,即认识到一个人的行为与其内在道德感相关联,并受这种道德感所激发。然而,对一个人之运用其道德感及其对这种道德感之理解的通盘把握,认为它是人性最好面向的一种表现,这也是“知道”一个人正很好地在做所意指的方面。我将此看作是仅仅在道德自我修养的更高层面上的发展。我们的理解、实践和满足感与另一个人的一起发展。我们还必须要把一个区分牢记在心中。孟子说,对道德行动的沉思产生了一种复杂的喜悦(joy)感觉——不是快乐(pleasure)。在做正确的事情时,我可以感受到深深的喜悦、成就和满足,而发觉不到稍稍的快乐。比如,如果我的一个妹妹需要做一个肾移植,我想到我会有勇气捐献一个肾给她。考虑这一行动,在知道我做了正确的事情时,我会感受到一种特殊的喜悦。然而,我不会强调这是令人愉快的(pleasant)。孟子认为善好的生活(the good life)引起喜悦和满足——而不必是愉快(pleasure)。有时候做正确的事情要求严峻的艰苦和令人极其不愉快的牺牲;偶尔它还可能号召我们奉献生命。然而,善好的生活是体验了解一个人生活得好的喜悦的唯一方式。
注意到如下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即孟子并不是在说做正确之事的喜悦和满足就是使得一个给定行为正确的东西。使其正确的是它依据于我们的本性并体察到了天道(Heaven’s plan)。一个给定行为的喜悦令其显得正确,而正是这种情感使自我修养成为一种实践的可能性。这后一点对于有关自我修养的所有伦理学都是真实的,至少对那些并不依赖于某种未来生活或彼岸奖赏的人来说是真实的。自我修养必定以某种清晰而又当下直接的方式产生满足,因为这就是让我们得以提升的动力。如果善好的行为经常让我们变得丑陋、悲惨或恶心,就不会有任何神志正常的人去追求或劝谏它们了。
孟子从未主张我们内在的道德倾向性自身就将导致道德的发育。这些只是德性的发端(the beginnings of virtue),它们需要我们的关注和努力以使其成长为真正的德性。孟子将人们引向自我修养道路的方法是由从他们之中激发出他们的自发道德行动开始的。[注]伦理学的绝大多数当代进路倾向于聚焦道德两难事例和两难抉择的时刻,这些进路专心于人类生活的时间切片或道德片断。中国人却倾向于根据实践和某种步骤来处理伦理问题,这种步骤需要我们以某种被设计出来的反思和行为举止经常性地加以践行,以改变我们的能力、态度和习惯。他们感兴趣的不是抉择的时刻,而是使人们朝向特定的方向,让他们处于(正确之)“道”(the dao or Way)上。在下面的结论处我还将返回到这一问题。对孟子来说,认识到我们拥有道德端芽是道德自我修养过程的第一步。正如我在下面将要论述的那样,对合宜的道德反应事例的沉思在道德施为者中激发了合宜的情感反应,并帮助她识别出道德关切的突出特征。
当我们逐渐意识到并开始理解我们的道德感时,孟子又敦促我们发展这些情感,并将之运用于其他合适的关切对象上。做到这一点的一个方法是通过对来自于历史的典型范例的学习。[注]例如,参见《孟子·公孙丑上》第二章中孟子对勇敢和圣人形象的讨论,或者他在《公孙丑上》第九章对“圣”(sageliness)的讨论。他运用这些讨论开始了日益精细的区分,并对这些卓越品质提供了一种更为细致入微的感知。应该注意历史上的典型范例也有助于阐发即兴创作并做出例外的需要。比如,参见《孟子·万章上》第二章。这些范例,为我们思考那些让我们领会到道德生活的形式特征(例如,一种运用的普遍一贯性也允许有特例)和适宜情感(例如,对他人的关切)的人,提供了道德上具有教化意义的榜样。[注]这些范例是向那些可能会扭曲和破坏道德发展的解释开放的。孟子通过坚持需要在某人的经典解释中加以引导的方式尝试巧妙地处理这一问题。例如,参见《孟子·尽心下》第三章。这样的范例也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和方向;它们给我们提供道德“脚本”(scripts),并鼓励我们尝试这些脚本。[注]我从K. Anthony Appiah那里借来“脚本(scripts)”一词。参见他的“Identity, Authenticity, Survival: Multicultural Societies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In Multiculturalism, Amy Gutmann (e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60. Appiah用这一术语来形容“人们能用来形成其生活计划并用来讲述其生活故事的叙述”。这是一个虽然相关但在某种意义上又比我心目中所想的稍有夸大的概念。他还担心这样的脚本如何能够约束一个人的自主性,特别是当他们与这样一种观点相关涉时,这种观点即: 一个特殊性别或种族的人们“被期望”应该做什么。这种学习让我们开始从事于认知、情感和实践的层面。[注]对于道德自我完善的这三个方面以及它们如何相互作用的讨论,参见Brad K. Wilburn, Moral Self Improvement.中国人更喜欢从历史中鉴古知今,而不是从虚构中借取榜样。尽管后者经常为儒家提供(尤其是)在伦理叙述中所重视的那种细节描述和微小差别,但它也可能提供不切实际、过度夸张的理想。[注]对历史的学习在儒家的道德教育中总是发挥着核心作用,并可凭此将儒家从其他思想学派如道家和法家中区分出来。早期儒家对待历史及其在道德自我修养中的作用的态度不同于休谟。玛莎·C.纳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曾论证道,文学以及尤其是小说在我们的伦理生活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参见她的Love’s Knowledge: Essays o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尤其参见第5章“‘良知良能’: 文学与道德想象”(“‘Finely Aware and Richly Responsible’: Literature and the Moral Imagination”)。另外,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虚构小说中的人物角色在如下意义上是抽象的,即他们与任何现实的人都没什么关系。相反,历史榜样却被认为是文化上和道德上的祖先(ancestors)。有人可能会争辩道,这种对历史的偏好恰恰是另一种表现,即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更喜欢从现实的具体榜样向更广泛的目标和理想提升,而不是从某套抽象、理想的原则下降到特殊的实例中。无论这些榜样是历史上的还是虚构的,在我们自己有关合宜的“角色榜样”(role models)的概念中可以发现这种一般敏感性在发挥作用。
孟子又提出了另一种方法来发展我们的道德敏感性,这种敏感性在被称之为“礼”(rites)的实践中处于核心位置。儒家的礼包括从大型国家宗教仪式到我们会称之为礼节(etiquette)的一切。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些可能会由某位总统的国家葬礼、阵亡将士纪念日的仪式或会见和迎接到访者的实践礼仪来表现。在儒家传统中,这种倾向性必定会将这些实践视为赫伯特·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在他那富有卓识的著作《孔子: 即凡而圣》(Confucius:TheSecularasSacred)中所称的“神圣礼仪”(Holy Rite)的不同方面。[注]Herbert Fingarette, Confucius: The Secular as Sacre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2.尤其参见第1章“作为神圣礼仪的人类群体”,芬格莱特对礼的向心性的讨论不仅是正确的,它还标志着对儒家思想的现代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时刻。他分析的其他方面存在更多争议,并且与此处所展示的理解有所差异。我会称“礼”为“社交仪式”(social ritual)。
社交仪式提供了另外一种我们能够发展我们的道德敏感性的方式。比如,欢迎的规范仪式,带着一种对它们能促进友好关系的功能的正确意识来加以实践,就能为我们提供绝好的时机来发展和理解对我们人类同伴的关切之情以及与他们团结一致的情感。一种令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榜样是葬礼仪式,它提供深切的时机,不仅使我们能够缅怀失去的亲人,而且还会让我们反思与他人的关系和对他人的需要,以及我们自己生命的过程和意义。[注]葬礼仪式,尤其是一个人父母的葬仪,对孟子和所有儒家人物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例如,参见《孟子·滕文公上》第五章。要再次注意孟子展示的不仅是那些精心编排、规范标准行为的案例,而且还有那些在其中普通礼节实践由于例外情形而被修正或被抛弃的例子。例如参见《孟子·离娄上》第十七章和《孟子·万章上》第二章。
孟子所主张的我们能够发展道德敏感性的另一个方法是在类似的、道德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例之间做出或注意去做出恰当的类比。[注]提出孟子运用类比问题的第一个人是刘殿爵。参见其文章,“On Mencius’ Use of the Method of Analogy in Argument,” reprinted in D.C. Lau (trans.), Mencius, London: Penguin, 1970, pp.235-263。然而,尽管刘殿爵确实讨论了孟子运用各种类比以澄清重要伦理观念的诸多案例,他却没有考察类比在涉及典型道德反应的案例中的运用。这后一种案例是由倪德卫在他对孟子的扩充所作分析中第一次加以讨论的。参见本文上面的注释。另参见David B. Wong, “Reasons and Analogical Reasoning in Mengzi,” in Essays on the Moral Philosophy of Mengzi, Liu Xiusheng and Philip J. Ivanhoe (eds.), Indianapolis/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2002, pp.187-220。例如,在我们下面将要考察的段落中,一位正要沿着道德的道路迈出他极不情愿的第一步的君主表现出如下一点,即他对一个苦难事例具有一种恰当的情感反应,但在另一个同样清晰的苦难事例上却又无法具有这种反应了。这暗示着一种对两个事例都甚为了解的意识以某种方式有助于影响对第二个事例的恰当反应,也就是说,“扩充”(extending)君主的道德敏感性。某些解读者曾提出这两个事例之间的认知相似性(cognitive similarity)在扩充过程中将发挥直接而又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将证明,在道德自我修养的这一早期阶段上,这两个事例之间我称之为“类比共鸣”(analogical resonance)的东西包揽了绝大部分的工作。这并不是说随着一个人的道德能力和理解力的增长,这种类比性的认知方面不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相反,我会表明一个人的道德能力的增长,当其发展到一定层次时,在很大程度上就会由这个人对道德生活的此种特征的理解力所决定。我的观点是在与一个极端观点相对照之下提出的,这个极端观点认为,一种对这两个事例之间类比性的认知理解力在第二个事例中保证了或产生了一种相应的情感反应。尽管我将要讨论的解释中没有任何一个解释提倡这样的极端观点,但它们却是倾向于它的,而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并不赞成在我将要考察的那段话中孟子强调的是情感共鸣,而不是认知类比的作用。
《孟子·梁惠王上》第七章事例中孟子的扩充概念
我要分析的这段话对于那些熟悉《孟子》文本的人来说是烂熟于心的: 《梁惠王上》第七章中孟子与齐宣王的讨论。一番公开的交流之后,齐宣王触及本质地问孟子,某个像他自己这样的人能否成为一个真正的王,以及需要拥有何种条件才能成为那样的王,即一个能统一整个天下,将天下置于他的统治之下的王。齐宣王知道孟子相信只有在道德上善好的人才能成为这样一个真正的王,而齐宣王的问题隐含着他自己的怀疑,即他并不拥有这种必要的能力。
孟子回答说,王确实拥有这样的条件,并且说他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他从别人那里听到的一件事情。根据这一报道,齐宣王最近舍不得一头牛,他注意到这头牛正要被牵去宰杀以用于祭礼,他命令用一只羊来代替。齐宣王确认这件事确实发生过。经过进一步的讨论,孟子使王相信他吝惜这头牛的唯一理由是他对它表示怜悯。正如齐宣王所说:“我不忍心看到它害怕地颤抖的样子,就像一个清白无辜的人正走向死刑之地一样(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注]参考刘殿爵《孟子》英译本,Mencius, London, Penguin Group, 1970, p.9。
孟子继续说,这件事表明齐宣王拥有成为一个真正的王的基本能力,也就是说,他具备一种道德心智(a moral heart and mind)。因此,“之所以没有给人民带来和平,是因为你没有践履仁慈……你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王,是由于拒绝去做,而不是因为没有能力去做(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注]同上,第10页。更进一步地,孟子解释道:“你需要做的就是将此心(或敏感性)运用于那个地方而已。以这种方式,一个扩充其仁慈的人就能为四海之内带来和平……古代人超越于其他人的一个方面只不过就是善于扩充他们的所作所为罢了。现在你的仁慈足以达及动物身上,而你的努力却还没有扩充到人民那里。这是为何呢?(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注]同上,第10页。
确切地说,孟子要齐宣王做什么?很显然,孟子的最终目的是让齐宣王成为一个好人,或至少是一个更好的人。这样的一个结果将是他会更加仁慈地对待他的人民。但是怎么能认为这个吝惜牛的例子会促成这样的目的呢?在一篇谨慎论证的重要文章里,信广来(Shun Kwong-loi)[注]Shun Kwong-loi, “Moral Reasons in Confucian Ethics,” in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Vol.16 No.3-4 (1989): 317-343.指出孟子将此事件作为一个案例提供出来,在其中齐宣王的道德感成功地激发了合宜的行动: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齐宣王为之感到同情而遭受心灵痛苦并恰当地行动予以缓解之的案例。表明这一点之后,孟子又指向人民,他们的处境代表另一种遭受痛苦的清晰案例。齐宣王将会看到他在这两个案例之间缺乏一致性,那么这一认识就开启了某种程度上在第二个案例中产生恰当情感反应的进程。然后齐宣王就会成功地将他的富有同情心的反应从动物的案例扩充到人民的案例中。正如信广来所说:“他同情牛是对牛所遭受痛苦的一种反应。知道这一点,并且还了解他的人民所遭受的痛苦,齐宣王应该明白他也要对他的人民抱以同情。明白了这一点,他就应该在实际上逐渐拥有了这种同情,从而也就完成了扩充的过程。”[注]Shun Kwong-loi, “Moral Reasons in Confucian Ethics,” pp.322-3.
然而,正如万白安(Bryan W. Van Norden)所表明的,对齐宣王来说,在消除了其对牛的同情时,一种同样的一致反应也将起作用。[注]Bryan W. Van Norden, “Kwong-loi Shun on Moral Reasons in Mencius,” in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Vol.18 No.4 (1991): 355.万白安提出了其他反对意见,并且提供了他自己的富有洞见和原创性的解释。我当前的工作与万白安的绝大多数分析相一致。实际上,根据以下事实来看,他对牛的吝惜看起来有点愚蠢,这个事实就是他只是用另一只生物(羊)替代了正遭受痛苦的生物。万白安令人信服地表明,一致性并不支持巩固孟子所诉求的东西;它似乎并没有在扩充的这一案例中扮演任何重要的、具有因果关系的角色。孟子也没有清楚地主张对不一致性的认识就是引起针对人民怜悯感情的那个东西。万白安指出,孟子试图让齐宣王将其注意力集中到在民众痛苦的案例中表现出来的他的道德感上:“他正将宣王的注意力引到现实(民众痛苦)的那一面和宣王自己的意向结构上去,相信这种注意力的集中将会增强宣王意向结构的那个方面。”[注]Bryan W. Van Norden, “Kwong-loi Shun on Moral Reasons in Mencius,” p.365.
这是一个明显更好的解释。在其诸多优点中,这一解读看到了孟子目标在牛和民众的两个案例中更大的相似性。因为在每一个案例中孟子都没有为宣王提供道德地(也就是诉诸一致性和合理性)行动的理由。然而,尽管万白安的批评是决定性的,他的说明也是正确的,他的分析并没有充分地解释在扩充的行动中被认为发生了什么。因为正如万白安所主张的,如果孟子只是“将宣王的注意力引到现实(民众痛苦)的那一面”,那似乎无需先前那个牛的例子他就能做到这一点。在万白安的说明中,牛的案例所扮演的唯一角色就是确定宣王确实拥有感受同情的能力。他已经确定,这个例子很明显要达成这个目标,并且也确实实现了这个目标,但我相信它也实现了其他目标,对于随后的扩充行动而言是决定性的那些目标。
黄百锐(David Wong)提供了有关《孟子·梁惠王上》第七章那段文字的另外一种引人关注且颇富启发的说明。[注]David B. Wong, “Is There a Distinction between Reason and Emotion in Mencius?” in Philosophy East & West, Vol.41 No.1 (January 1991): 31-44.他指出那种特定的情感,尤其是那些我们称为道德情感的特定情感,显示出拥有相当精密复杂的认知维度。这些维度不仅解决了由苏隆德(Ronald de Sousa)如此予人启发地讨论过了的框架性(framing)或突出经验(salience)问题[注]Ronald de Sousa, The Rationality of Emotion, Cambridge: MIT Press, 1987.尤其参见他在第七章对“salience”的讨论,等等。另参见Nancy Shermand在其著中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特殊例子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Making a Necessity of Virtue: Aristotle and Kant on Virtu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39-52。,而且它们也证明,为什么道德情感为那些并不能被归属于行为者自己的欲望,而是要依赖于另外一个人的处境或状态的显著特征的行动提供理由。比如,关于怜悯(compassion)的情感,黄百锐说:“怜悯由于某种对它所针对的情境构想出来的特征而与其他种类的情感区别开来。怜悯的意向对象使一个有情者(a sentient being)正遭受的、现实的或即将来临的情境之特征变得突出显著。”[注]David B. Wong, “Is There a Distinction between Reason and Emotion in Mencius?” p.32.
我想集中于黄百锐对这种道德情感解释的另一个方面,即他的有关像怜悯之类情感的内在普遍性的主张,因为这一点直接与孟子的扩充问题有关。黄百锐说:“在将怜悯解释为包含一种认知维度时,由于如下事实,即另一个人的苦难被直接识别为行动的理由,那就存在一种应用的普遍性含义。将一种情境特征识别为以某种方式行动的一个理由,伴随着如下假设,即一种相关的情境特征将会构成相同的行动理由。”[注]Ibid., p.34.
克雷格·井原(Craig Ihara)提供了对黄百锐分析的富有洞见的评论和某些批评。[注]Craig K. lhara, “David Wong on Emotions in Mencius,” Philosophy East & West, Vol.41 No.1 (1991): 45-53.他用这样一些话来总结黄的立场:“黄的主要论点是,情感,包括怜悯,并不仅仅是情感性的(affective),而且在两个重要层面上还是认知性的(cognitive): ⑴它们影响了一种情境中表现突出的那些特征,以及⑵它们识别出作为行动理由的突出特征。”[注]Craig K. lhara, “David Wong on Emotions in Mencius,” Philosophy East & West, Vol.41 No.1 (1991): 45.井原接受了第一个主张,即上面提到的框架性问题,但却拒斥了后一个主张,不仅作为孟子观点的一种描述,而且也作为对普遍道德情感的一项说明都加以拒绝。由于在这里我的主要兴趣是发展出对《孟子·梁惠王上》第七章中所发生的事情的最具合理性的解释,我将不去回顾井原反驳黄百锐作为对道德情感之普遍说明的第二个主张的论证(尽管一般而言,我与井原共享这方面的观点)。相反,我将指出他之反对这一主张的论证,作为对孟子的一种解释,主要是揭示了单纯证据的缺乏。他说:“就一个人所能确定的而言,……对齐宣王来说所必需的一切就是察觉到民众的苦难,而那就将自然而然地唤起怜悯的情感。没有迹象表明,在他能够做到这一点之前,他必定或明确或含蓄地拥有了那种认知,即所有有情众生的苦难是付诸行动的一个理由。”[注]Ibid., p.52.
我同意井原对黄百锐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析。当他声称将苦难看作是付诸行动的一个理由,就使如下信念成为必要,即所有有情众生的苦难是付诸行动的理由,他可能稍微夸大了这个案例,但是他的如下观点是对黄百锐立场看似合理的表述,即有必要以这样的理由识别出某些相当高层次的一般性,如果不是普遍性的话。然而,就像在先前的解释中一样,这一分析给我们留下了有关本性(the nature)和扩充地位(status of extension)的疑惑。因为要是为了唤起齐宣王的怜悯之情,“对宣王来说所必需的一切就是察觉到民众的苦难”,对于孟子关于牛的案例的讨论就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清晰的目的。我们可以将井原看作是提供了齐宣王可能会意识到并发展他的道德感的另一种方式——当面临真正的苦难事件时,注意到它(道德感)的表现——但是这并没有解释我们在《孟子·梁惠王上》第七章文字中所发现的扩充范例。
在他更早的评论中,井原似乎说,在齐宣王与孟子的对话过程中,扩充的行动真实发生过:“看上去最多不过是如下情况,即齐宣王慢慢理解了正是怜悯之心在牛的事例中触动了他,由于牛与一个清白无辜的人的相似性……”[注]Ibid., p.50.我说井原“似乎”是在说这一点,理由是他自己在这句话上所作的限定性条件,以及我所看到的在这句话和我紧接着上面引用的几句话之间的张力。我认为井原说的是,当齐宣王把牛比作“一个被引向死刑之地的清白无辜之人”的时候,他已经感受到(或许甚至意识到了他的感受)对无辜民众苦难的怜悯之情,并且这就引起(或触发)了他对牛的怜悯。他之将牛类比为“一个被引向死刑之地的无辜之人”是一个颇富想象力的联想,寄生在他已经拥有的两种情感反应上,即对某个过去的无辜者和对当下的牛的情感。在这两种反应中我根本看不到任何因果性的联系(井原的话也并不意指这一点)。不管怎样,我们仍然需要追问的是对如下问题的一个解释,即在牛的事例中的情感如何能被扩充到齐宣王的民众事例中。
我回顾这两个较早的解释以及对它们的回应的理由现在可能更为清晰了。我将这两个解释者看作是以一种类似的方式进行论证,就孟子的观点来看,这就形成了一种相似的错误。无论是信广来还是黄百锐,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把《孟子·梁惠王上》第七章中孟子的扩充视为涉及到为道德行动提供抽象、普遍的理由这个层面上。对于信广来而言,这一点就在于在两个相关的类似事例之间要求情感的一致性。对于黄百锐来说,齐宣王应该将他的同情心在民众的事例中加以扩充的理由,已经展现于任何真正的同情行动中了,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任何这样的行动都将包含于对减轻痛苦的一种普遍要求的认知之中。我所讨论的两种回应则展示了我认为是对这些企图的重要批评的内容,并指向我在这里将要提出的解释,但是这两者都没有为我们提供对《孟子·梁惠王上》第七章中出现的孟子扩充概念的合理说明。
在这段话中,孟子所关注的主要是使齐宣王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对其民众有所感。齐宣王正被引向道德生活,成为这种生活的一个极不情愿的生手。他是一个麻木不仁的家伙,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禽兽一样的家伙。孟子正尝试使他迈出第一步,企图使齐宣王明白他拥有一种道德感,感受到其力量,并将它扩充到他的民众身上。我们必须体会孟子这样一种方式是多么独特。与孟子不同,亚里士多德并未意识到如下情况有任何必要,即为了发展一种道德人格就必须从一开始就要辨认并保证我们的道德感。可能更令人震惊的是,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儒家传统的创始人孔子,或先秦最后一位伟大的儒者荀子,在这一事件上与孟子拥有同样的看法。
在《孟子·梁惠王上》第七章中,孟子并没有试图使齐宣王接受一种关于道义理由的观点,而且这样的理由在实现其主要目标方面也不能起到任何直接的作用。正如万白安所指出的,被设计出来的孟子关于牛的事例的原初讨论是要表明,齐宣王确实具备孟子断言的道德感,他被要求成为一个真正的王。除了确认齐宣王确实拥有这样一种道德感之外,孟子与他的对话使他明白(1)这种道德感感觉起来像什么,(2)它的某些普遍特征是什么,以及(3)如何着手去寻求它,关注它,并鉴别它。通过回想牛的事例并让他发挥想象力回忆他的领会及其对这种领会的反应,孟子给齐宣王上了第一堂课。这种对此事件的自觉回想不同于齐宣王所经历的原始情感。回想要求运用想象力,从而开始一个解释的过程,并且对于这个扩充过程而言,理解是至关重要的。通过让齐宣王为其行为思量可供选择的解释,并让他谈论有关牛的事例中是什么打动了他,令他如此去做,孟子给他上了第二堂课。齐宣王对这头牛的遭遇产生的那种联想,即“一个清白无辜的人正走向死刑之地”,正是这种对其真正动机的处于发展中的理解的一部分。最后,通过指导齐宣王如何去反思他的动机,孟子又给他上了第三堂课。他引导齐宣王集中精力于怜悯的特殊情感上,将其与其他情感相区别,并鉴别出与这种情感相关联的特殊满足。一旦齐宣王被引导着理解并识别出他的真正动机,他就“高兴(说)”起来,引用《诗经》:“别人有什么心思,我能揣度出其真实的意思(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然后说,“这正是你所说的意思啊(夫子之谓也)。”[注]参见刘殿爵,第9页。刘殿爵没能将这行《诗经》引文之前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说”字译为“高兴”(pleasing)。
有了这些课程在手,孟子之后又引导齐宣王关注民众的事例,一个在道德感知上更其复杂、更为困难的事例,并敦促他重申他在这种新情况下所学到的东西。他希望齐宣王在这第二个事例中也能体验到一种相似的恻隐之情,不是因为某种一致性的内在需要,或者考虑到对减轻痛苦的普遍要求的某种认可,而是因为他相信齐宣王在这个事例中必定将体验到一种类似的反应——只要他能拿出一点努力。早先的体验已经教会他恻隐感觉起来像什么,它的某些一般特征是什么,以及如何着手去追寻它,关注它并识别出这样一种情感反应。有了这样的体验和反应之后,齐宣王现在就对恻隐有了期待。这种预期就是,在这两个事例之间的类比性共鸣将引导齐宣王去寻求、关注并识别出第二个事例中的道德反应。如果他这样做了,他就将成功地扩充他的恻隐之心。
在另外几段同样著名的文字里,孟子把道德感比作我们对美味的食物和动听的音乐的喜爱。[注]比如说,参见《孟子·告子上》第七章。他相信一个道德上的行家或圣人就像是一位伟大的厨师或音乐鉴赏师一样,对于我们每个人都具备的某些能力和感觉的事物拥有更加敏锐和精确的鉴赏力。[注]关于孟子思想中道德鉴赏力观念的敏锐而富有洞见的考察,参见何艾克(Eric L. Hutton)的文章“《孟子》中的道德鉴赏力”(Moral Connoisseurship in Mencius)。[译者按]何艾克的文章参见刘秀生、艾文贺主编: 《孟子道德哲学论文集》,第163页以下。让我们从这些相关的艺术中考察两个例子以解释《孟子·梁惠王上》第七章中所发生的事情。第一个例子,教一个学生明白一个大七和弦听起来像什么。[注]这样一种和弦竟然出乎意料地在瓦格纳(Wagner)的名曲《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Tristan and Isolde)的前奏曲中听到了。感谢肯达尔·沃尔顿(Kendall L. Walton)为我提供了这个例子。这个和弦被用一个主音孤立地演奏给她听。它又以同样的主音与其他和弦相对照,并用不同的更为复杂的和弦进程演奏出来。这个过程被重复了好几遍,直至她能够经常地鉴别出这个大七和弦为止。她完全能够做到这一切,而不用知道她的和弦的名字,不用知道它与在跟它相比照时弹奏的其他的音和弦之间的确切关系,也无需关于音阶、和声或和弦的任何理论性掌握。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类比捕捉到了我认为孟子在他与齐宣王讨论牛的事例中所做的事情。他让齐宣王体验到了这个和弦(比如,恻隐之情),理解了它与其他和弦(比如可能会引发这种反应的其他情感以及过去打动过他的类似情感)的不同并发展了鉴别并关注它的能力(例如,集中精力于它,熟悉它,并识别出与它相关联的那种满足)。
现在我们的学生又移到了一个新音节上。各种各样的不同和弦都被演奏给她听,包括她已经学会辨别的那个和弦在内,然后要求她辨认出她的和弦。她在想象中回忆她的和弦的感觉,它与她所听到的其他和弦的差别,以及她是如何找出单独属于她的和弦的那个熟悉而又独特的品质的。需要注意为了做到这一点,她必须像齐宣王在牛的事例中所做的那样,发挥想象力重构并再次体验原初的感觉。正是这种富于想象力的重构,因其更加精确和精力更为集中,才与她产生共鸣并帮助她,在她当前的听觉刺激范围内鉴别出她的和弦。这两个例子显然是相类似的,但是单独对这种类似性的识别并不是在第二个事例中带来恰当情感的那种东西。正是这两个事例之间的共鸣才产生了所渴望的结果。以这种方式,她再次成功地挑选出她的和弦。而且,如果她把自己的课程学得够好,她就变得能够在一片互相干扰的杂乱声音里觉察到她的和弦。以同样的方式,孟子希望齐宣王也能从其他强烈的情感(如他对征服、情欲、财富和权力的渴望)中抉择出他的恻隐之情来,正是那些欲望阻止他关心他的民众。
如果齐宣王能够理解这些基本课程,他就会经常运用他的道德感。假如他确实这样做了,那就会有这样的运用足够刺激他采取行动的时机。对这种成功行动进行反思,反过来又会以我对孟子的自我修养的公开说明中所描述的方式加强他的道德倾向性。要是他坚持并持续停留于此道之上,他那刚刚涌现出来的倾向就将最终成长为完满的道德德性。他可能会适时地达到孟子的层次并显示出一种闻知并集中于其道德感上的教养能力,即使当它极其模糊微弱,几乎被干扰所淹没。此外,他将有能力辨别它是如何能够通过不同键盘的多样性,适应多种和弦的连续前进和组合(如其他的情感)的,以及这些又是如何以数不胜数的方法被安排以产生和谐的旋律的。在这些专门知识的更高阶段上,齐宣王可能会更加意识到这种情感的各种实例之间的一致性,并逐渐对道德生活拥有一种复杂和精致的抽象理解。确实,正如应该明确的那样,我将论证需要这种知识以便成为一个道德行家或圣人。然而,齐宣王并不需要这个以完成《孟子·梁惠王上》第七章中所描述的类比共鸣。[注]尚不清楚的是,孟子认为一个人要成为圣人,需要多少理论性的知识。与亚里士多德不同,他似乎曾在相当高的程度上相信自然的美德(natural morality)。某些极其稀有的个体似乎天生就拥有敏锐而又强烈的道德感,正如有些人天生就在辨别口味和味道上具备突出的完美感觉或超强的能力和敏感性。比如参见《孟子·尽心下》第三十章和《孟子·尽心下》第三十三章。
一个人能很容易地了解在烹调敏感性中也确实可能并经常会发生同样的过程。为了培养某人的味觉,他就要去接触像苦或甜之类的味道,像杏仁或牛至之类的口味,以及像在一杯红酒当中,在那些典型的、“唾手可得的”事物中的错杂的印象。[注]彼得·雷尔顿(Peter Railton)在他的《审美价值、道德价值与自然主义的野心》(“Aesthetic Value, Moral Value, and the Ambitions of Naturalism”)一文的开始部分提供了一个有关酒类鉴赏的卓越例子,此文载于Aesthetics and Ethics: Essays at the Intersection, Jerrold Levinson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59-105。他的文章对与人们在几个早期中国儒家思想家中发现的东西相类似的审美和道德价值提供了一个说明。与一位鉴赏师(或至少是一位好的厨师)讨论这些体验的特点,并学着去识别、孤立和品尝它们,即使当它们的存在极轻微,或者发现它们被混杂在更为复杂、压倒性的组合之中时。一个人通过类似的共鸣扩展这种敏感性,并且伴随着每一次练习,他做到这一点的能力就会得到发展和精细化。然而,在学习的早期阶段上,体验和教师的引导通常是导演和驱动此过程的因素。当然,在一种给定的味道或口味的两种不同体验之间存在着通常的一致性,并且比如说,某种我们称之为“杏仁味道”的东西将这些与其他体验这一味道的事例混合在一起,但是这些抽象的概念并不领先于也并不生成第二种以及随后的体验,这显然是真实的。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是相反的情况,它们起源于这些连续不断的体验,并构成了另一种更富理论水平的理解。
根据孟子,我们以发展和扩充其他敏感性——比如美食和美酒的味道或对爵士乐的欣赏——的同样方式发展和扩充了我们的道德敏感性。上述这些,以及其他的艺术激起了人的本性中内在固有的能力和倾向。然而,将它们之中的任何一种发展成为适当水平的教养就要求高尚品质的齐心协力。这种努力需要认知、情感和实践的一种联合。成功地培养这些敏感性要求我们接受高尚品质的影响;拥有良好品质的环境和好的教师经常会从根本上决定常人能否成功地培养这些品味。孟子承认几乎每一个人在能够去关心任何道德发展之前都需要基本的生活必须品。[注]例如,参见《孟子·告子上》第七章。另外,他相信我们大多数人至少在刚开始道德理解的过程时,都需要君子典范的激励和榜样作用,以及实践的规范——礼。当然我们也必须关注完善自我的目标并朝该目标努力。
在自我完善的过程中,将存在这样的时刻,即认知识别、引导情感和行为元素: 一个人领会并指向各种事例之间的相似性,被鼓励去寻求相应的情感。在其他时刻,情感反应将先于并鼓舞认知和行为元素: 一个人在看到其父母未被掩埋时感到恶心憎恶,或对一个将要掉进井里去的小孩感到惊心并表示关切,而这些反应引导他考虑如何处理这些困难的情境。还有另一些的时候,行为元素将导引认知和情感元素: 一个人在他完全领会或在情感上欣然接受这种行为是正确的以前,就学会了以礼仪向他人致敬并服从于老年人。[注]一个认知识别、引导情感和行为的例子,参见《孟子·梁惠王上》第四章。(对于这个例子,我要感谢何艾克。)情感反应起导引作用的例子,参见《孟子·滕文公上》第五章和《孟子·公孙丑上》第六章。(这两段文字描述了上述关于未埋葬的父母和将要掉到井里去的孩子的相关情节。)行为引导认知和情感的例子,参见《孟子·告子下》第二章。《孟子·离娄上》第十七章开始于我们第三种类型的事例——反对男女授受的通常禁忌——但是却用我们的第二种类型的例子——人的情感反应——颠覆了这一禁忌。
孟子不同于其他的道德自我修养者,例如亚里士多德,他主张道德发展发端于对某种前反思的道德倾向性的意识。如果我们的道德发展取得了成功,这些初期的道德情感必须被保留在道德发展的核心,因为按照孟子的观点,要是我们不从事于它们,我们就不可能完善自我。尽管道德自我修养的过程涉及论证、类比、想象、学习和反思,但这个过程却是围绕对我们的道德端芽的识别、承诺和培育而展开的。
在《孟子·梁惠王上》第七章中,我们看到孟子教人去确认、关注并鉴别他初期的道德感。孟子首先通过详叙牛的故事来做到这一点,这是一个有关齐宣王在行动中的前反思的恻隐之情的清晰例子。然后孟子又通过我称之为类比共鸣(analogical resonance)的东西力图引导齐宣王将这种情感扩充到他那正遭受苦难的民众那里。我将这一过程看作是被设计出来以增强齐宣王的敏感性和认识的一种治疗,而不是将其看作是由对行动之道德理性的本性的抽象理解所驱动,我的立场不同于我曾讨论过的那些论者。当人们沿着伦理之道(“Way”)前进时,他们将在不同程度上发展黄百锐和信广来所描述的那种理解。这种发展了的道德端芽将会识别出激起道德行动之关切的通常本性和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的需要。[注]我所关注的仅仅是在《孟子·梁惠王上》第七章中所阐述的“扩充”(extension)的特殊形式。在其他段落里(例如《公孙丑上》第六章和《尽心下》第三十一章等),孟子描绘了可能应该被认为是道德生活的这一通常特征的其他形式,而这些形式或许与黄百锐或信广来的说明更为一致。孟子的扩充是一种复杂现象,我并不会宣称在当前的研究中提供了一种完全的分析。当然存在道德的一种普遍性,但是根据孟子,它的普遍本性并非来源于有关一致性或可普化性(universalizability)[注][译按]译者采纳了沈清松先生对universalizability一词的使用方法而将之译为“可普化”,参见沈清松:《海外新儒家与西方哲学如何沟通?》,http://blog.sina.com.cn/s/blog_12ca105410102vfsa.html。的概念。毋宁说它涌起于一系列先天固有的道德感,孟子相信这种道德感是被所有人共同拥有,并且它们构成了人们独特的、与众不同的天资禀赋。因此我们发现,他的道德主张的终极基础诉诸于人性,并遵循和实现为这种人性的恰当发展而作的天道设计。
结论
通过持久的努力和反思,一个人能够把自己转变成更好的人,这个观点已经不仅是中国人而且也是很多其他东亚人所坚持的强烈关注。这种兴趣绝不是儒家所专有的;它也被其他伟大的东亚传统如道家和佛家所共同分享。尽管很明显这不是每一东亚思想家的特征,但是同样明显的是,它是一个被广泛坚持和具有深刻重要性的关注。它还鼓舞了拥有东亚古代血统的许多人的大量有意识的自我形象和潜意识的内在动机。此外,这种关注似乎成为大多数人常识性的道德思考的一部分。无论我们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它,我们都认为伴随着对高尚品质的充分思考和努力,我们能够变得比我们所是的更好。我们确实相信,坚定地去做,并期待这种完善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而且还是为了我们所珍惜的孩子和其他人。正如很久以前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这种设计正是所有伦理探究的真正目标。[注]“因为我们所要寻求的不是想要知道德性是什么,而是为了要变得好。”见《尼各马可伦理学》,1103b25—30。然而,我们大多数人并不系统地思考——如果真有人系统思考的话——如何实现这一点。我们如何才能逐渐变得比我们之所是更好?早期中国人给予这一主题以大量细致的思考,而我们能够从这些反思中不仅学到有关他们的重要实事,而且还能了解我们自身的伦理生活。
将道德自我修养视为道德哲学的一个核心特征和重要主题在当代西方伦理学中争议很大。虽然也有某些重大例外,但今天大多数哲学家倾向于把道德生活看作或者是关于依附于某种道德义务的,或者是关于扩大人类的公共善(the general good of human beings)的。[注]近来这一概括的绝大多数例外在德性伦理学的提倡者中被发现。这种著作的一个最近的参考书目,参见R. Kruschwitz and R. Roberts (eds.), The Virtues: Contemporary Essays on Moral Character, Belmont, CA: Wadsworth, 1987, pp.237-63。 See also P. French, T. Uehling and H. Wettstein (eds.) Ethical Theory: Character and Virtue-Volume XIII, Midwest Studies in Philosophy, South Bend,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8. 近来有两项关于德性伦理学的研究颇有价值,见Michael Slote, From Morality to Virtu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and Rosiland Hursthouse, On Virtue Eth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另可参看两本颇有助益的选集,见Roger Crisp and Michael Slote (eds.), Virtue Eth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and Roger Crisp (ed.), How Should One Live?: Essays on the Virtu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众所周知,这两种进路能受到完全不同且势不两立的行为过程的欢迎。无论这两个通向人所选择的伦理观的进路中的哪一个,遵循义务或扩大效用,他的慎思过程都会从抽象的范畴(例如,一个像扩大公共善这样的给定的规则或原则),下降到实际事务和具体情境。不管怎样,这并不是绝大多数中国思想家的进路(也不是某些西方思想家如亚里士多德关于此点的进路)。他们都倾向于在相反的方向上非常努力地工作,从具体的、典范的实例出发进行推论,直到普遍的规则、模式和践习。他们依靠历史事例和典范性的君子人格而不是抽象的原则。总之,中国思想家较少相信抽象的推理是通达道德真理的最好途径,或是促使另一个人以某种方式行动的最好途径。[注]对于这一主张,即使在先秦思想家当中也有重要的例外。例如杨朱、墨子及其后继者们都展示了更多抽象的道德理论。在他们寻找道德指引的过程中,他们宁愿回顾历史而不是从事于抽象化的工作。
正如埃德蒙德·平科夫斯(Edmund Pincoffs)曾经指出的,由规则或原则引导而通向伦理生活的进路倾向于把精力集中于两难事例,而这些事例是重要的,且揭示出需要考虑的典型。[注]参见Edmund Pincoffs, Quandaries and Virtues: Against Reductionism in Ethics, Lawrence, KS: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1986。然而,他们宁愿将我们的思考集中于伦理学专有情形的选择时刻,以及诸规则之中调和冲突的问题;他们专注于人类生活的时间切片或道德片断。与道德片断通向伦理生活的途径同样重要的是,假如我们单单致力于它,我们就会扭曲我们伦理生活的本质。因为伦理生活更像是一场演奏,而不是任何给定的场景,更像是一个故事,而不是任何单独的行动或处境。构成我们大部分伦理生活的人伦关系和义务承担要求我们自身和我们所重视之物的历时性概念。[注]关于在我们的道德生活概念中需要某种敏感性和历时性扩充观念(a temporally-extended perspective),乔尔·考普曼(Joel Kupperman)曾给出过一个清晰而又富有洞见的说明。参见他的“Character and Ethical Theory,” in Volume XIII, Midwest Studies in Philosophy, pp.115-25。
再考虑一下如下类比,即在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一目标与学习演奏小提琴或获得好的体形之类的目标之间的类比。首先,我们应该承认,这些被看作是合理的和普遍的人类之善,并不是由于某种共同的形式特征,而是因为它们与我们的本性相一致,并能实现我们的本性。在追求这些目标时,将会有一些重要的决断时刻,但是这些目标都不能化约为这样的时刻。它们是这样的一些过程,这种过程要求我们经常参与改变我们的能力、态度和习惯的实践。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获得美好的形体,我们并不需要一种关于健康或运动的非常复杂精致的理论,就像我们需要通过直接地体验它们而经常践行并学习鉴别这样一种生活的好处一样。我们的方法所需要的更多是治疗性的(目标是获得好的结果),而非理论性的(目标是达到正确严格的分析)。这就是孟子倾向于在其道德教诲中运用的那种方法,尤其是在开始的阶段。我已经论证,这就是他在《孟子·梁惠王上》第七章的例子中所做的事,在那里他运用了一种我称之为类比共鸣(analogical resonance)的方法,以便帮助齐宣王识别、领会并扩展他的恻隐之心(heart of compassion)。
如果一个人主要依据两难事例来看待道德生活,那么他就将关注像行动的理由(reasons for action)和可普化(universalizability)之类的问题,因为两个事例是否应该被同等对待以及如何这样做就是在此种观念之内的核心问题。然而,这种两难事例并不是孟子的核心关注。他认为他的首要任务是,让人们认识到基本的道德责任,并践行之,使他们正确地朝向道(theDaoor Way),并始终如一地行走于此道上。所以,在从事于最初使人们识别并承担他们自己的道德自我修养的工作时,他没有理由以某些现代诠释者所建议的方式去关心一致性和可普化的观念。